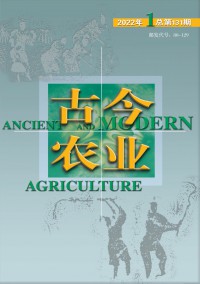宮崎駿動畫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宮崎駿動畫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宮崎駿動畫范文第1篇
縱觀宮崎駿執導的長篇動畫,不難發現,除1992年自傳性質的《紅豬》外,都是以少女為主角。《風之谷》(1984年)的娜烏西卡、《天空之城》(1986年)的希達、《龍貓》(1988年)里的小月和小梅、《魔女宅急便》(1989年)的琪琪、《幽靈公主》(1997年)的珊、《千與千尋》(2001年)的千尋、《哈爾的移動城堡》(2004年)的蘇菲、《懸崖上的金魚公主》(2008年)的波妞、《借東西的小人阿莉埃蒂》(2010年)的阿莉埃蒂,都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們純真、善良、外柔內剛、自立自強,兼具少年性格特征。那么,宮崎駿動畫的少女情結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個人的成長經歷
宮崎駿生于1941年,因二戰戰時疏散,舉家先后遷往宇都宮市和鹿沼市,居住在伯父經營的“宮崎飛機”公司,生活相對富足。幼年的宮崎駿因腸胃得病而身體虛弱,內心自卑,而母親對他十分冷酷,很少給予溫暖和慈愛。“對于藝術家而言,個人經歷往往能左右他的創作沖動,發生在不同時期的精神愉悅或創傷在以后的藝術創作中會不知不覺地表現出來。”在宮崎駿的動畫片里可以隱約瞥見其母的影子。宮崎駿的弟弟回憶說,他看到《天空之城》中的海盜婆婆不禁想起自己的母親,堅強、獨立、彪悍。宮崎駿對母親的情感痛苦而又復雜,他說:“對老媽的感情,一直是我心中難解的疙瘩。”他在《懸崖上的金魚公主》里塑造了一個以母親為原型的老太太,固執己見、尖酸刻薄而內心善良。在這部片子中,他讓一個小男孩宗介去溫暖她的心。在影片將近結尾處,波妞的父親藤本想把波妞和宗介帶回大海,這位老太太擔憂宗介和波妞的安全,緊急中從亭子里踉踉蹌蹌地走出來,竭盡全力接住宗介和波妞,這個大大的擁抱,圓了宮崎駿多年來渴望母親溫暖的夙愿。
宮崎駿的母親可謂是日本戰后堅強女性的代表,活潑、堅韌、嚴格,對宮崎駿的影響很大。在其母的影響下,宮崎駿的內心隱隱根植著女性主義的種子,對女性十分尊重。
日本社會因素
日本史前史曾有延續相當長的母系社會,大化革新之后,日本女性社會地位逐漸衰落。
之后由于外來文化尤其是中國儒家文化的影響,日本原有母系社會逐漸被父系社會取代,女性只能嚴格恪守“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的教條,家庭成了封閉女性的枷鎖。在人們的印象中,日本婦女社會地位低下,對丈夫百依百順,忍辱負重。恩格斯有言,“由于男性在物質生產中,占據主導地位,于是形成了全社會的男權中心主義,女性在家中被貶低奴役。”女性沒有對經濟的支配權,也就失去了掌握自己生活的能力和主動性,導致了女性地位低下。
二戰后, 軍國主義勢力在日本喪失了生存的土壤,由于國門洞開,西方的新思潮大量涌入,促使了日本女性獨立意識的覺醒。宮崎駿具有深切的社會意識和高度的人文關懷,經歷了二戰的他,將對女性主義的思考融入了作品中。
《風之谷》中的女主角娜烏西卡是風之谷的公主,集勇敢、智慧、堅強、善良于一身。當散發著毒瘴氣的菌類森林在不斷擴張,威脅到人們的生存時,娜烏西卡為了醫治父親和大家的病,駕著滑翔翼獨自在腐海里探索、發現,收集孢子培育腐海的植物。當失去幼蟲的王蟲被激怒,成群地向著風之谷沖去時,娜烏西卡將生死置之度外,將幼蟲帶回王蟲群里,免去了風之谷的一場災難。她的責任、擔當與勇敢無不令人動容。在宮崎駿的動畫里,一脈相承的以少女為主角,少男充當配角,在品質、智慧方面,少男稍遜一籌,顛覆了日本傳統的男尊女卑的社會觀念。宮崎駿在創作《魔女宅急便》的解釋中說“經濟上的獨立絕不等同于精神上的獨立,對于現代的女性來說,真正的貧窮已經不僅僅是物質上的缺乏,而應該是精神上的不自由。”對傳統女性形象的改變,也蘊含著宮崎駿的希冀,期待少女自立自強,實現物質和精神的獨立。
日本文化因素
丹納有言:“藝術家本身,連同他所產生的全部作品,都不是孤立的。有一個包括藝術家在內的總體,比藝術家更廣大,就是他所隸屬的同時同地的藝術宗派和藝術家族。”“這個藝術家族本身還包括在一個更廣大的總體之內,就是在它周圍和他趣味一致的社會。”宮崎駿的動畫青睞少女,與日本傳統的文化密不可分。
菊與刀文化
美國學者魯斯·本尼迪克以“菊”與“刀”來形容日本文化的雙重性。恬淡靜美的“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兇狠決絕的“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兩者分別代表著日本文化中柔美和暴力矛盾的兩方面。
這在宮崎駿的動畫里,表現在女性的柔美和尖銳的沖突中。《天空之城》里的海盜和穆斯卡,為爭奪飛行石去往天空之城拉普達展開了激烈的角逐。為解開飛行石的咒語,穆斯卡軟禁了拉普達王族后裔希達,當希達從軍隊飛行船上跌落后,海盜對希達窮追不舍,情節險象環生、扣人心弦。而希達的出現舒緩了影片的節奏,她為海盜們準備食物,和少年巴斯共渡難關,以女性特有的溫柔、細膩對待他人,使人頗感溫馨。希達的柔美和由拉普達展開的爭奪折射著日本“菊與刀”的文化。
櫻花的美學傳統
宮崎駿動畫范文第2篇
>> 解讀宮崎駿動畫電影的美學特色 宮崎駿動畫電影中的女性形象解讀 宮崎駿動畫電影的女性救贖模式解讀 宮崎駿動畫電影中的生態意識解讀 宮崎駿動畫電影分鏡頭之鏡頭運動研究 動畫電影《木蘭》的中西文化解讀 宮崎駿動畫電影作品研究 動畫電影中的美國文化解析 宮崎駿動畫電影分鏡頭之鏡頭景別研究 動畫電影“綠色批評”及“藍色批評”之解讀 動畫大師宮崎駿的動畫電影美學探究 宮崎駿動畫電影中的母性之光 淺論宮崎駿動畫電影的多樣性題材 宮崎駿動畫電影中的人文隱喻 試論宮崎駿動畫電影中的生態敘事 淺析宮崎駿動畫電影的人性主題 宮崎駿動畫電影中的生態主義思想剖析 宮崎駿動畫電影對大學生的影響 宮崎駿動畫電影中的意境美 宮崎駿動畫電影的女性形象分析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
[6] [日]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第二版[M].東京:巖波書店,1982.
[7] [日]藤田香.「m崎作品における女性像[OL].campus.jissen.ac.jp/seibun/contents/etext/gradtheses/2004/Fujita.pdf#search=.
[8] 「となりのトトロの自然Q,高x搿⒐崎駿作品研究所[OL].yk.rim.or.jp/~rst/index.shtml.
[9] 「もののけをiみ解く,高x搿⒐崎駿作品研究所[OL].yk.rim.or.jp/~rst/index.shtml.
宮崎駿動畫范文第3篇
在當今世界的動畫產業中,最具有影響力的當屬美國的迪斯尼動畫和日本動畫。而日本動畫的紛繁種類中,宮崎駿動畫無疑代表著其中最高的成就。與其他帶有濃重商業性的日本動畫不同的是,宮崎駿的動畫體現的不僅僅是能夠創造票房效應的商業價值,還能給觀眾帶來更多的藝術思考和人文關懷。宮崎駿的動畫作品之所以能在“快餐文化”盛行的動畫界取得種種殊榮,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對色彩的成功運用。在表達動畫世界中獨一無二的事物和情感方面,精心的色彩設計可以說是功不可沒,宮崎駿的動畫就很好地體現了這一點。
1 色彩設計對動畫作品結構的表達
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色彩在色相、亮度、飽和度等不同因素的影響下呈現出千變萬化的視覺效果。而在動畫中,色彩作為動畫內容的重要載體,對其設計和運用除了表達對客觀世界的摹寫外,更多地體現著創作者的主觀認識和情緒。在運用色彩來表達動畫作品的結構時,宮崎駿對色彩的獨到理解與運用構成了其作品中唯美畫面的誕生基礎。[1]并在這一基礎上,完成了眾多帶給人悠遠回味的經典動畫作品。
1.1 運用真實色彩表現理想世界
由于動畫作品受表現手段等限制,使其呈現在屏幕中的圖景與現實生活有著明顯的不同。這一特點決定了眾多動畫作品傾向于運用夸張、概括的作畫手法來完成內容的表達,使其與生活相似卻又有所不同。然而宮崎駿的作品卻經常打破這種動畫創作的常規,在色彩設計上力求接近生活中自然光線下的各種事物,細膩地刻畫場景,使畫面效果顯得更加逼真。因此,觀眾在欣賞的過程中,常常會在這些接近通常認識的色彩的引導下,對動畫中的世界產生更大空間的想象,逼真的色彩設計一方面更好的用虛擬來刻畫出真實的場景,給觀眾呈現出絕美的視覺盛宴;另一方面也使觀眾感同身受,拉近了動畫與觀眾的心靈距離。
宮崎駿的動畫作品一直以畫風精致唯美,富有浪漫的想象而著稱,作品中表現的往往是遠離世俗污染的理想世界。所以說,宮崎駿動畫在背景設置上,正是在運用真實感強烈的色彩,來表現生活中無法企及的理想世界,達到了一種亦真亦幻的獨特藝術境界。[2]例如,《幽靈公主》在一開篇,就為我們展現了令人向往的美好圖景。告別故鄉的阿席達卡在遠景鏡頭下與觀眾拉開距離,此時出現在觀眾眼前的是廣袤的丘陵,熱情的金色陽光照耀著勁風吹拂下的草叢,泛起了白色的波紋,天空中充盈著不甚明亮的云朵間或透出五彩的光芒。整個畫面被精心的色彩設計渲染得瑰麗無比,有一種深邃遼遠的空間感。這一畫面的展現,既能與真實景色的形成條件相一致,卻又在想象中加以理想化,因而能夠給觀眾帶來久違的感動,并在心靈深處引起共鳴,增強觀眾對動畫的認同感。
1.2 運用象征色彩渲染背景氣氛
強烈的色彩信號有時會對人們的心理活動起到不同程度的影響。例如,色彩鮮艷明快的圖像較之色彩暗淡的圖像,前者往往會給人造成更強的視覺沖擊。色彩的這一心理作用在漫長的藝術發展史中得到了不斷強化,今天人們對不同色彩形成的看法,已經打下了深深的主觀烙印。回到宮崎駿的動畫中,我們可以發現其作品中的色彩運用與情節發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出現特定的情節變化時,突出的色彩經常被大幅度地渲染和使用,并以此作為情節轉折的預兆。充分利用色彩的象征性的做法,不僅能夠以較為含蓄的方式對事件的進展進行說明,同時也表達了宮崎駿主觀上對作品內容的想法和認識。由于這種富于暗示性的色彩幾乎占據了觀眾所有的視覺空間,因而由色彩導致的心理變化就表現得極為明顯和迅速。舉例來說,宮崎駿在《哈爾的移動城堡》中對紅色的象征性運用,就很有代表性。故事中的女主角蘇菲因為得罪了荒野女巫而被下了詛咒變成老太婆,她從家里逃出時碰巧進入了哈爾的移動城堡,并在戰爭中逐漸對魔法師哈爾產生好感。這部動畫在表現戰爭爆發這一情節時,以馬魯克打開窗戶為轉折,畫面色彩發生了變化,隨著導彈落向地面,充滿象征意味的紅色瞬間覆蓋了天空、建筑和地面,空中也充斥著未完全燃燒的紅色火焰,黑暗與丑惡取代了之前的優美寧靜,告訴觀眾戰爭的來臨并同時營造出緊張的氣氛。[3]在哈爾救回蘇菲后,飛向了已變得黑紅相間的天空,同時又將陷入戰爭的城鎮用刺目的黑紅混合色彩表現出來,說明戰爭已波及很廣的范圍,與近景的硝煙彌漫共同塑造出絕望、壓抑的戰爭景象,成功地運用色彩表達出了反戰的思想和情緒。可以說,在這部動畫作品中,宮崎駿將色彩的象征性發揮得淋漓盡致。
1.3 運用對比色彩塑造人物形象
宮崎駿動畫范文第4篇
關鍵詞: 宮崎駿動畫 女性角色 引導性
1.引言
對于一部成功的商業動畫來說,要吸引大眾的眼光,除了要有符合大眾口味的劇情與線索,符合當代的價值觀和天馬行空的想象力和感動人心的視聽語言之外,還必須有符合大眾理想的生動角色。有很多經典的動畫片在多年以后,其故事情節可能已被遺忘,而觀眾最能記住的往往是“角色”。動畫大師宮崎駿的動畫之所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其角色塑造的成功。
本文以宮崎駿動畫中的幾個經典女性角色來分析動畫角色。
2.宮崎駿動畫中的女性角色
2.1宮崎駿動畫的主題
“救贖”是宮崎駿動畫中最主要的主題,同時也是推動劇情的法寶。幾個經典影片的最,都是主人公完成救贖或自我救贖的過程。娜烏西卡救民、救荷母,最終救敵人、救大家;千尋救父母、救白龍,最終救自己。
2.2宮崎駿動畫中的幾個經典女性角色
宮崎駿的長篇動畫作品多以少女作為主角,而且主角都背負著沉重的宿命,使得整部片子到了末尾,都會讓人感覺到相當悲哀,早期的作品1979年《魯邦三世劇場版:卡里奧斯特羅城》里的公主,還有1984年《風之谷》的女主角娜烏西卡,就是明顯的例子。當然,后來拍攝的1997年《幽靈公主》也是一例。而且作品中的女性角色的結局大多是大團圓,就算是反面角色,在最后也會給予機會改邪歸正。下面介紹幾個經典的女性角色。
《風之谷》的娜烏西卡作為風之谷的公主,善良、勇敢、溫柔,乘著滑翔翼像鳥兒一樣地飛行著。為了阻止多魯美奇亞企圖操縱整個世界而發起的戰爭,為了阻止巨神兵的重新降臨而讓一切又毀滅在于七日之火,為了阻止倍吉特被憎恨所蒙蔽的雙眼而發動的讓人嘆息的復仇,為了從滅亡中拯救風之谷,或者說得更直接,為了救一只年幼的王蟲,娜烏西卡在旋渦中張開自己的懷抱,只為了壓下倍吉特士兵的槍頭。當她猶如傳說中的圣人一般行走在王蟲的黃金草原上時,她那被王蟲鮮血染成藍色的衣裳,神圣,美麗,而憂傷。在這一刻,娜烏西卡重生了,觀眾的心靈在這一刻也重生了。
《風之谷》的庫夏娜在動畫中是身為想要征服世界的多魯美奇亞的三公主。她以邪惡的面目出現,以強有力的手段進入到劇情,占領風之谷并殺了族長,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強硬,瘋狂,欺軟怕硬,甚至有點神經質,進而走向悲劇的結局,最后在娜烏西卡的精神感染下走向新生。
《幽靈公主》的珊,這是一個充滿野性魅力的女性角色。她從小被狼養大,像狼一樣身手敏捷,強大而敏感,個性率直,喜怒哀樂都擺在臉上,對人類充滿了不信任與鄙視,為保護森林而與人類為敵。為了阻止森林的毀滅,平息神靈的怒氣,她化身為狼,竭盡全力地攻擊人類,搶奪麒麟的頭,忍受詛咒的侵略將頭還給麒麟,最終整個森林獲得了重生。
《幽靈公主》的幻姬,是一個受城中百姓愛戴,有優秀領導力與堅定意志的強勢女性。作為女性卻領導著城中的一切,相信人定勝天,為了自己的欲望差點讓邪惡的人鉆了空子,還失去了一只手,在麒麟面前最終悔悟,在巨大的自然力量面前獲得新生。
《千與千尋》的千尋,在宮崎駿的作品中,這是一個最平凡和普通的女主角。這個性格軟弱,笨手笨腳,對任何事情都無精打采的瘦弱女孩,既不漂亮,又沒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面對陌生的環境、冷漠的人事,她只能付出相當的努力,發掘自己內在的潛力,克服各種困境。最終,解救了父母和白龍,并成長成一個堅強的人。
《千與千尋》的湯婆婆,一個貪圖錢財,隨意掌控他人生死,但是對工作認真負責的魔女。她外表強硬,脾氣暴躁,但是對大頭嬰兒卻近乎溺愛,內心充滿脆弱和辛酸。這個看似壞人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千尋的成長。在最后,她放過了千尋的一家,對自我的欲望進行了反思。
2.3性別對宮崎駿的意義
女性性別在宮崎駿的作品中非常突出。她們既非常女性化,又不乏男性的所有優點。但是男性就差很多,經常在為一個錯誤的理念做錯事,甚至是缺乏能力的代名詞。像是《幽靈公主》里面的男主角,他雖然獲得超能力,但是這受到詛咒的能力隨時會奪取他的性命,所以后面他都身為一個調停者,嘗試去彌補自己殺戮這個過錯,放棄超能力以獲取新生。而作品中的終極大反角都是男性,這就是有關男性性別對于宮崎駿的意義:他們不斷在犯錯誤并缺乏糾正的能力。如果《幽靈公主》中有一個人物一直沒有犯罪,那就是公主,一個少女。雖然該片的唯一主角是少年,但中心英雄形象是標題中的幽靈公主,少年只是一個無力的角色,這就是宮崎駿一慣的男女角色的性別對換。
在現實生活中,雖然吉卜力里的女性員工只有男性的一半,但是女員工的休息室卻比男員工的大了兩倍,而且設備比較好。可能這是宮崎駿在表現他對女性主義的支持吧。[4]
3.動畫角色的引導性
3.1宮崎駿動畫中幾個經典女性角色的分析
“成長”是宮崎駿動畫中主角必然的結果,也是推動劇情前進的動力。比如《千與千尋》的千尋,這個沒有任何能力、無精打采的瘦弱小女孩,與現實中的普通女孩一樣。在失去父母的庇護后,她必須獨自面對那陌生的世界,自食其力。剛開始她軟弱膽小,在痛哭之后,慢慢堅強起來,勇敢地面對失控的白龍,請求錢婆婆的原諒,教導大頭嬰兒,最后拯救了父母和白龍,變成了一個堅強,有獨立意志的女孩。動畫讓這是個角色迅速地從一個孩子變成一個懂事的“大人”,而觀眾也跟著千尋一起成長起來,在油屋里洗滌自己的心靈,并相信自己的能力,重拾信心。
“包容”是宮崎駿動畫中女性角色所特有的品格之一,也是調和動畫中那些殘酷現實的調和劑。比如《風之谷》的娜烏西卡,這個能御風飛翔,與其他生物心靈相通,充滿不可思議親和力的女孩。不論是對殺害自己父親,霸占了自己家園的多魯美奇亞,還是對為了復仇而殘害幼王蟲的倍吉特,又或者是對被激怒而摧殘人類世界的王蟲,她都用自己嬌小的身軀包容起來,保護起來,不希望任何人受到傷害,就算犧牲自己。這種大無畏的精神,在她重生的那一刻讓無數觀眾感動,讓無數的人懺悔自己以前所犯下的過錯。面對這個猶如圣人般化生的理想角色,人們除了感動,就是反思和向往。
“懺悔”是宮崎駿動畫中蘊涵的暗示,在觀眾的耳邊輕聲提醒。比如《幽靈公主》的幻姬,這個受人愛戴,擁有強大能力的,本性不壞的女當家,因為欲望的驅使而與山神為敵,大量地砍伐森林,甚至不惜弒神。最后,她發現自己被小人利用,還差點丟失了性命。在麒麟的巨大力量面前認識到自己的愚昧無知,并改過自新,重新獲得新生。幻姬的強大能力就好像人類對統治世界的巨大欲望一樣,由于被欲望蒙蔽了雙眼,失去了很多自己不知道的寶貴事物。幻姬這個角色就在反射著現實的人類,讓觀眾看見自己的愚昧,進而跟幻姬一起在森林神的面前懺悔自己的過錯,尋找一條與自然共存的道路。
“選擇”是宮崎駿動畫中另一個提醒人們注意的內容。比如《風之谷》的娜烏西卡,一開始選擇了復仇,想要殺死多魯美奇亞士兵為報父仇,但是最后她還是選擇了原諒。《幽靈公主》的珊,開始她仇視人類,與山神共存,但是最后她還是選擇與人類共存,監督人類對森林的行為。《千與千尋》的湯婆婆,開始她只是想奴役千尋為她賺錢,要挾她的父母為人質,但是最后她還是聽從大家的勸解,放過了千尋一家。宮崎駿想從這些角色里告訴大家,不論是正義的還是邪惡的,都會面對善惡的交叉口,只要選擇正確,壞人也可以改過自新變成好人。宮崎駿給予觀眾一個機會,一個重新思考,重新認識自己的機會,也是給予人類一個機會。
4.結語
作為一個動畫大師,宮崎駿從來都嚴格地要求自己,時刻提醒自己所肩負的責任,只有優秀的動畫才能幫助孩子健康地成長,而一部優秀的動畫,必然會有設計優秀的角色。人們會從這些角色里吸取和模仿,甚至通過角色來令自己獲得新生,給予自己希望。畢竟這個社會已經畸形膨脹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只能塑造一些有美好人格的角色,通過媒體傳播來慢慢喚醒人們的潛在善良的一面,給青少年樹立良好的榜樣,起一個指引的作用。
參考文獻:
[1]宮崎駿.出發點?1979―1996[M].臺灣:萬里書店,2006.
[2]方田犬彥.日本電影100年[M].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3]九州出版社編委會.世界科幻電影[M].九州出版社,2004.
[4]沈黎暉,尹麗川.宮崎駿的感官世界[M].作家出版社,2004.
[5]薛燕平.世界動畫電影大師[M].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6.
宮崎駿動畫范文第5篇
關鍵詞:宮崎駿;人性;尋找;救贖
宮崎駿作為一代動畫大師,是日本三代漫畫家中承前啟后的精神支柱,他將自己對人類的深層思考和對人性的探索、人文關懷凝聚在作品之中,在表現人與自然矛盾的同時也反映了對人性“善”與“惡”的追根溯源。本文將以《風之谷》和《幽靈公主》為代表分析討論宮崎駿對人性的思考。
一、關于“人性”的思考
自古就有關于人性的探討。人性論有兩種。一種把“人性”視為中性詞,在中國文化中,有“人性”本善論的觀點,以儒家孟子為代表。也有“人性”本惡論的觀點,以儒家荀子為代表;另一種含義是指“人性”作為人的積極本性,指作為人應有的正面品性,比如慈愛、善良,類似于英文中的“humanity”。
“人性”本來就是一個值得探究和爭論的名詞。宮崎駿的電影不喜歡嚴格區分“善”與“惡”,而是讓觀眾主動思考,他的電影更傾向于循循善誘,讓觀眾站在主人公的視角“找尋自我”,把觀眾推到了“善”與“惡”較量的巔峰對決,從而達到人性思考。嚴格上說宮崎駿的作品結局并不悲觀,而且隱喻答案。宮崎駿說:“我并不想拍出一部電影告訴孩子:你應該絕望、逃避。”
二、關于“尋找自我”與“救贖”
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說:“我已經尋找過我自己。”“自己”作為“尋找”的目標,由內向外更加完善地認識自我、解釋自我。宮崎駿人性思考在影片中的體現就是“主人公的自我找尋、自我發現的過程”。故事的主人公是導演人性思考理念的最佳化身,主人公追尋自我遇到的種種挫折正是導演探求“人性”真理時的掙扎所在——究竟是“善”還是“惡”。
“救贖”作為另一個關鍵詞,“救贖”本身源自拉丁語“salus”,它是一個宗教概念。其本意就是做錯事情的人類通過犧牲自己來“贖清”曾經的罪孽,來獲得終極福祉和釋放,通向善和自然的回歸之路。作為主人公追尋自我的結果,故事發展的結局也是導演本人對“人性思考”所隱喻的答案。就像宮崎駿說的:“我希望能夠再次借助具有一定深度的作品拯救人類的靈魂。”
《風之谷》是宮崎駿1984年的作品,也是他平生導演的第一部長篇卡通電影。片中的未來世界與現實中的人類世界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不謀而合。娜烏西卡充當的角色正是現實中的人類,承載著宮崎駿本人的憂慮與哀愁。
當人類憎惡那些有毒的植物,憎惡飄揚著邪惡孢子的腐海,并絞盡腦汁去爭取最后生存的地盤時,娜烏西卡知道這毒源于人類,是人類的污染反噬自然。娜烏西卡偷偷地把樹木和花種在地下室的花園,用沒被污染的水澆灌,這是她對人類罪惡救贖的一小塊凈土和圣地。毒氣在向她的家園蔓延,人類與蟲爭奪著生存領地,甚至人與人之間也是無休止的侵略與征服,人類的野心竟驅使他們喚醒最具攻擊力的怪獸,以自我毀滅的方式去奪取夢想的財富,貪婪與自私讓人類只想到自己眼前的利益,從不考慮自然,重復用暴力去索取,似乎已經臨近生死存亡的邊緣卻渾然不知。
娜烏西卡代表人類心中那僅存的“善”念,是末世的人們所有生存的希望,她苦思著能使末世的人類逃離充滿有害孢子毒氣的方法,但最終一切努力宣告失敗。娜烏西卡以人為贖價的交換,以身為殉終于感動了以動物為代表的神明,從而在絕境中為人類尋找了一條生路。宮崎駿的電影正在用盡心血向人類發出一個危險的信號,希望人類重新審視自己,不要沉迷于自我毀滅的追求而喪失人性,尋找回自然應有的平衡。
《幽靈公主》是宮崎駿1985年的作品,雖然影片主人公為幽靈公主阿桑,但是以阿斯達卡的解除詛咒之旅為主要線索,把自然與人類不可調和的矛盾裸地擺在觀眾眼前,簡單明了但又發人深思。故事中一方立場是達達拉城,深處靜謐森林的鑄鐵之城,女城主幻姬為了人類的利益誓要侵犯神圣的森林并殺死叢林之神——山獸神,另一立場則是阿桑以及森林神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阿桑雖是人類卻對人類厭惡至極,她和莫娜以及乙事主(森林神獸之一)一心想要殺死幻姬,毀滅城池,讓森林重新覆蓋達達拉城。兩種立場,兩種不同的利益集團的對抗正說明了人類與自然界的矛盾癥結所在。
阿斯達卡的出現為解決這個問題帶來一線光明。阿斯達卡前往達達拉城一是為了找尋奇異事件的原因,二是為了解開自身的詛咒。他的旅行也恰恰是一次救贖之旅,就像宮崎駿以往的少年形象一樣,阿斯達卡是善良、勇敢、閃耀著人性光輝的勇士,像脫離某種立場的人類意識的“覺醒”,輾轉于達達拉城與森林之間,既會救城中的每一個無辜的人,也會為拯救森林慷慨赴命。
阿斯達卡作為人類救贖的化身,尋找著解決矛盾的方法,也試圖挖掘人類真善美的一面,他悲天憫人的情懷是導演寄予人類的美好的愿望,也是對人性探究的美好期待。影片結尾,阿斯達卡讓人類意識到殺死山獸神,危害自然等于毀滅自身。只有人與自然共同“活下去”才是生存之道,而掌管生死的山獸神在一夜之間吞噬了一切,又在黎明之際,讓大地重新生機盎然,印證阿斯達卡詛咒的破除,救贖成功,人類的一切將重新開始。
有社會學家認為,人應有兩種生存:一種是處在競爭本能中生存,即為了自己的生存而掠奪破壞其他外物;一種是處在共生調制中的生態生存,即以其他物種共存為自己的生存必要條件。我們現在還處于第一種生存狀態中,面對導演提出的堪憂,人類在人性面前的抉擇行動似乎有些遲緩,就像是人類在找尋自我歸屬的曲折之路,也如同宮崎駿導演本人在電影中種種矛盾的掙扎一般,雖然人性終歸本真,但是人類必定要為自己的行徑救贖并付出高昂的代價。
參考文獻:
1.秦剛,感受宮崎駿,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2.陳旭光,日本電影經典,北京對外經貿出版社
3.楊曉林,論宮崎駿的生態觀和人文困惑,電影評介,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