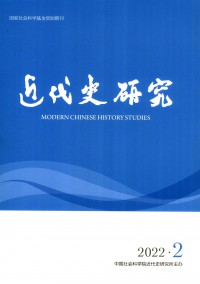近代科學論文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近代科學論文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近代科學論文范文第1篇
論文關鍵詞:知識產權 文化內涵
法律文化是一個國家法律制度的內在邏輯,也是其根基,正是由于法律文化土壤的差異,才會使得法律在各個國家各個時間段顯現出不同的形態。法律事實上是一種思維對現實的抽象,而法律文化決定了這種抽象的方式和導向。知識產權法也不例外,作為對人類智力成果進行保護和規制的工具,知識產權法與思維和主觀聯系更加密切,因此知識產權文化的厘清就顯得更加重要。
一、知識產權文化的內核
法律的構建事實上是一個社會共同意識形成的過程,知識產權法的發展和形成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真正意義上知識產權法大概誕生于18世紀以后,以1709年頒布的《安娜女王法令》為代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封建體制向資本主義、思想封閉向自由平等的多重過渡,以至于對于私權、私有財產、私人智力成果的重視不斷提高。也正是在當時,資本主義思潮興起之時,知識產權文化的內核逐漸構建并完善。
1.個人主義
個人主義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主導思想,其關鍵在于對人的解放,強調“私”的概念。個人主義可以被區分為價值論意義上的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意義上的個人主義,但對于“私”和人的尊重是兩層個人主義都應有的題中之義。隨著個人主義的觀念傳播,人的獨立、平等和互不干預的意識開始深入人心。在這樣的基礎上,以個人為中心,依個人為助力,推演開來的一切物、思想都打上了“私”的烙印,而知識產權的提出就是為了填補缺位的對于個人智力成果的保護。
2.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在18、19世紀的西歐發展到了鼎盛,無論是在經濟、政治、思想領域,自由精神都被作為指導原則貫徹。但事實上在歐洲,自由精神由來已久,絕不僅僅是在近代才逐漸興起。古希臘古羅馬時期,自由權是市民極為重要的一個權利,當時的市民社會事實上就是自由人的共同體。因此,在自然法領域,自由平等觀念源遠流長。自由主義可以分為物質自由和思想自由,而其中的思想自由就被認為是近代知識產權法律構建的靈魂所在,保障以思想為內涵的言論、著作、藝術等等的自由是知識產權法的重要內容。
3.理性主義
理性主義受到了啟蒙思想家們的極力推崇,成為了啟蒙運動的最主流的思潮。它崇尚的是人的理性,人運用理性認知世界,發現規律。這與法律上所強調的理性人的概念不謀而合,法律正是要以理性為標準對人進行約束。理性主義是對極端個人主義和放任自由主義的修正,在法律文化中時一個平衡的因素,而這個因素在知識產權文化領域又顯得格外的重要。知識產權的公共利益導向性和客體的特殊性,決定了其雖然是私權但事實上受到了外在和內在多方面的制約,這就需要以理性主義為指導來進行安排。社會科學論文
二、中國傳統文化對知識產權文化的阻滯
法律移植可以分為內源型和外源型兩種,我國對于西方法律的繼受顯然偏向于后者,帶有明顯的被動和消極的因素。因此,繼受法律如何適應本土文化土壤一直是近代法律界亟需解決的一個問題。我國歷史上長期顯現出知識產權意識的缺位,這種缺位并不僅針對知識產權的完整概念,甚至對于知識產權以上所說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理性主義的內核都一直并非我國歷史上的主流思想。
首先,從思想文化層面來分析我國傳統文化與知識產權文化的隔閡。在我國一直占統治地位的思想理念無外乎儒道佛三家,但這三家中的很多觀點事實上都可能造成對知識產權文化滲透的阻礙。我國傳統文化既有出世的一面,也有入世的一面。在入世方面,我國傳統文化強調的是一種公共主義、集體主義,以家本位代替了西方的個人本位。且中國傳統文化重視道德教化。有益于社會的思想和技術創造等自應推而廣之,不會受到私有的限制。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知識產權這種捍衛個人思想成果的制度顯然沒有適用之余地。而在出世方面,中國傳統文化講究淡薄中庸,所謂“文章不為糧稻謀”,任何追逐私利的行為都是為君子所不齒的。它更加強調人自身和內在的修養,而缺乏外向的求知,因而知識產權所規制的智力成果的流轉等關系也很難做到。
近代科學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烹飪飲食保健;茹毛飲血;自然火;人工取火;遺址;文化遺存;腦量;生食;熟食;植物原料;動物原料;膳食結構;文化特征
一、中國烹飪飲食保健文化的形成期年代
中國烹飪飲食保健文化形成年代,相當于考古學舊石器時代中、晚期以及新石器時代早期之無陶階段,古人類學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時期,距今約20萬年左右至距今1萬年左右。中國烹飪飲食保健文化的形成以晚期智人為主,我國境內發現的晚期智人遺址中,比較重要的有河套人、柳江人、麒麟山人、資陽人、峙峪人和山頂洞人等。
二、中國烹飪飲食保健文化形成期的主要標志是人工取火時期
原始人類人工取火是一項系統工程,它是人類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原始人類人工取火與原始社會經濟形態、原始社會生產力水平、原始人類所使用的生產生活工具以及制造這些工具所采用的技術、原始人類大腦的生理機能、原始人類動物原料熟食等因素息息相關。
1.中國舊石器時代中、晚期原始人類人工取火的社會背景。
(1)先進生產生活工具的出現。舊石器時代中、后期各類遺址出土了大量先進的生產生活工具:水洞溝遺址出土有骨錐、北京山頂洞遺址出土有骨針和鉆孔的獸牙、許家窯遺址出土有骨鏟以及一千多枚石球、河北陽原虎頭梁遺址出土有石矛頭,山西朔縣峙峪和沁水下川遺址出土有石鏃,遼寧海城小孤山遺址出土有骨鏢,柳州白蓮洞遺址出土有骨錐與骨針等等。
(2)狩獵經濟和漁獵經濟走上歷史舞臺。隨著石鏃、石矛、飛石索、弓箭、骨鰾等一大批先進生產工具的發明和使用。狩獵業、漁獵業已經成為社會生產活動中一個獨立的生產部門,采集、狩獵、漁獵已經出現分工。生產效率大大提高,原始社會的狩獵經濟和漁獵經濟得到了突飛猛進地發展,狩獵經濟和漁獵經濟已經成為社會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進入到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2.中國舊石器時代中、晚期原始人類人工取火的條件
(1)技術條件:人工取火所用到的技術有打、鉆、摩、刮等幾種,而在我國舊石器時代中、晚期的文化遺址中,這些功能都清晰可見。北京山頂洞人遺址,據碳十四測定,下窨骨化石年代距今18865,誤差在420年,文化層中的獸骨年代距今10770,誤差在360年。文化遺存有骨針(殘長82毫米,針身微彎,刮磨得很光滑,針眼系用尖狀器挖成的,針眼直徑3.1毫米,最大直徑3.3毫米)1件、磨光的鹿角1件、磨光的斑鹿下頜骨1件、磨鉆穿孔石珠7件、鉆孔小礫石1件、穿孔各種野獸獸牙125枚、磨制骨墜4件、磨制穿孔海蚶殼3件、鉆孔魚骨1件等等[1],這些文物的出土,標志著舊石器時代中、后期,磨制、鉆孔等制造生產工具的先進技術已經廣泛應用到工具的制作之中,人工取火的技術條件已成熟。
(2)智能條件:舊石器時代中、后期原始人類大腦機能的完善為人工取火提供了保障。原始人類大腦的生理機能與腦量的大小有很重要的關系,人類學家吳汝康研究認為:“在前一百多萬年內,人腦的腦量只有600-700毫升,大約一百萬年前后,人類的平均腦量是800-1000毫升,在二十到三十萬年,腦量的平均值與現代人相近,更后的人腦量雖在體積上沒有繼續增大的趨勢,但腦子的形態還在改變,內部結構日趨完善和精致,腦細胞的數量增多,密度加大,新的聯絡在發展。”[2]醫學家嚴健民在論述人腦進化時認為:“所謂人腦組織結構的進化,是指腦量的增加,腦神經元數量的不斷增多。如古猿的腦量只400-650毫升,經漫長的進化,猿人的腦量,早期猿人在800毫升左右,晚期猿人在1200毫升左右。25萬年前的古人,腦量已達到1300毫升左右。有資料反映,‘現代人的腦量多在1100-1500毫升之間,男人比女人稍大’。”[3]說明在大約距今20萬年左右,人類的大腦機能已經非常完善了。
(3)客觀需求條件:熟食是人工取火的核心推動力。舊石器時代早期,原始人類狩獵水平非常低,能夠捕獲獵物機會少之又少,所以用火烹飪動物原料的需求不大。原始人類保存自然火御寒,這種情況幾乎不存在,原始人的體質特征跟社會生產力水平是相適應的,他們體表有一層厚厚的皮毛完全可以抵御嚴寒,實在嚴峻,冬暖夏涼的山洞完全可以居住。需求是決定人工取火成功與否的決定性因素,舊石器時代早期,對火的需求不是很大,原始人類在保存利用自然火的過程中,經常出現斷火是非常可能的。當然,也不排除在某一區域或某一群落有連續存火的現象。但是,在舊石器時代的中、后期情況就大不一樣了,由于狩獵業和漁獵業的訊猛發展,狩獵動物和漁獵水產原料急劇增加,這些動物原料不適于生食,不然危急人體健康,用火烹飪食物的概率大幅度提高。一種既簡單又經濟實用符合歷史潮流的用火方式的出現勢在必然,在人類熟食的召喚下,人工取火便悄無聲息來到原始人類的生產生活中,一個斬新的時代-人工取火的時代誕生了。
3.中國舊石器時代原始人類人工取火的時間。
與我國古史傳說中“燧人氏”和“伏羲氏(庖犧氏、伏犧氏)”時期相當。《韓非子.五蠹》曰:“有圣人作,鉆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燧人氏’。”唐代史學家司馬貞的《補史記.三皇本紀》記載:伏羲氏“結網罟以教佃以漁,故曰宓犧氏,養犧牲以庖廚,故曰庖犧。”《尸子.廣澤》:“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漁,慮犧氏之世,天下多獸,故教民以獵。”《周禮.含文嘉》云:“燧人氏鉆木取火。炮生為熟,令人無腹疾,有異于禽獸。”等等,這些都是對人工取火的權釋。中國原始人類人工取火的年代在距今20萬年左右到距今1萬年左右。相當于考古學舊石器時代的中、晚期以及新石器時代前陶期,古人類學智人時期、新人初期。
三、中國烹飪飲食保健文化形成時期的特征
中國舊石器時代中、后期以及新石器時代早期無陶階段各遺址豐富的文化遺存,充分反映中國烹飪飲食保健文化形成時期的特征。
1.烹飪原料
舊石器時代中、后期,距今大約20萬年左右至距今1萬年左右,烹飪原料仍然以采集為主,但隨著生產力水平提高,狩獵工具大量涌現,不僅可以捕獲中小型的動物,還可以捕獲地面上的豺狼虎豹、空中飛禽和水中的魚類。狩獵經濟和漁獵經濟在原始人類的整個經濟中,所占的份額越來越大。舊石器時代中期許家窯遺址,1976年發現了1059個石球,最大的重達1500克以上,最小的不足100克,利用這些石球可以制作“飛石索”,石球與飛石索對狩獵都有重要的意義[4]。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峙峪的動物化石至少有一百二十匹野馬,八十八頭野驢[5],說明該時期的峙峪人已經以獵取大型動物為重要的生產活動了。新石器時代早期無陶階段,隨著砍伐器、石斧、石錛、磨盤、磨棒等生產工具的出現,農牧業文明的腳步慢慢跨入人類社會的歷史舞臺,原始人類的經濟形態在“攫取性經濟”的基礎上出現了新的經濟形態“生產性經濟”,原始人類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來生產食物,但規模有限。
2.烹飪熱源形態
熱源多元化是火食時期烹飪飲食保健文化的顯著特征。北京人遺址第四文化層距今27-33萬年[6]。第四層為上部灰燼層,由上紫、紅、黃、灰、綠、黑色等雜色灰土組成,內含燒骨、燒石。被燒過的動物骨骼中,有的變形或變成灰色。被燒過的石塊上,有許多裂紋。厚度大約6米。第六文化層有5米厚,也含有燒骨與燒石。中國舊石器時代各時期遺址的文化遺存幾乎都有燒骨、炭灰、燒石、燒土,而且隨著年代的推移,燒骨、燒石、燒土、灰燼層在文化遺存中越來越豐富。燒骨、燒石、燒土、灰燼這些物質都富含熱能,都有烹飪食物的功能。熱源越多,相對應的利用熱源的方式就越多。原始人類在烹飪食物時,除了直接讓烹飪原料與明火直接接觸外,還有更多選擇,除明火外,還可用燒骨、燒石、木炭、灰燼、燒土來加熱食物。明火有很重的煙熏味,燒石、燒骨、灰燼、木炭、燒土已充分燃燒,有充足的能量,但幾乎沒有異味,不僅如此,許多還有特殊的香味,經這些熱源烹飪出來的食物,風味更佳。
3.食物分解工具
分解食物的工具形態小形化、刀刃復雜化、用途專業化,骨刀、骨錐廣泛出現在舊石器時代中、后期的遺址中,研磨器、研磨棒等具有新石器文化標志的工具出現在舊石器時代晚期、中石器時代以及新石器時代早期無陶階段的文化遺址中。器形變小與狩獵業相適應,許家窯遺址是我國小型石器出土最多的遺址,許家窯遺址出土的與食物分解有關系的石器分刮削器、尖狀器、石砧、磨石、石球等。刮削器有七大類,尖狀器有五大類[7],小型刮削器和尖狀器可用于分割野獸的皮肉以及割斷動物的筋肉。石砧的出現,為分解食物提供了固定的場所,使食物分解衛生快捷。磨石可以將分解食物的工具加工得更加鋒利,方便食物的分割。石球既可以用來狩獵,又可以用來砸碎動物骨骼,取食骨髓。舊石器時代晚期和新石器時代早期的無陶階段,原始人類對于動物肉類的利用更加平常,該時期內各遺址的文化遺存中骨器很多。例如骨錐和骨刀,骨錐比起石尖狀器,更容易分解動物的皮肉。骨刀的出現,使食物的分解變得更加容易,骨刀刀刃通常都非常鋒利,在分解食物時的阻力更小。切割后刀口比石刀切割的刀口更清晰、食物形態更美觀,符合人類的審美要求。骨刀可以將食物分解得更小,保障食物均勻受熱、減少有害人體物質產生的概率,方便原始人類的進食。既豐富了烹飪飲食保健文化的內涵,又促進原始人類的文明進步。隨著研磨器、磨棒的出現,食物的形態除經石刀或骨刀分解成塊狀外,還可能將食物加工得更細,比如顆粒狀或粉末狀,無疑對食物的深加工具有積極的意義。火食時期分解食物的工具有:刮削器、尖狀器、砍砸器、砍斫器、石砧、石球、骨錐、骨刀、研磨器、研磨棒等。
4.烹飪方法
烹飪方法產生的客觀因素。熱源多元化、分解食物的工具多元化,決定了烹飪方法的多元化。石器時代的傳熱方式主要是輻射傳熱,其次是傳導傳熱和對流傳熱。烹飪之法有烤、熏、炮、燎、炙、燒、燔、焐。其中烤與炮近似、燎與炙近似、燒與燔近似,東漢人鄭玄認為:“燔,加于火上;炙,貫于火上;炮,裹燒之也”。最古老的烹飪方法應當是焐和燒,原始人類抓住獵物,直接將食物放在炭火上或灰燼中就可以將動物燒熟或焐熟,這是最簡單易行的烹飪法,越簡單越符合原始人的審美觀。在舊石器時代,原始人類有沒有用泥土將食物包裹起來投入炭火中或灰燼中焐熟呢?舊石器時代許多遺址的文化遺存中都有燒土,所以不排除這種可能。居住在巴西中部地區的克林-阿卡洛列印第安人其炊煮食物的方法是,用野香蕉葉把木薯和香蕉包起來,放在燒熱的石塊之間烙烤[8]。倘若果真如此,在舊石器時代烹飪飲食保健文化將翻開新的一頁,食物避開了與熱源的直接接觸,使食物受熱時的溫度更低,經這種工藝烹制出來食物更加安全衛生。烤的工藝是食物置于懸在炭火或灰燼之上,比食物直接放在灰燼中焐熟更衛生。“從人掌握了火的時候起,就開始了動物以及植物食品的燒和烤。最原始的燒和烤是在篝火上、在木炭上、在熱灰上、乃至在被燒熱的石頭上進行。”[9]樣的論述不夠全面。原料烹飪時的存在方式有四種:在熱源體中;在熱源體表面;在火苗中;在火苗或熱源體上方。在熱源體中,烹飪方法稱之為焐;在熱源體表面并且有火苗燃燒,烹飪方法稱之為燒;在熱源物上方的火苗中,烹飪方法稱之為燎;在無火苗的熱源體表面、在熱源體或火苗的上方,沒有煙霧或煙霧較少的,烹飪方法稱之為烤;在無火苗的熱源體表面、在熱源體或火苗的上方,煙霧較大的,烹飪方法稱之為熏。《古史考》:“古者茹毛飲血,燧人氏鉆火,始裹肉而燔之,曰炮。”這里的炮是在原料表面包裹有一層物質,比烤更進了一步。烤的年代遠遠比《古史考》上說的燧人氏時期要早。原始烹飪方法燒與現在烹飪方法燒的內涵完全不一樣,現在燒是指水傳熱。
煮、燒(指具有現代烹飪法意義)、燉、燜、煨、炒、烙等烹飪法的萌芽。我國舊石器時代許多遺址之文化遺存都有燒石、燒骨、燒土,這些富含能量的熱源物、食物以及水常常出現在原始人類的視線中,存在決定意識,將熱源物與食物、水有機地結合起來是完全可能的。原始人類狩獵后,將大型獵物剝皮后,去掉體內骯臟,將燒熱的石塊投入腹腔,再置于燒熱的坑內蓋上泥土加熱成熟[10]。近代美洲大草原印第安人燒煮肉食,是將水和肉放在輔了皮革的坑里或放在用木栓繃緊的形似鍋子的皮革內,然后向皮革內投進燒紅的石塊,直至把肉煮熟[11]。根據民族學資料,我國已有類似的情況:東北鄂倫春族淬瀹肉:將肉與水放入刳成空心的木頭容器中,不停地投入小燒石,以致肉熟。鄂倫春族吊燒:獵獲的獸胃洗凈,放進水和肉塊,吊在火上烤,胃焦肉熟。云南的傣族,殺死牛后,在地上挖一個大坑,剝下的牛皮墊于坑中,盛上水放入牛肉,投入燒紅的石塊,直至肉熟。食物的加熱方法是以水傳熱來完成的,這是煮、燉、燜、煨等烹飪方法的前奏。谷類、堅果之類的小形體原料,采用石上燔谷方式進行烹飪,《禮記.禮運》:“中古未有釜甑,釋米捋肉,加于燒石之上而食之耳。”此段話語隱藏了兩種烹飪法―炒和烙。將石板用火燒至很高的溫度,小形體整粒食物置于石板上炒熟,這是烹飪方法炒的原生形態。我國舊石器時代晚期和新石器時代早期前陶時期的文化遺址有研磨器、研磨棒出土,可用之將谷米研細,與水和漿,入燒石上烙熟,把食物經放在熾熱的石板上使之成熟,烹飪方法為
烙。根據民放學資料:獨龍族和納西族人用一塊圓形石板架在火塘上,把和好的餅漿倒在燒燙的石材上烙熟。的門巴族和珞巴族在燒熱的石上烙餅。它們的文化基因可能就來自于舊石器時代晚期、中石器時代或新石器時代無陶時期。
參考文獻:
[1]《周口店山頂洞之文化》 作者張汝玖、胡曉春編《裴文中科學論文集》[C]科學出版社 1990年出版P123-133
[2]吳汝康著《人類發展史》[M]北京科技出版社1978年P209
[3]嚴健民著《遠古中國醫學史》[M]中醫古籍出版社2006年P5
[4]《許家窯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址1976年發掘報告》作者賈蘭坡《賈蘭坡舊石器時代考古論文選》[C]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P154
[5]《山西峙峪舊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作者賈蘭坡《賈蘭坡舊石器時代考古論文選》[C]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P175
[6]宋兆麟、黎家芳、杜耀西著《中國原始社會史》[M]文物出版社1983年P31
[7]《陽高許家窯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址》作者賈蘭坡《賈蘭坡舊石器時代考古論文選》[C]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P139-141
[8]劉達成等編譯《當代原始部落漫游》[M],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P234
[9]斯科文著 張錫彤譯 張廣達校《原始文化史綱》[M]人民出版社出版1955 P110
近代科學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學/科學知識社會學
【正文】
傳統的科學哲學主要是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研究科學的,并且取得了累累碩果。但是,僅僅從這個角度來研究科學顯然是不夠的。科學也是一種社會系統或社會體制,并且科學知識本身同社會條件也的確存在著某種聯系,因此,還需要對科學進行社會學的研究。近些年來,隨著元科學研究的不斷進展,人們越來越發現傳統的科學哲學的定位存在著很大的局限性,以致想要在原有的基礎上作深入研究,感到困難重重。而另一方面,由于科學社會學與科學哲學相比起步較晚,加上其獨特的研究視角和誘人的應用前景,使得科學社會學研究正方興未艾。尤其是隨著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興起,大有從科學哲學走向科學社會學的趨勢。本文對元科學研究的這一發展趨向作了評析,認為:(1 )傳統的科學哲學的定位最突出的局限性之一,在于難以將社會歷史的觀點貫徹到底;(2)科學社會學的研究不僅有助于克服科學哲學的這種局限性, 從而促進其深入發展,而且也為整個元科學的研究開辟了廣闊的前景; (3)科學社會學(特別是科學知識社會學)也有其自身難以克服的局限性,并不能取代科學哲學對科學內容本身作深層的研究。
一、傳統的科學哲學的定位及其局限性
盡管關于什么是科學哲學這個問題存在著不同的意見,但是,一般說來,人們基本上還是傾向于將傳統的科學哲學定位于作為一級學科的哲學下面的一門二級學科。更確切地說,科學哲學的研究范圍基本上局限在認識論或方法論的領域內,并且把它所研究的認識論或方法論幾乎等同于“科學的邏輯”。這在約翰·洛西所寫的《科學哲學歷史導論》一書中體現得最為明顯。他將《科學哲學歷史導論》寫成了“科學方法觀點發展的歷史概要”。在他看來, 科學哲學主要探索下列問題:(1)哪些特征把科學研究與其他類型的研究區分開?(2 )科學家在研究自然時應遵循哪些程序?(3)正確的科學解釋必須滿足哪些條件? (4)科學定律和原理的認識地位是什么?因此, 科學哲學要比科學本身的實踐站得更高:科學從事的是對事實進行解釋,而科學哲學的主題是研究各門科學的程序和結構以及科學解釋的邏輯。([1],p.2)值得注意的是,約翰·洛西將邏輯實證主義和波普學派及其以前的科學哲學看作是“正統的”科學哲學,而將庫恩、拉卡托斯、勞丹、費耶阿本德等歷史主義的科學哲學看作是“非正統的”科學哲學。
約翰·洛西所謂的“正統的”科學哲學具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靜態地、非歷史地研究科學。似乎科學存在著一種超歷史的結構或方法論規則,而科學哲學可以站在科學之上,運用超歷史的元科學概念,揭示科學的程序、結構或科學解釋的邏輯。二是主張對科學進行純粹的理性重建,完全排除各種非理性因素。他們將科學認識論或方法論加以高度邏輯化和形式化,從而將邏輯理性推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而對各種非理性因素的考慮則到了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程度。三是純粹局限在認識論范圍內研究科學,完全忽視了社會學的因素,似乎科學只是個別科學家從事的工作,而不是一項集體的或社會的事業。
應當肯定,傳統的科學哲學關于科學理論結構的分析,關于科學方法的合理重建以及對若干元科學概念的邏輯分析等等,對于推進和深化科學認識論乃至整個哲學的研究,無疑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尤其是由于他們對于分析、還原和邏輯方法的強調和運用,使得科學哲學幾乎成了一門與科學研究相類似的相當嚴格和精密的學科。他們發起的“科學的哲學”運動盡管后來遭到失敗,但的確曾經將科學哲學帶進了最輝煌的時期,并且深刻地影響著哲學的發展。因此,從歷史的觀點看,傳統的科學哲學如此定位是有積極意義的,無論是對于推進哲學還是科學研究來說,也許都是必要的并且是不可逾越的。
然而,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人們越來越發現傳統的科學哲學定位的局限性和偏頗性;首先,雖然科學哲學的研究對象是自然科學,但是它本身卻應當屬于人文學科。因此,它與其它人文學科一樣,若是按照傳統的科學哲學家的理想,完全排除社會、歷史和心理等因素,純粹用邏輯和理性將科學哲學建構成類似物理學那樣的精密學科,顯然是不可能的。其次,僅僅從靜態的、理性的和認識的角度來研究科學,是遠遠不夠的。特別是,這種角度嚴重地忽視了科學在本質上是社會的這一重要特征:科學家在科學活動中往往并非單獨地從事研究,而是需要在某個科學共同體中從事研究;科學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社會(公共)性的事業,其中個人的行為要受到社會目標和規范的強烈影響;還有任何基礎性的科學研究往往不能脫離社會對技術上的要求等等。
如何克服傳統的科學哲學的局限性和偏頗性,將認識因素和社會因素密切地聯系起來,更進一步說,如何將科學哲學與科學社會學有機地聯系起來,在這方面,應當說,托馬斯·庫恩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庫恩提出的兩個著名的概念,即范式概念和科學共同體概念,可以說既是科學哲學又是科學社會學的重要概念。庫恩認為,科學哲學的主要問題是解釋科學的動態過程,并且首先要弄清楚科學究竟是怎樣發展的。在他看來,這種“解釋歸根到底必然是心理學或社會學的。就是說,必須描述一種價值體系,一種意識形態,同時也必須分析傳遞和加強這個體系的體制。知道科學家重視什么,我們才有希望了解他們將承擔些什么問題,在發生沖突的特殊條件下又將選擇什么理論。”([2],p.286)由此可見,盡管庫恩對科學進步的解釋帶有嚴重的相對主義色彩,但是,庫恩對于糾正傳統的科學哲學片面強調“科學的邏輯”的定位,溝通科學哲學與科學社會學、科學史和科學心理學的聯系,開辟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相結合的研究思路,其貢獻是巨大的。
自庫恩提出科學革命的理論以后,科學哲學逐漸經歷了從邏輯主義向歷史主義的轉變。歷史主義者們大大超越了傳統的科學哲學作為“科學的邏輯”的定位,更多地關注科學的實際發展,試圖建立歷史的模型,因而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歷史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等領域。他們主張一種與邏輯主義完全不同的方法論,即歷史方法論。這種方法論在本質上是辯證的,要比邏輯主義者所主張的“科學的邏輯”寬闊得多。
然而,盡管歷史主義者竭力倡導一種歷史方法論,但從整體上來說,他們的哲學仍然沒有擺脫分析哲學的基本框架,邏輯主義的色彩依然很濃。也就是說,歷史主義者最終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傳統的科學哲學的定位并克服其局限性,將社會歷史的觀點貫徹到底。于是,科學哲學依然困難重重。其中,最為典型的是關于科學進步的問題。本來,如果真正從這社會歷史的觀點看,科學進步是不言而喻的。因為首先,社會生產力在不斷提高,人們可以利用越來越先進的物質手段從事科學;其次,人們可利用的知識和信息也在不斷地豐富和增長;還有,每個時代每個社會的人的智力水平和文化素質也在不斷地提高和發展。但是,要想按照原有的科學哲學的定位,在分析哲學的框架內,用純粹邏輯的觀點來解決,科學進步問題卻變得極為艱難。正是由于這個緣故,科學哲學家們至今還難以擺脫這樣一種兩難困境:要么堅持某種超越歷史的普遍有效的科學進步標準來說明科學的進步性;要么接受庫恩的觀點即范式之間是不可通約的,因而否認了科學的進步性。由此可見,要使科學哲學擺脫這種困境,就應當真正突破原有的定位和框架,進一步開拓視野,積極吸取其他元科學研究成果,特別是科學社會學的研究成果,使科學哲學與科學社會學等學科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推動科學哲學乃至整個元科學研究的深入發展。
二、科學社會學的新視野
科學社會學與科學哲學對科學的研究視角有所不同。它們兩者的根本區別在于,科學哲學主要地將科學看作是一種認識,往往使用認識論的范疇(如“理論”、“因果性”、“實驗”、“假說”等等),對科學側重于進行方法論或認識論以及科學發展的內在邏輯的研究。然而,以默頓為代表的科學社會學在本質上將科學看作是一種社會體制,將科學的發展過程看作是科學在社會中逐漸體制化的過程。于是,科學社會學往往使用社會學的范疇(如“體制”、“規范”、“分層”、“權威”等等),對科學重點進行社會關系、社會結構和社會環境等方面的研究。具體地說,科學社會學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為元科學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
第一,與其他社會體制(例如政府、教育等)一樣,科學也是一種社會體制。“科學可以被樸素地表達成由許多科學家個人組成的共同體:他們觀察自然界,互相討論他們的發現并且把結果記錄在檔案中”,“在可能達到的最廣泛的范圍里,致力于建立觀點的合理的一致性。”([3],pp.17—18)科學作為一個社會系統,它的正常運行是通過許多公共的或社會的形式來實現的。例如,“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公共機構,如大學里的科系、學術社團及科學雜志,它們致力于各種各樣的公共活動,象科學教育,發表科學論文,對有爭議的科學問題展開辯論,或者對于著名的發現授予正式的獎賞。在更抽象的形式上,我們注意到了公共性影響,如教育課程的設置、研究傳統及研究綱領。每一個科學家都被要求去扮演各種各樣的公共角色,如研究生、研究管理人員或知名科學權威,并且受到公共行為規范的制約,如‘普遍性’或‘無私利性’等。”([3],p.13 )科學社會學(至少是“內部的”科學社會學)將這些公共建制、活動、影響、角色、規范等等看作是“科學的基本要素”,強調“如果不去探求科學家在他們的科學研究過程中,彼此是如何發生聯系的,那么就無法理解科學理論的地位,無法理解這些理論當初是怎樣被設想出來的。”([3],p.13 )這就是所謂“內部的”科學社會學的基本思想和出發點。概括地講,“內部的”科學社會學,按照齊曼的觀點,是以科學發現為背景,研究的是科學這種社會體制的內部結構、社會關系及其運行規律。
顯然,將科學看作是一種社會體制的研究綱領大大拓展了元科學的研究:首先,拓展了科學哲學和認識論的研究。盡管歷史主義的科學哲學也已經觸及到用社會歷史的觀點來看科學,但是,科學哲學在這方面的研究僅僅是綱要性的,并且可以想象在科學哲學的定位和框架下面是很難能將社會歷史的觀點貫徹到底的,充其量只是在大量歷史案例中去尋找科學發展的邏輯。相比之下,科學社會學不僅使這方面的研究成為可能,而且切切實實地推進了這方面研究。例如,科學哲學中提到的“范式”、“科學共同體”等等概念,在科學社會學那里已經不再是一種智力抽象,而轉變成為切實的研究對象。至于科學哲學中非常突出的“客觀性”、“真理性”和“合理性”等問題,科學社會學則用社會學的術語重新加以闡述。約翰·齊曼甚至提出了“社會學的認識論”的概念。在他看來,“社會學的觀點不僅闡明了科學的‘方法’;它也說明了科學認識論的基本問題。”([3],p.159 )他指出, “代替強調科學的認識方面的哲學透視,也許我們從一開始就應該采取社會學的觀點。”([3],p.149 )這些話可能有些夸張,但是, 對科學內部作社會學的研究對于科學哲學來說至少是一種補充和拓展。
其次,開辟了許多關于元科學的新的研究課題及其研究方法。例如,關于科學共同體的研究,關于無形學院的研究,關于科學交流體系的研究,關于科學獎勵制度的研究,關于科學家行為模式的研究,關于科學中的社會分層的研究,關于社會中的科學家的角色研究和關于科學評價的體制化研究等等,所有這些課題的研究,對于理解科學內部實際的社會運作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而且還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二,更重要的是將科學這種社會體制放到更廣闊的社會背景中來探討,深入研究科學、技術和社會三者之間的關系,研究科學對社會的影響,社會對科學的控制以及科學發展的社會條件和社會后果等等。科學社會學并不僅僅局限于從“內部”考察科學,相反,它更強調科學“這種社會建制植根于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完成一定的社會功能,并且和其他體制一樣,和法律、宗教、政治權力等等聯系在一起。”([13],p.163)因此,一方面,科學能夠對社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科學通過技術以巨大的力量導致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以及人們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等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發生巨大的變化。當然,科學的發展既能強有力地推動經濟的增長和社會的進步,同時也有可能由于不恰當的應用而給社會帶來諸多負面影響。另一方面,科學又受到社會的巨大影響、制約或控制。從經濟的角度看,科學技術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對技術上的需求,社會可以在人力、物力和財力上影響、制約或控制科學技術的發展及其方向;從政治的角度看,國家和政府需要借助科學技術來實現其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文化的和外交的目的;從文化的角度看,任何科學技術的發展都無法脫離它們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并受到這種文化環境的制約。作用于科學的巨大的社會力量,不僅可以將科學技術看作是一種工具,使它服從于各種社會需要,而且也可以從根本上改變科學的體制及其自身的活動方式。當然,社會對科學的影響、制約或控制也會有雙重效應:一是促進科學技術健康發展,從而推動社會的進步;二是也有可能破壞科學、技術和社會三者之間的良性互動,從而給科學與社會帶來負面影響。
毫無疑問,將科學這種社會體制放到更廣闊的社會背景中來考察,深入研究科學、技術和社會三者之間的社會互動關系,對于元科學研究來說,帶有革命性的變化。它的意義在于:
首先,突破了傳統的元科學研究的思維框架。一般說來,傳統的元科學研究(包括科學哲學、科學心理學、科學史、甚至“內部的”科學社會學)基本上都局限在科學本身的活動范圍內進行研究。這種研究方式的缺陷在于,它忽視了十分重要的社會因素,那就是科學正在改變著整個社會,與此同時,社會也在改變著科學。用約翰·齊曼的話來說,“作用于科學的巨大的社會力量,正在使科學自身內部的活動方式變得面目全非,并且這種力量正在向著科學哲學與心理學的核心滲透:而人們常常不能認識到這種情況。”([3],p.11 )也就是說,如果切斷科學與整個社會的聯系,即將社會對科學的影響忽略不計,而單純地研究科學本身,則多少帶有某種程度的盲目性。
其次,為多角度全方位地研究科學提供了可能性,傳統的元科學研究只是從“內部”研究科學,其視野顯然是極為有限的,充其量只是將科學看作一種學術活動,而科學的目的是“為科學而科學”。但是,僅僅從這個角度來理解科學是遠遠不夠的。的確,科學是一種條理化的知識體系;它采用了獨特的方法;它具有獨特的社會結構;它是具有特殊研究才能的人們做出的發現。然而,它更是一種與整個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體制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社會體制;它是一種實現各種社會目標的手段和工具;“它需要物質設備;它是教育的主題;它是文化的資源;它需要被管理;它是人類事務中重要的因素。我們的科學‘模型’,必須把這些相互差異、有時是相互矛盾的方面聯系起來,并且統一在一起。”([3],p.7)而要做到這一點,只有將科學、技術和社會三者聯系起來加以綜合研究,才有可能。
再次,開辟了元科學研究從理論走向現實的更廣闊的道路。由于對科學所賴以生存的社會環境因素的忽視,一般說來,傳統的元科學研究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理論脫離現實的傾向,它們所建立的各種科學模型充其量只是科學作為學術活動的模型,離科學作為社會體制的現實情況有很大距離。相比之下,科學、技術與社會相互關系的研究更著重于關注科學的社會現實:究竟科學實際上是如何通過技術影響社會的?社會又是如何實際地影響、制約或控制科學技術的發展的?作為一種社會體制的科學在現實社會中的現狀是什么?它將如何發展?科學對于現實社會的影響又是什么?有什么正面或負面影響?應當采取什么樣的對策促進科學、技術與社會三者之間良性互動,既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又推動整個社會的全面進步?所有這些問題都是科學社會學的理論問題,也是它所應當解決的現實問題。可以說,科學社會學的研究為著重運作的關于科學技術的政策性研究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三、科學知識社會學能否取代科學哲學
很明顯,將科學作為一種社會體制來研究的科學社會學同將科學作為一種認識活動來研究的科學哲學兩者不僅不是沖突的,而且起著相互補充的作用。然而,本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興起的科學知識社會學卻對科學哲學提出了嚴重的挑戰。這種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學科定位同原有的科學社會學大為不同,它脫離了以默頓為代表的科學社會學的研究傳統,并不是從社會體制這個角度來研究科學,而是強調要對科學知識本身進行考察,直接研究科學知識的內容與社會因素的關系。這便形成了科學知識社會學與科學哲學兩者之間的互相競爭關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愛丁堡學派代表人物提出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強綱領蘊含著這樣一種傾向,那就是科學知識社會學能夠而且應當取代科學哲學,來研究和解釋科學知識的內容和性質。這項“強綱領”指出,科學知識本身并不存在絕對的或超驗的特性,也不存在諸如合理性、有效性、真理性或客觀性這樣的特殊本質。所有知識,不管是經驗科學中的知識還是數學中的知識,都應當徹底地被當作社會學的研究材料來處理。([5],p.3)這無疑是在宣告以研究科學合理性、有效性、真理性或客觀性為內容的科學哲學應當終結,關于科學知識的一切應當讓位于科學知識社會學來研究。我們認為,這種見解不僅是相當偏頗的,而且也是難以經得起推敲的。
首先,科學知識社會學對科學知識所作的研究充其量只是一個側面,它根本無法代替科學哲學對科學知識本身作正面的認識論的研究。我們不妨可以看一看戴維·布盧爾在他的《知識和社會建構》一書中對“知識社會學的強綱領”的闡述。布盧爾說:“社會學家所關注的知識,包括科學知識,純粹是作為一種自然現象來看待的。”([5],p.5)他認為,科學知識社會學應當遵循以下四條原則:①知識社會學是研究原因的,即關注那些導致信念或知識狀態形成的條件。當然,除了社會原因以外,還存在著其它類型的原因,它們與社會原因一起促使信念形成;②知識社會學公平同等地對待真和假、合理或不合理、成功或失敗。這些對立的雙方都需要得到解釋;③知識社會學的解釋風格是對稱的。例如,用同樣類型的原因來解釋正確的信念和不正確的信念;④知識社會學是反身性的,從原則上說,它的解釋模式應當適用于社會學本身,否則社會學將是對它自己的理論的反駁。布盧爾將原因、公平、對稱和反身性這四條原則稱之為是知識社會學的強綱領的定義。([5],p.7 )由此可見, 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的是科學知識與社會環境條件以及社會結構之間的關系,并且主要研究的是產生科學知識的社會原因或社會條件。也就是說,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研究重點并不是科學知識本身。它甚至根本不關心科學知識的真或假、合理或不合理、成功或不成功等等這樣一些對科學知識來說帶有根本性的問題,而只是采取一種自然主義的立場,將所有科學知識都一味地同等地看作為“結果”;它將研究重點放到了科學知識的外部,放在社會條件或原因上面,即側重于研究是什么樣的外部的社會條件或原因導致什么樣的科學知識的產生。當然,科學知識社會學從這種角度來研究科學知識不能說沒有新意,也許是頗有意義的,但是,應當承認這種角度僅僅只是從一個側面來研究科學知識,而且過多地強調這個側面顯然是不可取的,因為其一,正如約翰·齊曼所批評指出的,“固執的社會學家可能大大地過高估計了社會利益的影響和其它科學以外的考慮”,從而“鼓勵從在科學中起片面作用的一系列因素出發的研究,并使之合法化,因而得出非常可疑的結論”;([3],p.155)其二,它大大低估甚至否定了科學知識本身發展的內在邏輯等認識因素,而事實上這也是科學知識產生的先決條件之一。毫無疑問,離開了人的認識,社會因素的作用再大,科學知識也無從產生。
其次,科學知識社會學本身也存在著難以克服的困難和局限性。勞丹認為,“任何認識社會學的解釋至少必須給出存在于某個思想家Y 的某種信念X與Y的社會狀況Z之間的因果關系。 (如果社會學的解釋具有‘科學的’意義的話)這就要求助于一條普遍的定律,此定律表明,處于Z類狀況之中的所有(或大多數的)信仰者都會采取X類信念”。([6],p.217)但是,在勞丹看來,盡管作了幾十年的研究工作,當代科學知識社會學其解釋還是“過于粗糙,遠遠達不到起碼的確切性要求。” ([6],p.218 )除了象勞丹這樣的科學哲學家以外,還有象科學社會學家默頓和對知識社會學最有建樹的社會學家之一卡爾·曼海姆都對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前景表示懷疑。默頓認為,“特定的發現和發明屬于內部科學史的范圍,并且大量地獨立于非純科學的因素。”( [6], p.220)而曼海姆則斷定說:“數學和自然科學”中的歷史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于內在的因素。”([6],p.220)一般說來,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困難及其局限性可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其一,社會條件對科學知識的產生和發展的影響往往是間接的,而不是直接的。也就是說,在特定的社會條件和特定的科學發現或發明之間不一定存在著必然的因果關系。其二,社會條件對科學知識的產生和發展的影響往往從宏觀上講比較說得通,而從微觀上分析比較困難。例如,我們可以從當時的工場手工業時期的經濟和技術上的需要來說明為什么在近代自然科學的各學科中,發展較快、成熟較早的是經典力學。但是,我們很難說明經典力學中的每一個定律的社會根源是什么。其三,科學知識社會學也許比較適合于那些原始的或經驗性很強的科學知識,但很難研究近現代那些理論性或邏輯性較強的科學知識。因為前者離社會現實比較近,或許同社會條件有某種直接的關系;而后者離社會現實比較遠并且已經高度數學化。更進一步說,科學知識社會學在科學知識可以用理性解釋的范圍內似乎沒有多大的用武之地。勞丹甚至明確指出,科學知識社會學只能限定“在不合理性假定的框架之內工作”,才有“廣闊的天地。 ” ([6], p.222 )當然,勞丹對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范圍的限定未免有些絕對,但是,他的確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科學知識社會學所固有的局限性。
最后,用科學知識社會學來代替科學哲學的后果也是不可取的。顯然,用科學知識社會學代替科學哲學至少有兩個嚴重的后果:其一,使得對科學知識的研究趨于平面化和表面化。因為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將科學知識僅僅看作是一種自然現象,所以,他們不希望、也不可能對科學知識作比“自然現象”更深層次的研究。他們將科學的合理性、有效性、真理性或客觀性問題擱置一邊的結果是,將科學知識等同于文學知識、道德知識、宗教知識或別的什么知識,使得科學知識完全失去其自身的有別于其它文化知識的特點。這樣一來,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們在否定科學哲學研究的同時,實質上也否定了他們自己所作的研究,因為既然科學知識同其它別的文化知識沒有什么根本區別,那么,科學知識社會學本身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其二,進一步為認識論和文化的相對主義敞開大門。事實上,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并不是拒斥所有的哲學觀點。確切地講,他們認為,默頓學派的局限與不足就是與實證主義哲學的聯系,而他們的目的就是在新的哲學觀點的支配下,為科學社會學轉向科學知識內容的研究作出貢獻;并且認為他們的研究可以論證這些新的哲學觀點。 ([7],p.228 )而這些所謂的新的哲學觀點最主要的傾向之一,那就是認識論和文化的相對主義。正如布盧爾所明確承認的,“知識社會學的強綱領依賴于一種相對主義。它采取了可以稱之為‘方法論的相對主義’的立場。這種立場體現在早先提出的對稱性和反身性兩條原則之中。所有的信念(不管它們得到如何評價)都將以同樣普遍的方式予以解釋。” ([5],p.158 )反之,若要用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結論來論證哲學觀點,那么勢必強化相對主義的觀點:首先,科學哲學中所探討的“客觀性”和“真理性”的概念,在科學知識社會學家看來,其真實的含義只不過是“主體間性”,即“許多人的意見一致”。這就是認識論的相對主義觀點。其次,正如齊曼指出的,“知識社會學原則的嚴格應用看來必將導致這樣一個不可避免的結論:科學僅僅是在理智領域中許多相互競爭的世界圖像當中的一種,而且它并不優越于一個社會團體能夠贊同的任何其它的系統方案,例如,贊德人的著名的巫術信念。”([4],pp.119—120)這就是文化相對主義的觀點。由此可見,如果說費耶阿本德從科學史的個別案例研究中得出認識論和文化相對主義的結論,從而宣告科學哲學的終結的話,那么,這些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們則試圖以更一般的經驗研究來強化費耶阿本德的觀點。可是,他們竟沒有想到,科學哲學的終結同樣也意味著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終結!
參考文獻
〔1〕 約翰·洛西:《科學哲學歷史導論》,邱仁宗等譯, 華中工學院出版社,1982年。
〔2〕 托馬斯·S·庫恩:《必要的張力》,紀樹立等譯,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
〔3〕 約翰·齊曼:《元科學導論》, 劉@①jùn@①jùn等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4〕
John Ziman, Reliable Knowledg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1978.
〔5〕 David Bloor, Knowledge and Social Lmagery, Th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6〕
Larry Laudan, Progress and Its Problem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