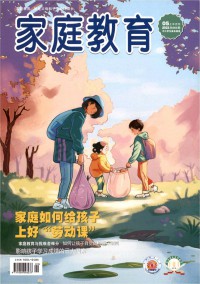我善養(yǎng)吾浩然之氣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我善養(yǎng)吾浩然之氣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fā)現(xiàn)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我善養(yǎng)吾浩然之氣范文第1篇
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yǎng)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謙于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氣”一詞《說文解字》解釋為:“云氣也,象形”。指的是天地之間一種無形的能量變化。作為能量的氣流動于自然之間萬化出風(fēng)雨雷電,四季更替,充盈于人的身體生出仁義禮智、愛恨情仇。那么什么是浩然之氣,如何培養(yǎng)浩然之氣?孟子講:“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剛至大,以直養(yǎng)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2)《孟子·公孫丑上》
首先,浩然之氣很難言說,它至大沒有界限,至剛不屈不撓。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yǎng)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然而餒,卻甚小也。”(《牡丹亭·言懷》)浩然之氣是人身上的能量,如果被人的私欲蒙蔽,就會空虛、沒小。所以孟子講“以直養(yǎng)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在這里,“直養(yǎng)”,趙岐注《孟子》說:“正直之氣”,“養(yǎng)之以義”。至剛至大的正氣,以義進(jìn)行培養(yǎng),義是孟子四端之一。因此養(yǎng)氣就是培養(yǎng)心中固有之義。
其次,“無害”。人心固有的義乃天地之自然,無需外界干涉。孟子之后舉出堰苗助長的例子,其喻意也在于此。養(yǎng)氣不可像“不耘苗者”那樣以為沒有益處而舍棄,也不可像“堰苗者”“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因此當(dāng)“氣”產(chǎn)生時不要強(qiáng)行阻止也無需刻意促進(jìn),而是自然而然地由內(nèi)發(fā)出,見于面龐,神氣溫潤,流于四體,充盈全身,行動自然,最終顯而易見。
再次,孟子又云“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浩然之氣盈于身,必須配合“義”與“道”。義是象形字,原字是上邊一個羊,下邊一個拿著戈的人。關(guān)于羊有兩種解釋,一者認(rèn)為,從羊的字形結(jié)構(gòu)來看,無論上面的兩點(diǎn)還是中間部分都是左右對稱,因此羊意味著公平。二者認(rèn)為,養(yǎng)在古代是供奉于祭祀的物品因而象征著信仰。除此之外,從結(jié)構(gòu)來看,“羲”一一羊下邊手拿兵器的我,其代表著為了公平或者信仰而勇于戰(zhàn)斗的人。所謂:“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義者也。”fll《孟子·告子上》由此可見,“義”是屹立于天地間手持兵戈誓死捍衛(wèi)心中信仰(四端)的勇士。再者,“道”是天理之自然。對于浩然之氣來說,道就是孟子所說的“良能”與“良知”。良能是指無需學(xué)習(xí)便可行為的先天能力,良知是指無需思考便可通曉的先天知識。良能與良知構(gòu)成了人固有的“完滿”一一“善”。因此孟子認(rèn)為養(yǎng)氣必配義與道,并使人的行為勇敢而無所竭慮。反之,沒有浩然之氣充于身,只憑借一時沖動行魯夫之勇,則與道義無關(guān),非天理之自然。
最后,孟子認(rèn)為培養(yǎng)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謙于心,則餒矣。”集義,朱熹認(rèn)為:“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于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營之襲。”《四書章句集注》意思是,浩然之氣乃時時事事出于義,行于體,心中無所愧作,從而氣自然發(fā)生于其中,運(yùn)行于四體,由內(nèi)向外孕育而生。隨著此氣越集越多,浩然之氣便自然而然地呈現(xiàn)于外。因此集義是內(nèi)心義的積累并向外發(fā)散的呈現(xiàn),而非外界義氣之偶合。孟子又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句較長,朱熹將勿正與勿忘斷開,心勿忘與勿助長斷開。讀作:“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近世學(xué)者將心與下文并讀:“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筆者認(rèn)為后者讀法更易理解此句的本意。前文講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
我善養(yǎng)吾浩然之氣范文第2篇
關(guān)鍵詞: 孟子 善辯 精神內(nèi)涵 浩然之氣 平等意識
孟子是戰(zhàn)國中期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散文家,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是僅次于孔子的儒學(xué)宗師。在諸子百家中,孟子以能言善辯著稱,這一點(diǎn)無論是當(dāng)時的學(xué)者還是后來的大師都是肯定的。當(dāng)時他的門人公都子就曾對他說:“外人皆稱夫子好辯。”郭沫若在《荀子的批判》(《十批判書》)中說:“孟文的犀利,莊文的恣肆,荀文的渾厚,韓文的峻峭,單拿文章來講,實在各有千秋。”縱觀孟子的作品,就會發(fā)現(xiàn)孟子與之辯論的對象,很多都是各國君王,面對國君,孟子與之對話很直接也很尖銳,表現(xiàn)出不亢不卑的氣度,保持了自己人格的尊嚴(yán)與獨(dú)立。在孟子善辯的背后,我們看到的是他強(qiáng)大的人格魅力,解讀其精神內(nèi)涵,可以說孟子善辯源于他的浩然之氣,源于他超越時代的平等意識。盡管在當(dāng)時孟子的思想不被統(tǒng)治者接受,但是他雄辯、善辯的才華,他的浩然之氣,“民貴君輕”的平等觀念,千百年來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精神追求的典范。
翻開《孟子》一書,我們可以看到孟子什么事都敢議,什么人都敢言,而且直言不諱,放語不憚。《孟子?梁惠王下》中有這么一段記載: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
王曰:“棄之。”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內(nèi)不治,則如之何?”
王顧左右而言他。
想象當(dāng)時的情境,孟子面對齊宣王并沒有咄咄逼人,而是從容道來,先假設(shè)性地提出兩個問題:“朋友不盡責(zé)該怎么辦?”“士師不盡責(zé)該怎么辦?”都使齊宣王只能有唯一的回答,也就進(jìn)入孟子的“彀中”,待到再問:“四境之內(nèi)不治怎么辦?”他就無話可答,無言以對,當(dāng)時齊宣王一定尷尬不已、面紅耳赤而且毫無回旋的余地,只好顧左右而言他。孟子在文武百臣中當(dāng)眾捋其虎須,使他置于理屈辭窮之境,其目的并不是有意讓他在眾卿家面前失面子,而是使齊宣王認(rèn)識到自己對人民應(yīng)負(fù)的責(zé)任,把國家治理好,實行仁政。
《寡人之于國也》里記載了孟子與梁惠王的一次耐人尋味的對話: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nèi)兇則移其民于河?xùn)|,移其粟于河內(nèi);河?xùn)|兇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對曰:“王好戰(zhàn),請以戰(zhàn)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如何?”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于鄰國也。不違農(nóng)時,谷不可勝食也。數(shù)罟不入闖兀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yǎng)生喪死無憾也。養(yǎng)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琢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shù)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jǐn)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fù)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涂有餓莩而不知發(fā),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于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這番對話是由梁惠王的“疑惑”而引起的。梁惠王自以為對國家的治理已十分“盡心”,他的“盡心”,具體表現(xiàn)在“河內(nèi)兇,則移其民于河?xùn)|,移其粟于河內(nèi);河?xùn)|兇亦然”。盡管鄰國之政不及他如此“用心”,可結(jié)果卻讓他大失所望:“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孟子沒有直接回答梁惠王“民不加多”的原因,而是以梁惠王熟悉的戰(zhàn)事設(shè)喻,告訴梁惠王他所謂的“盡心”與“鄰國之政”的不“用心”,并沒有什么本質(zhì)的區(qū)別,只是形式上和數(shù)目上的不同而已,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也就成為必然。
孟子以“王好戰(zhàn)”設(shè)喻,以子之矛攻之盾,一下就擊中梁惠王的要害之處,從而牽著梁惠王的“牛鼻子”,讓他順著自己的思路,接受“王道”及“仁政”的思想:“不違農(nóng)時,谷不可勝食也。數(shù)罟不入闖兀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yǎng)生喪死無憾也。養(yǎng)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孟子層層發(fā)問,綿里藏針,既針對梁惠王感興趣的問題步步誘導(dǎo),又令人信服地提出了自己仁政的思想。盡管雄辯滔滔,我們看到的卻是孟子對人的終極關(guān)懷,閃爍著人文精神的思想魅力。
其實孟子規(guī)勸國君實行自己的仁政思想很多時候也是循循善誘的,在《莊暴見孟子》一文中,孟子一開始和齊宣王討論音樂的問題,其間他利用“樂”的不同內(nèi)涵,巧妙地進(jìn)行了切換,把談音樂引到談“與民同樂”的話題上來,以此勸說齊宣王實行仁政。
當(dāng)孟子聽莊暴說齊王喜歡音樂,就主動去拜見齊王,并直截了當(dāng)提出這個話題。齊王聽了當(dāng)時就“變乎色”,老大不高興,還為自己辯解:“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孟子沒有直接批判齊王,而是先奉承他:“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又替齊王解圍:“今人樂猶古之樂也”,使齊王如釋重負(fù)。在孟子看來,作為統(tǒng)治者的齊王喜歡怎樣的音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以怎樣的形式喜好音樂。“樂”有兩種含義,一讀yuè,當(dāng)音樂講;另一讀lè,當(dāng)“快樂”講。在這里,孟子巧妙地把欣賞音樂變成欣賞音樂的快樂,有意設(shè)置了兩個簡單的問題讓齊王回答:“獨(dú)樂樂,與人樂樂,孰樂?”“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從而啟發(fā)齊王承認(rèn)“與人樂”更“樂”,“與眾樂”更“樂”。孟子成功進(jìn)行了“樂”的內(nèi)涵轉(zhuǎn)變,由己及人,由少及多,又不失時機(jī)恰到好處地向齊王提出:“請允許我給大王講講什么是真正的快樂吧!”充分顯示了孟子借題發(fā)揮運(yùn)用自如的談話方式,為后文宣傳“與民同樂”的政治主張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氛圍。
孟子仁政思想的最高境界就是施仁政以樂于民。孟子在這篇文章中對君王與民同憂樂的情景做了繪聲繪色的描述:“今王鼓樂于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龠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孟子認(rèn)為,統(tǒng)治者若能與百姓同憂樂,才是真樂,才能真正王天下。可以說孟子倡導(dǎo)的這種“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的思想,影響著后代無數(shù)知識分子以國家民族事業(yè)為己任,奏出了無數(shù)可歌可泣的感人樂章。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zé)”的思想信念皆源于孟子的這種憂樂天下的思想。
在孟子善辯的背后,我們看到的是他對百姓的終極關(guān)懷,看到的是他直言諫君、不畏權(quán)勢的浩然之氣,看到的是他為民為國的坦蕩胸懷。在《孟子》中我們找不到一句阿諛逢迎、趨炎附勢之語,摧眉折腰、違心背意之言。盡管孟子四處游說諸侯,以期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抱負(fù),但他卻從不以犧牲自己的人格尊嚴(yán)、人格獨(dú)立為代價。
《孟子說解?公孫丑下?將朝章》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fēng)。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吊于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王使人問疾,醫(y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于朝,吾不識能至否乎?”使數(shù)人要于路,曰:“請必?zé)o歸,而造于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nèi)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于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dá)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xiāng)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于伊尹,學(xué)焉而后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學(xué)焉而后臣之,故不勞而王。今天下地丑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在孟子看來,爵位、年齡、道德是天下公認(rèn)為寶貴的三件東西,齊王不能憑他的爵位而輕視孟子的年齡和道德,如果他真是這樣,便不足以同他有所作為,孟子也不能委屈自己去見他。可見在孟子心中,君和臣只是政治地位不同,人格上是平等的,他要求自己成為王者之師,而不是王的臣仆和奴役。孟子在君臣關(guān)系上的觀點(diǎn),超越了孔子一再強(qiáng)調(diào)的“君君,臣臣”,“君使臣,臣事君”(《論語?八佾》)的君臣主仆關(guān)系,強(qiáng)調(diào)了君和臣在人格上的平等。所以就不難理解孟子在《孟子―離婁》篇中表達(dá)的君臣觀念:“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這些均表現(xiàn)了孟子可貴的超越時代的平等意識。
我善養(yǎng)吾浩然之氣范文第3篇
1、原文:太尉執(zhí)事: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xué)而能,氣可以養(yǎng)而致。孟子曰:“吾善養(yǎng)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zhí)筆學(xué)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2、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xiāng)黨之人所見不過數(shù)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跡不足以激發(fā)其志氣恐遂汩沒故決然舍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杰。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fā),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
3、譯文:太尉執(zhí)事:我生性喜好寫文章,對此想得很深。我認(rèn)為文章是氣的外在體現(xiàn),然而文章不是單靠學(xué)習(xí)就能寫好的,氣卻可以通過培養(yǎng)而得到。孟子說:“我善于培養(yǎng)我的浩然之氣。”現(xiàn)在看他的文章,寬大厚重宏偉博大充塞于天地之間,同他的氣的大小相稱。司馬遷走遍天下,廣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之間的英豪俊杰交友,所以他的文章,疏放不羈,頗有奇?zhèn)ブ畾猓@兩個人,難道曾經(jīng)執(zhí)筆學(xué)習(xí)這種文章嗎?這是因為他們的氣充滿在內(nèi)心而溢露到外貌,發(fā)于言語而表現(xiàn)為文章,自己卻并沒有察覺到。
4、我出生已經(jīng)十九年了。我住在家里時,所交往的,不過是鄰居同鄉(xiāng)這一類人。所看到的不過是幾百里之內(nèi)的景物,沒有高山曠野可以登臨觀覽,以開闊自己的心胸。諸子百家的書,雖然無所不讀,但是都是古人過去的東西,不能激發(fā)自己的志氣。我擔(dān)心就此而被埋沒,所以斷然離開家鄉(xiāng),去尋求天下的奇聞壯觀,以便了解天地的廣大。我經(jīng)過秦朝,漢朝的古都,全國人依靠您而無憂無慮,四方異族國家懼怕您而不敢侵犯,在朝廷之內(nèi)像周公、召公一樣輔君有方,領(lǐng)兵出征,向方叔、召虎一樣御敵立功。可是我至今還未見到您呢。
(來源:文章屋網(wǎng) )
我善養(yǎng)吾浩然之氣范文第4篇
1、第一個樂趣是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指的就是家庭平安和睦。我們說家和萬事興,家庭平安、和睦是事業(yè)的基礎(chǔ),《大學(xué)》中也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中的修身齊家也是在治理國家、平定天下的前面。可見家庭是其他事業(yè)的基礎(chǔ)。所以家庭平安,是作為一個君子的第一個樂趣。
2、第二個樂趣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只有一個人的道德上沒有虧欠,這個人才能走得更遠(yuǎn),才更值得尊敬。一個人良心沒有愧疚,才能坦坦蕩蕩、光明磊落。始終保持善念,注重個人品德修養(yǎng),“吾善養(yǎng)吾浩然之氣”是作為君子的第二大樂趣。
3、第三個樂趣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孟子首先是一個教育家,每一個老師都希望自己的學(xué)生優(yōu)秀,成為國家的棟梁。其次,分享自己的知識和感悟,才會讓知識產(chǎn)生更大的價值。另外,文化的傳承也是對生命的延伸和升華。
(來源:文章屋網(wǎng) )
我善養(yǎng)吾浩然之氣范文第5篇
張軍,字浩然, 晉人張氏,生之汾河之畔,名字若何?因父之愿,望有右軍之境,故取名軍,因孟子曰:吾善養(yǎng)浩然正氣,故取字浩然。自由藝術(shù)者,畫家,初年幼癡與繪畫,尤喜寫意,十二歲拜師學(xué)藝,始知筆墨之妙,后接受學(xué)院派教學(xué),余以為凡有派別之分必有狹隘之嫌疑,故愿跟隨內(nèi)心以力追自由之境。師法古今中外,道法自然,由書入畫,漸進(jìn)中得心源。吾藝之道,唯上下求索,修身爾。
當(dāng)年我們中文專業(yè)最受人尊敬的要數(shù)“何博”,粉絲親切贈送外號“河伯”。身為博導(dǎo),教授中國古典文學(xué),也因為其在專業(yè)領(lǐng)域數(shù)十年如一日的鉆研,對古典文學(xué)的熱愛,在《易經(jīng)》研究上,達(dá)到相當(dāng)?shù)母叨取D欠輪渭兊臒崆椋踔聊芨腥镜矫總€人,在學(xué)生心中地位頗高,以至于其授課期間從未有逃課現(xiàn)象,反而慕名而來之人每天和本專業(yè)人士搶占第一排風(fēng)水寶座,只為能近距離感受到“河伯”的風(fēng)采,如今余音尚在,搶座人不在。
講到“建安風(fēng)骨”,魏晉南北朝,河伯贈我們一言,讓我們帶心來聽,他言及到,雖則數(shù)年之后好多東西早已記不起來,但總會有一些東西留在心里,而留在心里的東西才是我們上課的真正目的所在。及至現(xiàn)在,各種片段情景,油然心聲,如觀看老照片一般。曹植《白馬篇》的豪俠風(fēng)骨,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遺情千古恨的《洛神賦》,悼良會之永決兮,哀一世之異鄉(xiāng),遺情想象,故忘懷愁,浮長川而忘返,思綿綿而增慕。又可見其情思之細(xì)膩,悲痛之深,無奈之極。家國愛恨,皆是浮生若夢,他也只能撫心長太息,感物傷懷。及至左思有“郁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苗”感嘆文人不得志,含蓄蘊(yùn)極,高妙自然。亂世出豪俠英才,在中國魏晉時代可謂是很好的一例。一面是狂放不羈,一面是憂國無奈,所以阮籍,醉六十日,然不得言而止,然車轍所窮,則慟哭而返。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
青年書畫家浩然亦醉心于魏晉文化,其身世亦非富家子弟,經(jīng)歷崎嶇,雖年少,對生命亦有感懷,落筆抒情,也顯自然流暢。畫畫其鐘愛并受徐渭、、吳昌碩、任伯年、齊白石、潘天壽等影響。書法多臨摹王羲之、顏真卿、米芾。其畫《荷花》自有一種清淡雅致,風(fēng)骨及婀娜姿態(tài)皆相得益彰。自古梅蘭竹菊皆文人彰顯個人品格之厚愛,浩然亦畫竹,《墨竹》—竹的那份俊俏挺拔正如年輕的書畫家一樣,才情盡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