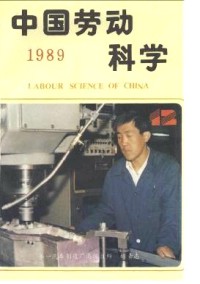勞動合同法的立法背景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勞動合同法的立法背景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制定《勞動合同法》是協調勞動關系、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需要,是建立和諧社會的需要。
我國現行勞動法嚴重滯后于現實需要。20世紀90年代我國開始了市場經濟的進程,為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1994年7月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頒布,1995年1月1日施行。這部《勞動法》是我國建國以來第一部調整勞動關系,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法律。自實施以來,它在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協調勞動關系,促進經濟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10多年來,我國勞動用工制度發生了巨大變革,勞動力市場機制得以建立,在全社會范圍內逐漸形成了競爭機制、風險機制和能進能出的機制,使勞動力資源的效率配置成為可能,勞動者的勞動權也日益受到重視。勞動法的實施、勞動制度的改革,不僅使勞動者的權益得到法律保護,使企業的效益有了提高,也極大地提高了我國經濟發展速度,人民物質生活水平明顯提高。但也不能不看到,10多年來我國政治、經濟發展迅速,制定于10多年前的《勞動法》日益顯現嚴重滯后于現實需要的弊端。
其弊端主要有:
1.適用范圍窄,影響勞動法作用的發揮。《勞動法》制定時,既為了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同時也是為了對企業用工制度進行改革,因而側重于企業勞動關系的調整。而對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及其其他用工形式的勞動者不完全適用,甚至不適用,造成適用范圍較窄,不能使所有勞動者都一律平等地能獲得勞動法的保護,這已成為影響勞動法權威性和發揮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作用的瓶頸。
2.勞動關系法律規制復雜化。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靈活用工形式增多,用工主體多樣化,用工形式多樣化,如勞務派遣用工、非全時用工、承包工、包工頭、民辦非企業單位用工等。這些新的用工形式在勞動法中沒有規范或規范較少,出現法律的真空。缺乏規制的結果就是權利維護的缺位。
3.勞動合同短期化現象普遍,影響勞動者職業穩定權和企業、國家的長遠發展。用人單位出于用工成本低廉的考慮,普遍與勞動者簽訂短期勞動合同,使勞動者缺乏職業安全感,影響構建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同時由于勞動者缺乏職業安全感,對企業沒有歸屬感,對企業的忠誠度低,員工流動率過高,企業長遠發展需要穩定的訓練有素的員工隊伍,短期用工的結果也會影響企業長遠發展,同時對國家拉動內需促進經濟發展也不利。
4.勞動關系法制化落實難。由于勞動法對法律責任追究規定不完善,致使法律明文規定的勞動者的權益不能得到及時有效地保護。據抽樣調查統計,我國勞動合同平均簽訂率并不高,特別是建筑業、餐飲服務業的簽訂率只有40%左右。農民工勞動合同簽訂率在30%左右,中小型非公有制企業簽訂率不到20%[①]。勞動法明文規定勞動合同應采取書面形式,但并未規定不以書面形式簽訂勞動合同將承擔什么法律責任,因此,這一規定雖已實施了10多年,但有些用人單位仍然無視法律不與勞動者簽訂書面勞動合同,致使勞動者維護權益時想要證明與企業之間存在勞動關系困難,國家勞動監察機構行使監察權也無法律依據。
5.勞動力成本持續探低,對國家經濟總體發展不利。企業在市場經濟中是追逐利潤最大化的經濟組織,人力資源的對策主要就是如何降低勞動成本,同時也由于勞動立法規范不夠或規范空缺等因素,使企業在用工時更多傾向于低勞動成本,如:工資標準長期得不到提升,勞務派遣工與非勞務派遣工的不同工同酬,非全日制工的低工資,試用期成“白用期”,廉價使用勞動力,拖欠工資嚴重等。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工資總額占GDP的比例呈現走低趨勢,1978年為16.1%,1990年為15.8%,2000年為10.7%,2005年為10.9%,而市場經濟成熟國家,勞動者的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普遍都在54%~65%之間,如美國為58%。即使像印度這樣的不發達國家,勞工工資也比我國高。印度人均GDP只有中國的一半,但是其制造業工人的全部報酬卻是中國的2.5倍[②]。勞動力成本持續探低,會造成用人單位將低勞動力成本作為取得競爭優勢的“法寶”,而忽視以科學管理、技術更新提高企業競爭優勢的積極作用,長此下去不利于科學技術的自主創新,影響國家科學技術水平的提升。而勞動力成本的探低,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勞動者職業安全感的喪失,會動搖其消費欲望,抑制其消費水平和消費能力,影響消費市場的擴張,乃至國民經濟的發展。
6.勞動者的擇業自由權受到極大限制。擇業自由權,是指勞動者根據勞動法規定,有自由選擇職業和工種的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31條規定:“勞動者解除勞動合同,應當提前30日以書面形式通知用人單位。”根據這一規定,勞動者單方解除勞動合同時,只需要履行提前30天書面通知義務,30天期滿,該解除就可以發生法律效力。而有的用人單位為了防止員工“跳槽”,約定違反勞動合同的期限即視為違約,即只要勞動者在勞動合同期限內提出解除勞動合同,即視為違約,設立高額違約金,以此限制勞動者自由擇業權的行使。
法律是反映社會現實的,是社會關系的調整器,勞動法實施過程中日益顯現的嚴重滯后于現實需要的弊端,就有必要立法予以調整。
同時,法律的調整與政府的執政理念也有關系。我國改革開放已有20多年,在改革開放之初,為使國民經濟迅速發展,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發展原則,這一原則的實施,對推動國民經濟的發展起了極大作用,我國國民生產總值連年上升,國力迅速增強,但發展中效率優先的結果,有失公平,犧牲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尤其是國有企業改制中的老職工的利益。在勞動領域,在追求勞動力效率配置的同時,忽視了公平。2006年10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16屆六中全會上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闡述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和原則,也確定了本屆政府的執政理念之一是構建和諧社會。而在構建和諧社會的活動中,必須把構建和諧勞動關系放在首位,因為勞動關系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最廣泛、最基本的社會關系,也是最重要的社會關系,勞動關系和諧穩定直接關系著整個社會的和諧穩定,關系著勞動者能否獲得權利的充分保護,企業能否獲得良好的發展空間,國家能否獲得可持續性發展。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勞動合同法是我國建立和維護勞動關系協調機制的基礎性勞動法律規范。
我國的國情也決定了有必要制定《勞動合同法》。我國的基本國情是就業市場嚴峻,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的狀況始終存在,用人單位相對于勞動者無論是在經濟上、組織上、就業市場上、資源的配置上都處于強勢地位。“強資本、弱勞工”現象在勞動關系領域普遍存在,在勞動領域發生的一系列問題,如:農民工工資被大量拖欠,黑煤窯奴役“勞工”,“血汗工廠”屢禁不絕,用人單位拖欠巨額社會保險費,勞動爭議案件連年遞增等,勞動關系領域的不和諧、不穩定現象,既損及勞動者權益,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障礙,也帶來嚴重的政治問題,勞動風險有可能演化為社會風險,甚而政治風險,會引發社會動蕩。在有關國家“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之際,勞動領域的問題也會有損我國的國際形象,給中國政府做負責任的大國的承諾帶來負面影響。可見,勞工權益的維護不僅是經濟問題,更重要的是政治問題。
我國工會的力量尚有限,尤其是基層工會組織,一般難于取得與用人單位平等的地位,集體合同、集體協商制度尚未完善,因此利用團體力量解決勞動條件、勞動標準的合理、公平問題還尚有一定難度,對勞動關系的調整更多地需要依靠國家立法。這也反映了我國勞動立法的特色,即側重于個別勞動關系的調整。
另外,從全球范圍看,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使我國經濟與世界經濟順利接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尤其是制造業發展迅速,在國際市場上占有一定的競爭優勢。產品價格包含勞動力的價格,我國豐富的、低廉的勞動力成本成為在國際市場上取得競爭優勢的因素之一。但一國競爭力的維持與提高是否可以長久、持續地依靠低廉的勞動力成本,顯然不盡然。在國際貿易競爭十分激烈的今天,不少發達國家出于對本國市場、就業的保護,以各種借口設置貿易壁壘,擠壓中國產品的出口空間,例如“反傾銷”,發達國家以低于市場價格傾銷為名,對我國出口產品征收高額反傾銷稅。根據世貿組織統計,1995年至2004年間,中國始終是全世界遙遙領先的反傾銷頭號目標國;據我國商務部統計,1979年至2004年5月底,已有34個國家和地區發起了637起涉及我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及特保調查,其中反傾銷調查573起,反補貼2起,保障措施調查51起,特保調查11起,涉及商品4000多種[③]。還有些國家設置“綠色標準”、“勞工標準”、技術標準、動植物衛生檢驗檢疫措施、知識產權保護等各種形式的貿易壁壘,限制我國產品的輸出,使我國依靠低廉的勞動力成本進行國際競爭越來越困難。在激烈的國際貿易競爭中,我國要想獲取市場,一方面適時堅持低勞動力成本的優勢,另一方面也必須適時調整,多方位發展,不能總是處于全球產業鏈的末端,要提高自有技術的含量,這屆政府也提出了自主創新的發展口號。而產業提升、產業機構調整,提高技術研發水平,乃至提高一國的科學技術水平,都必須在人力資源上投資,“科技以人為本”。
制定《勞動合同法》,是中國調整勞動關系的必然,是建立和發展和諧社會的必然,同樣也是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必然。勞工權益維護,社會和諧發展,提升科學技術水平,社會進步和文明的要求,都呼喚中國要加強勞動立法,盡早制定《勞動合同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