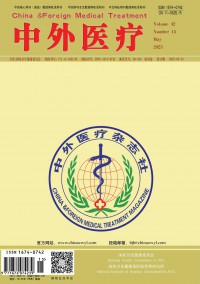中外教育史對比分析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中外教育史對比分析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當我們研究教育問題時,我們無法將一個個教育問題封閉起來,孤立地就事論事,我們不得不把目光投向歷史的深處,追根溯源,去探尋那些導致今天教育現狀的種種因素;我們也無法將我們的教育與世界其他國家的教育割裂開來,閉門造車。因為歷史的、別國的教育都對我們今天的教育產生著潛移默化的、不容忽視的作用。“任何出色的真實有效的教育都是民族生活與特點的寫照。它根植于民族的歷史中,適應于它的需要”[1](P65)。忽視我們自身的歷史傳統,我們的教育將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喪失生存的土壤。同時,“以正確的精神和嚴謹的治學態度研究國外教育制度的作用”,以便“促使我們更好地研究和理解我們自己的教育制度”[2],使本國人民意識到自己教育制度中的優勢、缺陷,尤其是“對照別國,發現本國的弱點,并予以改進”[1](P63),這同樣是不可或缺的工作。所以,當我們研究今天的教育時,不可能回避歷史的和別國的經驗。“古今貫通,中西融匯”,將古今中外的教育歷史融于一爐,對其進行比較鑒別,去偽存真,去粗取精,既吸取我國教育歷史中的精華,又借鑒國外教育歷史中的優秀成果,并結合當前教育面臨的實際問題,建立起一個既具有中國特色又有現代教育意識的教育史研究新體系,這是我們在碩士生階段教育史專業設置中外教育史比較方向的初衷。具體說來,有以下幾個方面的考慮:
(一)再發現———促使學生提高思維能力的重要路徑
從事高等教育的人都清楚一個事實:碩士階段的教育不同于本科階段的教育。相對而言,碩士教育階段更側重于對學生思維能力的訓練和科研能力的培養。那么如何鍛煉學生的思維,提高學生的科研能力呢?美國著名教育家、心理學家布魯納關于引導學生發現和再發現的主張給予我們很大的啟發。布魯納認為,人類的全部活動中的最獨特之點,在于人類能夠親自發現,人不是一個被動的有機體,人掌握概念、解決問題都是一個主動的過程。發現是教育學生的主要手段,教師向學生提出有關問題,引導學生搜集、鉆研有關資料,通過積極思考,自己體會,從而“發現”概念和原理。按布魯納的話來說,發現學習就是以培養探究性思維的能力為目標,以基本教材為內容,使學生通過“發現”與“再發現”的步驟來進行的學習。這里特別引起我們重視的是,布魯納指出學校中的發現學習不局限于對未知世界的發現,更重要的是引導學生憑借自己的力量對人類文化知識的“再發現”,其實質就是把“現象重新組織或轉換,使人能超越現象進行再組合,從而獲得新的領悟,包括尋找正確結構和意義”[3](P465-470)。具體在教育史研究領域,設置中外教育史比較研究方向的目的首先就在于使學生從歷史上已有的教育現象出發,通過自己的探究性學習,深入體會造成此種教育現象的社會歷史原因,并通過對中外教育史的比較研究,發現中外教育歷史中被遺忘的或尚未發現的新的研究領域。但更為重要的是,設置中外教育史比較研究方向的目的在于促使學生對已有的史料、史實、知識結構和教育問題進行再發現,使這些教育現象在學生的頭腦中重新組合,從而獲得新的體悟,尋找出教育的真諦。這種發現和再發現的過程是一個相當艱辛的過程,甚至是一種痛苦的、需要付出巨大精力的勞動過程,但也確實是使人意志受到磨練、思維得到升華的過程。因此,通過中外教育史的碰撞與比較,著實可以使學生走出僅從中國教育史著眼或僅從外國教育史入手研究教育問題的局限,促使學生從比較的視野重新審視以往對教育問題的看法,積極思考中外教育的異同,“發現教育問題,探討問題產生的原因及其在特定背景中的解決辦法,以及發展教育的原理或原則”[4](P436)。
(二)寬視野———拓展學生知識面的有效手段
在教育史領域,以往學生看問題,僅僅從自身所主攻的研究方向的角度出發。研究中國教育史的學生,埋頭于鉆研中國教育史方面的知識和史料,雖能達到一定深度,但對外國的教育歷史知之甚少,思路難以拓寬;而研究外國教育史的學生,雖然對外國的教育研究得比較到位,但卻缺少對中國教育歷史和現狀的應有了解,因而難以很好地對外來教育制度取其精華、棄其糟粕。而事實上,中外教育在歷史上是互相借鑒、互相融合的。“我們的祖先不僅曾以印刷術和指南針推動世界文化的歷史車輪前進,更曾以儒家思想和考選制度有功于各國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的建樹”[5](P4)。而隨著西學東漸的深化,西方的近代學制直接影響了中國現代型學校誕生的進程,為中國近代學制的完善與發展提供了有利的借鑒。可以說,“我國既是文化教育的輸出國,又是文化教育的輸入國”。“妥善地把東西方教育史溝通起來和妥善地把中外教育史掛起鉤來”[5](P4),有利于拓展我們的視野,使我們認識到人類教育歷史的整體性。因此,設置中外教育史比較研究方向,意在彌補碩士研究生培養中以上兩種偏向的不足,拓寬他們的視野,豐富他們的知識面,教會他們以比較的眼光和辯證的思維來看待中外教育發展中的史實,使其知識體系既植根于中國教育的肥沃土壤中,又能充分吸收外來教育中有益的成分為我所用。
(三)相碰撞———為教育改革尋找切實的借鑒
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世界的文化教育都不是絕緣體”,“世界文化總是通過彼此接觸而向前發展的”,“當各國在戰火紛飛的時刻,他們的教育文化常常是和平相處或互相取長補短的”,“當今各國的學校都是混血兒”[5](P3)。隨著亞歷山大的東征,客觀上使得東西方文化教育第一次發生了大規模的碰撞,產生了聞名遐邇的文化教育之城———亞歷山大利亞城,將當時世界各國的先進文化教育集于一堂,哺育了歐洲文化教育幾千年,成為“人類文化教育前進的淵源”[5](P4);在我國宋代,富有歷史使命感的理學大師們將外來的佛教、本土的道教引入到儒學中來,使它們發生碰撞,最終形成了以儒家為主體,融合佛、道的新儒學———理學思想體系,并成為封建社會后期統治思想的主干,影響中國文化教育事業達千年之久。隨著社會的發展、科技文教事業的進步,世界各國越來越緊密地聯系到一起,任何國家的教育事業都無法脫離其他國家而單獨存在,也不能脫離歷史傳統來研究教育問題,而應從各國歷史的經驗教訓出發,使它們與當前的教育改革發生激烈的碰撞,在碰撞中發現真理的光芒,使其成為我們切實有力的借鑒。如:我們當前的基礎教育改革,就在相當程度上借鑒了美國實用主義教育家杜威的思想,意在充分發揮兒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同時,也參考了新傳統教育派的主張,以便通過教師有計劃、有組織的“課堂教學”,使學生學會“人類積累的知識”,掌握某些人類歷史上“永恒不變的要素”[6](P236);而且,還主張發揮中國教育的優良傳統,對學生“言傳身教”、“因材施教”、“啟發誘導”,建構以“情”為根基的主體發展觀[7]。實踐證明,“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確實可以促使中外教育在現實的基礎上發生碰撞,為我們的教育改革提供切實的借鑒。
(四)融多元———當代教育發展的呼喚
當談及世界教育史時,人們關注更多的是以歐美為中心的強勢國家的教育,似乎世界教育的歷史只有西方的歷史,或僅僅是歐美幾個強勢國家的歷史。而事實上,“歷史從東方開始”[8](P160),人類教育的發達以東方為先。亞述、巴比倫、埃及、印度、中國等東方國家的教育是早于歐洲的希臘、羅馬而興起的,其在教育內容、方法以及管理上,在當時堪稱是相當完善的。各個國家和地區及其不同時期的教育各有其特征,人類文化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就世界教育的肇端和進步來看,多元論恰是正確的。很多現在看似弱勢的國家和地區的文化教育,都在歷史上作出過貢獻。如,古代阿拉伯的教育曾經為人類文化教育,特別是西歐文化教育的進步作出了重要貢獻。阿拉伯人在公元7世紀興起之初,其文化教育是相當落后的,但是由于推行開明的文教政策和尊師重教、鼓勵學術研究的有力措施,在繼承東、西方文化成果的基礎上迅速發展了自己的文化與教育,從而建立了“一種融合了猶太文化、希臘———羅馬文化和波斯———美索不達米亞文化傳統的混合文明”[9](P360)。阿拉伯偉大的數學家花剌子模創立了代數學,他編寫的《積分和方程計算法》于12世紀傳到西歐,一直到16世紀還是大學使用的教材。通過學習他的著作,西方懂得了使用阿拉伯數字。阿拉伯的醫學家伊本•西那被譽為“醫中之王”。他的《醫學原理》一書討論了傳染病、寄生蟲病、皮膚病、精神病等廣泛的醫學問題,記載了七百六十多種藥物,因而有“醫中圣經”之稱,該書在12世紀至17世紀一直是西歐大學醫學科教育的主要教材。阿拉伯哲學家伊本•路西德對亞里士多德著作所作的注解、提示和摘要在西方流傳了幾個世紀,對西歐重新認識古希臘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3](P153)。阿拉伯的赫克邁大學是中古和近代的第一所大學,當波倫亞、巴黎、薩勒諾、牛津、劍橋還沒有出現大學的時候,赫克邁大學已經將學術上的火炬高高地舉起了。阿拉伯的文化教育成果,傳入處于基督教統治之下幾近陷于愚昧的歐洲,使那些久已忘記希臘學術的士子耳目一新,從阿拉伯的譯著中重新發現古希臘文化教育的輝煌;使那些長期以來被基督教控制的學校從繁瑣的宗教論證和枯燥的教條記誦中解放出來,獲得新的學科內容和方法,這不僅給予歐洲學術文化以生機,更為中世紀大學的興起準備了條件,為文藝復興作了先導[5](P53)。可以說,“歐洲的文藝復興是在底格里斯河一帶預備的,不是在頓河、泰晤士河、萊茵河、第聶伯河一帶預備的。邁蒙、易斯哈格、薩頓姆、花剌子模和其他阿拉伯學者開辟了一條新的路徑;而佩特拉克、但丁、伊拉斯謨等,便是沿著這條路徑走去的。文藝復興既蒙阿拉伯人的引導,則人類文化應當感謝阿拉伯人的盛意”[5](P81)。因此,應該將東方古國教育史放在和西方古國教育史同等重要的地位,因為它們共同構成了多元化的世界教育,組成了世界教育史的框架。到了當代,世界的文明范圍進一步擴大,各個國家之間的交往和聯系更加緊密,各國都必須不同程度地面對多元化的世界。如何正確地認識處在多元化中的世界各國的文化教育及其對世界文明的貢獻,消除彼此之間的文化偏見,增進對自己文化的自尊和對他國文化的尊重與理解,是擺在當今世界各國面前的一個共同的議題。以歷史的眼光、比較的視野積極思考每個國家的文化教育存在的原因和價值,以及各種文化在一起互惠的益處,從而在世界各國不同文化教育之間進行積極的交流,使它們互相融合、吸收,取長補短,這是教育的使命,也是當代世界教育的呼喚。
(五)新領域———教育史研究的探新與拓展
用比較的方法研究中外教育史,近些年來,在國內除了少數幾所學校為碩士研究生開設此研究方向外,其他學校少有涉及。從目前的研究成果上看,雖然也有不少學者在研究中自覺不自覺地采用過這種方法,發表了一定數量的論著,但較有影響的還是張瑞幡、王承緒二先生主編的《中外教育比較史綱》,其中對中外教育歷史的發展與演變有較為系統的論述和比較,對后人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啟發性。但可能由于篇幅所限,該書對很多教育問題僅作了一般性的論述和比較,尚缺乏更細微的、全方位的探討和更深入的學理性分析。除此之外,在中外教育史比較研究方面,很難找到更為系統、全面的論著。可以說,中外教育史比較研究是一個新的研究領域,是一項具有開拓性的工作,既是對中國教育史研究的拓展,也是對外國教育史研究的拓展。我們從2002年開始招收第一屆該領域的研究生,至今已招收六屆,其中已畢業三屆,在中外教育史比較研究方面進行了艱辛但卓有成效的探索。
二、近年來的探索實踐
(一)篳路藍縷———師生同下真功夫
“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左丘明:左傳•宣公十二年),這正是我們在中外教育史比較研究這條崎嶇的山路上艱辛探索的真實寫照。我們企盼摸索出一條對我們今天的教育改革能提供有效借鑒的路徑。為此,我們刻苦鉆研、身體力行,師生同下真功夫。首先,導師以身作則,在招收第一屆研究生前已經在該領域探索了多年,數年如一日地埋頭于中外教育史比較研究,并與本校和兄弟院校的同行積極探討教育教學中的問題,努力提高自己的專業素養,力求做到“經師”與“人師”的結合。與此同時,歷屆學生也以導師為榜樣,刻苦鉆研學問,廣泛涉獵書籍,在此基礎上,根據自身的專業積淀和興趣愛好,初步確定自己的主攻課題,并細心鉆研有關資料,其中既包括古文獻資料,也包括外文資料,為自己的進一步深入研究積累有益的素材。如:對教育家的思想感興趣的學生,平時就注意搜集并鉆研有關資料,不僅僅只是教育方面的史料,而且包括與之相關的哲學、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科技等各方面的資料;對宗教文化與教育的關系感興趣的學生,平時就注意鉆研宗教和教育方面的書籍和史料,包括宗教的產生、傳播以及對教育的影響和教育對宗教信仰的反作用等。在廣泛積累的基礎上,殫精竭慮,深入進行比較思考。此外,學生們還注重自發組織讀書報告會和舉辦專業范圍內的學術討論會,交流思想,提高思維,互相取長補短。與此同時,在導師的鼓勵下,積極地參加專業領域內的各種學術會議以吸取學術營養;踴躍向專業學術期刊投稿,,將自己零星的想法通過這些學術交流構成一個完整的系統,內化為自身的獨特體悟。就這樣,師生一心,伏下身去,埋頭于中外教育史的浩瀚海洋中,下真功夫開創中外教育史比較研究的新局面。
(二)深思熟慮———把握選題,剖析研究的可行性、創新性與價值
碩士研究生的畢業論文寫作與答辯可以說是碩士生階段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它直接反映著碩士研究生培養的成果。而把握選題,又是整個畢業論文寫作過程的重中之重。為此,在碩士研究生畢業論文的選題上,我們緊緊圍繞中外教育史比較的有關問題,從嚴要求,認真剖析研究的可行性、創新性與研究的價值,務使每位學生的畢業論文具有較高的質量和水平。下面僅以2004級(即2007屆)碩士研究生王亞輝同學的選題為例來說明我們是如何把握選題的。王亞輝同學的選題為《“信仰”與“理性”的交織和互動———宗教視域下的宋代書院與中世紀大學之比較》,它的可行性在于宋代書院和中世紀大學是中西方高等教育史上兩顆璀璨的明珠,而且在辦學時間上也大致相近,具有可比性;前人又曾從兩者的形成機制、辦學精神、教學管理、藏書功能等方面進行過比較,這可以為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鑒。但是,從宗教的視域對兩者進行比較,國外還沒有此方面的論著;國內只有彭嵐同志2000年在《北京科技大學學報》上發表的《宗教對中國書院與歐洲中世紀大學影響之比較》的一篇文章。文中闡述了宗教對兩者的影響關系,但該論文是把儒學當作宗教———儒教來與基督教進行比較的,而把儒學作為宗教,在目前仍很有爭議。可以說,到目前為止,國內外還沒有真正從宗教的角度去研究宋代書院和中世紀大學之間關系的論著。而佛教、道教對宋代書院的影響和基督教對中世紀大學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歷史事實,對二者的比較研究既有現實意義,又有一定的深度。王亞輝同學利用自己幾年來對宗教和教育的研究積累,較深刻地探討了佛、道對宋代書院影響與基督教對中世紀大學影響之異同,這成為他的這個選題的創新之處。至于這一選題的價值,則在于它從客觀歷史的角度去進行宗教對兩者產生影響的共性及差異性的比較,透視中西方文化和教育,反思信仰和理性的關系,文章有個性、有深度,從而有助于加深思考,并有助于解決當前教育中出現的一些現實問題。
(三)初顯成效———探索取得了理論與實踐成果
數年來的探索使我們積淀了較為豐厚的研究基礎,在中外教育史比較方面產生了一批有分量的學術成果。如:導師先后承擔并高質量完成了國家教育部《中西方道德教育思想與實踐比較研究》、全國高等學校教學研究會《中外德育比較研究》、國家留學基金資助《中俄教育比較研究》等課題;出版了《人性:存在與超越的省視———中西方道德教育思想與實踐比較研究》、《大起大落的命運———杜威在俄羅斯》等著作;在專業雜志上發表了《文理學科的相互滲透與結合———當代中外高教改革面臨的共同問題》(《高等師范教育研究》)、《中西方道德教育思想與實踐之差異及其成因》(《教育理論與實踐》)、《中西方德育比較概論》(《河南大學學報》)、《基礎教育的中國特色:建構以“情”為根基的主體發展觀》(《河南大學學報》)等比較方面的論文,并在社會上產生了較為廣泛的影響。“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研究生們經過學術上的磨練,也在中外教育史比較的體悟方面上升到了新的高度,一篇篇研究成果脫穎而出,如:《倫理的政治化與倫理的哲學化———孔子與蘇格拉底的教育目的及其踐行過程之比較》(王娟華)、《傳統的反叛:中西方現代教育的思與行———歐美現代教育運動與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教育革新之比較研究》(于書娟)、《“中體西用”與“和魂洋才”———教育視野下張之洞與福澤諭吉西學思想之比較》(周娜)、《洪堡德與蔡元培大學改革思想與實踐之比較》(徐曉颯)、《“道法自然”與“以天性為師”———中西方自然教育觀之比較》(王文禮)、《返于自然與超越歷史———盧梭與梁啟超“賢妻良母”女子教育目的觀之比較》(李琳琳)、《“信仰”與“理性”的交織和互動———宗教視域下的宋代書院與中世紀大學之比較》(王亞輝)、《裴斯泰洛齊和晏陽初鄉村教育理論與實踐之比較》(張愛梅)、《中美高師生教育實習發展之比較》(常艷麗)、《中英教育督導制度發展之比較》(王為民)、《中美高等教育評估中介機構發展之比較》(楊婧)、《余家菊和森有禮國家主義教育思想之比較》(王雅芳)等,這些論文從不同視角、不同歷史時期進行比較研究,雖在某些方面尚顯得有些稚嫩,但畢竟對教育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在此過程中學生也感到收獲頗多。
三、探索中的體認與感悟
(一)難度之大,不容否認
如前所述,中外教育史比較研究是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只能在借鑒有限資料的基礎上“摸著石頭過河”。而且中國教育史、外國教育史兩者任通一史已是頗有難度的。就中國教育史來說,“中國教育的發展源遠流長,涌現出了眾多的教育思想家和實踐家,積累了豐富的教育經驗,形成了許多獨具的特點和優良的傳統”[10](P1)。如此豐富的教育內容,若要精通,必須深入鉆研,充分占有史料不可。而中國古代的史料可謂是浩如煙海,并且大都是不符合現代人閱讀習慣的、較艱澀的文言文。而外國教育史的內容也是極為廣泛的,“從縱向而言,它涉及從原始社會直到如今的人類教育的產生和演變的全部過程”;“就橫向而言,它涉及除我國之外所有國家和地區的教育的發展”[5](P1)。這么寬廣的范圍、浩繁的內容、龐大的體系,即使原始材料全是現代漢語,研究起來也是頗有難度的,何況原始材料大都是用各國自己的民族語言或被翻譯成國際通用的英語語言來書寫。要將中外教育史兩者結合起來,時兼古今、地兼東西,難度之大,可想而知。它非要我們有“坐冷板凳”的精神,幾十年如一日地潛心研究不可。然而,對中外教育史的比較研究無論難度有多大,卻是一件很有意義、值得做的事情。中外教育的歷史源遠流長,其中蘊含著無窮無盡的寶藏,有些寶藏必須通過我們比較鑒別才能發現它的現實價值。“教育史學家說,研究物質變化的自然科學,如物理學、化學等等,要在實驗室中進行;作為社會科學的教育科學則不盡然,雖則許多比較具體的課題可以通過實驗取得答案,但許多具有理論性、根本性和久遠性的重大課題是無法著手實驗研究的”[5](P1)。要論證或判斷這種課題,繼續借助歷史發展的往事并在比較中來反思和解決是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美國教育家杜威說,教育史不啻是教育科學的實驗園地。那么我們可以說,中外教育史比較研究是其中的一棵生命力旺盛的幼苗。
(二)知難而進,融通中西,尋找教育的真諦
“天下事有難易乎?為之,則難者亦易也;不為,則易者亦難矣”([清]彭端淑:為學)。面對困難,迎難而上,知難而進,追求學貫中西,是每一位杰出的教育家的人生態度。例如,被譽為“偉大的人民教育家”的陶行知,把教育事業作為救國救民、改造社會的武器,為爭取民族和人民的解放而奮斗一生,為改造中國的舊教育、創造人民的新教育而奮斗一生。陶行知先后就讀于家鄉私學、南京匯文書院、金陵大學、美國紐約州立大學、伊利諾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曾以美國著名教育家杜威、孟祿為師,并取得博士學位。他先后擔任過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教員、教授、教育專修科主任、教務主任,東南大學教授、教育科主任,《新教育》雜志主任干事。按照這樣的發展趨勢,他完全可以得到高官厚祿,但是他卻放棄優越體面的生活,走上了另外一條道路,投身于廣大平民的新教育、廣闊農村的鄉村教育的開拓中去。他輕視那種只是爭權奪位的“政客式的教育家”,認為“第一流的教育家”“要敢探未發明的新理”,或者“敢入未開化的邊疆”,“做個邊疆教育的先鋒”[11](P119)。懷著對民族、對勞苦民眾、對兒童的深摯感情,他先后開辦了曉莊師范學校、山海工學團、育才學校等教育實驗學校來實踐他的教育救國的理想;在此期間又撰寫了《行是知之始》、《教學做合一》、《在勞力上勞心》、《生活即教育》等文章,論述了“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等教育觀點,將他所學的中西方教育理論貫穿起來,應用于當時中國的教育實際,最終形成了其獨樹一幟的人民大眾的生活教育理論,他本人也成為我國現代教育史上偉大的教育家[12](P1)。大師的境界也許不是我們這些平凡的學者所能達到的,但是他們為我們樹立的榜樣,卻是可以令我們追求的。面對困難迎難而上,追求學貫中西,以比較的眼光,分析研究各個歷史時期人類教育理論與實踐發展的實際狀況和發展進程,總結教育發展的歷史經驗,體察教育發展的客觀規律,尋找到教育的真諦,為解決當前教育問題提供啟示與借鑒,是筆者數十年來所孜孜以求的。生命不息,追求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