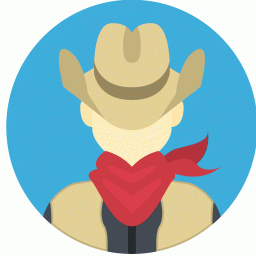陳小翠雜劇創作及其意義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陳小翠雜劇創作及其意義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本文作者:鄧丹作者單位: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
中國戲曲史上的女作家,有傳奇、雜劇流傳至今者不過十余人,其中絕大多數僅憑一二部劇作而留名,稱得上多產的,惟劉清韻和陳小翠二人。陳小翠(1902-1968),名璻,字翠娜、小翠,號翠侯、翠樓,別署翠吟樓主,浙江杭縣(今杭州)人,父為著名作家陳蝶仙(號天虛我生),兄陳小蝶(號定山)亦擅詩文、戲曲。陳小翠在當時主要以詩、畫名世,但其文、詞、曲、小說等皆不容小覷,鄭逸梅稱“在近數十年來,稱得上才媛的,陳小翠可手屈一指了”。[1]陳聲聰亦贊她“靈襟夙慧,女中俊杰”。[2](P.251)陳小翠自十六歲起開始在報刊、雜志發表戲曲作品,數年間共創作了《夢游月宮曲》、《除夕祭詩》、《黛玉葬花》、《自由花》、《護花旛》五部雜劇及《焚琴記》傳奇,①在女性戲曲史上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就劇作題材特點及采用的體制形式來看,小翠戲曲大多為傳統的傳奇、雜劇創作,可視作女性傳奇、雜劇創作的尾聲。眾所周知,在陳小翠生活的清末民初,文藝領域各種新舊力量激烈交匯,在急遽變化的社會現實中,她何以鐘情于這種古老的戲劇樣式,如何以之與明清以來戲曲創作的傳統相承接,是否于其中融入了她對于這一轉折時代的特殊感受、傳達出新的時代精神等等,都是值得探尋的問題。
一、“莫以閑情傷定力”[3]———《焚琴記》、《自由花》中的婚戀反思
陳小翠的《焚琴記》傳奇和《自由花》雜劇表達對愛情和婚姻問題的思索,其題材在二十世紀20年代中國文壇上較為常見,但卻是小翠戲曲中少見的直接表達作者對當下社會現象的反思的劇作。
《焚琴記》演蜀帝之女小玉與乳娘陳氏之子琴郎情緣幻滅事,其藍本為民間流傳的“火燒祆廟”故事,本事見于《淵鑒類函》卷五十八《公主三•玉環解》引《蜀志》:昔蜀帝生公主,詔乳母陳氏乳養。陳氏攜幼子與公主居禁中約十余年,后以宮禁出外。六載,其子以思公主疾亟。陳氏入宮有憂色,公主詢其故,陰以實對。公主遂托幸祅廟為名,期與子會。公主入廟,子睡沉,公主遂解幼時所弄玉環,附之子懷而去。子醒見之,怨氣成火而廟焚也。[4]
元明俗文學作品中,“火燒祆廟”作為男女情緣不遂之典屢為作家所化用,如《西廂記》有云:“白茫茫溢起藍橋水,不鄧鄧點著祆廟火。碧澄澄清波,撲剌剌將比目魚分破。”又《倩女離魂》:“全不想這姻親是舊盟,則待教祆廟火刮刮匝匝烈焰生,將水面上鴛鴦忒楞楞騰分開交頸。”“祆廟火”多用來形容使相愛者分離之力量。陳小翠在民初以傳統戲劇樣式演繹這一故事時,則賦予這一流傳已久的故事新的意涵。《焚琴記》保留了“火燒祆廟”故事前半部分情節,在后半部分作了較大修改和發揮:陳氏帶著兒子琴郎約見公主的密信入宮,不想此信為宮娥寶兒拾得,且將之映摹一份,欲向蜀帝告發。琴郎聞得公主將入廟拈香,先至廟中等候,困倦睡去。不久公主前來,兩人互訴衷腸,公主以所佩玉環相贈,以堅來世之約。蜀帝得知消息,下旨將琴郎鎖入廟中放火燒死,而公主被蜀帝鎖入南樓,愁病交加,嘔血而亡。寶兒后悔向蜀帝報信,偷來軟梯將琴郎救出,與陳氏會合后三人一同隱居山谷。琴郎夢見為一女子相引,至與公主相見,公主冷顏相對,后又化作厲鬼,琴郎頓時驚醒。不料醒來后母親告知焚廟、隱居諸事皆為一夢,公主其實畏禮而未曾至祆廟赴約,現蜀帝下詔將公主下嫁琴郎,琴郎喜不自勝,但瞬息之間,歡慶婚事的鼓樂聲變為宋兵進攻的軍鼓聲,諸人皆被驚散,原來又是一夢。此時春夢婆出面度脫,全劇在琴郎“愿天下的熱中人齊悟省”(《雨夢》)的感慨中結束。
原故事中,令相愛者情緣難遂的是天意,焚燒祆廟之“火”為陳氏子之欲火、怒火,表明人內心之情愿、欲望具有對抗天神安排的力量;而《焚琴記》中的“火”,則代表了一種否定、破壞人內心情欲的外在力量和人為因素。但是,不同于王實甫、鄭光祖等作家對“祆廟火”的控訴和張揚情性的立場,陳小翠構思蜀帝派人焚廟的情節其實更希望對公主、琴郎的越禮之“情”做出警示。在演述琴郎寄信的《病訊》一節之前,陳小翠增添了公主自抒懷抱,表達對琴郎思念之情的《閨憶》一出,抒寫女性情欲;當陳氏提出約會之請時,公主以“白珪應守女箴篇”為由并未應允,表現出內心情與禮的掙扎,但最終因情廢禮,如期赴約;原故事中公主赴約之后,雖未遂情,但未受到懲罰,而陳小翠令公主竟由此陷入絕境,懷抱遺恨,殞命南樓。這些改動,蘊涵著陳小翠欲借公主純潔愛情之悲慘結果來否定“情”的意圖,如第一出《楔子》中所言:“可知‘情’之一字,正是青年人膏肓之病。可笑近來女子,爭言解放,惟戀愛之自由,豈禮義之足顧,試看那公主以純潔之愛情,尚爾得此結果,況下焉者乎?”[5]作者對近來身邊的女子執意追求自由愛情甚至置禮義于不顧的舉動有所不滿,認為即使是像公主與陳氏子之間純潔、真摯的癡情也會令人備受煎熬,遺恨重重,遠不如忘情、超世能帶給人真正的自由和快樂。所以,劇末琴郎所感慨的“從今參透虛無境,好向那蝴蝶莊周悟化生,嚇,愿天下的熱中人齊悟省”正是全劇大旨,是改編者面對當時頗具病態的社會風氣、道德氛圍而提出的治療良方。
在進入對“火燒祆廟”故事的議論之前,《楔子》中有較長一段作者對當時社會風氣及國勢時局的議論,在陳小翠眼中,“世界潮流愈趨愈下”,十里洋場的男士競相以文明為幌子,女子以自由解放的謊言拋了家鄉,但又沉迷于醉生夢死的風流生活中,總而言之:[沉醉東風]一迷價煙昏霧漲,鬧昏昏生死全忘,沒頭蠅撞入迷天網,絕塵馬斷了藕絲韁。有多少魅魑魍魎,使出他千般伎倆。管什么禮義全忘,斯文全喪,便南山罄竹,寫不盡他奇形丑狀。
咳,算來年呵,[雁兒落]早則是好河山,歧路亡羊,挽西江洗不凈人心腌臜,更效法歐西說改良。皮毛可有三分像,倒把那國粹千年一旦亡。國事沸蜩螗,私怨還分黨,海橫流,倒八荒。堪傷,憑若個中流撐?何當,向中州學楚狂![5]陳小翠的這番議論表達了她對新舊過渡時期社會政治、道德等許多方面的看法。她在自己所生活的作為新舊思潮交匯點的上海,看到了過度的自由給青年男女帶來的強烈刺激和給傳統道德帶來的巨大沖擊,她認為舊道德(“禮義”、“國粹”)的淪喪是社會腐敗、落后的根源,喧囂一時的政治改良并不能真正挽救祖國危亡,反而會給國勢帶來更多紛爭,造成更多混亂。可以說,陳小翠與許多與她同時的作家一樣,是維護“以德治國”傳統的舊道德維護者。
與《焚琴記》問世時間相近的《自由花》雜劇也表達了陳小翠對新文化運動中婦女解放思潮的反思和對西方引進的自由平等學說的質疑。劇中受盧梭自由學說鼓動而逃離家里選定的舊婚姻、與心上人私奔的女學生鄭憐春,最終因所托非人而被心上人的悍妻賣入青樓,下場可憐。對鄭憐春的悲劇,陳小翠持同情態度,但是,作者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了“自由”,她讓鄭憐春一再感嘆:“世亂如麻,驚醒深閨井底蛙,說什么自由權利,愛國文明,羞也波查!口頭禪語盡情夸,倒變做了沒頭蠅蚋無韁馬!”“俺本是白璧無瑕,也只被盧騷學說誤儂家!”[5]在民初題材與此相近的吳梅《落茵記》、《雙淚碑》雜劇中,作者亦將造成此類悲劇的原因歸之于“自由”,這種對“自由”的批判態度看似是對女權、對婦女解放運動的否定,其實不然。吳梅在《落茵記》自序中說:“方今女權淪溺,有識者議張大之,是矣。顧植基不固,往往又脫羈覂駕,而身陷于邪慝,愚者又從為之辭曰:‘不得已也!’嗚呼,守身未定,他何足道!一失千古,誰共恕之?”[6]可見他并不反對女權和自由,只是希望女子對待自由選擇應該持慎重的態度,莫因“自由”而導致道德淪喪,導致邪惡,最終毀滅自己。如果說,吳梅對新舊交替時期的女性特別提出“守身”的要求體現著較為保守的文化觀念,那么,從女性立場和角度出發的陳小翠,則對同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她在《焚琴記》中否定“情”、強調面對“情”時的理性自制,在《自由花》中反對女子追求自由而走向自我毀滅,皆并不完全是出于對傳統倫理道德觀念的強調,更是基于女性對自我尊嚴的愛惜和堅守、對獨立人格的向往和爭取。
二、“倦鶴忘機品自高”[3]———四部短劇與陳小翠的自我呈現
《夢游月宮曲》、《除夕祭詩》、《黛玉葬花》和《護花旛》是四部單折雜劇,盡管篇幅短小,劇情簡單,但卻以夢、詩、花、仙等重要因素為媒介,共同實現了陳小翠在劇中的自我呈現。
《夢游月宮曲》是現今可知小翠發表的第一部戲曲作品,《文苑導游錄》將其原作與陳蝶仙正譜本同時刊出,不難發現改本與原作不僅在曲詞上有較多改動。劇作核心情節為女主人公為仙子所招,往廣寒宮游歷,聆聽霓裳法曲。當她正為月宮仙境所迷醉之時,適逢嫦娥歸來,仙子慌忙將其送回,由此驚醒,原來是南柯一夢。
關于女主人公入夢的緣由,改本為小翠面對秋宵圓月,想象天上廣寒宮之景致必定勝卻人間無數,故心生無限向往。原作的鋪敘則與此不同,女主人公觀賞《桃源圖》,對畫中所描繪的板橋茅屋、雞犬怡然之境十分神往,隨后即入夢,顯然夢游月宮之舉是她脫離紛紜塵境,向往隱居樂境之愿望的滿足。在小翠早年的詩作中,恰也可看出她對于隱居興趣濃厚,其《隱居》詩自注:“余每見荒僻之境,輒起幻想,以為得隱居此間,與靈鬼山狐談玄理于風清月白時,亦一樂也。”如果將《隱居》與小翠其他創作時間接近的詩作如感慨國勢的《感賦》、自傷身世的《午夜書懷》、《歷劫》等參讀,便知其脫離紛紜塵境之念并非發自深閨的無病呻吟,而是基于面對新舊轉折時期社會混亂狀況的厭倦和無奈。其《感賦》詩云:滄海橫流倒八荒,眼看歧路竟亡羊。過江名士嗤周顗,夾袋人材笑孟嘗。不信秋云能作雨,更無東海易成桑。跳梁跋扈今猶昔,越膽年來已厭嘗。
滿目瘡痍感不禁,漫天烽火郁重陰。經霜垂柳凄涼色,過雨秋蟲得意吟。豈有禮緣驕士設,從來患為摸棱深。賈生慟哭成何濟,治國難尋砭骨針。[3](卷二)《感賦》重在描繪世態,《午夜書懷》、《歷劫》則為自我寫照:年來失意感頻仍,枯寂真同入定僧。雨歇檐牙鈴作語,風來窗隙鬼吹燈。才能壽世何妨死,貧尚驕人信可憎。自笑孤高成底事,天涯潦倒女陳登。(《午夜書懷》)[3]歷劫歡場二十年,夢魂飛絮落禪邊。名心淡似煙中柳,詩思衰于秋后蟬。已分此生竟漂泊,何堪愁病尚纏綿。豪情不逐華年改,瘦盡形骸肯自憐。(《歷劫》)[3]在陳小翠看來,面對紛紜亂世,傳統文人已無可作為,有的甚至走向道德的淪喪;盡管不為世所重,但她仍愿保持著一份傳統文人的節操與傲骨。正因如此,她在《除夕祭詩》雜劇中塑造“孤高”、雖窮愁潦倒但“豪情不改”的詩人賈島便有了“借他人酒杯,澆胸中塊壘”的意味。
賈島除夕祭詩的故事在辛文房撰著的《唐才子傳》中有載,據說每至除夕,賈島“必取一歲所作置幾上,焚香再拜,酹酒祝曰:‘此吾終年苦心也。’痛飲長謠而罷。”[7]發抒的是知音難遇的感傷,而陳小翠《除夕祭詩》更加突出賈島對塵世不公的控訴和文人失路的嘆息,劇作以[醉扶歸]、[皂羅袍]、[好姐姐]三支曲子摹寫賈島心聲,從酣暢淋漓地抒發壯懷豪情到憤人間不公,再到無奈面對落魄的現實,對主人公性格及心聲的摹寫十分富有層次性。陳小翠筆下的人物,多與詩歌有親密關系,如《夢游月宮曲》中的小翠“耽情詩酒”,《黛玉葬花》中的林黛玉以詩祭花,而在《除夕祭詩》中,詩歌是更為重要的媒介,不僅是賈島的進身之階、獲罪之由,更以知心之友的身份實際“扮演”了劇中另一重要角色。這三部發表于1917-1918年、小翠較早時期創作的劇作,其中人物已借由詩歌這一媒介,呈現出共有的孤獨清高心態和清奇的人格特征,而這種心態和人格特征,與陳小翠早期詩作中的自我表達正可相印證。
如果說,“詩”在陳小翠作品及生活中是她呈現自我人格的重要途徑,那么,“花”因為與女性生命、青春的對應關系,寄托著她對于女性生命的愛惜和同情,表達了她的女性生命價值觀。在《黛玉葬花》、《護花旛》以及其他詩詞作品中,陳小翠一再表達對于花的熱愛和憐惜,認為女性命運同落花一樣,難逃飄零受摧殘的宿命。《護花旛》的本事為唐代處士崔玄微的傳說,在《博異志》、《酉陽雜俎》中皆有載,但陳小翠做了兩處明顯的改動,一是將受邀參加花神宴會并得到她們危難時重托的主人公由一名男性改名為“謝惜紅”的女子,那么,劇作的主題便由表現男性對女性的庇護變為了對女性間情誼的敘寫;第二,封十八姨對諸花的迫害起源于她與一位小花仙的矛盾,這一矛盾在原故事中是因封十八姨失手打翻酒杯,污了小花仙的衣裳而起,但陳小翠的《護花旛》卻塑造了一位“鄙逢迎心清骨清”的小花仙形象,她在封十八姨大施淫威、叫囂眾姊妹的榮辱皆掌握在她手中時,鄙視眾人的唯唯諾諾,敢于出言頂撞,表現出難能可貴的骨氣和勇氣。賈島、小花仙以及《黛玉葬花》中的林黛玉等形象隱含的清奇、剛烈的人格特征和對獨立人格的爭取可以說正是貫穿于陳小翠作品始終的精神命脈,她通過《自由花》中鄭憐春、《焚琴記》中蜀帝公主的遭遇所表達的對自我尊嚴的維護和強調,與此正相呼應和補充。
晚清民國時期,劇壇出現了大量取材于古代小說筆記、古代經史及其他文獻的傳奇雜劇,這些劇作演繹古人陳事,與現實的關系較疏遠,從表面看不出作者對當下的感受,正如論者所言:“絕大部分的此類作品的創作,當系作者興趣愛好的較直接的反映,很難發現其中有什么題外之旨和象征意味。”但因其直接反映作者的興趣愛好,故而可視作“考察與認識作家性情志趣、個性特征的重要材料”。[8]陳小翠的幾部短劇正是如此,作者在閨中創作這些作品時,生活閱歷有限,筆力較稚嫩,并未表達較為深厚的意涵,但是卻在筆下人物身上,構建并呈現著自己的人格理想,這便是其劇作的重要價值之所在。
三、“蛾眉絕學繼宗風”[3]———作為女性戲曲創作殿軍的陳小翠
中國戲曲史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是男性創作戲曲的歷史,富有戲曲創作才華的女性直至明中葉后始逐漸浮出歷史地表。盡管自明中葉至民初的數百年中,女作家留下的劇作數目終屬寥寥,但隨著重新發掘女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熱潮的興起,馬湘蘭、葉小紈、王筠、吳蘭征、吳藻、顧太清、何佩珠、劉清韻等女作家越來越受到學界關注。陳小翠生活的清末民初,傳奇雜劇的生存土壤已發生質的變化,但她仍鐘情于傳統的戲曲樣式,以之表達個人在急遽變化的社會現實中對這一轉折時代的特殊感受和思索,同樣為戲曲文學史貢獻了閨閣操練的經驗和成果。作為明清女性戲曲創作歷史鏈條末尾的重要一環,陳小翠的劇作既提供了新的思想內容,也體現出與明清尤其是近代女性戲曲傳統的承接,理應受到更多重視。首
先,就劇作所采用的藝術手段來看,陳小翠戲曲中的夢、詩、花、仙等敘事要素,在明清女性戲曲中較為常見,其中對夢境的表現尤為突出。我國戲曲多寫夢,因夢境不受時空的限制,可以給作家留下馳騁想象的廣闊天地,蟄處深閨的女劇作家尤喜以之抒寫個人在現實社會中未能滿足的欲望,如王筠《繁華夢》設想自己在夢中換身為男,經歷榮耀之仕途,獲取美滿之婚姻;何佩珠《梨花夢》借夢境容納/傾吐作者婚姻之外的情感渴求;顧太清《梅花引》以男女主人公戀情在仙界、人間、夢境中的幾經延宕隱寫作者與亡夫坎坷的婚戀經歷。可以說,夢作為戲曲表現性的舞臺意象,雖肇始于男性戲曲家所建立的傳統,但在女劇作家的筆下,卻更多的傳達出了女性的夢想與心聲,真實而細膩的呈現了女性的生存實況。陳小翠發表的第一部劇作《夢游月宮曲》即以夢境為全劇的重要構思,寄托著作者的人生理想和精神追求,至《焚琴記》更將“夢”作為推動情節發展的關鍵因素,主人公多番入夢、數次警醒的夢中套夢的情節遠較原故事本事為復雜,在中國古代戲曲中也十分罕見,它表明陳小翠非常重視以這一敘事手段來表達個人思索、傳遞某種理念。然而,若以舞臺演出的角度來考量,夢中套夢的表現手法對敘事的明晰度勢必會造成影響,從而影響到主題的凸顯,在一定程度上也削減了戲曲的藝術表現力,呈現出案頭化的創作傾向。
其次,陳小翠通過筆下的戲曲角色表達了強調個性尊嚴,展現高情逸致的人格理想,其精神意趣與吳藻、劉清韻等近代女曲家的作品正相近。明清女劇作家中多有具散朗的林下風致者,她們筆下不時呈現的是瀟灑無脂粉氣的筆墨文字,尤其至近代,吳藻、劉清韻、古越嬴宗季女等女作家的劇作中更包含著對女性社會角色不公平所作的思考和對女性尊嚴的強調。吳藻以詞、曲、畫名世,曾自繪《飲酒讀騷圖》以手持《離騷》不釋卷的形象示人,并撰《飲酒讀騷圖曲》(即雜劇《喬影》)抒寫個人懷抱,她對自己婚姻的不滿成就了自我獨立、孤高的形象。
劉清韻的《小蓬萊傳奇》十種及新發現的《望洋嘆》、《拈花悟》兩部劇作亦一掃傳統婦女文學的纖柔婉弱之風,既含清妙秀雅之詩筆,也有勁直豪逸之詞情。陳小翠對吳藻這位錢塘才女也推崇備至,鄭逸梅《藝林散葉》記:“陳小翠對清代女畫家,認為以吳藻為最杰出。”[9]俞劍華評小翠“書畫都很有功力。……于淡雅處時露其俊拔挺健之姿”。[10](P.127)
足見她不同一般的藝術追求中也包含著張揚自我的意味。不僅僅是畫作,小翠戲曲中也可看到吳藻的影響,《除夕祭詩》雜劇中的[皂羅袍]曲,采用“俺不愿……也不愿……不愿……俺只待……俺只待……”句式,即仿吳藻《喬影》中謝絮才自抒懷抱的[北雁兒落帶得勝令]而作,后者用一連十個“我待……”句法排比的曲詞,令人物的思緒如狂風驟雨般洶涌噴發,與此相對應的,正是作者反抗束縛、發展個性、追求理想的堅決態度。吳藻的志愿,并非少數女作家心目中的男兒夢,也不是傳統女性文學中的美滿婚姻,而是才情的展示與實現、精神的獨立與張揚,這是女劇作家在近代曲壇的振聾發聵之語,劉清韻、古越嬴宗季女的劇作中雖也透露出這樣的內容,但直至陳小翠筆下,這一理想方才有更為清晰的呈現。
陳蝶仙在《翠樓吟草》序中介紹小翠的閨中生活云:“(小翠)日惟獨處一室,潛心書畫,用謀自立之方。其母嘗曰:‘吾家豢一書蠹,不問米鹽。他日為人婦,何以奉尊章?殆將以丫角終耶?’璻則笑曰:‘從來婦女,自儕廝養,遂使習為灶下婢,夫豈修齊之道乃在米鹽中耶?’”[3]可知她在閨中時便是一位不甘于受裙釵之羈縛、有個人獨立之追求的女性。她與湯念耆的婚姻并不幸福,但中年時期與顧青瑤、馮文鳳、顧飛、余靜芝、楊雪玖等閨秀于上海創辦女子書畫會,不僅于詩詞書畫皆大有精進,更重要的是令自尊、自立之個性特征和追求得到充分施展。陳聲聰評陳小翠詩“郁有奇氣”、“洋洋灑灑,下筆自如,無矜持拘泥之態”[2];劉夢芙評小翠詞“詞筆極細膩靈幻之致,吐屬名雋,風調高華。且頗喜標新立異,常于柔美纏綿之旋律中迸發強音,婀娜剛健,一體混融”。
其藝術追求與高潔人品可見一斑。據云陳小翠與陳蝶仙的弟子、詩人兼戲曲家顧佛影早年頗相契合,但未得到陳蝶仙成全而致小翠另嫁,繼而佛影別娶,兩人詩翰往來幾十年,留下不少酬唱之作。其中一首作于抗戰勝利之后的《大風雨日寫示大漠》詩中有云:“莫以閑情傷定力,愿為知己共清談”,透露出小翠對待這份情的理性自制的態度,故而兩人能夠坦蕩相處幾十年。陳小翠并不以婚姻美滿為人生的重要旨歸,而一生汲汲于個人尊嚴與獨立之追求,在她的作品中很難見到兒女柔情、情長恨多之態,而常見豪邁灑脫、清雅俊逸的曠達之氣,與吳藻在人生經歷和藝術追求方面多有相似。
陳小翠的傳統文藝創作經歷貫穿其一生,其詩詞、散曲、書畫等隨著時間的歷練而愈趨成熟,然而其戲曲創作卻止步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究其原因,一方面與大的創作環境有關,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之后,整體政治文化環境的巨大變化對傳統文藝樣式的創作帶來很大沖擊,傳奇雜劇創作自此失去了往日的繁榮。另一方面,就陳小翠自身的創作經歷而言,她早期從事戲曲創作明顯受到家庭氛圍的影響,在其父陳蝶仙周圍,形成了一個父子(女)、師徒相互切磋、共同進步的創作氛圍,陳蝶仙及其子陳小蝶、弟子顧佛影的傳奇雜劇創作在晚清民國戲曲史上都留下了值得書寫的一筆。即以戲曲題材的選擇而言,陳小翠的《自由花》雜劇也是受到陳蝶仙《自由花傳奇》的影響而作,后者通過描寫因追求自由戀愛、自主婚姻而上當受騙的女子的不幸遭遇,表達了對當時頗為流行的新式愛情婚姻觀念的看法,陳小翠《自由花》雜劇關注的正是與此劇相似的具時代特點的問題。在戲曲創作風格方面,陳小翠早期的作品浪漫、俊逸的風格較突出,不無逞顯才學的痕跡,戲曲文備眾體,適合以之逞顯才學、磨練文學創作技巧;閨中女性在抒情言志時往往不愿意沒有阻隔地表現自己,戲曲代言體的文體特性正好可以滿足她們的這一要求,故而成為青年小翠所熱衷的體裁,而經歷了數十年家國巨變和人生風雨的磨礪之后,陳小翠的作品逐漸顯現沉郁、深婉的面貌,多自肺腑自然流出,她對于曲的興趣主要通過散曲表現出來,而疏淡了戲曲必備的經營故事、安排角色、調度場面等指向舞臺搬演的東西。陳小翠直至解放之后,仍多有散曲問世,且蘊含的情感愈加真實深厚、藝術技巧愈加純熟自然,正是專注于曲之長于抒情的文體特性了。盡管如此,陳小翠在青年時期所留下的這些戲曲作品,因構建并寄托著女性的人格理想,承接并進一步發揮了近代女性戲曲創作傳統,在中國戲曲史上應當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