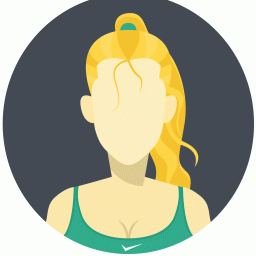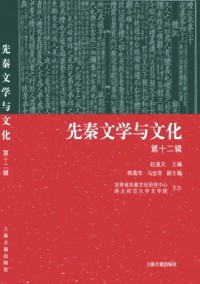先秦儒學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先秦儒學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先秦儒學博大精深。它是孔子、子思、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學派的偉大政治哲人們,站在春秋戰國這一特定的歷史時段之上,從倫理尤其是從政治的高度,對“三代”、“三王”甚至于更早以來的幾千年中國古代社會豐富倫理和政治生活經驗的概括和總結、反思與批判,凝聚著其思人所未嘗思、發人所未嘗發的智慧,而且這樣的智慧既是不可缺或又是不可多得的,永遠值得我們后人深思和玩味。
這一切當反映了他們對人生或存在的根本意義的不斷追索,對人世間的苦難悲天憫人般地繾綣之心和眷眷之情,對流俗之見的深刻質疑和勇敢挑戰,以及對當下經驗的全面審視、批判與超越;也反映了他們在諸如“新”與“舊”、“生”與“死”、“理想”與“現實”、“治亂”與“存亡”等等之間進行政治選擇的承負與焦慮[1];與此同時,這一切,更反映了2500多年前的老子、孔子、莊子等等中國偉大的政治哲人們,對人類生存與發展道路的大膽探索、對安定團結與有序親和之自然—社會秩序的有益訴求以及對整個人類美好、幸福生活的無限憧憬、追求和向往;或者用尼采的話說,對整個人類自然權利與歷史的永恒復返和回歸。
作為一種能夠在幾千年中國如此動蕩不安的社會歷史進程中從總體上維系著如此眾多人口、維持著如此安定秩序、保持著如此文明進步以及把偉大的中華民族凝聚成一個堅強而有力的整體并使之曾幾何時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長達幾千年的“先王之道”,作為一整套從幾千年的歷史中從容地走來、又從容地走過幾千年歷史的比較成形的傳統價值理念和堅強信仰體系以及作為中國政治思想史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份不可或缺的重要遺產,先秦儒學具有普遍而恒久的魅力。它不僅形成于以往的歲月里、影響過中國二千多年的社會政治生活,而且仍在一定程度上正影響著我們今天的社會政治生活,并且它還將不同程度地繼續影響和關照到未來中國社會的一切政治與生活——這大概就是以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永恒持久的頑強生命力之所在吧
曾記否,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上,那些個一度被稱作“國粹派”者曾指責當時的革命是“全法歐美而盡棄國粹”并且要大聲疾呼“祖宗之法不可變”——于今觀之,惡名之下,其情可憫——然而,君不見,當下中國社會之某些個具體而生動的文化生活情境和場景,的確倒極像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美國社會了:城市郊區化、住宅別墅化、生活消費化、嬉皮士與雅皮士、頹廢/垮掉的一代,媒體鋪天蓋地、無孔不入,形形色色、林林總總的人造娛樂活動讓人欲哭無淚、欲罷不能,工農兵學商,一切向錢看以及“有奶便是娘、無錢休稱爹”等等……然而,時至今日,人家卻是正在日益走出后現代并從此而逐步走向傳統與保守,而我們則是正熱衷于進入,前呼后擁、喧騰嘈雜,有如過江之鯽。那么,對此,在這里,我們似乎還可以反過來進一步套用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偉大詩人但丁的這樣一句話,生動而形象地作如是說:“走人家的路,讓自己說去吧”。而其最終結果到底會怎樣,今天看來,若我們可以用蘇格拉底的話說,就是“只有天知道”。
當下漢語思想界對先秦儒學研究無疑已陷入到一種“過于零碎、過于簡單化、過于平面化”的總體研究狀態,全然業已與先秦儒學本身所具有的豐富內涵及其在昨日、今日乃至于明日中國社會生活中已經起到的或顯而不隱、或隱而不顯的作用及其必將產生的這樣或那樣的不同影響,便顯得很不對等、很不和諧,同時亦顯得很不相稱。但其中的問題卻是,人自不覺。這正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百姓日用而不知”。要知道,當下無疑已是一個思想完全失去了高度的時代。牟宗三先生當年曾不無沉痛地感慨于“一個沒有圣賢的時代”;時至今日,無疑則更是“沒有大師的時代”,而有的只是“日用而不知”的“百姓”而已。孔子嘗有言曰:“朝聞道,夕死可矣”[2]。但其中的問題卻依然是,今天又有哪一個學人愿意而且能夠做到這一點?而且又有哪一個能夠做到“不降身,不辱志”呢?
盡管時至今日,我們仍然會看到,與此相關的研究工作還在繼續地開展著;同時,與此相關的研究成果也還在不斷地被發表,但從中我們卻已很少會看到,有哪一項與此相關的研究能夠做到獨辟蹊徑,從根本上已擺脫掉了這種“零碎”、“簡單化”、“平面化”的思想研究窠臼——當然,從中,我們也很少會看得到,有哪一項與此相關的研究成果能夠真正做到獨辟蹊徑、別有洞天,能夠真正做到自圓其說、獨善其身以及能夠真正做到從根本上全面而系統地徹底解決了“儒學”這一中國傳統政治哲學思想史上的基本命題。而且,其中的道理很簡單:對此,若僅憑當下這樣一種浮躁、瑣碎、“簡單化”、“平面化”,或者僅憑“撿起芝麻而丟掉西瓜”、“采其華而棄其實,識其小而遺其大”這樣一種難堪的學術研究狀態,則其將勢必永遠是做不好、也做不了的。由此看來,思想學術研究仍需沉下去、立起來,固守住本位,耐得住寂寞,仍需我們一代又一代學人們的不懈努力。
盡管時至今日,或者說尤其是時至今日,我們總可以看到,與此相關的大量研究成果仍不時地被訴諸文字、付諸報章,見諸刊物、雜志或者網站之上。然而,這一切的一切,正有如曾經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的哲學思想世界獨占鰲頭、獨步一時的風云人物李澤厚先生之所言,“文本之外無他物”。倘若對此詳加審視,則其中多半卻是一個個“只有能指、并無所指,無實在、無客觀、無本質”[3]的東西被不厭其煩地抄來抄去,多半卻是一簞簞看似相異而實則相同或相近的“剩飯”被樂此不疲地炒來炒去。然而,究其實,則其中多半卻是“共時性”而非“歷時性”的東西,多半卻沒有多少或者說根本沒有真正值得借鑒或者保留的余地。正所謂“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是也。而其一般結果卻往往是,一旦文章被看完了,或剛剛被看過了一半,甚或僅僅被看了個開頭,其所謂的“價值”與“意義”,也便由此而宣告全面終結。于是乎,我們為此而由衷地希冀:這一切的一切,再也不要繼續成為近百年來直至今日左右中國哲學家族歷史發展的一條根本宿命了而且再也不要如此這般地繼續下去了;否則,我們真的不知道中國的學術將往何處去?既如此,于是乎,我們還可以用當下的一句比較時髦的話語問:中國的哲學如何能夠走向世界,而且又如何能夠徹底地告別自說自話、自言自語并從此而真正地實現“與世界接軌”呢?今天看來,這些個問題無疑已是太大了,以致于,到頭來,我們竟一個都回答不了;或者說,一個也都不能回答。真是的。
曾子嘗有言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然則夫子不曰“其旨遠,其辭文”乎?不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3]乎?——時至今日,亦正有如李澤厚先生之所言,“世紀末的頹廢,正好碰上后現代”——于是乎,我們會看到,今天的學人們,他們或者張嘴“德里達”,或者閉嘴“利奧塔”,再不就是“鮑德里亞”或者“勒維納斯”;而且,我們完全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時至今日,中國的所謂“后現代者們”,已差不多快“找不著北”了,而且大有欲將古之前賢往圣置于所謂“解構主義”的泥淖之勢。所謂的“與時俱進”,到底是什么意思?當你把一切的一切都看得不名一文或者一文不值時,當你可以長命百年、萬世千年或者可以把一切的一切都看作是可以時過境遷時,那么你大概就可以“與時俱進”了。但問題卻是,這又如何可能呢?到底誰能真正做到“與時俱進”呢?而如此做法,又到底會給我們帶來什么?全盤地否定一切,人為地中斷傳統,這對我們來說,究竟會有什么好處呢?道之難言,已令古之前賢往圣們浩嘆不已,難道我們還要人為地阻隔的攔斷這一人最基本的生存情境么?難道“怨恨”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可以掩蓋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可以抬高自己原本卑微的地位和卑賤的命運么?民眾/奴隸就是民眾(themass),難道可以打著“人民”的旗號來反對主人/人民?
既如此,試問:人的敬意何在?人的敬畏焉存?而人的良知、良能和良心,又將飄落至何方?人的精神的家園到底安居在哪里?而人之成為人、成為其所是的心靈之花,又到底要花開何處、花落誰家?莊子百年無家,而我們又怎么樣?
以“全面解構”為本質特征的所謂“后現代主義”,如今正悄無聲息地一步步向我們走來。于是乎,適逢這一特定歷史時代的人們大概便已不必再去小心翼翼地尋覓、憂心忡忡地求索——這是因為,一切的一切似乎差不多均已被解構成了無數塊難以撿拾的碎片,破鏡重圓,破鏡難圓;于是乎,“宮闕萬間都作了土”,什么理想與信念以及什么價值和追求,轉瞬間,不是折戟沉沙、黯然銷魂,便是“檣櫓灰飛煙滅”。時至今日,竟都成了一堆堆迂腐可笑、不名一文的“破爛貨”,倏忽其來、倏忽其去,是那般輕飄飄的,或至少已不再有如往日那般莊嚴、肅穆、神圣或者凝重;于是乎,今天的人們大概便已不必再去像以往那樣地苦苦相盼、孜孜以求,希冀重塑或者祈望救贖——這是因為“此地乃真理,當下即實在”。于是乎,“玩的就是心跳”,“游戲即為人生”;“跟著感覺走”,“過把癮就死”[4]。正所謂“人生如白駒過隙,忽然而已。”既如此,則“何必嘆息,何必留戀”?既如此,又何不“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既如此,又“何不瀟灑走一回”?其實,還說什么這個那個的,時至今日,不過只是“符號”、“符碼”或“游戲”,不過只是玩玩而已!又何必當真?民眾們盡可以沉湎于當下林林總總、形形色色的諸多“人造娛樂活動”中去,不思也不想,任憑著自己的那顆高貴的頭顱不停地在那里傻乎乎地搖啊搖地——就像幾分鐘前自己剛剛服用過幾枚搖頭丸似的。如果將自己對“道”的追求視為稻粱謀、作為自己的工作職業和吃飯的本領的話,那么這樣的學人最終也同樣是不可能找得到“道”的,他們勢必亦與民眾/百姓一樣,而“百姓日用而不知”一句話,也同樣是說給他們這些所謂“學人”聽的。
既如此,則甚矣哉!為可悲也。然而,又如之奈何?
既如此,則夫復何言?我們無言以對;當然,更無話可說。
有關于此,本文則認為,倘若人們心中的道德未泯、良知尚存,棲身于政治社會而非墜入原始叢林,那么他們便定然可以有目共睹;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相關文章的大量面世,從一個側面倒是可以進一步地說明,這一現象,時至今日,業已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今日漢語思想學術界的普遍關注。此外,還可以進一步地說明,時至今日,對先秦儒學、“道”的課題,確實有作進一步研究的必要。如此看來,這一所謂“真實的情形”,又是根本不同于李澤厚先生所曾經表述的“只有批判和解構,并無建設甚至嘲笑建設”[5]那樣一種“實情”——至少說,并不總像李先生在其有關的文字表述中所烘托和渲染著的那樣悲哀、凄惶、悲觀、厭世甚至絕望;或至少說,并不像李先生那樣的夸夸其談、夸大其辭。會說的,不如會聽的;會寫的,不如會讀的——然而,其中的問題卻是,要細聽和細讀。
古人有言曰:“人世有代謝,往來成古今”。——但在這一點上,本文則認為,即使是李先生本人,恐怕亦未能幸免——當然,至于其他諸人,則“自鄶以下”,更無足觀,亦似乎同樣不能幸免。《老子•第二十三章》中有言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人乎?”《莊子•養生主》中則亦有言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此之謂也。而今日之所謂“與時俱進”一語,在明眼人看來,其實也不過只是一句有關于“完美”與“永恒”的神話而已——這是因為,追求完美本身,即意味著一種不完美,一種極端的不完美;與此同時,也許正是因為這種不完美,古往今來的人們,才總是要不斷地充滿著夢想和渴望——夢想和渴望著完美與永恒、長生或者不老,夢想和渴望著自由、平等或者民主以及夢想和渴望著到底什么才真正是人類美好和幸福的生活。換句話說,蘇格拉底的哲學問題,自它產生的那一天起,似乎便從來就不曾改變過。這一點不容懷疑。難怪乎我們雖檢索古文,但到頭來,卻總是找不到這樣一個詞匯呢!因此,對當代某些學者或者政客而言,不論其出于何種不可告人的目的,也不論其為此而如何絞盡腦汁、搖唇鼓舌,使出其渾身解數,當然更不論其為此而又如何生拉硬扯、牽強附會、矯揉造作地極盡粉飾、夸張、渲染之能勢,以備一時一地、彼時彼地或此時此地之需;但最終結果必將應驗這樣一句古話:“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沒有辦法,人世間的所有一切、萬世萬物,無一不是一種“偶在”,而其生命也總是十分有限的——這一點,對任何個人而言,其實也都是一樣的;而且即使對整個人類來說,亦并不例外。誰能真正做到“與時俱進”呢?這是根本不可能的。
對此,今天的人們可以拭目以待;當然,他們亦可以靜觀其變——或遲或早,時間總會說明一切的。然而,這個時間,卻是長時段的——它可能不只是一時;當然,也可能不只是一世,但它卻不可能是永世的。我們有理由相信,好在人類有的是耐心,也有的是時間、精力、信心和勇氣,去憧憬、向往、盼望和期待,他們不僅要期待著心想事成、諸事順遂,而且也要期待著美夢成真、舊夢重圓;與此同時,他們更要期待著真實而非虛假、自由而非控制、平安而非恐懼的真正美好和幸福的生活,并為此而牢牢把握著此在、當下以及今生今世而非來生來世彼岸性的幻夢與空想。然而,他們最終把握住了嗎?或者說,他們曾經把握住過?或者還可以這樣說,又會有誰能最終真正地把握得住呢?偶然性是無處不在的。因而回答也總是否定的——誰都不能,誰也不會。然而,盡管如此,但他們卻仍有機會進一步、持續不斷地這樣“試錯”下去。是是非非,非非是是,對對錯錯,錯錯對對,窮達以時,與時俱化,“得時鵲起,失時蟻行”,循環往復以至無窮。重要的是嘗試,至于最終是否能成功,倒顯得是次要的事。不可以成敗論英雄。
從認知上看,隨著在中國傳統文化大旗之下的那些個關涉著“先秦儒學”的林林總總、似是而非的字眼長期廣泛而深入地被傳抄和使用,一部先秦儒學本身,似乎在邏輯上已順理成章地演變為后來的閱讀者們所熟知的東西。然而,問題是,熟知未必真知。這一點正有如黑格爾所曾說過的:“一般人平時所自以為很熟悉的東西”,其實又“恰好就是他所不真知的”[6];而成中英先生,則亦明確認為,“先秦儒學是儒學發展的原初階段(公元前6世紀—公元前4世紀),對這一階段的理解至今仍未盡完全。”[7]事實上,也正是如此,正是這樣一種實際狀況。
然而,具體就先秦儒學的本質與核心——亦即就“先秦儒家中庸之道”而言,生活在當下的人們,似乎絕大多數已根本不知道其到底為何物:其中,有“賢者”或以為它是“和稀泥”、“墻頭草”或“和事佬”,是不辨是非、沒有原則的折衷主義;而為數眾多的“不肖者”們,則似乎更愿意不假思索地將其簡單而籠統地理解、認識,甚至最終要歸結為一種與儒家一樣陳舊、迂腐、呆板、不識時務、不合時宜的沒用的東西。于是乎,它在當日中國之情形,便正有如老子之所言:“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8]此之謂也——其中,所謂“上士”又身在何方?對此,我們不得而知;而我們所能知道的,則不過是周遭無處不在的對此“若存若亡”的“中士”以及對此報以“大笑之”的“下士”。笑吧,正所謂“不笑不足以為道”——對此,老子本人在這里不是已說得足夠明白了嗎?老子不是已經“不幸而言中”了么?既如此,那么我們還有什么其他更多的話可說呢?難道對此還有什么懷疑不成?要知道,這的確是當下的一種最真實的情形。若自己猶且不信,那么又如何可以讓別人信呢?如何可以“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其中的道理應當說是很簡單的:只有說服了自己才有可能去說服別人,只有感動了自己也才有可能去感動別人。
而,倘若欲使認知對象從“熟知”而變為“真知”,在本文看來,其實,似乎也沒什么大不了的,認認真真、踏踏實實地去做就是了;而且,時至今日,唯一而又有效的辦法,恐怕還是要再一次地追根溯源、從源頭之處重新做起——重新對其給予深入考量和全面省思。這正有如古人之所謂:“書上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與此同時,亦有如古人之所謂:“書讀百遍,其意自見”——一言以蔽之曰:“天道酬勤”。曾作如是說,“風物長宜放眼量”——其實,我們觀察人世間的任何事物,也都需要俯視和鳥瞰。就像我們坐壁上觀;或者說,更像我們透過飛機的舷窗上俯視和鳥瞰到的一樣。舉目四望、視野所及,滿眼的都是大千世界里縱橫交錯、橫七豎八地排放著的林林總總、形形色色的這樣或那樣的物什,什么房屋、樹木、道路、人與禽獸……等等等等,諸如此類的平日里無不讓我們十分在意的死物或者活物,此時此刻,在我們面前,又是變得那么的含混、那么的模糊,那么的沒有價值和意義以致于統統都不過變成了我們小的時候眼前和手中自由玩弄著的大大小小、奇形怪狀的積木而已——只有當飛機從天而降并且愈來愈接近地面之時,它們才會逐漸地變得如往日一般清晰,才會逐漸地變得如往日一般偉岸和高大,從而也才會重新恢復其如往日一般對我們來說不可或缺的重要、關鍵的價值和意義——這應當說是任何一位曾經坐過飛機的人都可能有過的一種真實而異樣的感覺。然而在這種感覺中,我們卻始終分辨不清,到底哪個是真、哪個為假?真真假假、實實虛虛,冥冥中大有“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深思杜鵑”那樣的一種感覺。此時此刻,已再有什么煩人的事兒會想不開,也不再有什么難解的怨恨會化不掉。張載嘗有言曰:“仇必和而解”。有趣的是,像馮友蘭這樣的中國現代著名思想家,在他們晚年的時候,總是會想到這句話。
有關于這一點,如果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地援引金景芳先生的一句話說的話,“據我了解,從當前各校教學和研究先秦史的思想來看,應該說有兩種形式:一種是照本宣科,拾人牙慧;一種是不斷創新,敢于向權威挑戰。我是向往后者。”[9]——金老先生的這番話,說得真是太好了。然而這段話難道不是一句實話、不是當下的一種最真實的情形?而且在今日大學的講堂之上,這種“照本宣科,食人牙慧”的現象還能說少么?到底又會有多少人可能說出自己心里面的話呢?若不說,長此以往,晚輩后學必將“無所措手足矣”,真不知到底該怎么辦才好。
其實,作為晚輩后學,我們又何嘗不是憧憬和向往著金老之所謂“后者”呢?
那就是——“原原本本”,“殫見洽聞”,還先秦儒學以本來面目;“創造轉化”,“綜合創新”,尋找中華民族遠去的精神家園,并使之走下廟堂,走出書齋,走向民間,走進新時代。絕不僅僅為學術而學術,而且也為人倫、為政治、為信仰,乃至于為自我的整個人生而學術——而這大概是因為,對人生而言,不管怎么說,信仰總是最為重要的吧?而且,它并不是其他任何別的什么東西,而是人類最高的價值追求,是人類生生不息、綿綿不絕的思想真諦與理論精髓之所在——對此,今天的人們,尤其是知識分子,不僅不應當報之以嘲弄、嘲笑或者嘲諷,而且,還應當向他們致以足夠的敬畏、敬重和敬意——這不僅是為他人,而且也為整個人類、為我們的后代,尤其是為我們自己——在此,千萬可別忘了,人總是帶著一顆會思想的高貴的頭顱而來到這個人世間、來到這個社會以及來到這個世界之上的;然而,在這個世界上,若不思亦不想,則豈不是枉費了這顆會思想的高貴的頭顱么?而且這又怎么行呢?
眾所周知,屈子嘗有言曰:“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汝其念之,吾其勉之。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這句簡短的話又是說得何其悲壯和慘烈呢?而且一個“道”字,真的有那么重要么?而且,它到底又是什么呢?程子亦嘗有言曰:“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11]此之謂也——讀了那么多年的《論語》、《孟子》,讀了那么多年的圣賢之書,研究了那么多年的先秦儒學,然而,到頭來,卻竟不知一個“道”字到底為何物?那么,書讀得雖多、研究得再深入,最終卻又有什么用呢?難道知識的真正價值僅僅體現在它本身是知識嗎?對此,今日之每一位讀書人似乎都應當毫不例外地靜下心來,捫心自問,有所思亦有所想——思想一下:自己到底在做什么?還有,這樣做,對別人,或者更準確地說,就算對自己,到底又有什么意義?要知道,由孔子本人所開創并以孔子為最大代表的先秦儒學,從來都是一門“實學”——一門“修己治人之學”。若不明乎于此,則是不是自己的完全誤識,是不是自己根本搞錯了呢?若如此,則既欺人又欺己、既誤人又誤己,這樣做,好么?
注釋:
[1]姜廣輝:《傳統的詮釋與詮釋的傳統》,《經學今詮初編》第2頁。
[2]《論語•里仁》。
[3]李澤厚:《歷史本體論/己卯五說》第142頁,三聯書店,2003年5月版。
[4]顧炎武:《日知錄》卷二。
[5]李澤厚:《歷史本體論/己卯五說》第144頁,三聯書店,2003年5月版。
[6]李澤厚:《歷史本體論/己卯五說》第144頁,三聯書店,2003年5月版。
[7]參見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一卷,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
[8]成中英:《第五階段儒學的發展與新新儒學的定位》,《文史哲》2002年第5期。
[9]《老子•四十一章》。
[10]金景芳:《創新與挑戰》,《我的學術思想》,吉林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11]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讀論語孟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