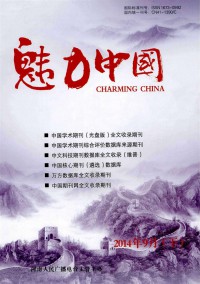中國工業(yè)經(jīng)濟發(fā)展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中國工業(yè)經(jīng)濟發(fā)展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chuàng)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一、關(guān)于中國農(nóng)村工業(yè)化的理論爭論與實證證據(jù)
在關(guān)于中國工業(yè)化過程的討論中,一個公認的事實是自改革開放以來國有企業(yè)地位相對萎縮,而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發(fā)展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即中國的工業(yè)化過程在很大程度上表現(xiàn)為農(nóng)村的工業(yè)化。許多學(xué)者認為,中國的改革由于采取了漸進主義的策略,所以模糊產(chǎn)權(quán)在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發(fā)展中起到了積極作用,即鄉(xiāng)村政府對企業(yè)的扶持和保護成為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高速成長的源泉,特別是在發(fā)展的早期。這主要是由于在不完全競爭和政策扭曲的情況下,公有產(chǎn)權(quán)是一個次優(yōu)的選擇。①D.Li(1994)通過理論模型來表明在灰色市場的環(huán)境中,模糊產(chǎn)權(quán)是一個最優(yōu)的制度安排。Che和Qian(1998)從另外的角度上說明,地方政府有效地防止了中央政府對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不利影響。此外,S.Li(1997)的模型認為,公有產(chǎn)權(quán)通過質(zhì)押關(guān)系和競爭為不完備的合約提供了自我實施的機制。在實證研究方面,趙耀輝(1997)總結(jié)了在中國的政策環(huán)境下地方政府潛在的積極作用:(1)稅收優(yōu)惠;(2)低利息的優(yōu)惠貸款;(3)獲取土地使用的許可權(quán);(4)獲取原材料;(5)贏得消費者的信任。這些潛在收益在很大程度上為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采取公有產(chǎn)權(quán)提供了理性基礎(chǔ)。但這種事后的推理往往會使人們忽略歷史的本來面目。正如Putterman(1997)所指出的,在改革之初,有能力發(fā)展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地區(qū),往往是那些在過去社隊企業(yè)已較為成功且地方政府也較有影響力的地區(qū)。Jin和Qian(1998)的實證分析證實了此點。給定公有產(chǎn)權(quán)在發(fā)展初期的存在性,許多理論模型成功地解釋了為什么其在后期依然得以維持。但它們未能證明公有產(chǎn)權(quán)就是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良好績效的原因。
就公有產(chǎn)權(quán)是否比私有產(chǎn)權(quán)更有效,文獻中有兩類實證結(jié)果。一類認為在生產(chǎn)效率方面二者沒有太大區(qū)別。Svejnar(1990)利用1975—1986年122個廠商的面板數(shù)據(jù),表明產(chǎn)權(quán)對產(chǎn)出并沒有顯著的影響。Pitt和Putterman(即將出版)則利用1984—1989年200個廠商的面板數(shù)據(jù),比較了在工資和就業(yè)決定方面集體和私營企業(yè)的效率,得出了同樣的結(jié)論。Dong和Putterman(1997)對上述數(shù)據(jù)集中的部分數(shù)據(jù)進行了隨機前沿生產(chǎn)函數(shù)分析,也證實在兩類企業(yè)的技術(shù)效率缺口方面沒有明顯區(qū)別。村屬企業(yè)的平均技術(shù)效率要高于私營企業(yè),但同時所有制類型與地區(qū)虛變量相關(guān),即在沿海發(fā)達地區(qū)村屬企業(yè)的比例較其他地區(qū)高。因此,在引入地區(qū)虛變量之后,所有制的影響就消失了。Jin和Qian(1998)研究了公有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對政府收入、農(nóng)村非農(nóng)就業(yè)和農(nóng)村收入的貢獻。他們發(fā)現(xiàn)貢獻是顯著的,但當保持非農(nóng)就業(yè)和地方公共品供給不變時,公有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并不能提高農(nóng)村收入。
他們的結(jié)論是,公有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作用是創(chuàng)造就業(yè)和供給地方公共品,盡管存在一定形式的低效率。第二類實證分析則提供了與前者截然相反的結(jié)論。Zhang(1997)基于對四川和浙江兩省630個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普查的結(jié)果發(fā)現(xiàn),在預(yù)算約束方面集體和非集體企業(yè)存在很大差別。集體企業(yè)的行為與國有企業(yè)十分近似,盡管地方政府掩蓋了這些問題。Yao(2001)研究了浙江省寧縣農(nóng)村工業(yè)化和勞動力市場整合之間的關(guān)系。Yao在就業(yè)選擇是內(nèi)部解而不是角點解的情況下,發(fā)展了一個計量模型來檢驗市場分割問題。檢驗表明,對于集體經(jīng)濟占主導(dǎo)的寧縣,工業(yè)就業(yè)中存在著配給,配給的程度隨著地方政府干預(yù)的程度提高而提高。Pitt和Putterman(即將出版)及Xu(1991)發(fā)現(xiàn)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實際工資高于勞動的邊際生產(chǎn)率,他們同時也發(fā)現(xiàn)了工作配給的存在。不過,他們未能發(fā)現(xiàn)集體和私營企業(yè)之間存在系統(tǒng)性的差異。姚洋(1998)利用1995年第三次工業(yè)普查對14670個企業(yè)進行的隨機抽樣數(shù)據(jù),比較了不同所有制類型、不同規(guī)模、不同行業(yè)及地理位置的企業(yè)在技術(shù)效率上的差異。他估計了12個行業(yè)的隨機前沿生產(chǎn)函數(shù),并得到了相應(yīng)的企業(yè)技術(shù)效率。將企業(yè)的技術(shù)效率和包含所有制在內(nèi)的一系列解釋變量進行回歸,回歸的結(jié)果表明私有廠商的效率比國有和集體企業(yè)分別高57%和35%。總之,模糊產(chǎn)權(quán)理論不能解釋中國農(nóng)村工業(yè)化的成功,微觀和宏觀的實證分析也均未能提供有力的證據(jù)。
二、經(jīng)濟發(fā)展戰(zhàn)略與工業(yè)化
中國農(nóng)村工業(yè)化成功的關(guān)鍵究竟何在呢?回答這個問題,需要我們從經(jīng)濟增長、技術(shù)進步和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變遷的基本邏輯關(guān)系入手展開分析。從新古典增長理論的角度看,無論是發(fā)達國家為了實現(xiàn)持續(xù)增長的目標,還是發(fā)展中國家要擺脫二元經(jīng)濟的格局,均要依賴快速的技術(shù)進步。因為在沒有技術(shù)進步的情況下,資本的邊際報酬會趨于遞減,所以如何引致技術(shù)進步是經(jīng)濟增長和工業(yè)化的關(guān)鍵。那么怎樣才能實現(xiàn)這一目的呢?林毅夫及其合作者(1996,1998,1999)從比較優(yōu)勢理論的角度對此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論述。他們認為,在一國的經(jīng)濟發(fā)展過程中存在兩個重要的外生變量:發(fā)展戰(zhàn)略和稟賦結(jié)構(gòu),①其他變量如技術(shù)水平、積累率、增長速度、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等均內(nèi)生于這兩個變量。
第一,一國最具競爭能力的技術(shù)結(jié)構(gòu)(或者說產(chǎn)業(yè)區(qū)段②)是由其稟賦結(jié)構(gòu)所決定的(對于一個成本極小化的廠商),因為不同的技術(shù)結(jié)構(gòu)必然與相應(yīng)的投入結(jié)構(gòu)相一致,而投入要素的相對價格則主要受制于本國的稟賦結(jié)構(gòu)。遵循比較優(yōu)勢,特別是按照本國的稟賦結(jié)構(gòu)來選擇相應(yīng)的技術(shù)結(jié)構(gòu),會使該國的產(chǎn)業(yè)最具市場競爭力,經(jīng)濟剩余最大,資本積累最多,要素稟賦提升最快,技術(shù)水平也就相應(yīng)得以迅速提升。因此,如何更好地利用本國的比較優(yōu)勢是經(jīng)濟持續(xù)增長和工業(yè)化的關(guān)鍵,任何人為的扭曲性干預(yù)均會造成效率和福利的損失。
第二,發(fā)展戰(zhàn)略這個概念是對政府的經(jīng)濟政策行為進行的高度抽象,從技術(shù)結(jié)構(gòu)和稟賦結(jié)構(gòu)的吻合程度上,我們可將之區(qū)分為遵循比較優(yōu)勢的戰(zhàn)略和違背比較優(yōu)勢的戰(zhàn)略,后者主要是指趕超戰(zhàn)略。發(fā)展中國家的政府往往只看到了先進技術(shù)的重要性,而忽視了技術(shù)進步的稟賦約束,進而在工業(yè)部門中實施技術(shù)趕超。
第三,一個企業(yè)的自生能力(即不需要政府保護和補貼而能賺取市場可接受的利潤水平的能力)決定于其選擇的產(chǎn)品和技術(shù)所在的產(chǎn)業(yè)區(qū)段是否符合其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yōu)勢。為了建立不具自生能力的企業(yè)以推行趕超戰(zhàn)略政府必須進行一系列扭曲的干預(yù),最終也帶來相應(yīng)的弊病:增長速度放慢,工業(yè)化進程被抑制(資金集中在少數(shù)幾個行業(yè),且效率低下),企業(yè)生產(chǎn)效率低下(無論是國有企業(yè)還是私營企業(yè)),收入分配不均(尤其是城鄉(xiāng)差距加大),金融壓制及結(jié)構(gòu)扭曲,經(jīng)濟的開放度低下,以及外部賬戶失衡等等。
第四,在趕超戰(zhàn)略的左右下,企業(yè)往往承擔了沉重的政策性負擔,從而造成了企業(yè)治理中信息傳遞的扭曲。與此同時,企業(yè)經(jīng)理人與政府談判的能力卻增強了。這就產(chǎn)生了預(yù)算軟約束,其存在與否不一定與企業(yè)的所有制類型有必然聯(lián)系。
總之,中國之所以在工業(yè)化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并實現(xiàn)了持續(xù)的經(jīng)濟增長,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逐步放棄了傳統(tǒng)的趕超戰(zhàn)略,而按照自身的比較優(yōu)勢來選擇技術(shù)結(jié)構(gòu)和產(chǎn)業(yè)區(qū)段。中國農(nóng)村工業(yè)化的成功是源于,自20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以市場為導(dǎo)向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在發(fā)展的過程中充分遵循了中國農(nóng)村勞動力豐富的比較優(yōu)勢。而城市(國有)工業(yè)由于承擔了政府趕超戰(zhàn)略的政策性目標,其生產(chǎn)成本過高而產(chǎn)品又不符合市場的需求,從根本上被抑制了發(fā)展的空間。我們在下文的實證分析中,①利用中國1978—1997年28個省的面板數(shù)據(jù)和幾種不同的計量方法檢驗了這一假說。②
三、計量模型
本文模型的核心問題是發(fā)展戰(zhàn)略(工業(yè)部門對本省比較優(yōu)勢的吻合程度)與工業(yè)發(fā)展績效之間的關(guān)系。為了簡化分析,我們假定投入只有勞動和資本,人均資本即要素密集度或稟賦結(jié)構(gòu)。設(shè)kRit和I*it分別是人均資本存量和最優(yōu)的工業(yè)資本密集度,下標i和t分別代表省份和時間。設(shè)I*it=I(kRit)(1)這里,I(•)是一個增函數(shù)。為簡單起見,假定函數(shù)關(guān)系是線性的且系數(shù)c*對于所有省份均相等,I*it=c*kRit(2)工業(yè)部門對本地區(qū)比較優(yōu)勢的吻合程度可以表示為實際資本勞動比kEit和I*it之間的比值Cit=kEitp/I*it=cit/c*(3)其中,cit是kEit和kRit間的比值。我們稱Cit為比較優(yōu)勢指數(shù),③在最理想的情況下,該指數(shù)應(yīng)等于1。因此,Dit就可以表示工業(yè)部門對本地比較優(yōu)勢的偏離程度,Dit=(Cit-1)2=(cit-c*)2/c*2(4)我們認為Dit越大,工業(yè)的發(fā)展就受到更多的阻礙。不過,當年的工業(yè)產(chǎn)出和Dit具有一定的內(nèi)生性,且資本配置不當?shù)挠绊懸膊荒荞R上得到體現(xiàn)。因此,我們的回歸中將使用滯后的kEit和kRit的比值以構(gòu)造cit。我們利用人均工業(yè)總產(chǎn)出Yit來測量一省農(nóng)村工業(yè)部門的規(guī)模,設(shè)Yit=A+α(Cit-1)2+eit=α0+α1c2it+α2cit+eit(5)式中,A是常數(shù),eit是隨機變量,α用來測量一省對比較優(yōu)勢的偏離程度,我們預(yù)期是個負數(shù)。可知α0=α+A,α1=α/c*2,α2=-2α/c*,于是有c*=-0•5α2/α1,α=α1c*2(6)顯然α與α1同號,我們的一個重要工作就是檢驗α1是否為負數(shù)。上式中,我們沒有考慮廠商在一省內(nèi)部的分布狀況,特別是當一省內(nèi)部存在許多大型的資本密集型企業(yè)時。例如,兩個省的人口和資本存量大致相同,即比較優(yōu)勢大致相同,但其中之一將資本均集中到少數(shù)大型企業(yè)中,而另外一省則較均勻地分配給所有的企業(yè)。顯然,前者的做法違背了比較優(yōu)勢原則,而對該省的長期增長有害。為了包含這種可能性,我們需要測度廠商的分布。
在下文對農(nóng)村工業(yè)的計量分析中,我們使用了按農(nóng)村人口平均的廠商數(shù)。這個數(shù)值越大,表明資本在廠商間分布得越平均,政府人為地趕超干預(yù)就越少。當然,如果大企業(yè)的生產(chǎn)具有很強的上下游關(guān)聯(lián)性,那么建立一些大企業(yè)未見得就會減少小企業(yè)的數(shù)目,這里我們排除了這種可能性,因為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大多生產(chǎn)中等消費水平的消費品,產(chǎn)業(yè)關(guān)聯(lián)性并不強。我們將廠商數(shù)量Nit和c2it、cit相乘以反映其影響,Yit=α0+α1c2it+α2cit+α3Nitc2it+α4Nitcit+eit(7)為了進一步明確α3和α4的涵義,整理上式得,Yit=(α1+α3Nit)(cit-c*N)2+θit+eit(8)c*N=-12α2+α4Nit2α1+α3Nit,θit=-14(α2+α4Nit)2α1+α3Nit(9)這里,c*N等同于c*。在理論上講,隨著廠商數(shù)量的變化,c*N應(yīng)當保持不變,因為它代表了工業(yè)資本密集度與當?shù)厝司Y本存量的理想比重,從而獨立于廠商的數(shù)量,①即c*N/Nit=0。于是有α2α3-α1α4=0(10)我們將檢驗該參數(shù)約束式。此外,α3可以解釋為包含了廠商分布的修正參數(shù),按照以往的分析,它應(yīng)當是正的。設(shè)Xit是其他解釋變量的向量,α5是待估計的參數(shù)向量,最終的計量方程式為Yit=α0+α1c2it+α2cit+α3Nitc2it+α4Nitcit+Xitα5+eit(11)
四、對于中國農(nóng)村工業(yè)化的實證分析②
我們收集了1978—1997年28個省的數(shù)據(jù),但在回歸中沒有使用1996年的數(shù)據(jù),因為在該年只有增加值的統(tǒng)計,沒有總產(chǎn)值的數(shù)據(jù)。由于缺乏幾個關(guān)鍵變量的滯后值,回歸中所使用的實際數(shù)據(jù)是從1981年開始的。我們使用雙向固定效應(yīng)方法(即固定省級效應(yīng)和固定時間效應(yīng))來估計(11)式,同時我們也用其他面板數(shù)據(jù)估計方法來進行參數(shù)敏感性分析。
(一)變量的選擇與測量被解釋變量是按各省1978年不變價計算的按農(nóng)業(yè)人口平均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總產(chǎn)出(1000元/人)。③解釋變量主要包括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技術(shù)選擇指數(shù)和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數(shù)量密度。當然,如何選擇其他解釋變量Xit也是個重要的問題,原則上宜選擇外生于企業(yè)產(chǎn)出且又對之存在較大影響的變量。這里,我們選擇了代表市場條件、基礎(chǔ)設(shè)施狀況、開放度、農(nóng)村工業(yè)部門特征、與國有部門的相互影響、經(jīng)濟體制改革、所有制類型、土地稟賦等因素的變量。以下是具體的變量選取。技術(shù)選擇指數(shù):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技術(shù)選擇指數(shù)是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資本密度比各省農(nóng)村人均資本存量。農(nóng)村資本存量是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凈固定資本、農(nóng)村集體凈生產(chǎn)性固定資本與農(nóng)民的儲蓄存款之和,所有的數(shù)值均按年末值計算。由于農(nóng)民的儲蓄作為一個存量有相當一部分已經(jīng)貸給了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并形成了資本存量,因此上述資本存量的估計顯然偏高。實際上,如果假定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難以通過銀行從城市儲蓄中獲得資金,那么該估計值就應(yīng)當是農(nóng)村生產(chǎn)性資本存量的上限(或者說是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可獲得的生產(chǎn)資本總額)。①相反,我們也可以把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可得資本定義為從銀行獲取的貸款,并將之看作可得資本的下限。我們在計量中同時考慮了這兩種測度方式,但在估計結(jié)果方面并沒有太大區(qū)別,上限估計和下限估計是正相關(guān)的。因此,我們僅報告利用上限估計值的計量結(jié)果。②企業(yè)數(shù)量密度:用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數(shù)目比農(nóng)村人口來表示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相對規(guī)模(個/10000人)。
市場條件:我們用城市化比率(城市人口占總?cè)丝诘谋戎?、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代表一個省對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產(chǎn)品的需求規(guī)模。由于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產(chǎn)品主要在同一省內(nèi)銷售,因此該省的需求規(guī)模可能是決定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發(fā)展的主要變量。基礎(chǔ)設(shè)施:我們使用公路網(wǎng)密度、有路面里程的公路網(wǎng)密度、鐵路網(wǎng)密度(公里/平方公里)表示交通便利程度。開放度:我們使用人均出口(元/人)和人均FDI(元/人)來表示各省的開放程度。出口和FDI均使用過去3年的平均值,因為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出口在總出口中占到了相當?shù)姆蓊~,而FDI則容易受到當年總產(chǎn)出波動的影響。FDI不僅是一省開放度的衡量,而且也是資本可得性的衡量。由于沒有FDI在城市和鄉(xiāng)村之間分布的數(shù)據(jù),因此未能將其加入到農(nóng)村地區(qū)的可得資本之中。人力資本:我們用技術(shù)工人占總雇員人數(shù)的比率作為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人力資本存量。國有企業(yè)的影響:關(guān)于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與國有企業(yè)的相互影響,我們使用了分省的人均國有工業(yè)企業(yè)產(chǎn)出(1000元/人)和國有工業(yè)企業(yè)的資本勞動比(1000元/人)。農(nóng)業(yè)體制改革:1978—1983年進行的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改革,是采取了漸進和不平衡的策略,因此我們在回歸中引入了采取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村莊所占比重這一變量。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以鄉(xiāng)村所有的企業(yè)在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總產(chǎn)出中的份額為了表示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土地稟賦:由人均耕地(畝/人)代表。耕地豐富一方面意味著該省有更多的比較優(yōu)勢來發(fā)展農(nóng)業(yè);另一方面,農(nóng)產(chǎn)品供給的上升也促進了食品加工業(yè)的發(fā)展。為了比較這兩種不同的效應(yīng),我們加入了土地面積作為一個輔助變量。
(二)計量結(jié)果按照表1中所給出的估計結(jié)果,發(fā)展戰(zhàn)略對農(nóng)村工業(yè)的影響與前文的理論判斷相一致。α1的估計值,即c2it的系數(shù),在5%的水平上負向顯著,從而為比較優(yōu)勢理論提供了實證支持。α3的估計值顯著為正,這也和我們的預(yù)期相一致。由于該估計值和Nit的平均值都很小,偏離比較優(yōu)勢的影響就近似等于α1的估計值。根據(jù)點估計的結(jié)果,c*N、技術(shù)選擇指數(shù)的樣本均值、及人均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產(chǎn)值,偏離理想技術(shù)選擇指數(shù)的負效應(yīng)的彈性是1•78,即cit-c*N的絕對值上升1個百分點,人均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產(chǎn)出將下降1•78個百分點。我們檢驗了(9)式中的約束,發(fā)現(xiàn)其在1%的顯著水平上接受,因此廠商的數(shù)量實際上并不影響理想的資本密集度。在表示市場規(guī)模的兩個變量中,人口密度對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存在正的顯著作用,而城市化比率則不顯著。這表明,農(nóng)村市場的大小是影響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發(fā)展的主要因素,而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產(chǎn)品也主要是供應(yīng)其所在地區(qū)。關(guān)于基礎(chǔ)設(shè)施的3個變量都不顯著,這意味著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可能主要是圍繞著城市分布,道路的密度,特別是通向邊遠地區(qū)的道路沒有太大的影響。另外一種解釋是,道路密度與某些不可觀測的省級特征(反應(yīng)在省級虛擬變量中)相關(guān)。模型Ⅲ和Ⅳ中的結(jié)論支持了這一猜測。對于代表經(jīng)濟開放度的變量,出口不顯著,而FDI則有正的顯著作用。前者可能是由于其在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產(chǎn)值中所占比例過小的緣故(大約在8%的水平上)。FDI的作用可能來源于幾個方面。
第一,FDI代表著資本的可得性;第二,外商投資企業(yè)是本地企業(yè)與國際接軌的重要橋梁;第三,FDI為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帶來了新的技術(shù)和管理經(jīng)驗(Yao,1998);最后,通過創(chuàng)造向上和向下的產(chǎn)業(yè)關(guān)聯(lián),FDI促進了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發(fā)展。在關(guān)于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自身的兩個解釋變量中,廠商相對于農(nóng)村人口的數(shù)量是十分顯著的,而具認證資格的技術(shù)工人所占比重則不顯著。后者的原因大致上是由于所選指標不能夠很好代表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人力資本存量。在發(fā)展的初期,大量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由于所使用的技術(shù)較為簡單,因而也不太需要技術(shù)工人。何況,政府政策也阻礙了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技術(shù)工人獲取正式的認證資格。國有工業(yè)企業(yè)的規(guī)模對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發(fā)展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其資本密集度的影響則不明顯。國有工業(yè)企業(yè)規(guī)模的影響可能來源于兩方面,①一是國有工業(yè)技術(shù)和人力資本的外溢,二是國有工業(yè)企業(yè)可以與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簽訂分包合同,從而直接刺激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增長(Wang和Yao,1998)。而這兩種效應(yīng)中,至少有一個獨立于國有工業(yè)的資本密集度。②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的實行對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沒有顯著影響。在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推行期間,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迅速上升,而非農(nóng)部門則相對下滑。公有企業(yè)的產(chǎn)出比重對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規(guī)模的負面影響在10%的水平上顯著。我們的結(jié)論要強于Jin和Qian(1998)的發(fā)現(xiàn),因為即使不控制住非農(nóng)就業(yè)和公共品供給,公有制廠商仍然呈現(xiàn)出負面的影響。③關(guān)于土地稟賦,我們的結(jié)論與Leamer(1987)相一致,曲線效應(yīng)明顯存在。
為了檢驗系數(shù)的敏感性,我們對上述計量模型的設(shè)定做了一些修正。模型Ⅱ中,我們?nèi)サ袅薱it和Nit的交叉項,結(jié)果技術(shù)選擇指數(shù)的影響依舊顯著。其他的參數(shù)估計值也沒有發(fā)生太大的變化,不過土地的曲線效應(yīng)減弱,而公有產(chǎn)權(quán)的負面影響增強,看來這兩項對交叉項較為敏感。模型Ⅲ是對(10)式的OLS估計,其目的在于檢驗我們的結(jié)論是否受到時間和省級特定效應(yīng)的影響。其中,技術(shù)選擇指數(shù)的影響變化不大,僅僅是c*N的估計值略有下降(與模型Ⅰ相比)。不過,模型Ⅲ的許多參數(shù)估計結(jié)果均與模型I存在較大的差異。公路網(wǎng)密度、滯后的出口、技術(shù)工人比重、國有企業(yè)的資本密度和公有企業(yè)的產(chǎn)出份額均顯著為正,城市化比率則顯著為負。這說明這些變量與時間和地區(qū)特定效應(yīng)高度相關(guān)。模型Ⅳ是在模型Ⅲ的基礎(chǔ)上引入了三個反映一省初始條件(1978年)的變量。這三個變量是人均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產(chǎn)出、人均國有工業(yè)企業(yè)產(chǎn)出和國有工業(yè)企業(yè)的資本密集度。人均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產(chǎn)出的系數(shù)是正的,而國有工業(yè)企業(yè)的規(guī)模則沒有顯著影響,國有工業(yè)的資本密度對于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發(fā)展起到了顯著的負作用。①之所以出現(xiàn)這樣的情況,一種可能是由于國有工業(yè)和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之間的關(guān)系一直在發(fā)生著系統(tǒng)性的變化。在發(fā)展的初期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更依賴于國有工業(yè)的技術(shù)外溢,國有部門的結(jié)構(gòu)偏向輕工業(yè)對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發(fā)展有利。但當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進入高速增長期以后,產(chǎn)品和市場的相互關(guān)聯(lián)則成為了國有工業(yè)對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最主要的影響渠道,直接的技術(shù)和人力資本外溢則變得較為次要了。此外,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技術(shù)進步也主要是通過市場和產(chǎn)品交易的方式來獲取。
另外一種解釋是,改革之初國有工業(yè)越發(fā)達,工業(yè)結(jié)構(gòu)越偏向重工業(yè)的地區(qū),就越受到政府趕超戰(zhàn)略的左右,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發(fā)展障礙就越高。當然,究竟哪種可能性占據(jù)主導(dǎo),尚需要進一步的研究。與模型Ⅰ相比,模型Ⅳ的結(jié)論說明cit的曲率是很弱的,即我們的結(jié)論對一些特定的初始條件很敏感。但其對省級的虛擬變量并不敏感,就是說,初始條件與更為持久的省級特定效應(yīng)相關(guān),而這些不能被觀測到的省級特征抵消掉了初始條件對我們結(jié)論的影響。實際上,當我們重新在模型Ⅳ中加入5個區(qū)域虛擬變量時,②cit的曲率再次變得十分明顯。模型Ⅲ與模型Ⅰ在變量估計值上的差異大多在模型Ⅳ中又重新取得一致。這些變量包括城市化比率、滯后的出口、具有認證資格的技術(shù)工人所占比重、國有企業(yè)的資本密度、公有企業(yè)的產(chǎn)出份額。唯一的例外是公路網(wǎng)密度,它仍舊顯著為正,盡管顯著性下降了。也就是說,所有這些變量均與省級特定效應(yīng)存在較強的相關(guān)關(guān)系,而與時間特定效應(yīng)弱相關(guān)。另外,有路面里程公路網(wǎng)密度的影響第一次顯著為正,即它也與特定的初始條件高度相關(guān)。
五、對于中國國有工業(yè)發(fā)展的實證分析
本節(jié)中,我們同樣使用1978—1997年28個省的面板數(shù)據(jù),并采取與上文基本類似的計量方法對國有工業(yè)的發(fā)展進行簡要的分析。通過與農(nóng)村工業(yè)的對比,我們試圖證明比較優(yōu)勢理論對國有工業(yè)部門具有同樣的解釋力。回歸中,被解釋變量是按各省1978年不變價計算的按總?cè)丝谄骄膰泄I(yè)企業(yè)總產(chǎn)出(1000元/人)。當然,解釋變量的選取與前文有一定區(qū)別。為了得到國有工業(yè)企業(yè)的技術(shù)選擇指數(shù),我們首先計算了各省的實際資本存量(使用了資本形成總額中的固定資本形成總額這一指標),具體方法是:先按照分省的固定資產(chǎn)投資平減指數(shù)將固定資產(chǎn)投資統(tǒng)一折算到1978年不變價的數(shù)據(jù)。然后,按照折舊率10%累計計算資本存量,所以資本存量均按照1978年不變價計算。將資本存量除以相應(yīng)省份的勞動力總數(shù),該比值即代表一省的稟賦結(jié)構(gòu)。國有工業(yè)企業(yè)的資本密集度主要是用其固定資產(chǎn)原值(按固定資產(chǎn)投資平減指數(shù)折算到1978年不變價)除以職工人數(shù)得來的。我們把國有工業(yè)資本密集度比上滯后一期的稟賦結(jié)構(gòu)值,然后再將該比值滯后一期就得到了國有工業(yè)的技術(shù)選擇指數(shù)。至于其它的解釋變量,如表示市場規(guī)模、交通條件和開放度的變量選取和測算與前文相同。所不同的是,我們引入人均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產(chǎn)出和滯后一期的(全省)輕重工業(yè)產(chǎn)值比,來反應(yīng)國有工業(yè)受到整體工業(yè)結(jié)構(gòu)和非國有工業(yè)部門的影響。同理,在反應(yīng)初始條件的變量中,我們也相應(yīng)地采用了1978年輕重工業(yè)產(chǎn)值比這一指標。
①其中,各組計量結(jié)果所采取的計量方法與表1完全相同。模型Ⅴ和模型Ⅵ均采用了雙向固定效應(yīng)方法,后者去掉了國有工業(yè)的廠商密度和技術(shù)選擇指數(shù)的交叉值。模型Ⅶ是OLS的結(jié)果,其目的同于模型Ⅲ,模型Ⅷ在模型Ⅶ的基礎(chǔ)上加入了3個初始條件變量。國有工業(yè)的技術(shù)選擇指數(shù)、廠商密度及其交叉項的作用與我們的理論預(yù)期相一致,但是技術(shù)選擇指數(shù)在模型Ⅵ中不顯著。看來,政府對國有工業(yè)的整體資金密度和資金在不同企業(yè)間的分布同時施加了的干預(yù)。因此,技術(shù)選擇指數(shù)對交叉項比較敏感。與農(nóng)村工業(yè)一樣,市場規(guī)模對國有工業(yè)同樣存在顯著正向影響,且城市化比重對國有工業(yè)的作用要明顯強于對農(nóng)村工業(yè)的作用。公路網(wǎng)密度的影響發(fā)生了相反的變化。在4組模型中,鐵路網(wǎng)密度的影響始終為負(無論考慮了時間和區(qū)域特定效應(yīng)與否),有路面里程的公路網(wǎng)密度的影響始終為正,但在模型Ⅴ、Ⅵ中顯著性均消失了,這說明交通條件對時間和地區(qū)效應(yīng)較為敏感。測量開放度的變量對國有工業(yè)企業(yè)的影響與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存在較大區(qū)別,國際貿(mào)易對國有工業(yè)企業(yè)有明顯的正向促進作用,而FDI則對之有顯著的負面影響。即外資更多的是作為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而不是國有工業(yè)的資金來源,這與前面的結(jié)論相一致。
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對國有工業(yè)的影響始終顯著為正,這說明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在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上與國有工業(yè)存在正向關(guān)聯(lián)作用。更重要的是,對于那些更遵循比較優(yōu)勢的省份,農(nóng)村工業(yè)和國有工業(yè)的發(fā)展均會超過其他省份。我們沒有考慮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結(jié)構(gòu)外溢效應(yīng),而使用了滯后一期的輕重工業(yè)產(chǎn)值比重這一指標。模型Ⅶ、Ⅷ中,該指標對國有工業(yè)規(guī)模存在負面影響,這意味著國有工業(yè)在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上更偏向于重工業(yè)(相對非國有工業(yè)而言)。不過控制時間和地區(qū)效應(yīng)后,這種影響的顯著性消失了。模型Ⅷ中,國有工業(yè)對其自身規(guī)模的初始條件十分敏感,而初始的工業(yè)結(jié)構(gòu)則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這說明初始年份中,國有工業(yè)越偏向輕工業(yè),整體發(fā)展規(guī)模越大,以后的發(fā)展績效也就越好。增加五個區(qū)域虛擬變量后,上述兩個變量的影響沒有明顯變化。在兩種情況下,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初始規(guī)模對國有工業(yè)的發(fā)展均影響不大。
六、結(jié)語
通過前文的分析,我們有如下幾個結(jié)論:(1)中國的市場化改革,特別是放棄了重工業(yè)優(yōu)先發(fā)展戰(zhàn)略,對農(nóng)村工業(yè)和國有工業(yè)的發(fā)展均起到了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2)偏離理想的資本密集度將損害工業(yè)的發(fā)展,無論是對于農(nóng)村工業(yè)還是國有工業(yè);(3)公有產(chǎn)權(quán)對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發(fā)展起到了負面的作用,因此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目前正在逐步改革自身的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以硬化預(yù)算約束;(4)雖然公有制比重的提高可能意味著政府干預(yù)的增強,但國有企業(yè)與技術(shù)選擇指數(shù)的實證關(guān)系說明,發(fā)展戰(zhàn)略的選擇在更基本的層面上決定著經(jīng)濟績效的高低,而產(chǎn)權(quán)并非是最關(guān)鍵的因素,即如果不放棄趕超戰(zhàn)略,私有化未見得一定會帶來工業(yè)增長;(5)農(nóng)村工業(yè)和國有工業(yè)的發(fā)展均受制于市場規(guī)模的大小;(6)在同一個省的范圍內(nèi),國有工業(yè)部門的規(guī)模越大,結(jié)構(gòu)越偏向輕工業(yè),農(nóng)村工業(yè)與國有工業(yè)的發(fā)展就越快;(7)在對外開放度方面,FDI在農(nóng)村工業(yè)的發(fā)展中是一個強有力的解釋因素,而對國有工業(yè)則起到了相反的作用;(8)假定其他條件不變,在具有中等水平耕地面積的省份,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發(fā)展要優(yōu)于耕地面積過少或過多的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