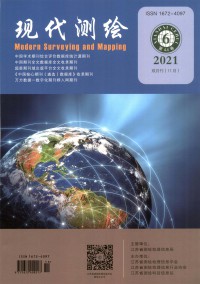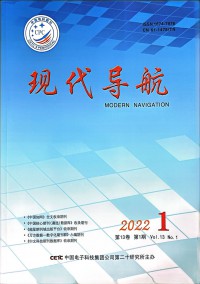現(xiàn)代繪畫藝術(shù)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現(xiàn)代繪畫藝術(shù)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chuàng)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內(nèi)容摘要:現(xiàn)代繪畫在不斷認(rèn)識自然和表現(xiàn)自然、學(xué)習(xí)傳統(tǒng)和勇于創(chuàng)新的過程中逐步走向了多元化。藝術(shù)家因各自不同的傳統(tǒng)積淀、學(xué)識和修養(yǎng)創(chuàng)造了世間風(fēng)格多樣而個性獨(dú)具的藝術(shù)作品。在視覺審美因素多樣化發(fā)展的情況下,以中西方融合為主線,有關(guān)中國文化藝術(shù)的論述在認(rèn)識西方現(xiàn)代繪畫發(fā)展的方式和方法上提供了一些不可或缺的幫助。
關(guān)鍵詞:現(xiàn)代繪畫交流融合影響
西方近代美術(shù)史的演變,曾被人喻為一個傳奇性的故事。由19世紀(jì)末到20世紀(jì)初,人們千變?nèi)f化的價值觀念,打開了許多未曾探索過的道路。一直到現(xiàn)在,“現(xiàn)代美術(shù)”仍是個令人迷惑的名詞,一些被公認(rèn)為藝壇巨人的畫家,如塞尚、馬蒂斯、畢加索雖已成為藝術(shù)史上的傳奇人物,卻仍然經(jīng)常被一般人所忽略,畢加索的立體派或荒唐或有趣,馬蒂斯的野獸主義或美觀或滑稽。但是這些“巨人”是如何創(chuàng)造出如此與眾不同的藝術(shù)流派的呢?他們的經(jīng)歷既辛酸又坎坷。在現(xiàn)代歐洲藝壇中,野獸派代表人物馬蒂斯,西班牙超現(xiàn)實(shí)主義畫家、抽象派繪畫的先驅(qū)者米羅,兼具立體主義、超現(xiàn)實(shí)主義、表現(xiàn)主義等多種風(fēng)格的俄國斯畫家夏卡爾,均為極負(fù)盛名的大師,被推崇為藝壇一代宗師。
1910年,馬蒂斯在慕尼黑觀賞了轟動一時的近東藝展,那次藝展對于他日后的繪畫方式,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力。近東的藝術(shù)富于艷麗逼人的色彩,而且也偏重于平面式的構(gòu)圖,用強(qiáng)烈而鄉(xiāng)間的純色彩、阿拉伯式的藤蔓花紋和各種只有東方味道的平面圖案。在他繪畫生涯的后期,馬蒂斯開始用彩色的紙,剪成彩色圖案,再用蠟筆和塑膠水彩來掩飾晚年以及疾病帶給他的不便。馬蒂斯的藝術(shù)之所以不朽,因?yàn)樗萘舜笞匀唬軌蜃屪约和笞匀缓隙橐唬c大自然的韻律起步而行。這一點(diǎn)同我國老子、莊子的順其自然頗為近似。“莊周夢蝴蝶,蝴蝶夢莊周,萬體更變易,萬事良悠悠。”“萬體更變易”便是馬蒂斯所強(qiáng)調(diào)的重點(diǎn)之一,人在不同的時候看同樣的一件東西,觀察的角度不可能完全一樣。西方美術(shù)自14、15世紀(jì)文藝復(fù)興以來,一向強(qiáng)調(diào)“獨(dú)一立足點(diǎn)”論,這是與東方美術(shù)完全不同的地方。東方美術(shù)幾乎不使用一個固定的立足點(diǎn),一幅畫總是由許多不同的立足點(diǎn)來構(gòu)成,馬蒂斯所擁有的,就是我們東方美術(shù)的這種“多重立足點(diǎn)”的觀念。因此他的畫顯得格外生動活潑,一點(diǎn)也不死板。馬蒂斯的空間利用恰巧符合我們“陰陽相間”的理論。馬蒂斯利用空間促使了畫中物體間氣韻的順暢,舉世聞名的現(xiàn)代美術(shù)評論家羅杰·弗萊在1912年評論馬蒂斯是所有西洋畫家中最了解中國美術(shù)精神的一位,這種啟發(fā)生命的韻律感,以及相對論的道理,確實(shí)是中國美術(shù)所強(qiáng)調(diào)的重點(diǎn)。他還認(rèn)為:“第十、十一、十二世紀(jì)的藝術(shù),亦即羅馬式藝術(shù),包含很多東方藝術(shù)的成分,這些成分在當(dāng)時還伴隨其他貨品,由東方輸入伊斯坦布爾、威尼斯,這些成分貢獻(xiàn)很多,它們經(jīng)過轉(zhuǎn)變,有了新的生命,而顯豐饒,它們開發(fā)新道路,也形成新環(huán)節(jié)。1920年的《宮女》,畫中的東方色彩(尤其是對波斯纖細(xì)畫的喜愛)以及作者筆下簡單的僧侶式人體、繁縟的背景同樣是扣人心弦的組合。他對線條的抽象、和諧、節(jié)奏的追求,強(qiáng)烈得常使人體的自然表象剝落盡至。”這樣的說法是正確的,無論如何,這時期的畫意念非常豐富,人體的簡化與靜物畫裝飾細(xì)節(jié)的增濃并進(jìn)。原因之一,是他長久以來對東方藝術(shù)的喜愛,這份喜愛在1910年9月他赴慕尼黑參觀回教藝術(shù)展時達(dá)到巔峰,后來他曾說:“我的靈感是來自東方。波斯纖細(xì)畫啟示我感官的一切可能,緊密的細(xì)節(jié)暗示出更大的空間,并幫我超越披露個人感情的繪畫表現(xiàn)。”馬蒂斯非常喜歡阿拉伯的蔓藤花,是緣于回教藝術(shù)的直接影響(日本版畫也有)。“我曾用彩色的紙做了一對小鸚鵡,我在作品中找到自己,中國人說要與樹齊長,我認(rèn)為再也沒有比這句話更認(rèn)真的了。”馬蒂斯晚年熱衷于剪紙藝術(shù)時說了這段獨(dú)白,他把東方的剪紙視為完全美的化身,從剪紙畫中得到過去從未有過的平衡境界。不取西方古典油畫的三維立體塑造,基本上是在二維空間的平面構(gòu)成中展示自己的彩色夢幻。但是由于彩色板塊里加進(jìn)了黑白板塊的分割、隔離以及物象的排映、濃濃的交織,畫面呈現(xiàn)出多重的空間層次,不僅生成平面的張力,而且生成縱深的張力,從而產(chǎn)生一種疊幻的視覺牽引力,使畫面欣賞起來如層層剝筍,十分耐品。他的靈感常常來自東方藝術(shù),用純色平涂,色彩鮮艷,但并不“野獸”般刺激,他夢想的是一種平衡、純潔、寧靜,不含有使人不安或令人沮喪的題材的藝術(shù),它像一種鎮(zhèn)定劑,或者像一把舒適的安樂椅。
在西方現(xiàn)代畫家中,保羅克利對東方人來說是最親近的。他的藝術(shù)觀念和東方神秘主義相通,即把創(chuàng)作活動視為不可思議的體驗(yàn),而這一體驗(yàn)過程乃是內(nèi)部幻覺與外界真實(shí)的統(tǒng)一,其哲學(xué)根源在人和自然之間本質(zhì)上的同一性。
自1916年至1917年,克利專攻中國文學(xué),接觸到中國書法和中國畫,從中汲取了文字可以造型的思想,并以獨(dú)特的方式進(jìn)行了實(shí)驗(yàn)。這一研究結(jié)果就是一系列的文字畫。而且以后還以單個的較大R字母出現(xiàn)在繪畫中,克利的繪畫藝術(shù)中,體現(xiàn)了中國繪畫的影響,在《隱士的住所》中的那所簡陋的小屋,是中國山水畫的面貌,不過,在這幅作品中,房屋的側(cè)面卻豎有十字架,它告訴人們這位隱士不是中國人。克利在藝術(shù)上與中國最重要的關(guān)系,與其說是主題還不如說主要表現(xiàn)在繪畫內(nèi)容上,尤其在中國文學(xué)中常見的大自然與孤獨(dú)者之間的對話,對克利產(chǎn)生了強(qiáng)烈的共鳴;與其說是受到中國的影響,還不如說是對中國的再認(rèn)識。如他畫的《中國風(fēng)俗畫I》《中國風(fēng)俗畫工II》和《曾經(jīng)在灰蒙蒙的夜色下徘徊》一樣,本來是完整的一幅,后來被裁為各不相同的兩幅作品,旨在表現(xiàn)中國油畫的風(fēng)格。他在創(chuàng)作《中國風(fēng)俗畫》前還有一個作品,編號是《中國陶器》。由此看來,在一段時間內(nèi),克利對中國產(chǎn)生了很深的感情。《大路與小徑》,都融會在這大大小小完全抽象的格狀作品中,垂直線和畫面,象征著廣闊的埃及原野,它們以多變的寬度,向著頂端的天藍(lán)色帶——尼羅河延伸;在斑斕的色彩映照下,廣闊的田野與顫動的空氣融為一體,大地流水、太陽、春光充滿著永恒的詩一般的境界,整個畫面形式與韻律結(jié)構(gòu)氣勢恢宏,這(轉(zhuǎn)第105頁)(接第108頁)與中國講究的人與自然相融合至高境界的理念是相符的。
克利在晚年的繪畫中使用很粗的線條,有些像中國的書法,“筆跡最關(guān)鍵的是表現(xiàn)而不是工整,請考慮一下中國人的做法。我們在反復(fù)練習(xí)的過程中,才能使筆跡變得更為細(xì)膩、更直觀、更神韻。”這是他的體會,克利依靠自己高度集中的精神,達(dá)到了與東方藝術(shù)家并駕齊驅(qū)的境界。像《鼓手》這幅畫,乍看幾乎和中國現(xiàn)代書法差不多:像“寫字”一樣的單純的黑色線條,在簡潔的形態(tài)中隱藏著深切的感動。此時,克利的手足已不能自由活動,于是他用最少的視覺語言記下了最后最多最明確的話語,熱愛音樂的克利,回憶起少年時代作為一名鼓手參加伯爾尼市管弦樂團(tuán)的演奏,便創(chuàng)作了這幅畫。大大的眼睛,強(qiáng)有力的胳膊,以及畫面的深紅色,表示他自己對人生執(zhí)著的追求,同時讓人感到在內(nèi)部隱藏著冷酷的命運(yùn)。常常“先行而后思”,不斷在實(shí)踐中思考總結(jié)自己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yàn)。參照他的繪畫,可以看出他“緊緊抓住‘綜合鏈條’,通過‘博大精深’,走向‘天人神會’”的創(chuàng)作思路。“天人神會”是克利追求的最高境界。畫天宇、畫日月,亦可見其所求。“博大精深”是克利經(jīng)歷的意象升華。他認(rèn)為繪畫語言的“非陳述性”表現(xiàn)為直觀性、可感性、符號性、有機(jī)性、意象性;而這些特性在中國畫里則體現(xiàn)為既非“具象”也非“抽象”而是“主客觀高度濃縮統(tǒng)一的形象”,即超乎“具象”與“抽象”的“意象”和“意境”。
筆者聯(lián)想到與之視覺語匯相近的中西兩種藝術(shù):一是漢代畫像石的拓片。漢代畫像磚、畫像石的拓片就是一種影像,是不見骨線卻很有力度、很有動感的一種影像。東方思維方式不像西方那樣主客對立、內(nèi)外分明,但由于修養(yǎng)、閱歷和個性之異亦各有所側(cè)重。
至少在今天或是不久的將來,中西文化的交融也只能限于局部,而且這種局部性的交流是在克服一個又一個阻力的前提下實(shí)現(xiàn)的。正是意識到這一點(diǎn),一些文學(xué)家才提出了關(guān)于不同文化交流的有限性思想。美國現(xiàn)代藝術(shù)評論家尤尼斯指出,西方人極力對中國文化表現(xiàn)出巨大的熱情,認(rèn)為中國精神離他們的精神世界是貼近的,這種思想是不客觀的,在尤尼斯看來:“‘中國精神離我們之近’顯然是有限度的”,假如我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diǎn),不顧客觀的事實(shí)去強(qiáng)行要求中西方文化和藝術(shù)走向統(tǒng)一,結(jié)果造成批評和認(rèn)識上的偏頗與狹隘的毛病。今天,在這個中西文化藝術(shù)空前交流的時代,中西方文化各自存在的排斥力,對于本文化來說,是導(dǎo)致文化意識走向封閉的重要原因;對他文化來說,則是阻礙通過交流來獲得更多生機(jī)的根源。所以,在這個已經(jīng)多方面開始文化間交流的時代,為特定文化意識框架制約的藝術(shù)家,就更需要有一種勇于超越束縛人的框架,對外來藝術(shù)持寬容態(tài)度的胸懷。同樣,中國的藝術(shù)家們?nèi)绻皇怯米约旱奈幕庾R框架去套西方藝術(shù),甚至把這種框架看作是絕對標(biāo)準(zhǔn)和永恒不變的,那么,中國藝術(shù)必定在沉悶的封閉空間中,反復(fù)吟唱一首遙遠(yuǎn)而古老的歌謠。在西方藝術(shù)空前影響和交流的今天,我們應(yīng)該意識到,寬容是理解和攝取的前提,寬容能為我們的思考和最終的選擇贏得寶貴的時間和天地。
筆者認(rèn)為,對藝術(shù)的探討并不僅僅是停留在藝術(shù)現(xiàn)象層面上的分析和理解的問題,藝術(shù)的現(xiàn)象和外觀固然是我們分析和理解中西藝術(shù)內(nèi)涵的媒介,但形式外觀不應(yīng)該成為我們進(jìn)行分析的研究終點(diǎn),而潛藏于藝術(shù)形式和各種藝術(shù)現(xiàn)象之后的區(qū)域的、民族的,以宇宙意識為核心的文化意識則是我們把握藝術(shù)整體的根本。離開了對中西藝術(shù)中顯示出的文化意識的理解,我們就不可能真正地、深刻地理解中西藝術(shù),從而也就無從把握未來中西藝術(shù)發(fā)展態(tài)勢,我們對中西藝術(shù)的全部熱情必定是膚淺和沒有意義的。
文檔上傳者
相關(guān)推薦
現(xiàn)代企業(yè)管理 現(xiàn)代漢語論文 現(xiàn)代教育 現(xiàn)代藝術(shù) 現(xiàn)代漢語語法 現(xiàn)代科技 現(xiàn)代陶藝論文 現(xiàn)代營銷論文 現(xiàn)代法治論文 現(xiàn)代設(shè)計(jì)論文 紀(jì)律教育問題 新時代教育價值觀
- 現(xiàn)代性和后現(xiàn)代
- 現(xiàn)代陶藝
- 后現(xiàn)代與現(xiàn)代教育探討
- 現(xiàn)代化思想
- 現(xiàn)代音樂藝術(shù)
- 現(xiàn)代音樂
- 政黨現(xiàn)代化
- 詞典現(xiàn)代化
- 現(xiàn)代音樂藝術(shù)
- 現(xiàn)代媒體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