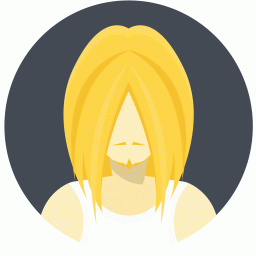戲曲形式變遷發展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戲曲形式變遷發展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在今天的中國戲曲研究領域,周貽白先生被稱為可與王國維并駕齊驅的“場上案頭一大家”。作為20世紀中國戲曲學術史上一位貢獻卓著的學者,他是繼王國維之后,對中國戲曲發展作通史性探討和總結的戲曲理論家,最先提出戲曲在聲腔上可以分作三大源流,即昆曲、弋陽腔(一名高腔,又作京腔)、梆子腔的見解。
周貽白先生1900年出生。1977年逝世,一生歷經了清末、民初、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三個時期。也是中國戲曲由盛而衰,再由敗而興的歷史發展期。本文擬對20世紀50年代開始席卷新中國的“戲改”浪潮,談談當時周貽白對“戲改”的看法。
一“戲改”的宗旨——“變”中求發展
1949年新中國成立,年底歐陽予倩和田漢即致函遠在香港的老友周貽白,邀其歸國籌備組建中國戲劇學院。周貽白聞訊沒有絲毫猶豫,立即辭去香港永華電影公司的職務,回到祖國。1949年7月,戲曲改進委員會召開關于“確定戲曲節目審定標準”的會議,確定:在戲曲藝術形式問題的改革上,無論修改劇本或創作新劇,都應該注意保存京劇和各種地方戲原有的特點和優點,而不要輕易將這些特點和優點拋棄。1951年,周貽白成為戲曲改進委員會委員后,開始撰寫“戲改”文章,發表在《人民戲劇》和《新戲曲》上,還經常被邀請去商談“戲改”問題。與此同時,周貽白也看到了中國戲曲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所產生出的弊端。在《中國戲劇本事取材之沿襲》一文里,他從中國戲曲舞臺演出的現狀反思了其無法反映現實生活的根源,他說:“中國戲劇的取材,多數跳不出歷史故事的范圍。很少是專為戲劇這一體制聯系到舞臺表演而獨出心裁來獨運機構。……中國戲劇不能更多地從現實生活取材,而只借歷史故事來藏褒寓貶,這對于中國戲劇而言。雖由此造成一種特殊的表演形式,但許多歷史人物,在舞臺上已成定型,如果仍舊在歷史故事上兜著圈子,則縱有新的形式,也將擺脫不了內容上的束縛。”
周貽白由此提出:“本事與體制的解放,應該是改革中國戲曲的先決問題。”并認為,有些大型劇種從形式到內容現在都已趨于僵化,根源在于很少專為戲曲這一體制聯系到舞臺表演而創作,他所說的戲曲“這一體制”自然是他始終堅持的“蓋戲劇本為上演而設”的特性。為了證明戲曲這種限于歷史故事題材沿襲,造成舞臺演出在內容和形式上無法脫離窠臼的局限,周貽白從宋元南戲到元明雜劇,再到皮黃劇本取材的歷史沿革中梳理出近三百種題材,有力地說明了中國戲曲發展到當時,已不能適應反映現實生活問題的嚴重性。他認為這在戲曲史的演進上,可窺其缺乏時代意義,而中國戲曲之不能作一種有力的開展,這是一個重要原因。今天看來。偏離了“戲曲體制”的創作,必然導致戲曲創作從內容到形式的偏于一隅,而走向歷史故事的局限便發端于此。“本事與體制的解放”對戲改工作從根源上著手解決,無疑提供了有益的思考;事實上,也只有改變了這種“仍舊在歷史故事上兜著圈子”的故事創作局限,通俗化的反映生活,才能讓中國戲曲回到廣大人民群眾的精神需求中去,才能使它重新煥發生命力!
特別凸顯這種意識的是他對于“京劇移步換不換形”的討論。1949年11月。記者許姬傳根據梅蘭芳的談話整理了《梅蘭芳談舊劇改革》一文,主張“京劇移步不換形”。周貽白認為此說過于保守,遂撰文《皮黃劇的變質換形》系統考證了皮黃劇的嬗變沿革,提出了皮黃劇可以變質換形的改革意見。以闡釋戲曲藝術發展的規律性是隨時代而前進的,衡量應以“場上”演出的理念和廣大人民群眾的精神需求為標準。周貽白認為,首先,從皮黃劇的歷史看:縱向發展為改昆為亂、改雅為俗;橫向發展是變弋、秦、徽、漢為京,變雜為純。其次,對皮黃形成后其唱詞、腔調、場子、伴奏、腳色、扎扮等方面進行了大量考證梳理:得出皮黃本為“改”中而來,又于“變”中求發展的結論。明確指出:這種“變”是藝術規律使然,劇種的生命力如此。此外,周貽白還認為:“清代,皮黃之所以盛行,雖由一般觀眾之愛好,其詞句聲腔之通俗,自為最大原因。”但京劇為什么發展到最后只能夠在廟堂之上來搬演,在民間漸漸失去了它的活力?因為這種雅化的唱詞觀眾不能理解,考慮到受眾面的問題,必須在創作中重視戲曲的平民化。凡戲班、演員、劇目等等。如果得不到觀眾的支持,必然會被淘汰,觀眾是最好的檢驗者。故此京劇需要改革。
從京劇等一些劇種的發展流變周貽白看到了新時代戲曲改革的可行性。這些規律性的探索。在于對戲曲觀眾的重視。戲曲只有根植于它的土壤——廣大人民群眾,才能具有鮮活的生命力。當那些帶有地方腔調、語言、風格特性的戲曲,流轉到其他地區時引起觀眾“接受”受阻,或不為社會新的主體群所接受時,這一劇種的轉承起合就到了關鍵時刻,這一劇種面臨改革的時機也就隨之而來。
二“戲改”的原則——傳統的精髓不能丟
周貽白看到“戲改”中創新的必要性,但更認為戲曲的傳統精髓不能因為“戲改”而被丟棄。如當時搞西洋音樂的同仁認為京劇的鑼鼓太喧鬧,主張廢除或減低,周貽白認為,這是京劇及秦腔之類的地方劇種的優點,減低或可,不能廢除;又有人主張京劇有胡琴過門也可不要,甚至主張唱時也不要加入動作,周貽白明確提出這是對傳統的毀棄。
對于楚劇、漢劇、同州梆子等劇種。周貽白認為對這些地方戲曲的改革要建立在自身傳統精髓不能丟棄的基礎之上,堅守此點是其作為獨立劇種存在的價值和意義所在。他提到楚劇本從鄉野中來,它是最便于反映現實生活的一項戲種,其本身具有唱多白少的良好條件,若能從這一基礎向新歌劇發展,其前途實未可限量。而楚劇的旦角向使本嗓,不愿教授女徒,解放后才打破了這一保守思想局限,于是他大膽提出:根據楚劇原有聲調,若以旦角的粗嗓改作女中音唱出,必然面目一新。同時指出:楚劇通過對漢劇或其他劇種學習使自己的藝術表現力更加豐富是有必要的,但以皮黃代替原有的腔調則似乎不妥。假令楚劇只知道以京劇為法,把原有的唱腔都拋棄。既不能與京劇爭長,同時也未必能與漢劇角逐。對于漢劇。周貽白認為雖因其一向規律化的服裝、動作而以歷史故事表演為主,但漢劇有許多小戲,特別是丑腳和貼旦,其表情、動作都能不拘成法,反映現實題材,并非全無基礎,如果一律凝固化了,則未免阻塞了它的發展方向。
1952年,全國第一屆戲曲觀摩演出大會召開,在這次大會上,周貽白看了同州梆子,觀摩結束后立即撰寫《同州梆子所給我的喜悅》、《同州梆子演出的三個戲》等文章,不但對其論證的中國戲曲聲腔的源流問題做出了新的補正,而且又將同州梆子這一古老的地方劇種在舞臺演出上的價值和意義做了深入思考。他認為同州梆子“這一劇種雖然相當古老”,但從其作為一項“民族遺產來看,其中未始沒有可供我們今日的表演藝術的參考之處。何況。從發展上來看。這一輩年輕的演員,已經具有了相當堅實的基礎,將來推陳出新,前途正未可限量。我這種看法。或不免偏于感性,但我的喜悅,卻是筆墨所不能形容的!”并從同州梆子《轅門斬子》中,進一步證實了京劇的“西皮”是通過“襄陽調”和“漢調”發展而來的脈絡。故得出結論:“同州梆子重視于舞臺,對于中國戲曲的發展情況而言,不僅顯示出中國戲曲民族遺產的豐富。同時也給予我們以不少的知識。”周貽白不但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號召中看到了地方戲的價值,而且對于類似同州梆子等地方劇種的保護和改革,提出了所應該遵循的原則:假若一定要以“昆劇”或“京劇”為主而力求一致,那就要抹殺同州梆子所具的特點。“百花齊放”,主要在于“推陳出新”,并不是要把許多不同風格的劇種,搞成同一類型,這些原則對我們新世紀的戲曲發展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總之,中國戲曲要保持它的生命力,首先要保持各劇種作為獨立劇種的意義,要從人民的需要和人民的愛好來著眼。故筆者認為,如何在響應“戲改”的號召下,保留傳統戲曲樣式的特點,周貽白的觀點非常明確:戲曲是為人民大眾服務的,平民化和通俗化才是戲曲存在的本質意義。戲曲要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