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改革核心是土地革命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農村改革核心是土地革命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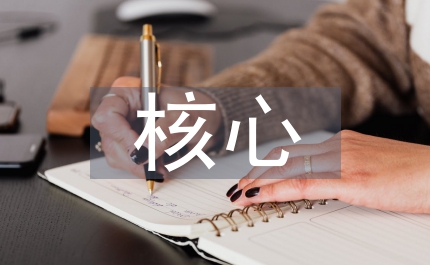
香港樂施會的年刊要我以2000字的篇幅介紹一下這20多年來農村改革的情況,這實在是個很難完成的任務,因為這20多年來中國農村改革千頭萬緒,兩萬字也說不完,只能勉為其難了。不過,根據我的理解,雖然中國農村改革的實踐過程和政策研究非常復雜,但都是圍繞著土地而進行的,即中國農村改革的核心是“土地革命”。
“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自古及今,農民占有土地的訴求是強烈而執著的,中國農村改革的發端也即因于此。中國共產黨正是通俗易懂地告訴農民,革命就是“”,“”就是“分地”,才激發起農民的革命熱情,從而把馬列主義與中國“農民革命”有效結合起來,最終奪取了政權。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共產黨兌現諾言,全國上下“分田分地真忙”,中國農民曾經一度成為土地的主人,也就是在這個時候,農民們真誠地喊出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但好景不長,1952年“社會主義改造”開始了,中國共產黨要帶領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農村掀起合作化運動高潮,先是“初級社”,后是“高級社”,1953年下半年到1956年初不到三年時間內,全國農村包括土地在內的所有生產資料被“集體化”了,農民們“當家作主”了,但他們怎么看土地也不象是“自己的”了。就在農民們困惑、抵制——浙江、安徽許多地方悄悄“分田單干”或“包產到戶”,甚至發動“反革命暴亂”(如陜西某縣)的時候,又于1958年發現“好”,于是,全國農民“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兩三個月時間,全國農村化,徹底“一大二公”了。至此,中國農民既失去了生產自主權,又失去了產品支配權,農民們此時發現,他們已經不僅是公社的“主人”,而且也是公社的“奴隸”,農民生產積極性喪失殆盡。1960年以后,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把農民牢牢地“固定”在“社會主義新農村”,“牢不可破”,“公社好比常青藤,社員就是藤上的瓜”,從此以后,中國農民就順理成章地充當起“社會主義大廈”的堅實“基礎”了。但是,歷史資料已經證明,1958年—1978年的20年間,中國農民的“幸福生活”猶如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
小崗村隸屬安徽省鳳陽縣小溪河鎮,是淮河岸邊的一個普通小村莊。1978年以前的小崗村,只有20戶人家100多人,是遠近聞名的“三靠村”——“吃糧靠返銷,用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每年秋后,家家戶戶都要背起花鼓去討飯。1978年秋天的一個晚上,小崗村農民們作出了一個大膽決定:包產到戶,“交足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就是自己的”,這就是后來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俗稱“大包干”,農村改革由此拉開序幕。小崗村實行“大包干”一年就大變樣,不僅結束了20多年吃“救濟糧”的歷史,而且上繳國家糧食3200多公斤。中共高層的一些明智之士發現,“大包干”是解放農村生產力的有效手段,對“大包干”給予積極支持,后經過激烈的“黨內斗爭”,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對“大包干”基本肯定,1979年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對其進行了進一步明確,“大包干”如星星之火,迅速燃遍了中國農村大地。從1982年開始,中共中央連續五年五個“一號文件”,對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核心內容的農村政策一步一個腳印地進行充實和規范,從而使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成為“黨的農村政策的基石”。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賦予農民部分土地產權和生產自主權,農民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糧、油、棉產量連年增加,甚至翻番,農民生活普遍改善,整個1980年代,中國農村一片欣欣向榮,農村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進入1990年代,情況發生了逆轉。農民收入增長率連年下降,有些年份甚至成了負數,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農村各種矛盾暴露出來了,農村基層政權向農民亂收費、亂罰款現象層出不窮,農民不堪重負,農村干群關系緊張,許多農民棄田撂荒。為了“促進農民增收”,“減輕農民負擔”,“保護農民生產積極性”,中共中央于2000年決定在安徽省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2003年農村稅費改革推向全國。農村稅費改革就是要把農村的稅費制度規范起來,要求農村基層政府以農民土地總產出的8.4%(農業稅7%,另加20%的農業稅附加)向農民收取稅費,除此而外不得以任何理由向農民收錢、收物,同時進行鄉鎮體制改革,壓縮縣鄉干部編制,加強民主監督,以減少基層政府財政支出。農村稅費改革表面上看涉及的是財政體制和行政體制,而其深層次根源仍然是“土地”問題。其理由有二,一是中央于1990年代確立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要遵循效率原則,以土地為生產資料的農業相對于城市的工業是弱質產業,因此國民收入分配必然向城市傾斜,農村就不可避免地掉進“發展中的陷阱”,從這個意義上說,1990年代農民收入增長乏力也就是“合理”的了,這就是為什么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政府都扶持農業、補貼農民的緣故;好在中央已經認識到這一點,2002年進行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實驗,變對農民的間接補貼為對農民直接補貼,2004年此項改革已推向全國。二是農民負擔過重只是表象,實際上,它反映的是農村土地產出已經不足以支撐農村上層建筑,從而引發多種社會矛盾;1990年代分稅制改革以后,作為政府主要收入來源的增殖稅由中央和省級政府分享75%,市、縣、鄉三級才共享25%,絕大多數縣鄉政府的收入來源于農業稅,農業稅占大多數縣鄉政府收入的70%以上,有些地方超過了90%,是農村土地產出支撐著中國農村基層政權的運轉,中國農村的縣鄉衙門實際上都是“土地廟”,1990年代由于縣鄉政府自主權擴大,其機構不斷膨脹,而與此同時農業產出占GDP的比重卻不斷下降,至2003年已經降到15%以下,很明顯農村土地有不能承受之重了。由此可見,如果說“大包干”是為了提高農村土地產出,那么農村稅費改革就是為了調整土地產出的不合理分配,從而緩解農村社會矛盾。
中國是個人口大國,農村人口占60%以上,農村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人均耕地只有1.2畝,農村剩余勞動力規模龐大,大量農民要靠外出打工謀生,而農民卻沒有政府所提供的社會保障,所以,對農民來說,農民所分得的承包地不僅是生產資料,更是他們的生存保障資料,即土地對中國農民具有社會保障功能。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土地和勞動力是必須盤活、使其自由流動的兩大要素,要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和農村土地的順暢流轉,就必須給土地對中國農民的社會保障功能尋找一個替代物,正因如此,近年來,中國政府著手進行統籌城鄉用工制度、農村養老保險、農村醫療保障等一系列改革實驗,雖然步履維艱,但正在奮力前行!
2003年,中央的改革政策進行了戰略調整,在中國共產黨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中央明確提出了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經濟體制改革的“五個統籌”和“五個堅持”,中央認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貫徹“五個統籌”,做到“五個堅持”,即要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堅持尊重民眾的首創精神,堅持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堅持統籌兼顧,堅持以人為本。按照“五個統籌”的要求提出改革目標,體現了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體現了改革、穩定、發展三者緊密結合、相互統一的思想,確立了可持續發展觀。在“五個統籌”中,“統籌城鄉發展”居于首位,自此以后,“三農”問題和農村改革被提高到中國今后社會經濟發展的首要問題的戰略高度。但這只是“戰略”上的變化,在農村改革的“戰術”上仍然是圍繞“土地”問題而展開的。作為貫徹“統籌城鄉發展”的具體措施,中央在《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對今后的農村改革提出了“四點意見”,即“完善農村土地制度”;“完善農產品市場體系,放開糧食收購市場,把通過流通環節間接補貼改為對農民的直接補貼,切實保護種糧農民的利益”;“深化農村稅費改革”;“改善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的環境······逐步統一城鄉勞動力市場,加強引導和管理,形成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的制度”。在這里,中央把“土地”問題仍然作為農村改革的核心問題放在“四點意見”的首位,提出“要長期穩定并不斷完善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依法保障農民對土地承包經營的各項權利”,“完善流轉辦法,逐步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改革征地制度”。其核心點就是要逐步培育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土地流轉市場,打破土地制度的城鄉分割局面,變土地流轉的行政化管理為市場配置,這說明,中央對現行土地制度的不完善和土地市場發育不全對我國市場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制約作用已經有了更清醒的認識。而另一方面,“四點意見”涉及的其他三個問題仍然是“土地”問題的衍生問題,關于農村“稅費改革”與“土地”的關系前面已有分析,我們來看另兩個問題與“土地”的關系。“完善農產品市場體系”,進行“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健全對農業的支持保護體系”,這實際上是為了解決“土地”產出的市場化問題,是“完善農村土地制度”的配套措施,因為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方向是,實現土地資源的市場化配置,按照經濟學的一般理論,只有要素市場和產品同時均衡,整個經濟才能實現均衡,所以,作為生產要素的“土地”市場化了,“土地”產出也就必須市場化。“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也是和“土地”問題緊密相關的,它是中國農村人地關系緊張、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同時,“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也是農村土地制度市場化改革的前提,如果不能把農村富余勞動力從“土地”上轉移出來,農村土地流轉就不可能實現,實現農村土地資源的市場化配置也就成了空話,所以,“完善農村土地制度”和“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這兩個問題是“一對雙胞胎”。可見,從“戰術”上看,在“四點意見”中,“土地”問題是深化農村改革的基礎和核心。說今后的農村改革還是“土地革命”,仍不為過!
綜上所述,我們很容易看出,二十多年來,中國農村改革雖然名目繁多,但幾乎無不與土地有關,土地問題既是改革的原因,也是改革的目標,所以,我認為,中國的農村改革實際上是新一輪的“土地革命”!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文檔上傳者
- 農村
- 農村離婚
- 農村講話
- 農村文化
- 農村講話
- 農村選舉
- 農村金融支持農村建設
- 農村改革及農村城鎮化
- 農村土地流轉
- 農村會講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