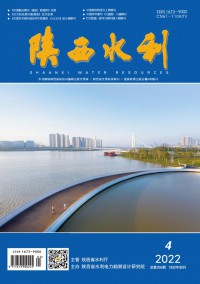水利史論文范文精選
前言:在撰寫水利史論文的過程中,我們可以學習和借鑒他人的優秀作品,小編整理了5篇優秀范文,希望能夠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借鑒。

明清江南市鎮和農村關系史概說
[摘要]有關江南市鎮的研究一向是明清社會經濟史關注的熱點,而從城鄉關系的角度透視江南地方社會的討論則顯得比較薄弱。本文回顧了以往大陸、港臺和海外學者研究明清江南市鎮與農村關系史的主要脈絡和學術取向,并對城鄉界線及其運作機制等前沿問題作了必要的思考。
[關鍵詞]明清;江南;城鄉關系
江南地區自唐宋時代開始逐漸成為中國的經濟中心,明中葉以后,當地傳統市鎮的軍事及行政機能漸趨退化,商業機能日漸凸現,其規模和數量遠超過宋代。至盛清時代,市鎮經濟呈現出空前繁榮的景象,市鎮和農村之間逐漸形成一種生產與貿易的連鎖體,構成市鎮網絡,“不僅僅只是在廣大的鄉村腹地中存在著的兩個或三個主要城市,而可以認為這一地區已經是一個城市化很廣泛的地區”。[1](P12)這背后有著水陸交通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也同當地經濟結構或經濟水平密切相關。長期以來,對明清江南市鎮的探討是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一個熱點,其研究成果令人矚目,尤其是自20世紀80年代始,有關江南市鎮的中外學術成果層出不窮,以涉及范圍之廣泛,論題之深入,幾乎可以說已經形成了一個專門的學術分支。不過,總的來說,以往的研究趨向,更關注的是市鎮的“中央性”機能。①或者強調市鎮在經濟、文化、生活等方面無比強大的“向心力”②;或者從特定區域以外尋找研究空間,熱衷跨區域的比較及與國內國際市場的經濟聯系。③較少注意市鎮與農村之間的關系,乃至將農村在城鄉關系中的位置懸置起來。城市與農村的關系問題是一個古老而又常新的問題。學界常以城鄉二分法或者城鄉連續體來概括傳統社會的城鄉關系,前者從人口的規模與密度、居住形態和社會異質性的角度,將城鄉分類進行論述,后者則完全打破二分法的框架,認為城市和農村各有其存在價值和功能,兩者共同構成了一個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共同體。隨著城市化理論的流行,連續體說逐漸占了上風。在城市化理論的影響下,從農村這一極向城市這一極的連續變化被設想成一個理所應當的過程,各種聚落形態都可以被確認為這一軸線上的某個位置。由于種種原因,過去有關江南市鎮研究,一向把市鎮本身④的討論當作優先任務,對于市鎮周邊的農村或者市鎮與農村關系的關注則嫌不足,即便有,也往往只具有作為市鎮研究附屬品的意味。雖則如此,本文仍擬在市鎮史研究的脈絡下,回顧一下國內外以往有關明清江南市鎮與農村關系史的各類探討⑤。并在此基礎上對未來研究中可能出現的某些趨向作一簡要前
一、國內(含臺灣)學者的相關研究
最早直接涉足江南市鎮研究的國內學者是傅衣凌,他1964年發表《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經濟的分析》一文,在“資本主義萌芽”的框架下,肯定了市鎮的成長,把市鎮經濟視作傳統地主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⑥他的開創性研究,為以后的明清江南市鎮研究奠定了基礎。1970年代,臺灣學者劉石吉首次對江南市鎮作了系統而全面的研究,他當時在《食貨月刊》和《思與言》上發表的三篇論文,后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在1987年以《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為書名在大陸出版。劉石吉的著作盡管在史料上有所局限,但其分析問題的趨向及提出的一些基本看法,如將江南市鎮劃分為棉織業市鎮、蠶桑絲織業市鎮、米糧業市鎮,以及對太平天國運動后的江南市鎮的發展、市鎮數量的分析,迄今仍很少為中外學者所超越。不僅如此,劉石吉的主要貢獻還在于,對大陸1980年代以來的江南市鎮研究具有啟發和推動作用。他的臺灣同行李國祁在1981年發表了《清代杭嘉湖寧紹五府的市鎮結構及其演變初稿》一文,將傳統市場分成省城、府城、縣城、鎮市、定期集市五個等級,強調了交通線路對市鎮分布外在結構的影響,并對施堅雅的六角形模式作了一定的修正。⑦劉錚云則從另
————————
漢學著規范
中國學世界化是中西文化交流進入更深層次的表現。對世界范圍內漢學研究論著的關注、介紹乃至,是所有人文學者不能回避,且應積極參與之事,如此可預學術之流。近些年伴隨著《世界漢學》、《法國漢學》等專刊,海外中國學論著等叢書的相繼出版,一批位于學術前沿的,用新理論、新法重新整理和審視中國傳統文化的國外研究成果開始得到相應地重視和有系統地引進,借此“”之橋,中外學者關于“國學”諸種問題的討論有了質的飛躍。但伴隨著這種交流,“漢學論著”作為一種不同以往的的新內容,面臨考驗,有進一步探索的必要,一些在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亟待解決。在我看來問題出于兩面:一,漢學論著著作既非文藝作品,也不是科技論文,但它兼具藝術性和科學性。對它的要求者的專業功力和外語水平同樣不凡。而目前我們的一些者往往偏重一面,或者滿腹經綸但文晦澀,全失原作的風格;或者行文流暢但疏漏百出,使原意走樣,不免貽笑大。二,由于這項工作興未艾,既缺乏經驗的累積,又尚未形成一定的規范和原則,因而出現作品的水平良莠不齊,、校等編輯、出版流程較為混亂等問題。以下就我所見漢學論著作品中的一些情狀,尤其是審讀美國學者施堅雅主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一書的中稿時發現的一些問題,談談自己對原則和規范的理解。
一.文化的還原
尋根溯源是漢學論著中不可忽視的技術問題之一。漢籍本身浩如煙海,文化內涵又廣博精深,海外學者對它的征引宛若隨意采擷,典故難尋;對它的解釋或體認有時推陳出新,有時又似是而非,因此文難于處理。所以文化上的,包括漢文人名、中文史料、歷史背景的還原就成了首要問題被提了出來。
漢文人名的還原。例如江蘇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中馬克斯·韋伯所著《儒教與道教》一書在描述漢代儒士反對司馬遷的重商思想時,把反對者“PenPiao”為“彭彪”(第頁,注),但實際上此人當為“班彪”。
又《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艾爾曼著,趙剛,江蘇人民出版社,年)第頁,倒數第行:“儲同舒(音,Ch’uTung-Tsu)《清代中國地政府》,斯坦福大學出版社,”。此處把“Ch’uTung-Tsu”誤為“儲同舒”,實際應為中國著名的社會學、歷史學專家,著有《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中華書局,年)一書的“瞿同祖”先生。
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法國學者勒內·格魯塞的《草原帝國》(年)一書中第頁有語:“可敦盡管還保留著這些野蠻的生活風俗,但她很信任中國大臣漢延惠,后者使契丹人開始走向文明。”文中“可敦”即指遼國蕭后,那么中國大臣當為“韓延徽”,不知成“漢延惠”的史料來源是什么?
經濟學理論
研究經濟史要有歷史學修養,又要有經濟學的基礎。我寫過一篇《論歷史主義》,是談歷史學理論的,可作為我以前所寫《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一文的續篇。[1]本文擬談經濟學理論,可作為《方法論》一文的另一續篇。
經濟學成為系統的科學,始于17世紀出現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本文所稱經濟學理論亦自此始。但不是說,在此以前的經濟思想就不重要。尤其象富國、富民思想,田制、賦稅思想,義利論、本末論、奢儉論等思想,在研究中國經濟史中無疑是很重要的。本文自古典政治經濟學開始,是因篇幅所限。也因為經濟史作為一門學科,是隨著古典經濟學的建立出現的;又是從方法論著眼,因為經濟思想成為系統的理論之后,才具有方法論的重要意義。
本文中,“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為同義語。
一、在經濟史研究中,一切經濟學理論都應視為方法論
經濟史是研究過去的、我們還不認識或認識不清楚的經濟實踐(如果已認識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因而它只能以歷史資料為依據,其他都屬方法論。經濟學理論是從歷史的和當時的社會經濟實踐中抽象出來的,但不能從這種抽象中還原出歷史的和當時的實踐,就象不能從“義利論”中還原出一個“君子國”一樣。馬克思說過:“這些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歷史就沒有任何價值。它們只能對整理歷史資料提供某些方便”。[2]這話也許有點過份,不過,“方便”可理解為方法。
J·M·凱恩斯說:“經濟學與其說是一種學說,不如說是一種方法,一種思維工具,一種構想技術”。[3]
商品流通基礎
經許多學者研究證明,清代前期的商品流通無論在數量方面,還是在規模上都較以往各朝代有了很大的發展,為其服務的基礎設施建設也相對較完善。可是,對這些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投入問題,則研究不夠。徐建青的研究【1】具有重要的意義,但還有多方面設施建設沒有涉及。一般來說,為商品流通服務的基礎設施涵蓋面十分廣泛,本文將探討為商品流通服務的交通(路、河、橋、渡船①)、交易(集市、貨棧、鋪房、旅店)、保安(巡船、巡役、航行標志、救生樁、救生船)三方面設施建設的投入問題。
一
在交通設施建設中,全國主要路、河、橋,由政府投資建設。政府把修建路、河、橋,作為各級官員的職責,順治元年、雍正三、七、八、十三年、乾隆十五、十六、二十六、二十九、四十一、四十五、五十五年、嘉慶四年,分別下達修理、維護的諭令。【2】(卷932《工部·橋道》)道光八年重申:“各省要路橋梁,間有損壞者,地方官查勘應修之處,詳報督撫奏明修理。”【3】(卷146,道光八年十一月乙巳,P.242)由于當時所建道路多為土路,修理起來較容易,各地官員大都能較好地完成。“惟良有司知道路、橋梁,皆王政之大,以時加意,無令病涉,庶有濟焉。”【4】(卷19,《津梁》)康熙十四年,黃梅縣受到洪水災害,道路被損壞。知縣李成林向黃州府申請修路,獲得批準。府下撥銀谷,李成林同縣丞樓自新“分頭督率,慘淡經營,仍捐貲,并設法募助,四閱月,工乃告成。”此役“共雇募人工四萬有余,約工價一千二百兩有零”。為使官道無坑陷之患,李成林采用以工代賑的辦法,令民“運沙一斗,給糧一升”,不到一月,百里官道鋪沙完畢。李成林得到政府獎勵,紀功一次。【5】河道的疏挖,在道光年間是十分繁重的工程,當時黃河經常泛濫,堵塞運河、淮河,嚴重影響了官方漕運,商品流通的運道,以及農業生產。“近年例撥歲修搶修銀兩外,復有另案工程名目。自道光元年以來,每年約共需銀五、六百萬余兩。昨南河請撥修堤建壩等項工需一百二十九萬兩。又系另案外所添之另案。而前此高堰石工,以及黃河挑工耗費,又不下一千余萬之多。”【3】(卷145,道光八年十月乙未,P.226~227)
各地區的道、河、橋則基本上是民間(包括官員以個人名義的捐助)捐資修建。民間修路的方式多種多樣,有“公買義路”;“捐地為往來通衢”;【6】(卷之10,《人物》)或捐廉、捐銀修筑,并在道路旁邊設有茶亭、路燈等設施。【7】(康熙五十七年七月十三日貴州巡撫黃國材奏,7輯,P.390)【8】(卷11,《風俗志》)以陜西省橋梁為例,雍正時期共修建30座,其中官建只有一座。知縣等各類官員修建的有11座,這中間可能包括官員用公款建筑,即政府出資的情況。即使把11座橋梁都算作政府出資,在全部橋梁中也不占多數。而民間投資自建、修建的橋梁占絕大多數。【9】(卷16~17,《關梁一~關梁二》)“與明代相比,清代民間捐修的數量明顯增多。”“民間捐資恐怕已成為地方交通事業的主要力量。”【1】在各地方志中,普遍反映出這種情況,有的占該地區總數的一半以上。②
政府規定在各地的河流沿岸設立渡船,“以渡南北往來文報、差使”,史書稱為官渡。渡船、渡夫、修船經費由地方政府支付,如有損壞,也由地方政府修補。乾隆“六年,更造一次,由司庫給領銀一百六十余兩。嘉慶十八年,改由陽曲等十縣攤捐。”【10】(卷39,《工制·水利五·通省官渡處所》)民間捐建的渡船,在一些地方志中稱為“義渡”。四川萬縣“湖灘上義渡,乾隆初年張燦若募設。”“黃連咀、陳家壩、擔子壩三處義渡,嘉慶年間陳大方、大中、楊學儒等捐設,歷數十年就廢。道光年間陳光烈、光黨等,倡募置業,三渡復興。”【11】(卷12,《地理志·義局》)因此官渡、義渡均不收渡錢。江西“至渡錢一項,除向系官渡、義渡不取錢文者仍照舊外,其余民渡,凡內河小港準取錢一文。”【12】(卷1,《渡船條規》)乾隆八年湖南也規定:“官渡渡夫不許需索錢文、米谷,民渡小船亦不許多勒渡錢。”【13】(卷2,《兵律·關津》,《江河渡口無論官渡、民渡,不許冒險多載。凡遇空手過渡,每人止許取錢一文,挑負貨物、行李,每人取錢二文,多索從重治罪,刊刻禁約,豎立渡口》)對民營渡船,政府限定渡價、載人量,進行管理。從目前筆者見到的史料看,廣東的情況與大部分省不同。廣東全省的渡船,都向乘客收錢,政府向渡戶收取渡餉。乾隆時詳定章程:“各府州縣所屬地方,設立渡船。……征收渡租谷,咨報充餉。如有應設之處,先由該管州縣勘明該地方實在情形通詳,候奉批準。示召年力壯健,熟識風色、水性之人,承充渡戶。一面取具供結,并鋪戶、渡鄰保結。由州縣加結申府,轉繳藩司詳院,飭府給帖開擺。不準一人兼承數支,網收漁利,及霸埠批租,私頂私擺情弊。”【14】(卷3,《戶例下·稅餉·各省渡餉》)有時也讓附近村民攤納,如靛行渡,“昔被豪右占踞。雍正元年,奉撫憲禁革,勒石永為官渡。其渡餉,歸附近鄉村攤納。”【4】(卷19,《津梁》)
在交易設施建設中,設置市場進行交易,需要征收一定的商業稅,因此城鎮市場多為政府設置。集市也以政府設立為主,民間捐助設立為輔。各地鄉村中的集市,有部分是前代遺留下來的,也有相當部分是清代建立的,大概是先有民間自然形成的交易市場,后由地方政府承認,并對其進行管理,征收商品交易稅。也有由政府強制官員捐資建立的集市,這類集市應視為政府行為。但與修建路、橋等設施不同,如果集市只占地而沒有店鋪等設施,也就不需要投資了,“在北方,村鎮的定期市都是在道路上,或者和道路相連的廣場上舉行,為此特別建筑房屋,似乎都是沒有的。”【15】(第3卷,P.96)“北方市集各有定期,邊境之人絡繹趨赴,各賃坐地,陳貨于左右,交易者權其值而與之。”【16】(卷之1,《地輿志·集市》)
人口壓力和清中葉經濟社會病變
【內容提要】清代中葉人口的持續高速增長使中國在18世紀末出現了人口過剩現象和人口危機,對當時社會造成了極大的壓力,使清中葉的經濟社會產生了一系列的病變,如資源短缺、物價騰漲、生態惡化、社會動蕩、經濟停滯等等,正是這些病變導致了中國社會近代轉型的舉步維艱。
【關鍵詞】清代中葉/人口壓力/經濟社會病變
關于清代的人口問題,近些年來學術界頗有研究,且成就斐然(注:主要成果有:周源和:《清代人口研究》(《中國社會科學》1982年第2期);程賢敏:《論清代人口增長率及“過剩問題”》(《中國史研究》1982年第3期);高王凌:《清代初期中國人口的估算問題》(《人口理論與實踐》1984年第2期);高王凌:《明清時期的中國人口》(《清史研究》1994年第3期);李伯重:《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長及原因》(《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周祚紹:《清代前期人口問題研究論略》(《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版)1996年第4期);張巖:《對清代前中期人口發展的再認識》(《江漢論壇》1999年第1期)等。)。但對清代人口,尤其是清中葉人口發展的看法卻是聚訟紛紜。本文的重點在對清中葉(1741—1851)的人口壓力作實證分析,并進而探討人口壓力對當時社會帶來的一系列負面影響。
一、清代中葉的人口壓力分析
清代中葉是否存在“人口過剩”和“人口危機”,這在學術界爭議非常之大。爭論雙方各執一詞,針鋒相對。但由于在對人口壓力的分析上不夠科學和全面,因而大多數論文并沒有得出令人滿意的結論。
所謂人口壓力,簡單的說就是人口與資源的比例狀況。由于不同的時代資源的內涵是不同的,因此,分析不同時代的人口壓力,涉及的指標體系和評價標準也是完全不同的。我們認為,分析處于前工業化時代的清代中葉的人口壓力,至少應包括人口數量、人口增長率、人口密度、人口結構、人均耕地、人均產值等一系列指標。而在對清中葉人口壓力強度作判斷時,既要有縱向的比較,即與中國歷史時期的比較;更要有橫向的比較,即與世界其它地區的比較,尤其是與工業化前后的西歐的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