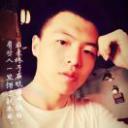淺議刑事案件閱卷難的成因及對策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淺議刑事案件閱卷難的成因及對策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閱卷難是律師執業難的一個側面反映,探究閱卷難的根源,提出閱卷難的解決辦法,不僅對解決閱卷難有益,對《刑事訴訟法》關于律師閱卷規定的修改、補充和完善也是十分有益的。結合相關法律規定,談幾點個人體會。
一、閱卷是律師行使辯護權的途徑、手段,更是律師行使辯護權的前提和基礎。
《律師法》第28條規定:“律師擔任刑事辯護人的,應當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
新、老《刑事訴訟法》均規定:辯護人的責任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
在刑事訴訟中控方負有舉證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證據的法定義務,而辯護律師則不負有舉證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無罪的證據的義務。應該說,針對控方而言,舉證不舉證證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無罪的證據是辯護律師的權利。換言之,只要控方拿不出被告人有罪的證據,被告人便無罪,法庭不會因為辯護律師沒有舉證被告人無罪的證據便判決其有罪。所以,辯護律師的一項重要工作便是以挑剔的專業眼光,“審查”、“核實”控方的證據能否成立,能否從法律上支持其控訴主張。
《刑事訴訟法》第43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必須保證一切與案件有關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觀地充分地提供證據的條件,除特殊情況外,并且可以吸收他們協助調查。”
根據該項法律規定,辯護律師的另一項重要工作是“審查”、“核實”控方有無全面、真實、客觀地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的證據,并及時向偵查、檢察機關提出相應的法律意見。
說辯護律師無舉證的義務是針對控方而言的,針對辯護律師的委托人而言,便有義務調查收集、舉證犯罪嫌疑人無罪、罪輕的證據。辯護律師的這項工作,能促進前兩項“審查”、“核實”工作,與前兩項工作是相輔相成的,是同等重要的。根據前述的“審查”、“核實”工作的需要,向偵查與檢察機關提出相應法律意見之后,如果不被采納,辯護律師則主動舉證被告人無罪、罪輕以及減輕和免除處罰的證據。從這個角度上說,辯護律師有點類似建設工程中的監理工程師,代表業主監督施工單位。有一點不同的是,監理工程師在什么情況下都不準親自“施工”,而辯護律師則可。
辯護律師要履行好自己的職責,一條重要的途徑、手段便是閱卷,因為與其委托方相關的大部分信息全在卷里。即便是律師自己調查取證的一部分工作也與閱卷息息相關,或靠閱卷發現線索提供信息。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閱卷是辯護律師行使辯護權履行辯護職責的前提和基礎,無此則無它。
二、1996年《刑事訴訟法》的修改,使本來不難的閱卷變得困難。
1996年修改以前的《刑事訴訟法》,對提起公訴的刑事案件,在第108條做了這樣的規定:“人民法院對提起公訴的案件進行審查后,對于犯罪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的,應當決定開庭審判。”包括此條在內的所有老的《刑事訴訟法》條文,并沒有哪一條明確規定檢察機關在將刑事案件移送人民法院提起公訴時,要將公安機關及檢察機關的偵查卷宗全部移送人民法院,但實踐中確是這么做的。公安機關偵查完畢后將偵查卷宗全部移送檢察機關,檢察機關在審查起訴完畢后,將檢察卷宗,至少是公安機關的偵查卷宗一并移送人民法院。辯護律師在人民法院查閱、摘抄、復制上述卷宗,幾乎不存在閱卷難,至少不存在閱卷的法律障礙和制度障礙。
1996年修改后的新的《刑事訴訟法》對提起公訴的刑事案件,在第150條做了這樣的規定:“人民法院對提起公訴的案件進行審查后,對于起訴書中有明確的指控犯罪事實并且附有證據目錄、證人名單和主要證據復印件或者照片的,應當決定開庭審判。”如果把新、老《刑事訴訟法》加以對照就不難發現,新《刑事訴訟法》悄然做了重大修改:只要求檢查機關向人民法院移送“證據目錄、證人名單和主要證據復印件或者照片”,所以檢察機關不再向以前那樣向人民法院移送公安機關的偵察卷宗和自己的檢察卷宗是不言而喻的。特別指出的是,即便是檢察機關向人民法院移送的證據也可以不是全部的,只移送“主要證據“就可以了。
檢察機關不移送偵察卷、檢察卷,辯護律師自然就難以閱到卷了。因此說,辯護律師的閱卷難是現行法律和現行的刑事訴訟體制造成的,而這一切又概源于1996年那次對《刑事訴訟法》的修改。
三、司法解釋力攻閱卷難卻彰顯新《刑事訴訟法》修改弊端,限制偵查、檢察卷宗移送的修改是倒退。
1998年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關于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一委兩院三部司法解釋)第13條第2款規定:“在法庭審理過程中,辯護律師在提供被告人無罪或者罪輕證據時,認為在偵查、審查起訴過程中偵察機關、人民檢察院收集的證明被告人無罪或者罪輕的證據材料需要在法庭上出示的,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向人民檢察院調取該證據材料,并可以到人民法院查閱、摘抄、復制該證據材料。”第41條規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款規定:‘法庭審理過程中,合議庭對證據有疑問的,可以宣布休庭,對證據進行調查核實。’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款規定:‘法庭審理過程中,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人有權申請通知新的證人到位,調取新的物證,申請重新鑒定或者勘驗。’根據上述規定,人民法院可以向人民檢察院調取需要調查核實的證據材料、人民法院也可以根據辯護人、被告人的申請,向人民檢察院調取在偵查、審查起訴中收集的有關被告人無罪或者罪輕的證據材料。人民檢察院應當自收到人民法院要求調取證據材料決定書后三日內移交。”
1998年9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最高院刑訴法解釋)第158條規定:“人民法院向人民檢察院調取需要調查核實的證據材料,或者根據辯護人、被告人的申請,向人民法院調取在偵查、審查起訴中收集的有關被告人無罪和罪輕的證據材料,應當通知人民檢察院在收到調取證據材料決定書后三日內移交。”
新《刑事訴訟法》做出前述的重大修改,顯然意在控制控辯雙方在證據信息方面的持有度,并且向控方做了傾斜,即由原來的全盤托出,變為現在有條件有控制地透露。除非辯方依法提出請求(這種請求還得受法庭許可限制),控方便只能按《刑事訴訟法》150條規定向辯方展示證據信息。控辯雙方均享有調查權,顯然這種調查權并不平等。控方除享有國家強制力做調查權的后盾外,對調查對象無任何限制;而辯方不但無任何后盾支持,對調查對象也做了廣泛的限制,辯護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調查權幾乎微不足道。在現行的刑事訴訟體制下,辯方的證據信息幾乎全部來源于控方。在控辯雙方在證據信息掌握本就極不對稱的情況下,新《刑事訴訟法》卻又做出了向控方傾斜的修改,顯然對辯方行使辯護權是極其不利的,稱其為倒退也不為過。
而上述一委二院三部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前述兩個司法解釋,顯然是為了彌補新《刑事訴訟法》修改后所帶來的此種弊端,因為上述三條司法解釋都一致強調人民法院(辯護人也有權向人民法院申請)有權調取在偵查、審查起訴中收集的有關被告人無罪或罪輕的證據材料,而這些證據材料在未修改《刑事訴訟法》之前是不需要人民法院調取的,檢察機關在提起公訴時自會一古腦移送過來。應該說,上述司法解釋的出發點是好的,甚至是用心良苦的,但美好的愿望在實踐中卻難以實現。因為無論是對法官還是辯護律師而言,達到司法解釋的目的有一個前提,那就是:辯護律師“認為”偵查、審查起訴過程中,偵查機關、檢察機關收集的證據材料中,有證明被告人無罪、罪輕的證據。而辯護律師未閱卷,又怎知有沒有?
新《刑事訴訟法》上述重大修改的利處未見,而其弊端是顯而易見的。于其這樣處心積慮多次反復彌補這種弊端,何如直截了當地再回到從前?!原本對審判機關、辯護律師不“保密”的偵查、檢察卷宗,又何必在修改《刑事訴訟法》以后猶抱琵琶半遮面變得如此神秘起來?這種本來在庭前就可讓審判機關、辯護律師了解的信息,非等到庭審過程中法官、辯護律師提出以后才被動地提供,除了浪費了寶貴的司法資源還有什么?!
四、上述三條司法解釋是解決目前閱卷難的充分法律依據和重要的法律保障。
應該說,一委兩院三部司法解釋第13條第2款中的辯護律師的“認為”,是一種主觀認識,強調的是主觀未強調客觀。也就是說,不論偵查、檢察機關收集的證據材料中,是否客觀存在對被告人無罪或者罪輕的證據,只要辯護律師“認為”有,就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調卷申請,人民法院就應向檢察機關調卷。只有這樣理解,該條司法解釋才具有合理性和實際意義,否則,便陷入了雞生蛋蛋生雞的怪圈,而變得毫無意義。如果能這樣理解該條司法解釋,檢察機關、審判機關又能不折不扣地依據該條司法解釋來執行,應該說,因新《刑事訴訟法》所做前述重大修改所帶來的弊端就完全消除了,困繞律師界的閱卷難這一老大難問題便不復存在了。果真如此嗎?
顯然對該條司法解釋的理解和執行均不盡如人意。著名的刑法專家、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刑事辯護專業委員會副主任顧永忠律師、博士、教授就沒有這么樂觀。他甚至認為該條司法解釋是公檢法機關為安慰律師閱卷難的情緒而做,只起安慰作用,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在2005年3月在海口舉辦的“中加刑事司法改革與辯護項目培訓會議”上,顧永忠律師做了《刑事辯護中的發問、舉證及質證》的精彩報告。顧律師在報告中一再強調“預測”的重要,諄諄告誡受訓律師“舉證前要對控方如何質證做好預測和對策”,“對控方未移送的證據做出分析預測”,而對前述三條司法解釋卻只字不提。當有律師就前述三條司法解釋請顧律師做出評價時,他便發表了“安慰情緒”的高論。正是因為他有了“安慰情緒”的“成見”,他自然不會對上述三條司法解釋有多高的評價。
顧永忠教授做為身經百戰的知名律師,他何償不希望上述三條司法解釋真的得到貫徹執行?“安慰情緒”論恰恰是上述三條司法解釋在實踐中執行情況的無奈真實寫照!法庭上的控辯雙方中的一方要靠“預測”來揣摩對方的證據信息,對辯護律師來說已經達到了可以用“殘酷”來形容的境地,沒有理由讓這種不對稱更是不公平的現象繼續下去了。
實事求是地說,如果不把一委兩院三部司法解釋第13條第2款中的辯護律師“認為”理解為一種主觀認識,而是理解為一種客觀存在,甚至要求辯護律師拿出“認為”的證據,顯然該條司法解釋在庭審前的意義和作用就不大了,但也不能說毫無作為。因為在控方庭前向法庭舉證的主要證據復印件里,往往辯護律師會發現一些蛛絲馬跡,這些完全可以做為辯護律師“認為”的證據。因為辯護律師的“認為”有了證據,其向人民法院的調卷申請便有了理由。
如果辯護律師在庭前找不到“認為”的證據,在庭審過程中,隨著控方全部證據的出示,隨著證人、鑒定人等訴訟參與人的到庭,辯護律師還有大量機會發現“認為”的證據。這時,當然可再向人民法院提出調卷申請。如果辯護律師被迫在庭審中提出調卷申請,正在進行的庭審也得被迫休庭。
正是從上述意義上說,將一委兩院三部司法解釋第13條中的辯護律師“認為”界定為“客觀說”不僅在邏輯上是矛盾的,對辯護律師是不公平的,對庭審也是不利的。一個不言自明的道理是:為什么一定要自己找自己的麻煩,把本來在庭前就應該解決也能夠解決的問題,一定放在庭審中被動地解決,一定要耗費不必要的人力物力才去解決?由此,也彰顯了此種訴訟體制在設計上的缺陷和不足。
上述三條司法解釋是在目前法律柜架下解決閱卷難的充分的法律依據和保障,盡管目前在認識上和執行上還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有充分理由相信,只要本著實事求是的思想,認真貫徹執行上述三條司法解釋,閱卷難在目前的訴訟體制下也完全可以得到有效解決。
文檔上傳者
- 藝術設計淺議
- 淺議副職領導如何盡責
- 班組績效管理淺議
- 星巴克營銷策略淺議
- 淺議寒冷地區造林模式
- 畜牧品種的良種現狀淺議
- 醫學地質學淺議
- 淺議廣告燈具的設計
- 淺議循證護理實踐研究
- 淺議油畫創作的動力來源
熱門文章排行
- 淺議城市軌道交通運營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