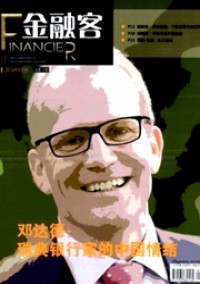我的地壇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我的地壇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我的地壇范文第1篇
如果真是這樣,課文兩部分惟一的聯系就是文章中“現在我才想到,當年我總是獨自跑到地壇去,曾經給母親出了一個怎樣的難題”的一句話,許多老師也正是通過這句話從地壇過渡到母親的。我們知道原文除了寫母親,還寫到了在地壇活動過的幾個人物:一對夫婦、一個唱歌的小伙子、一位運氣不佳的長跑者、一對兄妹等。這樣一來,文章就有了兩條線索,其一是物,其二是人,而兩者惟一的聯系是人在物中活動過,實質兩者是各自為政,缺少內在聯系的,因而活動在地壇中的人物之間也同樣缺少內在聯系。
筆者認為本文各部分是由作者對生命的感悟連成一個統一的整體的,對生命的感悟也是物和人之間內在的聯系。
讓我們來回想寫地壇的那部分。一個活到最狂妄年齡上的青年忽地遭到了人生的重創,這時他與一座廢棄的古園遇合了,它帶來的是一種生命的共鳴。作者理解了地壇的全部感情和意蘊,園子荒蕪但并不衰敗,在凝重、滯澀、艱難作底色的畫面中則洋溢著生命的律動,從而作者獲得了對生命、對生和死的感悟:“一個人,出生了,這就不再是一個可以辯論的問題,而只是上帝交給他的一個事實;上帝在交給我們這件事實的時候,已經順便保證了它的結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個必然會降臨的節日。”
作者終于走出了殘疾人自傷的陰影,這時“剩下的就是怎樣活的問題”了。有人認為這個問題地壇實際上已幫他解決了,從對地壇六個“譬如”的景物描寫中,可知作者明白了生命會有未知的突變,充滿滄桑,帶著苦難,但絕不能改變生命的本色,那就是熱愛生命、頑強地生活,并且活得光輝燦爛。可是我始終認為地壇給作者的只是一些道理上的啟示,關于怎樣活的問題,作者說“不是在某一個瞬間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能夠一次性解決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終身的魔鬼或戀人”。當然作者最終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證明他解決了這個問題,而這一切主要歸功于母親。“母親生前沒給我留下過什么雋永的哲言,或要我恪守的教誨,只是在她去世之后,她艱難的命運、堅忍的意志和毫不張揚的愛,隨光陰流轉,在我的印象中愈加鮮明深刻。”是母親艱難的命運、堅忍的意志和毫不張揚的愛讓史鐵生明白了怎樣活的問題。
對于母親毫不張揚的愛,我們從母親送、憂、找他時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中已經感受得很深了,而對作者的生命更有價值、更有意義的東西,那就是母親艱難的命運和堅忍的意志。
母親命運的艱難表現在以下幾點:一是生活操勞。她有一個殘疾的兒子,生活上必須照顧他。二是精神壓力。兒子殘疾后常常想著自殺,她時刻處于擔心害怕中,還要小心翼翼地維護兒子那可憐的賴以生活下去的自尊。三是病痛折磨。“她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來覆去地睡不了覺……”(史鐵生《秋天的懷念》)而這一切兒子卻全然不知,“一心以為自己是世上最為不幸的一個,不知道兒子的不幸在母親那兒總是要加倍的”,“這樣一個母親,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親”。可是這一切,母親一個人全都默默地承受住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沒有吭一聲。母親對待命運的堅忍、頑強、不屈不撓的意志在她死后愈現愈明。
母親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話是:“我那個有病的兒子和我那個還未成年的女兒……”(史鐵生《秋天的懷念》)作者說“我懂得母親沒有說完的話。妹妹也懂。我倆在一塊兒,要好好兒活……” (同上)作者在母親的身上找到了另一個問題――怎樣活的答案,母親用自己的一生告訴兒子“要好好兒活”,即不管命運是怎樣的艱難、不公、多舛,也要憑借堅強的意志,勇敢地走下去,直到生命的盡頭,同時寬容生命,多給予他人理解和愛。史鐵生用他的實際行動告訴我們,他做到了,他成為了一個成功的作家,他笑對人生,他學會了理解他人(史鐵生曾為失利的世界田壇巨人劉易斯作了一首詩,表達了自己對劉內心痛苦的理解,對此本文不再贅述)。
我的地壇范文第2篇
關鍵詞:史鐵生 《我與地壇》 自然與生命 詩與哲 經典性
我與地壇像一對戀人,一旦相遇,便再也無法長久地離開;一旦相遇,心中的躁動便兩相著落。于是我熱忱地享受生命,在我雙腿永遠無法著落的地壇上,至此,我與地壇彼此靜默十五年。地壇于我,就像是安置心靈的容器。
這便是筆者眼中的史鐵生與他的地壇。
《我與地壇》發表于1991年《上海文學》第一期。此時史鐵生40歲,四十是一個充滿迷惑與智慧的人生階段。史鐵生正是在這種狀態下,寫下這篇寓哲理與詩情為一體的散文。
“他覺得文學不僅是回應現實,而且是在一個千變萬化的社會里頭一直在尋找,尋找那個不變的、那個所謂的終極意義。這個尋找的過程是‘從不屈獲得驕傲,從苦難提取幸福,從虛無中創造意義。’”[1]
《我與地壇》正是這樣一個對自然、生存、生命、苦難、命運這些哲學母題的尋找:探尋自然之于人類的意義,追問苦難之于命運的價值,關注人類之于宇宙的存在。也正是這種尋找使史鐵生的散文成為“美文”,同樣的,對“自然”與“人生”兩大母題的闡釋也使《我與地壇》成為“經典”。
一.史鐵生對自然的解讀
《我與地壇》中的“自然”與我們平日說的“自然”不盡相同,它是一種具有局限性的自然概念。狹義地看,《我與地壇》中的自然指的就是地壇。然而從廣義來說,文中論及的園中事物,如古殿檐頭、草地頹墻、老樹石門、螞蟻瓢蟲、古柏藤蘿,文中涉及的園外意象,如滿地月光、石門落日、雪地腳印、雨燕之歌、秋風早霜,文中關于四季的比喻,關于園神的臆想都應該屬于自然范疇。
從這一界定出發,我們來看史鐵生對于自然的定位、態度及存在意義,就可以分別得出以下論斷:狹義的自然對于作家來說是“家”之存在,而廣義的自然則是作家的“審美”寄托,作者在對自然的書寫過程中流露出了明顯的自然崇拜傾向并將萬物賦予意志,帶有一定的泛神論色彩。
1.“家”之存在
“地壇離我家很近。……五十多年間搬過幾次家,可搬來搬去總是在它周圍,而且是越搬離它越近了。我常覺得這中間有著宿命的味道:仿佛這古園就是為了等我,而歷盡滄桑在那兒等待了四百多年。”[2]
對地壇的描寫從一開始就帶了明顯的暗示性意味。史鐵生運用了“宿命輪回”觀念來影射我與地壇的關系,打破了地壇與真實的家的界限,樹立了地壇“家”之存在地位。之后,作家又將地壇環境定位為一種“家的陳列”:“它為一個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準備好了”,這使得作家的心靈得到了歸屬感,此心安處是吾鄉,從而推出地壇是史鐵生盛放心靈的容器,寄托懷抱的家鄉,故而史鐵生對地壇的定位也不言而喻即“家”。
然而,這個“家”與我們世俗世界的家的定義又有不同:世俗之家上演著人間悲喜,而地壇卻是個“寧靜的去處”;世俗之家常有誤會猜忌,而地壇卻讓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它的意圖”;世俗之家有時讓人貪戀,有時讓人厭倦,而地壇卻讓我“再沒長久地離開過”。無論是從地理位置上,還是從契合程度上,地壇都完全符合“我”的心意,“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所以,史鐵生所描述的地壇,像家而不是“家”,明顯地表露出作家的個人喜好傾向,是作家主觀構建的微型“烏托邦”。
2.“審美”寄托
審美是對美的審視,既包括對美的探尋,又包括對美的理解。在《我與地壇》一文中,史鐵生通過自然與心靈的通感,嚴肅而又認真地思考“美是什么?”這一命題。而地壇在作家審美,追美的這一過程中充當了盛放“美”的具象化容器,表達了作家的審美觀念。
文本中的嗩吶聲無疑是一種象征,隱喻著“美的召喚”。我們一般認為,美無定則,而文中這樣形容嗩吶聲的來由,作家說“我看不見那個吹嗩吶的人”。如果“嗩吶聲”是“美”的象征的話,那么“吹嗩吶的人”則可以被認為是美的濫觴,美的本質,而美的本質是無法言說的,美的濫觴也是美學家一直追求而沒有結論的謎題。史鐵生不僅是一位哲學家,也是一位美學家,在追求美的道路中,他得出了“我看不見那個吹嗩吶的人”這樣的結論。
美有形態。美的本質無法界定,但世界上的美卻有各種各樣的表現形式。“嗩吶聲在星光寥寥的夜空里低吟高唱,時而悲愴時而歡快,時而纏綿時而蒼涼。”這正是美的形態,美無常型。
美是永恒存在。無論時代歷史如何變遷,無論審美傾向如何發展,人類思維中都會存在“美”的概念。它既具有共時性,又具有歷時性。正如文中所說:“我清清醒醒地聽出它響在過去,響在現在,響在未來,回旋飄轉亙古不散。”
在最后,作者寫道:“必有一天,我會聽見喊我回去。”很多人下意識地會想到:這是生命終結的召喚,是邁向死亡之音。但筆者卻認為,這正是史鐵生的“皈依”,對美的皈依,他走向的是永恒的美的歷史之流。這種“走向”,既是追求,亦是回歸。
寄托審美,這是地壇之于作家的最重要意義。
二.史鐵生對生命的解讀
史鐵生對生命的解讀是其散文中一以貫之的命題,學界在此之前也頗多論述。本文主要以其輪回觀、命運觀、生死觀三個維度來闡釋史鐵生對生命的理解。其輪回觀主要體現在他在《我與地壇》文本中對“人生三態”的敘述;命運觀則是以其對“苦難意義”的詮釋為代表;至于生死觀,更多的表達了對生命的禮贊以及面對生死兩事的態度。三個方面并立而行,各抒己見,又互為表態,相互佐證,拼湊起史鐵生完整的生命觀。
1.“人生三態”與輪回觀
“人生三態”指的是史鐵生在《我與地壇》最后一節中描寫的人生所必須經歷的三個階段:孩童階段、情人階段和老人階段,亦是人在認識世界過程中的三種狀態:好奇狀態、熱戀狀態、回歸狀態(抑或沉靜狀態)。
孩童階段的人對世界充滿了好奇心,他有無盡的精力與無數的念頭,這可以看作人的青少年時期:人剛剛打開自由認識世界的大門,對一切都新奇,渴望嘗試;情人階段的人對世界充滿了迷戀,他有對這個世界的基本認知,并且渴望享受世界、改變世界甚至創造世界,可以看作是人的成年期:人有能力去創造物質或精神產品,對于固有的物質精神基礎,或單方面享受以滿足自我需求,或積極創造以期實現個人價值;而老人階段的人則形成了對世界各自的獨立的理解,走向生命的終結,回到世界的起源,這可以看作人的老年時期:人經歷了好奇與熱戀狀態,開始回顧與思考,沉淀與升華,形成了自己對世界的理解,走向死亡。
史鐵生在這里對于死亡則稱為“回去”,這一詞是體現其輪回觀的關鍵,他認為死亡不是終結,而是一種新生。他認為:“有一天,我也將沉靜著走下山去,扶著我的拐杖。那一天,在某一處山洼里,勢必會跑上來一個歡蹦的孩子,抱著他的玩具。”我的死亡與孩子的誕生,正體現了生命不息,輪回不止的觀念。
“當然,那不是我。
但是,那不是我嗎?”
“但是,那不是我嗎?”是極其深刻的一問,其中表明了史鐵生的輪回觀:軀殼多樣,但靈魂不滅。靈魂經歷人生三態,再經過死亡的淬煉與出生的洗禮,復又重來,無止無息。正如他所說的:“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將一個歌舞煉為永恒。這欲望有怎樣一個人間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計。”他認為人的本質就是“欲望”,靈魂也是“欲望”。欲望不變,宇宙不滅,人類悲喜永恒上演。
2.“苦難意義”與命運觀
史鐵生在“最狂妄的年紀”失去了他的雙腿,這無疑是他人生中的最大苦難之一;而他在明白母愛之前失去了母親,這無疑又是他另一重大苦難。而命運的真正苦難其實在于其必然性與不可避免性。
生病貫穿了21歲之后的史鐵生的生命全部。21歲史鐵生大病,從此之后再也沒能站立。他生前曾經自嘲:“職業是生病,業余是寫作。”然而史鐵生在《病隙碎筆》中卻將生病視為別開生面的游歷“由病悟理,妙語哲思揮灑于字里行間。”
然而,生病的苦難并不因其自嘲終結,在《我與地壇》中,我因苦難而暴躁,造成對我的母親的傷害令作家再也無法挽回。作家在文中說:“只是在她猝然去世之后,我才有余暇設想,當我不在家里的那些漫長的時間,她是怎樣心神不定坐臥難寧,兼著痛苦與驚恐與一個母親最低限度的祈求。”母親對我的尋找,與我躲開母親的尋找成為主要情節之一,而不幸的是,我還沒有來得及體悟,母親就先一步去了。“多年來我頭一次意識到,這園中不單是處處都有過我的車轍,有過我的車轍的地方也都有過母親的腳印。”寥寥幾筆,便體現出喪母之痛與懊悔之意。
殘疾、喪母、疾病都帶給史鐵生沉重的苦難,然而真正的苦難――命運的必然性才是最令作家感到絕望的。他在《病隙碎筆》中起筆便詮釋命運與角色的獨特解讀:“所謂命運,就是說,這一出“人間戲劇”需要各種各樣的角色,你只能是其中之一,不可以隨便調換。”[3]在小說《一個謎語的幾種簡單的猜法》中有一段對于命運的絕佳闡述:“萬事萬物,你若預測它的未來你就會說它有無數種可能,可你若回過頭去看它的以往,你就會知道其實只有一條命定之路。”[4]在《務虛筆記》中史鐵生對于女教師O的塑造便是因襲了這樣一種理念:“如果你站在四歲的O的位置展望未來,你會說她前途未卜,你會說她前途無限,要是你站在她的終點看這個生命的軌跡你看到的只是一條路,你就只能看見一條命定之途。”
“命定之路”的反復出現充分佐證了史鐵生對于命運的必然性的確定即定命論。定命論是史鐵生命運觀的最主要觀點,也這種命運的不可琢磨性與不可改變性導致了史鐵生的絕望,但同時當作家將自身投擲于宇宙萬物之間,又將這“命定之途”看做是一種平衡,一種規律。
3.“生命禮贊”與生死觀
命運的不公并不能阻擋史鐵生對生命的熱忱,他熱愛生命以及生命的活力。
這體現在他在地壇中所看到的蕓蕓眾生相:十五年風雨無阻來院子里散步的夫妻,熱愛唱歌的小伙子,獨一無二的飲酒的老頭,樸素優雅的中年女工程師,最有天賦的長跑家朋友,一個漂亮而不幸的小姑娘和愛她守護她的哥哥。他贊頌著夫妻對愛情的詮釋,小伙子對夢想的執著,老頭體現的對個性的堅持,女工程師的生活態度,長跑家朋友的堅持與放棄,兄妹間相守相偎的親情,他贊頌,這些努力活著,存在著的人們,這些鮮活并有所堅持的生命。
史鐵生認為,生是既定的,人類在沒有選擇權的時候,就已經被確定了“生”的權利,而死也是既定的,同樣人類沒有自,那么,人類就只能努力活著,這種活著,無論呈現出怎樣的姿態,都值得禮贊,因為每個人都是向死而生。所以,生亦不可喜,死亦不可悲。這便是史鐵生的生死觀。
面對未知的死亡,史鐵生選擇了觀望:“甚至盼望站到死中,去看生。”[5];也有著本能的懼怕:“怕死的心理各式各樣。作惡者怕地獄當真。行善者怕天堂有詐。”[6]卻更選擇了淡然:“‘輕輕地我走了,正如我輕輕地來’――我說過,徐志摩這句詩未必牽涉生死,但在我看,卻是對生死最恰當的態度,作為墓志銘真是再好也沒有。”[7]
面對已然的活著,史鐵生在《我與地壇》中說“我有時候倒是怕活。可是怕活不等于不想活呀?……人真正的名字叫做欲望。”“活著不是為了寫作,而是寫作為了活著。”而史鐵生的欲望究竟是什么呢?再明顯不過,史鐵生的欲望就是活著,有意義地活著。寫作是他承載意義的體現其生命存在的形式載體。這種活著的欲望之強烈,讓人震撼。
史鐵生在《好運設計》中說:“過程!對,生命的意義就在于你能創造過程的美好與精彩,生命的價值就在于你能夠鎮靜而又激動地欣賞這過程的美麗與悲壯。”[8]我想這是作家設想的最好的活著的狀態。他在死亡殘疾的陰影下彰顯了一種欲望之力,對死亡不畏懼,對生活不輕視,令人肅然起敬。
三.“自然”與“生命”中的“詩”與“哲”
《我與地壇》的構思十分巧妙,它將作家對審美、秩序、自然、宇宙、輪回、苦難、人生、命運等宏大母題的思考,寄托在地壇公園這一載體上,從而使概念的詮釋擺脫了空洞、晦澀、抽象等理論解釋的危險,合目的地將概念具象化、平易化、詩意化,體現了史鐵生作為哲人的深刻與作為詩人的優雅,這也是史鐵生散文在當代文壇中獨樹一幟,別具一格的主要原因。
作家對“自然”的用情之深使《我與地壇》顯出濃厚的詩意,而他對“生命”的思索追問又使《我與地壇》蘊藉著沉重的哲思。“我與地壇”正是對位“人”與“自然”、“生命”與“自然”,二者既相互寄寓,又相互補充,作家用詩歌的深情禮贊自然,用哲學的深思謳歌生命。
“史鐵生以‘無我之問或無果之行’,去‘發現什么的根本處境,發現什么的種種狀態,發現歷史所曾顯現的奇異或者神秘的關聯,從而去看一個亙古不變的題目:我們的心靈的前途和我們生命的終極價值終歸是什么?’
史鐵生因此可以說:我已不在地壇,地壇在我。”[9]
“比天空更博大的,是人的胸懷。”史鐵生身處地壇,同時將地壇的一切內化于心,試圖通過對自然的感應,對宇宙的觀望,追問人類的終極價值。而在對“自然”與“生命”的詩性追問中找尋到了最理想的平衡狀態:
人類活著如同自然般自由,自然與人類同享活著的自由。
史鐵生散文中的“詩”與“哲”也是這樣平衡的關系。我們在閱讀史鐵生散文時,不僅可以得到審美的凈化,更可以攝取思考的快樂。從文本接受的角度來看,有機融合了“詩”與“哲”的文本帶給讀者的閱讀體驗更深層次亦更具持久,這也是我們論證史鐵生散文的經典性的主要論據之一。
另一方面,就文本本身而言,史鐵生散文所涉及的“自然”與“生命”這兩大主題,不僅是文學創作不可繞開的母題,更是哲學、歷史等人文科學領域中的“終極”問題。史鐵生的思考從一開始就是站在一定的廣度與深度上的,這種思考既是其行文的開始,亦是其行文的終極目的,故而我們說史鐵生散文的“經典”是主題內容上的,更是思想內涵上的。
除了內質的經典性,史鐵生散文的藝術手法也是其“經典性”的重要成因之一。語言的詩意優雅與深邃雋永,段落長短、敘述詳略及抒情節奏的恰到好處,文本情緒的跌宕起伏與收放自如使其散文既完整又完美。在藝術上,《我與地壇》更可比是現當代散文集大成之作。
“用殘缺的身體,說出了最為健全而豐滿的思想。他體驗到的是生命的苦難,表達出的卻是存在的明朗和歡樂,他睿智的言辭,照亮的反而是我們日益幽暗的內心。”這是對史鐵生散文內核的精練概括,也是史鐵生散文經典性的有力論證。
身負殘缺而自強不息,身遭不公卻厚德待物;生而筆耕不輟,如夏花之絢爛,死時平淡安詳,如秋葉之靜美;其文其人都為“經典”,其詩其思是當代文壇永恒的光耀,這才是哲詩人――史鐵生。
參考文獻
[1]史鐵生.靈魂的事[M].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4.
[2]史鐵生.史鐵生散文[M].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3.
[3]史鐵生.史鐵生作品系列?病隙碎筆[M].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
[4]史鐵生.世紀文學60家?史鐵生精選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7.
[5]王堯,林建法主編.薛毅著.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大系?荒涼的祈盼――史鐵生論[M].蘇州大學出版社.2012.6.
[6]劉錫慶.中國散文通史?當代卷下[M].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1.
[7]汪雨萌.史鐵生研究綜述[J].當代作家評論,2012(4):160-169.
[8]汪雨萌.史鐵生文學年譜[J].東吳學術,2013(3):122-134.
注 釋
[1]王堯:《錯落的時空?說史鐵生》,河南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155頁。
[2]后文此字體不加特殊說明皆為引用原文。原文參照《史鐵生散文》,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3月第一版。
[3]史鐵生:《史鐵生散文》,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第121頁。
[4]史鐵生:《史鐵生作品系列?命若琴弦》,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第348頁。
[5]史鐵生:《靈魂的事?輕輕地走與輕輕地來(代序)》,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第4頁。
[6]史鐵生:《史鐵生作品系列?病隙碎筆》,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第34頁。
[7]史鐵生:《靈魂的事?輕輕地走與輕輕地來(代序)》,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第1頁。
[8]史鐵生:《史鐵生散文》,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第43頁。
[9]王堯:《錯落的時空?說史鐵生》,河南大學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第155頁。
我的地壇范文第3篇
我首先“貪”的就是幽默風趣。我先來不喜歡看別人怒氣沖天的樣子,我認為他人的笑才是最美的風景。所以,當看到別人火冒三丈時,我總會馬上變成“開心糖”,讓別人發出來自內心的甜美的微笑。最后,心里愉快地說一句:“耶!我成功了!”
我又把寬容給毫不猶豫地 “貪”了。雨果曾經說過:“世界上最廣闊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廣闊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廣闊的是人的胸懷。”的確,退一步海闊天空。蕭伯納不就是這樣嗎?被別人撞了,還用幽默的話語寬容了別人。我又何嘗不是呢?還記得有一次,我穿著新衣服高興地去了學校,在美術課上被同學弄臟了,我并沒有生氣,而是一笑而過。回家后,媽媽見我的衣服上有污點,便問道:“衣服怎么弄臟了?”“哦,沒什么。同學一不小心把墨汁灑在了我的身上。”“那可洗不掉啊的呀!”“算了,大不了不穿了唄!沒事。”
我把不怕失敗也“貪”了。愛迪生的這樣一句話令我反復想了好久:失敗也是很重要的,它和成功一樣對我很重要。不錯,勝敗乃兵家常事。前幾天,我鼓起勇氣參加了班長的競選。可是,我失敗了,沒有如愿以償。在以后的幾天里,我想了很多。一開始,我確實不能接受這次失敗。后來,我想明白了,失敗是成功的階梯,如果我從失敗中吸取教訓,看到自己的不足。從而改進自己的做法,就能走向成功。我堅信,在不久的將來,我會成功!失敗一小步,成功一大步!
我的地壇范文第4篇
處處要吃(貪吃)
啊,陽光正好啊!我走在小路上,忽然,我看見蔣濤在一旁吃烤腸,我兩眼冒光,湊了上去,蔣濤見了我,感到情況不妙,立即裝著什么也沒看見,向一旁走去。我見了,一下子跳到他的跟前,大聲問道:“還是不是哥們了?”“不,不是”。蔣濤略帶恐慌地說。“好,你給我記著,下次……”還沒等我說完,蔣濤連連說道:“好,好,不就是一根香腸嘛,你咬一小口好了。”我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一口把香腸全吞了。忽然,我看見第五瑞卿在喝粉絲湯,又湊了過去……
玩字當頭(貪玩)
我這個人,可是只顧著玩,不顧著學。這不,星期六下午,我和媽媽在家。忽然,媽媽有事得出去一趟。哈哈!可以自由自在的玩嘍!媽媽前腳剛出門,我后腳就出門玩去了。我一直玩到五點多,媽媽突然打了個電話給我,說:“兒子,作業做完啦?那先回來檢查一下作業吧!”完了,這下“大難臨頭了”……
天天遲到(貪睡)
我這個人呢,就是每天早上愛睡懶覺。這可不,弄得我每天早晨都最后一個到班里,不過還好,每次到的時候老師都在做操,不用老師批。不過,今天就慘了。今天下雨,老師不用做操。我剛踏進教室的門,老師的問題就像一個個千斤重的石頭,壓得我鼻子酸酸的……
向爸媽要零用錢(貪財)
我呢,也不貪財,這根本是莫須有嘛。這是有些變本加厲。比如說,今天我要一塊錢,明天我會要二塊錢;今天要二塊錢,明天就要四塊錢。這可不是,我又向老爸要零用錢了。我苦口婆心的說道:“老爸,如果你不給我零用錢,我就沒有好心情,沒有好心情,做事就不認真,做事不認真,學習不認真,成績就不好,成績不好,就……”,但無論怎樣說,爸爸也不給。哎,真是的,一分錢也不給,卻浪費了我這么多時間。真是偷雞不成蝕把米。
嗨,我什么時候才能改掉這些壞毛病呢?
我的地壇范文第5篇
雀兒山路二小三?3?班:覃喬松
我的學校很漂亮,那風景美不勝收,令人心里永遠有一個字“美”。
學校的春天,陽光明媚,草地上開滿了綠油油的小草,五彩繽紛的鮮花顯得格外鮮艷。粗壯的大樹抽出了嫩芽,小鳥在樹上嘰嘰喳喳的叫,好像在說∶“春天的校園真美啊!”
夏天到了,茂盛的榕樹像一把巨傘,同學們在大樹下盡情地自由自在地游戲。看,他們有的乘涼,有的寫作業,有的看書,有的跳繩,還有的踢毽子,他們玩的多快樂呀!
秋天的校園又是一番景象。湛藍的天空,好像一塊用清水洗過的藍寶石一樣,茂盛的榕樹落葉了,一片片金黃的落葉飛落下來,好像一只只翩翩起舞的蝴蝶騰空而起,漂亮極了!
冬天的校園冷索索的。北風呼呼地吹,好像在說∶“冬天到了正是我值班的季節。”同學們正在操場上,做廣播體操,齊刷刷的動作,好像在說∶“春天還會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