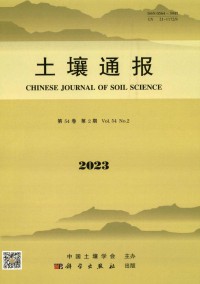土壤學總結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土壤學總結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土壤學總結范文第1篇
Abstract: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modern teaching in soil science courses and cultivate high quality talents with innovative consciousness and innovative ability, and based on inquiry teaching method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d the connotation of inquiry teaching method, and the concrete application in soil science course, and obtained good results.
Key words: inquiry teaching method; soil science; teaching reform
土壤是農業生產的重要自然資源,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土壤學不僅是與農業生產密切相關的一門學科,而且還是高等院校農林類專業的一門重要專業基礎課。伴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引起的自然資源日益短缺、食品安全和環境保護問題(這些都是土壤學服務的領域),學習土壤學知識顯得尤為重要[1-2]。
由于土壤學課程內容豐富,涉及知識面廣,概念繁多,知識抽象,理論性和實踐性強,而長期以來土壤學課程以傳統的“教師主導+學生被動”為特征的灌輸式教學方法為主導,形式單調,只注重對學生以授為主的單向知識傳遞,因而造成學生完全是被動地接受教師理解和整理過的土壤學相關理論知識,缺少師生教學互動,也談不上讓學生主動發現、思考和解決遇到的實際農業生產問題,更不能培養和增強學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同時也束縛了學生的個性發展,學生缺乏主動探索土壤學學科領域知識的精神,這不利于學生自主學習、科研素養和創新實踐能力的提高[3]。與此同時,《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和《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深化高等學校創新創業教育改革的實施意見》([2015]36號)文件也要求深化高等學校創新教育改革,改革傳統教學方法,以適應現代社會對高素質人才需求。因此要想克服以上土壤學課程的傳統教學缺點,只有通過引入先進的教學方法,充分提高和激發學生對土壤學課程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真正使教學成為學生好學、教師樂教,培養和提高學生對土壤科學探究和創新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為此,在土壤學課程中運用了探究式教學方法。
1 探究式教學法內涵
探究式教學法又稱發現法、研究法。它不同于教師“傳道、授業、解惑”和學生“聆聽、接受、模仿”的傳統教學方法,而是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模式,其宗旨是培養創造性人才。主要教學過程是在教師根據課程內容精心設計科學問題的誘導下,在學生掌握現有知識基礎上,引導學生在通過獨立自主學習和相互廣泛合作討論,為學生創造探索疑問、自由表達、深入討論問題的空間,使學生能自主完成探究學習、與本課程相關知識內容學習以及解決實際生產生活中問題的一種教學形式[4-5]。
探究式教學法突出以培養學生創新精神、創新能力、自學能力為教育理念,發散學生創新、創造性思維,引導學生利用現有知識通過自我探究學會學習的一種方法,培養他們終身學習能力以及為日后創新性工作奠定良好基礎。作為探究式教學引導者的教師,在充分駕馭相關學科知識背景前提下,依據教學要求篩選科學合理具有挑戰性的問題,啟發引導學生思考,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充分調動學生獲取新知識的積極性,培養學生“生疑、質疑和釋疑”的能力。與此同時,教師還要為學生積極營造融洽的探究氣氛,促使探究順利開展,把控探究廣度和深度,客觀、公正評價探究的得失經驗。另外,學生作為探究式教學的主人,在按照教師教學要求的基礎上,明晰探究目標,提高探究自覺性,主動思考探究問題,掌握探究方法,深入交換探究意見和建議,及時總結探究成果。由上可知,在探究式教學的過程中,既突出了學生的主體地位,又增強了學生的自主能力。可以說,探究式教學是教師為“導師”和學生為“主人”的雙方都參與的教學活動,是師生攜手探索新知識的學習過程。在整個教學過程中,學生不但學到了知識,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學到了獲得新知識的途徑。它不但滿足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高級專門人才這一高等教育任務,而且也符合當前國內外教育發展的新趨勢和當今社會對人才需求的標準[4,6]。
2 探究式教學在土壤學課程中的具體應用
2.1 科學合理創設問題情境,激發學生自身求知欲
探究式教學活動緊緊圍繞著探究問題展開。創設一個科學合理的探究問題情境,主要是讓學生形成問題意識,明確探究目標。這就要求教師科學設置一些既符合課程教學內容,又不越過學生知識面難度的適中問題情境。教師主要利用多媒體技術、網絡資源、實驗觀察、查看數據等方式,引導學生主動提出與土壤學課程內容有關的實際問題,比如種植綠肥為何能培肥土壤?小麥等作物為何要在春季追施氮肥?油菜為何會出現“花兒不實”[3],這些都能使學生在疑難情境中產生困惑,從而激發學生的求知欲,提高探究積極性,與此同時,也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和積極解決問題的能力,并進一步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和創新能力[6-7]。例如,在講解土壤有機質時,提出“土壤有機質對土壤肥力水肥氣熱有何影響?”這一問題。起初一看,可簡單地認為土壤肥力因素包括水肥氣熱,土壤有機質礦質化為植物提供養分就滿足土壤肥力“肥”這個因素;此時教師可以實時引導下一個問題“土壤有機質在土壤肥力中的作用還要考慮到改良土壤方面”,這就使得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產生了“土壤有機質是如何改良土壤”的疑問,讓學生明確下一步探究的任務,順其自然就產生了深入探究興趣,激發學生的探究欲望,主動地進入自學探究階段,主動通過各種途徑查閱相關資料,這樣不但培養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拓寬學生的知識面,也會給自學探究增添無限的動力和樂趣。
2.2 圍繞探究目標,充分挖掘學生自主探究潛能,最終完成主體探究
探究式教學的關鍵在于讓學生對開放性科學問題進行自主探究。對于充當“導演”角色的教師來說,應當積極正確引導和幫助學生根據已有經驗和知識水平對探究的問題展開相互討論,集思廣益,鼓勵學生提出不同假設和猜想。在教學過程中,積極營造和諧的探究教學氛圍,讓學生認為自己在學習過程中就是主導者,從而提高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鼓勵學生對提到的問題做出大膽假設,如種植綠肥的原因是肥料所含的作物所需營養元素比較多;油菜會出現“花而不實”是因為沒有蜜蜂的傳粉等。接下來,教師在制定詳細探究教學計劃的基礎上,幫助學生明確如何尋找科學合理收集證據的資料方法,引導學生通過試驗、觀察、查閱文獻、調查數據等多種途徑和形式圍繞問題收集有利于問題解開的相關資料。如小麥在不同生長期的需肥特點以及施入到土壤中氮肥的轉化和損失等,下一步,引導學生對所收集的相關資料進行綜合整理并對假設做出科學的解釋,比如小麥春季追施氮肥是由于小麥此時處于拔節期,需要大量氮肥,而氮肥在施入土壤后損失量比較大,所以必須分不同時期施給小麥等。最后引導和幫助學生再次檢查和思考探究計劃是否周密、資料收集是否完整和解釋是否科學,并對最后的結論做出可靠性評價。若結論與預先假設不符, 此時教師應引導學生重新確定探究方向,再次重新制定探究方案。比如根據油菜需肥特點,油菜會出現“花而不實”和蜜蜂的傳粉沒有關系,和油菜缺硼元素有關系;種植綠肥不僅是因為綠肥肥效高,而且能使土壤中難溶性養分轉化并有利于作物的吸收利用,改善土壤的物理化學性狀,促進土壤微生物的活動,最終引導學生明確種綠肥不僅是增辟肥源的有效方法,對改良土壤也有很大作用。再例如,學生對前文提到的“土壤有機質對土壤肥力水肥氣熱有何影響?”這個問題,主要提出了“土壤有機質是否可以提供植物生長所需要的養分?”、“土壤有機質是否可以改良土壤?”及“土壤有機質是如何改良土壤的?”這三個問題。教師要善于抓住時機,積極引導學生從以下2方面去加以探索:(1)土壤有機質給植物提供哪些生長所需要的養分?(2)土壤有機質改良土壤是改善土壤的水分物理性質及物理化學性質嗎?如果是,如何改善?進一步引導學生探究土壤有機質礦質化釋放植物所需營養元素,包括哪些養分元素?是否能滿足一季作物生長需要?若不能滿足,如何解決?與此同時,誘導學生弄清楚土壤水分的物理性質和土壤物理化學性質有哪些?它們是如何影響土壤肥力的?這樣既可以發散學生的思維,又能引人入勝,再加之學生自身具有強烈解決問題愿望,問題的釋疑也就水到渠成。這些對于對培養學生的綜合思維分析能力、提高應變能力等都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7-8]。
2.3 歸納總結,科學評價探究得失,引深探究
歸納總結,不但是對學生先前探究過程的總結,而且也是對探究成績的評價,其主要作用是了解學生是否掌握探究式教學方法。同樣在上面的問題中,問題的關鍵在于學生能否領會土壤肥力四大要素(水、肥、氣、熱)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也就是土壤有機質通過土壤有機質礦質化和土壤水分物理性質、物理化學性質來間接影響土壤肥力的四大要素。又如小麥在春季因為土壤中氮肥的轉化和損失要追施氮肥,那么磷肥、鉀肥是否也需要追施呢?學生很自然地聯想到土壤中磷、鉀肥的轉化和損失。也就是說通過這樣簡單的科學歸納,概括出要點,讓學生掌握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然后努力讓學生對自學和探究獲得的新知識真正運用自如,引深探究,學會舉一反三,能獨立解決類似問題。這樣學生既能收獲成就感,又能激發探究熱情,為日后探究學習打下堅實基礎。當然也要科學評價學生自主探究過程中的優點和缺點,學生或各組可以進行自評和互評,教師評價時要注重對學生在探究過程中的評價,不僅看最后的結果,也要給學生在探究活動中的表現給出有建設性的意見,這樣可以為學生今后解決類似或相關問題指明方向[7-9]。
土壤學總結范文第2篇
關鍵詞 項目教學法 課程實踐 探索
中圖分類號:G424 文獻標識碼:A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Project Teaching in Soil
Science and Agricultural Science Curriculum
LIU Qiaozhi, ZHANG Yan
(Xinjiang Shihezi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Shihezi, Xinjiang 832000)
Abstract Combine vocational education training mode, use the project teaching to put students into simulated work environment, through knowledge transfer, practical guidance, discuss cooperation to complete the study of knowledge and skills master, so that students better "Learning by Doing , doing in learning".
Key words project teaching; course practice; exploration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各國的課程改革都把學習方式的轉變視為重要內容。要使職業教育專業課的教學能“以技能為核心,以服務為宗旨”,與相關生產活動無縫對接,正確選擇教學內容――即項目內容是項目教學法產生有效作用的前提。結合目前職業教育的人才培養模式,為了給學生提供更多獲取知識的渠道和實際操作能力,筆者以職業院校灌溉與排水技術專業(節水方向)中的專業核心課程土壤學與農作學為例,研究探索項目教學法的具體運用,使學生在項目實踐過程中,理解和把握課程要求的知識和技能,體驗創新的艱辛與樂趣,培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思想和方法。
1 項目教學法在土壤學與農作學課程教學中的具體運用模式
將土壤學與農作學課程按照工作任務與職業能力、課程教學目標、教學組織與課程分配管理、教學內容與能力要求、教學方法與手段、考核與評價六大模塊的組織形式,進行項目教學法的具體運用。
1.1 工作任務與職業能力
按照該課程的內容特點,將工作任務與能力可根據實際教學的需要可按照如下模式進行(表1):
表1 土壤學與農作學課程工作任務與職業能力分析表
1.2 課程教學目標
以土壤――農作物為主線,指導學生掌握土壤學、農作學方面的知識。同時通過實驗、實訓提高學生的動手能力,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1.3 教學組織與課時分配管理
根據本課程的工作任務和職業能力分析,課程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綜合技能為宗旨,以行業領域發展趨勢為導向,遵循“依照行業標準、突出職業技能”的原則,采用項目教學法,將學習領域內容組織成為五個項目。在項目的實施過程中,將每個項目進一步細分為具體的學習型工作任務。具體教學組織形式參見表2。
表2 教學組織表
1.4 教學內容與能力要求
教學內容與能力要求按照每個項目的名稱、學習任務、教學目標、教學任務與實施過程、項目成果、行業標準技術規范、學生角色、教師能力、參考評價等具體內容進行,在進行土壤學的理論知識的項目講解中,可做如下設計(表3)。
1.5 教學方法與手段
按照工學結合、理實一體的教學模式,按照不同的教學內容和實訓條件可分別運用案例分析法、實物講解法、多媒體演示法、任務驅動等多種具體的教學方法與手段,讓學生通過各個項目的實戰演練,完成各學習任務,提高對知識的理解和對技能的掌握能力。
1.6 考核與評價
該課程按項目分別進行考核,考核成績則是項目考核成績的累計。每個項目成績都是從知識、技能、態度三方面考核,依據預習情況、表格的填寫情況、操作情況、實訓總結等完成情況進行打分,最后得出該課程考核成績。
2 結論
本課程中,學生結合工作任務與職業能力,按照學習目標,完成實踐項目,掌握本課程要求的各項專業知識及操作技能,充分體現了“項目教學法”最顯著的特點即“以項目為主線、教師為主導、學生為主體”,改變了以往“教師講,學生聽”被動的教學模式,創造了學生主動參與、自主協作、探索創新的新型教學模式,有效地建立了課堂和社會生產的聯系,有效地提升學生的多種能力,為學生今后的職業發展奠定基礎。
土壤學總結范文第3篇
1文化遺址區古土壤環境研究進展
1.1土壤粒度粒度組成對于查明沉積物的物質來源、搬運介質和動力、沉積環境及其變化均有重要的意義[7],且兼有相對完善的實驗原理和技術方法,被廣泛應用于古土壤沉積成因的環境研究中,是分析古土壤成因的有效途徑[8]。楊用釗[9]通過系統的環境研究江蘇綽墩古土壤不同粒徑土壤粒度的平均含量及眾數粒度,并與附近的鎮江下蜀黃土剖面的粒度特征進行比較,初步認定綽墩古土壤母質為下蜀黃土。周華等[10]通過分析江蘇連云港藤花落遺址土壤粒度發現,遺址文明存在期間曾發生過大規模或長時間水患事件,農業生產條件被破壞,最終導致整個文明走向衰落,同時,結合重金屬環境研究結果,發現龍山文化時期人類社會的出現與繁榮恰逢自然環境相對良好時期,并且文明衰落與消亡正好對應自然環境發生變遷階段,環境研究表明自然環境變遷是通過影響農業生產的興衰而導致文明的興盛與湮滅。張俊娜和夏正楷[11]運用河南洛陽二里頭南沉積剖面的粒度特征的分析結果指示了水動力條件的強弱,并與氣候的暖濕變化相對應,結合光釋光測年及磁化率環境研究結果,最終確定該剖面沉積過程經歷了3個階段,其中剖面中部地層曾經歷了一場河流階地被淹沒的特大洪水事件。
1.2土壤微形態土壤微形態是土壤組構在微觀-超微觀尺度上的具體表現,包含有大量在宏觀上用肉眼無法觀察到的細微現象,因此長期被作為環境研究土壤發展演替的重要途徑[12]。通過環境研究文化遺址內土壤微形態特征來恢復歷史時期人類的活動方式和環境特征是一種有效手段,近些年來在歐洲、中亞、中美洲等地的考古環境研究中開展了大量土壤微形態環境研究工作,并取得了豐富的成果[12]。Cornwall[13]首次根據考古遺址中土壤微形態分析的結果重建古環境變化的歷史,并解釋了灰燼、居住面等人類活動遺跡的特征;Biagi等[14]通過觀察土壤微形態對史前遺址周圍土地利用情況的影響進行了環境研究,為認識史前農業和畜牧業等經濟生活方式提供了重要信息;Courty等[15]在出版的《SoilMicromorphologyinArchaeology》中建立了一套相對獨立的土壤微形態環境研究方法,并通過對約旦河下游NetivHagdud和Salibiya前陶新石器遺址建筑遺存的土壤微形態進行分析,發現所有用來建筑房屋的土坯均是采用從附近的河流沖積物中專門挑選的原料制成,但不同地面所用的材料有所區別;Kemp等[16]通過土壤微形態環境研究,初步恢復了古耕作土壤特征及農耕方式;董廣輝等[17]對青海喇家遺址內外砂壤土進行顯微鏡觀察和土壤微結構分析,認為喇家遺址內成壤環境較穩定,受生物擾動較少,局部淋溶作用較強和有人類作用的痕跡,而遺址外土壤微形態受到生物強烈的擾動,并且經歷了古水流的作用。
1.3土壤元素自然環境變化引起的土壤環境變化是造成土壤中元素遷移轉化的根本原因,因此土壤中元素含量的多少及變化能很好地反映環境變化[18]。人類在某個地區定居下來,并進行各種人類活動必然會對周圍的環境造成影響,并改變周圍土壤中的地球化學元素組成[4]。不同的人類活動對周圍環境中的土壤會造成不同的地球化學元素改變,而土壤中化學元素組成的空間并不會因為房屋或者遺址的廢棄而改變,能更準確地反映遺址過去的空間分布[19]。當僅僅依靠發現的古器物不足以解釋某一區域問題的時候,土壤的元素組成能夠提供古人活動的重要線索[20-23]。Barba和Bello[24]在美國中部以及瑪雅地區,環境研究驗證了在中美洲可以運用化學元素推測古人類活動;Sandra和Christopher等[25]將衛星遙感影像分析和空間統計相結合,對多種化學元素進行疊加,用以鑒定馬拉納圣盧卡斯考古遺址的空間化學組合,結果表明當時的土壤條件難以生長自然植被,而地表化學富集受其他過程的影響。環境研究土壤元素在不同土層的富集和虧損可判斷遺址的殘留與遷移,可反映古人類對土壤的利用活動。元素磷在古遺址的尋找和解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席位[26-27]。1911年,埃及農學家Hughes注意到古人類居住地土壤磷含量高于周圍相同時期自然土壤磷含量[28],但最早系統地將土壤磷分析用作考古環境研究的是瑞典的Arrhenius,他于1929年發現包含維京農場和居民點遺骸地區的土壤中磷的含量高[29],采用富磷指示古人類活動這一結論運用于北國遺址環境研究中,證明此地3名婦女曾因使用巫術而被焚燒,此后,考古學家開始考慮通過環境研究土壤化學元素來反映人類活動;1963年,Arrhenius[30]證實富磷指示結論同樣適用于美國西南部考古遺址,跨文化跨地區卻相近的環境研究結論確立了富磷可作為重要指標指示人類定居點,同時也證明了環境研究土壤元素對考古具有一定的價值。董廣輝等[31]對河南大陽河遺址古土壤化學性質進行環境研究,發現文明起源時期的人類活動對古土壤化學性質產生了明顯的影響,土壤中有機碳、全氮和有機磷質量分數明顯增加,人類活動還使古土壤中元素質量分數的比值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由此說明環境研究地點的人類活動方式是生活和居住,而不是農作。與王灣三期相比,二里頭時期土壤中有機碳、全氮和有機磷質量分數明顯升高,這也說明環境研究地點二里頭時期人類活動強度較王灣三期有所增強。查理思等[32]環境研究了河南洛陽二里頭文化遺址區古人類活動對土壤化學成分的影響,結果表明古人類活動使土壤有機碳、全磷和有機磷含量顯著增加,還使土壤中元素含量的比值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有機磷含量與全磷含量的比值明顯增加,元素含量和比值變化特征說明環境研究地點為古人類的生活居住區。其他元素的分析也可以為古人類空間利用模式提供有效的線索,特別是一些重要的金屬元素[4]。土壤中高含量Fe與古人類加工龍舌蘭或者屠宰動物以及廚房區域有關[33];Ca、Sr含量的高值與利用貝殼沙作肥料的農田、靠近爐邊的位置密切相關[26,34];Hg的含量與手工制作區有關[35]、并且辰砂(HgS)常被瑪雅人用來作為裝飾或者進行某種儀式(比如葬禮)時的大紅顏料[36],Hg的含量與宗教儀式或葬禮有關[37];而Ba、La、Ce、Pr、K、Cs、Th和Rb在原先的小村落地區高度富集,可以指示當地古人的居住區域[26];Ca、Ba、Sr、Zn、P和Pb可以反映古人類不同的活動方式[34];而軟錳礦(MnO2)、孔雀石(CuCO3•Cu(OH)2)、藍銅礦也常被用作顏料[36]。李中軒等[38]對湖北遼瓦店遺址地層樣品的氧化物含量和地球化學元素含量的分析結果表明,K、Mn、Sr、Ba含量驟降地層說明該時期人類活動減少,其原因可能為自然災害,Pb含量的異常和Cu含量高值暗示遺址有青銅器制作活動,此外,Mg和Ca含量的高值與耕作區、墻壁灰漿、生活垃圾堆積等人類活動相關。周群英和黃春長[39]對陜西西周灃鎬遺址區土壤樣品中的Fe、Rb、和Se的含量進行分析,其結果揭示了與全新世環境變化相對應的成壤過程,土壤發育表現為邊沉積邊成壤,同時發現人類農業耕作活動主要是從西周人遷都至灃河岸邊時開始的。高華中等[40]通過分析三峽庫區中壩遺址(位于重慶市于忠縣境內)土壤中有機碳含量及其與周圍環境的關系,推測當人類活動強度大,地表自然植被破壞嚴重時,有機質的輸入量減少,土壤侵蝕量增大,土壤有機碳含量隨之降低;當氣溫下降時,往往降水隨之減少,對植被生長不利,從而造成有機質輸入量減少。
1.4土壤磁化率土壤磁化率是土壤各組分的磁性反映,是物質磁化性能的量度[41]。土壤磁性受環境控制,在評價氣候、母質、生物、地形和時間等主要成土因子的基礎上,能夠反映全球環境變化、氣候變遷和人類活動等綜合信息。有關土壤磁化率特征與土壤性質的關系及影響因素已有大量環境研究報道,特別是在一些文化遺址區內,環境研究結果顯示在土壤發生學、古氣候和環境變化等方面的應用已經取得較大進展,為相關考古環境研究提供了具有價值的依據。磁化率在黃土高原地區古氣候環境研究中被作為一種代用氣候指標[42]。安芷生等[43]指出:古土壤的較高磁化率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溫濕氣候條件下濕度增大促使植被密度增大、成壤作用增強;反之,低磁化率則指示了濕度較小、植被稀疏、發育黃土的干冷氣候狀況。霍俊杰等[44]對陜西大荔人遺址剖面進行了系統的巖石磁學性質環境研究,結果表明黃土-古土壤樣品的頻率磁化率曲線,古里雅冰芯氧同位素、細微粒濃度曲線,岐山五里鋪剖面有機質含量曲線在古氣候記錄方面具有一致性,均展示出至少從MIS5以來,氣候從冰期到間冰期的變化是漸變的,反之則表現了突變特征。洛陽盆地內二里頭遺址南沉積剖面位于遺址所在二級階地的前緣,屬于河流堆積,張俊娜和夏正楷[11]對剖面的沉積物樣品進行磁化率分析,發現磁化率的大小與水動力和氣候條件相關,環境研究發現該沉積剖面記錄了4000aBP前后龍山晚期發生的一次異常洪水事件,這次洪水事件對二里頭城址的選擇具有重要的影響。馬春梅等[45]結合磁化率和地球化學元素提取出安徽尉遲寺遺址地層記錄的環境演變信息,認為該區5050aBP以前即新石器時期為暖濕氣候,大汶口文化階段氣候偏干冷且波動頻繁,大汶口至龍山文化期間,氣候由冷轉向溫濕,為水稻生產提供了有利條件,促進了龍山文化的繁榮。張振卿等[46]對河南安陽殷墟地區3個土壤剖面的巖性分析和磁化率測試,發現巖性和磁化率變化之間均存在較好的一致性。磁化率從地表向下均有明顯降低的趨勢,黃土-古土壤序列的磁化率埋藏效應在殷墟地區河流相沉積物中同樣存在;土壤剖面中古土壤層磁化率相對其他層位明顯降低,且波動幅度較小,這種規律有別于目前已被廣泛接受的黃土中古土壤磁化率增強的土壤成因模式;殷墟地區土壤剖面磁化率在古土壤層上部急劇升高且波動劇烈,該層位年代和殷墟文化產生的年代相吻合。受人類干擾強烈的土壤,特別是文化層土壤,人類活動對磁化率起到了主要作用。史威等[47]對重慶中壩考古遺址多剖面地層進行高分辨率的質量磁化率(SI)分析,環境研究表明:磁化率分布表現異常,在很大程度上已掩蓋了氣候變化、成土作用等因素對地層磁化率分布的貢獻,反映出遺址堆積物曾受到人類長期異常強烈的改造,而堆積物來源主要以文化器物碎片、人為帶入的自然碎屑物和頻繁的洪水沉積物為主。碎陶片集中(尤其紅陶)的文化層表現為高磁化率,其中多次異常高值的出現可能與當時高強度用火、大規模燃燒等事件致使土層磁性礦物增加有關;而“洪水擾動層”則表現為低磁化率。
1.5多環芳烴多環芳烴(PAHs)是包括化石燃料煤、石油、煤焦油等有機化合物的熱解或不完全燃燒的產物,廣泛分布于大氣、土壤、古土壤、沉積物、有機生物體中[48],是人類活動的良好指示物[49]。曹志洪[50]在環境研究新石器時期水稻土時發現含有較高的多環芳烴(PAHs)等有機污染物,并通過實驗證明其主要來源于古人焚燒的稻草秸稈,其中有少量也可能是還原條件下的生物自然合成的[51]。Ramdahl[52]認為惹烯也能通過松類樹脂在低溫燃燒下降解形成,鄒勝利等[49]在金羅家遺址考古土壤中檢測到了卡達烯和惹烯兩種多環芳烴化合物,可推測高等植被是古人類生活用火的主要薪材。李久海等[53]運用聚類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環境研究了多環芳烴(PAHs)在含6000a(馬家浜文化時期)古水稻土剖面中的分布特征,環境研究表明、苯并(k)熒蒽、苯并(a)蒽、茚并(1,2,3-cd)芘、苯并(b)熒蒽、芘、苯并(a)芘、二苯并(a,h)蒽和熒蒽等化合物主要是人為產生,芴和菲由生物合成,而萘、二萘嵌苯和蒽則可能來源于人為產生和生物合成的共同作用。此外,熒蒽/菲、苯并(a)蒽/菲和苯并(a)芘/菲等可以作為與陸生植物和化石燃料燃燒有關的芳烴產物的標志,這些多環芳烴可能與人類活動有一定的關系,說明考古遺址土壤中的多環芳烴記錄能夠反映生活在該遺址上一些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和活動的信息[49]。
1.6土壤植物遺存植物考古的環境研究不僅可以探索與人類文化活動相關的植物遺存,如食物生產的起源與發展過程、人類利用其他植物的活動等;同時能復原古代生態環境。植物考古旨在解決考古學環境研究中的全面復原人類社會的歷史問題。通常在考古遺址中發現的植物遺存可歸納為三大類[54]:大植物遺存(Macroremains)、孢粉(PollenandSpores)和植物硅酸體(Phytolith,Plantopal)。大植物遺存主要包括木材、種子、果實、果核及外殼、莖稈等。由于植物產生大量的具有顯著形態學特征的種子并廣泛傳播,且易于保存,所以最為醒目和可靠的當屬能在遺址中找到較多的種子和果實[35]。考古遺址中的大植物遺存主要針對炭化過的植物遺存而言[55]。炭化的大植物遺存目前主要通過浮選的方法獲得,可以作為標本來鑒定植物來源種屬,并且方便進行直接的14C測年。如,閆雪等[56]通過浮選結果的量化分析,推測商代鄭家壩地區經營以粟為主的旱作農業,并且有豐富的野生核果、漿果類以及其他植物資源。王育茜等[57]通過分析遼寧查海遺址的炭化植物遺存,初步了解到該遺址聚落周圍廣泛分布闊葉落葉林,且其植被組合可能與全新世初期溫暖濕潤的氣候有關,聚落居民在房屋建筑材料和薪柴獲取活動中利用了聚落周圍的森林資源,而遺存的山杏、核桃楸、榛子和一些禾本科、豆科植物的發現說明采集是獲取植物性食物的主要方式。孢粉形體微小、形態各異、廣泛分布、易于保存,有助于環境研究史前時期地區較廣范圍的區域性植被的植物組成[54]。孢粉與遺址的各階段氣候、古環境變化和古人類的活動密切相關,而且顯示了古人生產活動的程度和能力。利用孢粉分析結果分析古代的植被狀況,推測當時的環境背景,有助于了解環境變化和人類文化演變之間的關系[58]。李珍等[59]在環境研究上海馬橋遺址時,利用文化層中各孢粉組合的差異反映了古人類活動環境的變遷,孢粉組合特征說明從良諸文化時期農業已有發展,由出土的錛、鏟刀等也可證實;孫雄偉和夏正楷[58]以土壤剖面為環境研究對象,通過高分辨率的孢粉分析表明該地區中全新世以來的孢粉組合以草本植物占絕對優勢,并根據孢粉組合的變化將剖面分為5個孢粉組合帶,探討了各個時期的古植被和古環境變化;張玉蘭[60]通過環境研究上海廣富林遺址、馬橋遺址探方樣品的孢粉、藻類,并結合前人已有的資料推測太湖地區良渚文化突然消亡的原因是水泛。植硅體是土壤中生物硅的一種[61]。考古遺址文化層在堆積過程中,由于人類使用植物的活動,有可能積聚較多的植物莖和葉,莖和葉腐爛后,其中的硅化細胞和組織———植硅體能夠得以保存,而且數量很大,在考古土壤、容器內含物、灰堆、陶器碎片、干糞中常可大量地發現。植硅體作為考古土壤中的原地腐爛的植物殘余,能夠反映細微的環境變化和過去人類對植物的選擇以及利用有關的文化活動[49,62]。姜欽華[63]通過測定河南潁陽遺址區土壤樣品中禾草類植硅石含量和花粉含量,結果表明在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晚期,登封地區的氣候溫暖濕潤,并且當時登封地區可能已經有一定規模的水稻種植。吳妍等[64]對湖北鄖西黃龍洞遺址區土壤中植硅體進行分析,發現地層中禾本科和木本科的植硅體特征顯示遺址古植被環境較好;較多海綿狀骨針反映古人類活動時期遺址周圍有較好的水源條件;洞內遺址活動層中較多碳屑樣品則反映鄖西人在洞穴內可能曾有過對火的控制和利用。結果表明當時氣候類型總體為溫暖型,鄖西人生活居住的洞內氣候較溫暖干燥,而洞外相對炎熱濕潤。
1.7土壤動物遺存動物考古旨在通過對遺址內動物的化石遺存環境研究,尋找人類與動物之間的關系。李新偉等[65]對河南靈寶西坡M27墓主腹部的土樣進行提取并進行顯微鏡觀測,發現有圓圓的寄生蟲卵,這種寄生蟲卵通常與食用豬肉有關;通過對骨骼內15N的分析同樣也可以反映出墓主的食肉情況,15N的含量高一般就表明使用豬肉較多;此外,對墓主人頭骨的環境研究,發現他的頭骨形態與西坡聚落另一座大型墓葬M8的頭骨形態非常相似,以此推測墓主極可能是一個當時社會上層家族的一員。國內外一些學者通過環境研究遺址出土動物牙釉質及骨骼來推測古環境。國際考古學界一般以出土的當地動物骨骼和牙釉質的鍶同位素比值建立遺址當地的鍶同位素比值標準。Ezzo和Price[66]測定了遺址出土嚙齒動物的牙釉質及骨骼的鍶同位素比值和同一遺址史前人類牙釉質的鍶同位素比值,環境研究表明二者非常接近。Bentley等[67]對出土動物牙釉質的鍶同位素比值的統計分析,得出豬的鍶同位素標準偏差遠遠小于其他動物,而且由于豬吃的食物主要是人類食物的剩余,所以可以用豬骨骼和牙齒中鍶同位素比值代表當地的鍶同位素水平。國內學者在環境研究遺址出土動物骨骼的基礎上推測當時的自然環境及生業模式,如,趙春燕等[68]通過測定河南瓦店遺址龍山文化晚期出土的鼠骨及豬、黃牛、綿羊牙釉質的鍶同位素比值,推斷由當地出產鼠的可能性最大,由出土鼠骨的鍶同位素修正得到瓦店遺址當地的鍶同位素比值范圍,并根據該范圍確定了出土的豬、綿羊和黃牛是否在當地出生;胡松梅等[69]對陜北橫山楊界沙遺址出土的所有動物骨骼進行了科學的收集和分類鑒定,環境研究表明至少代表3綱7目10科11個屬種,并推測遺址周圍的自然景觀以草原為主,草原上有草兔、綿羊等食草動物,不遠處的沙漠曾有鵝喉羚出沒,草原和沙漠間分布著一定面積的水域且有蚌類出現,飼養家畜和捕獵野生動物是當時人們的肉食來源,其中家養動物豬的肉量比例占到了整個食用動物群的87.9%;趙瑩[70]通過鑒定、環境研究銀梭島遺址出土的動物骨骼標本,探討了骨骼標本痕跡、骨角器的制作工藝以及該遺址先民的生存環境、生業模式、風俗習慣等;李永憲[71]通過環境研究卡諾遺址新出土的動物骨骼和生產工具,結果表明其用于“狩獵”、“畜牧”的石質工具從早到晚呈遞增趨勢,晚期狩獵業仍占有重要地位,農耕作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理條件的限制。綜上,目前能夠反映古環境信息的土壤特性如表1所示。
2文化遺址區古土壤環境研究展望
2.1借鑒相關環境研究指標近年來文化遺址區古土壤的環境研究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其環境研究方法主要是通過分析土壤粒度、土壤元素和土壤中的動植物遺存等方面來推測其所處時期的土壤條件、氣候環境以及人類活動情況,而幾乎沒有運用第四紀古土壤環境研究中常用于反映古氣候古環境的指標,如土壤顏色、土壤礦物、土壤黑碳等。
2.1.1土壤顏色土壤顏色是其在可見光波段的反射光譜特性,與土壤有機質含量、氧化鐵含量、質地、黏粒含量、水分、主導黏土礦物類型等理化性狀密切相關[72]。已有環境研究結果表明[72-78],土壤的顏色記錄在千萬年尺度上,土壤顏度指標中的紅度、黃度和亮度與氣候變化指標磁化率、粒度和碳酸鹽均有很好的相關性,能很好地再現氣候變化的特征,并能指示成土過程。比如,土壤紅化率指數可推斷古紅土成土母質風化成土作用[72];土壤紅度值與年降水量有一定的定量關系[73];土壤顏色的空間變化則可以反映氣候要素對土壤性狀的制約性[74]。因此,在環境研究文化遺址區古土壤時,土壤顏色作為氣候變化的代用指標是完全可行的[75],通過其顏度指標中的紅度、黃度、亮度及其與磁化率、粒度等的關系來反映遺址區的氣候狀況,從而推測當時的生業方式及農耕條件;亦可運用紅化率指數推斷成土母質風化成土作用。此外,若遺址區土壤中發現紅燒土[79]、灰燼[80]等顏色明顯的古土壤,可推斷古人類居住點的空間變化情況。
2.1.2土壤黏土礦物、土壤氧化物類礦物黏土礦物的沉積分異、組合特征,礦物含量及礦物結晶度均從不同方面記錄了環境變化的信息,使黏土礦物成為了環境變化信息的載體[81]。不少國內外學者[78,82-84]通過對黏土礦物的環境研究,解釋了沉積物的來源、古氣候變化以及古環境特征。此外,還有一些學者探討了總有機碳與黏粒含量及黏土礦物含量的相關性[85],或結合黏土礦物參數指標與土壤粒度特征、CH測年數據進行分析[86],提取沉積物記錄的古環境信息。因此,在環境研究文化遺址區古土壤的黏土礦物特征時,若發現由相同母質發育形成的古土壤中黏土礦物不同,可以推測其可能受到了古人類或古環境的擾動,進而對黏土礦物與有機碳、黏粒含量、粒度、測年數據等指標進行相關性分析,從而推測古氣候及古環境狀況。土壤中的氧化物常作為反映成土過程和成土環境的指示物,可以通過分析不同氧化物、氧化物分子比值特征來說明地層所反映的氧化-還原條件、古氣候的冷(暖)-干(濕)變化情況[87]。如全氧化鐵(TFe2O3)指標反映相對降水量變化,硅鋁鐵率(SiO2/(Al2O3+Fe2O3))指示風化強度變化,氧化度(Fe3+/Fe2+)指示古溫度變化,殘積系數((Al2O3+Fe2O3)/(CaO+M+Na2O))、化學蝕變指數(CIA)、硅鋁率(SiO2/Al2O3)、退堿系數((Na2O+CaO)/Al2O3)等風化參數也可以指示古氣候變化[87]。此外,鐵能夠很好地反映自然土壤和有人為擾動的農田土壤的特征[88];在相同或相近的降雨量、氣溫、排水狀況等成土環境下,氧化鐵可用于評價和推斷土壤發育程度和相對成土年齡[89]。上述實例說明,土壤氧化物可以作為一個良好的指標來分析文化遺址區古土壤特性及其反映的古環境信息。
2.1.3蝸牛蝸牛是黃土地層中一類最為豐富的生物化石,對氣候環境的變化十分敏感,能夠提供較物理、化學指標更為詳細的古氣候、古環境信息[90]。已有學者[91,92]根據蝸牛化石組合推測氣候環境的波動情況,如粉華蝸牛代表耐干旱、寒冷氣候的生態特征,而齒螺代表喜潮濕、溫暖的生態學特征[93]。因此,環境研究文化遺址區古土壤時,可通過蝸牛化石的環境研究來推測古氣候、古環境信息,進而結合其他指標推導古人類活動。
2.1.4土壤黑碳目前黑碳仍沒有統一的定義[94-96],唐揚等[94]總結國內外學者關于黑碳的環境研究,認為黑碳是有機物不完全燃燒產生的具有較高熱穩定性的焦炭、木炭、煙灰和高度聚集的多環芳烴類物質,此外包括生物體自然降解的殘余物以及微小的有機碎屑。土壤黑碳可用于推斷特定區域內較大尺度時間(10000a)內所發生的大火事件,也可用于人類活動對土壤黑碳組分的影響[94],并且何躍等[97-98]環境研究發現土壤黑碳與有機碳比值可以反映不同燃燒活動的物質來源。此外,Wang等[99]通過對全新世土壤的黑碳記錄環境研究顯示,表層土壤的質量沉積速率相對于下層土壤有大幅度的增加,可能與人類活動的影響有關。因此,通過測定文化遺址區的土壤黑碳濃度,可以重建古火災事件,進而反映歷史氣候干濕變化及化石燃料的使用歷史。
2.2進一步加強土壤學與考古學的結合考古地層學環境研究是現代文化遺址區時空界定的重要標尺,也是考古學中最為重要的理論。在發掘過程中,根據土質土色來判斷層位關系,是考古發掘過程中最常用的方法。但是對土壤缺乏科學系統的認識是目前考古學不可回避的事實。如果能在考古發掘過程中引入土壤學的相關知識,以其理論和方法統一考古對土壤的描述,加深土壤的系統環境研究,不僅可以促進考古學的規范化,同時也方便學科間的交流;并且可利用土壤特性分析成土時期周邊的氣候環境狀況,從而為我們環境研究古代文化提供便利。例如文化層的年代順序主要根據考古器物的(如陶片、瓷片、磚瓦塊等)顏色、圖案、花紋和形態類型與已確定年代的考古器物特征進行對比分析來確定,其結果可輔證土壤14C、熱釋光等測年結果,也可為大致判斷對應自然層的年代提供參考。程鵬和宋誠[100]在環境研究良渚文化時指出,考古遺址的環境研究包括對考古遺址的時空位置和遺址自身的環境研究,前者主要通過分析古人類居住點的空間變化,后者則是通過對遺址的地層堆積的環境研究,從全局到局部的環境研究思路,同樣可運用到土壤學環境研究中,從全局土壤一般性質到局部土壤特殊性質,變化差異可印證區域性和地方性環境演變與古人類生存活動的關系。王建新[6]通過對河南澠池縣班村遺址及周圍地區地層堆積情況的環境研究,確認了四種不同的地層,從遺址中心到遺址以外,人的作用越來越小,自然的作用越來越大,從而總結了將遺址邊緣區作為紐帶連接文化層與自然層的環境研究思路,再通過人工制品遺物和土色土質這兩種標準的對應和結合,就可以找到自然層與文化層之間的關系,將遺址及其周圍地區的環境與氣候的變遷環境研究與考古學文化的分期環境研究對應起來,從而準確地為考古學文化變遷的環境研究提供環境與氣候的背景。此外,農耕土層和文化斷層值得特別注意[6],農耕土層往往與自然土層相似,但其堆積的原始書理被破壞,可通過檢測其中植物孢粉和硅酸體等的種類及數量予以確認,將農耕土層與遺址內外的自然層和文化層對應起來,進而推測農耕土層的文化時期;而文化斷層是自然災害的指示物,可以通過尋找文化斷層來尋找自然災害信息[101]。
2.3建立文化遺址區古土壤的診斷技術指標曹志洪[50]通過對中國史前灌溉稻田和古水稻土連續4年多的環境研究,提出了一套診斷古水稻田和古水稻土的技術指標,并獲得了新石器時期“火耕水溽”———原始灌溉稻作技術的科學證據,以揭示7000a以來我國稻作農業的興衰與全球氣候變化的關系以及灌溉稻田和水耕人為土起源及其對世界文明的貢獻。古人類活動在土壤中留下了許多的肉眼看得見和看不見的信息,事實上,土壤是我們環境研究古人類活動信息最主要的來源,在我們能夠破譯這些信息之前,土壤也是保護這些珍貴古人類信息的最好載體。因此建議建立文化遺址區古土壤的定性與定量化診斷技術指標體系,通過土壤結構、元素、微形態、動植物遺存、遺物遺跡等具體指標來推測古土壤特性及其所反映的古環境信息,并進一步推測古人類活動,以此對文化遺址區古土壤環境研究提供技術支持,同時有助于更明確地保護和環境研究古文化遺產。
2.4豐富文化遺址區古土壤的環境研究方法過程—響應關系是一種確定的土壤過程和由此產生的土壤特性之間的因果關系[102]。土壤過程會導致不同的、可量化的屬性,如黏土淀積作用,并且這些特征是可診斷的[103-104]。考古土壤學的主要目標是以此聯系某種土壤診斷指標和單一的因果過程或整套流程,下一步的環境研究目標則是量化這種關系[102]。這是因為文化遺址區考古土壤的過程—響應關系具有殊途同歸性,即不同影響因素的組合可以產生相同的最終結果[105-106]。如Carter和Da-vidson[107]、Usai[108]通過土壤微形態探討粉質黏粒膠膜與古耕作活動的關系,結果表明二者沒有直接的相關關系,其形成可能與耕作,也可能與繼承母質等非人為因素有關;Macphail的實驗表明,經踐踏和凍融過程后的粉質黏粒具有相似的特性;Courty[109]甚至對這種粉質黏粒膠膜給出了至少六種解釋,以此例證了可能性解釋的多樣性。2014年9月在波蘭托倫召開的第十三屆古土壤大會上,主要由來自俄羅斯、墨西哥和中國的土壤學家介紹了遺址區古土壤環境研究新進展。TamaraCruz-y-Cruz在墨西哥北部和中部含有動物化石遺址區通過分析土壤中有機質、大型土壤動物骨骼化石、動物膠原蛋白和牙釉質的穩定碳同位素(δ13C)含量,還原出C3和C4植物含量比例,從而推導出古氣候特征。Sycheva在舊石器文化Divnorie遺址運用土壤發生學推導古成土過程,并結合有機質、炭屑、連二亞硫酸鹽和草酸鹽含量分析以及孢粉譜測試結果,相互之間印證推導出古土壤成土環境。吳克寧在河南仰韶村文化遺址通過分析土壤的粒度、質地、磁化率、色度、孢粉和植硅體從而還原古環境特征,并推論出仰韶文化演變和氣候變化的耦合關系。因此,可進一步探索運用新的氣候替代指標和古人類活動檢測方法來環境研究文化遺址區的古土壤,獲取更多受古人類活動直接或間接影響的特殊指標數值,并分析各影響指標之間的相關關系,進而豐富文化遺址區古土壤的環境研究方法。
2.5加強對文化遺址區土壤的分類環境研究中國是歷史悠久、文化輝煌的國家,其寶貴的文化遺產中蘊含著深厚的歷史文化信息。對于文化遺址土壤這一特殊環境研究對象,土壤學家可通過考古資料推導不同時間尺度下古人類土地利用方式以及古氣候環境;而考古專家在推測古人類生產生活方式需考慮土壤肥力、土地利用、土壤發育過程對遺存物含量及位置變化的影響。土壤學家和考古學家相互合作,有助于還原文化遺址區的景觀環境和古人類活動,逐步加強土壤學和考古學的結合,不僅可以促進考古學的規范化,使環境研究成果更加科學,同時也方便學科之間的交流。環境研究古土壤已成為國際土壤學界新的環境研究熱點,2006年在美國費城召開的世界土壤學大會上將“古土壤”增列為“土壤的時空演變(Division-1)”大專業下的“第6專業委員會”。
土壤學總結范文第4篇
【關鍵詞】土壤;重金屬;污染源;等標污染負荷
一、問題的說明
現對A城市為例對土壤地質環境進行調查。將所考察的城區劃分為間距1公里左右的網格子區域,按照每平方公里1個采樣點對表層土(0~10厘米深度)進行取樣和編號,并用GPS記錄采樣點的位置。應用專門儀器測試分析,獲得每個樣本所含的多種(8種)重金屬元素的濃度數據。另一方面,按照2公里的間距在那些遠離人群及工業活動的自然區取樣,將其作為該城區表層土壤中元素的背景值。列出采樣點的位置、海拔高度及其所屬功能區、8種主要重金屬元素在采樣點處的濃度、8種主要重金屬元素的背景值。
我們引用2011年全國數學建模大賽附錄中的A城市城區土壤重金屬的調查數據,建立數學模型,研究地區重金屬污染源的確定方法。
二、問題的求解方法
由于土壤重金屬污染呈擴散傳播,既污染源附近重金屬富集程度最高,距污染源越遠,元素濃度越低,所以,污染最嚴重的地點既是污染源,運用等標污染負荷法,通過對污染物和污染源進行標化計算,得出一個量化指標,使指標的值在0~1之間,采用這個共同的指標能夠來衡量各個重金屬污染源或污染物污染能力的大小。
等標污染負荷法模型的建立與求解:
(1)處理數據。
每相鄰五個取樣點通過求取平均值,合并成一個較大取樣點(即每五平方公里一個取樣點),求得64個合并取樣點,用于分析數據。
(2)建立模型。
1)進行符號說明:
(將As、Cd、Cr、Cu、Hg、Ni、Pb、Zn分別記為元素一至元素八)
1、Aij―樣本點i的第j種元素的污染物濃度
2、Bj―第j種元素的自然值;
3、aij―區域內第i個取樣點第j種重金屬元素的等標污染負荷量aij (即污染物濃度與背景值之比:aij=Aij/Bj)
4、bi―樣本點i的等標污染負荷量(即該取樣點所有的重金屬污染物等標污染負荷量之和:bi=(i=1,2,3,…64)
5、c―城區內的等標污染負荷量(即區域內所有取樣點的等標污染負荷量bi之和:c=)。
6、ai―城區內樣本點i等標污染負荷量的比值(即每個取樣點等標污染負荷量bi與區域內的總等標污染負荷量c之比:ai=(i=1,2,3…64)
7、di―i個等標污染負荷量的比值a按從小到大依次疊加
8、x―取樣點橫坐標
9、y―取樣點縱坐標
10、h―取樣點海拔
補充:將bi和c帶入公式ai=可得
ai=(i=1,2,3…64)
2)整理數據帶入相應公式可得每個樣本點等標污染負荷量的比值a
3)將城區內的等標污染負荷之比值ai由大到小依次排列,并將比值從小到大依次疊加得到di
4)將di從小到大排列,我們將最高的8個di列入下表得到表5-1:
樣本號i 8 4 6 9 5 52 37 2
di值 0.607 0.635 0.662 0.691 0.719 0.777 0.84 1
表5-1等標污染負荷量的比值a按從小到大依次疊加
由表可知,取樣點2的疊加值di超過90%。
5)于是從附錄中找到2號取樣點的5個原始樣本的數據。
分別為i=6、7、8、9、10號樣本。
再在這5個點中找出污染最重的區域。
上面的研究是對64個點的分析,下面的研究只對這五個點進行研究即可,研究方法和原理與上面的相同。
6)通過計算可得:
第八點污染最為嚴重,可將第八點作為污染源。
所以,該城區污染源為點x=2383m,y=3692m,h=7.及其附近區域。
7)在樣本點較少或者用計算機進行計算時,不必進行第一步的樣本點合并,直接求出di超過90%的原始樣本點,作為重點污染源。
三、方法模型的總結和擴展
伴隨《環境影響評價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等法律的出臺,國家對環境污染的防治力度大大增強。確定污染企業的位置,
對環境污染的治理,有著關鍵性的作用,等標污染負荷法計算簡便,原理清晰易懂,能夠準確地確定污染源的位置,為有關部門尋找重點污染企業,提供了簡便有效的方法。
參考文獻
[1]楊蘇才,曾靜靜,王勝利,南忠仁.蘭州市表層土壤 Cu、 Zn、 Pb 污染評價及成因分析.市場周刊?理論研究第,2004,11.
[2]吳邵華,周生路,潘賢章,趙其國.城市擴建過程對土壤重金屬積累影響的定量分析.土壤學報,2011.5.
[3]劉麗瓊,魏世江,江韜.三峽庫區消落帶土壤重金屬分析特征及潛在風險評價.中國環境科學,2011,31(17):1204-1211.
[4]彭 勝,陳家軍,王紅旗.揮發性有機污染物在土壤中的運移機制與模型.土壤學報,第38 卷第3 期2001 年 8 月.
[5]王雄軍,賴健青等.基于因子分析法研究太原市土壤重金屬污染的主要來源.2008.17(2):671-676.
土壤學總結范文第5篇
關鍵詞: 園林植物;資源調查;鹽害;濱海地區
中圖分類號:S68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2641(2013)05-0000-00
濱海地區由于受海潮和海水型地下水的雙重影響,土壤養分含量低、鹽堿化嚴重,因此難以建立植被,嚴重制約這些地區園林綠化的質量和數量[1~3]。鹽分對植物個體發育的影響主要是抑制植物組織和器官的生長和分化,加快植物的發育進程[4],因此影響園林綠化景觀效果。濱海地區綠化樹種的鹽害問題受到越來越多園林工作者的重視,調查在濱海鹽堿地生長的綠化植物,從植物形態適應評價植物耐鹽能力[5~8],對篩選出可利用的鹽生植物具有重要意義。
深圳地處廣東省中南沿海北回歸線以南,與香港相鄰,東隔大亞灣,西臨珠江口伶仃洋。深圳市行政轄區內的土地總面積為2 020 km2,其中經濟特區土地面積327.5 km2,地形多為低丘陵地,間以平緩的臺地,西部沿海一帶是濱海平原。中國已有多個濱海城市對耐鹽園林植物資源進行了調查統計[9~12],深圳地區尚未有園林綠地植物受鹽害狀況的系統調查。本文對深圳濱海地區園林植物受鹽害狀況進行調查研究,對耐鹽堿植物的形態進行總結評價,并總結出可用于深圳濱海鹽堿地園林綠化的耐鹽植物種類,以期為廣泛而系統地篩選耐鹽植物提供參考依據。
1 研究地概況
深圳市(22°27′N~22°52′N,113°46′E~114°37′E)屬亞熱帶海洋性氣候,年平均溫度22.4℃ ,最高溫度36.6℃ ,最低溫度1.4℃;相對濕度為71%~85%;年平均降雨量為1 948.6 mm,5~9月為雨季。
調查地段包括深圳主干道濱海大道和深南大道。濱海大道為東西走向,經度范圍是113°91′E~114°11′E,緯度為22°52′N;深南大道位于深圳城市中央偏南,經度范圍是113°91′E~114°14′E,緯度為22°55′N,全長28 km。濱海大道總長9 655.24 m,綠化總面積1 040 000 m2,是深圳市區西部重要的海岸綠地;深南大道為對比路段,調查地點包括錦繡中華路段、世界之窗路段、市民中心路段、投資大廈路段、五洲賓館路段以及香蜜湖路段共6個路段,段與段之間約為2 km。
紅樹林海濱生態公園(以下簡稱海濱公園,面積為0.24 km2)及濱海長廊(約長4 km,寬25~85 m)位于深圳灣畔,113°96′E~114°00′E,22°52′N,是深圳特區內惟一密集的城區濱海帶。這兩大片區毗鄰海邊,園林景觀豐富多樣,海濱公園的主要調查范圍是距離海岸100 m以內的區域;濱海長廊調查全范圍。
2 調查內容和方法
2.1 濱海園林植物資源調查及其景觀效果評價
采用實地勘查法,記錄研究地段內主要樹種的名稱、生長情況(包括葉片受害情況)和病蟲害情況,每個樹種選擇30株進行調查。
2.2 濱海土壤pH值和電導率的測定
在調查區域內共采集了16個土壤樣本進行pH、電導率的檢測。采樣點包括近海區和遠海區不同生長狀況的植物;深南大道包括市中心園林景觀豐富的行政、商業或旅游景點等,每個點采1~2個土樣。土壤的采集共分兩層:A層為地面以下0~20 cm;B層為地面以下20~40 cm。
土壤pH值檢測使用pHS-25型pH酸度計;土壤電導率使用DDB-303A型便攜式電導儀進行測定,然后換算成土壤含鹽量。按照土壤學上的劃分,土壤酸堿度的分級為強酸性、酸性、中性、堿性和強堿性[13](表1)。鹽土的分級標準參照國家分類(表2)。
2.3 濱海園林植物耐鹽性評價
植物受鹽害的表現癥狀有:葉色異常;葉片枯焦;葉片脫落;枝葉枯萎[15]。受害程度劃分為五個等級[16](表3)。
3 結果與分析
3.1 濱海立地條件的比較
3.1.1 不同調查地域的土壤pH值比較 深圳市濱海地區及深南大道的園林植物根際土的pH檢測結果(表4)表明,濱海大道8個土樣的A層土和B層土的平均pH值分別為7.41和8.07,即土壤呈中性至微堿。除1個羊蹄甲根際土的pH值為5.7外,濱海大道其它土壤A層土的pH值在7.41~8.16之間;B層土的pH值為7.45~10.34(表4);而深南大道8個土樣的A層土和B層土的平均pH值分別為7.30和7.27,即土壤呈中性。即濱海大道與深南大道的A層土樣pH值差異不大,都呈中性;但B層土則有區別,濱海大道的B層土pH值較高。
海濱公園G點的測定值偏大,估計因為局部海水滲透或排水不暢或與該種植物所吸收的離子類型有關。深南大道世界之窗處亦出現同樣的問題,但可排除海水滲透的可能。
3.1.2 各調查地區的含鹽量統計 通過檢測土壤的電導率,進而根據導電率得到土壤的全鹽含量(表5)。結果表明,濱海大道土樣的土壤含鹽量比深南大道(0.41~0.40 g?kg-1)稍高,為0.47~0.49 g?kg-1。海濱公園f~的測定值偏大,估計因為局部海水滲透或排水不暢或與該種植物所吸收的離子類型有關。深南大道B點與海濱公園G點的pH值相近,但海濱公園的含鹽量為深南大道的3倍多,估計是濱海地區受海水影響而鹽化所致。
根據我國濱海鹽堿土的分級標準(表2),濱海大道和深南大道的土壤絕大部分為中性土壤,適合大部分植物的生長,只有局部地方如深南大道的市民中心A和海濱公園G處為輕度鹽化土。
3.2 深圳濱海綠地園林植物種類
深圳市濱海區所應用的園林植物達119種及變種,隸屬于47科98屬(表6)。濱海路段最常見的種類是榕樹、椰子、大王椰子、假連翹、福建茶、黃金榕和蔓馬纓丹等。填海區的常見行道樹有大葉相思、臺灣相思、尾葉桉、椰子和黃金榕。出現輕微受害癥狀的有雞冠刺桐、馬占相思、海紅豆、花葉艷山姜、蒲葵、軟葉針葵等29種植物;整體受害較嚴重的有菩提榕、紅花羊蹄甲、洋紫荊、董棕、散尾葵、椰子、油棕7種。在濱海區生長的119種栽培植物中,有36個樹種出現受害癥狀,占濱海區園林植物總數的30.3%(表6)。
深圳濱海地區園林植物種類比較豐富的科有棕櫚科、桑科、含羞草科、蘇木科、夾竹桃科和桃金娘科(表7)。其中棕櫚科植物種類最為豐富,受鹽害程度也最為嚴重,18個種(含變種)中有16個種受不同程度鹽害。夾竹桃科與桃金娘科耐鹽能力較強,所含的幾個種均未受鹽害影響。
3.2調查點園林栽培植物受害程度
在濱海大道整體受害嚴重的8種植物多為Ⅰ級輕微鹽害(表8)。受害較嚴重的有菩提榕、散尾葵、柚木、董棕,受III級鹽害以上的超過了調查總數的20%。其中董棕受IV級鹽害的占了調查總數的40.5%,受鹽害程度遠高于其它幾種植物。這8種植物多是葉片發黃程度、葉斑較嚴重,用于深圳園林綠化將影響景觀效果。
3.3 深南大道植物生長情況
與濱海大道園林植物的生長情況相比,深南大道大部分植物的生長狀況類似,但受害程度稍輕。其中,菩提榕、椰子的受害癥狀與濱海大道的癥狀幾乎相同,紅花羊蹄甲、董棕、油棕和散尾葵則在深南大道受害程度相對較輕。另外,在濱海大道輕微受害的狐尾椰、蘇鐵、花葉艷山姜和四季桂在深南大道則生長正常。
4 結論與討論
4.1 深圳市各調查地區土壤pH值特點
土壤酸堿度不僅直接影響植物生長,還影響土壤的肥力,特別是土壤養分的有效性及有害物質的產生[17]。對深圳市濱海園林植物根際土的理化性質分析后結果顯示,除紅樹林外,深圳市濱海土壤呈微酸性、中性或微堿性,適于大部分植物生長。深圳市濱海園林綠地土壤pH值多為6.5~7.5,少數低于6.5或高于7.5。但在所檢測的城區非濱海區的5個土樣中,有3個土樣pH值大于7.5。由于有些城區綠地土壤為客土,因此尚難以判斷這些土樣呈堿性是自然因素造成的還是客土的性質。進一步擴大市區非濱海路段園林植物根際土土壤養分調查可能有助于找到出現堿性土的原因。
我國濱海地區的鹽堿土主要由Na+、Ca2+、Mg2+等3種陽離子和CO32-、HCO3-、Cl-、SO42-等4種陰離子形成的12種鹽構成[1]。本研究結果顯示,深圳市濱海區的5個土樣和填海區多個土樣的土壤電導率均很低,均未達到對植物造成傷害的程度。初步推測濱海園林植物的鹽害不是根系吸收離子所造成的。因為濱海區海水經海風刮起形成鹽沫,這些含鹽量很高的小水珠在重力作用下沉降,有些植物雖然根系能耐土壤中鹽分,但其枝葉對空氣中鹽分較敏感[18]。如在浪花飛濺區,植物鹽害主要因為鹽霧的影響[19]。濱海公園路段為濱海路段,缺乏障礙物阻隔,濱海植物很容易受到鹽沉降的影響,所以濱海公園路段可能有比較頻繁的鹽霧沉降現象。深圳應用的園林植物中,葉片受鹽霧影響比較敏感的種類有假連翹、芒果等,而黃槿和苦楝等的葉片較耐鹽霧。
4.2 深圳市濱海地區園林植物受害調查結果比較
調查結果顯示,深圳市濱海區應用的園林植物達119種及變種,隸屬于47科98屬,其中有36個樹種出現受害癥狀,占濱海區園林植物總數的30.3%。深圳濱海區所應用的園林植物大多數生長正常或表現較好,只有少數的種類出現嚴重的受害癥狀。有輕微受害癥狀的園林植物有狐尾椰、蒲葵、金山葵、加那利海棗、魚尾葵、短穗魚尾葵 Caryota mitis、絲葵、三角椰子、青棕、國王椰子、酒瓶椰子、砂糖椰子、軟葉針葵、蘇鐵、非洲楝、蒲桃、海紅豆、陰香、雞冠刺桐、柚木、馬占相思、四季桂、翅莢決明、朱蕉、花葉艷山姜和白蝴蝶;受害嚴重的園林植物有紅花羊蹄甲、洋紫荊、菩提榕、董棕、椰子、油棕和散尾葵。
4.3 深圳市濱海地區園林植物應用現狀及前景
深圳有較長的濱海綠化帶,這些地區的綠化對城市環境的改善和地域特色的展示具有重要意義。本調查結果顯示,深圳濱海綠地現在應用的園林植物種類非常豐富,約有119種,但多為外來種或園林栽培種,其中有30.3%的種類或變種出現了鹽害。地處熱帶亞熱帶過渡地帶的華南沿海地區具有豐富的濱海耐鹽植物[20],如周凡等[21]報道了紅樹植物共7科9種,半紅樹5科6種,許建新等(2010)在深圳濱海地區共記錄了56種濱海野生植物,其中比較耐鹽的喬木類有黃槿、苦楝和海芒果Cerbera manghas;灌木類有牡荊Vitex negundo var. cannabifolia和春花Raphiolepis indica等;地被類有厚藤和首冠藤等,紅樹林區植物有草海桐和苦郎樹等,這些野生樹種均適合用于深圳市濱海區園林綠化。本研究對深圳鹽堿地區園林景觀植物進行系統調查和評價,以期為耐鹽園林植物的選擇以及豐富濱海鹽堿地的園林景觀提供理論經驗。
參考文獻
[1]劉擁海,俞樂.濱海地區園林植物耐鹽性研究[J].廣西農業科學.2005,36(5):412-414.
[2]張文淵.濱海地區鹽堿土類型與形成條件分析[J].水土保持通報.1999,19(1):19-23.
[3]O. Borsani1, V. Valpuesta , M.A. Botella. Developing salt tolerant plants in a new century: a molecular biology approach[J]. Plant Cell, Tissue and Organ Culture.2003,73: 101115.
[4]黃勝利.杭州灣濱海鹽堿地綠化植物篩選[D].北京林業大學碩士學位論文.北京,2005.
[5] Ashraf M (1999) Breeding for salinity tolerance proteins in plants[J]. Crit. Rev. Plant Sci. 13: 1742.
[6] Niknam S R,McComb Jen. Salt tolerance screening of selectedAustralian woody species-a review[J]. Forest Ecology and Management, 2000, (139):1-19.
[7] 宋丹,張華新,白淑蘭,等.植物耐鹽種質資源評價及濱海鹽堿地引種研究與展望[J].內蒙古林業科技,2006(1): 37-38.
[8] 趙可夫,范海.鹽生植物及其對鹽漬生境的適應生理[M].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5.
[9]卞阿娜,王文卿.廈門海灣大道耐鹽園林植物的選擇與配置[J].漳州師范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09(3):125-129.
[10]王玉珍,劉永信.山東省東營市耐鹽植物資源及開發利用[J].安徽農業科學.2009, 37(20):9543-9546.
[11]劉會超,孫振元,彭鎮華.鹽堿土綠化植物的應用與評價[J].中南林學院學報, 2003,10(5):30-33.
[12]徐家林.鹽堿地城市的園林綠化.園林科技.2009,3:22-25.
[13]林大儀.土壤學[M].中國林業出版社.2002.
[14] 劉廣明,楊勁松,姚榮江.影響土壤浸提液電導率的鹽分化學性質要素及其強度研究[J]. 土壤學報.2005,42(2):248-249.
[15] 龔洪柱,魏慶莒,金子明等.1986.鹽堿地造林學[M].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39-40.
[16] 王業遴,馬凱,姜衛兵等.五種果樹耐鹽力試驗初報[J].中國果樹, 1990,(3):8-12.
[17]趙軍霞. 土壤酸堿性與植物的生長[J]. 內蒙古農業科技 2003,(6):33,42.
[18]王良睦,王文卿,王謹.廈門地區耐鹽園林植物的篩選[J].中國園林,2001,(6):65-67.
[19]林鳴,王文卿. 浪花飛濺區高山榕鹽害機制初步探討[J]. 廈門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 2006,45(2): 284-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