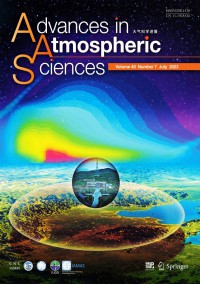大氣污染治理心得體會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大氣污染治理心得體會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fā)現(xiàn)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大氣污染治理心得體會范文第1篇
[關鍵詞]環(huán)境史 環(huán)境問題 歷史研究對象 歷史認識論 歷史方法論
〔中圖分類號〕K2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000-7326(2007)08-0089-05
在多年的環(huán)境史研究和教學實踐中,無論是自己的思考,還是同學們的詢問,都涉及環(huán)境史研究的意義問題。關于這一問題,筆者有些心得體會,并通過多種方式,與學生們做過或深或淺的交流。這里,將近年來的一些想法以及研究工作中的一些思考總結(jié)出來,以饗讀者。
關于環(huán)境史研究的意義,當然可以從多種角度去思考和表述,對于不同的受眾來說尤其應該如此。對于從事環(huán)境史學習和研究的歷史學專業(yè)的同學來說,筆者重點強調(diào)的是,從推動歷史學發(fā)展的角度來理解環(huán)境史研究的意義。具體而言,是從歷史研究對象、歷史認識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加以把握。
一
我們知道,史學界已有人認識到,環(huán)境史的一個突出的貢獻,是使史學家的注意力轉(zhuǎn)移到時下關注的引起全球變化的環(huán)境問題上來,這些問題包括:全球變暖,氣候類型的變動,大氣污染及對臭氧層的破壞,森林與礦物燃料等自然資源的損耗,核輻射的危險,世界范圍的森林濫伐,物種滅絕及其他的對生物多樣性的威脅,外來物種向遠離其起源地的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入侵,垃圾處理及其他城市環(huán)境問題,河流與海洋的污染,荒野的消失及宜人場所的喪失,武裝沖突所造成的環(huán)境影響,等等。[1] (P2) 上述認識,顯然是從歷史研究對象的角度對環(huán)境史研究意義的一種闡發(fā)。簡言之,環(huán)境史研究大大拓寬了史學的范圍,其中一個方面,如上所示,即史學家已經(jīng)將長期以來受到忽視的環(huán)境問題或環(huán)境災害納入史學的范疇,加強了這方面的研究。這也是對人類歷史內(nèi)容之認識的一個很有意義的突破。關于這個方面,筆者曾結(jié)合洛維特的《世界歷史與救贖歷史:歷史哲學的神學前提》中的一個觀點,[2] 談過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洛維特在書的“緒論”中說到:“無論是異教,還是基督教,都不相信那種現(xiàn)代幻想,即歷史是一種不斷進步的發(fā)展,這種發(fā)展以逐步解除的方式解決惡和苦難的問題。”[2] (P7) 針對洛維特的這一說法,筆者不敢肯定異教或基督教是不是“都不相信那種現(xiàn)代幻想”,但筆者認同,世界歷史進程的確催生了這樣一種現(xiàn)代思維現(xiàn)象,即歷史在進步,時代在發(fā)展;其中一個衡量標尺,是“我們這一代”比上一代活得更好,而活得更好的體現(xiàn),則可能是物質(zhì)的占有量更多,精神的自由度更大。并且,如果將這種“歷史不斷進步的發(fā)展”認識,全然說成是一種“現(xiàn)代幻想”,肯定會惹來眾多的非議,因為對很多人來說,他們無需用什么深奧的道理,只要列舉憑經(jīng)驗就能感知并觸摸的諸多事例,就可以指證洛維特的“現(xiàn)代幻想說”的虛妄。
然而,愚見以為,洛維特的上述說法是有著深刻的道理的,因為,時下的環(huán)境史研究幾乎可以證明的,不是“現(xiàn)代幻想說”的虛妄,而是“那種現(xiàn)代幻想”的虛妄。換言之,環(huán)境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已表明,“歷史是一種不斷進步的發(fā)展,這種發(fā)展以逐步解除的方式解決惡和苦難的問題”確乎是一種現(xiàn)代幻想,因為它可以通過并已通過一個個實證研究,無情地向人們揭示,人類在維系自身存在的同時,很可能打破了神圣的自然秩序,或者說切斷了偉大的“存在之鏈”(The Chain of Being)。這樣,不管他如何抗爭,到頭來未必能逃脫“弒父娶母”的悲慘命運。所以,我們很不情愿地看到,在人類文明史,尤其是近代以來以“現(xiàn)代化”為發(fā)展方向的歷史進程中,有多少生命、多少存在成為了現(xiàn)代化進程的祭品。可以說,人類在“以逐步解除的方式解決惡和苦難的問題”的同時,也在“自毀長城”――制造了更多、更深的苦難與惡;其中最為深重的,可能莫過于人類自己制造的核彈有可能將人類文明及其賴以支撐的大地炸得粉碎。如今,“生存還是毀滅”,的確成了問題。并且,今天人類的生死之憂,并非只是像哈姆雷特那樣對“人”的生生死死這一個體問題的憂慮,而是對生養(yǎng)人類的大地母親及其養(yǎng)育的無數(shù)生命之存亡的整體問題的思索。因為,如果不諱疾忌醫(yī)的話,我們就應該坦承,人類文明的發(fā)展其實包含著重重悖論。在一定意義上,人類為生存所需,可能有意無意地破壞了“存在之鏈”。創(chuàng)造即毀滅。人類為改善衣食住行所創(chuàng)造的哪一項物質(zhì)成就,不是以其他存在的被消耗或死亡為代價的?譬如水泥路面的建造。人們在發(fā)明堅固耐久的材料,用它來構(gòu)筑平整光潔的路面時,也阻塞了地下水源的涵養(yǎng),干涸了地上、地下生物的生命之泉;更何況,這樣的材料可能還是以挖空、炸碎山體而取得的。
的確,環(huán)境史家所研究的各類環(huán)境問題,是一個事關包括人類自身的整個地球的“生死之憂”的大問題。由此,筆者認為,即使環(huán)境史研究停留在這一層面,也足以體現(xiàn)它存在的價值,因為它已驚醒一度沉睡在“發(fā)展”、“進步”之春秋大夢中的人類。在人們當下所制定的應對環(huán)境問題的各種措施中,不能說沒有環(huán)境史學家所貢獻的智慧。關于這一點,美國環(huán)境史學家沃斯特在《我們?yōu)槭裁葱枰h(huán)境史》一文中作了精辟入理的分析,[3] 其看法頗具代表性。
當然,環(huán)境史研究肯定不能也不應停留在為人類文明大唱挽歌的層面,畢竟,人類所擁有的理性“又是一個最坦誠的監(jiān)督者,會對人類生存的偏頗行為發(fā)出調(diào)整的信號”。[4] (P431) 其實,理性在“對人類生存的偏頗行為發(fā)出調(diào)整的信號”時,也不能不受“自然感性”的感召,所以,我們斷不能將它們兩者割裂開來。實際上,人類也正是在其理性和自然感性的共同催促下,一次又一次地發(fā)出要求人類自身調(diào)整的強烈信號的。梭羅、繆爾、利奧波德、卡遜……無數(shù)先賢往圣的言與行,正是他們在面對人類偏頗行為時所發(fā)出的這樣的信號。我們既然有志于環(huán)境史研究,就不僅要學會傾聽和接收這樣的信號,而且還要以我們自己的方式來宣揚這類榜樣的力量。
從這個方面來說,納什在《大自然的權(quán)利――環(huán)境倫理學史》一書中,[5] 已經(jīng)為我們勾勒了如何把握這種“信號”的清晰線索。筆者近幾年在這一領域也有所探尋,并擬定了系統(tǒng)研究的計劃。目前,已從政府立法和民間環(huán)保兩大層面著手,指導研究生共同研究。在政府立法方面,已指導同學研究過英國1876年的《河流防污法》和1906年針對空氣污染的《堿業(yè)法》(制堿業(yè)在19世紀中葉以來一直被英國人視為污染空氣的大戶)。[6] 在民間環(huán)保方面,我們目前關注的主要是發(fā)達國家的相關內(nèi)容。譬如:關于美國,有同學研究了以繆爾為首的自然保護主義者和以平肖為代表的資源保護主義者之間的交鋒。[7] 關于英國,有同學研究了“國民托管組織”(The National Trust for Places of Historic Interest or Natural Beauty)的環(huán)境保護行動,[8] 有同學梳理了“皇家鳥類保護協(xié)會”(The Royal Society for Protection of Birds)興起和發(fā)展的歷史,并分析了其活動的意義和影響,[9] 還有同學正在研究和總結(jié)“皇家防止虐待動物協(xié)會”(The Roy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的歷史和成就。關于日本,有一位同學從環(huán)境社會史的角度研究日本新水俁病問題,探討水俁病患者與同情他們的人士的維權(quán)行為。為此,他去日本留學一年,除了收集文字資料,還作了必要的調(diào)研工作,從而將一個普通的日本匠人――旗野秀人在35年里積極支持水俁病患者并倡導地域再生的言行呈現(xiàn)出來。他在畢業(yè)論文中,花了一節(jié)的篇幅記錄了他對旗野秀人的采訪。從中可以看出,在一些日本人眼中的這位“怪人”在幫助那些面對死亡和痛苦的患者時,以他自己的人性之美,呼喚著人們對人與自然之愛的追求。[10]
2006年,我們編寫了《和平之景――人類社會環(huán)境問題與環(huán)境保護》一書,[11] 該書分三大部分,主要梳理了20世紀人類社會存在的環(huán)境問題和環(huán)境災害,人們面對環(huán)境問題所作的反思,以及各方面力量針對環(huán)境問題所采取的行動。這項工作的開展,從兩個方面增進了我們的認識。一方面,我們從學科層面認識到了環(huán)境史可以拓展和深化的歷史內(nèi)容,以及未來研究的發(fā)展方向。我們認為,環(huán)境史在開辟新的研究領域,譬如物質(zhì)環(huán)境史的同時,還可以與政治史、社會史、思想史、軍事史等相結(jié)合,從而發(fā)展出環(huán)境政治史、環(huán)境社會史、環(huán)境思想史、軍事環(huán)境史等眾多的次分支領域。并且,我們已對其中某些領域及相關的問題進行了初步的探討。[12] 另一方面,我們在思想層面領悟到環(huán)境史研究可以揭示出人類所具有的深刻的悲劇精神。自近代以來這種悲劇精神的某種體現(xiàn),在于哈姆雷特式的形而上沉思始終在與克勞狄斯式的冷靜計算相較量。雖然后者可能一時占上風,甚至仍在變本加厲,但是,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在人類文明史中,對真實的、有機的“家園”之愛和冥想,一直不曾中斷;對自然之內(nèi)在價值的倡導似乎越來越成為這個時代的強音。①
以上是從歷史研究對象的層面來談環(huán)境史研究的意義的。對此,我們還可以補充說,就歷史研究領域和主題的擴大,以及重新探討與解釋眾多的歷史事件和歷史現(xiàn)象而言,譬如,重新探討19世紀英國的霍亂,[13] 重新解釋近代歐洲國家的殖民活動[14] 等,環(huán)境史無疑具有重大的推動作用。
二
那么,從歷史認識論層面,我們又如何把握環(huán)境史研究的意義呢?對于這一問題,筆者在《世界近現(xiàn)代史基本理論和專題》研究生課程教學中,講過“環(huán)境史:作為一種反思的史學理論”這一專題。在此筆者想同大家一同思考這樣的問題,當史學工作者受到當代環(huán)境問題和環(huán)境保護運動的影響,而著手研究環(huán)境史時,他們看待歷史的視角有什么變化?他們對史學作出了什么樣的新的思考?為此,筆者從認識對象、認識主體和認識中介三個方面進行了分析,并且突出強調(diào),當我們說環(huán)境史學工作者從人與自然互動的角度來認識歷史運動,意識到人與環(huán)境的關系自古以來在每一個時期都具有塑造歷史的作用時,我們還要進一步追問并深入研究,環(huán)境史到底應如何認識人、認識自然、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
關于環(huán)境史對人的存在的認識及其意義,筆者曾做過專門的分析。[15] 目前筆者正在思考和研究的是環(huán)境史對自然、對人與自然之關系的認識和書寫問題。對前一個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的高國榮先生在其博士論文《20世紀90年代以前美國環(huán)境史研究》中有一章專門談及,而且談得比較透徹。筆者認為,環(huán)境史研究者在思考這個問題時,除了要充分揭示各時期各文明(包括各學科)中的人們關于自然的“實然”認識外,還應該進一步挖掘他們針對人類自己、約束人類自己而賦予自然的“應然”蘊涵。在這方面,生態(tài)哲學、環(huán)境倫理學無疑是我們從中汲取思想養(yǎng)分的寶庫。其中,尊重自然、敬畏生命、大地倫理學、深生態(tài)學、自然價值論、動物解放論、動物權(quán)利論等學說或主張,對于我們?nèi)绾握J識和定位環(huán)境史的自然觀,可能會很有啟發(fā)。在筆者看來,生態(tài)價值或自然價值本身,不是一個有待證明的問題,而是一種信仰,既然是信仰,信以為真即可。誰都能感覺到,人類能存活到今天,全仰賴著大自然的恩澤;迄今,人類也只能從大地母親那里獲得滋養(yǎng)的乳汁,這是個不爭的事實。但饒有興味的是,自然之先在的權(quán)利和價值作為不爭的事實為何在今天非得經(jīng)過論證還要大力倡導不可呢?這倒是值得研究的問題,而納什在其著作中已為我們勾勒了這一研究的線索。
關于人與自然的關系,筆者在教學中從物質(zhì)、能量和信息之交換的角度進行了論述,現(xiàn)在看來,我們的認識停留在這一步是很不夠的。固然,環(huán)境史研究作為多學科交叉的產(chǎn)物,必然要借鑒其他學科尤其是自然科學所提供的數(shù)據(jù)資料,① 乃至范疇和思想,但是它肯定不應滿足于對有關事實的陳述和對外在關系的認識。我們不要將環(huán)境史局限于專門之學,而要首先將其主張的人與自然互動的核心理念視為一種通識觀念,以重新考察人類的歷史運動,從而如上文所述,對許多歷史現(xiàn)象作出新的解釋。其次,還要將環(huán)境史的人與自然互動理念內(nèi)化為一種情感。這樣,在涉及人與自然之關系問題時,雖然我們已看到,古人早有“天人交相勝”的論述,其中既有交相利的一面,也有交相害的一面,但是我們?nèi)匀恢鲝垼伺c自然之間存在內(nèi)在的生命關聯(lián),人應該踐行對自然的無條件之愛,而這種愛是不需要論證和計算的。為此,也需要我們通過研究將歷史上本來存在的這類愛與美的言行揭示出來,使其中的思想智慧融入今天的生態(tài)文明建設之中。
三
還有,從歷史方法論的角度,我們也可以認識和分析環(huán)境史研究的意義。對此,筆者從治史原則、敘述模式與具體方法等方面,談過環(huán)境史應有的特色及其推動史學發(fā)展的重大意義。譬如,關于環(huán)境史的治史原則,筆者的看法是“上下左右”,這是從環(huán)境史的研究對象出發(fā),并結(jié)合傳統(tǒng)史學和新史學的原則而生發(fā)出來的。具體而言,“上下左右”是對環(huán)境史的研究對象,即人與自然的關系史的形象概括。其中,“上下”主要有兩層含義,一是社會中的上層、下層,一是自然中的天上、地下;“左右”主要指人周圍的動、植物和其他環(huán)境要素。而對上下左右的有機聯(lián)系及其歷史變遷的認識和研究,因?qū)⑸鐣臍v史和自然的歷史勾連起來,從而與傳統(tǒng)史學和新史學相比,可能會更全面、更準確地反映或揭示歷史的存在。這樣,環(huán)境史凸現(xiàn)的“上下左右”的原則,即是對傳統(tǒng)史學的英雄史觀和新史學的“自下而上”原則的繼承和發(fā)展。在這里,“繼承”可以從人及其社會的角度來認識,“發(fā)展”可以從自然的角度來理解。關于環(huán)境史的敘述模式,筆者的表述是“天地人生”,這是對環(huán)境史敘述的立體抽象。其含義是,環(huán)境史的敘述,包含了天、地、人、生物等各種要素,人們通過講述這些要素之間因相互影響、分合交錯而演繹的各種故事,構(gòu)建了一種立體網(wǎng)絡狀的歷史畫面。② 至于環(huán)境史研究的具體方法,尤其是跨學科研究,已有不少學者作了論述,③ 這里不再贅述。
綜上所述,關于環(huán)境史研究的意義問題,我們可以從諸多方面加以把握。對于筆者個人來說,從事環(huán)境史研究也是自己擺脫環(huán)境無意識、增強環(huán)境意識的環(huán)境啟蒙過程。這確實是實情,因為在這之前,筆者從沒考慮過自然的意義這類帶有哲思的問題,即使對自然有些認識,那也只是人人在與自然打交道時都必然會有的那種樸素的直觀的想法。現(xiàn)在,筆者這方面的認識多少有些升華,對自然的愛、對弱者的關懷已內(nèi)化為自己的心性氣質(zhì),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夠較好地遵循深生態(tài)學的理念,儉樸、節(jié)制已成為一種自覺意識。這樣,筆者從事環(huán)境史研究也就能做到更自覺、更積極;不盲從、不懈怠。
如果筆者不研究環(huán)境史,就產(chǎn)生不了上述各方面的認識;換個角度說,筆者以前所學習和研究的歷史,并沒有教給筆者上述那些可能更為這個時代所需要的史學智慧。此外,對于環(huán)境史研究的社會功用或現(xiàn)實意義,筆者曾用三句話來概括,這就是:環(huán)境史研究是認識環(huán)境問題的一條路徑,是解構(gòu)有關環(huán)境問題之不當論調(diào)的一種方法,是增強環(huán)境意識的一個措施。而且,為了將這種認識運用到對現(xiàn)實環(huán)境問題的理解之中,筆者還于今年4月申報了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規(guī)劃“百人工程”項目,倚重“北京地球村環(huán)境文化中心”的兩位朋友,計劃對北京市危險生活垃圾的現(xiàn)狀展開調(diào)查,并從廢物流的角度加以分析。我們期望,通過關鍵問題和關鍵角度,從一個方面切實深入地把握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分類回收和處理的狀況及存在的問題,以便對危險生活垃圾的收集、處置和管理提出具體的建議,并為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的管理,特別是分類回收體系的建設提供決策依據(jù)。這一調(diào)查計劃已得到有關部門的批準,并已按計劃進行。可以說,這項調(diào)查工作的開展,正是環(huán)境問題研究者和環(huán)境教育宣傳者接觸現(xiàn)實、了解現(xiàn)實問題的一種方式,也是環(huán)境史研究的現(xiàn)實意義的一種體現(xiàn)。
[參考文獻]
[1]Hughes,J. Donald. 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M]. Cambridge,UK: Polity Press,2006.
[2][德]卡爾?洛維特著,李秋玲、田薇譯. 世界歷史與救贖歷史:歷史哲學的神學前提[M]. 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2.
[3][美]唐納德?沃斯特,侯深譯. 我們?yōu)槭裁葱枰h(huán)境史[J]. 世界歷史,2004,(3).
[4]周春生. 悲劇精神與歐洲思想文化史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5][美]羅德里克?弗雷澤?納什著,楊通進譯. 大自然的權(quán)利――環(huán)境倫理學史[M]. 青島:青島出版社,1999.
[6]郭俊. 1876年英國《河流防污法》的特征與成因探究[A].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世界史專業(yè)2004屆碩士學位論文;張一帥. 科學知識的運用和利益博弈的結(jié)晶――1906年英國《堿業(yè)法》探究[A].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世界史專業(yè)2005屆碩士學位論文.
[7]胡群英. 資源保護與自然保護的首度交鋒――1901-1913年美國人關于修建赫奇赫奇大壩的爭論[J]. 世界歷史,2006,(3).
[8]宋俊美. 為國民永久保護――論1895-1939年英國國民托管組織的環(huán)境保護行動[A].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世界史專業(yè)2006屆碩士學位論文.
[9]魏杰. 英國皇家愛鳥協(xié)會的興起、發(fā)展及其意義[A].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歷史學專業(yè)2007屆學士學位論文.
[10]陳祥. 從日本安田町反公害運動的新模式看地域再生的內(nèi)涵與意義[A].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世界史專業(yè)2006屆碩士學位論文.
[11]梅雪芹主編. 和平之景――人類社會環(huán)境問題與環(huán)境保護[M]. 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
[12]賈B. 高技術條件下的人類、戰(zhàn)爭與環(huán)境[J]. 史學月刊,2006,(1);劉向陽. 環(huán)境政治史理論初探[J]. 學術研究,2006,(9);劉向陽. 從環(huán)境政治史的視野看20世紀中期英國的空氣污染治理[A].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世界史專業(yè)2007屆碩士學位論文.
[13]毛利霞. 霍亂只是窮人的疾病嗎?――在環(huán)境史視角下對19世紀英國霍亂的再探討[A].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世界史專業(yè)2006屆碩士學位論文.
[14]艾爾弗雷德?W?克羅斯比著,許友民、許學征譯. 生態(tài)擴張主義:歐洲900-1900年的生態(tài)擴張[M]. 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