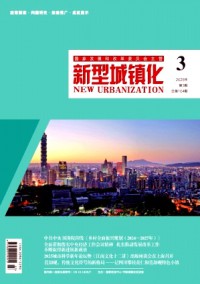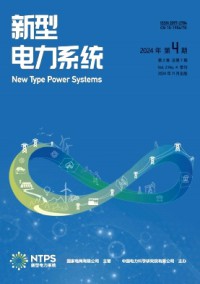新型城鎮(zhèn)化均衡發(fā)展基礎(chǔ)教育論文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新型城鎮(zhèn)化均衡發(fā)展基礎(chǔ)教育論文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chuàng)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一、轉(zhuǎn)變思路,遏制農(nóng)村教育的衰敗
二十多年快速的城鎮(zhèn)化,城市的數(shù)量和疆域不斷擴張,農(nóng)村人口也越來越涌向城市。農(nóng)村人口的這種大規(guī)模流動,使得城市和農(nóng)村發(fā)展呈現(xiàn)出截然相反的兩面:城市建設(shè)熱火朝天,而農(nóng)村卻逐漸走向衰落。法國著名農(nóng)村社會學(xué)家孟德拉斯(HenriMendras)在其著作《農(nóng)民的終結(jié)》中所描繪的場景正在中國上演,隨著“農(nóng)民的終結(jié)”,農(nóng)村也正經(jīng)歷著前所未有的變遷,以往“家長里短”的鄉(xiāng)村正呈現(xiàn)“空殼化”的景象。有人說鄉(xiāng)村出現(xiàn)了“產(chǎn)業(yè)空、住房空、年輕人空、干部空”的“四大皆空”現(xiàn)象,用“鄉(xiāng)村的終結(jié)”一語來形容我國農(nóng)村的衰敗走向雖顯得夸張,但也在某種程度上表達著人們對當(dāng)前農(nóng)村現(xiàn)狀的擔(dān)憂。農(nóng)村的空巢化也使得本來就薄弱的農(nóng)村教育呈現(xiàn)出蕭條的景象,也正成為人們議論的熱點。“從宏觀上來看,城市化是轉(zhuǎn)移農(nóng)村剩余勞動力、提高農(nóng)民收入水平、改造村落社會結(jié)構(gòu)的必由之路。而且我們通常認(rèn)為,這個城市化的過程是充滿農(nóng)民的歡慶、喜悅和夢幻的。然而,在村落城市化的最后一環(huán),在村落的終結(jié)點上,我們看到的卻是一個千年村落文明裂變和新生的艱難。”中國的城鎮(zhèn)化道路應(yīng)該有別于西方國家“圈地式”的“被動城鎮(zhèn)化”,不應(yīng)成為一種被動的“上樓運動”。作為一個后發(fā)型國家,我們要規(guī)避西方在城鎮(zhèn)化過程中所走的彎路,走一條不遺棄農(nóng)村發(fā)展的新型城鎮(zhèn)化道路,將城鎮(zhèn)化與新農(nóng)村建設(shè)結(jié)合起來,“雙輪驅(qū)動”中國的發(fā)展。新型城鎮(zhèn)化的這一特征必然要求我們在推進城鎮(zhèn)化的過程中,轉(zhuǎn)變觀念,切切實實重視農(nóng)民的需求和農(nóng)村的發(fā)展,將農(nóng)村教育辦好。
第一,重新審視農(nóng)村小規(guī)模學(xué)校的價值,分類處理農(nóng)村學(xué)校面臨的困境。“農(nóng)村小規(guī)模學(xué)校”,一般指的是100人以下的農(nóng)村學(xué)校,包括農(nóng)村教學(xué)點、不完全小學(xué)和一部分完全小學(xué),它們主要分布在經(jīng)濟落后、交通不便、人口密度小的農(nóng)村地區(qū)。由于“小規(guī)模學(xué)校”從其經(jīng)費投入與教師配置上來看,顯得有些“奢侈和浪費”,與教育上的“規(guī)模效應(yīng)”理論是不相符的,因此,我國開始了十多年的“撤村并校”“布局調(diào)整運動”,雖然國家一再明令禁止地方在布局調(diào)整上的“隨意化”舉動,但是,此輪“布局調(diào)整”從始到終飽受爭議。一直到2010年后,隨著由“撤村并校”造成的學(xué)生上學(xué)所引發(fā)的“校車事故”頻發(fā),國家才又重新開始審視此輪“布局調(diào)整運動”中的“盲動”行為。2012年國務(wù)院《關(guān)于規(guī)范農(nóng)村義務(wù)教育學(xué)校布局調(diào)整的意見》,提出“堅決制止盲目撤并農(nóng)村義務(wù)教育學(xué)校”,標(biāo)志著我國農(nóng)村義務(wù)教育的發(fā)展進入一個重新反思和改革的階段,宣告我國農(nóng)村基礎(chǔ)教育進入“后布局調(diào)整時代”。面對農(nóng)村“小規(guī)模學(xué)校”,首先,我們應(yīng)重新審視他們存在的價值。要將農(nóng)村學(xué)校視為一方水土之文脈,重視農(nóng)村學(xué)校對農(nóng)村社區(qū)發(fā)展所具有的價值,意識到若斬斷這條文脈,一方土地也將失去其存在的文化根柢。這并非是文人學(xué)者“鄉(xiāng)土情結(jié)”的自我悲情,而是應(yīng)實實在在樹立的一種教育理念,鄉(xiāng)村社會隨著鄉(xiāng)村學(xué)校的消逝必然走向消亡,因為在現(xiàn)代鄉(xiāng)村社會中“學(xué)校教育”儼然成為鄉(xiāng)村的“心臟”,若“心臟”不在,鄉(xiāng)村民眾也將“心不在焉”,逐漸逃離故土。“學(xué)校是一個社區(qū)組織,學(xué)校的存在是一個社區(qū)適宜居住的標(biāo)志與象征。如果學(xué)校脫離了鄉(xiāng)村社區(qū),從文化的意義上說,它就不再是什么鄉(xiāng)村學(xué)校了。而農(nóng)村學(xué)校布局調(diào)整的過程恰恰使學(xué)校越來越遠離鄉(xiāng)村社區(qū),從而加劇了鄉(xiāng)村的荒漠化。”因此,除非必要,否則,我們不應(yīng)因“規(guī)模小”而對學(xué)校進行撤并。其次,從發(fā)達國家農(nóng)村基礎(chǔ)教育發(fā)展的軌跡來看,諸如美國,在經(jīng)歷了20世紀(jì)中期的農(nóng)村學(xué)校合并運動后,在反思與質(zhì)疑聲中,從20世紀(jì)70年代開始,特別是到了90年代,重新掀起了“小規(guī)模學(xué)校運動”。我們的近鄰、同屬東亞文化圈的韓國也經(jīng)歷了大致相同的軌跡,目前韓國已經(jīng)開始調(diào)整農(nóng)村小規(guī)模學(xué)校合并政策,通過改善教育財政制度、建立適當(dāng)規(guī)模學(xué)校、建立特色小規(guī)模學(xué)校、加強農(nóng)村小規(guī)模學(xué)校的師資建設(shè)等措施來糾正以往政策的偏差。因此,我們應(yīng)正視農(nóng)村小規(guī)模學(xué)校存在的問題,避免盲目撤并。再次,要認(rèn)識到小規(guī)模學(xué)校因為班容量小、師生比大,易于教師因材施教,因而具有推進個性化教育等優(yōu)勢。在正視農(nóng)村小規(guī)模學(xué)校價值的基礎(chǔ)上,我們再分類解決農(nóng)村小規(guī)模學(xué)校問題,雷萬鵬提出了較為合理的建議,他指出應(yīng)以公正的程序?qū)r(nóng)村小規(guī)模學(xué)校進行準(zhǔn)確定位,對不同類型的小規(guī)模學(xué)校采取分類發(fā)展政策:(1)對于需要關(guān)閉的小規(guī)模學(xué)校,應(yīng)在學(xué)生分流、校車服務(wù)、校產(chǎn)處置等方面實施配套政策;(2)對于過渡期保留的小規(guī)模學(xué)校,應(yīng)在校舍穩(wěn)固、兒童安全、師資供給等方面保障兒童合法權(quán)益;(3)對于永久保留的小規(guī)模學(xué)校,應(yīng)當(dāng)在經(jīng)費投入、師資配置、基礎(chǔ)建設(shè)、設(shè)施設(shè)備和學(xué)校管理等方面實施傾斜性政策,促進農(nóng)村小規(guī)模學(xué)校特色化發(fā)展。
第二,在新型城鎮(zhèn)化背景下,應(yīng)立足本土,重視農(nóng)村教育的特色化發(fā)展。當(dāng)前,隨著義務(wù)教育學(xué)校標(biāo)準(zhǔn)化建設(shè)的開展,農(nóng)村學(xué)校在硬件上已有很大改進,但農(nóng)村教育如何辦出特色卻是今后需要深入思考的一個問題。筆者認(rèn)為農(nóng)村教育只有扎根本土,開門辦學(xué),與自己所處的社區(qū)相聯(lián)系,認(rèn)識農(nóng)村本土的文化,才有可能辦出特色。當(dāng)前我國農(nóng)村教育的問題之一就是盲目仿照城市教育的辦學(xué)模式,而忽略了自己的本土特征。“當(dāng)城市的幼兒園注重生態(tài)教育,走進大自然,帶領(lǐng)兒童體驗大自然時,農(nóng)村的幼兒園卻置自己得天獨厚的自然環(huán)境、自然資源于不顧,學(xué)著城市幼兒園開辟植物園、種植角。當(dāng)城市的幼兒園課程走向‘生成化’、‘生活化’時,農(nóng)村的很多很多幼兒卻被關(guān)在小小的教室里,用著小學(xué)生退下來的課本,按著小學(xué)生的作息時間與課表上課,沒有活動,沒有游戲……”由于一直以來受“離農(nóng)”教育的思維束縛,我國農(nóng)村教育已經(jīng)喪失了文化之根,形成了不自覺的“向城性”。當(dāng)前,隨著新型城鎮(zhèn)化和新農(nóng)村建設(shè)的推進,我們應(yīng)將農(nóng)村教育置于新農(nóng)村建設(shè)的文化場域中,視農(nóng)村學(xué)校為農(nóng)村社區(qū)的“文化堡壘”。在新農(nóng)村建設(shè)的過程中,隨著農(nóng)村面貌的改善,農(nóng)村教育應(yīng)當(dāng)樹立自信心,重新發(fā)現(xiàn)農(nóng)村之美,發(fā)現(xiàn)農(nóng)村之于城市之優(yōu)勢。這一點成都市蒲江縣的探索是值得學(xué)習(xí)的。蒲江縣在發(fā)展農(nóng)村教育的時候,結(jié)合當(dāng)?shù)禺a(chǎn)業(yè)發(fā)展,創(chuàng)造性地開展了以“自然、綠色、融合、開放”為特征的現(xiàn)代田園教育。大力整合普通中小學(xué)教育和社區(qū)教育資源,建立了“一校掛兩牌”的學(xué)校運營機制,逐步探索出“學(xué)校+家庭+企業(yè)+社區(qū)”四位一體的教育模式。學(xué)校與茶葉產(chǎn)業(yè)相結(jié)合,“學(xué)校內(nèi)外都是茶園,茶園處處皆教育”,不但使學(xué)校具有濃厚的文化氛圍,也推動了當(dāng)?shù)夭枞~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成為農(nóng)村學(xué)校服務(wù)農(nóng)村經(jīng)濟、農(nóng)村教育反哺農(nóng)村社會的典型縮影。當(dāng)然農(nóng)村教育問題的根本解決并非僅靠教育的創(chuàng)新就能完成的,鄉(xiāng)村教育中呈現(xiàn)出的“文字上移”的無助情形,也并非能靠教育改革就能夠挽回的,我們應(yīng)將農(nóng)村教育置于中國社會發(fā)展的整個大背景中,才能從根本上認(rèn)清和理解“文字上移”的原因。“中國社會正在從鄉(xiāng)土中國走向離土中國,其間有政治、經(jīng)濟、社會、文化的種種表現(xiàn),其中最基本的,是中國農(nóng)村居民的生存狀態(tài)也越來越不依賴于土地或以土地為中心,更不用說城鎮(zhèn)居民了。正是這一趨勢決定了村落學(xué)校教育的‘終結(jié)’,既然人的生存越發(fā)不依賴于鄉(xiāng)土,人們生活的重心越發(fā)遠離村落,那么,以人為目的的教育和文字也就必然地不再留戀鄉(xiāng)土和村落,這一趨向在以普遍性和抽象性為特征的現(xiàn)代教育身上將體現(xiàn)得更為明顯而堅決。”
二、以城帶鄉(xiāng),推進城鄉(xiāng)教育的一體化發(fā)展
傳統(tǒng)的城鎮(zhèn)化以重城輕鄉(xiāng)為基本發(fā)展取向,在發(fā)展城市的同時,不顧及農(nóng)村的發(fā)展,城鄉(xiāng)二元結(jié)構(gòu)明顯,城鄉(xiāng)差距巨大。而新型城鎮(zhèn)化要求統(tǒng)籌城鄉(xiāng)發(fā)展,發(fā)揮城市在農(nóng)村發(fā)展中的引領(lǐng)作用,強調(diào)以城帶鄉(xiāng)。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上,提出了“兩個趨向”的著名論斷,指出在工業(yè)化初期階段,農(nóng)業(yè)支持工業(yè),為工業(yè)提供積累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但在工業(yè)化達到相當(dāng)程度以后,工業(yè)反哺農(nóng)業(yè),城市支持農(nóng)村,實現(xiàn)工業(yè)與農(nóng)業(yè)、城市與農(nóng)村協(xié)調(diào)發(fā)展也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我國現(xiàn)在總體上已到了以工促農(nóng)、以城帶鄉(xiāng)的發(fā)展階段。因此,當(dāng)前我們在推進城鄉(xiāng)教育均衡發(fā)展的過程中,一定要發(fā)揮城市教育的引領(lǐng)作用,將城市優(yōu)質(zhì)教育資源輻射到農(nóng)村,帶動農(nóng)村教育的同步發(fā)展,促進城鄉(xiāng)教育一體化發(fā)展。一方面,采用結(jié)對聯(lián)動的形式,向農(nóng)村教育輸出先進教育理念和優(yōu)質(zhì)教師資源,帶動農(nóng)村教育的發(fā)展。如成都市在推進城鄉(xiāng)教育均衡發(fā)展的過程中,注重頂層設(shè)計,按照其特殊的城市三圈層經(jīng)濟地理結(jié)構(gòu),提出了“全域成都”、“三圈一體”的發(fā)展理念,將三個圈層的教育發(fā)展當(dāng)成“一盤棋”來考量。利用處于第一圈層的城區(qū)優(yōu)質(zhì)教育去帶動處于二、三圈層的薄弱教育。2010年成都市教育局的《關(guān)于深化城鄉(xiāng)學(xué)校結(jié)對發(fā)展工作的意見》,提出了中心城區(qū)學(xué)校對第三圈層學(xué)校的幫扶計劃,由第一圈層的學(xué)校與第三圈層學(xué)校結(jié)對發(fā)展,錦江區(qū)與青白江區(qū)和金堂縣學(xué)校結(jié)對,青羊區(qū)與蒲江縣、崇州市學(xué)校結(jié)對,武侯區(qū)與崇州市和新津縣學(xué)校結(jié)對,成華區(qū)與大邑縣學(xué)校結(jié)對,金牛區(qū)與邛崍市學(xué)校結(jié)對,高新區(qū)與都江堰學(xué)校結(jié)對。除此之外,各個郊區(qū)(縣)的城區(qū)學(xué)校還要與農(nóng)村學(xué)校結(jié)對發(fā)展,于是就形成了主城區(qū)—郊區(qū)城區(qū)、郊區(qū)城區(qū)—農(nóng)村地區(qū)這樣兩個輻射圈,構(gòu)成了全域成都教育發(fā)展的獨特模式。結(jié)對互動的內(nèi)容主要包括:學(xué)校管理、教學(xué)教研、干部教師、德育工作等。成都市推進城鄉(xiāng)教育一體化的探索取得了豐富的經(jīng)驗,取得了不少成績,并于2013年9月成為中西部地區(qū)首個通過教育部義務(wù)教育基本均衡發(fā)展督導(dǎo)認(rèn)定的城市。另一方面,在政策設(shè)計方面,要進行城鄉(xiāng)教育的一體化設(shè)計,縮小城鄉(xiāng)教育的人為差距。如蘇州市在推進城鄉(xiāng)教育一體化的時候就提出“六個一樣”,即“校園環(huán)境一樣美,教學(xué)設(shè)施一樣全,公用經(jīng)費一樣多,教師素質(zhì)一樣好,管理水平一樣高,學(xué)生個性一樣得到弘揚”。成都市在推進城鄉(xiāng)教育一體化時,著力從六個方面的一體化入手:發(fā)展規(guī)劃城鄉(xiāng)一體化、辦學(xué)條件城鄉(xiāng)一體化、隊伍建設(shè)城鄉(xiāng)一體化、教育質(zhì)量城鄉(xiāng)一體化、評估標(biāo)準(zhǔn)城鄉(xiāng)一體化、教育經(jīng)費城鄉(xiāng)一體化,尤其在教師隊伍一體化建設(shè)方面,探索出了“縣管校用”的模式,打破了學(xué)校對教師的“一校所有制”,打破了教師“從一而終”的模式,讓校長教師真正“流動”起來,為城鄉(xiāng)教育的順利交流互動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創(chuàng)新機制,推進城市教育的校際間均衡
城市中的擇校問題從根本上說是城市優(yōu)質(zhì)教育資源不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對優(yōu)質(zhì)教育資源的需求而出現(xiàn)的,城鎮(zhèn)化在其中起著很大的助推作用,可以說城鎮(zhèn)化加劇了城市中的擇校問題。隨著農(nóng)村人口向城市的聚集,一方面農(nóng)村出現(xiàn)了“空殼校”,另一方面也使得城市中本來就稀缺的優(yōu)質(zhì)教育資源更加緊缺。因此,擴大城市優(yōu)質(zhì)教育資源的覆蓋面,促進城市學(xué)校間的校際均衡,也成為新型城鎮(zhèn)化的要求之一。近幾年來,我國一些大城市在推進校際教育均衡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探索出了不少擴大優(yōu)質(zhì)教育資源覆蓋面、促進教育均衡的機制。其中最典型的當(dāng)屬名校集團化和學(xué)區(qū)管理制兩種方式。
第一,名校集團化。名校集團化是一個區(qū)域的名校在地方政府的介入下,為實現(xiàn)名校優(yōu)質(zhì)教育的輸出與薄弱校教育質(zhì)量的迅速提升,將區(qū)域內(nèi)一些較為薄弱的學(xué)校納入名校的治理下,采用分校的形式,使名校與薄弱校形成名校集團這種學(xué)校共同體,以名校為龍頭,在教育理念、學(xué)校管理、教育科研、信息技術(shù)、教育評價、校產(chǎn)管理等方面統(tǒng)一管理,實現(xiàn)管理、師資、設(shè)備等優(yōu)質(zhì)教育資源的共享。名校集團一般有一定的治理結(jié)構(gòu),這種治理結(jié)構(gòu)包含了政府、名校和分校三者的權(quán)力和利益,其中政府起協(xié)調(diào)作用,名校本部起主導(dǎo)作用,分校起主體作用,分校在名校本部的幫扶下成長。在我國,杭州市較早地對名校集團化進行了探索,并取得了有益的經(jīng)驗。杭州名校集團化的探索始自20世紀(jì)末。1999年,浙江大學(xué)附屬小學(xué)———求是小學(xué)接管了城西新建小區(qū)配套學(xué)校———競舟校區(qū),拉開了全國名校集團化探索的序幕,2002年10月,浙江省首個公辦基礎(chǔ)教育集團———杭州求是教育集團在西湖區(qū)正式成立,這是中國第一個以實現(xiàn)義務(wù)教育優(yōu)質(zhì)均衡化為目標(biāo)的公辦基礎(chǔ)教育集團。在總結(jié)求是教育集團等名校連鎖辦學(xué)成功經(jīng)驗的基礎(chǔ)上,杭州市將“實施名校集團化戰(zhàn)略”作為推進教育均衡的重要手段,并有力地推動了杭州市基礎(chǔ)教育的均衡發(fā)展。在杭州名校集團化探索的同時,全國一些大中小城市也開始了運用名校集團化模式來促進基礎(chǔ)教育的均衡發(fā)展,如成都、合肥、濟南、哈爾濱等,均取得了較大的成效。
第二,學(xué)區(qū)管理制。學(xué)區(qū)管理制在有些地方又被稱為“大學(xué)區(qū)制”(如西安)或“聯(lián)合學(xué)區(qū)制”(如天津)。與名校集團化類似,學(xué)區(qū)管理制也是擴大優(yōu)質(zhì)教育資源輻射面,迅速提升薄弱學(xué)校教育質(zhì)量的一種很好的嘗試。“學(xué)區(qū)化管理”是按照區(qū)域內(nèi)優(yōu)質(zhì)教育資源分布狀況和行政區(qū)劃,以街道為單位劃分若干學(xué)區(qū),每個學(xué)區(qū)都有各級各類優(yōu)質(zhì)教育資源,通過建立資源共享信息平臺,實現(xiàn)學(xué)校設(shè)施設(shè)備資源、課程資源、人力資源共享,使學(xué)區(qū)間的教育資源相對均衡,以促進教育優(yōu)質(zhì)均衡發(fā)展。實施學(xué)區(qū)制的學(xué)校一般由教育行政部門指定一所優(yōu)質(zhì)學(xué)校為學(xué)區(qū)長,吸納3至5所同類型、同層次的相對薄弱的成員學(xué)校,就近合理組建成為一個大學(xué)區(qū)。納入大學(xué)區(qū)管理制改革的學(xué)校,可通過緊湊型、松散型或混合型等多種形式,實現(xiàn)捆綁式發(fā)展。在我國,北京市東城區(qū)較早地開展了學(xué)區(qū)制的改革,從2004年10月起,東城區(qū)開始在和平里學(xué)區(qū)進行學(xué)區(qū)化管理試點,根據(jù)東城區(qū)優(yōu)質(zhì)教育資源的分布狀況和街道行政區(qū)劃,將全區(qū)10個街道劃分為5個學(xué)區(qū),東城區(qū)的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廣州市越秀區(qū)的學(xué)區(qū)制改革也較為成功,越秀區(qū)學(xué)區(qū)制管理模式的主要內(nèi)容可以概括為“三個共享、兩個建立”,即共享學(xué)區(qū)教學(xué)資源、共享教師人力資源、共享合作發(fā)展平臺,建立學(xué)區(qū)管理體系、建立學(xué)區(qū)評價機制。此外,近些年很多城市都開始推廣學(xué)區(qū)制改革,如天津、鄭州、貴陽、武漢、西安、長沙等。
四、關(guān)注弱勢,推進城市教育服務(wù)的均等化
我國近十年的城鎮(zhèn)化速度雖然迅速,但是卻存在“虛假城鎮(zhèn)化”的危險,據(jù)數(shù)據(jù)顯示,2012年,我國的城鎮(zhèn)化率達52.6%,而按城鎮(zhèn)戶籍人口計算的城鎮(zhèn)化率僅35.3%,之間存在著17.3個百分點的差距。這說明,2.5億農(nóng)民工和約7500萬城鎮(zhèn)間流動人口在城市還沒有享受到與城鎮(zhèn)戶籍居民同等的公共福利。一些學(xué)者將城鎮(zhèn)化的這種現(xiàn)象稱為農(nóng)村流動人口的“半城市化”,即農(nóng)民雖然進入了城市,在城市找到了工作,也生活在城市,但是,問題在于,城市只把他們當(dāng)作經(jīng)濟活動者,僅僅將他們限制在邊緣的經(jīng)濟領(lǐng)域中,沒有把他們當(dāng)作具有市民或公民身份的主體,從體制上沒有賦予其基本的權(quán)益,在生活和社會行動層面將其排斥在城市的主流生活、交往圈和文化活動之外,在社會認(rèn)同上對他們進行有意無意的貶損甚至妖魔化。進入城市的農(nóng)民并未真正轉(zhuǎn)變?yōu)槌鞘械氖忻瘢]有享受到城市人所享有的公共服務(wù)和福利,他們中的一部分成為“城市中的邊緣人”,成為城鄉(xiāng)二元結(jié)構(gòu)外的第三元,使得城市內(nèi)部又出現(xiàn)了特有的二元結(jié)構(gòu)。面對城鎮(zhèn)化中存在的這一問題,新型城鎮(zhèn)化將人的城鎮(zhèn)化作為城鎮(zhèn)化推進的重點,將推進公共服務(wù)均等化作為城鎮(zhèn)化發(fā)展的關(guān)鍵。基礎(chǔ)教育作為國家公共服務(wù)的一部分,使進城農(nóng)民子女享有均等的基礎(chǔ)教育入學(xué)機會和升學(xué)機會就成為新型城鎮(zhèn)化背景下我國基礎(chǔ)教育均衡發(fā)展的重要內(nèi)容。讓進城農(nóng)民子女享有均等的教育服務(wù)關(guān)鍵是要打破我國城鄉(xiāng)分割的二元化的教育制度,破解這一問題表面上看有賴于戶籍制度的改革,但從實質(zhì)而言,我國城鄉(xiāng)分割的二元化結(jié)構(gòu),是由依附于戶籍制度的一系列不平等制度所造成的,如入學(xué)制度、升學(xué)制度、就業(yè)制度等,因此,逐步剝離依附于城鄉(xiāng)二元戶籍制度上的各種教育制度,才是我們推進城市公共教育服務(wù)均等化的根本所在。就當(dāng)前而言,除了要進一步解決好流動兒童的就學(xué)問題,有序推進異地高考問題也已顯得非常必要。
作者:劉秀峰單位:四川師范大學(xué)教師教育學(xué)院
文檔上傳者
相關(guān)推薦
新型縣域經(jīng)濟 新型能源管理 新型包裝技術(shù) 新型醫(yī)學(xué)技術(shù) 新型農(nóng)業(yè)論文 紀(jì)律教育問題 新時代教育價值觀
- 新型農(nóng)民培育
- 新型磁力儀
- 企業(yè)新型員工
- 新型治水模式思考
- 新型膠凝材料
- 新型玻璃語文教案
- 新型農(nóng)村醫(yī)療試點情況
- 創(chuàng)新型城區(qū)意見
- 新型載體檔案管理
- 新型農(nóng)民培訓(xùn)動員講話4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