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整理技術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檔案整理技術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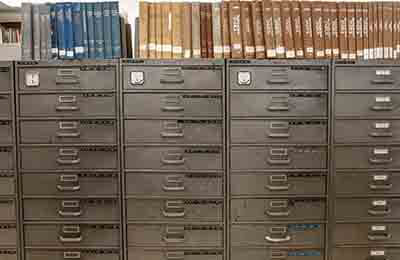
在全世界,已經相當成熟的傳統檔案實體整理技術,在電子文件出現之后遭遇了無法克服的困難,檔案整理技術進入了一個最為活躍和多樣化的變革時代。
對此,西方檔案界已經取得了比較一致的認識和實踐成果,他們以“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為理論基礎,以文檔一體化為實踐基礎,在電子政務平臺上,創造了元數據的檔案整理技術,從而結束了西方傳統檔案實體整理的技術時代。而中國檔案界,一方面是迅速地引進了西方的元數據檔案整理技術,另一方面則又提出了自己的多種多樣的檔案整理技術,如“以‘件’為單位的檔案整理技術”、“雙套制的檔案整理技術”、“不同載體的混合檔案整理技術”等等。雖然中國一下出現了如此之多的檔案整理技術,顯得有些混亂,但這些檔案整理技術具有一個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它們并不使用“元數據”來整理檔案。這不是一般的技術上的不同,而是顯露出了中、西方迥然不同的檔案整理技術走向。我們始終認為,中國現有檔案整理技術的出現,必然有它形成的道理。所以,我們借此篇文章,通過對不同檔案整理技術的比較,來揭示檔案整理技術的本質及其我國檔案整理技術的發展趨勢。
“元數據檔案整理技術”已被檔案界普遍接受,“非元數據檔案整理技術”則還是一個剛剛提出的概念。這里只是利用“非”這一重要的邏輯概念表明,只要西方的“元數據”不是檔案整理的唯一技術,那么在“元數據”之外,就應該有“非元數據”檔案整理技術的存在。大家必須理解,我們提出“非元數據檔案整理技術”,并不是要去反對和否定元數據檔案整理技術,而只是要用“非元數據檔案整理技術”的概念開道,來梳理在中國已經出現的檔案整理技術,并證明它們同樣是現代的,而且是更適應中國檔案實踐的檔案整理技術體系。
一、元數據檔案整理技術
“元數據檔案整理技術”是西方檔案界提出的一種檔案整理技術。而西方產生這種技術的實踐基礎是,他們利用計算機網絡及其技術實現了“電子政務”,并且使“電子政務平臺”成為他們日常行政管理的實踐基礎和管理工具。
在這種特殊的條件下,電子政務系統本身不僅能產生著電子文件、而且也能提供電子文件的實體信息(數據),并且能根據電子文件生成的具體環節,提供隱含在具體環節背后的、電子文件與社會實踐及其過程之間的對應信息——元數據(數據的數據),即檔案實踐通常所稱的“檔案歷史聯系信息”。于是,嵌在電子政務平臺中的檔案整理系統就可以在電子政務的支持下,利用所采集的“元數據”完成“檔案歷史聯系”的整理,它不但獲得了“電子文件實體集合”,而且具有了足以使這一文件實體集合轉化為檔案的“檔案歷史聯系的記錄”。而“電子文件實體集合”和“檔案歷史聯系的記錄”這兩種物質實體的獲得,就構成了它所要得到的電子檔案實體。因此“元數據檔案整理技術”本身是一個具有科學性、高自動化程度的檔案整理技術體系。
由于現在西方和我國還只是將“元數據檔案整理技術”嵌入到了電子政務系統,所以有人可能誤認為,元數據檔案整理技術只適用于電子政務。其實不然,它不但能適應電子政務的檔案整理,而且也能適應諸如電子銀行、電子商務、電算化會計等等電子管理平臺的應用。事實上,只要人們能為某一社會實踐的管理建立電子管理的平臺,那么元數據檔案整理技術就能嵌入這個電子管理系統,成為適應它的檔案整理技術。所以“元數據檔案整理技術”本身是一種具有很寬實踐范疇的實用檔案整理技術。
“元數據檔案整理技術”所具有的特征是,它徹底變革了傳統檔案實體整理的技術,成為“文件實體整理”與“檔案歷史聯系整理”分離的技術。這種文件實體與檔案歷史聯系整理的技術分離,使元數據檔案整理技術中的“檔案歷史聯系整理”,不再受電子文件實體的干擾,而使檔案整理真正地進入了多元的時代,使檔案整理原則從一維的“來源原則”,發展為具有“實踐主體”、“實踐客體”和“年代”的多維“歷史原則”。“元數據檔案整理技術”所具有的“文件實體整理與檔案歷史聯系整理技術的分離”、“檔案歷史聯系整理的多維化”、“檔案整理原則的多元化”和“檔案物質實體的雙重構成”是其檔案整理技術的四大特征。
二、非元數據檔案整理技術
在檔案整理技術中“非元數據”與“元數據”是相對存在的兩種檔案整理技術。從概念上說,除了“元數據”的檔案整理技術之外,都屬于“非元數據”檔案整理的技術范疇。但本篇文章不再研究傳統的檔案實體整理,它包含的只是新提出的“以‘件’為單位的檔案整理技術”、“雙套制的檔案整理技術”和“不同載體的混合檔案整理技術”。
不管是“以‘件’為單位的檔案整理技術”,還是“不同載體的混合檔案整理技術”,它們的檔案實體整理與檔案歷史聯系整理都是相互分離的。“雙套制的檔案整理技術”比較特殊,從表面上看,它是用整理紙質檔案的方法完成了電子檔案的整理,但它同樣告訴我們,也能夠用整理電子檔案的方法整理紙質檔案。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中國檔案界提出的這些非元數據的檔案整理技術,具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它們都是“檔案實體整理”與“檔案歷史聯系整理”相互分離的檔案整理技術。由于這些“非元數據檔案整理技術”是“檔案實體整理”與“檔案歷史聯系整理”相互分離的技術,所以它們就同樣都能實現檔案歷史聯系的多維化。它的檔案整理原則,也可以從一維的“來源原則”,過渡到具有“實踐主體”、“實踐客體”和“年代”的多維“歷史原則”。它們最終都要形成由“文件的實體集合”和“檔案歷史聯系的記錄”兩種物質實體共同構成檔案。
于是我們發現,中國提出的非元數據檔案整理技術雖然還存在著許多的缺點,但在“質”上,這些非元數據檔案整理技術都具有“文件實體整理與檔案歷史聯系整理的分離”、“檔案歷史聯系整理的多維化”、“檔案整理原則的多元化”和“檔案物質實體的雙重構成”的四大檔案整理技術的特征。
三、兩種典型檔案整理技術的比較
我們的研究發現,雖然非元數據和元數據檔案整理技術的技術環境、流程和操作方法有著很大的不同,但它們具有相同的四大特征,并且這兩種檔案整理技術具有相同的內在結構,完全可以用同一的《檔案整理結構的模型》來認識和解釋它們的機理和過程。或者說,是因為它們具有相同的檔案整理結構,所以它們才具有它們的共同特征。所以非元數據和元數據檔案整理技術這兩種看似非常不同的檔案整理技術,其實是同一檔案整理結構的兩種不同技術表現形式。
為什么會產生這兩種不同的檔案整理技術形式,或者說,西方為什么采用元數據檔案整理技術,而中國為什么要采用非元數據檔案整理技術,而這是相同的檔案整理原理為適應不同國家檔案實踐條件而產生必然結果。在中國,其實始終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檔案實踐和理論體系。一種是,從民國時期開始的“文檔連鎖法”,后來的“文檔一體化”和現階段提出的“文件中心”,與之相應的則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論;而另一種則是,與文書實踐分離的檔案實踐,在解放后,中國接受了前蘇聯的檔案實踐和“立卷人——檔案室——檔案館”的檔案實踐體制,同時也就形成了有別于西方的檔案學理論。
原理、價值和理念要過渡到實踐,就需要技術的中介,由于技術離實踐更近,所以它更要受到實踐的約束,先進的技術并非在哪里都適用,對誰都是具有實用的價值。中國人民大學王健教授在國家社科基金項目“OA環境下的文件、檔案一體化管理研究”的技術報告中就客觀和直率地提出,在中國“無論是檔案行政管理機構,還是檔案館,都無權指導各機構的文件工作,……因而無法具備全面的一體化功能。”①對于在中國建立文件中心的問題上她也指出“全盤否定檔案室的態度是不科學的,完全撤銷檔案室的做法是不現實的,在保留檔案室的基礎上再重建一套文件中心是不必要的,簡單地將檔案室改名為文件中心也解決不了根本問題。”②這些認識對于認識檔案整理技術的發展同樣有效。
我們應特別注意,計算機化與現代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比如,一種檔案整理技術雖然沒有實現計算機化,但如果它能實現多維的檔案歷史聯系聯系整理;而另一個雖然實現了計算機化,但它形成的檔案歷史聯系卻是一維的,那么我們究竟應該將哪種技術判斷為現代檔案整理技術呢?檔案整理技術現代化的關鍵是檔案整理技術內容上的現代化,計算機化只是檔案整理現代化的一種外在的形式。
在自動化和計算機技術應用的程度上,元數據顯然要高于非元數據檔案整理技術。但在中國發展元數據檔案整理技術,有著諸多檔案界自身無法克服的現實障礙,但只要我們放棄部分元數據檔案整理技術的高自動化要求,那么就可以在不改變檔案工作體制、不需要實現“文檔一體化”、能脫離電子政務環境、不用制定也不依賴“檔案元數據集”的條件下,創造出一種可應用于文書和科技檔案、并適用于紙質文件、電子文件和實物混合的、非常實用的檔案整理技術。所以不要簡單化地根據計算機技術的應用程度,來論檔案整理技術的長短。
四、中國檔案整理技術前景的展望
通過“非元數據檔案整理技術”與“元數據檔案整理技術”的比較研究,我們認為:
中國檔案界,須在元數據和非元數據檔案整理技術之間做一抉擇,這是不能回避的。它不是單純的檔案理論和技術問題,而是干系到中國檔案事業未來發展的一次抉擇。它是檔案工作者、檔案學者和中國檔案事業的領導者都必須傾心關注的問題。
不應該排斥元數據檔案整理技術,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非元數據檔案整理技術”應該是一條更適應中國國情的檔案整理技術路線。我們甚至認為,它是遲早要被國人所接受的一種檔案整理技術。
“非元數據檔案整理技術”雖然已經有了基礎,但技術整體還處于相當混亂的狀態。我國應該在夯實它的檔案學理論基礎、簡約它的技術、注重它的實用性的前提下,統一制定中國的檔案整理技術規范。其結果應該是創造出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檔案整理技術體系和理論。這也是中國檔案界在世界有所建樹的一個契機。
我國在轟轟烈烈引進元數據檔案整理技術的過程中已經積累了許多實踐經驗,現在是否應該對它進行一次階段性的總結,召開一次高端研討會,客觀地評價一下得失,這可能是一個非常有益的建議。
注釋:
①②王健:《電子時代機構核心信息資源管理》,中國檔案出版社2003年版,第58~5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