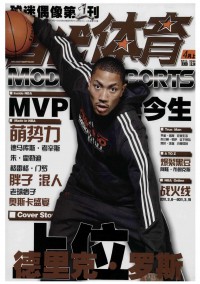體育舞蹈拉丁舞與敦煌舞的契合點(diǎn)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體育舞蹈拉丁舞與敦煌舞的契合點(diǎn)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chuàng)作提供參考價(jià)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gè)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一、拉丁舞與敦煌舞在舞蹈形態(tài)上的契合點(diǎn)
(一)都具有“直曲并存”體態(tài)特征
在舞蹈形態(tài)上,拉丁舞與敦煌舞都具有“曲直并存”的體態(tài)特征。在西方審美文化的影響下,拉丁舞同芭蕾舞一樣都具有“開(kāi)、繃、直、立”的特點(diǎn)。這種“直”的特點(diǎn)將英國(guó)皇室貴族的風(fēng)度和氣質(zhì),外化于形態(tài),在動(dòng)作中表現(xiàn)為身體軸線的垂直。拉丁舞“曲”體態(tài)的體現(xiàn),是舞者運(yùn)動(dòng)時(shí)身體重心下沉、骨盆擰扭所致的一種螺旋狀曲線形態(tài),即“S”型體態(tài)。在身體軸線垂直的前提下,舞者身體重心下壓,導(dǎo)致人體髖部向旁擺出形成側(cè)面的曲線。因此拉丁舞曲直并存的體態(tài),是在軸線垂直基礎(chǔ)之上身體的擰扭擺動(dòng),是一種以“直”為基礎(chǔ)的“曲”。敦煌舞的“直”同樣是指身體軸線垂直,動(dòng)作中的任何舞姿都是在軸線垂直及重心穩(wěn)定的前提下所完成的。而敦煌舞“曲”的體態(tài),也是以直為基礎(chǔ)的“S”型體態(tài),即舞者髖部、肋部?jī)烧叩姆聪蚶В缱y、扭腰、沖肋、歪頭等形成的“三道彎”體態(tài)。由此可見(jiàn),拉丁舞與敦煌舞都具有直曲并存的體態(tài),這是兩者融合的契機(jī),兩種舞蹈語(yǔ)匯融合塑造飛天形象是完全可以實(shí)現(xiàn)的。
(二)都具有“擰扭”運(yùn)動(dòng)態(tài)勢(shì)特征
在運(yùn)動(dòng)態(tài)勢(shì)上,拉丁舞與敦煌舞都具有鮮明的擰扭運(yùn)動(dòng)態(tài)勢(shì),兩者在動(dòng)勢(shì)上都存在上下肢呈反方向的擰扭運(yùn)動(dòng)態(tài)勢(shì)。拉丁舞是上肢相對(duì)固定,下肢圍繞垂直軸做擰扭運(yùn)動(dòng),如拉丁舞中恰恰舞步原地?fù)Q重心,是舞者肋骨以上的位置向前,肋骨以下的位置做相反對(duì)抗轉(zhuǎn)動(dòng)。而敦煌舞多是下肢相對(duì)固定,上肢圍繞垂直軸進(jìn)行橫扭動(dòng)勢(shì)運(yùn)動(dòng),如橫擰腰、擰仰腰、回轉(zhuǎn)腰等。兩個(gè)舞種的擰扭都集中于腰部的發(fā)力,這種動(dòng)勢(shì)能夠體現(xiàn)出婀娜的風(fēng)格特征,這是兩個(gè)舞種融合的又一基礎(chǔ)。
(三)都具有“圓弧”運(yùn)動(dòng)軌跡特征
“圓弧”運(yùn)動(dòng)軌跡的產(chǎn)生,與上述擰扭動(dòng)勢(shì)密切相關(guān),也可以說(shuō)是擰扭態(tài)勢(shì)帶出了圓弧運(yùn)動(dòng)軌跡。在拉丁舞技術(shù)中非常強(qiáng)調(diào)身體中段的擰扭動(dòng)勢(shì),這種韻律感使得動(dòng)作之間環(huán)環(huán)相扣,呈現(xiàn)出一種圓弧的運(yùn)動(dòng)軌跡。如拉丁舞中倫巴舞步伐“庫(kù)克拉恰”,一方面舞者通過(guò)髖部的擺蕩、轉(zhuǎn)動(dòng)及身體重心的推動(dòng),完成髖部“8”字圓弧運(yùn)動(dòng);另一方面舞者通過(guò)手臂與身體的對(duì)抗完成由大臂到肘關(guān)節(jié)、小臂再到手指尖的延伸,也是一種圓弧路線的運(yùn)動(dòng)。同樣,在敦煌舞中,擰扭動(dòng)勢(shì)形成了敦煌舞的“S”型運(yùn)動(dòng)軌跡,很多姿態(tài)的形成也是經(jīng)過(guò)平圓、立圓的路線所完成的。在《絲路·行》的倫巴舞段中,創(chuàng)編者掌握了倫巴舞與敦煌舞共有的“圓弧”運(yùn)動(dòng)軌跡,將倫巴舞動(dòng)作與敦煌舞姿融合在一起。
二、拉丁舞與敦煌舞在舞蹈文化上的契合點(diǎn)
(一)東西方樂(lè)舞文化的“同源性”
舞蹈作為一種文化現(xiàn)象,受其所在的地域環(huán)境、歷史人文、生活習(xí)俗、宗教信仰等因素影響,因而呈現(xiàn)出千姿百態(tài)的舞蹈形態(tài)。由于舞蹈文化具有流動(dòng)性,從其產(chǎn)生的那一刻起,就呈現(xiàn)一種從發(fā)源地開(kāi)始向四周輻射、滲透與流動(dòng)的現(xiàn)象,其所覆蓋區(qū)域的舞蹈種類和其它的文化形式,都會(huì)融入它的基因,形態(tài)上也呈現(xiàn)出與其相近似的特征[1]。從《絲路·行》作品來(lái)看,體育舞蹈拉丁舞動(dòng)作元素與敦煌舞動(dòng)作元素的融合,不僅代表了兩種不同舞蹈元素的融合,也映射出了西方樂(lè)舞和東方樂(lè)舞樣式的淵源。古埃及位于尼羅河流域,歐、亞、非大陸的交界處,由于其一直被認(rèn)為是東方國(guó)家,因此其樂(lè)舞風(fēng)格也具有典型的東方樂(lè)舞風(fēng)格特征。古埃及舞蹈形態(tài)特征突出,具體表現(xiàn)為腰部、腹部的快速扭動(dòng)為主,即“扭腰出髖”的形態(tài),并且具有浮雕藝術(shù)般的美感,這種形態(tài)傳入歐洲后,在歐洲“十字架”文化及審美影響下多元融合,影響了包括芭蕾舞在內(nèi)的很多歐洲的舞蹈種類,使得歐洲的舞蹈具有很強(qiáng)的雕塑感和造型性。金千秋也在《古絲路樂(lè)舞文化交流史》中指出:“古埃及舞蹈扭腰出髖、出肋的舞姿極大地影響了古希臘人體雕塑藝術(shù)[2]。”這種古希臘人體雕塑后隨亞歷山大東征傳播到西亞及印度地區(qū),后以犍陀羅佛教形式傳入我國(guó)西北地區(qū),影響了我國(guó)古代龜茲樂(lè)舞,也繼而影響了敦煌樂(lè)舞,從而使我國(guó)洞窟壁畫(huà)也同樣呈現(xiàn)出極強(qiáng)的造型藝術(shù)。事實(shí)上,這種雕塑感和造型性便是東西方樂(lè)舞文化的源頭所流淌下來(lái)的內(nèi)在基因,使體育舞蹈、敦煌舞等都受其影響。造型性和雕塑感較強(qiáng)的拉丁舞與敦煌舞也便成為體育舞蹈表演性作品《絲路·行》創(chuàng)作成功的內(nèi)在文化因素之一。
(二)“混合型”舞蹈的包容性
于海燕在《世界舞蹈文化圈縱橫談》中指出,“東西方文明,包括舞蹈文化是互相依附存在,互相滲透而前進(jìn)的。大至拉丁美洲混合舞蹈文化,小至菲律賓舞蹈文化,無(wú)一不是復(fù)合體。”因此,拉丁舞與敦煌舞都是有典型特征的復(fù)合體,也就是“混合型”舞蹈種類。在其發(fā)展的過(guò)程中,也都不可避免地吸收著不同種類的舞蹈形態(tài),互相交織、兼容并蓄,而這種混合型的舞蹈種類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不斷的吸收性和強(qiáng)大的包容性,它們?cè)谖璧副倔w中可以容納有助于其完善和發(fā)展的舞蹈形態(tài)。拉丁舞最初被稱為拉美民間舞,是15世紀(jì)末殖民運(yùn)動(dòng)興起與多種文化大交融,15世紀(jì)新航路開(kāi)辟及16~19世紀(jì)長(zhǎng)達(dá)4個(gè)世紀(jì)的黑奴貿(mào)易使拉丁民間舞變成了印第安文化、歐洲文化、非洲文化三種文化混合的舞蹈。拉丁民間舞經(jīng)多元融合發(fā)展后,在不同地區(qū)以不同形式呈現(xiàn)出來(lái):如巴西激情澎湃的桑巴、北美活潑俏麗的恰恰、古巴柔情婀娜的倫巴、西班牙氣勢(shì)恢宏的斗牛舞以及美國(guó)西部詼諧跳躍的牛仔舞。拉丁舞的五個(gè)舞種風(fēng)格各異,每一個(gè)舞種在發(fā)展中又都吸收了各式各樣的民間舞成分,這種強(qiáng)大的包容性為中國(guó)風(fēng)格的融入奠定了基礎(chǔ)[3]。敦煌舞就是絲路文化交融的產(chǎn)物。公元前2世紀(jì),張騫出使西域,西域的文化藝術(shù)沿著古絲綢之路進(jìn)入中原,自此構(gòu)成了一種典型西域風(fēng)格的中國(guó)傳統(tǒng)樂(lè)舞。石窟壁畫(huà)上的“飛天”是中西結(jié)合的最完美的佛教樂(lè)舞形象。飛天舞姿大幅度地、十分性感的扭腰出髖、伸臂揚(yáng)掌、動(dòng)作舒展具濃朗的特點(diǎn)。”[4]佛教文化剛傳入中國(guó)時(shí),敦煌壁畫(huà)飛天舞姿因其典型的西域風(fēng)格,呈現(xiàn)出婀娜、豐腴的特點(diǎn),后來(lái)由于受中國(guó)傳統(tǒng)審美文化的影響,飛天舞姿也逐漸趨于寧?kù)o和諧、典雅內(nèi)斂的特征,但動(dòng)作上仍然保留著“扭腰出髖”的凸顯女性人體美的西域舞蹈特征。“東西方舞蹈藝術(shù)從表面上來(lái)看,它們的形態(tài)迥然不同,但從共時(shí)性來(lái)看,它們之間有著互相牽連的,扯不清的淵源關(guān)系。”[2]敦煌舞“飛天”形象融合了中西方舞蹈文化各自的典型特征,呈現(xiàn)出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點(diǎn),因此敦煌舞這種“混合型”舞蹈融合在體育舞蹈形式之上,也能找到與自己相同的部分基因,兼容并蓄,被中西方觀眾所接受[5]。
(三)人們對(duì)“飛天美”的客觀性認(rèn)同
東西方文明由于巨大的文化差異會(huì)滋生出不同的藝術(shù)形態(tài)及藝術(shù)形態(tài)的外化形式,但對(duì)不同的藝術(shù)形式及外在形態(tài)的內(nèi)在含義趨于一致的“事物”,即便在文化差異下,也會(huì)產(chǎn)生共同的體驗(yàn)。隆陰培曾在《舞蹈藝術(shù)概論》中指出:“不同時(shí)代的不同階級(jí)具有各不相同的審美意識(shí),這是普遍現(xiàn)象,但歷史上和現(xiàn)實(shí)生活中也有不少舞蹈,由于它們符合歷史變革的進(jìn)步意義或者反映了包括不同階級(jí)廣大群眾的共同愿望,符合廣大群眾的共同利益,其內(nèi)容具有一定的人民性,所以也能引起不同階級(jí)群眾的共同美感[6]。”此外,隆陰培還曾說(shuō),“由鮮明生動(dòng)的舞蹈語(yǔ)言、多樣統(tǒng)一的舞蹈結(jié)構(gòu)、精湛超絕的藝術(shù)技巧和新穎獨(dú)特的表現(xiàn)手法所構(gòu)成的舞蹈藝術(shù)的形式一種相對(duì)獨(dú)立的客觀存在,如果舞蹈家們能夠成功而恰當(dāng)?shù)剡\(yùn)用它們,就會(huì)突破時(shí)間和空間的限制,超出民族和國(guó)界的范圍,贏得全人類的共同喜愛(ài)[6]。”由此可見(jiàn),拉丁舞與敦煌舞這兩個(gè)舞種對(duì)于共同事物的詮釋雖有“形”的差異,但創(chuàng)作者依然可以將之貫通,探索到東西方意象符號(hào)的共通性,從而獲得了西方體育舞蹈愛(ài)好者對(duì)作品所傳遞的“飛天美”的客觀性認(rèn)同;另一方面也是因?yàn)槲璧竸?chuàng)編者對(duì)于兩種語(yǔ)匯的恰當(dāng)運(yùn)用,使得人們對(duì)作品的認(rèn)知超越了時(shí)空的界限和地域的范圍贏得了人們的共同喜愛(ài)[7]。
三、結(jié)語(yǔ)
綜上所述,《絲路·行》創(chuàng)編者是在對(duì)東西方舞蹈文化深刻了解的基礎(chǔ)上,選擇了恰當(dāng)?shù)奈璧副憩F(xiàn)形式和舞蹈創(chuàng)編技法,打破了兩種舞蹈文化的差異,實(shí)現(xiàn)了西方的體育舞蹈與東方的敦煌舞的“對(duì)話”,這是《絲路·行》創(chuàng)編成功并獲取認(rèn)同的關(guān)鍵。由此可見(jiàn),融入“中國(guó)敦煌舞元素”的體育舞蹈表演性作品《絲路·行》也必然會(huì)超越時(shí)空、種族、國(guó)家及地域的界限,使世界體育舞蹈愛(ài)好者產(chǎn)生一種“共同美感”的體驗(yàn),成為融合性體育舞蹈表演性作品的“經(jīng)典之作”。
參考文獻(xiàn)
[1]包蕊,崔敏.國(guó)際標(biāo)準(zhǔn)舞在我國(guó)發(fā)展的階段劃分[J].藝術(shù)科技,2018,31(02):89.
[2]金千秋.古絲綢之路樂(lè)舞文化交流史[D].北京:中國(guó)藝術(shù)研究院,2001.
[3]胥燕.拉丁舞的審美文化特征淺談[J].戲劇之家,2020(10):112.
[4]史敏.敦煌壁畫(huà)伎樂(lè)天舞蹈形象呈現(xiàn)研究––動(dòng)靜中的三十六姿[J].北京舞蹈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7(4):109.
[5]包蕊,崔敏.體育舞蹈本土化發(fā)展中文化融合的路徑研究:“藝術(shù)創(chuàng)新”抑或“文化混亂”[C].第十一屆全國(guó)體育科學(xué)大會(huì)論文摘要匯編.北京:中國(guó)體育科學(xué)學(xué)會(huì),2019:4200–4201.
[6]隆蔭培,徐爾充.舞蹈藝術(shù)概論[M].上海:上海音樂(lè)出版社,2009:163–174.
[7]包蕊.“武舞復(fù)蘇”的現(xiàn)象對(duì)武術(shù)國(guó)際化傳播的啟示[J].沈陽(yáng)體育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3,32(3):125–128.
作者:包蕊 崔敏 單位:沈陽(yáng)體育學(xué)院 濰坊理工學(xué)院
文檔上傳者
相關(guān)推薦
體育舞蹈 體育 體育教育 體育舞蹈論文 體育工作總結(jié) 體育營(yíng)銷(xiāo)論文 體育發(fā)展論文 體育碩士論文 體育實(shí)訓(xùn)總結(jié) 體育產(chǎn)業(yè)論文 紀(jì)律教育問(wèn)題 新時(shí)代教育價(jià)值觀
- 體育體育社團(tuán)
- 體育體育運(yùn)動(dòng)美
- 體育講話
- 體育思想
- 體育趨勢(shì)
- 傳統(tǒng)體育
- 學(xué)體育教育對(duì)終身體育思想的滲透
- 體育備課計(jì)劃
- 體育訓(xùn)練
- 體育局農(nóng)村體育教育半年總結(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