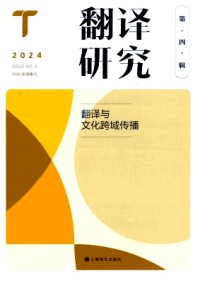翻譯學潛科學現(xiàn)狀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翻譯學潛科學現(xiàn)狀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chuàng)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內(nèi)容提要:本文論證如下的事實:中國傳統(tǒng)譯學理論及當代翻譯理論均尚處于潛科學階段。使中國翻譯理論成熟,從而變成顯科學須假以時日。
關(guān)鍵詞:傳統(tǒng)譯論;當代譯論
OnChineseTranslationTheories’Status-quoofPotentialScience
LIUYing-kai
(CollegeofArts,ShenzhenUniversity,Shenzhen518060,P.R.China)
Abstract:ThepresentpaperattemptstodwellontheactualfactthatbothtraditionalandcontemporaryChinesetranslationtheoriesareatthestageofpotentialscience.IttakestimetomakeChinesetheoryoftranslationmoreandmorematuresoastobecomeamanifestscience
Keywords:traditionaltranslationtheory;contemporarytranslationtheory
WolframWills認為翻譯學應(yīng)該是一門“認知性/闡釋性/聯(lián)想性的科學”(Wills,Wolfram,2001)。筆者認同翻譯學的科學觀,但是認為翻譯學尚未發(fā)展成為一門成熟的科學,而是處于發(fā)展的幼年期,是一門潛科學。這種定位十分重要,因為學科的現(xiàn)狀研究是所有學科的學科建設(shè)中一個重要內(nèi)容,翻譯學當然也不例外。對翻譯學的學科現(xiàn)狀進行定位,首先要克服認識上的若干誤區(qū)。
1.數(shù)量即效益。一種自覺或不自覺流露出的觀點認為:近些年來國內(nèi)共出
版了幾十部書,發(fā)表了幾千篇論文即是學科發(fā)展的明證。可是,正像有“泡沫經(jīng)濟”一樣,“泡沫學術(shù)”在翻譯理論界也在不斷泛起:不少專著和文章還在以增詞、減詞、反譯等為內(nèi)容、以感性體驗和經(jīng)驗歸納為特點的翻譯技巧之類的層次上蹀躞彳亍。在譯學理論研究不斷向縱深發(fā)展的二十一世紀,譯學著述如果不能在科學精神、學術(shù)思想、學科意識、理論視野和開放心態(tài)方面有若干新的亮色,那么,每年的學術(shù)成果清單即使再長再厚也好似經(jīng)濟方面“沒有發(fā)展的增長”,不能視為學科建設(shè)的進步和發(fā)展。要想把產(chǎn)值轉(zhuǎn)化成效益,就應(yīng)當不斷努力地尋找學科發(fā)展的新的生長點。
2.規(guī)模即效應(yīng)。一種觀點認為:譯界的研究范圍在不斷拓展。但是,我們
在承認這一事實的同時,應(yīng)當再深思一下:不少研究是否東鱗西爪,自亂途轍,其源在于學科發(fā)展方向不清;而另一方面,具體研究中的開鑿是否還極待進一步加深。例如對傳統(tǒng)譯論的研究,文章和專著均為數(shù)甚伙,但卻如揚自儉所言,“依然是語文學的研究,主要是考證加解釋,缺少理論的開拓和方法上的創(chuàng)新”。(揚自儉2000:5)。再以西方翻譯史的研究為例,現(xiàn)有專著還基本上是對西方主要國家翻譯活動本身進程及譯論家的觀點按歷史分期而做的歷時性記錄,缺少以史帶論或以論帶史的機鋒,未能超越學術(shù)史初期研究的通病,大體上還屬于資料整理歸檔的層次,即是說:較少以科學發(fā)展的一般形態(tài)為視角揭示西方譯事本身的分合變遷過程;較少對某個歷史時期國與國翻譯活動發(fā)展變化歷程以及翻譯理論的共時比較;較少從宏觀的把握上揭示翻譯學孕育和發(fā)展的內(nèi)在邏輯;較少涉及各個歷史分期間翻譯觀念和譯論研究方法的演變。當然作者篳路襤褸的開拓之功絲毫不能抹煞。
在超越了如上認識之后,讓我們站在高處,來檢閱一下翻譯學的潛科學現(xiàn)狀。
科學發(fā)展史表明:已得到確證、為世所公認的那些科學理論構(gòu)成的常規(guī)科學稱為顯科學,其特征為具有前后一致的術(shù)語體系;具有實證性(包括證實和證偽),即能接受實踐檢驗;具有邏輯體系,科學事實的真實性必須同時具有邏輯上與經(jīng)驗方面的有效性;具有抽象性,即從廣泛搜集材料開始然后進行從個別到一般的抽象在此基礎(chǔ)上可以歸納與演繹結(jié)合,分析與綜合并舉,將現(xiàn)象與屬性和本質(zhì)統(tǒng)一起來;具有預(yù)測性,能對尚未發(fā)生但受規(guī)律制約的事實作出預(yù)測;有明確的規(guī)定性,不能亦此亦彼;具有互恰性前后論斷互相支撐不能有相互矛盾的命題(徐煉等,1998;夏禹龍,1989)。那么,顯科學的前身,即處在孕育階段,不甚成熟的科學思想就可稱為“潛科學”(解恩澤,1987)。由于翻譯學尚未完全具有上述顯科學的應(yīng)具特征,因而只能定位為處在孕育階段的潛科學。
一,中國傳統(tǒng)譯論的潛科學現(xiàn)狀
潛科學是科學的幼年期。中國傳統(tǒng)譯論就科學發(fā)展的一般形態(tài)而論,即處于潛科學狀態(tài),中國傳統(tǒng)譯論的潛科學現(xiàn)狀表現(xiàn)在如下幾個方面。
1.缺少一以貫之的術(shù)語體系。
術(shù)語體系是一門成熟學科的重要參數(shù)。可是中國傳統(tǒng)譯論從其爛觴時期開始就呈現(xiàn)出原始的模糊性和易變性,缺少明確定型的界說,而且數(shù)千年無大改善。如《禮記.王制》中記載的表當代“譯人”這一說法就因“五方之民,言語不通”而形成“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譯”(羅新璋1983:1)其中“寄”,“象”、“狄”和“譯”的不同說法似乎成了中國譯論數(shù)千年來術(shù)語體系一大缺失的預(yù)兆和定讞。到了佛經(jīng)翻譯時代及近代,表示我們當代“原文文意”這深層含義的術(shù)語就有“本”(如“案本而傳”;“趣不乖本”)“大意”(如“雖得大意殊隔文體”);“實”(如“依實出華”);“文意”(如“善披文意”);“辭旨“(如”雖辭旨高簡,然其文猶隱”);“旨”(如“搜研本正,務(wù)存經(jīng)旨”);“意思“(如“意思獨斷,出語成章”)以及“義”(如“音雖則別,義則大同”)等等。中國傳統(tǒng)譯論之缺憾尤其表現(xiàn)在有些要表達的意思竟然通過非術(shù)語來表示。如玄奘的“五種,不翻”。這個“不翻”二字從術(shù)語學的角度看,違反“以名舉實”的名詞(詞組)性原則是無資格成為“術(shù)語”的。而這種非術(shù)語只能憑語境猜出,是指的“音譯”。不成熟的術(shù)語體系標示了中國譯論的潛科學地位。
2,未形成明確的的學科意識
中國傳統(tǒng)的譯論,無論是佛經(jīng)翻譯時期的“案本而傳”、“五失本”、“三不易”、“八備”和“十條”;“依實出華”;“從方言,趣不乖本”,還是近代的“信達雅”都是翻譯家的因事生論,并非出于作為一種科學的翻譯學的學科意識。本世紀50年代,董秋斯首先提出寫“中國翻譯學”的“大書”的建議(羅新璋,1984)。但是董秋斯本人的呼吁未引起太大注意。學科意識的真正覺醒,三十年以后才得以實現(xiàn)。因此董秋斯之后傅雷標舉的“神似”論,錢鐘書推出的“化境”說均難脫出有感而發(fā)的隨機評點的窠臼。所以迄今為止,我們還沒能產(chǎn)生一本自成體系的翻譯學論著。至于有學者說我國已形成了一個“自成體系的翻譯理論”,則不過是他把中國兩千多年來代表著共同歷史淵源的翻譯觀點的那些絲絲縷縷人為地編織到一起的一個系統(tǒng)而已。正因為傳統(tǒng)譯論缺少自覺的學科意識,中國迄今沒能構(gòu)建起翻譯學理論體系,這就是學科發(fā)展仍處于潛科學時期的一個重要標記。
3,未形成邏輯體系
傳統(tǒng)譯論屬于“經(jīng)驗知識形態(tài)”,它所依賴的思維方式是感性直覺,
側(cè)重于體驗。譯論的先哲們指導(dǎo)譯經(jīng)時著重啟發(fā),每每是因事指點,隨機接引。所以其特點是零章片語的語錄和注疏居多。它們雖然簡明扼要、語多精粹,卻不能伴以分門別類、綱維并舉的分析性。就其知識內(nèi)部而言,呈現(xiàn)著散點式的無序狀態(tài),形不成結(jié)構(gòu),因而就為其多義性和多變性的存在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就知識之間的關(guān)系而論,則又彼此缺乏邏輯聯(lián)系。這種知識內(nèi)部與外部均缺少邏輯之光照耀而形成的暗淡,與中國語法簡便、邏輯學(如《墨經(jīng)》中的有關(guān)部分)興起較遲,尚未形成規(guī)模就在“獨尊儒術(shù)”的喧囂聲中遽告中絕有關(guān)。而西方由于其語法復(fù)雜,如希臘語法中,動詞竟有三百種變化。因此西方從個體的自幼發(fā)展到整體的文化特征均得力于語法訓(xùn)練,因而以長于剖析為其優(yōu)點。(許思園,1997:33)其各個學科,包括翻譯理論均以其邏輯力量優(yōu)于中國。缺少邏輯聯(lián)系的譯論雖有雋語的簡明、凝練和精警(如信達雅三字訣何等言簡意賅!),卻如閃閃發(fā)光的一粒粒明珠,串不成串,無法形成體系。缺少邏輯聯(lián)系又是潛科學的一個特征。
二,中國當代譯論的潛科學現(xiàn)狀
1,對引進的西方譯論檢驗和改良尚嫌不夠
八十年代以來,西方譯論大規(guī)模地引進中國,為譯論研究人員帶來了全新的視角,隨之引發(fā)了新方法的嘗試和新領(lǐng)域的開拓。這是繼嚴復(fù)時代以來的又一場學術(shù)革命,其重大意義已經(jīng)顯示出來,而將繼續(xù)顯示下去。但對于這一引進過程,不少人大搖其頭,批評這是“趨新獵奇”、“標新立異”、“新術(shù)語堆積”……站在歷史的高度看,這些批評是不正確的。從本質(zhì)上講,這是某些學人缺少外向型的和前瞻性的理論視野、缺少海納百川的學術(shù)胸懷的表現(xiàn)。但是,我們也應(yīng)當看到這一引進潮中確實出現(xiàn)的不少問題和不良傾向。一是譯文質(zhì)量較低的問題較為普遍,典型的例子如李運興教授對穆雷《翻譯的語言學理論》漢譯本中諸如詞義和句法結(jié)構(gòu)的理解有誤、表達欠清晰及學術(shù)觀點未能準確傳達等四方面問題的分析(李運興,1995)。穆雷在譯論界較有名氣,對譯論理解應(yīng)高于一般譯者,推出的尚“不是一個合格的譯本”(李運興,1995),論者所謂譯論中不能準確傳譯西方學術(shù)觀點的問題的廣泛性于此可見一般。二是有人不是對外國譯論家進行建樹又見林與見林又見樹的科學剖析,從而把握住其思想體系。而是各取所需,片面摘引。例如,奈達的翻譯思想,越過其紛披的枝葉,其體系主干的本質(zhì)屬性當然是功能主義,這應(yīng)當是不爭的事實(Nida&Taber,1969:202)。但是有人卻片面征引奈達的如下論述“不考慮形式只求達意的譯文往往失去原作的風姿,味同嚼蠟”,來論證“奈達也是重視形式”的。這種見樹不見林的任意分割、任意取舍的學風無助于高屋見瓴地把握外國譯論家的翻譯思想的核心和本質(zhì)。這對于我們系統(tǒng)引進的大局是有害無利的。還有一種傾向是把外國環(huán)境中因特殊背景(傳教)而發(fā)展起來的奈達翻譯思想奉作我們的權(quán)威,出現(xiàn)了論者所謂“言必稱奈達”的局面,長期用來指導(dǎo)我們的實踐和理論;此長彼消,因而對其他已引進的外國譯論便減少了進行更深層次分析的注意力,同時相對忽略了對國外不同觀點的及時引進和攝取——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由許鈞主編的、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外國翻譯理論研究叢書,是一件功在譯界的大好事,它們滿足了人們希望更加全面了解外域譯論思想的饑渴之盼。這種缺欠中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外域譯論引進之后對其辯認、識別、驗證、取舍、改良和融合的工作還沒能有序和全面地展開。一段歷史時期內(nèi)引進工作中的這種畸輕畸重上表現(xiàn)出來的系統(tǒng)性全面性的缺乏及研究工作各方面表現(xiàn)出來的深入性的缺憾,都耽擱了翻譯學從潛科學向顯科學躍升的進程。
2.相對主義對譯論界的不良影響
相對主義片面夸大事物性質(zhì)的相對性,抹煞其確定的規(guī)定性,否認主次性,否認相對中有絕對,否認客觀的是非標準。這種相對主義在譯論界有微觀和宏觀的各種表現(xiàn)。
微觀的例子如“異化”和“歸化”的關(guān)系問題。常識告訴我們,“異化”和“歸化”在翻譯實踐中都不能不采用,沒有哪一種譯文是完全異化或完全歸化的,二者缺一即不成翻譯。但是翻譯觀念同任何別的觀念一樣,都“隨發(fā)展而異,與時代同新”。在我們已經(jīng)邁入21世紀,面臨著文化加速度(culturalacceleration)大幅提高,世界已成為地球村的今天,翻譯的“異化”已成為“異化和歸化”這對矛盾中的主要方面。因此在探討二者關(guān)系時,譯論界應(yīng)當旗幟鮮明地確立二者的主次關(guān)系。曖昧則不折不扣地意味著保守,就會影響世界文化的融合。筆者在一篇文章中談到,“‘盲人國里,獨眼為王’最初譯到漢語中,算不上有閃光之處,但至少有獨特之處,但這點獨特在時間的熨斗熨來熨去之后,早已變得熨貼自然,甚至有些陳腐了,可是直到1998年還有人在《中國翻譯》上著文,認為它不符合漢語習慣和表達方式,應(yīng)當用形象替換,譯成“山中無老虎,猴子成大王”。(劉英凱,1999:3)。問題的嚴重性在于,這種抱殘守闕并非孤立的個案,以其為特點的翻譯實踐和觀念帶有相當大的普遍性。而導(dǎo)致這種結(jié)果的深層原因就是在于翻譯觀念上不分次序的相對主義對譯論界的長期影響。其實,正如絕大多數(shù)國家經(jīng)濟中都是市場經(jīng)濟和計劃經(jīng)濟共存,但以市場經(jīng)濟為主一樣,在異化和歸化的關(guān)系中也應(yīng)當確認何者為主,何者為次。可是在我們譯論界,現(xiàn)在卻有一個相當時髦的觀點:在異化和歸化的關(guān)系上有一個“度”。每讀到這個“度”字,筆者就不免有個疑問:這個“度”如何界定?由誰來界定?“度”的界定有沒有操作性、程序性和可傳授性?如果這些都沒有,那么,它的可檢驗性何在?這豈不是又墜入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這類的空泛玄虛的不可知論的泥潭里去了嗎!
有些眼光銳利的學者早已正確地預(yù)見:“隨著兩種語言和文化的接觸和交流日益頻繁,異化的成份越來越多,這種趨勢肯定將會繼續(xù)發(fā)展。也許在將來,異化的譯文會占上風”。(郭建中,1999:6)既然如此,在我們的討論命題中為什么不敢態(tài)度鮮明地加進“規(guī)定性”和“主次性”呢。列寧曾尖銳指出:“把相對主義作為認識論的基礎(chǔ),就必然使自己不是陷入絕對懷疑論、不可知論和詭辯;就是陷入主觀主義。”(列寧1972)。從純學術(shù)的角度體味,這句話可以給譯論研究者以驚聳般的啟示,我們應(yīng)當從思維的慣性和定勢中解脫出來了!
相對主義的較為宏觀的表現(xiàn)則是在譯論研究中“中學”與“西學”的主次性問題上也有頗為明顯的曖昧傾向。目前在繼承和“引進”關(guān)系問題上,有如下幾種主張:一,以“中學”的繼承為主;二,“中學”和“西學”平行發(fā)展,不必交叉,三、將“中學”與“西學”融合。誠如許多學者及本文上文所言,“中學”——中國傳統(tǒng)譯論與華夏各文化分支一樣,具有“先天”的一些文化局限:以整體把握為特點,缺少分門別類的邏輯精細;以零章片語、概念模糊的經(jīng)驗知識形態(tài)為特點,未能形成完整的知識形態(tài)。這類獨具的特色與現(xiàn)代科學精神頗有距離。清末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已無功而返,那么,譯學上的在理論構(gòu)建上并未形成邏輯系統(tǒng)性的“中學”也將必然難于闖出局面;而且由于肖規(guī)曹隨,率由舊章,極易因循,難于通達,將使中國翻譯學的學科建設(shè)大大陷于落后狀態(tài)。第二種“中學”和“西學”平行發(fā)展論是最近一年內(nèi)有學者在論著序言中提出的。這一觀點的漏洞在于忽視了中國目前并非閉關(guān)鎖國的基本事實。在一個開放的社會里,傳統(tǒng)譯論的任何研究者不受“西學”——西方譯論的半點影響,而只埋頭于故紙,就能在其中創(chuàng)立出自外于任何別國的翻譯理論體系無疑是不可能的。研究者只要接觸了外國譯學理論,不知不覺中受它的影響,那么,他/她就會列入到“融合”派之中。而融合派——將“中學”與“西學”融合,即指:繼承我國傳統(tǒng)譯論的精華,融合吸收外來新理論使之發(fā)展,最終為中國提出具有現(xiàn)代化和國際化特征的理論。平心而論,這是中國譯論獲得突破的真正出路。但是,為了高效地達到這一目標,我們還應(yīng)考慮:在融合的過程中是以“中學”還是以“西學”為坐標?結(jié)論顯然是后者。但是不管誰提出這一主張,都會立即遭到某些學人的反對,甚至于有可能會被嗤之為:崇洋媚外!但是,我們一旦平靜下來,從情緒化的反應(yīng)中走出來,就會接受這一結(jié)論:第一、它是有事實為依據(jù)的。打開中國的每一本學術(shù)期刊,考察一下翻譯研究的論文,它們會有幾篇是以傳統(tǒng)譯論為依托展開論述的呢?而其大部分都是對外國譯論的介紹、詮釋、研究、以外國譯論為理論依據(jù)對翻譯現(xiàn)象和譯學基本理論的探討等等。可以說,為譯論研究的大潮推波助瀾的主要是西方的,而非中國傳統(tǒng)的譯論;而且,能夠鉤深致遠,探賾尋隱的那些高質(zhì)量論文離開西方譯論的理論依托是無法想象的。這種傾向甚至走過了頭!一些并無新意的論文也要把未經(jīng)咀嚼消化的新術(shù)語、新學說加進,作為點綴。這一不正常的現(xiàn)象,從反面證明了“西學”譯論在人們心目中不可動搖的地位。這些都是勝于任何雄辯的硬梆梆的事實。第二,西方譯論比起中國傳統(tǒng)譯論,在淵源和現(xiàn)狀上都更具科學思維和理論意識,更是論者們一而再二而三研究和論述過的課題。然而,在前所未有的學術(shù)民主的寬松氣氛下,以西方譯論為坐標建構(gòu)中國現(xiàn)代翻譯學體系的思路,并未成為人人心中所想,其根源之一就是相對主義長期對人們浸染的結(jié)果。這當然不能不說是中國翻譯學向前邁進的一大障礙。
3.翻譯學科意識建立的艱難
直到今天,仍有一部分學者堅持認為:翻譯活動中兩種不同語言的符號之間不存在共同的規(guī)律,雙語轉(zhuǎn)換沒有轉(zhuǎn)換規(guī)律可供遵循,因而翻譯似乎只能是“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受規(guī)律支配,因此也就不能成為科學(潛科學也談不上---根本不是科學)。他們把屬于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潛科學范疇的翻譯學同自然科學等同起來,認為翻譯學只有像自然科學及工程技術(shù)那樣立竿見影地對于社會產(chǎn)生顯性功能,才可能稱為科學。有的學者則更堅持說:“解決翻譯難點求助于翻譯理論無異于緣木求魚”(張經(jīng)浩,1996)。很顯然,這類學者要求翻譯學必須對翻譯活動產(chǎn)生解決“難點”的“速效”。可是他們沒有意識到:非自然科學的學科產(chǎn)生的社會作用具有滲透性和遲效性。從學科的宏觀角度講,任何學科都需要經(jīng)歷從模糊到清晰,從無序到系統(tǒng)化的過程。科學精神對這一過程不斷滲透,最終會實現(xiàn)翻譯學體系的建立。從翻譯學的社會功能角度講,同一切非自然科學的學科一樣,其功能具有“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潛移默化特點,其滲透性,遲效性決定了它的社會效應(yīng)不可能是速成的。學者們把這一現(xiàn)象稱為功能理論的“非直接還原性”:即指由于其形而上的性質(zhì)及其高度集中、抽象、典型化的特征,不能把理論概念看作與現(xiàn)實直接等同的東西,……迫使現(xiàn)實與理論概念相吻合……(徐煉等,1998)。因此期望翻開翻譯學的著作就產(chǎn)生立竿見影的解決難題效應(yīng)的觀點是違反人文及社會科學的一般常識的。
這派學者認為,理論必須立即產(chǎn)生實用價值,否則就把它說成是空疏無用的東西。張經(jīng)浩教授就直白地說出“任何理論,離開實用價值便沒有存在的必要”(P9)。這種以理論為筌蹄的功利主義思想是我國數(shù)千年來工具理性浸染的結(jié)果。
中國傳統(tǒng)文化確實有一種功用至上的傾向(雖然也有與之沖突的另一側(cè)面:經(jīng)書至上,仁義至上,降至現(xiàn)代演繹出不講效用的教條主義)。所謂“六經(jīng)注我”、“經(jīng)世致用”都強調(diào)了功用至上的價值取向。學術(shù)研究的目的不是學術(shù)發(fā)展,而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培養(yǎng)的目標不是探索型的思想家和理論家,而是“經(jīng)邦濟世”者。這與古希臘的純理論探索精神以及由此引發(fā)的學術(shù)繁榮大異其趣。在中國,就連老莊的出世思想居然也可刪削成“修仙得道”的致用工具。“書中自有黃金屋”及“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實用意識如此地氤氳在讀書人的靈魂中,以致唐朝開科取仕以來,讀書不是為了致用--做官的讀書人簡直可說是寥若晨星!
許思園先生認為:古希臘人與近代歐洲人十分重視純知識活動。而在中國,……春秋以前,禮,樂,射,御,書,騎為貴族子弟學習,均離不開實用……戰(zhàn)國中期學術(shù)極盛,出現(xiàn)莊周,惠施,公孫龍,鄒衍,墨子等析解知識、探究邏輯的愛智之士,然而純知識活動方開其端而毀謗隨至,其罪狀一言蔽之為不實用,而儒生與農(nóng)民一脈相承,均敵視純知識活動。中國歷代史家推崇者依次為政治家、道德家和文學家,而科學家則被流于“術(shù)士“之列。至于科學,國人對應(yīng)用科學還稍微重視,理論科學幾乎無人問津。(許思園1997)
在植根于農(nóng)業(yè)社會的中國實用主義者心目中,純粹理論知識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因此一直受到鄙視。直到當代,在我們這個十分務(wù)實的民族中杰出的政治家也都把“行”放到“知”的前面。王元化因此認為大多數(shù)人都強調(diào)實踐,不重視理論。“實踐出真知”因一再濫用而變成排斥理論的實用主義套話。”(王元化1996:43)。可以說,致用、實用的價值觀已滲透在不少中國人的血脈中,以張經(jīng)浩教授為代表的這派學者認為“理論離開實用價值就沒有存在的必要”正是實用和功利的這一民族“集體無意識”的自然流露和集中體現(xiàn)。問題恰在于:這種實用致用的價值觀已強烈地體現(xiàn)在翻譯理論界。這就使得翻譯理論界理論意識、科學精神和開放心態(tài)都難以形成大的氣候。國內(nèi)翻譯實踐上的一流學者和其他有成就的譯者中不乏張經(jīng)浩教授的同道和支持者。他們不相信翻譯理論能解決翻譯難點卻又在翻譯實踐中成績卓著。這就很大程度地抵銷了翻譯學研究者在譯學學科建設(shè)上的矻矻窮年的努力。一個學科社會承認度不夠正是鑒定科學地位不高的重要參數(shù)。
4,學科建設(shè)中尚存在違反“互恰性“原則的不和諧因素。
互恰性原則是指科學理論的前后論斷在邏輯上必須一以貫之、互相支撐。表現(xiàn)在體系的綱與目上的各個概念和原理之間呈現(xiàn)出和諧和互補的關(guān)系。它不該存在、甚至不允許推導(dǎo)出矛盾的命題。命題如有變化,那只能表現(xiàn)在認識上的周密化、完善化和深化,而不是命題真值的更改。
可是對中國譯學學科建設(shè)起過重大影響的奈達以及首批呼吁“必須建立翻譯學”的譚載喜教授的翻譯觀就違反了命題的互恰性原則。吳義誠曾經(jīng)這樣評價:被西方尊為現(xiàn)代翻譯開山鼻祖的奈達70年代以前一直持翻譯的科學觀,而70年代以后又持翻譯的藝術(shù)觀。并且強調(diào)譯者才能的天賦性。無獨有偶,譯介西譯論成績斐然的譚載喜先生,80年代認為翻譯不是科學,只能是藝術(shù)或技術(shù);而90年代卻又贊同“翻譯是一門科學”的觀點。……大幅的搖擺使我們無所適從。’’(吳義誠1997.5)。還應(yīng)補充的是:1988年譚教授又提出:“翻譯不是科學,翻譯學才是科學”(譚載喜1988:2).正如郭建中正確指出的那樣:“因為更換了辯論的命題,就更難為對方接受”(郭建中1999.6)。程度上更有過之的類似批評還可以在李田心(《福建外語》2001.1)的論文中找到。如果說李先生因為持“不存在所謂的翻譯(科)學”觀點與“必須建立翻譯學”的呼吁必然發(fā)生牴牾,其觀點容或有些許不盡客觀之處,而一向以思考深入、持論平和而引起譯界密切關(guān)注的吳義誠以及對譯論思深力遒且又成績卓著的郭建中的評論就不能不對翻譯學學科建設(shè)的現(xiàn)狀引起深層次的思索:只要持心開意豁、平正通達的態(tài)度,就不能不承認,譚載喜教授無論在西方譯論的引進,還是對譯學學科建設(shè)的推動上都是走在頭排的擎旗者;那么,他的觀點的“大幅搖擺”及由次引起的非正面評說則尤易于使人想到:對翻譯學推動最力者之一自己對翻譯本質(zhì)的基本問題的認識尚處在動搖之中,人們因而難免會對翻譯學的建立引起疑問,甚至據(jù)此提出反證。在此情況下,加大譯學理論的清晰度應(yīng)成為譯論研究者未來工作的重頭戲:在翻譯學的定義、功用、定位等基本理論問題的論述上,我們要努力把不確定性和不穩(wěn)定性減少到最低程度。而自恰性原則上存在的如上問題也是學科地位尚難于躍升到顯科學的另一明證。
5,學科建設(shè)中尚存在著違反可檢驗性原則的不和諧因素
是否符合可檢驗性原則是學科成熟度的另一重要參數(shù)。按照這一原則的要求,一種理論不應(yīng)該是毫無經(jīng)驗內(nèi)容的空論。以此觀點對照:我們譯界中幾位有重大影響和貢獻的可敬學者如劉宓慶教授為翻譯理論搭起的宏大框架就存在著是否能夠過得去可檢驗性這一關(guān)口的問題。這一現(xiàn)象促發(fā)我們研究一下科學的研究方法。
19-20世紀之交,嚴復(fù)等著力引進西學的人出于歷史緊迫感和高度的理論自覺,向國人介紹來源于西方的嚴于實證的科學方法。嚴復(fù)自己就認為:西方科學的昌明主要根源于其“實測內(nèi)籀之學”。這里,“實測”的當代意義即“觀察與實驗”,而“內(nèi)籀”則指“歸納”。他認為,通過內(nèi)籀概括出一般的“公例”(一般原理),再將公例放到實驗過程中加以驗證,使之成為定理。(引自揚國榮1999)
這種從材料的歸納中抽繹出原則的方法是符合從感性到理性這一認識論的一般規(guī)律的。按此方法,研究者必須從廣泛地蒐集材料開始,然后分析加工,進行從個別到一般的抽象,最后提出觀點或理論,這就是從歸納到演繹的過程。
中國傳統(tǒng)思維重演繹而輕歸納,往往從主觀出發(fā)求證推理。胡適所述“大膽的假設(shè),小心的求證”就走的就是同這種“從歸納到演繹”相反的路徑。(當然,我們并無意否認個別情況下演繹法的能動作用,愛因斯坦發(fā)現(xiàn)相對論就主要是訴諸科學家大膽假設(shè)的結(jié)果)。王元化在總結(jié)兩種不同治學之路的利弊時指出,由于湯用彤‘處處注意證據(jù),無證之說雖有理亦不敢用’,所以其“《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及《魏晉玄學論稿》等書迄今仍被人認真閱讀,并往往加以征引。而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之類,已被后出的著作所取代了”。(王元化1994)
以上分析應(yīng)使譯論研究者從中得到啟示。在學科知識纖維形成的概念范疇和知識單元尚未真正成熟之前,過早地規(guī)劃出宏觀體系,那么,其綱與綱之間,目與目之間,綱與目之間是否能形成有機網(wǎng)絡(luò),就不能不讓人產(chǎn)生疑問。有學者對劉宓慶教授所設(shè)計體系的內(nèi)部和外部系統(tǒng)批評時所指出的“分類和歸類“的諸問題(林璋1999:6)其實質(zhì)就指向這種網(wǎng)絡(luò)有機性上的缺陷。
這里還應(yīng)指出,因求大求全搭起過大的框架,而又不伴以有強力支撐功能的事實憑據(jù)以及客觀可行性和解釋力的論述,這樣一來,就缺少證實或證偽的功能,缺少可檢驗性,因而也就難于有足夠的普遍有效性,隨之就令框架設(shè)計者不期而然地給人以過于形而上的玄虛之感,有可能使人生疑,乃至生厭,從而又有可能把已走上新路的人推回到老路上去。
宏觀體系之外,作為其綱與目的若干分支體系也存在著不同程度地違反可檢驗性原則的問題。這當然也是翻譯學尚處于不成熟階段,因而不能稱為顯科學的又一明證者。
結(jié)語
中國翻譯學的潛科學現(xiàn)狀還有別種表現(xiàn),以上不過是其中犖犖大者。改善如上缺陷的過程,即是其不斷成熟的過程。但是構(gòu)筑常規(guī)科學——顯科學的科學形態(tài)絕非一朝一夕之功,心懷全局,力爭做好每件學術(shù)產(chǎn)品的深加工工作似應(yīng)成為每位譯論工作者的不斷追求。為達此目的,努力適應(yīng)當下綜合研究的時代要求,善于利用相鄰學科的科研成果便勢在必行。有些學科的研究已成績斐然。只要善于學習,轉(zhuǎn)益多師,我們就可收到“水漲船高”的效益。這方面,國外的學科共同體的經(jīng)驗可供我們借鑒。跨學科的研究和跨地區(qū)的研究機制都似應(yīng)盡早建立起來,人們期望中國譯協(xié)等單位起更多的組織和協(xié)同作用。在上下一心的共同努力下,中國翻譯學早日完成由潛科學向具備國際性和現(xiàn)代性的顯科學的躍升自然不會是一場迷夢!
參考文獻
1.郭建中.中國翻譯界十年(1987-1997):回顧與展望[J].外國語,1999.(6):58
2.李運興.《試評翻譯的語言學理論》[J].中國翻譯,1995:(3)
3.列寧.列寧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36
4.林璋.論翻譯學的基礎(chǔ)研究[J].外國語,1999(6):64-65
5.劉英凱.信息時代翻譯中“陌生化”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J].外語研究,1999.(3):51
6.羅新璋.翻譯論集[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4.1
7.Nida,E.A.&C.R.Taber.TheTheoryandPracticeofTranslation.Leidon:E.J.Brill,1969:202
8.譚載喜.翻譯學必須重視中西譯論比較研究(J).中國翻譯1998(5):22-27
9.王元化.思辯隨筆[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43/33
10.Wilss,Wolfram.TheScienceofTranslation.Shanghai: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2001:13
11.吳義誠.關(guān)于翻譯學論爭的思考.[J]外國語,1997.(5):66-73
12.夏禹龍.《社會科學學》[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216-220
13.解恩澤.潛科學導(dǎo)論[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7:1
14.徐煉等.人文科學導(dǎo)論[M].長沙:中南工業(yè)大學出版社,1998:32-33;78
15.許思園.中西文化回眸[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58/34
16.揚國榮.科學的形上之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43
17.揚自儉.對譯學建設(shè)中幾個問題的新認識[J].中國翻譯,2000.(5):6
18.張經(jīng)浩.譯論[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8;9
文檔上傳者
相關(guān)推薦
相關(guān)期刊
- 翻譯論文
- 翻譯實踐開題報告
- 翻譯專業(yè)的實習報告
- 翻譯文學論文
- 翻譯實習工作計劃
- 翻譯英語畢業(yè)論文
- 翻譯美學研究綜述
- 翻譯文學
- 翻譯軟件
- 翻譯專業(yè)實踐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