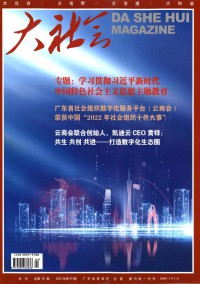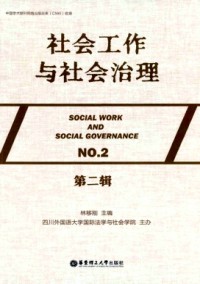社會發展觀和科學發展觀的討論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社會發展觀和科學發展觀的討論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一、農業文明與自然主義發展觀
人們深受此觀念的影響,認為所謂的社會發展也必然是循環、輪回的,受此觀念支配的人們自然把歷史上曾出現的某時段視為定可再求的理想,而不認為未來必定越來越好。循環、輪回也意味著一種不可抗拒的命運,一種也許只有直覺才能把握的內在力量支配著的命運。最后,“自然主義發展觀”強調社會的發展應是“天人合一”甚至是“順天”的。它強調在社會的發展過程中人必須尊重最高本體的運行規律,做到天人和諧,這在中國古代的思想中尤其明顯,即便是在西方的社會發展理論中,也曾多次出現過“大一統”的學說(其主要代表便是斯多葛學派)。大一統的前提是人人皆為自然之子,都秉有一份自然本性。人是自然這個大宇宙中的小宇宙,是大宇宙神圣火焰飛濺出來的一朵火花。這些理論都崇尚自然法則,承認自然的客觀性及其發展變化,并把它引入發展理論。這樣一來,“自然主義發展觀”使人們在發展生產的過程中樹立了樸素的生態意識,對自然也常常是倍加呵護。
二、傳統工業文明與物本主義發展觀
自然主義發展觀所引發的問題幾乎微弱到可視而不見,從而導致人類在那個階段缺乏對發展問題進行認真嚴肅思考,直到工業文明開始之后,發展觀問題才真正提上議事日程。由農業經濟時代轉變為工業經濟時代,是人類社會歷史長河中的一次偉大的變革。在這個階段,發展主要體現在對“物”的關注上。早在20世紀20至40年代,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學派之一的法蘭克福學派就提出了不同于“農業文明觀”的“工業文明觀”,他們主張應當以工業產品的量的增長作為衡量是否發展的唯一標準。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法蘭克福學派的觀點被理論化與邏輯化,并得以迅速傳播且得到普適性認可。美國社會學家塔爾科特•帕森斯認為,“經濟增長”作為衡量社會發展的指針性尺度并非肇始于法蘭克福學派鼎盛時期,工業革命較早的英國最先以此作為價值尺度,隨之18世紀的法國、19世紀的美國無一不步其后塵;發達國家走過的軌跡和由此取得的成就,似乎使人們達成了一種“工業文明共識”,只要經濟發展,其他一切錯綜復雜的社會問題就都會順勢得以解決;再次是二戰后新獨立的民族國家,基于追趕的壓力,迫切希望國力強大,并且普遍性認為“經濟決定政治”,因而也把發展的核心等同于經濟發展。由此可以看出,工業文明時代的發展觀是一種經濟主義發展觀,同時也是“物本主義”的發展觀。這種“以物為本”發展模式的主要表征為:一是在眾多社會子系統中,經濟子系統的增長在整個社會大系統中處于不可動搖的基礎性地位,高投入、高產量、高消費是其主要特質,過度放大經濟在整個社會發展理論體系中的作用。二是這種發展觀把第二產業取代第一產業與工業現代化程度作為社會是否發展的指示器,社會發展的基本目標是國民生產總值是否增加和企業經濟利潤是否增長,人的主體性、物質文化與人文文化的協調、社會公平等這些問題在整個社會發展系統中處于邊緣化的地位。三是這種發展觀把人看作是無論在本體論或認識論層面相對于自然界都具有絕對優先的地位,這種發展觀所秉持的自然哲學是:自然是無“內在價值”的,它只具備工具性價值,自然作為人的目的性生存,可被人類粗暴簡單地征服與利用、無償掠奪與宰割。由于“物本主義”發展觀把發展著眼于經濟的增長與擴張上,因此,這種發展觀實際上是以GDP為核心來進行構建的。不是說“科學的”發展觀不重視GDP,問題是在“物本主義”發展觀視域下的GDP考評本身也是存在先天缺陷的。在傳統GDP那里,“好”的與“壞”的GDP不問是非的全部統計在國民財富之中,無法準確看到實實在在的真正推進社會與人進步的GDP數據;在傳統GDP那里,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是不證自明、為我而“客觀存在”、“無需付費”的財富,資源的耗竭與生態的退化不但沒有從GDP報表中體現出來,而且因“生態補償”等方案的實施擴大了GDP數字;在傳統GDP那里,看得見的、能進行價格化或貨幣化的勞務得到了統計,而某些對社會或許有更大貢獻的勞務或服務卻因為無法量化被摒除在GDP統計之外。因此,傳統GDP無法真正反映生態成本、社會成本,無法反映經濟發展方式以及經濟增長的效率、效益和質量,無法反映經濟發展的科技貢獻率,無法反映社會財富的總積累,無法衡量社會分配和社會公正,無法反映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人文發展、生態發展的匹配程度,相反卻助長了一些部門和地區為追求高數量的GDP而不惜破壞環境、耗竭資源、漠視社會公平與公正的行為。相對于農業社會自然主義發展觀,工業文明時代以來的大部分國家秉持的都是以物質財富與產品數量增加、拉抬消費情勢為目標的物本主義發展觀。在這里,發展等同于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又被短視地歸結為經濟增長。這種發展觀導致出現了諸如分配不平等、道德倫理危機、生態危機全面爆發等問題,使人們感覺到“經濟發展了,我們的幸福指數卻下降了”,“經濟增長了,我們賴以生存的自然生態環境卻每況愈下了”,等等。我們并不是否認經濟發展、物質生產在整個社會發展體系中的基礎性地位,馬克思指出:“最文明的民族也同最不發達的未開化的民族一樣,必須先保證自己有食物,然后才能去照顧其他事情。”“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因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為基礎。”因此,傳統發展觀在某一特定時空階段具有某種歷史的“必然性”與“合理性”。但這并不意味著這種“合理性”是可持續的,因為人類社會的終極價值取向并不是物質本身,而是人、社會與自然的全面協調發展。而物本主義發展觀把人的價值異化為物的價值,把一切社會關系歸結為物質性關系,把“物”當作決定人的命運的終極因素,發展的根本動力反而是作為手段的“物”。人成了手段而不是目的,這是這種發展觀的致命性缺陷。
三、發展觀的新革命:
從可持續發展觀到科學發展觀由此可見,GDP至上主義的發展觀的一個致命的缺陷在于,它對于如何快速實現物質增長與經濟的關注遠遠超過“為了什么、為了誰而發展”和“什么方式的發展才是真正好的發展”。如何在發展觀的問題上實現“事實”與“價值”的有機整合,成為發展理論迫在眉睫需要解決的問題。20世紀60年代以來,一些西方學者開始對傳統的發展觀進行反思,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綜合發展觀”和“以人為中心”的社會發展觀。美國學者丹尼斯•古雷特提出要重新界定“發展”,要將倫理因子嵌入發展理論。他在加入發展倫理學因素后,重新提出了發展的三個核心價值:生存、自尊與自由。在他看來,那種以增加人類痛苦和忽視人類長遠未來為代價的發展實際上是“反發展”,它與人類發展的價值本質背道而馳。美國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認為發展應包含的五大基本向度是:增長、公平、民主、穩定、自主。學者們對傳統發展的反思,在學理上催促了“可持續發展”概念的提出。針對工業時代人類面臨的一系列經濟、社會、環境問題,特別是人類社會造成的嚴重環境污染和廣泛的生態破壞以及它們之間關系的失衡,布倫特夫人首次提出“可持續發展”概念,即發展應該“滿足當代人的要求,又不損害子孫后代滿足其需求能力的發展”,這是關于人、社會、自然和諧發展的一種主張,是人類走出生態危機的一種理性選擇。聯合國發展計劃署在它發表的《1996年人類發展報告》中曾指出過五種“不可持續發展”的情況:一是無工作增長(joblessgrowth),即經濟增長并未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二是無聲增長(voicelessgrowth),即經濟增長并未伴隨著政治參與和民主的擴大;三是無情增長(ruthlessgrowth),即經濟增長的好處大部分落入了富人手中,貧富分化加劇;四是無根增長(rootlessgrowth),即市場化、全球化導致了本土文化的危機以及民族沖突的發生;五是無未來增長(futurelessgrowth),即經濟增長破壞了生態環境。除第五種“增長”外,前述四種“增長”均與“人態環境”的惡化有關。相對于傳統的“以物為本”發展觀,可持續發展觀建基于人類社會的整體價值和長遠價值,立足于“人—社會—自然”系統的內在聯系反思發展問題,強調發展的代際性與持續性,在價值哲學層面上進一步豐富了發展的實質與內涵,從時間維度上看,是人類發展社會價值取向軌道變遷。有必要指出是,可持續發展觀確實針鋒相對地對“物本主義”發展觀所展現的一系列問題做出了戰術層面的回應,從發展的“不可持續”衍變為發展的“可持續”,因而它尤其注重“社會系統—自然系統”的吻合與對接。但是,發展的終極價值是什么這一戰略層面的問題依舊沒有得到很好的解答。從這個角度而言,歷史地看,雖然可持續發展觀較之“物本主義”發展觀,毫無疑問是一種嶄新的進步,但兩者都是在“就發展論發展”,缺乏對發展的形而上的終極價值思考,“實然”與“應然”的整合問題仍然懸而未決。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是對傳統發展觀與可持續發展觀理論上的不足的理性回應。科學發展觀是在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上正式提出來的。它的基本內涵概括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相對于已有的發展理論,它的理論創新之處在于,提出了“以人為本”作為發展的價值歸宿。這樣,它就不僅回答了可持續發展觀的“怎樣發展才是好的發展”這一手段性與技術性問題,而且它還堅定地回答了可持續發展觀遮蔽掉的“為了什么與為了誰而發展”的這一價值性與戰略性問題。它深刻地揭示出,人的本質是社會性的,人文、人性和價值才是其真正的精髓。發展的結果,應該是在人的“物質家園”變得極其豐富的同時,人的“精神家園”不會越來越荒蕪;發展的價值,光有物質維度的全面提高是遠遠不夠的,更重要的是“人的精神”“人的價值”與“人與自然的和諧”的全面提升。基于此,我們也把科學發展觀稱為“人本主義”的發展觀。盡管“以物為本”的發展觀仍在繼續影響著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但“以人為本”的發展觀不僅是人類未來發展的正確方向,而且也符合當今時代的潮流。科學發展觀是對人類發展史上經濟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的理論表達。它吸納了發展哲學理論研究與世界經濟社會發展實踐經驗的優秀成果,也是中國共產黨人長期執政經驗的科學總結。在這里,科學發展觀中的“科學”并非一般意義上的科學,而是意味著在發展問題上的主觀與客觀的統一、合規律性與和目的性的統一、真理與價值的統一、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即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把握其固有的內在規律性,把它作為行動的價值指針。從這個意義上說,科學發展觀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實事求是”在社會發展領域中的具體表達方式。如果把科學發展觀本質上理解為一種社會發展層面的價值觀,那么,科學發展觀是高舉了價值理性的大旗,在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之間添加了張力因素,避免了工具理性的肆意橫行。科學發展觀追求的“以人為本”,體現了價值理性至上的長遠與終極關懷原則,在具體實踐層面上,科學發展觀運用基于價值理性之上的工具理性,追求“經濟發展—社會發展—人文發展—生態發展”內在協調與統一,以及“物質文明—社會文明—精神文明—生態文明”的深度吻合與匹配。其次,“公平與效率”的問題也納入了科學發展觀的理論視野。科學發展觀批判了“效率至上”原則。在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同時關注諸如公平與正義、民生、自然生態環境等一系列不僅僅是從“效率”維度可以解決的問題。在思維方式上,科學發展觀反對還原主義或過度的分析主義,強調整體主義思維方式。在這里,集體邏輯與整體邏輯遠遠勝過個人邏輯,提倡集體主義或整體主義。因而它主張發展不是為了某個人或某個利益集團價值的實現,它強調的是“個體社會”相協調、“個體利益整體利益”深度統一性。基于此,可以理解為科學發展觀的意義在于用價值理性的張揚抗衡了工具理性的無原則性的膨脹,用全面發展抗衡了片面發展,用經濟、社會、人文與生態的協調發展抗衡了“發展等于經濟增長”,從而防止了發展中出現價值偏離。
作者:傅如良張豐盛李進兵單位:長沙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文檔上傳者
- 主導社會服務社會
- 社會政策
- 社會政策
- 社會公正社會主義遺產和社會民主主義
- 社會主義現象和社會主義本質
- 和諧社會與社會學
- 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失誤
- 社會公正和社會穩定
- 社會主義社會矛盾
- 和諧社會增強社會活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