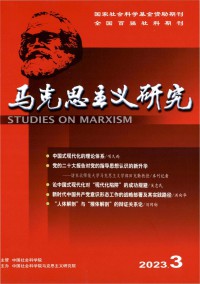馬克思主義現代性構建主義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馬克思主義現代性構建主義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現代性在不同的國家與民族有不同的實現方式。現代性在中國的生成與建構,是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地聯系在一起的。中國現代性的建構,歷史地確定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起點、任務與方向。因此,有必要認真清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與中國現代性建構的內在關聯。一、中國通過馬克思主義確立并獲得現代性的資格與身份中國現代性的建構并不是設定好的規劃,而是首先需要爭取權利。正是為了爭取這一權,20世紀前期,中國的一批精英,在眾多西方思潮中,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并走上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與此同時也開始了現代性的建構歷程。中國為什么要引進并實踐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現代化的境遇以及馬克思主義在西方世界以及整個現代人類文明進程中的重大影響有關。從外部境況看,中國是在西方強勢的現代化背景下表達其現代化訴求的,并且,西式的現代化從本質上否定了中國現代化的內生性與自主性,也否定了中國獲得現代性身份的可能性。外部條件已不允許中國以同一的方式參與全球性的資本主義運動,而近代西方非馬克思主義思潮,不僅從理論上、也從利益上拒斥和否定中國現代化。從內部境況看,以民族資產階級為主體,只能展開一種不徹底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更無法擺脫依附性的和弱勢的民族地位,中國的民族解放與獨立道路,必須要解放和發揮大多數社會中下階級的主體性與創造性。而且,在近代中國,基于自身的弱勢處境以及對自身文化傳統的信心不足,中國已無法內生性地開出一種堪與西式現代化相抗衡、進而能夠積極地影響全球現代化浪潮的思想文化資源。歷史表明,中國現代化的思想資源,不能純粹源自于西方,但又要求具有西方形式;不能直接源自于自身的文化傳統,卻又要充分考慮到文化傳統及其現代轉換的內在要求。這正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背景。馬克思高度肯定了資本主義所創造的歷史成就,并認為資本主義帶來了現代性的世界圖景:“一切固定的僵化的關系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系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東西都被褻瀆了。”與西方學者總是把現代性與資本主義制度捆綁在一起不同,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促進了現代性的歷史形成,但現代性本身的拓展和完善卻要超越和揚棄資本主義。在西方社會已經建構起一個相對穩定的資本主義秩序時,馬克思斷定資本主義必然走向終結,代之而起的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只是為現代社會積累了豐富的物質財富,但在政治制度與精神文明方面反倒構成了現代文明的障礙,因此,必須變革資本主義政治制度,批判其消極頹廢的精神文明狀況,創建新的政治制度與精神文化體系。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之間,存在著一種斷裂性的歷史轉折,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主體將通過反叛和革命促成這一轉折。而且,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轉變,實際上也是“西方化”的終結、以及歷史由區域歷史向世界歷史時代的轉變。當黑格爾等哲學家把現代性與西方化等同起來并看成是歷史的完成時,在馬克思看來,真正的歷史尚未開始,因為真正的歷史必然是向包括非西方在內的整個人類開放的,現代性也要歷史地表達為人類性。可見,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內在地反叛和超越西方近代思想、蘊含著非西方價值與關懷、并直接指向人類共同未來的現當代思想文化。也正是其面向時代的開放性與深刻的人類性,使得馬克思主義成為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社會獲得現代性身份的思想武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接著”馬克思思想的開放性“往下說”的。的確,按照馬克思本人的觀點,社會主義應當首先在西方發達國家實現,因為西方發達國家才具有使西方歷史地轉變為社會主義的條件。這看起來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限制,但馬克思對西方世界政治與文化結構的否定性批判,使得中國的知識界與思想界有理由放棄對西方資本主義的模仿,晚年馬克思對俄國能否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問題的高度關注,也激起了東方馬克思主義的想象。蘇聯十月革命的成功,直接奠定了關于馬克思主義的新的理解:總體上落后的國家,完全可以通過首先取得政治權利,然后開展現代化建設。這也正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接口,正如所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正是在這樣一個歷史背景下,中國開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探索,并最終取得了政治的合法性,從而確立起中國現代性的資格與身份。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使中國實現了兩大啟蒙任務就個體的群體性啟蒙而言,中國文化傳統歷來具有群體觀念并強調高度的群體整合性,但這種群體觀念一般說來還是消解個體自我意識、并以君王觀念為軸心的籠統的群體觀念,具體整合方式也是抽掉了個人性的“集體”主義,在這種群體觀念及整合方式中,不僅個性得不到保證,而且團隊、族性、社會以及人類,都難以得到一種反思性的理解與自覺。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視野內,個人的群體性啟蒙不同于資產階級啟蒙,資產階級啟蒙強調的是個人主義,這種個人主義不僅難以為中國文化傳統接受,更難以為正處于族群認同焦慮的近現代中國人所接受,但是,個人面對群體的自覺或者群體對個人的責任又需要得到體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所回答的正是個體價值與群體價值的現實統一:個人首先認同于其所隸屬于的那個階級,并通過階級意識體現其個人意志,個人不再只是以前的籠統的群體中的無差別的散漫個人,而是積極參與集體性事業并以恰當的角色發揮反思功能(集體內民主)的戰士;群體作為共同體也不是外在于人的存在,因為群體本身就包含并承擔著個人的發展要求,“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因而,共同體本身就具有積極的人格,先進的政黨正是這一積極人格的代表。因此,新的群體整合的綱領不再只是諸如君主的個人意志,而是具有群體契約性并發揮著社會示范效應的政黨組織、黨性觀念、規章制度以及集體主義精神,政黨組織的先進性遂成為整個社會系統現代性的榜樣。民族意識的現代性啟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根本性的政治任務。自進入世界范圍的現代化以來,中國的民族性始終處于焦慮狀態,自近代以來中華民族遭遇的種種折磨與屈辱,也不斷動搖著國人對民族認同的自信心。但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視野內,正如無產階級只要具有反抗意識并付之于行動,就一定會成為先進的社會主體,處于被壓迫的民族,通過階級的或民族的自覺也會完成向現代民族性的轉換。在馬克思那里,資本主義的階級矛盾主要發生于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東方馬克思主義則把這一矛盾進一步拓展到西方資本主義與非西方落后國家的矛盾,并在這一矛盾中將西方資本主義本質化為帝國主義。斯大林曾賦予十月革命以一種東方民族現代性覺醒的意義:“第一,它擴大了民族問題的范圍,把它從歐洲反對民族壓迫的斗爭的局部問題,變為各被壓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從帝國主義之下解放出來的總問題;第二,它給這一解放開辟了廣大的可能性和現實的道路,這就大大地促進了西方和東方的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把他們吸引到勝利的反帝國主義斗爭的巨流中去;第三,它從而在社會主義的西方和被奴役的東方之間架起了一道橋梁,建立了一條從西方無產者經過俄國革命到東方被壓迫民族的新的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線。”這一段話,正是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引用的,其用意就在于強化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民族解放與人類建構意義,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同樣也將馬克思的階級分析方法運用到了東西方民族矛盾的分析上,并通過國家及民族的獨立與解放,初步實現了現代性的民族自覺。當然,相對于整個中國現代性建構使命而言,上述啟蒙還只是初步的,它還需要歷史性地拓展和提升為面向現代性社會與人的全面發展的深度啟蒙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