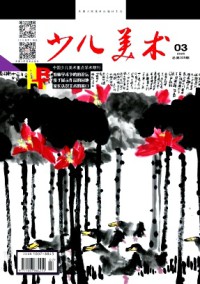少兒文學論文范文精選
前言:在撰寫少兒文學論文的過程中,我們可以學習和借鑒他人的優秀作品,小編整理了5篇優秀范文,希望能夠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借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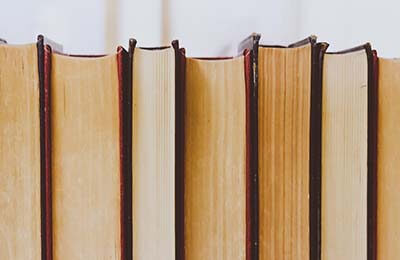
中國文學論文:少兒文學中頑童的演變
本文作者:侯亞慧作者單位:淮陰師范學院文學院
被改造的頑童
自從兒童文學在中國成為一門獨立的文學形式確定下來以后,文學作品層出不窮,對兒童文學理論的研究也日益加深,圍繞著“兒童觀”問題,理論家也給出了各自的理論構想。“兒童觀”是一種文學觀念,它是成人對兒童心靈、兒童世界的認識和評價,表現出成人與兒童之間的人際關系,持有什么樣的兒童觀,決定著兒童文學作家的創作姿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兒童文學是教育兒童的文學”的觀念就一直占據主導地位,影響極其深廣。尤其是經歷了“”之后,面對社會上出現得一系列問題,側重從教育的觀點去看待兒童文學的價值功能,強調文學作品對小讀者教育工具與共產主義教育方向性原則。因此這一時期文學作品中的頑童大都受到社會主義的教育,他們身上的“游戲精神”往往會被社會階級立場抹殺掉,他們身上的“頑皮勁”必須被改造。這蘊含著作家“教訓主義”的兒童觀,把兒童看作是一部未成熟的作品,認為他們是缺乏判斷力、理解能的弱者,然后按照成人自己的人生去教育兒童,他們本都是調皮好動的孩子,在接受教育后最終都告別了頑童生涯。
張天翼繼在上世紀30年代創造《大林和小林》后又創造了一個生活在隊旗下的新少年———羅文應。羅文應是一個六年級的學生,他和所有同齡孩子一樣愛“玩”。如放了學就收不住腳步,溜市場、逛商店、玩具店門旁盆里的小烏龜和打克郎球的人們勝敗的情景,他都要仔細看看,琢磨,常常不知不覺地浪費幾個小時,可是他并不快樂,因為心里老是惦記著作業沒寫完,功課沒復習。由于時代要求少年必須是有理想、有目標,于是作者就安排在解放軍叔叔和全班同學的幫助下,“管住了”自己,養成了按時學習、勞動、休息,不再浪費時間的好習慣。張天翼的另一部長篇小說《寶葫蘆的秘密》里小主人公王葆愛幻想,想出風頭,出人頭地,他突然得到一個神奇的葫蘆,這個葫蘆甘愿成為他的奴隸,幫他偷爸爸的錢,學校圖書館的書,老師的備課稿以及抄別人的作業。寶葫蘆發揮自己神奇的力量,幫王葆取得體育比賽的獎杯,幫他拼湊模型,讓王葆在學校大集體中顯露光彩,滿足了他的虛榮心。在大多數讀者的眼中,王葆是變異的頑童,他用寶葫蘆制造惡作劇,捉弄老師同學,看似滑稽可笑的行為,其實正是那個階段兒童內心世界的展現。本是一個頑皮愛惡作劇的孩子卻不得不被“改邪歸正”,王葆在經歷了許多事情之后,內心產生了矛盾,在老師和家長的教訓與幫助下,最終扔掉了寶葫蘆,其實也就是扔掉了兒童身上不切實際的幻想和不通過努力就實現愿望的妄想。這儼然有一種說教意味。這些頑童的改變大都是受到新中國成立后形成的“教育兒童文學”思潮的影響。即使是到了上世紀70年代,中國兒童文學一直拖著“教訓主義”的尾巴。
當然,文學向來都不是千篇一律的,尤其是作家介入社會生活的視角的差異,頑童形象各有不同。結束了動亂年代后的人們對祖國和自己的未來充滿了信心,昂揚向上的樂觀氣氛和嶄新的社會制度使主流意識形態把少年看做是“祖國的花朵”,時代氣氛感染了兒童文學作家,把兒童文學創作中描寫兒童在社會主義的陽光沐浴下幸福的生活,茁壯的成長,歌頌偉大祖國歌頌社會主義定為這時期的主題。“陽光、春天、鮮花、海浪、燕子、小樹苗、向日葵”———這些洋溢著蓬勃生命力的詞匯是這時期兒童文學美學的另一個縮影。于是,在這個時期的作品中,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充滿“游戲精神”,“優于成人”的頑童。杲向真以生動的文字刻畫了一個頑童———小松(《小胖和小松》)。小說開始就描繪出一個爭強好勝、自尊自強的頑童形象,寫小松到公園像脫韁的小馬,到處亂跑,一不小心撞倒在叔叔的腿上,叔叔彎腰扶起他,但是他卻對叔叔說:“我自己會起來”。小松被扶起后又特意照樣兒倒下,再爬起來。這就突出了天真活潑的倔強好勝的心理。后來,因為和姐姐走散哭起了鼻子,卻被一顆槐樹上的大肚子蜘蛛看見,害怕被嘲笑,自尊心又驅使他向大肚子蜘蛛發起了進攻,學著解放軍叔叔,用三角形的小木板當作手槍,對準蜘蛛,嘴里還發出“嗵”聲。這一系列的行為動作無不使小讀者受到感染。一塊三角形木板在小松心里轉化成威力無比的真槍。是否是真的手槍、是否真的可以把大蜘蛛打死并不重要,因為在小松稚氣的心里,這一切顯然都是真的,感受都是那么真實,這種“我向思維”才真實地顯露出頑童的本質。小說中小松很淘氣,渾身透露出一股快樂的、無拘無束的、蓬勃生命力。那么一種“頑氣”讓人覺得天真、活潑、可愛。更為可貴的是,在小松的身上還表現出豐富的想象,認真模仿,大膽的挑戰,表現出這個年齡階段的男孩子所特有的爭強好勝、自尊自強,以及追求不平凡的事物、向往英雄業績的性格特點。這些兒童文學作品中頑童初顯“兒童本位”的兒童觀,既不是“教訓主義”兒童觀用教育說教的方式用成人的主觀想法去改變兒童,也不是“童心主義”兒童觀那樣從成人的精神需要出發利用兒童,而是從兒童自身的原初生命欲求出發去解放和發展兒童,并且在這解放和發展兒童過程中,將自身融入其中,以保持和豐富人13性中可貴的兒童觀。
可以說在文學發展的過程中,文學理論和觀念的發展對文學作品的創作有很大的影響,同樣,優秀作品的誕生反過來又會推動文學和理論的發展前進。而在那個充滿“教訓主義”的兒童觀時代,這些洋溢著“游戲精神”頑童的出現就引領著新時期“兒童本位”觀念的到來。
當代文學論文:科技主題少兒文學發展探究
本文作者:郝婧坤1許軍娥2張美紅3作者單位:1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特種警察學院2咸陽師范學院3北京師范大學
“反科技”的聲音
“反科技”的聲音早已出現,提出“回歸自然”口號的啟蒙運動時期法國著名思想家盧梭曾就科學技術對人的道德產生消極的社會道德功能展開批判。他指出科學技術在其發展和應用過程中,逐漸成為支配、控制人的工具,人類喪失了自然人性與美德。至19世紀,馬克思比盧梭更為深刻地指出:“在我們這個時代,每一種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們看到,機器具有減少人類勞動和使勞動更有效率的神奇力量,然而卻引起了饑餓和過度的疲勞。財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種奇怪的,不可思議的魔力而變成貧困的源泉。技術的勝利,似乎是以道德的敗壞為代價換來的。隨著人類愈益控制自然,個人卻似乎愈益成為別人的奴隸或自身的卑劣行為的奴隸。……我們的一切發現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成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現代工業和科學為一方與現代貧困和衰頹為另一方的這種對抗,我們時代的生產力和社會關系之間的這種對抗,是顯而易見的,不可避免的和無庸爭辯的事實。”[4]77520世紀被公認為是科學技術迅速發展的時代,科學技術得到了加速的發展和應用。一方面,科學技術在經濟、社會領域的廣泛應用和滲透,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創造了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另一方面,卻摧毀了人類自身賴以存在的生態環境,導致全球性的生態危機即不可持續發展危機全面爆發的危險,人類又一次遭受著空前的危機考驗。于是,一些學者和思想家繼續對科學技術展開批判,從而審視、反思科學技術,兒童文學界以捍衛孩子未來良好的生存環境為己任,也積極傳達出他們的隱憂與預警意識。
(一)對受控與異化的揭示
周銳在《遙控健身操》中傳達了人類被科技所掌控和異化,必須對科學技術有所限制的觀點,他提醒人們對科技的潛在巨大風險應保持警惕。小說中的“阿嗡”大夫發明了一種遙控機器,在機器中輸入做健身操、表演、講課、背誦課文、洗臉、刷牙等等各色各樣的程序后,再給被遙控的人服下“里應外合劑”,就可以準時準點、準確無誤、身不由己地把設定程序中的各類行為“演練”出來。起初,遙控機器給人們帶來了便利,“舞盲”們吞下“里應外合劑”,就可以瀟灑自如地跳“探戈”、“恰恰”;兩個剛入門的乒乓球愛好者通過遙控技術保證對打三百回合也不會失誤……但弊端也隨之接踵而來。嘗試過“遙控門診”技術苦頭的阿嗡大夫意識到:“遙控健身操無疑是一種了不起的創造。但如若這種創造的結果恰恰只是防礙了人們的發展和創造,那么,盡管已經付出了不少努力,也只得拋棄它。現在差不多每個人體內都存有‘里應外合劑’了,也就是說,大家隨時隨地都會身不由己地接受遙控。要是盜賊設法遙控銀行職員、侵略者遙控了邊防軍……那該多可怕。”(《遙控健身操》)更可怕的是,如果技術被戰爭狂人或恐怖集團所掌握,那么后果不堪設想。由此暴露出科學技術具有統治的意識形態功能,這無疑會嚴重抹殺個體人的自主創新性。哈貝馬斯也認為科學技術必然具有消極的作用,主張把科學技術作為直接的批判對象來加以批判。在周銳的這部短篇小說中,也開始深刻表現技術異化人類的問題了。人們被禁錮在看得見的裝置和看不見的控制中,“越來越少地與人面對面打交道了。電腦自動化管理、自動取款機、自動驗票系統、自動駕駛儀……我們實際上逐漸把自己的日常行為‘托付’給了機器來‘照看’”,甚至于哭、笑等精神活動在小說中也受到了技術的控制,正如生態批評家魯樞元所言:“先進的科學技術正以它的巨大威力滲透到人類個體的情緒領域和精神領域,并力圖以自己的法則和邏輯對人類的內心精神生活實施嚴格精確的、整齊劃一的現代化管理。當科學技術日趨精密復雜時,人卻被簡化了,這又是熱心發展現代科學技術的人們始料不及的。”[5]269這無疑是科技高度發展的信息時代給人類內部帶來的一種本質意義上的“精神污染”。我們如今確已生活在一個機器智能的時代,電腦在某種程度上已成為了當代的機器人保姆,而信息技術目前正以勢不可擋的趨勢向前發展,人類已從中產生了受控感、異己感和非人感,如果我們不想變成冷冰冰的機器,反思是必要的。
(二)科技的尷尬與自然的勝利
文學語言論文 :基于詞語角度論少兒文學
本文作者:陳曉斌作者單位:中國地質大學外國語學院
我們可以看到疊音作為一種特殊的詞語使用形式在兒童文學中被大量運用,存在著AA、AAA、AAB、ABB、AABB、ABAB等多種形式。在兒童文學中,疊音詞語的使用具有重要作用。
一方面,相同音節的復疊使得兒童文學的語言自然而然地透出兒童式的稚嫩、童真,給人以兒童特有的“小”“、可愛”“、親切”之感。兒童特別是幼兒,受自身語言生理機能的制約,本身就常用疊音詞,兒童文學中疊音詞的使用迎合了幼兒的這一語言特點,保留了“幼兒自然口語的原生狀態”,“用最簡潔、最自然的語言形式傳達出了幼兒最本真的生命意趣”(王金禾2009)。
另一方面,相同音節的復疊和諧了音韻,調整了節拍,或模擬聲音、或描繪色彩、或狀寫情態、或摹寫動作,使語言流暢、生動,極大地增強了作品的音樂性和美感。比如,例(11)中的“喵喵叫”、“咪咪笑”、“哇哇喊”“、嗚嗚叫”,通過疊音的運用,既使得前后音韻和諧流暢,讀來朗朗上口,又是對貓和女巫聲音的模擬、狀態的描寫,生動地展現出了狂風來之前的愜意、悠閑和狂風來之后的緊張、慌亂。例(13)中的“濕答答”、例(14)中的“黑乎乎”分別描述了小青蛙剛從池塘里跳出來的狀態和小熊餅干烤糊了后的顏色,疊音的使用摹其聲、繪其色,既顯得具體真切,讓人產生了相關形象的聯想,讀來又顯得親切可愛,兒童味十足。
綜上所述,兒童文學,作為面向兒童的文學作品,其讀者的特殊性決定了其語言也必然具有特殊性,必須是兒童所“易”于接受和“樂”于接受的語言,必須具有“兒童味”。為實現此目的,兒童文學的語言必然受到方方面面的諸多制約。本文選從詞語的使用這一方面對兒童文學的語言展開了討論。從詞語的使用形式上來說,疊音詞的使用是兒童文學中的一個普遍現象,具有多種不同的疊音形式,不僅使得兒童文學的語言顯得稚拙、質樸,兒童味十足,而且和諧了音韻,調整了節拍,增強了作品的音樂性和美感。當然,限于筆者本人的能力,本文對兒童文學語言詞語上的討論只能是淺嘗輒止,很多方面還有待今后進一步深入的研究和探討。
大眾傳媒論文:傳媒對少兒文學表現的影響
本文作者:孔凡飛作者單位:沈陽化工大學
實際上,大眾傳媒與文學之間是一個相互影響和滲透的過程,只不過在今天,大眾傳媒的強大優勢讓其對文學的影響更為擴大。“文學在大眾傳媒的力量作用下發生的變化更多更大,也更為深刻,表現出文學對大眾傳媒這一強勢文化力量的趨附和大眾傳媒對文學內部的深度進入。這既是大眾傳媒時代大眾傳媒掌握文化領導權的必然結果,也是市場經濟時代的文學,作為文化產業構成部分的文學所做出的功利性選擇和商業化的轉化。”[7]大眾傳媒不僅通過改變文學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從外部對文學的藝術表現進行干預,同時,它也以媒介本身的技術條件,通過普通使用電腦及網絡,無形中對文學創作的內部進行改變,從而讓文學創作在思維、內容、表達方式、審美趣味及語言的運用上都發生變化。
對創作思維的影響
在大眾傳媒的時代,電腦成為作家寫作的重要工具。正如有專家預見的那樣,“在電腦上書寫不僅使作家的書寫方式發生變化,而且影響到作家的創作方式和思維方式”[8]。但是,這種影響隱晦而不易察覺。從用筆書寫變為用電腦書寫,是書寫的一次技術革命,但對思維影響而言,則有可能是災難性的。用筆書寫是文字在頭腦中不斷建構形象的過程,而電腦寫作則是用手指敲打鍵盤,僅僅是文字的輸入過程,作家關注的是文字呈現的過程。傳統的文學是用筆逐字逐句的創作過程。在寫一篇作品之前,作者需要想好如何開頭,如何結構作品,如何結尾,是一個完整而嚴謹的過程。寫作思維是一種線性的思維方式。而電腦寫作則打破了線性思維的結構,可以發散性思維進行,因為電腦帶來了思維空間的開闊性和思維結構的高速性。再加上網絡上尋找資料的方便性,作者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在網絡上找到更多需要的資料,只要對其進行簡單的復制就可以完成,這就削弱了作者對資料的深層加工。在用電腦寫作過程中,可以不斷地增添或者刪除內容,甚至可以先寫其中一個部分,再寫其他部分,然后再連接成一個整體。電腦寫作帶來的一個負面效應就是可能造成文學創作的淺表性,不追求作品的深度,故事有大眾化傾向,甚至出現某種程度的模仿他人或模仿自我,這也被成為“備份式寫作”。“備份式寫作以一種復制的眾多性取代了創作的獨一無二性,追求標準化、程式化,它使陌生的創新變成庸俗的成規。”[9]不可否認,近些年遼寧兒童文學作家的創作可謂豐富,然而真正能夠產生影響的卻寥寥無幾,盡管作品的銷售也很可觀,但大多數作品都被湮沒在兒童文學創作的滾滾滾洪流中,如前文提到的那些迎合市場而創作的魔法系列就是如此。可以說,這些作品都不約而同地呈現出故事的大眾化傾向,缺乏獨特的生活體認,作品也缺乏相應的深度,塑造的都是魔法、巫師形象,不可避免地有雷同的印象,更何況J•K•羅琳的珠玉在前。作家自身也會就某種題材出現雷同。如劉東的“奧運小子”系列中,他創作的《閃電手的故事》和《林大腳的故事》無論在形式還是內容上都有“標準化”的趨向。主人公一個打籃球,一個踢足球,在他們的各自生命中都有一個精神上的引路人出現。《林大腳的故事》中出現的是球星李皓,而《閃電手的故事》中出現的是坐輪椅的女大學生趙越。主人公都在一系列故事中體味到運動對人生的意義。而同一系列的其他幾位遼寧作家的創作似乎也沒有逃過這樣的“標準化”趨向。同樣,薛濤的那部具有文體突破意義的“山海經系列小說”,也有同樣的問題。三部小說分別和中國古代的三個神話故事“盤古開天”、“精衛填海”、“夸父逐日”相對應。而小說中的主人公都穿越現代與古代,小說的構架都是相同的,這和真正意義上的幻想小說中的“新神話”模式是有一定區別的。盡管該小說開拓了中國本土幻想小說的新領域,但卻因故事構思的同構性稍顯精致有余而大氣不足。電腦化寫作對創作思維的這種影響,讓人覺得寫作似乎可以批量化,而不是創作。正如馬克•波斯曾擔心的那樣,“電腦寫作清除了書寫中的一切個人痕跡,而使所有的東西變得非個人化了。”[10]個人化是文學創作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標尺,它標志著作者個人風格的形成,個性精神的獨特展現。而電腦化寫作導致的寫作思維的改變,“備份式寫作”的形成,會讓文學趨于平庸。
對文學表現方式的影響
文學的表現方式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日新月異、手法多樣、文體的交融、文本的超越,成為今天的文學創作的一道新的風景。新聞報道是大眾傳媒的重要載體,新聞報道以及時性、真實性和典型性而著稱,而生活在當下的人們似乎更愿意通過新聞報道來體會喧囂的現代生活。因此,在大眾傳媒影響下,新聞語言的敘事方式對小說的敘事影響越來越大。這種小說新聞化的敘事方式在成人文學中屢見不鮮,但對于兒童文學來說,這種新聞化的敘事還沒有形成規模,畢竟兒童文學就其語言來說有其特殊性。但是這種創作傾向卻在某些作家那里得到印證。劉東的那部獲獎無數的《轟然作響的記憶》就是此類作品。該作品由12個獨立的故事組成,號稱“中學生的口述實錄”,作者將其稱為“采訪小說”。該作品以紀實的新聞手法向讀者講述了12個少年的成長故事。每篇作品的后面都附一篇作者手記,這更增加了作品的真實性與典型性。這或許也是這部作品受到輿論好評的原因。單瑛琪的“小哥倆兒”系列,則在作品中贈送與作品內容相關的視頻光盤,讓讀者在讀書的同時還可以通過播放光盤進入到游戲當中,從而使文學創作超出原有的文本,形成“超文本”。這種文學文本與視覺文本的互動,開拓了文學表現方式的新類型。而實際上這種超文本的形式可能會成為未來圖書出版的一種新形勢。大眾傳媒對作者和讀者審美趣味產生重大的影響。文學的寫作和閱讀在大眾傳媒流行之前,一直被視為一場高雅的精神活動,甚至有“貴族化”的趨向。然而,在大眾傳媒的時代,文學的消費者追求的不再是細細品讀作品的高雅情趣,相反,追求最貼近自身生存狀態的生活趣味,追求閱讀作品傳達出的感官快樂,成為一種常態。有學者認為,“他們更喜歡在都市的奇異故事與刺激的場面中尋求感覺與情感的通道;他們更傾向于欣賞節奏歡快、情節突變、充滿荒誕、驚險場面的‘藝術品’。”[11]其實,兒童文學在一定程度上是強調其故事的輕松有趣,倡導“游戲精神”,這或許和大眾傳媒時代的要求不謀而合。遼寧兒童文學的創作曾一度以深沉厚重而著稱,但是,在大眾傳媒時代的背景下,生活化和娛樂化的創作也層出不窮。董恒波的那些以幽默著稱的創作如《清明時節》《危險的實驗》等反映城市少年兒童生活的小說作品,在驚險而輕快的敘事中,讓讀者體驗快樂,感受成長。單瑛琪的“小哥倆兒系列”是強調游戲精神的作品。故事以情節的歡快、荒誕而著稱,一對雙胞胎兄弟的那些讓人啼笑皆非的故事,讓讀者感受著成長的可愛與稚拙。這是當下非常流行的一種低幼兒童文學創作的方式。而以劉東的《稱心如意秤》《鏡宮》等作品為代表的創作,大多講述生活在城市中的少年,在一系列奇異的經歷中尋求成長的過程。《鏡宮》通過主人公南海進入電腦網絡中一個被稱為“鏡宮”的網站,實現不同人生交換的目的,而在一次次的人生交換的過程中,他體味到成長中所要面對的親情、友情和愛情等等必須面對的問題。故事本身很吸引人,在和主人公一同交換人生的過程中,讀者似乎也尋找到一種情感宣泄和體驗的過程。
兒童成長論文:少兒文學對孩子人格的影響
本文作者:梁英姿作者單位:泉州幼兒師范高等專科學校
健康人格的培養需要滋養心靈的童話
童話是每個人成長路上不可缺少、也是最早接觸文學的一種重要形式,它的幻想、夸張以及無盡的可能讓人們感受到文學的樂趣,它引領著孩子們快樂生活在童話所營造的環境,讓孩子們感受愛,感受美,感受善,讓孩子們在這片土地上健康成長。
(一)兒童的心理特征決定了童話的特殊地位
孩子從三歲左右開始,已經能用初步的口頭語言表達自己的想法,并且對成人所描述的語言有了一定的了解,大部分有心的家長都會在這一時候開始每天給孩子講一個簡短的故事(包括童話)。孩子對童話的好奇可以持續到十一、二歲(甚至更久)。從三歲開始,孩子身心正處于快速發展時期,對周圍世界有著無盡的好奇。但是他們對事物的認識多是表面的、片面的,一般只能認識個別具體事物的個別特征;他們的思維帶有明顯的具體性和直觀性,邏輯思維能力隨年齡的增長開始萌芽,抽象概括能力也處于開始發展的階段;注意力不大容易集中,尤其是對他們不感興趣或枯燥的學習內容更是無法集中注意力。處于這時期的兒童活潑好動、精力旺盛,他們好奇、好模仿、好幻想,對周圍的事物具有“擬人化”傾向。正是兒童期的這些心理特征,童話所獨有的表現形式為兒童所接受、所喜歡,成為兒童成長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糧”。
(二)童話所具有的心理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