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語言特征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小說語言特征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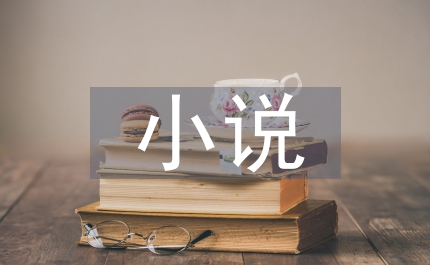
小說語言特征范文第1篇
關鍵詞:環境政策;規制績效;波特假說;重點調查產業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71063006); 國家軟科學項目(2012GXS4D089);“贛鄱555工程”領軍人才培養計劃項目(贛組字[2011]64號);2011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項目 NO20111042135)。
作者簡介:萬建香(1973-),女,江西南昌人,博士,江西財經大學信息管理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環境經濟學研究。
中圖分類號:F06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1096(2013)01-0115-05收稿日期:2011-07-24
引言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大量文獻關注政府環境規制對企業競爭力的微觀影響,并形成了傳統觀點、波特假說、不確定性假說三種觀點。傳統觀點認為,環境規制的執行以提高生產成本或對盈利性、生產性投資的擠出為前提,從而必然降低產業績效。Brock 等(2005)就認為嚴格的環境規制使企業承受額外的規制成本,阻礙了產業生產能力和創新能力的提高。傳統假說受到波特假說的嚴峻挑戰。波特假說認為,環境規制給產業造成的負擔可以通過技術創新途徑加以彌補從而提高產業績效(Porter et al,1995)。龐瑞芝等(2011)運用中國1998年~2008 年省際面板數據評估了轉型期間我國新型工業化的增長績效,最終支持了波特假說。王國印等(2011a)關于我國中東部面板數據的實證表明,波特假說在較落后的中部地區得不到支持,而在較發達的東部地區則可以。何潔(2010)利用中國29個省份1993年~2001年工業SO2的排放數據來估計模型,對波特假說再次進行了驗證。趙紅(2008)運用1996年~2004年中國產業數據,再次驗證了波特假說。不確定性假說認為,環境規制對產業績效的影響可正可負,具有不確定性。環境規制強度、政策工具特點、產業和市場結構都影響環境規制的產業績效,各自表現為成本負效應或創新正效應,兩者的強弱決定環境規制的最終績效。王國印等(2011b)運用我國東中部地區面板的實證表明, 較發達的東部地區的情況支持波特假說,而較落后的中部地區則不支持。陳艷瑩等(2009)研究發現只有當環境管制引致技術創新節省的成本大于污染控制增加的成本時,波特假說才成立。單雪芹等(2009)從構筑國家競爭優勢時加強環境保護的必要性出發,分析了波特假說的不確定性問題。
上述研究大多假定一旦形成引致創新,就能提升產業競爭、獲利能力,而實際上兩者之間存在一定差距,至少存在時間滯后,其合理性、實用性有待驗證(趙紅,2007);其二,三種假說以波特假說最受推崇,同時也飽受爭議。因此,本文專門針對波特假說存在性問題,運用江西省24個重點調查企業①2002年~2009年的面板數據,設定產業競爭能力、創新能力、環保能力為被解釋變量,重新驗證波特假說的存在性,驗證其是否適合江西省的經濟實際。
文章第二部分為變量選擇和數據描述;第三部分為模型估計、經濟意義解釋及績效彈性分析;第四部分為結論。
一、變量選擇與數據描述
小說語言特征范文第2篇
【關鍵詞】語言風格;自然樸實;細膩透徹;明快率性;親切溫柔
丁玲是我國“五四”新文學第二代杰出的女作家,她初期創作的14個短篇小說,以口語和翻譯語體為主要語言資源,兼用方言與古語,形成了獨特鮮明的語言風格:自然樸實、細膩透徹、明快率性、親切溫柔,震驚了當時的文壇,贏得了廣大讀者特別是年輕大學生的喜愛和歡迎,在我國現代文學語言建設中具有重要意義。
一、自然樸實的語言風格
自然樸實是丁玲早期小說語言風格的一個突出特征。丁玲一生執著于追求
文學語言的質樸無華,追求“樸素的,合乎情理的,充滿了生氣的,用最普通的字寫出普通人的不平凡的現實的語言”[1],形成了樸實自然、不尚雕飾的語言風格。這個特點不僅表現在小說用語富于口語化、平實易懂,也表現在小說的句式簡短小巧,靈活多變,富于生活氣息,表現在修辭上多用排比、對比、比喻、比擬、夸張等語言材料普通,與現實生活貼近,為人們所普遍熟悉的辭格。這種語言特點充分顯露于丁玲早期小說的字字句句之間,給人以親切平實的深刻印象,讀之覺得好像是在和作者說話聊天、促膝談心一樣。如:
本來,酉陽是不必有那樣多學校的……只要有花,至少可以抓下一把來,底下看的人便搶著去撿花片。勻兒總該記得吧!” [2]
這段文字描寫了酉陽中學氣派堂皇、優美宜人的校園景致。文中多用口語詞、
語氣詞、疊音詞,少用成套的關聯詞;多用短句、省略句,少用成串疊加的附加
語;多用所用辭格都是人們習見習用的比喻、對比等辭格。這些表達手段的恰切
使用,讓我們覺得好像在跟著勻珍媽媽漫步于酉陽中學校園一般,感到十分親切
自然。這種自然天足的文學語言,能夠“使讀者如置身其間,如眼見其人,長時
間回聲縈繞于心間。”[3] 體現了丁玲早期小說語言的魅力。
二、細致透徹的語言風格
細致透徹是丁玲早期小說語言風格的一個顯著特征,也是丁玲早期小說著稱文壇的鮮明標志。作者善于抓住一個中心、一個焦點,濃墨重彩地加以點染,把應該突出的部分寫得極為充分、詳盡;且喜用關聯詞語、數量詞語和成串使用同類詞語,使表意周全詳盡;同時多用長句、松句,使句子架屋疊床,盤桓繁復,信息量大,表達充分完整;排比、反復等辭格的綜合使用,使小說語言流暢繁復。這些風格手段的恰當使用,起到了積極的修辭效果。如:
現在她把女人看得一點也不神奇……依舊忍耐著去走這一條在純物質的,趨圖小利的時代所不屑理的文學的路的女人。[4]
引文運用長句造成了語言細致透徹的特點。作者在“阿毛真不知道……”這個長達170字的長句中嵌入了結構繁復、多達109字的附加成分,即“自己燒飯……在許多高壓下還想讀一點書”、“把自己在孤獨中見到的……趨圖小利的時代所不屑理的文學的路”,使句子枝繁葉茂,把城里那些以寫作為生的女人的生活和心理寫得紛紛揚揚,淋漓盡致,顯得語言腴厚,內容豐富,表意細致完整,給人以詳盡透徹之感。作者在刻畫人物心理時更是多方鋪敘、分析、闡釋,唯恐表意不盡,力求寫出人物復雜多變、深邃莫測、錯綜盤曲的內心世界,尤為體現了繁豐細致的語言風格。
三、明快率性的語言風格
明快率性是丁玲早期小說語言風格的一個鮮明特征。小說詞語意義明晰,多用直義;多用關聯詞語、方位詞語、序數詞語等,清晰連貫,層次分明;多用短句、反問句和斷然的肯定或否定句等,語意顯豁,情感鮮明;多用比喻、排比、借代、頂真、比擬、反復、對照等辭格,明白好懂。如:
我總愿意有那末一個人能了解得我清清楚楚的……我真愿意在這種時候會有人懂得我,便罵我,我也可以快樂而驕傲了。[5]
文字直寫莎菲不被人們理解的社會現實,直抒她因不得理解而倍感寂寞、孤獨、苦悶、失望、不滿的心境。詞語都是直義,讀時不需揣摩、推測、意會,一看就明;關聯詞語的運用使表達流暢,層次分明;副詞“總”、“真”、“偏偏”起到了強調的作用,使感情鮮明凸顯。以短句為主,結構簡單,表意單一、明確、清晰,沒有歧義,沒有疊加的修飾語;而“我總愿意……”、“我真愿意……”、“我真不知……”、“我要……做什么?”、“愛我的……肺病嗎?”等肯定句、否定句和反問句的較多使用,使表述更加直露明快。主要使用了反復辭格,詞語反復,語意凸顯,感情強烈,鮮明地表達了莎菲渴望被人理解的愿望。這些風格手段的綜合使用,充分顯示出小說顯豁明朗、率性明快的語言風格,這與丁玲豪爽、豁達、坦誠、大氣的性格是分不開的。
四、親切溫柔的語言風格
親切溫柔是丁玲早期小說的一個突出特征。小說擅長使用能夠觸動心靈深處、表現細枝末節、細膩深沉、柔和溫馨的詞語,以及疊音詞、語氣詞、代詞、模糊詞語、昵稱、尊稱等;注重長短句交錯,整散句結合,多用插入語,且句子的主語、修飾語、賓語又長又多,結構自由散漫,節奏松軟;修辭上常用擬人、比喻、摹擬、婉曲等辭格,顯得親切委婉。如:
更使阿毛不愿常見的……并且每天她和他都并坐在一張大藤椅里,同翻一本書,或和著高低音共唱一首詩歌。
這段文字一是選用了大量表示親近甜蜜的詞語,如“斜靠”、“漫步”、“擁著”、“踏著”、“并坐”、“同翻”、“和著”、“共唱”等;二是使用了多組音節自然和諧、悅耳動聽、表意細膩的疊音詞,如“鏗鏗鏘鏘”、“細細柔柔”、“談談講講”、“悠悠閑閑”等;三是在句中使用了語氣助詞“的”,用逗號分開,輕聲,舒緩了節奏;四是使用代詞“那樣”,增加了音節,大大舒緩了語言的節奏,與后面的兩組疊音詞“細細柔柔”、“談談講講”相結合,似實似虛,柔婉溫馨;再加上結構松散、自由散漫的句子,讓人感覺如春風拂面,如潺潺流水,輕柔婉轉,秀麗嫵媚,纏綿繾綣,表現了阿毛對美好生活的熱切憧憬和向往之情。正是因為小說“終是比別人要來得溫柔細膩,所以歡喜看這類文章的讀者還不十分零落。”溫柔親切的語言風格為丁玲及其小說贏得了讀者,贏得了廣大年輕讀者的喜愛。
丁玲早期小說的語言風格特征,是她在“五四”白話文運動中辛勤耕耘、努力探索的心血和結晶,其內容十分豐富,而且對我國的現代文學語言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這里論述的四個方面,雖然還不夠全面科學,但基本上能夠反映出丁玲早期創作語言藝術風格的概貌輪廓。關于這些小說語言藝術更深入的研究,有待于在今后的學習和研究中進一步探討。
參考文獻:
[1]丁玲.美的語言從哪里來[A].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8卷[C].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340
[2]丁玲.夢珂[A].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3卷[C].(第1版).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5
[3]丁玲.談與創作有關諸問題[A].丁玲全集?第7卷[C].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336
小說語言特征范文第3篇
關鍵詞:高中語文;小說教學;四面體
中圖分類號:G427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992-7711(2014)19-092-1
一、由小說三要素與小說主題形成的小說“四面體”
三要素,也就是我們常常提到的小說三要素,包括小說的人物,環境和情節;而四面體,則是由三要素與小說主題構成的“四面體”。其關系圖如下:
以主題為中心,三要素為點,構成一個四面體,且將之稱為“小說四面體”。
小說閱讀鑒賞,主要就是解決這個“小說四面體”所反映的種種問題,解決了“小說四面體”中幾個要素的關系,也就解決了小說的閱讀鑒賞問題。
在“小說四面體”這個圖中,各個要素之間的關系都是相互的,是不能脫離任何一個要素而獨立存在的。“小說三要素”之間也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相互制約,所以,在“小說四面體”中的幾個要素都是以一個整體而存在的。
人物在典型環境中活動,環境反映人物典型性格,人物成為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典型環境同時影響或推動人物命運發展,即推動或影響情節發展。
人物、環境之所以典型,是主要通過情節來表現。情節是按照因果邏輯關系組織起來的一系列事件。高爾基說:情節“即人物之間的聯系、矛盾、同情、反感和一般相互關系――某種性格、典型的成長和構成的歷史”。由此可以得知,小說典型人物的塑造需要通過情節來表現。小說通過情節表現人物性格特征,通過情節揭示小說主題,情節也可以暗示環境,渲染環境氛圍,突出小說主題。
環境描寫有多種作用,或反映時代特點,或反映地方風情,或渲染氣氛,或推動清節,或表現人物性格,或提供人物活動的場所……環境是人物的語境,因此小說教學必然要引導學生分析環境描寫。環境揭示小說主題的前提與背景,脫離了一定的環境,尤其是社會環境,也極大地影響了對小說主題的揭示。
另外,這里的人物包括主要人物與次要人物,環境包括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在這個關系圖中,人物中的主要人物與次要人物,環境中的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都存在著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關系。
小說“三要素”與小說主題構成了一個“小說四面體”,他們之間關系都是息息相關,緊密聯系的。若想解開小說主題的謎底,還需要從小說“三要素”下手,逐個破解。
二、典型化理論與小說教學
在“小說四面體”中各要素之間的關系中,小說人物與環境都具有典型性特征。這是小說這種文學樣式的典型特點。
典型化的基本內涵就是按照典型的特征塑造形象和形象體系。使之具有鮮明的獨特性和深刻的普遍性。也就是由不典型或不充分典型的生活原形變為典型的藝術形象的過程。
因此,小說作者將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作為目標,揭示小說主題。對于讀者而言,只有抓住了小說人物與環境的典型性特征,便把握了小說的靈魂。
在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小說的情節可以虛構,人物可以虛構,但是,小說的典型環境和人物的典型性格需要真實,否則,小說主題便失去了它的現實意義。
以《祝福》為例,祥林嫂這個人物可以是虛構的,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但是,與祥林嫂這樣的社會底層的勞動婦女形象相似的,在社會中是存在的,并且是某一類中的某一員。魯鎮這個地方可以在現實中不存在,但是跟魯鎮這個環境相似的社會環境在現實中是存在的,不是“魯鎮”,可以是“李鎮”、“劉鎮”。也就是別林斯基所說的“熟悉的陌生人”,小說人物與環境對于讀者而言,既熟悉又陌生,這就是典型性特征。
三、鑒賞“環境”描寫,揭示小說主題的秘鑰
文學鑒賞中,所有鑒賞都離不開對語言的鑒賞與把握。雖然小說語言相比其他文學文體作品而言比較通俗易懂,但必要時候,我們仍需用鑒賞詩歌語言的方法對小說語言加以鑒賞,方能理解其精妙。
小說《祝福》中還有關于“人物”的精致表現和“情節”的巧妙安排,已經有很多名家談過這類問題,這里就不再一一贅述。小說“主題”的揭示都離不開小說典型“人物”的塑造和“情節”的處理安排,因此,關注“小說四面體”是通向深入鑒賞小說的有效途徑。
小說語言特征范文第4篇
摘要劉慶邦的《梅妞放羊》、《鞋》、《遍地白花》、《春天的儀式》等一系列鄉村題材小說之所以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以及評論界的一致好評,個性化的語言是其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享有“短篇王”美譽的劉慶邦十分重視小說的語言,其語言個性主要表現為地方化、本色化、審美化三個方面的特色。
關鍵詞:劉慶邦 語言 地方化 本色化 審美化
中圖分類號:I206.7 文獻標識碼:A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文學創作的過程,其實就是作者個性生命體驗的文字呈現過程。小說作為文學的一種形式,語言的成功與否是小說成功的關鍵。享有“短篇王”美譽的劉慶邦十分重視小說的語言,他認為“創作上語言是第一位的,帶著自己呼吸、有個人氣質的獨特的語言才美”。他的《梅妞放羊》、《鞋》、《遍地白花》、《春天的儀式》等一系列鄉村題材小說之所以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以及評論界的一致好評,個性化的語言是其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劉慶邦小說的語言個性主要表現為地方化、本色化、審美化三個方面的特色。
一 地方化語言
方言是地域文化重要的載體,鄉土文學作家們無不有意識地從方言寶庫中提煉、采擷鮮活的富有表現力的語匯進入文學作品,用浸潤著泥土氣息的語言創作出優秀的文學作品。劉慶邦生于河南沈丘,他在這塊大平原上生活了19年,那里的地方語言在其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故其創作中使用農民方言俗語時是信手拈來,隨心所欲,濃郁的鄉土氣息使人感到既親切又自然。比如,豫東地區方言中名詞后面往往帶上“子”這一后綴,這一語言現象在劉慶邦的鄉村題材小說中有充分的體現:瓜庵子、瘋杈子、玉米辮子、辣椒串子、箔籬子、奶漿子、白面劑子,這樣的詞語隨處可見。劉慶邦還善于使用民間語言寶庫中一些表現力極強的詞語,比如:
吹奏者塌蒙著眼皮,表情是職業化的。(《響器》)
她家院子里就有一棵棗樹,四月春深,滿樹的棗花開得正噴。(《鞋》)
凡是高玉華的消息都是好消息,一聽到有關高玉華的消息,他心里就美氣的不行。
二姨以為香當著母親的面礙口,想把香拉到一邊去問個究竟,二姨一拉,香就一“卜楞”,二姨不能夠拉她走。(《閨女兒》)
這孩子,恐怕要丟搭壞。(《小呀小姐姐》)
這是一只大號的瓦碗,雞蛋茶盛得溜邊溜沿,不只是五個六個,還是九個十個。荷包蛋已經成疙瘩打蛋。(《相家》)
上述語句中加點的詞是豫東方言乃至河南方言中極富地方特色的詞語,這些詞語在一定區域內被一代又一代人長期使用,很傳神,具有很強的生命力,在日常口語表達中常常有規范的普通話詞匯不能替代的作用和魅力。比如“塌蒙”一詞所表達的意思類似于“耷拉”,但“耷拉”很難表達出眼皮下垂蒙蓋在眼珠上的那種狀態。“噴”的意思是花開得正旺,但卻比“旺”顯得更有氣勢。“美氣”一詞則蘊含了興奮、快樂、幸福等多重意思。“卜楞”寫出了對外力拉拽的推拒和反抗。“丟搭”指的是由于忙碌、貧窮等原因而疏于對孩子、家禽家畜的照顧。“溜邊溜沿”指東西盛得很滿,但卻比一個“滿”字要具體生動得多。
地方化的語言也為人物形象增色不少,因為方言是真正地來源于生活,和人們的情感有著難舍難分天然一體的牽連。劉慶邦在小說中還大量運用民間俚語歌謠等表現農民對生活的體驗和理解,一腔一韻表達著農民最樸素而豐富的思想,使其小說語言既新鮮、生動,又很有嚼頭。比如:
二姨笑了,說,我說過這兩個孩子是一對兒,不會有錯兒,一個葫蘆嘴,一個嘴葫蘆,都抱著葫蘆不開瓢。(《閨女兒》
好看不過對肚子瓜,當媒人的兩頭夸,母親允許表叔的話有所夸張。待到表叔把話說成了車轱轆,母親才說了一句:她叔,閨女的事讓您操心了。(《相家》)
在鄉村題材的小說中,用地方化的語言去敘述產生、流行這種語言的地區的生活,可以起到兩方面作用:第一,做到“文”與“言”的統一,即內容與語言的協調,增加真實的質感,對人事生活的敘述得以自然而然地完成,于是產生鮮明的地域或地區文化特色。第二,對于本地域、本地區的讀者,自然有一種親切感,增加其閱讀興趣;對于外地域讀者則有一種陌生感、距離感,這也可以使之產生閱讀興趣。在詞匯現代化的今天,有許多方言土語都在迅速湮沒,而劉慶邦小說中運用的地方化語言不僅原汁原味地反映了當時農民們活生生的口頭語言,同時也反映了特定的地域文化,富有濃郁的地方風情和生活氣息,具體生動,可聞可感。
二 本色化語言
劉慶邦的小說立足于民間生活,站在民間的立場來寫民間。其民間立場不僅表現在其作品的思想內容、敘事風格上,在小說語言上也有所反映,具體表現在:某種程度上放棄知識分子在語言上的優越感和敘事中根深蒂固的自我意識,用極富鄉土本色的語言來書寫鄉村人物與鄉村生活。
劉慶邦認為:“我們寫小說寫什么呢?無非是寫人,寫人的喜怒哀樂,寫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寫多姿多彩的人生形式,寫人性的豐富性……”那么如何來寫人物呢?劉慶邦強調要貼著人物寫:“看來還得貼著人物寫,這是我們寫作者的惟一選擇。要貼著人物寫,我們腦子里起碼要裝著一些人物。這些人物或者是故鄉的鄉親,或者是以前的工友,或者就是自己的親人親戚,等等。對這些人物,我們是應該比較熟悉的,知道他們怎樣說話,怎樣走路,怎樣哭笑,怎樣咳嗽。閉上眼睛,他們如在眼前。否則我們就無從貼起。”貼著人物寫,表現在人物語言上,就是盡量讓人物用他自己的語言來講話,讓人物說貼合自己身份、性格及生活環境的本色語言,怎樣的人,處在怎樣的地位,具有怎樣的情趣,便現出怎樣的語言風采。
《誰家的小姑娘》里農村小姑娘改的弟弟開放哭時,改的娘問:“放兒哭啥哩?”得知兒子餓時,她又說“一會兒不嚼我他就不能過”,娘雖然累得沒勁了,還是“一聲沒吭”讓兒子“嚼”她。后來娘讓改把地里的魚送到黑叔魚塘里去,改拒絕去,娘問“那是為啥?”改只說“啥也不為”。在娘中暑暈倒時,改帶著哭腔喊“娘,娘,你咋啦?”小說中僅有的幾處人物語言充滿了泥土般的質樸氣息,通過這些簡短而生動的口語,娘的辛勞和改的倔強躍然紙上。在小說《鞋》中,因為妹妹動了守明視如珍寶的鞋,守明跟妹妹吵起來了,守明質問妹妹:“誰讓你動我的東西,你的手怎么這么賤!”“還敢嘴硬,看看上面你的臟爪子印!”母親過來勸架,把鞋底看了又看,說這不是干干靜靜的嗎!守明說:“就臟了,就臟了,反正我不要了,她得賠我,不賠我就不算完!”母親說:“不算完怎么了,你還能把她吃了,你是姐姐,得有個當姐姐的樣兒。”這是一場真實生動的吵架場面,幾乎是將生活中姐妹吵架、母親勸架的語言原滋原味地搬到作品里了。
不僅人物對話是人物本色語言,與之相關的敘述語言也是非常符合被刻畫的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特征的。小說《鞋》中有這樣一段敘述:“又開始給棉花打杈子時,守明心里像是生了杈子,時不時往河那岸望一眼。河那邊就是那莊子的地,地盡頭那綠蒼蒼的一片,就是那莊子,她的那個人就住在那個莊子里。”沒有激情澎湃的語言,沒有用到“思念”、“相思”、“刻骨銘心”之類的詞語,只是寫主人公時不時往河那岸望一眼的動作,作者用極富鄉土氣息的語言刻畫出了鄉村少女內心對未婚夫“才下眉頭,卻上心頭”的思念與渴望。再如《夜色》寫周文興定親后,心里“美氣”得不行,走起路來都格外“帶勁兒”,“美氣”和“帶勁兒”是最實在最真切的農民語言,表現了周文興定親后掩飾不住的興奮與激動。《相家》描寫“母親”將要親自去為閨女兒相家:“她想把這個事暫且丟下,該干什么還干什么。可是不行,她低頭是這個事,抬頭人還沒有出門,夢里去相家已經去了好幾次了。”這幾句話簡潔素樸,通俗明白如家常話,既貼近農村婦女的身份和性格,又極富生活氣息,令人回味無窮。
本色化語言的運用使劉慶邦的鄉村題材小說從意識形態話語和知識分子精英意識所形成的夾擊里突圍而出,以生動傳神的對話和細膩到位的心理刻畫再現了民間生命豐富的情感世界。
三 審美化語言
劉慶邦曾說過:“每一個漢字都是一個有生命的東西,它的底蘊是很厚的,根是很深的……用這些字的時候我是懷著敬畏之心,生怕哪個字用得不是地方,每句話,每個字都要推敲。”劉慶邦對待小說語言的態度是嚴肅的,他大量擷取民間語言寶庫的可貴資源用于小說創作,并沒有放棄知識分子對小說語言的駕馭,他的鄉村題材小說語言在地方化和本色化之外,還體現出審美化的特色。
審美化首先體現在對原始民間語言的提純凈化。在小說創作中,無論是地方化語言還是高度貼合人物身份、性格、生活環境的本色語言,對于鄉土文學作品的創作均具有普通話語匯難以替代的作用。但來自民間的東西往往是很俗的,如若把握不當,就會使得作品語言顯得過于粗糙、野性,甚至造成讀者理解的困難。劉慶邦在處理運用來自民間的語言時是很講究的,“俗”的表現方式也是極有分寸的。如《小呀小姐姐》對羅鍋子弟弟平路驅雞、罵雞的描寫,是用敘述人語言轉述的。這是一段日常生活小事的描寫,用的是極其簡潔樸實的本色化語言,有幾分俏皮風趣,令人忍俊不禁。農家頑童那股子野性、倔勁活脫脫躍然紙上。若將口語中“罵雞”的語言原封不動地寫出,那必定給人一種過于粗俗之感,但經敘述人轉述,就化腐朽為神奇,既沒有改變原味,又顯得干凈和文雅多了。劉慶邦對少兒向來持肯定贊美態度,出于詩意化的需要,他把少兒的語言作了純凈化處理。
審美化還體現在小說敘述語言的詩意。敘述語言是敘事作品中使故事得以呈現的陳述語句本身,也就是作者為表達寫作意圖而使用的敘述、描寫等語言手段,它直接影響著作者表情達意的效果和讀者進行接受的效果,凡是優秀的作家,無不在這些方面刻意追求。劉慶邦的短篇小說都是從生活中捕捉一個人、一件事,或一個場景,娓娓道來,雖沒有驚天動地的故事,也沒有委婉曲折的情節,敘述語言簡練含蓄,朗朗如白話,但卻總是能夠讓人感到一種細微而美妙的韻味,這就是他的敘述語言的魅力。如《野燒》中這樣描寫一條黃狗:黃狗似乎也認為自己這樣空嘴而歸對于三位貪吃的哥子不好交賬,它顯得很抱歉,遠遠地就塌下眼皮,低下頭,前腿一伸,臥倒在地,自我解嘲似地回過頭來啃自己的背。這樣的文字描寫,描神繪物,宛在目前,如同中國畫中花前月下必有一蝶一蟲一樣,在意境的寧靜平和中,增加了畫面的動感,強化了視覺效果。《曲胡》中也不乏優美雅致的語句:“秋葉飄零的夜晚,月白如霜,琴聲悠悠揚揚傳來,如泣如訴,使好多善良的農人癡癡呆呆,嗟嘆不已。”“三月春風戶外飄,柳條擺動,麥苗起伏,塘邊的桃花花蕊微微顫動,托春風捎去縷縷清香。”上述描寫典雅而通俗,有詩的意境、詞的節奏和散文的韻律,同時也與小說主人公凄美的愛情和諧一致。這份詩意更多的時候是素樸的、自然的,且看幾篇小說的開頭:
“清明節快要到了,地上的潮氣往上升,升得地面云一塊雨一塊的。趁著地氣轉暖,墑情好,猜小想種點什么。”(《種在墳上的倭瓜》)
“太陽升起來,草葉上的露珠落下去,梅妞該去放羊了。”(《梅妞放羊》)
“麥子甩穗,豌豆開花,三月三到了,三月三是柳鎮的廟會。”(《春天的儀式》)
這樣的開頭與汪曾祺的手法極其相似,開門見山,直入話題,用的是純自然的語言,自然得如日出日落、花開花謝、春雨冬雪一樣應時而至,于平淡中氤氳著素樸的詩意。
誠如劉慶邦所說:“我深信一個寫作者的價值就在于他對這個世界個性的獨立的表達。”作家在形成自己對生活的獨特體驗與發現之后,就要努力使小說的語言具有個性。反之,小說的語言個性又在某種程度上決定著小說的存在個性。劉慶邦鄉村題材小說的個性魅力即來自作家對鄉村生活充滿了審美理解的感受與關注,也離不開其地方化、本色化、審美化的個性文學語言。
參考文獻:
[1] 劉慶邦:《民間》,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 劉慶邦:《河南故事》,昆侖出版社,2004年版。
小說語言特征范文第5篇
關鍵詞:趙樹理作品;民間;民間視角
趙樹理的小說從始至終站在農民的立場上,以民間文化為本位來進行文學創作,力圖真實的反映農村、表現農民現實生活。他運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立足農民的立場,真實的表現了解放區農民大眾的愿望,并運用山西農民最熟悉的語言和形式,講述了一個個通俗易懂的故事,從而博得了普通農民大眾的真正認同和喜愛。以下主要探討趙樹理作品的民間視角。
一、 人物綽號的使用
翻開趙樹理的小說,有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借著自己的綽號走進讀者的視野,留在讀者心里。可以說這里綽號是人物性格的鮮明標志,綽號對人物性格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小腿疼”是一個五十來歲的老太婆。她的小腿常因時因事因地而疼,“高興時不疼,不高興時就疼”,逛廟會、看戲、串門串戶的時候不疼,她的丈夫死后兒子還小的時候,有好幾年不疼,一給孩子娶媳婦就疼起來,入社后凡活好干的時候不疼,不好干就疼。因此人們送她的綽號是“小腿疼”。“吃不飽”是個中年婦女,她為了逃避集體勞動常對人們說:“糧食不夠吃,每頓只能等張信吃完了刮個空鍋,實在勞動不了”,實際上在家里明規暗訂條約,捉弄虐待自己“過度時期”的丈夫。“小腿疼”“吃不飽”這樣的綽號簡直讓讀者真切地感受到農村中落后的潑婦身上好吃懶做,損公肥私,損人利己,偷奸耍滑的性格。再如《三里灣》中的“使不得”,真名叫王申,是一個“被土地牢牢束縛著”的莊稼人,他熱愛土地,熟悉農耕精通農作,特別是別人做過的活,他總得再修理修理,一邊修理還一邊不停地說著“使不得,使不得”,“借用別人的什么家伙”,也是一邊用著一邊不停地嘮叨“使不得,使不得”。于是人們給他送個綽號“使不得”。這綽號浸透著王申老漢做起農活那種精益求精的精神,凝聚著王申老漢對生活認真嚴謹的態度。
二、婆媳關系的敘述
民間的婆媳關系是趙樹理較為注重表現的一個方面,這種關系雖沒有權利關系那樣復雜,但也蘊涵著一些深刻的東西。在婆媳關系的敘述中,趙樹理更擅長的是對婆婆的刻畫,她們身上沉積著異常復雜的文化因素,她們既是父權文化下的被壓抑者,又是壓抑同性的施虐者,既是父權文化的犧牲者,也是父權文化的寄生者。婆婆身上更多地包含著民間社會的生存密碼,而趙樹理對這些民間密碼有著豐富的知識。《登記》中的小飛蛾嫁給張木匠之前喜歡的是保安。張木匠的母親得知后給兒子出主意:“人是苦蟲!痛打一頓就改過來了!”因為她“年輕時候也有過小飛蛾和保安那些事,后來是老木匠用這家具打過來的”。張木匠母親年輕時所受的折磨就成為她折磨另一個女人的經驗,她用自身的悲劇造成了小飛蛾的悲劇。在封建社會,女性處于社會的最底層,封建的倫理道德壓制了她們作為一個獨立自由的人的尊嚴,她們成了家庭或男人的附屬品。當受氣的媳婦熬成婆后,封建倫理的受害者也開始參與害人,成為封建文化的幫兇。“男人有男人的活,女人有女人的活,”《傳家寶》李成娘的話真實地道出了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就是“夫在從夫,夫死從子“,自己完全沒有獨立的地位。
三、 喜劇情境的創設
趙樹理小說中的喜劇情境,是翻身農民歡樂情緒的外在表現形式,是帶著時代的特征的,因為在作家寫作的時代,農民已經在黨的領導下進行偉大的斗爭,他們開始對自己的力量表現出信心。趙樹理的幽默是勝利者發自內心的歡樂笑聲,是一種勞動者樂觀主義精神的體現。趙樹理創造喜劇情境的獨特性,就在于他總是努力的探索、發掘著生活中常被人們忽略的喜劇因素,并把它移植到筆下的人物身上,塑造出嶄新的人物形象,使之成為美戰勝丑,正義戰勝邪惡的一種力量,或者成為淳樸、善良、正直、樂觀等品德性格的化身。《套不住的手》中的陳秉正那雙看起來“真像是用樹枝做成的小耙子”的手,鬧出了一連串的笑話“別人害怕跟他握手,因為“被他握住像被鉗子鉗住那樣疼”,兒孫們為他買了一雙毛線手套,但一戴上很快就被撐破了;把手套塞在口袋里卻一次又一次地丟掉……。通過這些富有喜劇情境的細節描寫,一位老農民憨厚勤勞的秉性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在這里喜劇情境就表現為對優秀品德的熱情謳歌。
四、小說語言的口語化
趙樹理小說語言最大的特色便是源于百姓的日常口語,這在人物語言和敘述描寫上是統一表現的。在趙樹理的小說中,人物的言語和對話都是具有鮮明的口語感染力和個性特征的。首先,農民群眾的語言都是樸素而真實的,例如《登記》中小飛蛾挨了打后,對保安送給她的羅漢錢痛訴情感:“要命也是你,保命也是你!人家打死我我也不舍你!咱倆死活在一起!”語句雖直白,但顯示出人物熾烈的情感。而且,趙樹理十分注重人物語言的個性化,讓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詞語、語調、方式表達。例如二諸葛這個信奉陰陽八卦的老迷信說的是“命相不對”、“恩典恩典”,善于奉承的世故之人張得貴就愛說“慢待慢待”、“你老人家”,官僚作風的王聚海總是拿腔作勢地指點“鍛煉鍛煉”,等等。再次,描寫環境時,采用的都是百姓慣用的詞匯和語言習慣。例如,在《李有才板話》中,他是這樣寫道:“閻家山這地方有點古怪,村西頭是磚樓房,中間是平房,東頭的老槐樹下是一排二三十孔土窯,地勢看來也還平,可是從房頂上看起,從西到東卻是一道斜坡。”白描的手法沒有精致優美的修辭,“古怪”、“村西頭”“一道斜坡”等口語化的敘述就表明了村子中的貧富差距和階級劃分,簡實卻蘊含內容。(作者單位:貴州大學人文學院)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