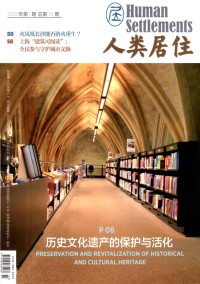人類學研究方法論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人類學研究方法論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人類學研究方法論范文第1篇
關鍵詞:音樂人類學;思潮;方法論;系統性;思辨
“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隨著1980年南京“全國第一次民族音樂學學術研討會”的成功舉辦,音樂人類學逐漸為中國學術界所熟悉,近年來呈方興未艾之勢。正如洛秦所說,音樂人類學似乎成為了“顯學”。
音樂是一種文化,還是指音樂現象本身?音樂與文化存在著什么樣的關系?我們該如何去研究音樂?在西方,有關此類問題的闡釋可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音樂學派代表人物胡德認為:“民族音樂學領域的研究主題是音樂,但是與這個主題基本上不同而又互相依存的不妨包括一些有關這些學科的研究,如歷史、人種史、民俗學、文學……”[3]人類學派代表人物梅里亞姆則主張“對文化中的音樂的研究”,將音樂放入整個文化中去探討。此后,恩凱蒂亞又提出通過音樂去研究文化的中介性概念。那么,我們該如何面對,并實時地了解西方音樂人類學的最新動態?音樂人類學這門學科的建立,最早是從西方興起的,所以,翻譯與閱讀有關的原著就顯得相當必要。近年來,國內許多學者做了許多有益的嘗試,這方面的譯著有《民族音樂學(比較音樂學)譯叢――音樂與民族》①《民族音樂學譯文集》②《音樂詞典詞條匯輯――民族音樂學》③《西方民族音樂學理論與方法》④等,不一而足。這些譯著為我們學習、掌握音樂人類學的方法論提供了很大的幫助。音樂除了形態以外是否還蘊含著深層次的內容?我們如何透過音樂本身去剖析它的文化特質?這些問題都可以從這些譯著中找到答案,省去了我們查找原始資料的痛苦。讀一本好的譯著,猶如與原著作者近距離對話一般,從中也能使我們領略到漢語的魅力。最近,一次偶然的機會,筆者在圖書館翻閱了上海高校音樂人類學E―研究院資助出版的《音樂人類學:歷史思潮與方法論》(以下簡稱《湯著》),雖然是一本翻譯著作,但書中也閃爍著作者思辨的火花。
下面擇其要點,不揣淺陋,談談筆者讀《湯著》的感受與思考,以饗讀者。
一、博學睿智 善于思辨
雖然是以翻譯為主的著作,《湯著》不囿于資料的堆積,而是帶有一種思辨的“再論證”。 一本著譯需要閱讀大量來自其它國家的文獻資料,但湯亞汀先生并沒有使自己的頭腦成為別人思想的跑馬場,而是將這些方法論運用到自己的“他鄉田野”和“家門口田野”的研究當中,例如第十章“城市音樂人類學”中的“英國東北部的民間音樂生活”,及第十一章 “上海猶太難民社區的音樂生活”研究,都是作者最近學術成果。這種嘗試也是《湯著》與國內其它譯著的區別所在,并為自己的研究增加了一種厚重感。正所謂“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作者的這種創新不僅有力地回擊了西方學界認為中國學術界“只有材料堆積,少有新方法和新視角,也很少通過方法演繹出理論”的觀點。同時,也給中國的音樂人類學研究注入了一顆強心劑。主位與客位的問題是民族音樂學研究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湯亞汀認為沒有純粹的主位與客位,它需要研究者具備“雙重視角”,既要有局外人獨特的視角,也要尊重局內人的話語,這樣才能更好地理解所要研究的對象。此外,從兩者的分析模式中我們又可得出什么啟示?西方學者是如何研究中國音樂?他們有哪些我們所忽略的內容或我們沒有的客位方法?我們能否用純粹的“主體”觀來研究自己國家的音樂?我們研究西方音樂是不是一直太“主位化”了?是不是也應該來點“客位化”?一系列的問題無不閃爍著作者思辨的光輝。
二、立足前沿 關注當下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后現代主義對現代主義產生了巨大的沖擊,其中一個鮮明的特征就是“反思”,反基礎主義、反對理性,消除現代性,否認整體性、同一性,注重人性化、自由化,注重體現個性和文化內涵,關注時代,關注現實。音樂人類學作為一個方法論,它兼收并蓄各個學科的方法與思想來充實自己,近年來音樂人類學也受到后現代思潮的影響,在社會性別、亞文化群體、背景研究等領域,已有了基于當代人類學的理論框架里的認識論上的重新取向。“西方人類學領域中的后現代主義,通常以反思傳統民族志和倡導實驗民族志為其鮮明特征,把研究的重點放在民族志的寫作風格和修辭方面。”[4]后現代主義對文化人類學的基礎――田野民族志進行了反思,對功能主義把社會文化當作一個整體去研究的做法提出了質疑,因為這種整體研究在后現代主義看來容易忽略對個體的關注,那么關于民族志的描寫還值得依賴嗎?后現代主義的這些思想,從上個世紀80年代后期也進入了民族音樂學領域。在第七章“后現代思潮”中,《湯著》對美國《民族音樂學》雜志中的《專題論叢:音樂實踐的描述與描述的實踐》進行了評介。音樂人類學由于受到后現代思潮的影響,在關于人類學中“他者”的認識上有了新的取向,給“他者”以足夠的重視,“他者”被賦予主體地位,而非客體地位,這時,個性和亞群體的現實已更重要,共性再度讓位于個性。
在西方的民族音樂學研究中,過去很少注意女性與男性的差異,對婦女的音樂活動研究也沒有引起足夠的關注,后現代主義致力于消除性別、種族、階級之間的界限的思想,為西方民族音樂學注入了活力基因,也為女性主義迎來了一次新的發展機遇。《湯著》以“社會性別與音樂”為題,對西方民族音樂學社會性別研究的方法論及社會性別意識形態對女性音樂創造的影響都給予了重點關注。“人類社會的權力有壓迫與平等之分,價值觀有高低之分,社會性別行為有男性性征與女性性征之分,我們需要創造一種綜合模式來研究音樂活動。”[5]
三、旁征博引 厚積薄發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引用和借鑒國外先進的理論研究成果為我所用,是我們學習的一種途徑。作為一本著譯,《湯著》從源頭做起,引用了大量西方音樂人類學的文獻資料,作者這種對資料“竭澤而漁”的收集方式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在“學科定義與名稱”一章節中,作者參閱了國內外諸多學者和辭典對ethnomusicology的不同解釋,并通過縝密的思考與分析,認為ethno(或ethnic)現在已經超越“民族”的界限,進入了“人類”這一更加廣闊的范疇,因此,可用人類音樂學或文化音樂學來命名該學科,以結束該術語原譯(民族音樂學)所造成的混亂。
《湯著》收錄了作者1990年至2004年編譯與撰寫的論文,是作者近年來部分研究成果的一個集中展示。此著共計約45萬字,字里行間凝聚著作者的智慧與才華,是一部心血之作,其間的辛酸是不言而喻的。湯亞汀先生從上世紀70年代后期就翻譯了《非洲音樂》一書,并為《中國大百科全書》撰寫了“非洲音樂”等條目。為了拓寬自己的知識面,1994年赴英國研修音樂人類學,學習期間應他人之邀,為英國《新格魯夫音樂與音樂家辭典》(第二版)撰寫了“中國猶太音樂條目”。湯亞汀先生現為上海音樂學院公共基礎部外語教研室教授、譯審、上海師范大學音樂學院兼職教授、上海翻譯家協會會員,出版的譯著與著作主要有《20世紀音樂》《韋伯恩》《民族音樂學與現代音樂史》《城市音樂學觀》等。有了這些前期的鋪墊,才最終促使了《湯著》的問世。
目前,市場上相關的譯文層出不窮,但翻譯的質量卻顯得參差不齊。某些所謂的專家翻譯的著作,聽起來如雷貫耳,細讀起來卻味同嚼蠟,沒有絲毫的價值,一來浪費資源,二來誤導讀者。西文的翻譯不僅要考慮語音、文字、構詞法、句法等諸多方面,同時,地域的文化差異也是必須要注意的。某些學者為了顯示自己的翻譯水平如何如何好,喜歡故弄玄虛,翻譯的文章用一些讓人費解的詞匯,弄的讀者一頭霧水。這些“天書”不僅使讀者看不懂,浪費資源,而且也沒有很好地將原著的精神展現出來。“美學論文,乃至一切文藝學研究和批評文字,不論它的思想多么深邃,不論它的表述多么高妙,無一例外都是人寫的,也是寫給人看的,都是人類交流思想、發展學術的一個方式,因此必須具有起碼意義上的可解性和可讀性”。[6]美學論文如此,譯著又何嘗不是這樣,目的都是要給讀者看的,最起碼要讓業內人士讀明白,如果這個要求都做不到,還不如當個擺設放在書柜上,以顯博學。作為一本以譯文為主的著作,《湯著》措詞嚴謹,文筆流暢,使我們讀來也甚感舒服。《湯著》的成功出版,究其原因,筆者認為主要有:一方面是湯亞汀先生對西方音樂人類學發展動態的積極關注,再者是作者得天獨厚的外語翻譯水平,并克服了語言與文化的地域差異,在準確性與可讀性之間找到了一種平衡。
作為一個翻譯家,湯亞汀先生翻譯了許多具有影響力的作品,作為一個學者,對“他鄉田野”與“家門口田野”的研究也頗有見解。對于一個業已退休的教授來說,功成名就,本可隱居山野,但作者并沒有對取得的成績沾沾自喜,仍然懷著一顆對知識渴求的熾熱之心,繼續自己的研究,他當前的研究課題是《上海工商局交響樂隊史:1870―1940年代》《音樂人類學理論與個案15講》。作者這種對學術孜孜以求的精神,為年輕的學者樹立了榜樣。
《湯著》的出版不僅為我們打開了思想之門,而且也方便了讀者,減輕了我們找原始資料的痛苦,使我們在學習上少走彎路,從而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當然,《湯著》也存在著不盡完美的地方,如對日本學界的關照略顯不夠。一些西方著作是通過日譯本傳入中國的,同時日本學者通過自己的實踐所得出的民族音樂學理論對中國也有較深影響。瑕不掩瑜,雖然《湯著》關注更多的是對西方音樂人類學歷史思潮與方法論的梳理,但這些問題絲毫不影響該著作的價值,我們也不能苛求一本譯著囊括所有相關的資料。
注釋:
①上海音樂學院音樂研究所、安徽省文學藝術研究所合編
《音樂與民族》,1984年版內刊。
②董維松、沈洽編《民族音樂學譯文集》,中國文聯出版公
司1985年版。
③人民音樂出版社編輯部編《音樂詞典詞條匯輯――民族音
樂學》,人民音樂出版社1988年版。
④張伯瑜編譯《西方民族音樂學理論與方法》,中央音樂學
院出版社2007年版。
參考文獻:
[1]湯亞汀.音樂人類學:歷史思潮與方法論[M].上海:上
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08.
[2]沈洽.民族音樂學在中國[J].中國音樂學,1996(3):5.
[3]楊民康.音樂民族志方法導論[M].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出版
社,2008:11.
[4]瞿明安.西方后現代主義人類學評述[J].民族研究,2009
(1):31.
[5]湯亞汀.音樂人類學:歷史思潮與方法論[M].上海:上
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08:199.
人類學研究方法論范文第2篇
在人類學研究領域,極端的后現代民族志是 20 世紀中后期開始在西方人文社科領域廣泛流行的后現代思潮在人類學研究領域的集中表現,它 “從反思以 ‘科學’
自我期許的人類學家的知識生產過程開始萌發”;,對人類學學科領域經歷了幾代人的努力才得以建立完善的學科理念、學科方法以及一整套嚴格的田野作業規程,甚至對學科的知識論基礎都提出了全面的反思、批判和質疑。學術史的發展表明,任何學科的發展和完善從來都離不開學科內部的自覺反思、批判和質疑,人類學學科內部的事實也表明,發端于上世紀中后期的這場后現代民族志思潮,對于推動人類學學科的發展和完善確實碩果累累。它催生出了人類學的文化批評這一璀璨奪目的成果。
人類學大量的文化批評實踐,如跨文化并置、化熟為生的批評策略等,其意義已經遠遠超越了人類學的學科界限而廣泛影響到了當代人文社科研究的諸多領域。從較寬泛的意義上說,格爾茨的解釋人類學也是這一思潮的產物,它自身也是在對傳統人類學進行深刻反思的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然而我們看到,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一些人類學家在這一反思中走向了另一極端,走向了極端的懷疑主義。這種極端的懷疑主義對于人類學學科的生存來說,其危害是致命的。本文就打算對格爾茨的“深描說”;在后現代民族志極端懷疑精神對人類學學科危害的情境下所具有的 “解毒”;功效進行一些粗淺的分析,從而揭示其重要的當代意義和價值。一格爾茨的 “深描說”;主張把族群文化事象納入其生存的文化系統中進行一種“微觀”;的考察,以確定其在文化系統意義結構 ( structure of signification) 中的位置,從而獲得對該文化事象的理解和深層次解釋。從這個意義上說,格爾茨認為民族志描述應該具有四個方面的特點: “它是解釋性的; 它解釋的是社會話語流 ( the flow ofsocial discourse) ; 這種解釋努力把 ‘說’ 的話語從轉瞬即逝的狀態中解救出來,以可供閱讀的形式固定下來”;,另外 “它還是微觀的”;。
20 世紀 60 年代以前,以馬林諾夫斯基等人為代表的人類學家,正是不滿足于人類學早期那些探險家、傳教士以及旅行者憑借那種浮光掠影的觀看獲得的淺表印象的所謂考察,或者僅僅依據從道聽途說中獲得的奇聞軼事來對異文化做獵奇性質的報道,開始親自長時間地深入田野,與“野蠻人”;一起生活,對他們的文化進行系統的觀察、記錄,并在這些實地考察資料的基礎之上對其文化進行系統描述。這樣,經過長期努力,這批人類學家逐步在公眾的心目中為人類學學科樹立起了 “科學”;的形象。經過幾代人的努力,這種謹嚴的學科形象似乎從事實基礎到方法論,再到話語表述都是無可懷疑、不可撼動的。然而,20 世紀 60 年代末,人類學內部開始對人類學家的知識生產過程展開反思,這種反思首先觸及到的是人類學的學科倫理。
這種反思指出,人類學在其自身學科發展歷程中,“科學研究”;與 “權力話語”;始終是糾纏在一起的,許多人類學家的田野工作直接為殖民政府的殖民統治甚至戰爭服務。接著是馬林諾夫斯基日記的發表,拉比諾 《摩洛哥田野作業反思》的發表等一系列事件,它們對人類學家的田野作業過程本身進行全程 “曝光”;。這一系列的 “發現”;,摧毀了人類學家權威、客觀、中立的形象,所謂客觀的人類學知識也不過是為某種 “權力話語”;統治服務的工具,人類學知識的生產過程中充滿了隨意、不確定甚至肆意歪曲的因素。
至此,后現代民族志這種極端的懷疑直指人類學知識生產的根基: 人類學研究、人類學的田野考察能不能真實、客觀地“再現”; 其 研 究 對 象——— “異 文 化”; 的“本來面目”;? 所謂的人類學學科的 “科學性”;體現在哪里? 這其實是長期以來困擾西方哲學的本體論問題在現代哲學知識論領域內的一次集中爆發,這種爆發逐步蔓延到了包括人類學在內的所有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于是,“現代認識論的觀念于是便轉向了對主體表征的澄清和判斷”;,這也是拉比諾的解決之道,人類學的 “社會事實”;
人類學研究方法論范文第3篇
一、田野考察研究方法的意義
所有實地參與現場的調查研究工作,都可稱為“田野研究”或“田野考查”。田野考查涉獵的范疇和領域相當廣,舉凡語言學、考古學、民族學、行為學、人類學、文學、哲學、藝術、民俗等,都可透過田野資料的收集和記錄,架構出新的研究體系和理論基礎。北京大學王銘銘教授曾在他的專著《人類學是什么》中提出“參與當地人的生活,在一個有嚴格定義的空間和時間的范圍內,體驗人們的日常生活與思想境界,通過記錄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來展示不同文化如何滿足人的普遍的基本需求、社會如何構成。”這便是田野考查,同時也是一個人類學家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
田野考查被公認為是人類學學科的基本方法論,也是最早的人類學方法論。它來自文化人類學、考古學的基本研究方法論,即“直接觀察法”的實踐與應用,是研究工作開展之前,為取得第一手原始資料的前置步驟。在人類學的研究過程中,田野考察工作無疑是一項最基本的研究工作,也是最為基本的研究方法。長期以來,田野考察工作幾乎是正確認識研究對象內容、形式、規律的唯一途徑。
美國生物學家斯托金曾把田野工作稱為“人類學家的前期必備訓練”。所有的人類學者都知道,是田野訓練造就了“真正的人類學家”,而且人們普遍認為,真正的人類學知識均源自于田野調查。中山大學教授陳春聲就提出在田野調查中,可以搜集到極為豐富的民間文獻:可以聽到大量的有關族源與村際關系,以及和社區內部關系等內容的傳說與故事。他認為對這些口碑資料進行相應的闡釋,就可以揭示出文獻記載所未能表達的社會文化內涵。陳春聲教授立主從鄉民的情感和立場出發去理解所見所聞的種種事件和現象,也只有這樣才會給我們帶來一種只可意會的文化體驗與新的學術靈感。美國斯坦福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古塔弗格森提出“決定某項研究是否屬于‘人類學’范疇的重要標準實際上就是看研究者做了多少‘田野’”。田野工作已經成為人類學知識體系中的基本組成部分。方李莉教授在她的論文《走向田野的藝術人類學研究》中指出:“要理解藝術人類學這門學科,首先要理解藝術人類學的田野工作方法”。
李立新教授在他的專著《設計藝術學研究方法》中提到:“對于設計藝術學而言將人類學的視野和方法引入研究之中,表明設計正是極其重要的人類文化現象。在充分吸收人類學田野工作經驗的同時,針對設計藝術學自身的特征,可以歸納為三個基本的研究觀點:①設計藝術學田野考察應該強調人而不是物,考察人在生活中如何創造和使用這些物的;②應該強調整體觀而不是單一現象,不把握住生活整體就不能理解物的意義;③應該強調跨文化的比較研究,因為每一種設計的形成都會與其文化有關。”240從中我們不難看出,“整體觀”就是要從社會文化和人類行為的各個方面和層次去研究社會文化元素和行為,而“跨文化比較”就是要從對不同的文化進行廣泛的比較研究中還原出由人的行為所構成的社會文化藝術現象及其內部隱藏著的深層結構。設計藝術學田野考察的研究目的就是以全面的方式理解人這個個體,正如羅薩爾多教授提出的那樣,即“通過對他者的理解,繞道來理解自我”。
二、“設計田野考察”內在的理論鏈條
1、由“物品主體——行為主體——思想理念”①構成的設計藝術田野考察的結構模式
李立新教授指出:“在對‘物品主體’做調查時,也應對‘行為主體’做深入的調查,同時還要關注‘思想理念’的各個方面。”245這是一個對人類生活的綜合考察過程,要以物為起點,關注人,關注人的行為,關注思想的產生、發展、形成的過程,關注價值觀的產生和價值評價體系確立,關注社會、文化的發展歷程。
從“原始”到“現代”,從“鄉村”到“城市”這樣的擴展,要求我們對“田野”這一充滿了意味的概念加以重新認識。“田野”在時空上的意義不再是原始、鄉村、邊寨、過去之類的理解,而是“指一切離開書齋、案桌而面向社會藝術生活實踐的現場”244
2、由“‘他者’的理解——文化的‘自我’——設計的‘自我’”
“雖然我們過去強調在調查中要注意這些工藝物品在當地人生活中有什么意義,而不是對考察者有什么意義。但現在我們關注的是,要在了解這些物品對‘他者’生活意義的同時,還要注意對‘自我’的意義,這個‘自我’不是考察者個人的‘自我’,而是文化的‘自我’,是現代的、整體的、設計上的‘自我’”。246那么,對于“文化”與“設計”的正確定位和認識也就是對田野考察目的和意義的重新認識。田野考察的實質就是從“特殊潛入普通,一度潛入永恒”的過程演變,在這里“特殊”與“一度”強調的是田野調查的切入點,即對“他者”的理解,而“普通”與“永恒”強調的就是在社會、歷史、文化的選擇中形成的設計的價值體系。德國哲學家文德爾班教授曾提出:“我們可以把一句古話稍微改動一下說:人是有歷史的動物。人的文化生活是一種世代相承愈積愈厚的歷史聯系:誰要是想參加到這個聯系中去通力協作,就必須對它的發展有所了解。”要做到對“文化生活”的全面了解,就必須深入到社會的廣闊“田野”中,從對“如實描寫的范式到反思‘自我’的范式”246的轉變,也就是從人的個性、自由、藝術、感性與社會、文化、經濟的關系出發來分析人的現象和人類社會文化,從而把握整個人類社會及其歷史發展中的設計藝術過程,并以此作為設計的立足點。正如德羅伊森在其專著《藝術與方法》中談到的:“作為我們研究對象的并不是過去的事件本身,而是它們的遺留物,以及它們的觀念。遺留物之所以是遺留物僅僅是基于歷史的考慮。它們作為完整的東立地存在于現在的世界。它們中的許多東西,盡管支離破碎,同時卻提醒我們,它們曾跟現在很不一樣,比現在都活躍和重要;另一些東西則變了形,仍然在一種活躍的現實中起作用;另一種東西則面目全非,幾至無法辨認,而融入現在的存在和生活中。”285田野考察所面對的不是無情的、僵化的物質環境與人類遺存,而是一幅鮮活的人類生活圖景。這些人類生活設計的遺留物,“從表面上看是物質形態的設計,他的存在……必須通過一種文化形式來轉化,這種轉化將一些雜七雜八的造型色彩、一堆看似毫無生氣的物質形態構筑成一個有序的能夠表達人類情感并有較好實用功能的物品,由此處理成一幅優美的生活場面,在人的意識中形成一個完整的價值體系。在這一過程中,設計藝術的物質性與精神性以文化因素賦予其形式和內涵的不同特征,并不斷深化,直至與整個社會歷史的發展一致,構成統一完整的整體。”23
3、設計田野考察的三個階段
(1)準備工作階段
(2)實地考察階段
(3)整理分析階段
三、田野考察具體的研究方法
1、田野考察的基本方法
(1)直接觀察
直接觀察就是指考察者進入實地,深入到被考察對象的日常生活和工作行為的過程中進行的觀察。英國社會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曾把這一方法叫做“參與觀察”,俗語言:“百聞不如一見。”因此,參與觀察、直接觀察至今仍是田野考察的最基本的方法。“在社會學研究中,有研究者裝扮成流浪漢,浪跡街頭,親身體驗,甚至取得當局同意,裝扮犯人,進入監獄觀察交談。這種參與性觀察能獲得極為真實的資料。”258在設計的田野考察中,通過直接觀察一些傳統技藝的制作過程,捕捉其中的關鍵點,挖掘技巧背后的其他材料,也是獲得生動可信的第一手材料的極佳途徑。
(2)深度訪談
“深度訪談一般有兩種性質:一種是正式訪談,一種是非正式訪談。”259田野考察所要面對的考察對象往往具有十分特殊的歷史背景,不是三言兩語就能夠道明的,所以只有通過正式訪談,深入其里,才能從中概括出所要收集的重要信息,田野考察的深度訪談應以正式訪談為主。在深度訪談中,“研究者需要從被訪者日常生活的角度去了解、觀察其行為目的過程及意義。”261
(3)實物測量
在設計田野考察的實際工作中,對“遺留物”的考察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田野考古工作流程》規定(見圖一),調查必須實地勘察,對其全貌和重要的局部攝影、繪圖,重要的碑刻、題記等應取拓片,并按《田野考古調查記錄表》所列項目逐一填寫,有的須寫出詳盡的文字記錄”261
(4)資料采集
資料采集是設計田野考察的主要工作,一般應該注意以下幾個事項:
①盡可能多地收集調查內容背后的各種現象資料,使該主體資料內容豐富并具有完整性。“完整性”的提出對于主體資料內容的豐富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即使當代人講述在他們時生的事件,在這些事件中,他們眼見耳聞的又有多少呢?一個人的視聽覺把握到的總是事件的一部分、一個側面和一種趨向。”261怎么把一部分、一個側面和一種趨向轉換成鮮活的、多側面、立體的、全方位的物質資料,是設計田野考察工作資料采集的重要步驟。德國歷史學家德羅伊森曾在《藝術與方法》一文中提出:“我們關于古代的知識多么膚淺和不可靠,在具體問題上我們獲得的觀點是多么瑣碎和有限,這些即使在我們研究這樣的時代時也會意識到。”286因此資料采集的“完整性”不能僅僅局限于“遺留物”本體的完整性上,而是應該更多的去關注“遺留物”背后的社會文化現象。
②要善于捕捉新內容,著重收集新資料
③注意收集與考察內容不同于其他地區同類主題的資料
④注意所收資料的可信度與準確性。
(5)歷史溯源
作為人類生活的必需品,在其漫長的歷史演變的過程中,一部分物品消亡了,而大部分物品繁殖衍生,復雜多變,延續至今。設計田野考察要做的就是對“尚存”、“不存”與仍在“使用”的物品作認真的梳理和闡述工作,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過的那樣,在歷史過程中技藝可能失傳許多次,而又重新發現……歷史中存在著種種累積效應。即使斯賓格勒也被迫承認,當各種新文明建立在就文明的廢墟之上時,它們的特征部分地取決于新的生命吸收、適應并圍繞著舊文明的廢墟而生長的方式。這就必須要追溯歷史淵源。然而溯源過程是一個有趣的過程,一方面要比照田野考察中所得的數據與結構,一方面要對圖像資料作出合理的判斷。
(6)科際整合
方李莉教授在運用社會學的方法對傳統手工藝陶瓷社區做了深入細致的個案研究之后說:“我在考察中力圖避免傳統的那種孤立的考查方式,而是把一種社會事實放在一個具體的社區和一個完整的‘情境’中來理解。”話中所提的“避免傳統的那種孤立的考查方式”主要是指要在科際整合思想的引領下,以廣闊的學術視野下將眾多學科整合起來進行綜合考察,從而來研究同一對象。“情境”主要是指將傳統的民間手工藝建構在整體的設計歷史的大構圖之下。
2、田野考察中如何凸顯“人”
設計藝術的普遍特征是“用與美”的統一,著名人類學家喬建教授提出,到實際生活中去,探求藝術的有用還是無用,美還是不美,應該是“以人為本”,①顯然,設計藝術的田野考察要關注的是人,關注人是如何在生活中創造并使用這些東西的,圍繞這些物品產生過怎樣的關系,人們是如何把這些變成了傳統又怎樣繼承下來的,并發展出新的物品的。
如教授對“中國女紅文化”(見圖二、圖三)的研究中著重于整個手工藝主體——女性生活的調查,研究女性生活的藝術化表達,女性藝術語言特征以及傳承方式包括女性勤儉、賢惠品格和她們的情感與理想;又如安麗哲對“黔西長角苗人服飾的考察”中,不止關注服飾作品的圖案、制作技術、方法,而是重點考察服飾制作的主體——婦女的婚姻觀念的變化在傳統民族服飾傳承中所起的作用;再如菅豐對“浙江象山竹根雕”(見圖四、圖五)的調查研究中,同樣不是去關注竹根雕本身,而是從一開始就關注“人”,這一群竹根雕藝人是怎么產生的?藝人的名號是如何被承認的?藝人與政治、權利上下層的互動關系?藝人與社會組織之間的關系如何?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
因此在田野考察的過程中,我們應該著重強調和重視的就是作為創造主體的“人”,正如李立新教授所提出那樣:田野考察必須要選擇凸顯“人”與“結構關系”這樣的方法,透過具體、微觀的“人”及其行為來認識特定的設計藝術活動的社會、政治、文化編碼,理解其中的意義,而不是只拘泥于作品本體的形態以及制作過程。
3、田野考察的民族志方法運用
民族志是早期人類學家的研究結果,有兩個過程,一個是田野作業,一個是文本撰寫。所以,它既是一種方法,也是一種文體,由此也就構成了民族志的雙重性。
對于設計的田野考察來說,除了要對物品本體的考察外,還要觀察人們日常生活的總體。而“民族志”的方法強調的正是一種“整體觀念”,一個民族只有把文化看成是一個系統,并考察這一系統的方方面面的時候,才能準確的了解物品本體的內在含義。
4、田野考察的比較研究法
在田野考察中,對于田野工作所得到的事實,研究者要通過比較的方式,做出自己合理的解釋。比較研究可以有一個縱向的歷史發展觀,也可以有橫向的跨文化研究,比如我們對于設計藝術現象的研究更多的是考慮文化對造物影響、人造物之間的相互作用、工藝技術的吸取、借鑒等因素之間的比較關系。通過這些因素之間的比較來分析在設計藝術活動內部所隱藏著的深層的文化結構,這是超越了形式、圖形、色彩這些的表面元素,運用比較研究的方法,從信仰和觀念出發,以文化的傳承為目的的豐富立體的“設計構圖”。
人類學研究方法論范文第4篇
【關鍵詞】民族生態學;美國;蘇聯/俄羅斯;學科比較
【作 者】付廣華,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專業博士研究生,廣西民族問題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南寧,530028
【中圖分類號】C9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11)03-0067-007
A Comparative Study on Ethno-ecologies from U SA and Soviet Union/Russia
Fu Guanghua
Abstract: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compared ethno-ecology from US tradition with one from Soviet Union/Russia based on their theory origins, research objectives, research methods and academic influence Thus makes Condusion that although the ethno-ecologies were born within anthropology or ethnology, and who did the researches were mainly anthropologists or ethnologists, they had great differences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was the difference of meaning of prefix “ethno-” The prefix “ethno-” within Soviet Union/Russian ethno-ecology was only related to “ethnos”, however, within US ethno-ecology, the meaning of the prefix “ethno-” was “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 was a kind of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ic
Key words: Ethno-ecology; United States; Soviet Union/Russia; Discipline comparison
民族生態學是一個跨學科的學術領域,吸引了來自民族學、生態學、植物學以及其他學科的學者參與到其中來。在中國,民族生態學的發展還比較滯后,存在的理論盲點亦比較多,如國內學術界在學理上對美國傳統的民族生態學(以下簡稱“美國式民族生態學”)與蘇聯傳統的民族生態學(以下簡稱“蘇/俄式民族生態學”)之間區分不夠,因此難以整合來自兩個不同學術傳統的學者,從而影響到整個學科的健康、快速發展。美國式民族生態學是在人類學界內部發展起來的,后來才影響到其他學科,從而擴散成一個龐大的學科;而蘇/俄式民族生態學雖然也是由民族學家提倡,但它屬于民族學和人類生態學的交叉學科,是針對民族地區進行的生態學研究。因此,兩種傳統的民族生態學雖有一些相同之處,但相異之處又頗多。本文從理論淵源、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學術影響上對美蘇兩種傳統的民族生態學予以比較,希望能為學科發展略盡綿薄之力。
一、理論淵源
理論淵源最能說明一個學科的屬性,因此歷來學科史的回溯都是指引一個學科發展的必要工作。美蘇兩種傳統的民族生態學雖然都誕生在人類學家(民族學家)手中,但由于在理論淵源上有所區別,才導致了它們之間異同共存的現象。
在美國,民族生態學的誕生有一個發展的歷程。早在1875年,鮑爾斯(Stephen Powers)就提出了“土著植物學”的概念,是今日民族植物學能夠追溯的最早起源。二十年后,考古學家哈什伯格(John W Harshberger)在美國費城的一次學術會議上第一次提出了“民族植物學”一詞。1914年,美國民族學家亨德森(Junius Hendersen)和哈林頓(John Peabody Harrington)在美國民族學局組織的“動物在塔瓦印第安人中的地位”的調查中首次提出“民族動物學”這一新詞[1]。從這一學術史追溯來看,民族植物學、民族動物學這兩門民族生態學的分支學科的誕生都比較早。直到1954年,“民族生態學”這一術語才為康克林(Harold Conklin)首創。康克林通過考察菲律賓哈努諾人(hamunoo)植物術語的內容和結構,證實了民族植物分類的等級本質。康克林提供了第一個人類的自然資源概念的真實洞察,而不像以前的民族生物學研究首先關注的是記錄人類對生物的應用[2]pp846-848)。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前,民族生態學的研究基本上限制在具體的人與動植物關系的研究上,人類學家們花費大量力氣去創建動植物的清單,并記述其使用狀況。雖然這樣的研究缺乏理論的框架,但卻有助于發現傳統社會的動植物分類體系的本質。不過在此之后,由于受到認知理論的影響,民族生態學研究開始轉向民族科學的方法,即把個體視作文化生成體和把語言視為信息編碼的媒介。這樣以來,雖然人類學家的民族生態學研究的主要內容仍是記述動植物分類及其應用,但是其目的卻是試圖依此透視支配人類行為的思維的深層結構。鑒于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具備主位立場、民族志方法、認知的視角等特征,因此被有些人類學家稱為系認知人類學的一門分支學科。還有的學者認為民族生態學的學術譜系要比上述更為龐雜,如墨西哥生態學家托萊多(Victor M Toledo)就認為民族生態學是融合了民族生物學、農業生態學、生態民族志意義上的民族科學以及研究自然資源傳統管理體系的環境地理學等的總學科[3](pp5-21)。最近又有學者聲稱,民族生態學有社會科學、生物科學和闡釋藝術與科學3個父母:社會科學中人類學發展了主位立場等民族生態學研究的基本工具;生態學家和其他生物學家提供了大量的重要的、細節的適應系統的研究報告;闡釋作品展示了反思的必要性和價值[4](pp5-15)。當然,這些都是一家之言。總的來說,美國式民族生態學最初的理論淵源更多地在人類學內部,雖與描寫語言學的認知理論有一定的交叉,但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所有的民族生態學家都具備人類學家的身份。只不過最近一二十年生態學者的介入使得民族生態學的情況發生了一些顯著的變化。這一點將在第四部分中詳述。
民族學人類學研究
與美國式民族生態學一樣,蘇/俄式民族生態學的理論淵源也較為復雜。在蘇聯存續后期,蘇維埃民族學家們認為民族學是一門以研究世界民族為對象的學科[5](p3)。不過,由于民族總是在一定區域內逐漸形成的,受到所在地區生態環境的制約,采用各種方式去適應這樣的自然條件,因此民族文化常常具備適應環境的特點。科茲洛夫認為“可以把處于目前這種狀態下的民族學明確為其研究范圍包括民族共同體這一最穩固和最重要的人們集體生活形式之一的產生和存在的各個方面的綜合性學科。”[6](p215)這樣,摒棄了傳統研究范圍“本位主義”態度以后,民族學家們積極地參加了反映社會需要的新領域的工作,民族生態學的形成正是如此。蘇聯民族生態學的奠基人之一――勃羅姆列伊(Julian Bromley)也類似地指出:“當代民族學由于自己的主要研究課題的多樣性,實際在某種程度上同民族(民族社會)過程各方面的研究都有關系。這對于圍繞民族學所形成的日益眾多的相鄰學科――從民族經濟學和民族生態學到民族社會學和民族心理學,尤其如此。”[7]( p246)事實上,早在1981年,勃羅姆列伊就發表了《人類生態學的民族方面》一文,雖然文中尚未提到“民族生態學”這一術語,但其中關于各民族利用自然環境的特點、各民族對自然環境影響的特殊性等民族生態學原理已在這篇論文中得到充分運用。與此同時,蘇聯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集體編寫的《社會與自然》一書中也已包含民族生態學的許多原理,比如該書強調指出了歷代民族文化傳統對保護生態是有意義的[8]。勃羅姆列伊還在1982年俄文版的《民族學基礎》第三章“非洲各族”單列“地理環境”一目,其中言道:“非洲的地理條件十分復雜,各種自然因素及其區域性配合都很協調,為非洲境內各民族的生存提供了必要的生態條件和相應的食物和技術資源。幾千年來,人們適應自然和征服自然的過程,構成非洲各民族全部經濟文化史的物質基礎。”[5](p155)在借鑒同仁們理論、觀點的基礎上,科茲洛夫充分吸收了來自人類生態學的思想,于1983年正式提出了名為“民族生態學”的學科。科茲洛夫認為,民族生態學是一門由民族學和人類生態學相互滲透而形成的學科。由于其與人類生態學的密切聯系,民族生態學的形成取決于作為人的特殊共同體的民族的特點,而且這一特點表現在生物方面,也特別表現在社會文化方面。民族生態學形成的比較緩慢,是在吸收民族地理學、民族人類學、民族人口學等與人類生態學有關的內容的基礎上形成的。1978年開始的由美蘇兩國民族學家、人口學家、體質人類學家等共同參與的“為提高各民族和民族群體長壽率開展人類學和民族社會學的綜合研究”,對蘇聯民族生態學的形成具有促進作用[9]。
兩相比較,我們可以看出:美國式民族生態學是在人類學界內部產生的,它吸收了描寫語言學的認知理論,變成了民族科學的一個亞領域,后來也受到農業生態學、闡釋學以及環境地理學等學科的影響;而蘇/俄式民族生態學則是在民族學界內部產生的,是由民族學和人類生態學交叉而產生,甚至包含有民族地理學、民族人類學、民族人口學等學科的若干領域,可見其理論淵源之混雜。
二、研究對象
蘇聯民族學家勃羅姆列伊認為:“每個學科的對象是在形成一定傳統的學科實踐中形成的。在確定今天某一學科的輪廓時,不能不考慮到這些傳統……而一個學科研究對象的確定,相應地又同闡明它與相鄰知識領域的相互關系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7](p235-236)從勃氏的上述論斷足可得見研究對象對一個學科的重要性。民族生態學自也不能例外,其研究對象的確定對學科的存續與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自從康克林1954年提出“民族生態學”之后,學者們對民族生態學的研究對象和范圍一直有所爭論。然由于康克林不是特別重視理論上的研討,因此這項工作留給了后來的民族生態學家。到1964年,斯特蒂文特(William Sturtevant)提出,“ethnoecology”一詞中的前綴“ethno-”有著特殊的意義,它指的是那些從群體自觀出發的研究。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民族生態學的研究對象就變成了群體自觀下的生物內在聯系[10](p216)。稍后,美國人類學家布羅修斯(J Peter Brosius)等人在界定民族生態學時暗示出其研究范圍是傳統群體如何組織和分類其環境知識和環境過程[11]。這樣看來,民族生態學在當時的研究對象是處于傳統社會的群體,范圍則僅限于這些群體如何認知環境,如何看待人與自然的復雜關系。不過,民族生態學家馬丁(Martin)認為,民族生態學涵攝了地方性群體與所有的自然環境因素之間相互關系的研究,研究范圍包含了民族生物學、民族植物學、民族醫藥學以及民族動物學等諸多亞領域。在研究對象上,民族生態學家大多聚焦于土著人環境知識的研究,但他同時也指出,民族植物學家也樂意研究農民傳統的農技實踐,而他們不認為自己是土著人[12](pxx)。當然,一些生態學家、人類學家正試圖擴大民族生態學的研究對象和范圍。他們認為不僅農村居民值得研究,城市中也有民族生態學存在的空間;不僅要研究特殊群體的傳統生態知識,而且要關注漫長歷史時期內的生態變遷。從已有的研究成果來看,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家仍然繼續關注傳統居民的動植物利用和資源管理實踐,關注這些傳統生態知識在維護生態安全上的獨特價值。
與美國有所不同,蘇聯式民族生態學最初就是圍繞民族(ethnos)來展開的,因此任何跟民族有關的人類生態學問題當然是其職責所在。這里的“ethnos”不同于英語中的“nation”或者“people”,用蘇/俄式民族生態學的奠基人之一的勃羅姆列伊的話說就是指“歷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相對穩定的文化特點、確定獨立的心理特點以及區別于其他類似共同體的聯合意識的人們共同體”[13-15]。一般來說,“ethnos”大致相當于英語學界流行的“ethnic group”。正是根據這樣的理解,科茲洛夫認為民族生態學的形成取決于作為人的特殊共同體的民族(ethnos)的特點[8],而且其所涉及的問題超出了民族地理學、民族人類學和民族人口學的范圍。“該學科的主要任務是研究族群或族共同體在所居住地區的自然條件和社會文化條件下謀取生存的傳統方式和特點,當地生態系統對人體產生的影響,族群或族共同體同大自然作斗爭的特點及對自然界的影響,它們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的傳統,民族生態系統形成和發揮職能作用的規律等等。”[16]到1991年,科茲洛夫主編出版了名為《民族生態學:理論和實踐》的論文集,共匯集16篇論文。除涉及生存保障體系外,它還與地理學、人口學、生物學、醫學和心理學等學科相交叉,闡述特殊的地理環境對各民族的生計、飲食、物質文化、精神文化、體質、人口再生產和心理等方面的影響。科茲洛夫在這本書的前言中寫道:民族生態學的主要任務是研究在自然和社會―文化條件下生活的各民族共同體的傳統生存保障體系的特點,復雜的生態聯系對人們健康的影響;研究各民族利用自然環境以及對自然環境的影響,生態系統形成的規律和功能[17](p43)。實際上講的就是各民族與自然生態環境之間的互動作用。科茲洛夫接著論述道,首先要研究人們對自然環境的生物適應和與他們的經濟活動相聯系的社會―文化適應,這些適應反映在物質文化特點(飲食、服裝等)中,甚至反映在民族植物學和民族醫學中;其次研究人們在個體和集團層面對周圍環境和異民族的社會―文化環境之心理適應的主要方式,預防或降低環境壓力的傳統方法等;再次還需研究族群和自然的關系,對生態恐怖、生態災難趨勢的預測并借助利用那些物質資源的傳統進行生態學教育和其他目的的教育[17](pp43-44)。與1983年發表的2篇論文相對照,科茲洛夫在1991年的這篇前言中對民族生態學的研究對象和范圍作了進一步的論述,補充了一些原來尚未涉及的內容,如“預防或降低環境壓力的傳統方法”、“對生態恐怖、生態災難趨勢的預測”等。對于蘇/俄式民族生態學的研究對象和范圍,中央民族大學任國英教授認為其“不僅僅局限于民族學與生態學兩學科的交叉,他們(指蘇聯/俄羅斯的民族生態學家)的學術理念是將生態環境與各民族的方方面面都納入到本學科的研究框架內。”[17](p44)堪稱一語中的。
兩相比較,我們不難看出: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僅僅是民族科學(認知人類學)的一個研究領域,其研究對象也基本上限制在傳統的居民群體,范圍主要圍繞這些群體的植物、動物、土地的分類與利用以及他們資源管理的實踐等傳統生態知識來進行。而蘇/俄式民族生態學研究對象界定為族群或族共同體,范圍是與族群或族共同體有關的生態環境的方方面面,范圍十分廣泛。從這個意義上講,蘇/俄式民族生態學與當前歐美人類學界流行的生態人類學的研究對象和范圍基本類似。
三、研究方法
對一個學科來說,確定其研究對象之后,就會面臨著如何去研究的問題,亦即采用何種研究方法的問題。民族生態學要想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就必須要在方法論上有自己獨特之處,方才能得到相關學科學者的承認,在學術譜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由于美國式民族生態學是民族科學(認知人類學)的一門分支,因此它很大程度上采借了其正規的資料收集方法。為了解被研究群體對自然環境的認知,民族生態學家們常常會設計幾個層級的問題,他們首先會問本地有哪些生物?其中有哪些植物?其中有哪些是樹?常綠樹和落葉樹有何差異?這里有哪些不同種類的針葉樹?針杉和松樹有何不同?……這樣一直到最低層級為止[18](p60)。通過向該群體的不同的人提問同樣的問題,經過分析綜合,基本上就能夠獲知被研究群體對他們所處的自然生態環境的認知總圖。不過,后來民族生態學家們逐漸發現,由于他們采用這種假設性的分類,一些被訪談者可能會依照訪問者的邏輯去推定,甚至創造出當地沒有的事物來。于是民族生態學家們只好又重新依靠人類學的參與觀察和無結構訪談的方法,雖然這兩種方法費時又費力,但好在這兩種方法的有效性很高。在參與觀察的過程中,民族生態學家們常常需要正確記錄動植物的當地名稱、學名、科屬,必須涉及到它的日常用途和儀式用途、利用的部位以及特殊的去除毒素之類的加工技術,甚至還需要了解有關的神話傳說,以便更好地把握它們在地方文化中的功用。有時,研究者還被要求采集和保存那些他們記錄下來的動植物標本和材料。當然,如今的民族生態學研究雖然在資料采集和分析方法上與以前差別不大,但他們看待這些資料的視角卻有了新的變化。比如美國民族生態學家納扎里(Virginia D Nazarea)就指出,民族生態學是“從某個點出發的視角”,它不僅要摒棄以前那種無歷史和政治的傾向,而且要看到權力和風險在塑造環境解釋、管理和妥協的重要性。只有這樣,民族生態學者才能在跨學科研究中發揮重要作用,甚至在生物多樣性保護和促進可持續發展中充當主角[19](pp1-19)。
蘇聯民族學家們認為直接觀察是獲取民族學情報資料的基本方法,但蘇聯民族學界起初轉向“綜合集約調查法”,后來則以夏季短期的小組或個人旅行來排斥綜合調查,總的來看是逐漸放棄了“定點”的直接觀察方法。鑒于上述民族學調查方法的走向,民族生態學的奠基者之一勃羅姆列伊聲稱一定要堅持直接觀察、定點長期調查的方法,同時還可以根據研究客體變化的實際情況適時采納問詢調查法、歷史比較法、類型學方法等其他的研究方法[20](pp136-146)。但勃羅姆列伊的主張未能堅持多久,蘇聯就遭遇了解體。隨后,民族學也遭受前所未有的學科危機。正是在這個階段,科茲洛夫總結了蘇聯民族生態學的發展歷程。在1994年出版的《民族生態學――學科形成和問題史》一書中,科茲洛夫全面闡述了蘇聯民族生態學的學科性質、基本理論、流派和研究方法及與其他學科間的關系;其中還對阿塞拜疆的阿塞拜疆人和格魯吉亞的阿布哈茲人進行研究,開拓性地把移民和民族沖突問題納入民族生態學研究的視野[17](p43)。從前人翻譯的2篇論文和任國英教授的總結來看,蘇/俄式民族生態學仍然堅持民族學的田野調查方法,同時吸收了人類生態學的方法,從而在方法論上有了自身一定的支撐。20世紀末以來,由于西方的民族學人類學理論與方法的傳入,俄羅斯的民族生態學研究注意同國際接軌,研究中借鑒和引用西方的理論觀點,在研究方法上更加注重實地調查,將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結合[17](p44)。筆者曾就這一問題向俄羅斯繼科茲洛夫后最負盛名的民族生態學家亞姆斯科夫(Anatoly N Yamskov)請教,他認為蘇/俄民族生態學依然堅持經典的田野工作方法,創造性地發展了民族生態系統的概念,同時注意使用精細的統計數據和自然地理資料。
兩相比較,我們可以發現:美國式民族生態學由于誕生在認知人類學內部,因此它不僅繼承了人類學的參與觀察和無結構訪談等田野調查方法,而且以其獨特的研究步驟和視角獲得了很大的發展。蘇/俄式民族生態學初創于20世紀80年代,直到蘇聯解體以后才形成了較為完備的理論體系,因此研究方法上更多地依賴民族學的直接觀察的方法,同時也適當吸納了系統生態學等理論與方法。只有在俄羅斯民族學界與西方人類學界廣泛交流一段時間以后,民族生態學研究才獲得了新的理論與方法源泉,從而推動了這一新興交叉學科的發展。
四、學術影響
一個學科的生命力是否夠強,關鍵還在于它的學術影響力。對美蘇兩種傳統民族生態學的學術影響的分析,筆者認為要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一是看其民族學人類學內部的影響力;二是看其對其他學科學者的號召力;三是看其對境外國家和地區學術的輻射能力。
美國式民族生態學誕生于人類學內部,本身是民族科學(認知人類學)的一個亞領域。雖然認知人類學在20世紀60-70年代曾經風靡一時,但隨著實踐理論、闡釋人類學以及反思人類學的出現,民族生態學本身也成為某些學者清算的材料。不過,在文化人類學內部,民族生態學作為一種方法和視角,還是得到廣泛的承認的。這從《美國人類學家》、《美國民族學家》、《當代人類學》等頂級雜志上刊登的為數不菲的民族生態學研究論文上可以得到證實。在人類學界之外,民族生態學的理論與方法也得到了植物學、動物學、生物學、生態學、地理學等學科學者的認可,還有的學者針對性地進行了理論方面的探討,如墨西哥生物學家托萊多、資源地理學者巴頓(David Patton)都有專門的研討文章問世。不過,最能說明一個學科影響力的也許要看它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輻射能力了。由于美國社會科學在當今世界研究社群中居于統治地位,單從其數量龐大的實踐者、分配到的資源以及學科方法論的影響力上就可以略見端倪,因此美國式文化人類學領導著世界人類學理論與方法的發展,印刷文本的廣為傳播更是奠定了美國文化人類學的學術優勢地位[21]。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如今也已在英國、法國、德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印度、中國、墨西哥、韓國等國家和地區生根發芽。英國與美國同文同種,因此較早接受了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坎特布理肯特大學的埃倫(Roy Ellen)博士更是這一領域中享譽世界的學者,他與《皇家人類學刊》合作出版了名為“Ethnobiology and the science of humankind”的特刊,集7篇專門研究于一體,足見民族生態學在英國人類學界的影響。事實上,即使在俄羅斯國內,從事民族生態學研究的學者們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國傳統的影響,如今他們在英語寫作中已把自身原來應用的“ethnoecology”改稱為“ethnic ecology”,且認為俄羅斯的民族生態學跟美國的文化生態學或生態人類學相差無幾[22-24]。
蘇/俄式民族生態學雖然創立較晚,但不論在蘇聯時代,還是在俄羅斯時代,都能在民族學界占有一席之地。俄羅斯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還成立了民族生態學部,專門從事民族生態學研究。從1997-2005年,俄羅斯民族學家與體質人類學家聯合會共舉辦了5次大會,每次會議都有15-20篇的民族生態學專題研究論文參與[22]。在論文的發表上,俄羅斯權威的民族學期刊《民族學觀察》(即以前的《蘇聯民族學》)從1975-2004年共刊發了24篇民族生態學方面的論文,雖然與民族政治研究相比仍有較大差距,但跟民族心理學、民族社會語言學等其他新興研究領域一起處于第二序列[24]。值得高興的是,俄羅斯的學者們還在圣彼得堡創立了名為《民族地理學與民族生態學研究》的叢刊,專門刊發民族地理學和民族生態學研究方面的論文。在學術研究之外,學者們還積極參與生態學評估。1999年,民族生態學家斯泰潘諾夫(Valery Stepanov)還主持編纂了《民族生態學評估方法》一書,為俄羅斯民族生態學家參與生態學評估提供了學術指引。由于民族生態學研究在俄羅斯國內已經有了上述良好的基礎,因此地理學、生態學、社會學等其他學科的學者在進行研究時也深受影響。對此,亞姆斯科夫曾經說道:“在土著人土地權利和傳統居住領域內進行研究的許多專家,他們有著民族學、地理學、生態學(生物學)以及社會學的訓練背景,如今喜歡稱呼自己為‘民族生態學家’。”即使在一些地方法案的建議草稿中,甚至流行的術語“傳統自然資源應用領域”(TTUs)也正在轉變成“民族生態學領域”[25]。不過,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的學術影響力下降,因此俄羅斯傳統的民族生態學對外傳播并不是很廣泛,僅在原來的加盟共和國內流布。中國從1984年開始譯介相關理論,然迄今為止,僅譯介過科茲洛夫的2篇論文,且其中尚有不同程度的重復之處。2009年,任國英教授的《俄羅斯生態民族學研究綜述》一文算是稍微彌補了這方面的缺憾。
兩相比較,我們就會發現:兩種傳統的民族生態學在人類學或民族學界內部仍充滿活力,都對其他學科造成一定的影響,也都有向其他國家和地區傳播的輻射力。但美國式民族生態學更具活力,如今已經得到植物學、生態學等領域學者的認可,跨學科的合作日益增多,兼且美國式民族生態學的向外傳播更為廣泛,如今已經影響到世界上主要的民族學、人類學研究大國。
五、結果與討論
透過以上四個方面的比較,我們發現美蘇兩種傳統的民族生態學雖然都誕生于民族學或人類學界內部,從事研究的也都是民族學家或人類學家,但兩者之間卻有著比較大的區別。筆者認為,造成這種差別的主要原因是美國和蘇聯(俄羅斯)民族學人類學研究的不同的對象所致。我們知道,美國號稱為“文化人類學”,其研究的對象是人及其文化,文化在其中尤占重要地位,這跟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始終追求理解土著居民的生態觀念有著根本聯系。蘇聯(俄羅斯)既然號稱為“民族學”,而且在實際研究中都是圍繞“民族”(ethnos)來進行的。蘇聯式“ethnoecology”中的前綴“ethno-”僅表示著與“民族”(ethnos)或族群單位相關,而并不像美國式“ethnoecology”中的前綴“ethno-”,其意思乃是“文化持有者的內部眼界”,是一種主位的對人與環境相互關系的研究。前綴“ethno-”意義的區別乃是兩種傳統的民族生態學之間的根本差別。鑒于這種意義上的差別,一些俄羅斯學者已經采用“ethnic ecology”來指稱蘇/俄式民族生態學。
在準備和閱讀材料的過程中,筆者還發現,并不是所有的蘇聯/俄羅斯民族學者都認同這種跨領域的學科。如俄羅斯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教授切什科(Sergei Cheshko)就認為民族學中出現的民族生態學等之類的亞學科大部分都是夭折的分類。因為它們不能改變任何事情,學者們只是繼續做他們過去做的東西罷了,而且以后這些亞學科的繼承者會為他們抓住的一點皮毛而沾沾自喜起來,甚至會聲稱一切事物離開了生態學無法解釋[26]。切氏的論述提醒我們,如果我們只是在學界內部劃分一下勢力范圍,而沒有理論方法上的升華,這種劃分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事實上,如果民族學人類學者因為沉迷于分支領域的研究,而未能堅持“全貌觀”的基本準則的話,那么這種分支不要也罷。
依上述認知去審視美蘇兩種傳統的民族生態學,我們會覺得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具備其自身的學科特點,而且具備完善的方法論工具,是一種人類學生態研究范式的更新。而蘇/俄式民族生態學則不然,它更多的是對人類生態學的一種類比,主要作用在于劃分學術領域,既沒有形成獨特的學科特點,也沒有完善的方法論工具。當然,這并不是說蘇/俄式民族生態學一無是處,它所開拓的文化適應不完善的思想、對不同族體的心理適應的研究、景觀民族特點的論述,對民族學人類學的生態研究仍然具有其獨特價值。
(致謝:俄羅斯科學院亞姆斯科夫博士曾向筆者提供他的論文電子版以供參考,還在電郵中耐心地回答了筆者的疑問,特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參考文獻:
[1]〔法〕喬治•梅塔耶、貝爾納爾•胡塞爾著,李國強譯民族生物學(上)[J]世界民族,2002(3)
[2] Justin M Nolan Ethnoecology[A] H James Birx Encyclopedia of anthropology (vol2) [C]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06
[3] Victor M Toledo What is ethnoecology?: origins, scope, and implications of a rising discipline[J] Etnoecologica, 1992(1)
[4] David Patton Ethnoecology: The Challenge of Cooperation[J] Etnoecologica, 1993(2)
[5]〔蘇〕Ю•В•勃羅姆列伊、Г•Е•馬爾科夫主編,趙俊智譯民族學基礎[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6]〔蘇〕BN科茲洛夫關于民族學的界限問題[A]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學譯文集(三)[C]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7]〔蘇〕Ю•В•布朗利從邏輯系統分析看民族學的對象[A]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學譯文集(三)[C]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8]〔蘇〕科茲洛夫著,黃德興譯民族生態學的任務[J]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1984(3)
[9]〔蘇〕B科茲洛夫著,王友玉譯民族生態學的基本問題[J]國外社會科學,1984(9)
[10] Catherine S Fowler Ethnoecology[A] D Hardesty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C] New York: Wiley, 1977:216
[11] J Peter Brosius, George W Lovelace, and Gerald G Marten Ethnoecology: An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Knwledge[A] Gerald G Marten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in Southeast Asia [C] Boulder: Westáview Press, 1986
[12] Gary J Martin Ethnobotany: A Methods Manual [M] London & Sterling, VA: Earthscan, 2004: xx
[13] Marcus Banks Ethnicity: Anthropological Constructions [M] London: Routledge, 1996:19
[14]〔蘇〕尤里•勃羅姆列伊著,李振錫、劉宇瑞譯民族與民族學[M]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39
[15]潘蛟勃羅姆列伊的民族分類及其關聯的問題[J]民族研究,1995(3)
[16]〔蘇〕B•И•科茲洛夫著,殷劍平譯民族生態學研究的主要問題[J]民族論叢,1984(3)
[17]任國英俄羅斯生態民族學研究綜述世界民族,2009(5)
[18] Emilio F Moran Human Adaptability: An Introduction to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M]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2
[19] Virginia D Nazarea, A View from a Point: Ethnoecology as Situated Knowledge [A] Virginia D Nazarea Ethnoecology: Situated Knowledge/Located Lives [C]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99
[20] Ю•В•布朗利、MB克留科夫民族學:在科學體系中的地位、學派和方法[A]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學譯文集(三)[C]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21] Valery A Tishkov US and Russian Anthropology: Unequal Dialogue in a Time of Transition [J] Current Anthropology, 1998(1)
[22] Anatoly N Yamskov Applied Ethnology in Russia[J] NAPA Bulletin, 2006(1)
[23]Elena Tinyakova Fieldwork: Man in the System of Nature and Priority of Natural Laws in Human Life [J] Coll Antropol 2007(2)
[24]Sergey Sokolovskiy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in Russia: Draft Case Report [Z] Paper presented at “Anthropology in Spain and Europ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Madrid, September 2-7, 2008
人類學研究方法論范文第5篇
[關鍵詞]格爾茨;民族志;深描;解釋人類學
在殖民背景下產生的民族志寫作,實際上是一個建構非西方文化的過程,而不是一個再現、反映的過程。格爾茨的巴厘島民族志“深描”寫作實踐,是在反思性民族志寫作傳統的基礎上進行的。格爾茨將文化看做是意義系統、強調意義、符號象征、語言,并強調民族志的寫作是一種人為的認識過程,文化以及社會活動的意義是可以被觀察者“閱讀”的。同時格爾茨運用解釋人類學的方法,強調民族志書寫的意義在于理解并闡釋一個族群對自己深處其中的文化的理解,并把觀察者的自我反思意識融入到對異文化的理解和解釋中。這與以馬林諾斯基為代表的傳統民族志的寫作實踐是完全不同的。
一、格爾茨關于 “斗雞”的深描
如何進入田野,如何讓調查對象接受你,這可能是每個有志于田野調查的人類學家將要面臨的難題。格爾茨與他的妻子也不例外。他們初到巴厘島,巴厘人對他們熟視無睹,視他們如“一陣風,一陣云”。十天之后,為了給學校籌集資金,一次大規模的斗雞將在公共廣場舉行,在第三輪比賽進行得正酣之際,警察進行了突然襲擊,參與者與圍觀者四處逃竄,格爾茨和他的妻子與其他人一樣開始逃跑,在無處可逃時,隨一名巴厘男子進入其院落,這位男子的妻子立刻擺好桌椅及其他相關物品替他們掩飾。此后,巴厘人正式接受了他們。
巴厘島男人酷愛斗雞,同時對雞照顧也極為周到。盡管當地政府公開取締斗雞游戲,但是當地人仍然迷戀斗雞。對此,格爾茨進行了分析,其認為巴厘人如此迷戀斗雞是因為表面上在斗雞場上搏斗的公雞實際上是男人的化身。公雞是他們的自身的象征表達或放大,即自戀的男性自我。在斗雞中,人與獸、善于惡、自我與本我、激昂的男性創造力和放縱的獸性毀滅力融合成一幕憎惡、殘酷、暴力和死亡的血的戲劇。
斗雞之所以能夠得以運作,關鍵在于它是一種賭博。在斗雞游戲中充斥著兩種不同性質的賭博:差額和數額相等的錢。一種是在賽圈中心進行的參與者之間雙的軸心賭博;另一種是散在賽圈周圍的觀眾個體之間的賭博。斗雞表面上是一種“金錢賭博”,其實深層的斗雞是一種“地位賭博”。從表面上看,巴厘人斗雞是在賭錢,而事實上,他們是將巴厘人的社會地位等級移入到斗雞這種形式中,因為斗雞是自戀的男性自我,是他們主人的人格者。
格爾茨認為巴厘人在斗雞事件上表現出的“焦慮不安”以“某種方式”來源于斗雞的三種屬性組合:直接的戲劇狀態、隱喻的內容以及它的社會場景。令人“焦慮不安”的原因不是它的物質影響,而是它將自尊與人格連接起來,將人格與公雞連接起來,又將公雞與毀滅連接起來。斗雞最有力地說明的是地位關系,并且它說明這些地位關系是生死攸關之事。聲譽作為至關重要的事情,作為一種波利尼西亞的名銜階級和印度種姓制度融合的特殊產物,尊卑等級是整個社會的道德支柱。只有在斗雞中,這些等級制度建立于其上的道德情感才顯露其本色。同時,格爾茨指出,斗雞的真正功能在于它的解釋作用:它是巴厘人對自己心理經驗的解讀,是一個他們講給自己聽的關于他們自己的故事。它使得巴厘人能夠看到他自身的一個主體性維度。
至此,格爾茨用“深層游戲:巴厘島斗雞的記述”完成了對自己文化深描說最好的詮釋。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一種大眾都知道的意義,何謂深描,深描是“解釋他人的解釋”,人類學家的任務就是通過小事實說明大問題。斗雞是一種游戲,表層是斗雞,深層是男人之間的較量;斗雞是一種賭博,表層的是金錢賭博,深層的是地位的賭博。在對斗雞游戲的再解釋中,格爾茨完成了他對文化的深描。
二、格爾茨的“解釋人類學”
何謂解釋人類學?簡單說,解釋人類學關注的是文化符號的破譯以及對文化行為的深層描寫及闡釋。有學者認為,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人文學科領域兩大革命性的思想家,一個是福科,另一個則是格爾茨。如果說福科是西方舊有思想和知識的顛覆者,那么格爾茲則試圖成為顛覆破壞之后的新的知識的闡釋者和再造者。如果說福科對話語以及事物本源性進行考古學的挖掘,進而批判性地重新認識西方人文知識領域的許多定論式的命題、質疑理性主義,那么格爾茲則致力于再造顛覆后的認知體系和文化話語。格爾茲強調一種立場――土著的眼光。在此基礎上, 他提出了一種新的認知視野――地方性知識和新的符號手段――深描,當然,格爾茲的地方性知識不僅是一種視野,更是一種身體力行的方法論。他又是如何實踐這種方法論的呢?這應該歸功于他提出新的符號手段――深描。具體說來,深描強調描寫和觀察方式的特定化、情境化,并有長期的、小地方的、具有一定語境的理論要求。在他看來,文化具有公共性質,是處于文化之網的人們文化研究之間交往的符號。解釋人類學就是要解釋這些由眾多的、具有意義的符號編織的文化之網。也就是說, 要在一定的文化環境的基礎上進行闡釋,要闡釋符號活動背后的觀念世界,并揭示文化的差異性與多樣性。格爾茲心目中理想的民族志應該具有三個特色:第一它是闡釋性的;第二它所闡釋的對象是社會話語流;第三這種闡釋在于努力從一去不復返的場合搶救對這種話語的言說,把它固定在閱讀形式中,它還必須是微觀的描述。
要理解格爾茨解釋人類學的意義,就應該把人類學放到學術脈絡中去思考。凡是對西方人類學發展脈絡有所了解的人都應該知道,格爾茨所處的時代正是結構主義人類學遭到批判和質疑的時代,格爾茨以解釋人類學作為武器,在人類學的戰場上贏得一席之地,同時也使上個世紀60年代以來的人類學危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格爾茨提出人類學的宗旨是擴大人類話語的范圍,他認為符號學的文化概念特別適合這個宗旨。“作為由可以解釋的記號構成的交叉作用的系統制度,文化不是一種引致社會事件、行為、制度或過程得到可被人理解的――也就是說,深的――描述。”
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格爾茨提出了文化的深描說,以理解他人的文化。同時,他認為理解他人的文化并不是鉆到別人的頭腦里去,人類學要做的事情是通過對他人文化的理解來理解我們自身,也就是理解我們人之所以為人的原因。所以,格爾茨用斗雞等來給我們展示了他人理解他人何以成為可能,又可以通過對他人的理解來理解我們自身。
三、民族志寫作手法的革新
首先,在格爾茨關于巴厘人斗雞的民族志描述中,他不再純粹以外來者的“客觀”、“公正”、冷靜的態度對待土著文化,取而代之的是人類學家深入地融入到土著社會生活中的一種與土著居民情感、生活方式的強烈互動。這里,人類學家不再如以往一樣像一個手持手術刀的外科醫生,將文化看做是置于手術臺上的被局部麻醉的一副肉身,而是一個充分理解土著社會以及土著居民的道德理想、審美觀念與情緒心理的土著人的朋友。在他的筆下,民族志不再以科學、理性作為寫作的唯一指導,而是更多地深入到土著居民的內心世界。與馬林諾斯基和埃文斯普理查德的功能主義文化體系以及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主義意義上的符號體系相比,這樣的民族志寫作方式顯然是不同的,因為其關注的是特定文化所獨有的、屬于意識形態范疇的社會情感和社會心理。
這里,筆者同時想要說明的是,格爾茨并不是反對科學和理性的寫作方法,也不是反對客觀和公正的探索精神,他真正反對的是人類學長期以來對于科學方法的奴性十足的模仿。誠如馬爾庫斯和費徹爾在其書中所說,以格爾茨為代表的人類學家將人類學的注意力,從強調行為和社會結構的“社會自然科學”轉移到強調意義的符號象征、語言。也就是說,解釋人類學將文化看做是意義系統來進行研究,并強調民族志是一種人為的認識過程,文化以及社會活動的意義是可以被觀察者“閱讀”的。我們需要感謝格爾茨,因為正是從格爾茨開始,人類學開始轉變了方向,從一種機器似的科學研究變成一種有感情,有智慧、可以批評的人文學科。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格爾茨的解釋人類學在某種程度上與文學等其他人文學科之間形成了對話。解釋人類學對于文化符號及其展示過程的深刻細膩的觀察描繪,對于文化符號的社會背景的揭示,對于文化符號與人之間深刻互動表現出來的心里緊張與情緒沖突等等,都與以人為描寫對象的文學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華勒斯坦在其《開放的社會科學》一書中指出,在格爾茨之前,民族志強調研究者必須采用一種圍繞實地調查而建立起來的方法論,并且還必須在某一特定的地區以參與者的身份進行觀察,從而滿足對所觀察的文化具備深層知識的要求。這是一種為理解所需的知識,當然,由于科學家置身于一種完全陌生的文化之中,要獲得這種知識是非常困難的。其實,民族志的事業從本質上說就是翻譯:即用本文化的語言去翻譯“他者”的文化。因為沒有一個人類學家的民族志能夠對文化完全是純粹客觀的書寫,對任何一種文化的書寫,人類學家都存在著一種文化翻譯的問題,他所做的工作從本質上說就是在運用他的語言、觀念與文化去翻譯“他者”的文化。人類學家Godfrey Lienhardt指出:當我們同野蠻人住在一起,說他們的語言,學著按他們的方式來向我們自己表述再現他們的經驗時,我們是盡我們所能地接近了像他們那樣思維同時又不失掉我們自己。最終,我們試圖用我們從小就學習使用的邏輯概念來系統地表述他們的觀念……向別人描述一個遙遠部落的成員如何思維。這個問題……開始顯出大半是個翻譯的問題了,是個如何把原始在它所真正存活的語言里所具有的連貫性盡可能清楚地在我們的語言里表現出來的問題。
在前代的民族志寫作中,人類學家都會選擇與土著人共同生活一段時間,目的是為了全面了解該土著的語言、他們的生活方式以及他們的社會結構政治制度等等。表面看來, 人類學家嘗試運用土著人的觀念或者表達方式向現代社會的人們再現土著人的經驗的時候, 其實是在探索西方人自己的思想和語言是否具有足夠強大的力量和智慧, 用來表述非西方社會的文化。人類學家的任務是要在他自己思維方式之中找到可以與他在土著社會所見所聞所感知的事實相匹配、相符合的范疇, 去建構非西方世界, 再現非西方世界, 并作為非西方世界代言人。英國功能學派人類學家馬凌諾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書, 雖然只是描述新幾內亞土著人的貿易關系, 但作者把該社區中社會的、文化的和心理的所有方面作為一個整體來處理, 盡管本書的主題是經濟, 卻涉及了社會機制、巫術力量以及神話傳說等等諸多方面,將新幾內亞的庫拉圈的研究置于科學的、整體的視野之中。
因此,民族志的文化翻譯實際上是一個建構、制造非西方文化的過程, 而不是一個再現、反映的過程。其實, 并不存在一種自然化的西方/非西方的區別, 西方/非西方的對立是一個歷史、文化的建構過程。人類學家標榜的田野調查、實地考察只是一種方法而已, 民族志的寫作所表述的, 則是人類學自身對于一種文化的主觀性經驗。
參考文獻:
[1]克利福德?吉爾茲. 地方性知識[M]. 中
央編譯出版社,2000.
[2]克利福德?格爾茲. 文化的闡釋[M]. 上
海人民出版社,1999.
[3]喬治?E?馬爾庫斯, 米開爾?M?J?費徹
爾. 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M]. 生活?
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
[4]華勒斯坦. 開放社會科學[M]. 生活?讀
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
[5]特賈斯維莉?尼南賈納. 為翻譯定位
[C]//許寶強,袁偉. 語言與翻譯的政治.
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6]馬凌諾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M]. 華
夏出版社,2002.
[7]酒井直樹. 西方的錯位與人文學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