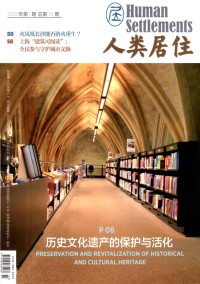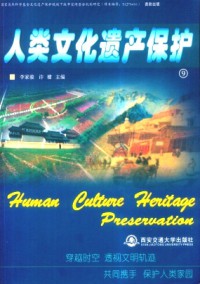人類學(xué)的研究方法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人類學(xué)的研究方法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fā)現(xiàn)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人類學(xué)的研究方法范文第1篇
俄羅斯學(xué)者葉梅利亞諾夫說:“今天已無須證明,在社會人文科學(xué)的所有概念中,對于研究和理解人而言,沒有哪一個概念能比‘文化’概念更重要了。”可見文化的重要性,因此文化是任何社會科學(xué)門類的重要話題之一;同時,文化的內(nèi)容之豐富、內(nèi)涵之深刻、范疇之廣泛,為各社會學(xué)科提供了寬廣的研究空間。人類學(xué)、心理學(xué)與傳播學(xué)在人類文化研究上的應(yīng)用日益發(fā)展,各種基于文化的交叉學(xué)科理論和方法也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世界各地區(qū)思想、習(xí)俗、制度以及共享的價值觀念,對不同學(xué)科角度的文化研究理論和方法進行總結(jié)對于文化研究的進一步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有重要意義。
一、文化研究的學(xué)科起源
“文化研究”起源于20世紀50年代,是興起于歐美的關(guān)于人文社會科學(xué)研究的理論思潮與研究模式,這一研究模式實現(xiàn)了文化的跨階層和各學(xué)科交叉研究,它是以工業(yè)社會中的文化現(xiàn)象為研究對象,結(jié)合了社會學(xué)、文學(xué)理論、媒體研究、文化人類學(xué)等進行交叉研究[1-2]。文化研究的起源、所涉獵的問題和研究方法是多學(xué)科視角的交疊,而不是限定于某一學(xué)科領(lǐng)域。一方面文化本身受到多個學(xué)科的共同關(guān)注;另一方面文化研究是探討文化與其他社會活動領(lǐng)域的相互關(guān)系,其目的是要對這一系列關(guān)系進行合理的詮釋,因此文化研究必須與其他學(xué)科研究緊密結(jié)合,特別是人文學(xué)科和社會學(xué)科。
從文化研究所探討的內(nèi)容與范圍來看,許多方面都與人類學(xué)、心理學(xué)、傳播學(xué)有關(guān),接下來本文將從人類學(xué)、心理學(xué)與傳播學(xué)這三個角度來分析文化研究的方法。
二、多學(xué)科的文化研究的方法
1.文化人類學(xué)的基本觀點。“文化是我們關(guān)于我們自身的故事。”[3]文化人類學(xué)研究的目的是解釋人類文化的異同,探求人類文化發(fā)展的共同規(guī)律,特別是與人類生存密切相關(guān)的三種關(guān)系:(1)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尤其是涉及生計、工藝和物質(zhì)文化的關(guān)系。(2)人們之間的關(guān)系,尤其涉及社會制度、組織、習(xí)俗和社會文化的關(guān)系。(3)人與自身心理的關(guān)系,特別是涉及知識、思想、信仰、態(tài)度、行為和精神文化的關(guān)系。
2.文化人類學(xué)的方法。文化人類學(xué)采用直接來自人際環(huán)境的資料,屬于“第一手”的資料,因此與其他社會學(xué)科相比,擁有明顯的方法論優(yōu)勢。文化人類學(xué)家通過野外考察,親身融入人們的日常活動,觀察人們在飲食、交流、娛樂等日常行為,真真切切的感受生活并從他們的角度來理解生活。
文化人類學(xué)又包括三個學(xué)科:考古人類學(xué)、語言人類學(xué)、社會文化人類學(xué)。考古人類學(xué)是通過發(fā)掘人類遺留下來的遺物、遺跡對遠古人類文化進行研究[4]。考古人類學(xué)家以一種更加廣闊的視野把文化遺跡進行整合性的思考。在考古人類學(xué)家看來,文化的演進過程是關(guān)注的重點,而并非簡單的對遠古社會進行描述或者分類。語言人類學(xué)家主要是對語言的結(jié)構(gòu)以及它的各個部分之間連貫的溝通系統(tǒng)進行研究;此外,不同語言是如何演化發(fā)展、如何分布;語言受到什么因素影響,年齡、性別、族群本質(zhì)及社會階級等因素如何影響語言;人類的思維方式受到語言怎樣的影響,人類的信仰與價值觀對語言表達方式有什么影響等都受到關(guān)注。社會文化人類學(xué)是從民族學(xué)和民族志兩個方面來研究人類社會與文化的傳承問題。民族學(xué)主要研究現(xiàn)存文化的種類及其演化過程,是社會文化人類學(xué)中最大的分支,系統(tǒng)與比較的方法是民族學(xué)中最重要的方法;民族志是以收集各民族的文化資料為基礎(chǔ),通過對這些資料的整理達到對各個社會的文化及其過程進行描述和記述的目的。在研究過程中,二者密不可分,必須相互結(jié)合。
(二)心理學(xué)的文化研究
1.心理學(xué)文化研究的基本觀點。隨著心理學(xué)的發(fā)展,“文化”逐漸進入心理學(xué)家的視野,受到心理學(xué)家的廣泛關(guān)注。文化心理或文化行為是心理學(xué)的基本概念,表征人在特定的環(huán)境下對特定文化的反應(yīng),即特定文化中的人內(nèi)在固有的對刺激的解釋和以此為基礎(chǔ)表現(xiàn)出的行為模式或方式。文化進化和發(fā)展中不同的文化有不同進化程度或不同等級,這也是文化進化過程的基本特征,這一過程也是客觀的,文化是一種自變量,行為是因變量。
2.心理學(xué)的文化研究的方法。心理學(xué)綜合運用多種方法來研究文化。既有實證方法,也有解釋學(xué)方法;既有量化方法,也有質(zhì)化方法[5-6]。
(1)主位與客位研究。主位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者親自介入研究對象的實際生活來了解其文化行為,客位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者從一個特定的文化外部去研究其成員的行為[7]。主位研究方法實際上是研究者親身走入研究對象的生活環(huán)境,體會他們的習(xí)俗、觀念,這強調(diào)了調(diào)查對象作為信息提供者的作用,研究者使用的描述概念使調(diào)查對象更生動、更富有意義,使得研究更為客觀。在客位研究方法中,研究者與對象的交談了解其內(nèi)心世界,這樣的方法強調(diào)了研究者的作用,研究者可以使用對自己有利的概念、捕獲自己需要的信息,并在此基礎(chǔ)上對概念進行整理分類,可以促進研究工作的深入進行。
(2)跨文化研究。跨文化研究有時也被稱為全文化研究,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被試,對與文化相關(guān)聯(lián)的心理和行為特征做假設(shè)檢驗,研究兩種及兩種以上的文化背景因素對心理及行為特征變量的影響[8]。跨文化比較研究通常假設(shè)一種文化背景下的某個心理變量的得分顯著高于另一種文化背景下的心理變量得分。跨文化驗證研究雖不及一般的文化研究應(yīng)用廣泛,但此研究對于考察在一種文化中發(fā)展出的心理測量工具在其他文化背景研究下的適用性、等值性、作用及意義有著重要作用。
(3)解包研究。此研究關(guān)注不同文化背景下研究變量的差異,測量變量差異產(chǎn)生的原因變量。“文化”在通常意義下被認為是非具體化變量,而在解包研究中,“文化”將以某些更具體化的變量的形式出現(xiàn),以便于能在統(tǒng)計意義上解釋文化差異的程度。這些更具體的變量被稱作背景變量,背景變量的統(tǒng)計差異就解釋了文化差異,為了使得所有的文化差異都能得到解釋,研究將會不斷引入新的背景變量。
(4)生態(tài)學(xué)水平研究。與大多數(shù)跨文化研究不同,生態(tài)學(xué)水平研究將假設(shè)檢驗研究的分析單元從個體被試轉(zhuǎn)向了國家,文化得分則是個體被試的得分總和或均值。在對研究結(jié)果進行解釋時,生態(tài)水平研究反映的是總體水平的關(guān)系,而并不反映個體水平的關(guān)系。
(5)人種學(xué)研究。人種學(xué)研究指研究者從客位角度對一個民族的文化習(xí)俗、特性進行研究,此方法包括大量觀察與實地工作,可獲得豐富的研究資料。此方法要求研究者與所研究的群體生活在一起,周密地觀察、記錄、參與“他文化”的日常生活,獲得該文化群體的習(xí)俗、傳統(tǒng)、觀念及生活方式,正確地感受、認識“他文化”。在完成田野工作后,細描、說明所觀察和體驗到的“他文化”,并將自己獲得的第一手資料與另一種文化進行對比。
(三)傳播學(xué)的文化研究
1.文化傳播學(xué)的基本觀點。文化傳播學(xué)是研究人類文化傳播現(xiàn)象及其規(guī)律的科學(xué),是文學(xué)、文化性和傳播學(xué)等學(xué)科的交叉學(xué)科[9]。
2.文化傳播學(xué)研究的方法。傳播學(xué)主要分為歐洲批判學(xué)派和美國經(jīng)驗學(xué)派兩大流派。這兩大流派的主要的差別在于傳播學(xué)研究方法上的分歧:歐洲的批判學(xué)派認為傳播學(xué)的研究應(yīng)堅持人文主義,而美國經(jīng)驗學(xué)派更傾向于實證主義。人文主義者認為社會科學(xué)的研究方法應(yīng)該有著不同于自然學(xué)科的獨特研究方法。實證主義者則更愿意將自然學(xué)科的研究方法應(yīng)用到社會科學(xué)研究領(lǐng)域,運用實證研究的方法對社會現(xiàn)象進行因果性的說明。在社會科學(xué)研究領(lǐng)域中,實證研究主要分兩類:質(zhì)化研究和量化研究。質(zhì)化研究方法包括民族志研究、田野研究、個體訪談、集體訪談、案例分析等;量化研究方法包括問卷調(diào)查法、縱向研究法、實驗研究法等,其中的具體方法與社會學(xué)、心理學(xué)上運用的方法多有重合。
梅瓊林認為在傳播學(xué)史上,人文主義和實證主義兩種不同的方法論始終糾纏在一起,在沖突中走向融合,也在融合中持續(xù)沖突,并在這兩種研究方法的基礎(chǔ)上建構(gòu)了現(xiàn)代傳播學(xué)的理論體系[10-12]。
人類學(xué)的研究方法范文第2篇
[關(guān)鍵詞]美學(xué)人類學(xué);學(xué)科性質(zhì);學(xué)科構(gòu)想
[作者]張佐邦,云南大學(xué)人文學(xué)院教授。昆明,650091
[中圈分類號]C912.4 [文獻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08)01-0039-004
隨著文化人類學(xué)、文藝心理學(xué)、文藝美學(xué)等學(xué)科研究的縱向深入和橫向拓展,以及探索原始人類審美心理生成及其文化表現(xiàn)形態(tài)奧秘的需要,我認為,在這三門學(xué)科的邊緣交叉處建立一門新興的多邊緣交叉學(xué)科――美學(xué)人類學(xué),既有可能,又有必要。因為,它已經(jīng)具備獨立的學(xué)科性質(zhì)、特定的研究對象和獨特的研究方法。同時,也是人類學(xué)學(xué)科發(fā)展的時代要求。
一、美學(xué)人類學(xué)的學(xué)科性質(zhì)
隨著人類對世界認識的擴展和深化,各學(xué)科領(lǐng)域正在發(fā)生革命性的巨變:一方面,一些層次更高、綜合性更強、視野更廣闊的新興學(xué)科應(yīng)運而生,一系列突破原有疆界而實行新的分化與整合的交叉學(xué)科、邊緣學(xué)科不斷涌現(xiàn),跨學(xué)科研究盛行;另一方面,同這種高屋建瓴、覆蓋極廣的宏觀把握相對照,學(xué)科分類卻越來越細,探索原始人類審美心理生成及其原始文化表現(xiàn)形態(tài)的奧秘,越來越成為當(dāng)今人類學(xué)研究的熱點。
美學(xué)人類學(xué),是文化人類學(xué)、文藝心理學(xué)和文藝美學(xué)的邊緣交叉而產(chǎn)生的新興學(xué)科。文化人類學(xué)與文藝心理學(xué)、文藝美學(xué)有不解之緣。一方面,人類進化的歷史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一部人類審美心理(精神)的生成史,人類審美心理的生成是文化人類學(xué)研究必須涉足的領(lǐng)域;另一方面,人類審美心理的研究成果,能給文化人類學(xué)、文藝美學(xué)以巨大的啟示。而人類從感知自然環(huán)境和打制第一件石器開始,就和文藝心理學(xué)、文藝美學(xué)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因而,文藝心理學(xué)、文藝美學(xué)與文化人類學(xué)的這種相互依存、相互滲透、邊緣交叉的必然存在,使“美學(xué)人類學(xué)”作為一門新興的多邊緣交叉學(xué)科,必然產(chǎn)生出它不朽的生命力。
美學(xué)人類學(xué)作為文化人類學(xué)、文藝心理學(xué)和文藝美學(xué)的一個跨學(xué)科研究的領(lǐng)域,其內(nèi)涵十分豐富,外延相當(dāng)廣闊,涉及多種學(xué)科研究的知識。但在文化人類學(xué)+文藝心理學(xué)+文藝美學(xué)這個邊緣交叉領(lǐng)域中,它既是一門新興的交叉學(xué)科,又是人類學(xué)的一個分支學(xué)科,即美學(xué)人類學(xué)。
所以,所謂美學(xué)人類學(xué),就是研究原始人類審美心理的生成及其文化表現(xiàn)形態(tài)的一門新興的多邊緣交叉學(xué)科。其目的在于:主要運用文化人類學(xué)、文藝心理學(xué)、文藝美學(xué)的方法和成果來研究原始人類審美心理的生成規(guī)律及其原始文化表現(xiàn)形態(tài),揭示出文化藝術(shù)最原初因而有可能是最本質(zhì)的規(guī)定性,而這種規(guī)定性又恰恰是在進入文明時代以后被遺忘了的,或者是被某些文化現(xiàn)象所遮蔽了的,甚至是被某些似是而非的理論和學(xué)說所歪曲了的。從而,最終揭示出原始人類之所以要創(chuàng)造出這些原始文化藝術(shù)的原始動機、審美心理狀態(tài)、社會文化背景,以及原始文化藝術(shù)的本質(zhì)。從而,初步建構(gòu)起一個較為科學(xué)系統(tǒng)的美學(xué)人類學(xué)的學(xué)科體系。
二、美學(xué)人類學(xué)的研究對象
一門學(xué)科能否獨立存在,還取決于其是否具有自己明確的研究對象。美學(xué)人類學(xué)是多邊緣交叉學(xué)科,其中最主要的是文化人類學(xué)、文藝心理學(xué)和文藝美學(xué)的邊緣交叉。可以說,正是以這三門學(xué)科為主線的多邊緣交叉處成為美學(xué)人類學(xué)的研究領(lǐng)域。從這里入手,運用文化人類學(xué)、文藝心理學(xué)、文藝美學(xué)的研究成果,去探索、推測、揭示原始人類審美心理的生成及其文化表現(xiàn)形態(tài),發(fā)現(xiàn)原始人類隱藏在原始文化藝術(shù)中的藝術(shù)生命的核糖核酸和遺傳密碼,揭示文化藝術(shù)的本質(zhì),這是美學(xué)人類學(xué)應(yīng)該承擔(dān)的責(zé)任。
在美學(xué)人類學(xué)研究對象中,原始人類審美心理的生成是一個核心的命題,是貫穿美學(xué)人類學(xué)的一根“中軸”。從研究原始人類審美心理的生成這一中心命題出發(fā),美學(xué)人類學(xué)的研究任務(wù)主要包括兩大內(nèi)容:
(一)人類審美心理生成論。主要包括人種進化對原始人類審美心理的奠基、自然環(huán)境對原始人類審美心理的滋養(yǎng)、圖騰崇拜對原始人類審美心理的培育、宗教巫術(shù)對原始人類審美心理的模塑、神話傳說對原始人類審美心理的浸潤、倫理民俗對原始人類審美心理的規(guī)范等內(nèi)容。由此,我們得出一個結(jié)論:原始人類的審美心理潛伏于高等動物(人猿)的種族先天生理遺傳之中,發(fā)端于原始人類時空觀念的形成和對自然美的感知體驗,表顯于第一件石器工具(也是第一件藝術(shù)作品)的制作,生成于自然崇拜、圖騰崇拜、宗教巫術(shù)、神話傳說、倫理民俗等后天自然環(huán)境和社會文化影響。
(二)人類原始文化形態(tài)論。主要包括原始宗教文化的表現(xiàn)形態(tài)、原始文學(xué)的表現(xiàn)形態(tài)、原始表演藝術(shù)的表現(xiàn)形態(tài)、原始造型藝術(shù)的表現(xiàn)形態(tài)、民族服飾文化的表現(xiàn)形態(tài)、民族節(jié)日文化的表現(xiàn)形態(tài)等內(nèi)容。通過這些內(nèi)容的研究,我們得出第二個結(jié)論:原始文化是原始人類審美心理的外化。原始文化表現(xiàn)形態(tài)是原始人類審美心理外化的表現(xiàn)形式,原始人類審美心理與其原始文化表現(xiàn)形態(tài)之間存在著深層次的對應(yīng)同構(gòu)關(guān)系,原始文化起源于原始人類審美心理生成的地方。我們不同意國內(nèi)外學(xué)者認為原始人類審美心理與原始文化藝術(shù)同步生成的觀點,認為原始人類審美心理生成在先,原始文化藝術(shù)起源在后。沒有先在的審美心理圖式,原始人類的第一石器工具(也是第一件藝術(shù)作品)是無法打制的。只是原始人在打制過程中(相當(dāng)于現(xiàn)今的藝術(shù)家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審美心理結(jié)構(gòu)圖式又得到了提升,達到新的審美結(jié)構(gòu)層次。如此循環(huán)往復(fù),直達現(xiàn)今。
三、美學(xué)人類學(xué)的研究方法
學(xué)科的研究方法是由學(xué)科的性質(zhì)和研究對象所決定的。美學(xué)人類學(xué)作為文化人類學(xué)、文藝心理學(xué)和文藝美學(xué)的多邊緣交叉學(xué)科,它的研究方法必須采用綜合研究的方法。其中主要是:
(一)文化人類學(xué)方法。即用文化人類學(xué)的方法和成果探討原始人類審美心理發(fā)生發(fā)展的軌跡及其文化表現(xiàn)形態(tài)。文化人類學(xué)考古發(fā)現(xiàn)的文化遺存,是原始人實踐活動的產(chǎn)物,是歷史的見證,可以作為我們探索原始人類審美心理的生成及其文化表現(xiàn)形態(tài)的直接依據(jù)。因為每一件石器、每一幅原始壁畫巖畫、每一件原始工藝品,以及刻繪在這些工藝品上面的花紋、圖案,不管它是粗陋的還是精細的,都是原始人類實踐的產(chǎn)物,都是他們的審美心理外化或物態(tài)化的表現(xiàn)形態(tài)。只是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這些原始文化遺存留給我們的,還只是原始人類審美心理的物化形式和產(chǎn)品,而不是他們的審美心理結(jié)構(gòu)和活動過程本身。只有對這些物化的審美心理成果進行科學(xué)的分析,才能透視原始人類在制做這些物品時的審美心理的活動特征和美學(xué)水平。此外,世界近代特別是中國西南一些較好地保留著原始文化的特殊的少數(shù)民族,它們?nèi)缤盎畹纳鐣保瑥囊粋€個橫斷面上生動地再現(xiàn)了原始文化的發(fā)展史,從而為我們研究原始人類的審美心理及其文化表現(xiàn)形態(tài)提供了可以直接觀察的經(jīng)驗材料,彌補了史前資料的不足。這就主要牽扯到兩種田野作業(yè)方法:一是社會田野作業(yè)。即親身參與到研究場城里,觀察體驗、調(diào)查搜集各種素材;二是文本田野作業(yè)。即在文本
里搜集自己所需要的研究素材。被稱為“坐在安樂椅子上的人類學(xué)家”的弗雷澤的《金枝》,就是其范例。
(二)文藝心理學(xué)方法。其中包括兩項內(nèi)涵:(1)將“審美心理”和“審美意識”明確區(qū)分。“審美意識”是審美心理的自覺部分,它與理性思維密切相關(guān),是審美心理的表層部分,與原始人類審美心理的切合點極少。“審美心理”則充滿審美思維內(nèi)在空間結(jié)構(gòu)的全部,特別是占審美心理絕大部分空間的個體無意識和集體無意識(種族無意識),對研究原始人類審美心理的生成及其原始文化形態(tài)極為重要。因為,在發(fā)生學(xué)研究中,我們面對的是原始人類非自覺、非理性的和深層的心理整體以及各種心理機能的綜合形式結(jié)構(gòu),因而采用“審美心理”才能準(zhǔn)確、貼切地指稱原始人類的精神整體。(2)采用文藝心理學(xué)的研究方法。主要運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學(xué)、榮格的分析心理學(xué)、阿恩海姆的格式塔心理學(xué)、馬斯洛的人本主義心理學(xué)和亞杰的發(fā)生認識論心理學(xué)的理論及相關(guān)心理學(xué)方法,如觀察推測的方法、內(nèi)省體悟的方法、問卷的方法、心理測試的方法等。使我們的研究進入到目前文化人類學(xué)尚未深入到的深層領(lǐng)域,逐步接近原始人類的精神特征和生命本質(zhì)。
(三)文藝美學(xué)方法。文藝美學(xué)是對文化藝術(shù)現(xiàn)象和形態(tài)作形而上的宏觀闡釋的美學(xué)的分支學(xué)科。它著重研究文化藝術(shù)活動這一特殊審美活動的特殊規(guī)律以及審美活動規(guī)律在文化藝術(shù)領(lǐng)域中的特殊表現(xiàn)。文藝美學(xué)把審美主客體的關(guān)系、文化藝術(shù)的本質(zhì)、文化藝術(shù)的審美構(gòu)成、文化藝術(shù)形態(tài)、文化藝術(shù)闡釋接受、文化藝術(shù)審美教育等作為主要研究對象。文藝美學(xué)方法最大的優(yōu)點在于:將美學(xué)與詩學(xué)統(tǒng)一到人類的詩思根基和人的感性審美生成上,透過文化藝術(shù)的創(chuàng)造、文本、接受這一活動系統(tǒng)去看人自身審美體驗的深拓和心靈境界的超越。文藝美學(xué)方法的發(fā)展趨勢是:(1)對創(chuàng)作主體的研究,主要采用精神分析和直覺主義等方法;(2)對作品文本的研究,主要采用格式塔心理學(xué)、結(jié)構(gòu)主義、俄國形式主義、新批評等方法;(3)對接受主體的研究,主要采用接受美學(xué)、讀者反映批評等方法。從而,達到對文化藝術(shù)多層次審美規(guī)律的把握和文化藝術(shù)生命底蘊的深拓,探尋人類文化藝術(shù)的生命意義和人類感性審美生成的奧秘。
(四)跨文化比較研究方法。其中包含四個內(nèi)涵:(1)跨民族比較。這就需要我們真正借助文化人類學(xué)的宏觀視野,走出民族自大或民族虛無主義的怪圈,采用比較方法闡釋原始人類審美心理生成的共同特征及族群間審美心理的個性差異。(2)跨文化比較。原始人類的各族群由于人種遺傳、自然環(huán)境、宗教倫理等不同,必然形成不同的審美心理特征和文化形態(tài),美學(xué)人類學(xué)研究必須進行跨文化比較,才能祛除單一文化視野的盲視,增加和擴展理論推演的準(zhǔn)確性和涵蓋率,使美學(xué)人類學(xué)的研究取得理想的效果。(3)跨學(xué)科比較。除對文化人類學(xué)、文藝心理學(xué)、文藝美學(xué)進行比較研究,較好地實現(xiàn)它們的邊緣交叉外,還要吸收與研究對象密切相關(guān)的體質(zhì)人類學(xué)、考古學(xué)、人種學(xué)、思維學(xué)、腦科學(xué)、生理學(xué)、社會學(xué)、社會心理學(xué)等“近鄰學(xué)科”的洞見。(4)跨時期比較。即將原始人類與文明人類的審美心理和文化形態(tài)進行縱向比較,以說明兩類審美心理與文化形態(tài)的傳承和區(qū)別。其中必須鮮明地確立起三個參照系統(tǒng):一是高等動物靈長類特別是人猿的審美心理特征。這是人類原始思維和審美心理由此發(fā)生的自然前提。二是文明人的審美心理特征。這是原始思維的歷史終點和審美心理的嶄新層次。以此為參照,我們將容易判斷原始人類的原始思維、審美心理和文化藝術(shù)在其各個階段的特征和所達到的美學(xué)水平。三是兒童心理的發(fā)生過程。這屬于人類個體心理的早期階段,它和原始人類的思維和審美心理是一種個體與種系的關(guān)系。以此為參照,也將有助于我們具體把握人類審美心理各個階段的特征。由此,建構(gòu)起一種文化人類學(xué)式的整體觀和整合觀。
人類學(xué)的研究方法范文第3篇
關(guān)鍵詞:文化;人類學(xué);危機;生命文化學(xué)
眾所周知,人類學(xué)家宣稱,人類學(xué)是關(guān)于人類歷史的科學(xué)。美國的人類學(xué)研究傳統(tǒng)分為四支(特別是在Boasians的研究推動之后):生物人類學(xué)、考古人類學(xué)、語言人類學(xué)和文化人類學(xué)[1]。Robert Borofski(2002)的研究揭示出來,在文化人類學(xué)的子分支之間的聯(lián)系已經(jīng)非常薄弱[2]。人類學(xué)的分支越來越專一化。過度的專業(yè)化是人類學(xué)面臨的一個問題。
人類學(xué)面臨的第二個問題是“文化”這個詞本身。20世紀初,人類學(xué)家把人類學(xué)界定為關(guān)于文化的科學(xué),而現(xiàn)在人類學(xué)家逐漸變?yōu)槲幕芯糠矫娴膶<襕3]。人類學(xué)家把文化界定為他們用來研究世界上不同人類群體的生活方式的理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工具。大量關(guān)于文化的概念起源于20世紀的上半個世紀[4]。盡管文化的概念眾多并且沒有確立一個統(tǒng)一的標(biāo)準(zhǔn),但是人類學(xué)家普遍承認這樣的假設(shè):文化是后天習(xí)得的,基于符號的歷史產(chǎn)物。換句話說,文化與自然相對,擁有自己存在和進化的方式。
而到了20世紀下半葉,文化達到了一種濫用的程度,尤其是被“種族中心論”的人誤用。Adam Kuper陳述了它的成功:“現(xiàn)在每個人都進入到文化中來。”[5]換句話說,我們正在見證這個世界的文化膨脹。
Keesing在1974年預(yù)測了未來的研究熱點:“‘雅諾馬米文化’、‘日語文化’、‘文化的發(fā)展’、‘自然與文化’:我們的人類學(xué)家仍然使用這個詞,我們?nèi)匀徽J為這意味著什么。但是從靈長類動物存在的學(xué)習(xí)傳統(tǒng),使用工具和操縱符號,我們再也不那么肯定文化符號的習(xí)得性遺傳是人類所獨有的了。”
僅僅一年后,Edward Wilson出版了《社會生物學(xué):新的綜合》。他定義社會生物學(xué)為“所有社會行為生物學(xué)基礎(chǔ)的系統(tǒng)研究。[6]”同時,他宣稱社會生物學(xué)的目的是“利用當(dāng)代綜合進化論的成果重新規(guī)劃社會科學(xué)。[7]”
自從70年代以來,所謂的進化派社會科學(xué)一直在學(xué)術(shù)界中發(fā)展和傳播。我用“進化的社會科學(xué)”這一標(biāo)簽來稱謂用進化論的方法來研究人類文化的那一派研究。這個標(biāo)簽反映了在科學(xué)和社會科學(xué)研究前沿的交叉,現(xiàn)在有很多學(xué)者使用這個詞。在進化的社會科學(xué)領(lǐng)域最先進的無疑是社會生物學(xué)、進化心理學(xué)、人類行為生態(tài)學(xué),人類行為學(xué),模因論、以及“基因――文化”共同進化的的方法。上述學(xué)科的代表發(fā)展了他們自己關(guān)于文化的概念,我們稱之為文化進化論。
那么,早期文化人類學(xué)家把文化定義為一種后天習(xí)得的基于符號的歷史產(chǎn)物,而社會生物學(xué)家的定義則是完全對立的,他們認為文化是一種生物學(xué)上的適應(yīng)性,或者說文化是符合“自私的基因”的利益的。進化心理學(xué)和人類行為學(xué)中也有關(guān)于文化的類似表達。
人類行為生態(tài)學(xué)和“基因――文化”共同進化理論,都在文化人類學(xué)對立的角度使用文化的概念,但是在研究方法上兩者有所不同。他們認為文化不是生物適應(yīng)的產(chǎn)物,基因并不能操縱文化。
在行為生態(tài)學(xué)中文化是在某種特定的生態(tài)環(huán)境下生物最大化自己繁殖度的適應(yīng)性策略。他們在人類行為的水平上研究文化;他們認為文化是一種對于當(dāng)?shù)厣鷳B(tài)環(huán)境和社會文化環(huán)境的適應(yīng)型策略(SmithWinterhalder1992).那么,文化是一種行為的適應(yīng)性。
共同進化方法包括基因和文化之間的相互動力系統(tǒng)。例如,William Durham已經(jīng)列出了基因與文化作用的五種關(guān)系(1991):cultural mediation(文化調(diào)節(jié)),genetic mediation(基因調(diào)節(jié)),enhancement(增強),neutrality(中立)and opposition(反對).前三種是互動的,后兩種是比較的(Durham 1991,205207)。總之,他認為兩者在互動中可能會影響到對方。基因與文化的關(guān)系將參照:(1)相同的目標(biāo)(增強);(2)矛盾的目標(biāo)(反對);(3)不同,但目標(biāo)并不矛盾(中立)。文化不能解釋為基因進化的產(chǎn)物。在協(xié)同進化理論中,文化是基因與社會文化環(huán)境協(xié)同進化的產(chǎn)物。
在前面的論述中,我概述了目前的被看作是整體科學(xué)的人類學(xué)中的危機。首先是,人類學(xué)的過度強調(diào)分支化和跨人類學(xué)的薄弱的合作性。其次,危機的根源是,文化概念在人類學(xué)中的滑坡,它被指責(zé)將西方的工具加在非西方的社會中的一種中心主義的建構(gòu)。第三個根源是,“文化”這個概念的膨脹,人類學(xué)成功地給出“模因”,并認為它承載了一個更為寬泛的意義,它最終將涵括任何東西。并且如果是在這種意義上,文化實際上是一個空洞的詞匯。危機的最后一個根源是,在進化社會科學(xué)中對文化這個概念的寬泛的討論。它的表征是從人類學(xué)意義上來使用這個概念,但是一般來說,這并不是一個合適的背景。
基于文化學(xué)理論框架的生命文化學(xué),方便了人們對進化社會科學(xué)和人類學(xué)的理解,生命文化學(xué)是一個文化學(xué)的分支。生命文化學(xué)這個概念是由美國人類學(xué)家伊諾?若斯在1980年提出的,它是一個物理人類的分支的標(biāo)簽,主要是從文化人類學(xué)的觀點,來關(guān)注文化和生物現(xiàn)象。生命文化進化從文化屬于非生物學(xué)的適應(yīng)性這個前提出發(fā),將人類與其它生物區(qū)分開來,但是它并不意味著,人類獨立于他過去的進化。
相反,文化有它進化的根源,人類是被他的特征所決定的,并且建立在人類基因的生物進化過程中。另外,生命文化學(xué)處理一種更為寬泛的主題包括動物和人類的不同。生命文化學(xué)進一步研究的是生物和文化適應(yīng)性及進化之間的關(guān)系,分析社會生活的主要因素,并關(guān)注后天PK先天討論的結(jié)論。生命文化學(xué)可以從文化人類學(xué)的傳統(tǒng)這一方面和從進化社會學(xué)另一方面,為了支持人類作為生命文化個體的整合性研究。簡單來講,生命文化學(xué)采用了從科學(xué)和社會科學(xué)中認識的相關(guān)的發(fā)現(xiàn)并從文化角度來進行解釋。
生命文化學(xué)對于目前的人類學(xué)在三個方面的難題起作用。首先,生命文化學(xué)支持科學(xué)和社會科學(xué)的交叉性學(xué)科的合作性研究。其次,它將文化看作是在科學(xué)對人的研究中理論上、認識論上和方法論上的工具。最后,它方便了對人類學(xué)和進化論方法在文化的研究上,對人類本質(zhì)的二分的難題的克服。
[參考文獻]
[1]Kuper,Adam(2000):Culture:Anthropologists’Accoun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Kuper,Adam(2000):Culture:Anthropologists’Accoun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Borofski,Robert(2002):The Four Subfields:Anthropologists as Mythmakers.American Anthropologist,104(2),s.463480.
人類學(xué)的研究方法范文第4篇
20世紀70年代以來,人類學(xué)內(nèi)部逐漸出現(xiàn)了一股“歷史化”(historicization)的思潮,即:人類學(xué)日漸注重歷史研究的視角,開始關(guān)注“他者”的歷史,由此產(chǎn)生了新的理論洞見和新的研究方法。一方面,揭示了“他者”是有歷史的,并在歷史建構(gòu)中具有重要的能動作用,以此為基礎(chǔ)提出了“文化界定歷史”的創(chuàng)新性理論架構(gòu),沖擊了傳統(tǒng)的“客觀歷史”說,根本性地突破了人類學(xué)中長期存在的“文化”與“歷史”、“結(jié)構(gòu)”與“歷史”、“結(jié)構(gòu)”與“事件”等基本矛盾的對立。另一方面,傳統(tǒng)民族志也得到了更新改造,人類學(xué)研究方法從單一的田野調(diào)查中解脫出來,走進了歷史的“田野”之中,融文獻史料、田野調(diào)查于一體,人類學(xué)文化撰寫方式日漸呈現(xiàn)綜合性、多元化的發(fā)展態(tài)勢;同時,這種方法論意義上的發(fā)展與更新還相應(yīng)帶來了認識論上的深刻變革,凸顯了“他者”與世界共享著同一時間和空間的歷史,對隱藏于人類學(xué)知識生產(chǎn)過程中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論思想進行了解構(gòu)。總之,人類學(xué)的“歷史化”,正如弗賓(James D.Fauhion)所言,“已經(jīng)成為一種多變的社會和文化現(xiàn)象,它并不僅僅代表一種純知識體系上的更新變革,也標(biāo)志著倫理、道德和政治上的轉(zhuǎn)型”。除了上述社會環(huán)境的影響之外,筆者認為,有利的學(xué)術(shù)環(huán)境是促動西方人類學(xué)“歷史化”的不容忽視的深層次因素。本文將對西方人類學(xué)“歷史化”的學(xué)術(shù)環(huán)境進行系統(tǒng)梳理,以期能對全面、深入理解西方人類學(xué)的“歷史化”有所裨益。
一、西方新史學(xué)對人類學(xué)理論與方法的關(guān)注
德國蘭克史學(xué)作為西方傳統(tǒng)史學(xué)(政治史階段)的代表,在進入20世紀尤其是在二戰(zhàn)后,遭到了法國年鑒學(xué)派、英國史學(xué)和美國社會科學(xué)史學(xué)的批判。這些后起學(xué)派主張跨學(xué)科,提倡總體史,注重底層的歷史(history from below),關(guān)注經(jīng)濟社會史,由此引發(fā)了戰(zhàn)后以經(jīng)濟社會史為主要標(biāo)志的西方新史學(xué)(社會史階段)的到來。在稍后的70-80年代,以后現(xiàn)代主義文化批評、歷史敘述主義和文化人類學(xué)為理論源泉,新文化史應(yīng)運而生,即西方史學(xué)又出現(xiàn)了由經(jīng)濟社會史向文化史過渡的新趨勢。在實現(xiàn)這兩次轉(zhuǎn)型的過程中,西方史學(xué)對人類學(xué)理論與方法表現(xiàn)出極大關(guān)注,或者說人類學(xué)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第一次轉(zhuǎn)型過程中(社會史階段),西方史學(xué)開始對人類學(xué)傳統(tǒng)主題和方法產(chǎn)生興趣。法國年鑒學(xué)派主要開創(chuàng)者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創(chuàng)造奇跡的國王》(1923年),從那時的宗教禮儀、風(fēng)俗習(xí)慣、醫(yī)療狀況等為傳統(tǒng)史學(xué)家所忽視的史料人手,研究了法國民眾的風(fēng)俗與信仰,揭示了當(dāng)時的普遍社會心態(tài);另一位開創(chuàng)者呂西安?費弗爾(Lucien Febvre)的《拉伯雷的宗教》(1942年),沒有像傳統(tǒng)史學(xué)那樣以拉伯雷的書為史料去探討拉伯雷的思想,而是著力考察拉伯雷所處時代的社會文化和風(fēng)俗,剖析該時代的各種社會文化因素和社會心態(tài)結(jié)構(gòu)。法國年鑒學(xué)派的第二代領(lǐng)軍人物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在《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時期的地中海世界》(1949年)中,強調(diào)了長時段中的結(jié)構(gòu),認為傳統(tǒng)史學(xué)所關(guān)注的事件并不是重要的。法國年鑒學(xué)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勒華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蒙塔尤》(1975年),利用宗教法庭的審訊記錄,吸收了民族志撰寫中的一些表現(xiàn)手法,生動地描繪了蒙塔尤這個14世紀法國小村莊普通村民的家庭生活狀況。英國史學(xué)家愛德華?湯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1963年)中,把19世紀英國工人階級的態(tài)度和意識作為研究對象,研究其文化的構(gòu)成,認為工人階級身份的真正形成不僅僅是社會經(jīng)濟意義上的,還包括工人階級對自身地位的文化認同。
在第二次轉(zhuǎn)型過程中(文化史階段),人類學(xué)中的一些重要思想和新方法被借鑒到史學(xué)領(lǐng)域中來,對史學(xué)的影響更為直接和強烈。被視為“宏觀意義上”的歷史學(xué)家的美國人類學(xué)家吉爾茨(Clifford Geertz),將文化比喻為尋找解釋意義的文本(text),倡導(dǎo)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寫作方法。這些見解和方法受到了許多新文化史家的青睞。戴維斯(Natalie Z.Davis)的《馬丁?蓋赫返鄉(xiāng)記》(1984年),以16世紀法國農(nóng)村中的一個冒充農(nóng)婦丈夫的陌生人如何被接受和被拒絕為題材,指出通過深入研究該地區(qū)的社會經(jīng)濟狀況和兩性關(guān)系的史料,史學(xué)家可以重構(gòu)該農(nóng)婦的思想歷程,即歷史學(xué)家可以通過一個朝著史料定向但又超越于它以外的想象力來填補史料中的漏缺。在戴維斯看來,事實與虛構(gòu)之間并元明顯的界線,但首先要承認來源于解釋學(xué)的、存在一個諸如農(nóng)民文化之類的更大的整體性聯(lián)系,這樣的重構(gòu)才能成為可能。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的《屠貓記》(1999年),從解釋18世紀的一群印刷工人集體屠貓這樣一個事件出發(fā),用人類學(xué)家研究異文化的方式來處理自身的文明,用民族志觀察入微的方式來洞察歷史,揭示了當(dāng)時法國人心態(tài)中對貓的種種象征意義以及屠貓行為所具有的儀式性和文化解釋,深入探討了18世紀法國人的思考方式。
自結(jié)構(gòu)功能學(xué)派產(chǎn)生到20世紀60年代,西方人類學(xué)在整體上多是拒斥歷史的,這使得人類學(xué)“主動疏遠”了歷史學(xué),它們之間的界限也變得涇渭分明。而西方史學(xué)在二戰(zhàn)后的兩次轉(zhuǎn)型,對人類學(xué)理論與方法的關(guān)注和借重,使兩個學(xué)科之間的關(guān)系重新密切起來,達到了更高層次上的“合流”(convergence)和“復(fù)交”(reapprochement),從而為20世紀70年代以來人類學(xué)的“歷史化”傾向營造了良好的學(xué)科外部環(huán)境。
二、在西方人類學(xué)中的興起和影響
20世紀70年代的人類學(xué)是人類學(xué)的時代,孕育了法國結(jié)構(gòu)和英、美政治經(jīng)濟學(xué)等新的人類學(xué)理論流派。這些新流派試圖對的某些方面加以應(yīng)用、修正和新的詮釋,從不同角度體現(xiàn)人類學(xué)對“歷史”的“關(guān)懷”,為70年代以來西方人類學(xué)“歷史化”潮流的發(fā)生和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有利的學(xué)科內(nèi)部氛圍。
西方人類學(xué)發(fā)端于法國,英、美等國的人類學(xué)界也受到影響。二戰(zhàn)后,法國人類學(xué)界出現(xiàn)了列維一斯特勞斯(Levi-Strauss)的結(jié)構(gòu)主義人類學(xué),列維-斯特勞斯相信支 配歷史進程的是一種無意識的潛在因素,這種潛在因素只有通過理論上的分析才能揭示出來,而的“唯物史觀”(historical materialism)相信歷史是由寓于生產(chǎn)方式運動之中的內(nèi)在矛盾決定的,矛盾又是人們經(jīng)過精心的研究之后才發(fā)現(xiàn)的。因此,在列維-斯特勞斯看來,他的“結(jié)構(gòu)”概念和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是內(nèi)在一致的。在上述思想的影響下,以葛德利爾(Maurice Godelier)為代表、試圖對馬克思的生產(chǎn)模式(mode of production)理論進行修正的法國結(jié)構(gòu)學(xué)派應(yīng)運而生。1966年,葛德利爾出版了代表作《經(jīng)濟上的理性與非理性》。該書強調(diào)文化中非經(jīng)濟性制度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組織中所發(fā)揮的經(jīng)濟,并以功能性的階序觀來取代生產(chǎn)模式觀。葛德利爾主張把生產(chǎn)模式看成一個系統(tǒng),而內(nèi)部各個結(jié)構(gòu)分別為小的系統(tǒng),小系統(tǒng)在整體中發(fā)揮不同功能,若超越了相互之間的約束力即功能相容性的范圍時,則發(fā)生社會組成和歷史的變遷。這與把系統(tǒng)內(nèi)部的矛盾尤其是階級斗爭視為歷史發(fā)展的動力已經(jīng)有了本質(zhì)上的區(qū)別。葛德利爾對歷史發(fā)生興趣的目的在于修改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使之在的基本構(gòu)架下適用于前資本主義社會演變的研究,所以他所研究的歷史其實是在“靜態(tài)”的結(jié)構(gòu)理論的架構(gòu)上建立起的社會進化史,盡管其材料來自人類學(xué)家的實地研究,并在很大程度上已經(jīng)擺脫了早期進化論者的臆測。“歷史在葛德利爾那里,既不是年代學(xué)的重擬,也不是人類學(xué)合作主體借以建構(gòu)他們的世界的過程,正確地說,歷史是把社會現(xiàn)象的起源看作從社會制度的邏輯中推演出來的派生物。”因此,雖然葛德利爾聲稱人類學(xué)是人類學(xué)與歷史學(xué)差別消失的地方,但真正的歷史研究卻被他忽略了。盡管法國結(jié)構(gòu)學(xué)派受到了種種批評,但它以其特有的方式關(guān)注了歷史分析,為發(fā)展出一種具有“批判性”的解釋理論做出了貢獻。
二戰(zhàn)后,美國人類學(xué)界出現(xiàn)了懷特(Leslie Alvin White)的新進化論和斯圖爾德(Juliar Haynes Steward)的多線進化論。與摩爾根(Lewis Henry Morgan)的早期進化論相比,懷特的進化論體現(xiàn)的是一種更為系統(tǒng)化的技術(shù)決定論,強調(diào)進化過程的不可分割的整體性;斯圖爾德則更注重進化路線的復(fù)合性和多樣性。他們都企圖對的歷史發(fā)展階段理論進行修正。哈里斯(Marvin Harris)把斯圖爾德和懷特的理論統(tǒng)合起來,提出了文化生態(tài)學(xué)和文化唯物論的觀點,尋求環(huán)境需求與社會制度之間的直接因果關(guān)系,尋求支配歷史發(fā)展的新法則。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抨擊哈里斯的基礎(chǔ)上,提出社會文化決定生產(chǎn)過程的新觀點――因為文化既決定人們要生產(chǎn)什么,又決定人們怎樣去生產(chǎn)。此外,薩林斯還對馬克思的歷史決定認識性質(zhì)的觀點做了新的詮釋。在薩林斯看來,人類創(chuàng)造了自身的歷史,但人類只能根據(jù)自身的意識來創(chuàng)造歷史,因為認識總要受制于文化。斯圖爾德的學(xué)生沃爾夫(Eric R.Wolf)和敏茲(Sidney W.Mintz)則著重應(yīng)用世界體系理論以及中資本主義制度下有關(guān)農(nóng)民社會的有關(guān)理論,研究了農(nóng)民社區(qū)內(nèi)外的階級關(guān)系,研究了地方性、小規(guī)模農(nóng)民社區(qū)與其所處的廣闊政治經(jīng)濟過程之間的關(guān)系,將地方史置于世界史的范疇和視野之中。
20世紀20年代到60年代的英國人類學(xué)界,功能論、平衡論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因此往往忽略了強調(diào)階級沖突和矛盾的,對研究中的殖民情境(colonial situation)幾乎視而不見。英國曼城學(xué)派的代表人物格拉克曼(Glackman)強調(diào)社會沖突,但從整體上講他從沒有采納過的理論。他的弟子沃斯利(Peter Worsley)在題為《號角即將吹響》(1957年)的一項研究中,強調(diào)被研究的那些部族正在受到廣大地域中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剝削和利用,才日漸顯示了觀點的影響。1973年,由阿薩德(Talal Asad)編輯的論文集《人類學(xué)與殖民遭遇》已經(jīng)明顯受到了的影響,開始對以往英國人類學(xué)靜態(tài)的、和諧的、無歷史的功能論展開嚴厲批判,揭示了人類學(xué)與殖民主義之間的深層次關(guān)聯(lián):功能論者用“原始人”來代替“被殖民化的人”,缺乏一個對殖民情境的整體性概念,沒有把殖民形式整合到他們的分析中去;以馬林諾夫斯基為代表的應(yīng)用人類學(xué)更是與“間接統(tǒng)”、“殖民地管理”密切聯(lián)系在一起,將作為政治和歷史問題的殖民制度與人類學(xué)之間的聯(lián)系掩蓋起來,他們既是非歷史的(a-h(huán)istory,以拉德克利夫一布朗為代表),也是反歷史的(anti-h(huán)istory,以馬林諾夫斯基為代表)。自此,以功能論、平衡論為特色的英國人類學(xué)逐漸改觀,開始注意“他者”的歷史,關(guān)注隱藏在研究者與“他者”之間的矛盾和斗爭。
三、西方人類學(xué)的反思
西方社會科學(xué)的整體反思(reflexivity)或解構(gòu)(deconstmction),建立在西方20世紀60年代以來蓬勃開展的各種社會反省運動的基礎(chǔ)之上。這種反思,來自對“殖民情境”的檢討,源自對西方政治權(quán)威、學(xué)術(shù)霸權(quán)的解構(gòu)。當(dāng)知識創(chuàng)新的批評精神在現(xiàn)象學(xué)哲學(xué)、解釋學(xué)、后現(xiàn)代主義思潮滲入實地調(diào)查的經(jīng)驗研究以后,在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催生了人類學(xué)的反思意識。以往的“無歷史”的田園詩般的“現(xiàn)實主義”民族志描述方式成為反思和批判的對象,歷史人文主義成為新的實驗民族志的主要追尋目標(biāo)之一。
由后現(xiàn)代主義等新思潮武裝起來的新一代人類學(xué)家,試圖使人類學(xué)帶有敏銳的政治和歷史感,力求使人們對文化多樣性的方式有新的洞察。他們在對傳統(tǒng)的文化撰寫方式進行反思、對寫作的文本本身進行解構(gòu)的同時,開始嘗試和實驗新的表述方式:一是涉及對描述困境的新感受性,即在文化全球均質(zhì)化觀念下表述文化差異所存在困難的感受;二是涉及對歷史和政治經(jīng)濟現(xiàn)實的再認識。在后一種實驗策略中,又有兩個不同的走向:其一,受到政治經(jīng)濟學(xué)、世界體系理論的強烈影響,試圖克服以往人類學(xué)將自己局限于地方社會、相對缺少歷史觀點的局面,將大規(guī)模政治經(jīng)濟體系與地方文化狀況聯(lián)系起來。這種走向還對民族志美學(xué)化、詩學(xué)化提出了批評,認為要把民族志作為一種歷史現(xiàn)象去理解,結(jié)合社會、政治和物質(zhì)去理解。其二,受到解釋學(xué)的影響,探討民族志敘述中歷史時間與場合的恰當(dāng)?shù)谋硎龇绞剑瑢鹘y(tǒng)民族志或者將敘述置于歷時背景之下或者將歷史一并放棄的種種做法提出批評。這種新的實驗策略就是要使民族志富有歷史感,在民族志敘述框架中展示時間和歷史的視野。
美國人類學(xué)家哈里斯認為,后現(xiàn)代主義在人類學(xué)中最有代表性的體現(xiàn)之一就是后過程主義(postproeessualism),即:不存在客觀的過去,我們對過去的呈現(xiàn)只是源自個人社會文化視角所制造的文本,是我們自己的一種“創(chuàng)造”。他指出,考古學(xué)等研究進化的科學(xué)忽視了社會行動的意義建構(gòu)以及人類文化的歷史特殊性,科學(xué)思想根深蒂固的早期人類學(xué)家試圖客觀地描 述現(xiàn)在,但實際上與寫小說無異。后現(xiàn)代主義等思潮對科學(xué)、技術(shù)負面影響的批判,對被科學(xué)扭曲的人性的關(guān)注和推崇,使20世紀70年代的人類學(xué)逐漸從“科學(xué)”人類學(xué)的影子中走出來,“人文歷史主義”成為新一代人類學(xué)家深切關(guān)注和反思的時代主題。有學(xué)者認為,這會從整體上對人類學(xué)造成危機;但也有學(xué)者認為,這是人類學(xué)激動人心的新時代的開始。
人類學(xué)自身的反思,既是時代整體反思的產(chǎn)物,也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人類學(xué)在自身反思與實驗過程中所體現(xiàn)的對人文歷史主義的推崇、對民族志描述歷史化的訴求,加速了人類學(xué)研究方法的轉(zhuǎn)換、更新,促進了人類學(xué)“歷史化”思潮的醞釀與形成。
四、美國民族歷史學(xué)的特殊貢獻
民族歷史學(xué)(ethnohistory)的概念,最初可能是由博厄斯(Franz Boas)的學(xué)生威斯勒(Clark Wissler)于1909年率先提出來的。在他看來,民族歷史學(xué)就是依靠結(jié)合民族史和考古學(xué)的數(shù)據(jù)來重建史前文化,就是紀實檔案(documentary)的同義語。當(dāng)然,這種檔案并不是由當(dāng)?shù)赝林鴣硖峁┑摹?915年,博厄斯的另一個弟子羅維(R.H.Lowie)對民族史研究中口述史的真實性做出了負面評價,進一步擴大了民族史研究的影響。當(dāng)時的民族史方法論,無論對人類學(xué)家還是對史學(xué)家而言,都是一樣的,即主要利用檔案資源來討論“他者”的過去。在20世紀上半葉,美國民族歷史學(xué)基本上以北美、非洲、大洋洲等地的小規(guī)模族群社會為研究對象。這一時期,無論是人類學(xué)家還是歷史學(xué)家,對此都不太關(guān)注,因為小規(guī)模族群社會并不是當(dāng)時史學(xué)研究所關(guān)注的重點,而人類學(xué)的研究目光也主要聚焦于尚與歷史有嚴重隔閡的現(xiàn)在時民族志上。因此,20世紀上半葉的美國民族歷史學(xué)作品數(shù)量不多、影響有限,其主要作用在于最初填補了人類學(xué)與歷史學(xué)之間的空白領(lǐng)域。
20世紀30-40年代,以博厄斯的學(xué)生克魯伯(A.L.Kroeber)、米德(Margaret Mead)、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等形成的所謂心理結(jié)構(gòu)學(xué)派(文化與人格學(xué)派),幾乎背離了博厄斯所開創(chuàng)的歷史主義傳統(tǒng)。隨著心理結(jié)構(gòu)學(xué)派的興起,美國民族歷史學(xué)在二戰(zhàn)前的作用和影響更為微弱。二戰(zhàn)后尤其是50年代,歷史主義重新在美國民族學(xué)、人類學(xué)界抬頭,1954年創(chuàng)刊的Ethnohistory則突出體現(xiàn)了這種情緒。這一時期,美國民族歷史學(xué)主要有兩大方面的特征:利用文字檔案材料探討印第安各部落的傳統(tǒng)邊疆問題,以幫助他們維護自己的土地所有權(quán);出現(xiàn)了所謂的“經(jīng)濟人類學(xué)”,即從歷史主義的觀點、用現(xiàn)代的經(jīng)濟概念去研究原始社會。其方法論依然如故,以有文化的非土著所提供的檔案等為主,而不是本土的口述資源。自此,美國民族歷史學(xué)作為一種獨特的學(xué)術(shù)思潮和新的研究范式,才登上了西方學(xué)術(shù)舞臺,并日漸繁盛。
20世紀上半葉,人類學(xué)與歷史學(xué)之間的劃分是明確的,但從70年代以來,這兩個學(xué)科明顯匯合了。人類學(xué)家使用歷史材料和歷史學(xué)方法,史學(xué)家也使用人類學(xué)的田野調(diào)查方法。由此,原初作為在人類學(xué)與歷史學(xué)問起聯(lián)系和溝通作用的民族歷史學(xué),隨著時代的變遷,其內(nèi)涵的界定也就變得越來越困難。有學(xué)者猶豫地仍稱之為民族歷史學(xué);有學(xué)者簡單地將之視為歷史學(xué);有學(xué)者認為,民族歷史學(xué)不再是一門學(xué)科,而是一種方法;有學(xué)者認為民族歷史學(xué)是重建無文字民族的歷史;有學(xué)者則將之界定為歷史意識(historical consciousness)的研究;還有學(xué)者則戲稱民族歷史學(xué)為“歷史學(xué)與人類學(xué)的雜種兒子”。
在凱奇(Shepard Krech Ⅲ)看來,20世紀70年代以來人們已經(jīng)對民族歷史學(xué)本身的界定持有懷疑態(tài)度,很難對“ethnohistory”、“historical anthropology”抑或“anthropological history”進行明確區(qū)分。有些學(xué)者拒絕使用“ethnohistory”這個名稱,而代之以“anthrohistory”或者其他術(shù)語。民族歷史學(xué)已經(jīng)逐漸失去了“民族”(ethnos,ethnicity,ethnic)的味道,不再像原來那樣帶有某些歧視色彩地用來專指部落少數(shù)民族的民族史(ethnohistory),而變?yōu)闅v史人類學(xué)(historical anthropology)或者人類學(xué)史學(xué)(anthropological history),成為人類學(xué)理論方法與史學(xué)理論方法互換、混合的產(chǎn)物,成為人類學(xué)“歷史化”的產(chǎn)物。“Ethnohistory”這個名稱,也逐漸為“historical anthropology”或者“anthropological history”所取代。無論哪種取代,都合乎邏輯,都不會辱其名,因為人類學(xué)學(xué)者應(yīng)該關(guān)注“anthropological history”,正如歷史學(xué)者應(yīng)該關(guān)注“historical anthropology”一樣。凱奇認為,使用“anthropological history”更為合適,“anthropologieal history”能表征時下“ethnohistory”所代表的真正內(nèi)涵,能大致消除用語上的混亂局面。
席費林(Edward Schiefflin)和耶韋特(Deborah Gewertz)的討論主要在于揭示民族歷史學(xué)的本質(zhì)特征。在他們看來,“在過去,民族歷史學(xué)指的是利用文獻或考古材料建構(gòu)民族史。對歷史學(xué)家(及許多人類學(xué)家)來說,傳統(tǒng)上民族歷史學(xué)指的是替沒有文字歷史的民族重建歷史,……對我們來說,這種民族史的觀念即使不能說不對,也是不適當(dāng)?shù)摹褡鍤v史學(xué)……最根本的是要考慮到當(dāng)?shù)厝俗约簩κ录窃趺礃?gòu)成的看法,以及他們從文化角度建構(gòu)過去的方式”。這種見解,與之后以薩林斯為代表的西方人類學(xué)“歷史化”思想的主旨是一脈相承的。
人類學(xué)的研究方法范文第5篇
“范式”這一概念最初是由托馬斯?庫恩(Thamas Kuhn)提出來的,指的是常規(guī)科學(xué)所賴以運作的理論基礎(chǔ)和實踐規(guī)范,是從事某一科學(xué)的科學(xué)家群體所共同遵從的世界觀和行為方式。科研范式?jīng)Q定了某一科學(xué)共同體在某一專業(yè)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基本觀點,為他們提供了共同的理論模式和解決問題的框架,形成了該科學(xué)共同的傳統(tǒng),并為該科學(xué)的發(fā)展規(guī)定了方向。
教育人類學(xué)在“田野工作”(field work)的基礎(chǔ)上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研究范式。這種研究范式主張從書齋的思辨式研究轉(zhuǎn)移到注重實際的調(diào)查研究。書齋思辨研究重視理論推理,重視邏輯的嚴密性、理論的普適性,但由于過分關(guān)注理論本身的邏輯結(jié)構(gòu),使得學(xué)術(shù)研究容易脫離生活實際。在田野調(diào)查基礎(chǔ)上的研究則完全與之相反,其關(guān)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教育教學(xué)行為,重視對教育現(xiàn)象的搜集和整理。因此,從書齋到田野研究范式的改變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研究者的信念和科研模式。
教育人類學(xué)研究范式主要體現(xiàn)為以下四點:一是“跨文化研究”。教育人類學(xué)以不同文化背景的教育為研究對象,從而發(fā)現(xiàn)和解釋不同民族與文化背景下教育的差異。因此,研究者必須深入他者文化中,從該文化背景的教育實際出發(fā),在具體的文化中進行研究、分析。二是田野工作的研究方法。田野工作的具體技術(shù)為實地觀察法,要求避免單純理論想象和假設(shè)推斷,主張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要求研究者長期生活在被調(diào)查的對象之中,融入其生活并與其建立良好的人際關(guān)系,從而搜集、記錄和整理當(dāng)?shù)厝说男袨榛蛎咳瞻l(fā)生的事情,“其目標(biāo)是在基于直接觀察和準(zhǔn)確理解當(dāng)?shù)厝说恼鎸嵱^點的基礎(chǔ)上,對教育的事件、情形作充分的描述,其目的是為對某一民族或語言等特殊問題作進一步深入了解提供信息”。三是重視個案研究。教育人類學(xué)反對那些宏大敘事的抽象論述,主張深入實際、在詳細調(diào)查基礎(chǔ)上的個案分析。四是理論建構(gòu)。教育人類學(xué)的研究不僅僅體現(xiàn)在對不同文化背景下教育現(xiàn)象、問題的調(diào)查,同時強調(diào)在這種實地調(diào)查基礎(chǔ)上的理論總結(jié)與概括。也就是說,教育人類學(xué)研究者不僅是一位實踐的探索者,而且還是理論的建構(gòu)者,在田野工作中通過實地觀察、訪談、問卷分析等形式,發(fā)現(xiàn)新問題,驗證假設(shè),形成正確判斷,構(gòu)建新理論以及為社會實踐作出貢獻。
二、田野工作:教育人類學(xué)研究范式的基本方法
田野工作最先由動物學(xué)家哈登介紹到人類學(xué)中,隨著博厄斯、摩爾根、馬林諾夫斯基等對該方法的成功運用,使其成為人類學(xué)研究區(qū)別于諸如歷史學(xué)、社會學(xué)、政治科學(xué)、文學(xué)、宗教研究的重要標(biāo)志。田野工作也是教育人類學(xué)最基本的一種研究方法,它要求教育人類學(xué)研究者于某一地點或區(qū)域住上一段時間(人類學(xué)研究一般在1年以上),把握當(dāng)?shù)啬甓戎芷谥薪逃虒W(xué)的基本過程,與教師、學(xué)生形成密切的關(guān)系,參與他們的生活和學(xué)習(xí)活動,從中了解他們的教育教學(xué)、人際活動、風(fēng)俗文化等。
我國教育人類學(xué)的田野工作大致分為三種:一種是對少數(shù)民族教育的研究,注重研究少數(shù)民族和原始部落人群的教育問題;二是對弱勢群體教育問題進行的田野工作,這類研究除了研究少數(shù)民族兒童的學(xué)習(xí)問題外,還注重對一些處境不利或弱勢人群的教育進行調(diào)查研究,如出生在城里的少數(shù)民族子女、進城農(nóng)民子女或貧困家庭子女的教育問題等;三是應(yīng)用人類學(xué)方法,從文化的角度對主流文化教育進行研究。因此,不同研究取向在田野點的選擇上就有較大區(qū)別。有一點值得肯定的是,無論哪一種田野工作,研究者必須把他感興趣的事件放在自然發(fā)生的情境中,資料的搜集來自于自然式的研究場域――田野,如教室、餐廳、學(xué)生宿舍、教師休息室、學(xué)生家庭等,通過持續(xù)地與研究對象進行接觸,獲得第一手資料。
教育人類學(xué)田野工作的具體技術(shù)為參與觀察法和深度訪談,另外可以配合一些問卷調(diào)查等其他研究方法。參與觀察法要求研究者在調(diào)查點長期居住下來,參與被調(diào)查者的生活與學(xué)習(xí),觀察他們的教育活動和個人言行舉止。因此,參與觀察法亦稱為“局內(nèi)觀察法”或“居住體驗法”。馬林諾夫斯基在其名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對特羅布里安德群島土著文化進行的就是參與觀察式的田野工作。在教育人類學(xué)田野調(diào)查中,僅靠研究者個人的觀察是不夠的,大部分的資料須依靠一些研究對象提供,這就必須采用深度訪談的方法。訪談的對象可以是教師、學(xué)生、學(xué)生家長。訪談的內(nèi)容既可以是針對訪談對象自身的教育問題,也可以是他所知曉的其他情況。一般而言,對訪談對象須精心選擇,對重點訪談對象更是如此。他(她)的年齡、性別、社會閱歷、職業(yè)、文化程度、社會地位、工作態(tài)度、語言表達能力、社會關(guān)系等都是必須予以認真考慮的。
教育人類學(xué)的迅速興起在于倡導(dǎo)了這種獨特的研究方法,改變了以往哲學(xué)思辨及詮釋的方法,注重田野工作,在調(diào)查研究的基礎(chǔ)上進行理論建構(gòu)。教育人類學(xué)研究不是從概念出發(fā)或沿用以往的解釋套路,而是依據(jù)田野工作中與調(diào)查對象共同生活所進行的參與觀察獲得的第一手資料,并使之與文化背景聯(lián)系來加以分析和闡釋。“教育的田野”賦予研究鮮活的生命和時代意義,記錄了社會文化下真實而豐富的教育發(fā)展,它會因時間的流逝而愈益散發(fā)出特有的時代價值。
三、踐行?做小?求真:教育人類學(xué)研究范式的科研精神
從書齋走向田野為教育人類學(xué)提供了一個從歷史發(fā)展高度全方位考察教育發(fā)展的新方法和新維度,其科研精神體現(xiàn)為如下幾點:
(一)躬行實踐,深入田野
20世紀初,部分人類學(xué)家意識到要想創(chuàng)造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就必須像其他科學(xué)家研究他們的對象那樣來研究自己的對象。為了更準(zhǔn)確地對文化進行描述,他們便開始同所研究的民族生活在一起,觀察并參與他們的某些重要事務(wù),并向土著詳細詢問他們的風(fēng)俗習(xí)慣,就這樣人類學(xué)開始了它的田野調(diào)查。作為人類學(xué)的分支學(xué)科,教育人類學(xué)強調(diào)田野工作的研究方法,主張深入田野,進行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深入“田野”,才會不斷創(chuàng)新,不斷發(fā)展;不進行調(diào)查,只顧埋頭于故紙堆里,就會因失去科研的源泉,致使創(chuàng)新干涸、枯竭。教育人類學(xué)研究者要進入校園、課堂、社區(qū)與家庭,與研究者長時間地交往、接觸,如有機會還要多參加一些地方的民俗活動,以更好地了解當(dāng)?shù)氐奈幕尘啊T谡{(diào)查過程中,研究者要以一個人類學(xué)家獨特的視角,以一定的身份,如一名老師的身份或輔導(dǎo)員的身份,融入教學(xué)過程中,參與到學(xué)生的活動中。“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這是一個教育人類學(xué)研究者的終身理念和不懈追求。
(二)知微見著,精益求精
中國古代哲學(xué)家老子提出:“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必作于細”。教育人類學(xué)研究側(cè)重于建立在個人經(jīng)驗基礎(chǔ)上的個案研究,反對那些毫無個人經(jīng)驗的宏大敘事。教育人類學(xué)主張作于“小”,“小”就是你從任何角度去放大或縮小,都不會變成模糊的視點;從任何局部去撫摩,都是豐潤飽滿的點觸;從任何時間去審視,都能成就經(jīng)久不衰的優(yōu)秀作品和完美演繹。“小”是一種厚積薄發(fā)的經(jīng)驗積累,是一種獨辟蹊徑的敏銳角度。也就是說,研究者的研究范圍和研究對象必須是
他能夠親眼觀察到的、親身體驗到的和親自了解到的。在這種經(jīng)驗基礎(chǔ)上,對個案進行深入調(diào)查、分析,最終目的是要由小見大。滕星先生所著《文化變遷與雙語教育――涼山彝族社區(qū)教育人類學(xué)的田野工作與文本撰述》一書可以說是國內(nèi)教育人類學(xué)研究的經(jīng)典之作。其以四川涼山彝族社區(qū)教育為研究對象,對20世紀后50年來語言與教育的社會變遷過程進行了描述,揭示了少數(shù)民族在力圖融入現(xiàn)代主流社會、分享現(xiàn)代化社會的權(quán)利與成果的同時,試圖保存自己的傳統(tǒng)語言與文化的兩難困境,并從教育人類學(xué)者的立場上給予意義上的解釋。之后,國內(nèi)又有多部教育人類學(xué)方面的著作問世,其共同的特征就是重視個案的研究,充分體現(xiàn)知微見著、精益求精的科研精神。
(三)追求本真,崇尚實學(xué)
早期的人類學(xué)者根據(jù)“野蠻人”或“原始人”的社會文化資料、殖民當(dāng)局的檔案、旅行家以及傳教士的記述,在“安樂椅”上進行理論建構(gòu)。人類學(xué)集大成者馬林諾夫斯基,一戰(zhàn)期間在新幾內(nèi)亞進行了為期兩年半的三次田野調(diào)查,之后出版了一系列與調(diào)查相關(guān)的著作。其集田野調(diào)查、民族志撰寫、文化功能學(xué)說的提出于一身,奠定了科學(xué)人類學(xué)的規(guī)范,同時為崇真尚實的學(xué)科精神奠定了基礎(chǔ)。他要求田野工作者以“文化持有者的內(nèi)部眼界”,去觀察當(dāng)?shù)匕l(fā)生的人和事。要求融入當(dāng)?shù)厣鐣M量做出符合“客觀實際”的描述和記錄。教育人類學(xué)秉承人類學(xué)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教育問題,通過實地調(diào)查有效地搜集研究對象的行為和背景資料,在參與研究對象的各種活動中感知其文化背景,在深入調(diào)查中踐行追求本真、崇尚實學(xué)的學(xué)科精神。教育人類學(xué)在中國的迅速發(fā)展,與其重視調(diào)查的研究范式及學(xué)科精神有著必然的聯(lián)系,它如一縷清風(fēng)在國內(nèi)的教育學(xué)研究中掀起一絲的波瀾;又如一塊隕石,厚重而深遠,滌蕩著學(xué)術(shù)氛圍中的浮躁,代表著學(xué)術(shù)研究的航標(biāo)。
四、田野工作的局限:教育人類學(xué)研究范式反思
(一)他者的聲音:能否反映真實情況
從書齋到田野,其本意就是盡可能多地接觸并了解研究對象,在這個過程中,強調(diào)主位研究(從研究對象的角度進行的研究)和客位研究(從研究者的角度進行的研究)的結(jié)合。基于田野工作,深入研究對象,與研究對象共同生活、學(xué)習(xí),在相互接觸和了解的基礎(chǔ)上進行研究,可以最大限度地發(fā)揮主位研究的科研價值,最大程度地反映研究對象的真實情況。
但是,田野工作畢竟有其局限性――他者的聲音能否反映真實?我們在做田野調(diào)查的時候,有人會說:“你怎么相信他們向你陳述的東西?他們向你講述的都是編出來的謊言,除了他們自己這些謊言可以蒙騙所有人。”在調(diào)查的過程中,我們也經(jīng)常地思考,研究者對教育現(xiàn)象或教育問題能夠較好地把握,但是能否真正理解教育現(xiàn)象背后的文化因素就不得而知了。另外,在有些田野工作中,還存在語言不通的情況,這就要求研究者想辦法解決語言障礙。解決這個問題有兩種途徑,一是掌握這門語言,二是通過翻譯。在短時間內(nèi)學(xué)習(xí)一門新的語言顯然是比較困難的,在筆者周圍的一些文化人類學(xué)研究者,他們在這種情況下經(jīng)常采取雇用當(dāng)?shù)厝藶榉g的做法。這種方法,對調(diào)查固然有立竿見影的效果,然而經(jīng)過翻譯這中間環(huán)節(jié)之后,收集的信息可能已經(jīng)帶有很多翻譯者主觀的因素,一定程度上可能會影響研究本身的真實性。教育人類學(xué)研究者深入教育第一線與研究對象長時間交往,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了解對方的文化,爭取更加扎實的田野工作。但是無論你如何與研究對象和諧共處,你永遠無法擺脫“他者”的身份。
(二)部分與整體:個案的選擇如何具有普遍意義
教育人類學(xué)的田野工作多是個案研究而非整體研究,這可能與因注重田野而限定了人類學(xué)的旨趣有關(guān)。由于方法論的特點,即要求參與觀察法,這就注定了研究者只能在某一個地區(qū)進行研究,因為對于一個稍大的區(qū)域進行研究是比較困難的。在回答“解剖麻雀”的微型調(diào)查在科學(xué)方法上有什么價值的問題時說:“如果只調(diào)查了一個中國農(nóng)村把所調(diào)查的結(jié)果就說是中國農(nóng)民生活的全貌,那是以偏概全,在方法上是錯誤的。如果說明這只敘述一個中國農(nóng)村里的農(nóng)民生活,那是實事求是的,但問題是只敘述一個中國農(nóng)村的農(nóng)民生活,有什么意義呢?”實際上,只是把江村調(diào)查看作是他進入這個“了解中國社會”領(lǐng)域的開始,他后面的調(diào)查和研究成果,如《祿村農(nóng)田》、《鄉(xiāng)土中國》、《行行重行行》等,都是把微型研究和宏觀研究相結(jié)合,用比較的方法從局部走向整體的結(jié)果,以此來反映中國社會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