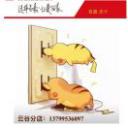談廣告的體驗偏向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談廣告的體驗偏向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一、媒介即體驗
(一)媒介的感知偏向
將自己的著作《古登堡星漢璀璨》視為伊尼斯觀點注腳的馬歇爾•麥克盧漢是加拿大學派當之無愧的旗手,甚至被戴上了“媒介環境學之父”的桂冠。在《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一書中,他開宗明義地闡明了其“媒介即訊息”的觀點,以表達傳播媒介的進化之于社會發展的重要意義,這一點與伊尼斯是一脈相承的。在這個中心思想主導之下,麥克盧漢在書中又提出“媒介是人的延伸”的觀點,他認為,印刷文字是眼睛的延伸,廣播是耳朵的延伸,衣服是皮膚的延伸,車輪是腿腳的延伸,電力技術是人中樞神經系統的延伸,游戲是人的延伸等等。這個他稱之為“人的延伸”的表述,擴展提出了媒介在感官上的偏向,即“延伸論”的表皮下隱含的是麥克盧漢的媒介感官偏向觀。從他對于“眼睛”、“耳朵”、“中樞神經”等的論述,我們可以肯定其延伸論主要圍繞著人的五官的感受進行,即任何一種媒介不過是嫁接在我們的五官上的“另一副五官”而已。“實際上,麥克盧漢說,只有兩種基本的感知空間或感知偏向:視覺和聽覺-觸覺(后者也叫聲覺)。在個人身上表現出來的最有趣的現象,并不是他擁抱哪一套思想、哪一個哲學體系,而是他喜歡哪一種感官。如果知道這一點,你就知道他這個人了,你就知道他棲居于哪一個空間——視覺空間還是聲覺空間,他的其他方面,包括哲學觀,你都可以推導出來了。”[2]麥克盧漢的一生都很執著于他的“媒介的感知偏向”觀。在后期他提出的“媒介即按摩”等更“離經叛道”的觀點,其實也是對“媒介感知偏向”的發展。
(二)媒介即體驗
伊尼斯的時空偏向觀、麥克盧漢的感官偏向觀、波茲曼的意識形態偏向,作為媒介偏向觀的三種不同觀點(由于篇幅限制這里不詳述),它們或批判,或樂觀,或憂慮,看似觀點不同,但卻又實質性的內在關聯,都認為某種特定的媒介形式會偏向于某些信息某些內容。如果說麥克盧漢的感官偏向論,其實就是一種體驗觀;那么,其他眾多學者尤其是媒介環境學者的在這方面的隱含、沿襲或發展,也已給我們繪制了一幅“媒介體驗”的圖譜。麥克盧漢強調的媒介帶來的巨大變化特別是感官的變化,其實談的就是“體驗”。這一觀點在某種程度上也影響了伊尼斯后期的研究。比如伊尼斯在其《傳播的偏向》一書中說了一句麥克盧漢式的話:“在口耳相傳中,眼睛、耳朵、腦袋以及感官和官能之間都協同運動,忙于合作和競爭,在功能上互相引導、刺激和補充。”即使不強調伊尼斯對于感官偏向的認同,我們也應知道,伊尼斯有關時空偏向的觀點,強調人的體驗活動憑借不同的媒介在時間維度和空間維度得到拓展等,其實已在他的媒介研究中提出了有關“體驗”的二元命題[3]。如果說這一時空體驗劃分,已建立了媒介體驗論初步基礎的話,麥克盧漢則更是將媒介與體驗的關系發揮到了極致。只不過,他強調的不是時空的體驗,而是轉向感官的體驗。而且在幾種感官體驗中,他又著重強調了視覺和聽覺。麥克盧漢很快就超越了伊尼斯,向前跨進一步。他認為,雖然每一種媒介對人的一切感官都產生影響,但是它們特別突出的影響,要么是視覺,要么是聽覺。反過來,這個影響的重點,又深刻影響著媒介使用者的整個觀點。[4]將麥克盧漢奉為教父的媒介環境學派繼承了他這一關注方向。如波茲曼在對“媒介環境學”定義的時候,首先強調了“媒介環境學考察媒介傳播如何影響人的感知、理解、情感和價值”這一重心,其實是承認了媒介的體驗特性。在麥克盧漢理論建樹的基礎上,媒介環境學有了它的兩個層面上的意義:作為感知環境的媒介,作為符號環境的媒介。媒介環境學者林文剛對這兩個層次有較清晰的交代:“正如麥克盧漢(1964)正確地提出的那樣,傳播媒介是我們(感官)的延伸。每一種媒介都體現著一套感官特征。對每一種媒介的使用都要求使用者用特定方式使用自己的感覺器官。”[5]“一方面,我們憑借視覺、聲覺、嗅覺、觸覺和味覺來感覺或感知我們周圍的物質世界;另一方面,我們又從媒介的符號世界內部去思考、感知、言說或表征物質世界。……從上述觀點來看問題,對作家而言,世界‘讀起來’就像一本書;對電影制片人而言,世界‘看上去’就像一連串并置的現象和聲音;如此等等。……”[6]無論是“作為感知環境的媒介”,還是“作為符號環境的媒介”,均可視為媒介所創造的體驗環境。“媒介體驗論”在其他學者的觀點中也有展現。如保羅•萊文森在其著作《數字麥克盧漢》、《思想無羈》中提出了“人性化趨勢”的媒介演化理論、“補償性媒介理論”等,主要認為在媒介歷史的演化中,人的媒介體驗有兩個目的(動機),即一是滿足渴求和幻想,二是彌補失去的東西,所有媒介終將變得越來越人性化。約書亞•梅羅維茨在《消失的地域:電子媒介對社會行為的影響》一書中提出的媒介場景理論則更是對體驗的環境作出了自己的解釋。“媒介體驗觀”的傳播學理論基礎可以追溯到媒介和受眾的充分的互動,它隨著媒介的升級變化而形成不同的體驗層次。如果說伊尼斯所崇尚的是口頭傳統以及時間和空間的平衡,而之前的無論印刷技術還是廣播技術,都割裂了這個完整的體驗;那么現今迅猛發展的新媒體技術似乎給整合和平衡創造了可能。依據保羅•萊文森的觀點,因特網作為一個“大寫的補償性媒介”,幾乎修補了之前所有媒介的不足。它擴大了人類感性實踐的范圍,是媒介體驗方式的革新,也是人類生存方式、感覺方式、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的革命。約書亞•梅羅維茨認為:“新媒介不僅影響了人們行為的方式,而且它們最終影響人們覺得自己應該怎樣行為的方式。行為和態度的這種變化,在‘更新’共享媒介環境內容時對系統進行了‘反饋’,這加強了電子媒介的整體影響。”[7]
隨著新媒體的發展,以及媒介的融合,媒介體驗可謂日趨人性化、多功能化,建筑在媒介平臺上的廣告的體驗也日趨綜合化,呈現出不同的體驗偏向。這個偏向,從多年來廣告業所倡導的“體驗經濟”、“體驗廣告”就可見一斑。最早提出體驗經濟一詞的是《第三次浪潮》的作者阿爾文•托夫勒,1970年他在《未來的沖擊》一書中提出,在經歷了農業經濟、工業經濟和服務經濟之后,經濟發展將走向體驗經濟(ExperientialEconomy)這一新的階段。體驗經濟將成為最新的發展浪潮。在他提出這個概念之后,1999年美國戰略地平線LLP公司的兩位創始人約瑟夫•派恩和詹姆斯•吉爾摩合著了《體驗經濟》(TheExperienceEconomy:WorkIsTheatreandEveryBusinessaStage)一書,體驗經濟才引起了廣泛關注。派恩認為,體驗經濟是一種以商品為道具,以服務為舞臺,通過滿足人們的各種體驗而產生的各種經濟形態,是一種最新的經濟發展浪潮,它超越了傳統簡單的買賣形式,使人們得到物質享受的同時得到精神享受。他們認為,在農業經濟時代,土地是最重要的資本;在工業經濟時代,產品是企業獲得利潤的主要來源,服務會使產品賣得更好;而體驗經濟則是服務經濟的最高層次,是以創造個性化生活和商業體驗獲得利潤的。他們觀察到,與傳統的商品和服務相比,消費者開始更喜歡消費體驗:“體驗是經濟所提供的第四種消費形式……當一個人購買一項服務的時候,他實際上是在購買一整套以他的名義進行的無形的活動。但是當他購買一種體驗時,他是在為抽時間享受一系列公司所組織的值得紀念的活動而付錢。這些公司所組織的活動就像是在一場戲劇演出中一樣,是為了使他以個人的方式參與……[8]”從“工作是劇院,業務是舞臺”的書名,我們就可以看到,盡管“體驗經濟”立足于經濟和營銷領域,但其探討的主要內容與前面所說的媒介體驗觀、媒介場景論卻是一致的。理查德•佛羅里達也曾重點提及創意階層成員的“體驗”需求:“約瑟夫•派恩與詹姆斯•吉爾摩在這里所談到的主要是像迪斯尼所提供的那類事先包裝好了的體驗。創意階層成員更喜歡更積極一些的、正宗的、參與性體驗,在其中他們可參與建構。……對體驗的追求超越了購買的范疇。……不管人們怎樣看,有一點是清楚的:體驗正在取代商品和服務,因為它們刺激了我們的創造官能、增強了我們的創造能力。[9]”在這樣一種理論背景和業界實踐背景下,體驗廣告、體驗營銷開始大行其道。按照波恩德•H•施密特(BerndH.Schmitt)所提出的理論,營銷工作就是通過各種媒介,包括溝通(廣告為其之一)、識別、產品、共同建立品牌、環境、網站和消費者,刺激消費者的感官和情感,引發消費者的思考、聯想,并使其行動和體驗,并通過消費體驗,不斷地傳遞品牌或產品的好處。根據他的體驗分類方式,體驗可以分為感官體驗、情感體驗、思維體驗、行動體驗、關系體驗等。那么隨之而來我們可以將體驗廣告分為感官體驗廣告、情感體驗廣告、思維體驗廣告、行動體驗廣告、關系體驗廣告等。其中的感官體驗廣告就是通過媒介來給消費者創造視覺、聽覺、嗅覺、味覺和觸覺等的綜合體驗。從這個角度上來講,體驗廣告的基本思想與麥克盧漢等媒介環境學學者的看法是不謀而合的。雖然很多人僅將體驗廣告當作是一種廣告形式,與其他廣告形式并列,但筆者不認為,每一則成功的廣告必然都是激起了受眾的某種體驗,只是這種體驗可能有偏向的,也可能是整合而均衡的。
三、廣告的體驗偏向:說辭、觀賞與游戲
無論按照媒介的體驗偏向理論譜系,還是體驗經濟的脈絡,我們都有理由假設,利用媒介平臺進行活動的廣告傳播,也是有偏向的。而這個假設可以在廣告傳播理論和實踐中得到驗證。根據媒介的不同發展階段,廣告時而偏向于話語,或偏向于形象,且大致分屬于不同的時期。
(一)語言的文化和形象的文化
在廣告中,存在著從“讀文”到“讀圖”的轉化。這與媒介的變遷,以及整個文化的文字為中心轉向形象為中心的軌跡是吻合的。我們的文化正處于從以文字為中心向以形象為中心轉換的過程中,思考一下摩西的訓誡對我們也許是有益的。……我相信,某個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對于這個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質重心的形成有著決定性的影響。[10]在后現代的理論建構中,利奧塔將“話語的/圖像的”二分,演繹為通常意義上的“現代/后現代”的二分,亦即“現代”是理性的話語中心,而“后現代”則呈現為感性的圖像中心。英國社會學家拉什根據利奧塔的二元結構,進一步提出了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的兩種藝術形態:現代主義藝術是“話語的文化”,而后現代主義藝術是“形象的文化”。雖然有學者對讀圖時代的到來和感性話語能幫助受眾審美的特點表示了肯定,但多數學者還是對于讀圖時代帶來的淺薄、支離和非理性表示了充分的憂患和擔心,如鮑德里亞、波茲曼等等都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這種趨勢的潛在破壞力。而美國學者道格拉斯•凱爾納則在其《媒介奇觀——當代美國社會文化透視》一書中將這種文化稱之為“媒介奇觀”,批判了消費主義社會中的奇觀現象。這種由語言和形象的文化區分同樣可以在廣告理論和思潮中展現。在20世紀以來的廣告思潮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USP理論、定位理論、議程設置理論,與品牌形象理論、CIS理論等等在“話語”和“形象”上有不同的偏重。而這種偏重,與傳播媒介的變遷又是統一的。
(二)根據媒介體驗論對廣告傳播理論的分期
在《當代廣告學》中,威廉•阿倫斯從經濟角度將廣告發展歷程劃分為4個時期—前工業化時期、工業化時期和后工業化時期。在定位理論當中,阿爾•里斯和杰克•特勞特曾提出三個時代的觀點,即產品至上時代、形象至上時代、定位至上時代。武漢大學張金海教授將20世紀廣告傳播理論及其發展分為產品推銷期、轉型期、新的理論發展時期(或稱“整合期”)三個時期[11]。推銷期的主要理論流派是“原因追究法派”、“情感氛圍派”、“科學推銷派”,USP理論屬于這個階段。轉型期理論從訴求走向創意,以奧格威品牌理論為代表。整合期的廣告理論從單一走向系統與整合,開始逐步營銷與傳播并重,標志是90年代整合營銷傳播理論的產生和發展。以上幾種廣告理論或實踐的分期方法,有其內在一致的地方,即均強調了推銷階段和形象階段。在這些分期觀點的基礎上,筆者嘗試用媒介體驗觀來闡述廣告傳播理論的發展脈絡和軌跡,其目的不是要精確地概括某個時間段上的廣告理論和實踐特點,而是較為宏觀的探尋和追蹤20世紀廣告傳播思潮(包括經典的理論和當時時興的思潮)和實踐發展的媒介體驗脈絡和體驗邏輯,并探索廣告發展的應然方向。追溯讀文與讀圖的流變過程,我們可以看到,從口語傳播時代,到印刷傳播時代,電子傳播時代和現在的網絡傳播時代,我們的廣告傳播理論確實是隨著媒介的發展呈現出不同的體驗上的偏向:讀文時代的偏向于說辭,讀圖時代的偏向于觀賞、網絡互動時代的偏向于游戲。
1.讀文時代的“說辭偏向”
至于“讀文”和“讀圖”,人類歷史上也經過了一個漫長的流變過程。人類的視覺活動可以說是與生俱來的,中國的文字最早也來源于圖畫,更別說各個民族的圖騰,因此在人類早期的漫長階段以讀圖為主的,準確地說是“前工業化早期”以前,均屬于視覺時代。此時,“在大眾教育出現以前,由于大多數人都不識字,因此人們采用代表商品或服務的符號或象征物進行廣告宣傳,如用一只靴子代表修鞋鋪。[12]”。到前工業化晚期,隨著紙張、印刷術的發明和運用,文字開始普及,人類開始進入到“讀文時代”。如尼爾•波茲曼對“讀圖”和“讀文”兩個時代如此評述:兩個世紀以來,美國人用白紙黑字來表明態度、表達思想、制定法律、銷售商品、創造文學和宣傳宗教。這一切都是通過印刷術實現的,也正是通過這樣的方式,美國才得以躋身于世界優秀文明之林。對于印刷機統治美國人思想的那個時期,我給了它一個名稱,叫“闡釋時代”。闡釋是一種思想的模式,一種學習的方法,一種表達的途徑。所有成熟話語所擁有的特征,都被偏愛闡釋的印刷術發揚光大:富有邏輯的復雜思維,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對于自相矛盾的憎惡,超常的冷靜和客觀以及等待受眾反應的耐心。到了19世紀末期,由于某些我急于解釋的原因,“闡釋年代”開始逐漸逝去,另一個時代出現的早期跡象已經顯現。這個新的時代就是“娛樂業時代”。[13]印刷術發明和推廣之后,“視覺符號的霸主地位受到文字的挑戰,出現了從視覺向語言過渡的趨勢。成前工業化后期廣告從視覺主因向語言主因過渡的原因有:一、印刷術的發明推廣促進教育的擴散和大眾傳播的發展;二、工業革命前,商品經濟不甚發達,廣告多集中用于土地、奴隸買賣、捉捕逃亡者和車輛運輸上,廣告內容通常僅限于解答兩個基本問題:什么地方和什么時間。回答這樣的問題,文字比圖片具有清晰準確的優勢。”[14]在印刷術主導的漫長的讀文時代,或者說“闡釋年代”,廣告傳播理論和思潮也呈現出“說辭偏向”。在20世紀六十年代以前,廣告理論和實踐上強調“勸服”的效果,包括理性勸服和情感勸服,但以理性勸服為主。“說辭偏向”階段的理論以約翰•肯尼迪的“印在紙上的推銷術”和羅瑟瑞夫斯的“獨特的銷售主張”理論為代表。“說辭”階段的理論和實踐強調“承諾,大大的承諾”,它著眼于運用各種方法來加強說辭的影響力。這種偏向發展到過度和極致,就轉變為“巧舌如簧”,其背后是對消費者的誤導與欺騙。
2.讀圖時代的“觀賞偏向”
到了工業化時期,電子媒介出現了,電視以其不可抗拒的方式進入到人們生活的主流,印刷媒體也開始再次強調視覺效果,消費主義漸成為主流的意識形態。人類社會再次進入“讀圖時代”,廣告也開始了其注重“觀賞”的階段。電視媒體對文化偏向的影響是巨大的,波茲曼、梅羅維茨等學者都曾探討過電視所帶來的場景的變化和對認知習慣的影響。電視對于廣告而言,則是使得廣告開始注重“奇觀化”和“觀賞性”,注重其“表演”特性。美國的商人們早在我們之前就已經發現,商品的質量和用途在展示商品的技巧面前似乎是無足輕重的。不論是亞當•斯密備加贊揚還是卡爾•馬克思百般指責,資本主義原理中有一半都是無稽之談。就連能比美國人生產更優質汽車的日本人也深知,與其說經濟學是一門科學,還不如說它是一種表演藝術,豐田每年的廣告預算已經證明了這一點。[15]從波茲曼稍顯偏激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出,他對于廣告所具有的“表演”傾向的深刻認識。確實如此,在電視為主導的時代,視覺觀賞的思維進入方方面面。這時候,廣告的文案和圖像就算同樣重要,文案所用的說辭性質也已開始悄然轉型,開始從印刷術時期的理性說辭,開始轉向感性說辭,也就是更具“觀賞性”的說辭。這些都是視覺感官的綜合影響。文字是一種思辯性的推理符號,故而“讀文時代”的話語本質是一種理性話語。而圖畫、圖像則是形象性的感覺符號,故而“讀圖時代”更重視視覺形象的感受和刺激,其話語是一種感性話語。20世紀六十年代之后的廣告理論就呈現出這樣的特點,如大衛•奧格威的“品牌形象理論”、李奧貝納的戲劇性理論以及業界風靡的CIS理論是這一階段的代表。在這個階段,不僅是廣告中更看重視覺效果,更是視覺思維控制了廣告實踐過程,廣告文案也更追求感官刺激。這種“觀賞偏向”,雖然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人們的視覺審美需求,但對其的過度追求,產生了消費主義意識形態,催化了社會上的物欲崇揚,產生種種弊端。
3.網絡互動時代的“游戲偏向”
按照萊文森的“補償性媒介理論”,數字媒體尤其是因特網作為一個“大寫的補償性媒介”,幾乎修補了之前所有媒介的不足。如果說之前的廣告傳播因為媒介的偏向的影響,偏向于視覺或聽覺,偏向于說辭或觀賞,那么因特網所主導的傳播則提供了整合這些感知偏向的條件,給予了融合的機會。而在網絡所有的廣告傳播形式當中,能夠彌合“說辭”與“觀賞”的偏向,并充分調動受眾的參與和互動,最能體現因特網感知融合的趨勢和互動特性的,莫過于“游戲”傾向的廣告傳播。這種“游戲”傾向的廣告傳播,被理解為“游戲廣告”顯然就太狹隘了,根據傳播學和西方文藝理論中有關美和游戲的思想,我們可以將它定義為那些能夠調動受眾參與性的、給受眾帶來愉悅的感受和美的體驗的廣告傳播實踐。早在幾十年前,心理學家斯蒂芬森就曾在其《傳播的游戲論》一書中提出了其游戲論思想,他將人類的所有行為分為工作和游戲兩種,由此分出兩種傳播:工作性傳播和游戲性傳播,并集中探討了傳播的游戲性質。雖然他把大眾傳播視為游戲性的傳播,被很多人認為是太過于夸大了傳播的游戲功能;但這一說法在新媒體時代卻很容易找到其落實的根基。以網絡為主的新媒體平臺極大地釋放了人們在工業化時代被禁錮的游戲天性,人們的游戲需求、對心靈自由的追尋以及對自然天性回歸的渴望,在這個已然被“異化”的時代里表現得格外強烈。由于新媒體的出現,我們早已進入“游戲時代”,游戲無處不在,互動、參與、分享等新媒體特征在游戲中多有展現。而廣告,也已開始著眼于增加消費者的游戲體驗,進入了游戲為主的階段。這一階段的實踐上,有各類體驗廣告的愉悅特性的增加以及網絡游戲廣告的風靡實踐為證。若是把這種對游戲和自然天性的向往解釋為簡單的娛樂化,是不合適的,也不利于引導未來的廣告傳播理論發展的正確方向。在西方哲學和文藝美學中“,游戲”是一個常與“美”并提的概念。席勒、赫伊津哈等多位學者都在很早的時候就談到過游戲的意義,都曾給過游戲很高的贊譽。席勒說:“只有當人充分是人的時候他才游戲;只有當人游戲的時候,他才完全是人。”荷蘭著名文化史學家約翰•赫伊津哈在其著作《游戲的人》前言中寫道:“歷經多年,我逐漸信服文明是在游戲中并作為游戲并展開的。”就連我們熟悉的麥克盧漢也在其《理解的媒介——論人的延伸》中專辟一節談“游戲——人的延伸[16]”。席勒認為美就是“純粹的游戲”,現實存在的美與現實存在的“游戲沖動”是等同的,都是追求心靈的自由。“游戲”常被分為“感性的游戲”(獲得快感愉悅)和“審美游戲”(獲得美的體驗)兩個層次,若是借用這個層次劃分來反觀目前游戲體驗式廣告和環境藝術廣告等的實踐,我們可以說現實廣告傳播中的游戲性中蘊含著“美”的潛質和“美”的努力,但目前還大都處于感性游戲、快感愉悅階段。若是能使“感性游戲”走向“審美游戲”,那么,我們就有可能從現實傳播的游戲偏向中尋求到糾正“說辭”之偏和“觀賞”之偏的曙光。由于此階段游戲傾向的傳播實踐中對“美”的追尋,本身亦在嘗試階段,加之還未達到真善美統一的生態之境,故它也是有“偏向”的。值得注意的是,這時候的游戲,雖然目前僅是一種潮流,卻已具備了成為發展方向的可能性。這時候的游戲偏向階段,從媒介體驗的角度,已立足于調動消費者的各種感官形式,或借助于一定的平臺(如網絡)實現各種感官體驗的平衡和愉悅,因此也是一個試圖抹平時空偏向和感官偏向的時期,是一個體驗被整合和均衡的階段。以上三個階段有理論和實踐出現的大致時間先后關系,但又部分相互重疊,形成了從強調“說”到強調“看”到強調“互動”的這樣一個理論和實踐發展模型。理論的走向映證和迎合了媒介發展的脈絡。說辭、觀賞、游戲,不僅僅是“說”、“看”和“玩”的等級變化,它還是從“被動”到“旁觀”到“參與”的變化,是從或偏理性、或偏感性再到感知和諧的變化,并與不同媒介時代緊密相關。目前的“游戲偏向”階段雖然更多的表現為快感愉悅的滿足上,精神愉悅的追求還較少。但我們期待著這種游戲偏向能帶領著廣告傳播理論與實踐走向真善美統一、感性和理性和諧的生態廣告階段。
作者:范小青單位: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2009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