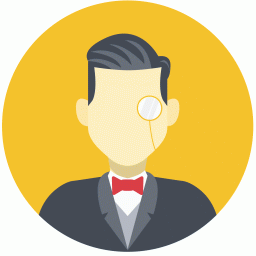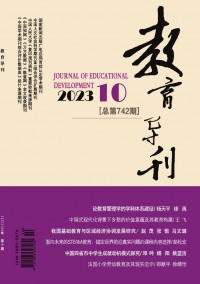教育理論表達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教育理論表達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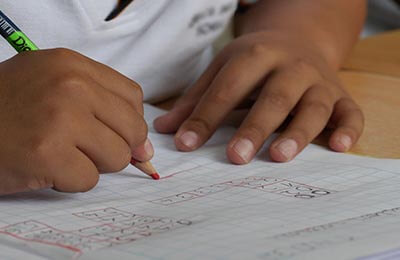
教育理論脫離教育實踐已引起人們的警覺,諸如教育理論研究重理論輕實踐的傾向,教育研究評價重數量輕質量的誘導,教育實踐運作的權威主義的主導以及教育實踐評價的唯升學考試的逼迫,等等。不過,除了上述原因之外,教育理論未能恰當、貼切地表達教育實踐,也是造成教育理論脫離教育實踐的一個重要原因。為了進一步拉近教育理論與實踐的關系,本文就教育理論如何表達實踐這一問題進行學理分析,認為教育理論要想恰當、貼切地表達實踐,需要從敘述對象、敘述邏輯、敘述風格與敘述線索上重新進行反思與審視,教育理論需要從觀念敘述、實體敘述、宏大敘述及單一本質敘述轉變為現實敘述、關系敘述、事件敘述及多元本質敘述。這樣,教育理論才能更加恰當、貼切地表達教育實踐。摘要:教育實踐是教育理論的生命之源,同時也需要教育理論的滋養。但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之間卻出現了深深的裂痕乃至鴻溝,由此產生了教育理論如何表達實踐的問題。教育理論要想恰當、貼切地表達實踐,需要從觀念敘述、實體敘述、宏大敘述及單一本質敘述轉變為現實敘述、關系敘述、事件敘述及多元本質敘述。這樣,教育理論才能更好地表達教育實踐。
關鍵詞:教育理論;教育實踐;敘述
一教育理論是由一系列概念、范疇、命題、判斷與推理所組成的系統知識。教育理論在其展開的過程中,必然要選擇某一敘述對象作為理論的起點,需要遵循某種敘述的邏輯,進而形成某種敘述風格,而敘述對象的選擇、敘述邏輯的遵循與敘述風格的形成與敘述線索的確定有著密切的關聯。從一定意義上說,敘述線索對應著理論言說者的本體論,是理論言說者考察敘述對象的根本視角,也是作者世界觀、價值觀的集中體現。下面就具體地透視傳統的教育理論在敘述對象、敘述邏輯、敘述風格以及敘述線索上的特征,并分析這些特征導致教育理論脫離教育實踐的緣由。
在敘述對象上,傳統的教育理論常常從抽象的觀念出發,即使聯系到教育實踐也是用現存的教育事實來論證自己的教育理論的科學性與合理性,采用的是“原理+事例”的敘述方式,這種做法只是在形式上看來是將教育理論與實踐溝通聯系起來,而實質上卻只是用已有的理論裁剪教育實踐。“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1]因此,這種以某一抽象的觀念、論斷為敘述對象的教育理論,難免與教育實踐產生阻隔,因為教育實踐總是處在一定的社會———文化的境脈中,那種脫離一定的社會———文化境脈的敘述無疑是“紙上談兵”。在敘述邏輯上,傳統的教育理論之所以從某一抽象的觀念、論斷開始,就是秉承、遵循著一種實體邏輯的緣故。所謂“實體邏輯”就是相信自然、社會的發展變化存在著某種先在的固定秩序,某一抽象的觀念或論斷就是對這種先在的固定秩序的反映。這種先在的固定秩序反映到人們的頭腦中,在柏拉圖那里是“善”的理念,在神學那里是“上帝”,在黑格爾那里是“絕對精神”,在普通人那里也許是“終極真理”。而所有這些觀念、符號在后現代主義者看來無非是人們自己套在自己脖子上的“枷鎖”,“只是一種由于猶太—基督教的神學/形而上學概念在西方文化中的千年統治而造成的某種知識論上霸權的幻象而已。”[2]具體到教育理論的闡述,受這種實體邏輯的限制,總是想表達一種能夠解釋、規范、指導多樣的、變化的教育實踐的“萬能”理論,崇尚、追尋一種“烏托邦”式的理論表達,而這種“萬能”、“烏托邦”式的理論表達至多只是表達了一種教育實踐的樣式。拿這種“萬能”、“烏托邦”式理論規范教育實踐難免會產生“水土不服”的不良反應,乃至造成“善”的惡果。在敘述風格上,倘若信奉實體存在,沿著抽象觀念、論斷闡述教育理論,就難免使教育理論高懸在天國之中,慣于宏大敘述,使教育理論的表達僅僅停留在知識、觀念層面上,而遇到概念、范疇的沖突就用辯證法加以化解。即使在思考現實的教育問題時,也常常跳過對客觀現實的精確判斷,直接以大而化之的“應該”來對付,而不是深入調查研究教育的實際狀況,直接以理想的“應該”置換復雜的“本來”。在教育理論的闡述中,大量存在著“既……又……”、“一方面要……另一方面要……”的言論,這種教育理論表達的至多是一種邏各斯/思想上的“可能性”,或一種“無條件/無限制的”可能之道。而教育實踐需要的是一種實踐者的“踐行之道”,而這種“踐行之道”總是受著特定的教育條件的限制,而那種“無條件的”、“無限制的”涵蓋一切可能性的可能性只能屬于上帝,因而對人而言是“空洞的”、“不可能的”可能性。即便教育理論闡述的是在邏各斯/思想上的“可能性”,但這種“可能性”并不必然等同于教育實踐的“可行性”。[3]當把“可能性”誤當成“可行性”而強迫教育實踐遵循時,其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在敘述線索上,之所以傳統教育理論難以融入教育實踐,不僅因為它大多抽象地觀念性觀照教育實踐,而且因為它大多追求一種單一的教育本質。當教育理論宣稱自己找到或發現這種教育本質時,也就會用所謂的客觀規律或真理來裝扮自己,并進而用這種教育理論強制教育實踐就范,宰制教育實踐。實際上,自從有了人類,也就有教育,也就有了人們對教育的思考。教育到底意味著什么?如果從人類教育演變的歷程來考察,教育則具有多重意義。“教育意味著工具,教育意味著生活,教育意味著事實,教育意味著對教育的反省。”[4]在這一長串的“菜譜”背后是否有一種統一的理解?可以說,如果有對教育的統一理解的話,這種統一的理解也只能產生于人們所共同持有的話語語境中。當話語語境(共同設定的判斷前提)發生變化時,教育的意義也就隨之發生變化。因此,言說教育的教育理論,不能是眾口一辭的“大合唱”,而只能是眾聲喧嘩。好的教育理論只能是以“真”的方式對教育“價值/好”和達至教育“價值/好”的途徑的訴說,不可能提供一種完滿的絕對真理的回答。
二如果說傳統的教育理論在表達教育實踐時,在敘述對象、敘述邏輯、敘述風格及敘述線索上存在著不足,那么,新的教育理論應該如何表達教育實踐?而要回答這個問題就需要搞清楚教育實踐到底需要什么?眾所周知,任何教育實踐都是具體的,都存在于一定的社會———文化的境脈之中,都具有由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所形塑的獨特特征,因此,教育實踐需要的是適合其具體情況的“踐行之道”,而這種“踐行之道”顯然并不是那種“大而全”或虛無縹緲之道,即這種“踐行之道”需要的并不是那種所謂的“普適真理”。這種“踐行之道”的獲得只能是在現實的具體教育問題的刺激下,經由提出假設,不斷試錯到解決問題的過程。同時,這種“踐行之道”也會隨著教育實踐的發展和新的問題的產生,再提出新的假設,再建立新的“因應之道”,從而使“踐行之道”的探求成為一個持續不斷的提出假設、驗證假設到解決問題的周而復始的踐行過程。
這樣看來,教育實踐需要的“踐行之道”是具體的,而這種具體的“踐行之道”又是多樣的、變化的。但是,教育實踐需要的具體的、多樣的、變化的“踐行之道”并不意味著所有的“踐行之道”都具有同等的地位,沒有高下優劣之分,沒有對錯好壞之別。正是由于教育實踐是發生于一定的社會———文化的境脈之中,是在一定的時間、地點、情形、背景下的踐行,這種踐行就會受到特定的社會———文化的境脈的制約,也會受到具體的時間、地點、情形的限制,從而使具體的、多樣的、變化的“踐行之道”有了比較優劣高下,判別對錯好壞的可能,這也是為什么教育實踐需要教育理論的原因所在。
一旦搞清楚了教育實踐的需要,并知道了“踐行之道”的特征,那么教育理論如何更好地表達教育實踐,從而彌補傳統教育理論的不足。既然傳統的教育理論運用觀念敘述、實體敘述、宏大敘述及單一本質敘述并不能夠很好地表達教育實踐,難以滿足教育實踐的需求,那么新的教育理論的表達就必須改弦易轍,另起爐灶,就需要從觀念敘述、實體敘述、宏大敘述及單一本質敘述轉變為現實敘述、關系敘述、事件敘述及多元本質敘述。在敘述對象上,新的教育理論要面向教育實踐的具體問題。也就是說,教育理論要想真正表達實踐,就得直面現實的教育問題,使教育理論植根于活的教育實踐之中。這既是教育理論更好地表達教育實踐的立足點,也是教育理論改善教育實踐的前提。倘若沒有對現實的教育實踐問題的關懷、聚焦,就根本談不上對教育實踐的改善。這樣,如何從紛繁雜多的教育實踐的矛盾與困惑中提煉出有意義的問題,則成了建構新教育理論的關鍵。而要想提煉出有意義的教育實踐問題,就需要對教育實踐有深刻的感受與體驗。擁有教育實踐的感性經驗和情感體驗是導引教育理論表達的內在動力,也使教育理論的闡述擁有了深厚的教育經驗與體驗的鋪墊與支撐,從而使教育理論的言說成為一種真實而富有生機的教育思想的流動。
在敘述邏輯上,新的教育理論要摒棄那種實體敘述,運用關系敘述深刻把握變動不居的教育實踐。實體敘述實質上并不是從教育實踐的構成因素間的關系和以教育實踐為基礎的人的主體性關系中去思考教育問題,而是把教育實踐中的諸多關系自覺或不自覺地分解、分化開來,然后再以其中的一極為基點,建立起絕對一元的實體理論。比如,在教育與社會發展的關系上,我們有時信奉教育萬能論,有時則悲嘆教育適應論,而缺乏對二者關系的動態把握,陷入了一種二元對立的實體敘述的窠臼之中。而用關系敘述置換實體敘述,才能在對教育實踐的經驗感受、情感體驗的基礎上,深入探究教育實踐諸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與影響,才能深刻把握教育實踐發展變化的動態規律,才能準確洞察教育實踐發展的多種可能性,進而獲悉支配教育實踐和引導教育實踐發展的多種可能性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從而才能全面地闡明教育實踐發展的邏各斯/思想上的多種可能性,為指導、規范教育實踐提供一幅清晰的認知圖景。
在敘述風格上,新的教育理論要變宏大敘述為事件敘述。宏大敘述雖然能夠給人們提供教育發展的整體信息,但是對于具體的教育實踐而言,這種宏大敘述也存在空泛、朦朧之弊。事件敘述就是關注日常教育生活的細小事件,運用“個案深度詮釋”方式,充分展現、揭示其蘊涵的意義。當然,要想對某一教育事件進行有價值的“個案深度詮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對教育事件獨具的意義有一個準確的判定,既要判斷這一教育事件是否特殊,也要辨別它是否具有一定的普遍意義。同時,對教育事件的“個案深度詮釋”還要做到真實、真誠地描述與呈現,要避免公共話語的裝扮和華麗辭藻的美化,其價值不在于是否能夠確證某一預設的觀念或理論,而是要真實地展示一種有關教育的新發現。如果說人是懸浮在自我編織的意義之網中的動物,那么對教育事件的“個案深度詮釋”,則是對其所編織的意義之網和它的主體的發現或再發現。
在敘述線索上,新的教育理論要變單一本質敘述為多元本質敘述。教育實踐是客觀性與主觀性、穩定性與流變性以及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集合體,那種單一本質的敘述并不能全面揭示教育實踐的“事實本身”。而一旦直面教育實踐的“事實本身”,也就回到了那種心物尚未分離的活生生的“現象世界”,就可以使人們生活于其中的教育實踐以其本來的面目呈現在人們面前。對這種教育實踐的“事實本身”的呈現、表達,從原則上說,需要教育理論以“真”的方式對什么是“有價值/好”的教育以及如何達至“有價值/好”的教育進行訴說。[5]所謂以“真”的方式訴說有兩重基本的含義:
(一)教育理論陳述需要建立在實證科學對教育實踐的現實狀況,教育發展諸因素的因果關系以及教育發展的規律的研究之上,這是教育理論言說什么是“有價值/好”的教育和如何達至“有價值/好”的教育的基礎和前提。教育理論的言說不能訴諸想象,而必須匍匐在現實的粗糙地面上。
(二)盡管教育理論的訴說包含著描述,但卻決不能停留于描述,更不能以描述為目的。教育理論的訴說是對有根據的教育理想的建構和訴說。沒有了這種對教育理想、對什么是“有價值/好”的教育的訴說,教育理論就失去了色彩與光芒。之所以在教育理論的言說中提出如上原則,是因為教育實踐是具體的、現實的,不管我們喜歡與否,都必須首先接受以往教育實踐給我們留下的財富與負擔,而把教育理論的陳述建立在實證科學對教育實踐的確切把握上,我們才能更好地改善教育實踐。同時還因為要想改善教育實踐,教育理論就不能缺失了對什么是“有價值/好”的教育和如何達至“有價值/好”教育的言說。
三教育理論恰當、貼切地表達實踐并不是教育理論的最終目的,其最終目的在于在多大程度、范圍上改善了教育實踐。可以說,貼切、恰當地表達教育實踐只是改善教育實踐的前提和手段,而衡量教育理論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最終標準是解決(不僅是解答)現實教育問題的能力。誠然,無論怎樣自詡要改善教育實踐,教育理論都不能直接改善教育實踐本身。這是教育理論的限度。教育理論只能通過改變實踐者的觀念而改變教育實踐,并通過教育行動而解決教育問題。至于教育理論如何實現改善教育實踐的最終目的,需要哪些中介,采取哪些措施,則遠不是本文所能包容的;但探討教育理論如何恰當、貼切地表達實踐,顯然有助于實現教育實踐的改善,這也是本文的用意所在。
[參考文獻][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2][3]王慶節.真理、道理與講理[A].趙汀陽主編.年度學術2005———第一哲學[C].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103.[4]周浩波.教育哲學[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104.[5]馮平.面向中國問題的哲學[J].中國社會科學,2006,(6).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