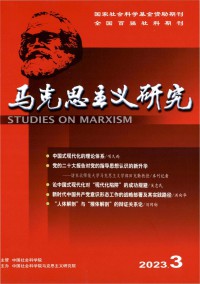馬克思主義化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馬克思主義化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一、馬克思主義民族化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問題馬克思主義創立時就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工人沒有祖國”,但是工人“本身還是民族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91頁)馬克思主義的這一觀點,揭示了工人階級即現代無產階級的一個基本特性——無產階級的世界性、國際性蘊含在民族性之中,其國際性和民族性是辯證統一的。現代無產階級的這一基本特性,在思想上引申出一個理論原則,共產黨人的理論原理“是現存的階級斗爭、我們眼前的歷史運動的真實關系的一般表述”;“這些原理的實際運用,正如《宣言》中所說的,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同上,第285、248頁)這就是說,馬克思主義一經落腳現實世界,成為一個民族的無產階級的理論思想和行動綱領,就必須回答和解決當時當地的社會問題;一個民族的無產階級成功地實踐著馬克思主義,一定會給馬克思主義增添新的語言、新的內容,為實踐著的馬克思主義帶來了民族風格。馬克思主義民族化的實質,就是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的基礎上,運用馬克思主義創造性地解決本國的實際問題,首先使本民族的無產階級事業取得勝利的發展。無疑,馬克思主義民族化是馬克思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則。十月革命是馬克思主義的偉大的勝利,是把馬克思主義成功地運用于俄國社會實踐而產生的列寧主義的偉大勝利。列寧主義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把馬克思主義俄國民族化的第一個成功的范例和第一次成功的回答。1920年,列寧闡明了俄國布爾什維克在理論與實踐之統一的馬克思主義民族化方面取得的一些基本認識和基本經驗:“每個國家的工人運動在取得對資產階級的勝利之前雖然都要預先經過本質上相同的鍛煉,但這一發展過程又是按各自的方式來完成的。”“只要各個民族之間、各個國家之間的民族差別和國家差別還存在(這些差別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在全世界范圍內實現以后,也還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國共產主義工人運動國際策略的統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樣性,消滅民族差別(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運用共產黨人的基本原則(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時,把這些原則在某些細節上正確地加以改變,使之正確地適應于民族的和民族國家的差別,針對這些差別正確地加以運用。在每個國家通過具體的途徑來完成統一的國際任務,戰勝工人運動內部的機會主義和左傾學理主義,推翻資產階級,建立蘇維埃共和國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都必須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點和特征,這就是一切先進國家(而且不僅是先進國家)在目前歷史時期的主要任務”(《列寧選集》第4卷,第199、200頁),等等。列寧在領導俄國布爾什維克成就十月革命的同時,敏銳地覺察到“極大的世界風暴的新的發源地已在亞洲出現”、“我們現在正處在這些風暴以及它們‘反過來影響’歐洲的時代”,提出了“亞洲的覺醒”、“落后的歐洲和先進的亞洲”的判斷。(《列寧選集》第2卷,第307、315、317頁)十月革命后,列寧更是把民族殖民地問題作為未來世界革命發展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大問題,當作新建立的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的一項重大任務。列寧認為,這是全世界共產主義者已經面臨和沒有解決的一個十分艱巨的任務,對亞洲民族完成這一偉大的歷史任務滿懷希望。列寧的遠見在中國得到實現。中國革命的勝利,不僅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勝利,也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成功地運用于中國社會實踐而產生的思想的偉大勝利。思想是繼十月革命和列寧主義之后,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民族化的又一個成功的范例和成功的回答。二、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列寧及其領導的俄國布爾什維克為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化開通了世界歷史前進的道路,但是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要中國化即民族化的口號的,是其后的中國共產黨和。那么,為什么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口號呢?又是怎樣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呢?“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選集》第4卷,第1471頁)中國先進分子學習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握了西歐第二國際破產的教訓,吸取了世界上最先進的革命理論和革命經驗。年輕的中國共產黨接受的是共產國際的指導。因此,實現從共產國際領導中國革命過渡到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中國革命,不僅是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相互關系的重大問題,更是中國共產黨自身建設和發展的重大問題。中國共產黨面臨的問題是:怎樣結合中國的國情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如何把十月革命和俄國布爾什維克的成功經驗轉變為中國共產黨獨立指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路線和政策。這些問題關系到中國革命的前途。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在怎樣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重大而基本的問題上,有著這樣兩種態度,一種是教條主義的態度,一種是實事求是的態度。教條主義的態度,在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時往往只注重結論,忽視了引出結論的具體事物的背景和過程。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明確指出,他們關于“未來非資本主義社會區別于現代社會的特征的看法,是從歷史事實和發展過程中得出的確切結論,不結合這些事實和過程去加以闡明,就沒有任何理論價值和實際價值”(《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676頁)。在教務主義式的思維和活動中,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那種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積極、主動、靈活的思想方法被忽略了,往往不能把讀到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上級的指示與當前的革命斗爭、社會生活很好地結合起來。對于中國共產黨幼年時期發生的這種理論與實踐脫離的現象,是認識最早最深刻的人。1930年,他在《調查工作》即《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形象而生動地分析了這種現象的心態和做法:“以為上了書的就是對的,文化落后的中國農民至今還存著這種心理。不謂共產黨內討論問題,也還有人開口閉口‘拿本本來’。我們說上級領導機關的指示是正確的,決不單是因為它出于‘上級領導機關’,而是因為它的內容是適合于斗爭中客觀和主觀情勢的,是斗爭所需要的。不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討論和審察,一味盲目執行,這種單純建立在‘上級’觀念上的形式主義的態度是很不對的。”“那些具有一成不變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樂觀的頭腦的同志們,以為現在的斗爭策略已經是再好沒有了,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勝利,只要遵守既定辦法就無往而不勝利。這些想法是完全錯誤的,完全不是共產黨人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完全是一種保守路線。這種保守路線如不根本丟掉,將會給革命造成很大損失,也會害了這些同志自己。”(《選集》第1卷,第111、116頁)那個時代,中國共產黨內的教條主義有兩個緊密結合的特點,一是思想上的懶漢,不勤于思索中國革命的各種問題;二是組織上的依賴性。這樣的問題,若發生在基層,一般來說影響或危害還不算太大;若發生在中央和決策機關,影響和危害就是全局性的。所揭示的“本本主義”的現象,不僅描述了那時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之間的相互關系,也揭示了那時革命發生挫折的基本原因。響亮地提出了“反對本本主義”和“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的口號(同上,第111、115頁),提醒和告誡創建革命根據地的同志們,要自己調查周邊的敵我雙方的情況,主動出擊,創造性地做好自己的各項工作,不要因為消極等待上級或遠方的指示,而喪失根據地發展的大好時機(當時國內正值軍閥混戰)。鮮明地提出“反對本本主義”和“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的口號,表明以為代表的一批中國共產黨人開始自覺地思考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體現著一種深邃的理論思維的覺醒,是馬克思主義走向中國化的重大突破。與教條主義的態度相反,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注重多思多問,提出了中國“革命的對象究竟是誰?這個革命的任務究竟是什么呢?這個革命的動力是什么?這個革命的性質是什么?這個革命的前途又是什么呢?”(《選集》第2卷,第632-633頁)等一系列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要解決的問題。在總結學習馬列主義的經驗時曾說:“馬列主義的方法有三條,一是理論同實際相聯系,二是反對自發論,三是批評與自我批評。”(《文集》第3卷,第75頁)是怎樣看待理論聯系實際的呢?調查研究、理論聯系實際往往是一個艱苦的、長期的過程。如果以為調查研究、理論聯系實際就是認真讀書,冥思苦想;或者下到基層,短則七八天,長則個把月,搞出個調研報告,就算是理論聯系實際了,這是遠遠不夠的,有的甚至是自欺欺人。批評了這兩種做法。對于前者,說:“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斗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里能夠產生的,它是要在群眾的斗爭過程中才能產生的,這就是說要在實際經驗中才能產生。”(《選集》第1卷,第115頁)對于后者,說:“有許多人,‘下車伊始’,就哇喇哇喇地發議論,提意見,這也批評,那也指責,其實這種人十個有十個要失敗。……我們黨吃所謂‘欽差大臣’的虧,是不可勝數的。(《選集》第3卷,第791頁)的理論聯系實際是從社會調查入手,但是他的做法與眾不同。首先是時間長。就拿調查農村問題來說吧,不是只調查一時一事,而是調查了一生。從1927年上井岡山到1945年去重慶談判,僅這段時間,靠兩條腿,從南走到北,在十幾個省的農村一住,工作加生活,就是整整18年啊!在看來,農民問題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關系重大,要真正徹底了解農民,了解農村,與農民打成一片,使農民相信和依靠中國共產黨,絕非一朝一夕、三年五載所能做到的。在中國共產黨里,首先認識到,“一般地說,中國幼稚的資產階級還沒有來得及也永遠不可能替我們預備關于社會情況的較完備的甚至起碼的材料,……所以我們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特殊地說,實際工作者須隨時去了解變化著的情況,這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也不能依靠別人預備的。所以,一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對于只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情況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和實際相聯系。”“我現在還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國事情和國際事情的必要,這是和我自己對于中國事情和國際事情依然還只是一知半解這種事實相關聯的,并非說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黨同志一起向群眾學習,繼續當一個小學生,這就是我的志愿。”(《選集》第3卷,第791-792頁)總結出一種富有成效的學習方法:“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從戰爭學習戰爭——這是我們的主要方法。沒有進學校機會的人,仍然可以學習戰爭,就是從戰爭中學習。革命戰爭是民眾的事,常常不是先學好了再干,而是干起來再學習,干就是學習。”(《選集》第1卷,第181頁)不是別的人而是提出了關于調查研究的一個原理: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參見《文集》第1卷,第267頁)同樣是做社會調查,與他批評的“欽差大臣”不同在哪里呢?——在鮮明的立場,在堅定而明確的出發點,即始終堅持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腳踏實地,走出了一條群眾路線。在中國共產黨內,是首先倡導并畢生實踐著這樣一種群眾觀點:“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須明白: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選集》第3卷,第790頁)以生動通俗的話語,點明了“群眾”的重要性,點明了“知識”的源泉這樣一些平凡而偉大的道理,這些話語閃耀著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光輝。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這樣勇于自我批評又誨人不倦的話,是毛澤工作、學習和生活的寫照。正是因為有這樣的態度、這樣的出發點,調查研究的結論才是準確的,解決問題的辦法才得到人民群眾的歡迎,因而在實踐中才是可行的、成功的。所以說,在中國共產黨內,是提出了解決農民問題的正確的政策和策略。刻苦學習馬列主義,為后來系統地解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基礎。由于在社會實踐和理論研究兩個方面有扎實而雄厚的功底,從而在運用十月革命的經驗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這個重大問題上,提出了新的系統的理論思想。認為,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是農民問題,革命的主力軍是農民,中國革命的道路就是在農村建立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奪取政權,進而一步一步解決整個中國的革命與建設的問題。可是在有教條主義思想的同志那里,對這樣一條中國革命的邏輯覺得不可思議,說什么“列寧沒有講過”(《文集》第3卷,第74頁)!在他們的思想里,“革命的力量是要純粹又純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筆直又筆直,圣經上載了的才是對的”(《選集》第1卷,第154頁)。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但是在同一個原則下,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基本地不是經過長期合法斗爭以進入起義和戰爭,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鄉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把馬克思主義關于暴力革命的原理和十月革命的經驗,經過加工提煉而中國化了。教條主義既可能以“左”的形式表現出來,又可能以右的形式表現出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和王明的先是“左”傾機會主義后來又是右傾機會主義,無不以刻板地套用馬克思主義或外國的歷史為思想的出發點。20世紀20、30年代,中國共產黨經歷了右傾機會主義給革命帶來的失敗,經歷了農村根據地和紅軍的蓬勃發展,經歷了“左”傾機會主義指導而遭受的巨大挫折,經歷了抗日戰爭初期右傾機會主義干擾的局部損失,積累了豐富的正反兩方面的實踐經驗,開始獨立領導中國革命。在中國共產黨六屆六中全會上,全黨團結在的周圍,從中國革命的戰爭戰略、統一戰線、黨的建設、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等若干方面,開始全面而深入地檢查教條主義的錯誤。在這樣的時候,明確提出了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思想:“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并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系的。對于中國共產黨說來,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的環境。成為偉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和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選集》第2卷,第534頁)在領導下,中國共產黨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