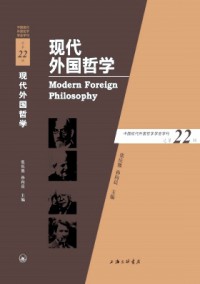哲學限界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哲學限界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后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這個詞本身暗示一種兩可的境遇。“后”(post)作為一時間指示詞既未表明反對也未說贊成。不過“后”代在變異上不大可能與上一代表現得如此偏離以致于轉換了種屬“非我族類”。后現代主義與分析的科學哲學觀點的相互牽涉就是一例。〔1〕但在真理問題上,后現代主義與分析哲學的關系,似不太為學界注意。本文試圖表明,后現代主義者羅蒂、費伊阿本德、麥金太爾等人對分析哲學這種“經驗主義”的現代形式的拒斥中掩蓋了這樣一個事實:他們“告別啟蒙”、“告別哲學”、“告別真理”、“告別理性”的運思恰恰來源于分析哲學考察真理問題某些最堅定的引導假定。
一、真理的神話是怎么破除的?
邏輯實證主義(更普遍的說法是“邏輯經驗主義”)最早破除了啟蒙以來真理概念本身代表某種神秘意義或合理性標準的根深締固的迷信。卡爾納普指出,令a為任何詞,S(a)為出現這個詞的基本句子,那么a有意義的充要條件就可以用下面每一個表述提出來;這些表述歸根結締說的是同一件事:(1)已知a的經驗標準;(2)已知規定了“S(a)”可以從一些記錄句子推出來;(3)S(a)的真值條件確定了;(4)已知S(a)的證實方法。〔2〕S(a)的真值條件比“S(a)是真的”這種斷言更重要。“P是真的”中“真”是多余的,P真僅是斷定命題P的一種方式。“P是真的”可以翻譯成一些等值的句子,這些等值句子并不包括“真”或它的任何同義語。問題在于這種翻譯的標準而不在于“真”本身代表一種真正的性質或關系。要求在對“什么是真理”問題的回答中有比分析“P是真的”更多或某種實在的性質是以往哲學家的誤區。真理論在澄清了“P是真的”這類句子的病癥后,可以附帶地討論命題的真值條件的確定或命題“證實方法和標準。”〔3〕字、詞、句及命題的“意義”的分析成為哲學的中心任務與“真理”這個詞的遭冷落無疑是同時的。分析哲學在對意義的可證實原則的深入探討進程中成為現代經驗科學的理性構架的“科學的”(scientific)哲學代言人,公然成為一種“科學主義”的意識形態。這個進程在科學哲學的歷史主義學派那里以“真理”概念的取消而告終。
人們發現,“如果證實的意思是決定性地、最后地確定為真,那么我們將會看到,從來沒有任何(綜合)語句是可證實的。我們只能越來越確實地驗證一個語句。”〔4〕這是由于,假定有一個語句S,對它已經做了一些檢驗性觀察,S在一定程度上被這些觀察所確證,但對其接受卻取決于進一步的證據以及滲透在觀察中的理論預設,并沒有一般的規則來限定我們的決斷。當然“紙是白的”這個陳述中決定我們的決斷的約定因素大大少于非約定的客觀成分,甚至在做了若干次觀察以后,確證程度將十分高,以至我們實際上不能不接受這個語句。但理論上仍舊有否認這個語句的可能,約定的問題仍然存在。證實或確證標準作為經驗科學的合理構想本身也難免成為“約定”和“建議”而無法證實或確證自身。總而言之,真理可以說就是按“我們”的標準可合理地接受的。
為了避免這種困境,波普借助塔斯基的真理論提出一種“逼真性”概念的理性構架。〔5〕在其中,可以把經驗證偽概念精致化,設想理論是較好中較差地接近真理。但這樣無非是一種巧妙的為真理概念辯護的企圖:缺乏真理標準不能用作反對真理概念的邏輯合法性的論據。塔斯基證明,給定了一個形式化語言(一個使用符號邏輯表達特定陳述的形式符號系統),人們如何能夠在更強的語言(所謂元語言)中為那個語言定義什么是真的:
(T)“雪是白的”是真的,當且僅當雪是白的。
按任何一種真理理論,“雪是白的”都等價于“‘雪是白的’是真的。”如果實證主義以“雪”和“白”對于某人是不可證實的而聲稱“雪是白的”是無意義的,他們仍然可以說如果某人了解上面的(T)等式,他就知道“‘雪是白的’是真的”是什么意思,它意味著雪是白的。這與晚期卡爾納普以來經過波普和拉卡托斯發展的按照“科學共同體”(“我們”)的觀點判定一個具體的理論是否是“理由充足的”歷史主義科學哲學設想并不沖突。
歷史主義發展到勞丹和費伊阿本德,邏輯經驗主義以來的科學知識增長模式徹底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不可通約”(incommensurability)的后現代主義文化相對主義策略。正是對不可通約性這一后來成為后現代主義“核心詞”的闡發,〔6〕費伊阿本德等人摧毀了分析科學哲學關于“理性”“科學”“客觀性”的神話。不可通約性表明,相互異質的研究傳統使得人們之間的爭執和討論達到理性的一致是不可能的,人們說著不同的事情,即使使用相同的語詞也實際說得是不同的意思。就象兩可圖形,你可以要么看到A要么看到B,但你絕不可能同時看到A和B。勞丹也不贊同以往的經驗主義科學圖式和理性構架,更強調按照豐富多彩的科學史的本來面目去認識科學理性,從而在更廣泛的文化過程背景下思考科學理性。但他還是始終強調最低限度的理性可接受標準的存在,并在理性構想中力圖維護客觀性的地位。正因為如此,他對“真理”概念的否棄就更令人震動。他是以反對波普的逼真性理性構架入手的。他認為,如果科學進步在于得到一系列聲稱越來越接近真理的理論,那么科學就不可能被證明是進步的。之所以有這種與“真理”相聯的科學進步觀,是源于我們有這樣一種真理論假定:(1)一種理性可接受標準可滿足真理論關于命題如何有效或至少是擁有“真內容”的實質性標準(說到底這還是因襲了陳述與事實相符合的經典的真理符合論);(2)根據理性可接受標準我們可以進一步解決知識的合理增長問題并把知識的進步、科學與非科學的劃界合理地描述為:科學擁有較多的真命題。但這不符合科學活動的實際。科學是一個尋求解決問題的體系,解決問題的能力與“真實性”沒有任何直接的聯系。如果反過來不以含糊的逼真性標準界定科學進步,而以“進步”(注意:這在勞丹中是自然主義式的對“進步”價值的預設。容下文分析)來構設合理性模式,情況就成為:合理性在于選擇能最大限度的增進知識進步的研究傳統。而知識的進步在于解決越來越多的重要問題。“重要問題”是個相對概念,它意指一個研究傳統解決的一個問題不僅其它與之競爭的研究傳統沒法解決而且解決起來勢必與其基本預設相沖突,〔7〕或者,其它研究傳統根本看不到這個問題,以至于由此牽涉的更多的從屬問題它們更是談不上解決。通過對知識體系或理論解決問題能力在特定時期解決問題的數量、質量、速度等的動力學分析,我們可以擬訂科學與非科學的劃界、可接受的理論與可參考的理論(乃至不可接受的理論)等的劃分。沒有必要認為合理的理論評價模式必定導致對理論的真實性、虛假性、證實或確證的判定。合理性在于接受最有效的研究傳統,也就是說對一個理論和研究傳統的合理評價必須涉及到對該理論或研究傳統所解決的經驗問題的分析和對它產生的概念問題和反常問題的分析。任何對接受一定的理論或研究傳統的合理性評價都有三重相關性:其一,與它同時代的競爭對手相關;其二,與流行的理論評價學說相關;其三,與該研究傳統內先前的理論相關。我們的目的是解釋理論(尤其是科學)是怎樣被評價的,“真理”作為(科學)理性的目的在這方面毫無用處。〔8〕
二、真理是一種癥候?
哲學的最終目的就在于把握真理,人類的最高理想莫過于真善美的統一,這差不多成了不言自明的常識。但在當代一些西方哲學家看來,這種情況令人驚恐:因為它消除還有新事物、反常話語的可能性,消除了詩意的而非僅只是思考的人類生活的可能。〔9〕打著真理的招牌人類犯下的獨斷、封閉、不寬容的錯誤是如此巨大而以至于經常讓人懷疑“真理”本身能否逃避責難?也許,沒有真理概念我們照樣過得很好。費伊阿本德等人對科學沙文主義的批判使得后現代主義分析哲學可以繞過語義學上真理概念的保守性而直面普遍的文化領域和日常經驗的真理癥候。我們可以從日常詮釋學經驗出發,考慮用一個例子說明這種觀點。
一篇文章寫得更實在更可讀的標準是什么?如果說(1)條理性,(2)明確的主張,(3)可供討論的證據,(4)通俗性、更多使用日常語言這四個(也許還有更多)標準是普遍不難接受的,那么,文章里“有東西”并且可讀應該說是有某種“合理性”依據的“解釋技巧”的。
我們從各種可供選擇的合理性構架出發,不偏好任何一種源于意義的證實原則的經驗主義理性解釋模式,有如下幾種釋讀技術規定的“可讀”情況:
(a)為其它閱讀者(或理論和批評)提供了表明自己贊同或反對(尤其是反對)某種觀點的楔入點。(可讀性在于反駁與證偽的理性評價模式)
(b)不易于提出多種解釋,任一解釋、讀法擁有較少的反常讀法和解釋(可讀性和可讀方案在于能提供并解決較多經驗和概念問題而面臨較少的理論反常問題,即文章留給人很少的“根本”無法解決的閱讀疑難:勞丹式的“進步”研究傳統的可接受模式)。
(c)可證實的、與某種直接被給予的感覺契合。直覺式寫作、跳躍,有更多的共同觀察語句。(經驗證實模式)
(a)既未表明文章是更可讀還是不可讀,這并非一種理想的解讀(釋)模式。(b)(c)恰好構成對立。為什么?(c)雖是憑直覺方式給出的,可對于讀者來講,由于期待視野、閱讀(解釋)成見的存在,盡管人們都認為自己理解了文章的內容,卻出現這種情況,每個人都承認文章可以有一種唯一成立的解釋,但每一種解釋都是不可比較的。(c)類文章被視為既可讀又不可讀、一方面它也許以精巧的方式表達了我們生活方式的基本信條、我們生活與人性的敏感性、生命的精神世界的多重價值傾向,但究竟應該把(c)確定為何種絕對解釋之下,人們不抱希望。(c)表達了我們生存形態的客觀成分,甚至(c)的解讀(c)'可以是無窮多的并且每個(c)'都力求作到(b)類模式要求,即對(b)的解釋不存在各種相互矛盾的觀點,這不排除各種從(b)模式來看觀點明確的文本各自含有觀點的很大分歧。
在后現代主義者庫恩、費依阿本德這樣一些人看來,(b)(c)文本的并存造成了文化、生活方式、傳統之間的不可通約性。在這種情況下,客觀、中立的“理性”評價模式不過是占統治地位的西方文明科學沙文主義的幻像和真理病的體現,即使有一人試圖放棄“真理”與理性目的的那種宿命式的神秘關系也抹煞不了其根深締固的效應。當我們為一些富有超凡特質的“經典文本”、“經典研究”的某些精悍異常的論述與分析心有靈犀時,“真理病”就捕獲了我們。它促使我們進一步相信,所謂“理想地”一般可接受的風格或論證方式是普遍可接受的從而是可行的。但任何一種“理性”“直覺”確證的所謂“標準的生活方式的游戲規則”(維特根斯坦意義上的)在加以應用時,就成了地地道道的沙文主義。而且考慮到我們的閱讀偏好受到時尚的影響,然而時尚卻搖晃不定總是比我們的個人偏好顯得有理。我們的閱讀活動經驗中的“真的東西”為“有理”的東西滲透后,我們說自己“真的讀”什么就好象:一個人用閃爍的眼睛看著你從你身邊走過,說“你難道能否認×××是真理?”你好象就能相信他!不要用“真”“悟性”這些東西阻礙我們對新的經驗的理解、對反常話語的寬容。文本(text,就其最廣泛的意義而言)召喚著一切可能的讀者,必須容忍作品的湮滅和意想不到的復興。甚至偉大作品或我們所處的經典傳統不以“單純”或“清晰”偉大——如果就“純形式”來考察則言——勿寧是以含混、歧義、較大的異議激發力為背景的。
分析哲學的非理性主義的反叛者對最低限度的理性概念的反駁側重點在于對客觀中立理性框架神話的破除,而理性可接受標準的研究行將放棄的真理概念卻在后現代分析哲學中找到了新的用武之地。正是在對客觀中立理性主義神話摧構同時,后現代主義哲學復興了作為主觀性宏揚機制的“真理政治學”,而這種策略與分析哲學傳統發生了微妙的關系。分析哲學的傳統立場不僅體現在將真理論與意義理論對“證實”“證偽”等理性原則的探討聯系起來,而且還有我們在前面提及波普證偽主義逼真性認識論時看到的另一種趨勢,即將真理論發展為與經驗主義教條無關的中立的、形式的真理論。后現代主義分析哲學代表人物羅蒂60年代曾以主編《語言學轉向》蜚聲分析哲學界。他對分析哲學的薄弱環節可謂心中有底,因而他對分析哲學的進攻的重點放在認識論(也稱分析的科學哲學)是。實際上,他批判的西方理性主義傳統對“真理”的偏好主要是以波普學派逼真性“科學邏輯”為背景的。認識論在標準的“科學發現的邏輯”或“科學證明的邏輯”〔10〕中預設一種科學與理性全知全能的“上帝之眼”式的獨斷論:“(認識論)導向一種標準符號系統的建立,后者描摹前實在的真實的和最終的結構。”〔11〕在羅蒂看來,任何諸如此類的論證,都難以最終驅散對科學、“唯科學論”以及被太多的知識變為物而不再成為人的恐懼,對一切話語將成為正常話語的恐懼。〔12〕
與此相對照的,羅蒂對塔斯基以來直到戴維森的分析哲學的形式真理論則大加贊辭。分析的語言哲學的最新趨勢表明,真理論不過是一展示英語語句間關系的純語言轉譯構想。甚至艾耶爾在把“真”作為附加語從“命題P為真”中刪去時就已經考慮到含有“真”概念的句子轉釋成不含有“真”的句子對于真理論的意義。但形式真理論的重點不是“真”本身是否有意義,而是闡明何以人們通過把較長語句的真看作人們稱較短語句為真的函數的方式去稱某些較長的語句為“真”。真理論除了在語法學家的系統領域(即企圖找到描述語句的方式,以有助于說明這些語句是怎樣使用的)之外,不可能有任何特珠的領域。建立一種英語真值理論的意義,不在于使哲學問題能表述于一種形式的言語方式中,也不在說明字詞與世界的關系,而只在于清楚地展示一種社會實踐的某些部分(使用某些語句)和其它部分(使用其它一些語句)之間的關系。這樣,“真理”概念就與鼓勵不同實踐領域的廣泛交流的文化體制、政治制度聯系起來,與實踐理性聯系起來。真理概念描述了:我們作為參加對話的一方雖不是最終認可的某種確定的可接受的命題、事實、理論乃至某種傳統,由于與我們已有知識相互融通因而是有我們的(種族中心的)〔13〕“真值”指派的。真理的取得既如此,就不奇怪哲學真理論一方面取消了與認識論邏輯關系,也把哲學從對鏡式本質的追求中解放出來。鏡式本質預設了相互異質的傳統可以找到這種客觀中立的達成一致的條件:當且僅當我們找到一面對某個不可獲致的世界加以精確表象的“自然之鏡”。而在人類不同傳統中不同生活領域之間促進持久對話的無鏡的哲學成為一種“真理的政治學”。這種真理政治學表明為保持持久、開放、平等、自由的對話所需的政治制度(如羅蒂所稱的自由主義民主)甚至優先于哲學,悍衛這種制度并以這種制度為前提的鼓勵開放式討論、差異和對話的哲學成為政治的一部分。正因為此,這種哲學或任何類似的哲學就不能成為代表全人類的普遍的大寫的Philosophy,而只能成為存在于特定傳統為特定傳統的合理性習俗辯護的小寫的philosophy。后哲學文化:實用主義傳統的復興、解構主義和形形色色的后現代主義文化思潮、唯科學主義文化的敗落、純語言論的非認識的真理論、多元主義的自由主義民主體制的持續存在等等匯合在一起為解釋學的、小寫的哲學提供了文化的可能性。
三、真理的政治學還是分析性?
羅蒂其實是這樣考慮西方傳統中的合理性標準與真理的關系的:假設他所處的傳統(如英語共同體)判定某些理論是“有意義的”,那么意味著這里發生了一種成功的轉譯,即這些理論依據傳統的引導假定而被指派了“真值”,轉譯標準也就是他所說的合理化習俗〔14〕,包含諸如“經驗證實”“符合觀察語句的”等從屬的以及更具體的從屬標準。他承認真理論從而為更好地理解認同自己所處的啟蒙傳統提供了一種“合法性”的辯護。但他沒有考慮這種可能性,如果轉譯意味著融通已有的東西與新的東西的關系,那首先意味著比較。比較牽扯到選擇機制,而選擇機制即使在同一文化的生活領域各部分之間也是可變的。邏輯經驗主義及其形形色色的修正者對理性評價機制提出了各種方案,包括勞丹的研究傳統選擇理論。羅蒂的“融通”觀念最后竟使他最終認同于保守的邏輯經驗主義方案。另外,前面提到他的哲學觀的前提是從真理融貫論出發的“鼓勵差異和對話的”無鏡的反體系的所謂“元哲學”,那么,“元哲學”如何能避免對一切元敘述的懷疑主義指責?如果一種“元哲學觀”試圖成為有吸引力的并讓人接受它的真理論它難道不要進行一些對其它理論的比較分析嗎?如果說羅蒂的真理觀最終提供了對西方自身傳統的合理化習俗的一種辯護,他在對話、討論、比較中暗含地使用了這些合理化習俗是合法的嗎?這難道不是表明真理概念仍然無法擺脫理性的構架的影響?更為重要的是,后現代分析哲學產生的效應是把真理性及其相關的“癥狀”(如“自明性”“本真的與非本真的生存”“現象與物自身”等等),理解為特定生活方式和傳統對引導假定和支持系統(“保護帶”)的一種內部的“真”指派。可是它所支持的特定生活傳統內部的轉譯所達到的那種內部真理難產不表明存在一種超越于特定轉譯的理想的一元的真理概念?
分析哲學家普特南復興了一種既與理性構架相聯系又保持真理概念相對于特定理性構架(或稱合理性標準)的超越性的傳統的真理觀和分析哲學元敘述悖繆的解決方案。〔15〕
人們發現,比如說在特定時刻、特定的進行交流的個體,他持特定的轉譯標準或理性標準對“真”事物或真現象乃至真理論的判定可以是一定的。但這一切又是會發生意想不到的變化的。給出真理概念的特定理論作為轉譯機制的元陳述(這無法避免)恰好也必須依賴于它在進行元陳述時對其它看待真理的方式以某種判定。主觀性在理性選擇中的滲透或不可通約性、意想不到的改變,這種見解也可以說是我們經過選擇得出的一種“承諾”對話、問題的探討不被獨斷的中止的策略。
基于此,普特南認為,(1)我們關于“好”的理想論決定或優先于我們關于理性上可接受標準;(2)理性可接受的切合性標準并不能取消真理作為最理想的適切性的極限概念的地位。(3)而真理理論卻須以合理性理論為先決條件。“真理概念本身,就其內容而言,依賴于我們的理性可接受標準,而這些標準又依賴于我們的價值,并以我們的價值為先決條件”。〔16〕在普特南的真理論中合理性概念起著中樞作用。他承認判定是不是事實的唯一標準就是看接受它是否合理,而這種構想允許價值事實存在。但我們為什么不可以依據合理性決定事實進而價值事實得出決定合理性構想的“我們關于好的理論”作為價值事實也是受合理性標準支配的一種選擇?前面羅蒂使用合理化習俗去表達“元哲學”的循環論的合法性問題在這里同樣出現了。
普特南提出“先天推理”概念為分析哲學展開的“真理論”等元陳述討論的合法性辯護。他認為,我們討論涉及“指稱問題”“真理符合論”“形而上學實在論”等始終是:在探究什么是理性的可能的意義上假定某些一般前提、或做出某些極為寬泛的理論假定。這樣一個步驟既非“經驗的”也非完全“先天的”而是同時具有這兩種研究方式的因素。這個方法同康德所謂“先驗”的研究有十分密切的關系。我們“關于好的理論”承諾的“連貫性”“進步性”(如勞丹所強調)等價值與合理性構想處于不斷的相互作用。先天推理可以提出人類理性的可能設想,但不能視為一勞永逸地解決了理性構架問題。新問題、新設想還會意想不到地出現:我們必須承諾,總有一天人們也許會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依據他們的知識狀況提供的條件考慮完全不同的問題,至于他們稱之為“哲學”還是“菜根”我們沒法知道,我們為什么要知道呢?但目前,哲學還是可以為真理、理性甚至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提供一種確定的辯護的。
后現代分析哲學強調理性標準的可變性,為了防止滑向相對主義深淵,又不得不在“先天推理”的哲學“分析性”框架下保留普遍而中立的“真理”概念,并指出分析性框架本身與合理性標準相互作用,積極推動哲學與具體科學、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的對話,及同文化傳統的對話,不失為一種面對日益嚴重的西方哲學危機的解決方案。對于我國理論界深化對哲學的課題、發展方向,哲學在當前文化和社會變革中的作用等的認識有一定的借鑒作用。不過實際上,正如傳統分析哲學在客觀中立的價值無涉的瑣碎的經院式論證外觀下變相地確認現存制度的合法性一樣,當代的所謂“合理化習俗”論證仍然偏好所謂“自由社會”,強調“民主先于哲學”,為自由主義社會現實辯護。對此,我們應該警惕。
注釋:
〔1〕參見R·薩索爾《后現代主義與科學哲學》《國外社會科學》1995.4。
〔2〕〔4〕洪謙主編《邏輯經驗主義》商務版1989,第18、69頁。
〔3〕艾耶爾:《語言、真理、邏輯》上海譯文1982,第99頁。
〔5〕波普:《客觀知識》上海譯文,1986,第46—64頁。
〔6〕P·費伊阿本德:《反對方法》上海譯文1992,第191—252頁。
〔7〕這就聲名狼籍地求助于特設假說違背基本信條去解決一個具體問題。
〔8〕L·勞丹:《進步及其問題》上海譯文1991,第131頁。
〔9〕〔11〕〔12〕〔14〕羅蒂:《哲學與自然之鏡》三聯1988,邊碼第388—389、300、388頁,附錄《協同性還是客觀性》。
〔10〕參見K·享普爾《自然科學哲學》,魯德納《社會科學哲學》。
〔13〕羅蒂:《后哲學文化》上海譯文1992,第17頁,又見譯序轉引文第51頁。
〔15〕〔16〕H·普特南:《理性、真理、歷史》遼寧教育1988,第226、2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