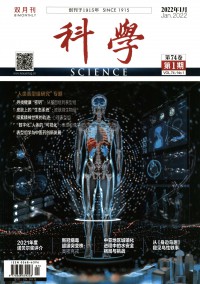科學哲學思想管理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科學哲學思想管理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當代西方哲學存在著兩大思潮:以英美為主體的分析哲學和以歐洲大陸為主體的人文哲學。兩大思潮的哲學家之間缺乏溝通的接觸。但是最近幾十年,哲學家們開始進行“綜合”和“貫通”的努力。其中較為出色的當推美國哲學家庫恩與羅斯。作為歷史主義學派的創始人庫恩,通過提出范式和科學發展動態模式,把科學社會學和科學心理學引入了科學哲學。羅斯是當代美國新一代的科學哲學家。他通過考察自然科學的社會和政治重要性,提出了對作為多方面的、復雜的社會實踐的科學知識的一種分析,從根本上改變了經驗主義科學認識論的混亂局面。但是庫恩和羅斯并不是“簡單地把英美和大陸研究結合”〔1〕而是在不削弱科學知識力量的基礎上,提供一個對科學進步及其合理性的更好理解。但是在一系列相關問題上,兩人還是存在著很大的分歧。
庫恩:科學革命的闡釋
在人類認識史上,有一個難題一直困擾著哲學家,那就是:自然科學是否存在有方法論的理想模式?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關系是怎樣的?傳統的看法認為:自然科學家說明自然現象;而社會學家則是理解社會現象,一個是關于事實的判斷,一個是關于價值的判斷,兩者之間存著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從19世紀開始逐漸形成兩大對立的派別:一是以實證主義和邏輯經驗主義哲學家為代表,認為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在認識論或方法論上沒有原則上的區分,自然科學在進步和發展中建立的認識論或方法論的理想模式完全適用于人文科學,另一派與此相反,狄爾泰、泰勒等人認為,在闡科學意義上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完全不同:“自然需要說明(explaination),人則必須理解(unelerstanding)”〔2〕庫恩從科學史角度反對實證主義的教條,同時又對泰勒等人的闡釋學區分不以為然。在庫恩看來,自然科學同樣需要闡釋,也與文化相關。1988年庫恩與泰勒為此展開一場大辯論。泰勒認為,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區別:人文科學的對象本質上是自我解釋的;而自然科學的對象則不必,也不應該被理解為自我解釋。如果說自然科學在某種意義上是解釋的,那么人文科學則是雙重的解釋:不僅提供解釋,而且是解釋的解釋。庫恩基于對自然科學的歷史發展或進步的動態模式,對庫恩的區分方式表示置疑。他認為,“自然科學在任何時候都是建立在現代實踐者從他們的前人那里繼承來的概念基礎上的。這個概念是歷史的產物,它包括在文化中,是現代實踐者通過訓練模仿得來的,而這只有通過闡釋學的技巧,由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去理解其思想模式后,才能影響社會的其它成員。”〔3〕在此,庫恩已意識到我們所接觸的世界被前理解所表述過的世界;我們關于自然知識,是對先天知識以及它所倒置的成功或失敗的一種反應。如電池、共鳴器或電子振蕩器以及化學反應等,都屬于人類活動的一個有意義的范圍,處于歷史中并具有與歷史不能分割的意義。在他的《從必要的張力》一書序言中,庫恩使用了“釋義學”這個詞,是為了對亞里士多德《物理學》一書作釋義學的理解。庫恩實際上已經揭示了自然科學的釋義學特征。
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是實在論問題。實在論是這樣一種觀點,即認為在某些領域里信念的真假,依賴于對象在該領域里的真實特性即它們所擁有的特性,而不管人們的信念、實踐或標準是什么。泰勒就自然科學對象這一意義來說是實在論者,庫恩則在自然科學方面對實在論發起猛攻。在庫恩看來,在不同的時間、地點和環境中,人們對自然會作出不同的科學說明。他引用泰勒《闡釋與人的科學》一文中同樣的“天空”例子說:“雖然我們不能把我們的天空與日本的天空相比較”,但是可以肯定,“我們的天空與古臘的天空是不同的。”〔4〕而且,我們和希臘人對天空的分類也不同,因為我們的天體分類學與希臘人的天體分類學截然不同。庫恩立論的科學革命,他堅持相互競爭的科學的實踐和標準的不可通的約性,并且否認我們能夠立于科學歷史而達到對世界真正認識。這在人文科學領域如此,在自然界也同樣如此。
如果說在上述兩個問題中,“庫恩和我(指羅斯)站在一邊”〔5〕始終保持一致的話,那么在最后一個問題上兩人則出現了分歧。這個問題即:對于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來說,是否在認識論上存在有區別的解釋活動?泰勒堅持一種強的觀念,在那里,詮釋是人文科學獨有的;自然科學獨立于文化,因而是非詮釋的。庫恩反對泰勒的區分方式,但仍然承認兩者存在有不同的解釋活動,特別是在實踐中,當我們面對不熟悉的或使人迷惑的本文(text)時,歷史學家和人種學家必須經常進行詮釋,而物理學家或經濟學家則根本不必這樣做。羅斯反對庫恩的這一區分,把科學的解釋范圍界定為實踐的解釋,在這一背景下,任何把科學同其他文化領域區別開來的普通的方法論或合理性的標準,都是不存在的。羅斯認為在某種程度上,庫恩的這種區分同羅蒂曾經在闡釋學與通常的演說之間所作的區分是相似的〔6〕。
羅斯與庫恩的分歧是從他閱讀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開始的。首先在他對庫恩的“兩種理解”中,羅斯比庫恩本人“更樂于把他的科學陳述觀點遠遠地作為一種實踐,”并聲稱這樣做是“為了加劇兩個庫恩的明顯區分。”他說“我的目的不是詮釋,而為了發展科學的解釋,而這在庫恩那是經常不被注意的”。〔8〕因此與庫恩不同,羅斯把范式看作實踐活動的共同領域而不是信仰的共同領域。其次,語言與世界實在的關系,在庫恩那里沒有得到有意義的說明。羅斯強調語言和社會實在的不可分離性,認為語言的區分及其使用方式,深深地同我們社會實踐情境聯系在一起。同時這種實踐情境,離開了合適的語言來源就不可能存在。在此基礎上,羅斯提出了他對科學知識的批判分析。
羅斯:科學批判理論
如果說現代闡釋學最初是人文科學陣營內部,以理解作為人文科學獨特方法開始去反對實證主義科學認識論的“稱王稱霸”,那么羅斯與庫恩出發點相同,都是從自然科學出發對泰勒等人的闡釋學進行分析的。一方面與庫恩一致,羅斯看到泰勒為建立人類科學唯一性所作的論證恰恰也適用于自然科學的陳述,從而證明了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之間并沒有闡釋學方法論的區分。另一方面不同于庫恩,羅斯否認闡釋學或闡釋學的解釋區別于其它質疑形成。他認為庫恩對此所作的區分“是不成立的”。〔9〕
羅斯的主要哲學思想包括兩個方面:第一是對作為實踐活動領域的科學的關注。第二,我們不能把科學的認識論范圍和科學的政治范圍截然區分開來。正是說明科學知識增長的實踐,在政治范圍內,也必須理解為貫穿科學本身和對我們其它的實踐和團體產生重大影響的,進而最終影響我們自身理解的種種權力關系。
在羅斯看來,“在人文科學中存在有一種與其自身的實踐背景的合法關系,但是這種關系在物理學或生物學中具有同樣的重要性〔10〕。在他的《知識與權力》一書中羅斯談到,科學家經常聯系實踐的敏感性、精確性、有效性以及技術技能從事科學研究。他聲明,重要的不在于我們是否完善地描述自然特征或者自然是否由我們“創造”,而在于我們通過實踐在一定的場境中與自然交往是恰當的。從某種意義上說,羅斯在實踐方面比庫恩走得更遠。羅斯把庫恩科學革命的思想發展為激進的庫恩—庫恩。不同于庫恩:把科學團體當作信仰者的共同體,“對于庫恩來說他們是實踐伙伴的共同體”。(11)前者認為共同體不能容忍基本的異議,后者認為科學共同體充滿了不一致。科學共同體的特征,是由共同的問題和技巧以及由對相同成果的說明規定的,而不是獨立地由共同輿論決定的。異例不是理論之間的沖突,而是實踐的困難。而危機的到來,則標明科學家們不再有共同的活動領域。區別于庫恩,庫恩并不是強加給科學歷史一個固定的發展模式,常規科學和危機并不是歷史的過程,而是實踐科學的方式。那種通常認為在某一范圍內科學革命核心概念和理論變化是同一的觀點,對于庫恩未必是事實。新的設備、技術或現象,能夠在某一確定的研究中發生同樣的基礎性變化。
羅斯用“實踐理性”代替了長期以來統治科學的“理論理性”,進一步闡明了科學知識與政治和權力的相互關系。在他看來,科學實踐以及自然世界通過實踐呈現的方式,是語言與實踐構形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科學實踐屬于副科學稱為“統治”的領域:“統治并不是僅僅指政治結構或國家的管理……統治就是去構造其他人行為的可能范圍”。(12)一個行為領域,是由材料背景,技術能力和在該背景中的共同理解這兩者組成的。羅斯認為,科學實踐在它有助于以兩種方式構造我們的行為領域這一意義上是政治的。它改變了我們的材料背景和技術能力;也有助于規定(及被規定)表明行為的概念和實踐。他說:“我們同自然世界的聯系……在廣泛的意義上必須被看作是一個政治觀點”。(13)羅斯是從兩個方面闡明科學解釋的政治特征的。一方面科學革命改變了舊的自然秩序的理想,揭示了一個無限的宇宙,同時也是改變了人類面臨的種種問題。對于我們現代人來說,自然世界已不再是中立的,而是不斷變化的。另一方面,我們與自然世界的關系也包含了政治觀點。因為我們對自然的理解及其評估包含了客觀的理性,這種理想反過來又與我們作為行為者的自我觀念有著密切的關系。正如海德格爾所說:“客觀性是揭示對象的一個主觀的特性”。羅斯強調,無論如何,客觀地理解自然的恰當觀點是什么,并不能從我們是誰以及我們能夠和應該怎樣彼此聯系這些政治問題中分離出來。
對于怎樣理解權力和知識,最近大多數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的解釋是:權力和知識是人類關注的不同領域;但兩者仍以某種重要的方式相互作用。羅斯對此有不同的看法。在他那里,權力關系,知識的產生和評估“不代表不同的領域”,而是以某種相互關聯的方式“關注同一領域”。(14)在《知識與權力》中,羅斯對權力和知識作了重新的考察,他把權力從狹窄的社會相互運行,展為包括實踐及事物過程變化的更豐富的內涵。同樣地,科學知識也是能動的,知識不是一種擁有或可交換的東西,而是由不同的相互競爭的共同體思考獲得的一個過程。因此,“一個陳述,技能或模式并不孤立地被看作是知識,在對它的認識過程中依賴于其它許多的實踐和能力關系,特別地依賴于再生產的改變的和擴展的關系”。(15)對于這樣一個復雜的實踐領域,羅斯稱之為“場境”(fielel)。它包括了一個比信念網絡更多的內容:技能和技術,可供操作和使用的儀器及物質系統,可用的資源(包括資金、設備、信息及職員等)、團體結構及相關的其它社會實踐或政治關注,等等。
對于權力與知識、科學的關系,羅斯察覺到至少有兩個重要的觀點是傳統哲學未提及的。第一,正是要求對象領域精確或更易于了解后努力,使權力與知識趨于一致。第二,社會運動或變革可能同時在認識論和政治上產生影響。羅斯總結說:“權力和知識既不是兩個不同的東西,又不是同一個東西”。(16)兩者代表我們認識世界和彼此交往的不同方式。沒有對權力與知識的相互關注,就不可能達到對科學知識正確的批判性的認識。
幾點結論
從上述分析我們不難看出庫恩與羅斯對科學的闡釋,科學的合理性及其發展,科學與實踐的關系等問題存在著很多共同一致的看法,同時也有分歧。
(1)庫恩與羅斯批判地分析了實證主義和邏輯經驗主義,從方法論與本體論方面打破了科學理性的一統天下。不同在于,庫恩是從科學革命的角度展開這種批判的。庫恩不滿意于當時邏輯實證主義撇開科學史孤立研究科學著作時,能夠讓歷史發揮更大的作用”。羅斯也反對實證主義科學知識和科學研究,“超越根限的地位”。(17)但他是從科學知識與權力的關系,從科學實踐(包括技術設備,物質條件等)的角度進行批判的分析。
(2)羅斯與庫恩都關注于自然科學領域,關注自然科學的闡釋特征,責怪泰勒等人對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闡釋學區分,認為自然科學也同樣需要闡釋。盡管如此,庫恩還是承認在認識論上存在有不同的解釋活動。他說:“雖然自然科學可能要求一個稱作闡釋學基礎的東西,但它們本身并不是闡釋學的事業。另一方面人文科學則經常沒有任何選擇的余地”。(18)它徹底需要闡釋學的闡釋。這是因為人文科學缺乏范式,沒有自然科學式的常規解疑研究。羅斯反對庫恩上述區分,認為它“預設了科學理論的一種構想(19)”
(3)羅斯與庫恩都反對自然科學的實在論,強調科學本質上不是一項一成不變的事業,反對科學行為定下不變的,不可違反的規則和規范方法論。但是對于范式及科學革命等,兩人仍存在著分歧。作為科學哲學中社會歷史學派的代表人物,庫恩創造性地在科學哲學中引進了心理學與社會學,為突破實證主義的科學主義作出了重大貢獻。
注:
〔1〕〔7〕〔8〕〔10〕Rouse,Joseph.KnowledgeandPower:Towardapoliticalphilosophyofscience,filstpublished1987bylornelluniversityPxi,chap2,P27,P177,P32,P187,P40,P181.
〔1〕狄爾泰《狄爾泰全集》第5卷P144
〔3〕〔4〕kahn,Tomass,TheNaturalandthehumanseience,intheInterpvetiveTurn.ed.byDavidR.Hileyandothers,cornell1991,P22,p19,P23
〔5〕〔6〕〔9〕Rouse,Joseph.InterpretationinHumanandNotualScience;intheInterpretiveturn,ed,byDavidR.Hileyandothers,cornell1991,P44,P45注〔3〕P43
Foucault.Michel.ThesubjectandPower;InDreyfusandRabinow1983,P221.
Rouse,Joseph.ThePyhamicsofpowerandknowledgiinscience,ed,byTheJourhalofphilosophy;inc,P658.P661.P665
庫恩:《必要的張力》1981年福建人民出版社P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