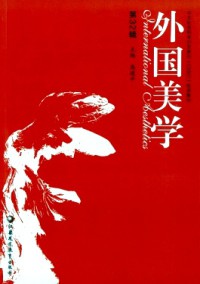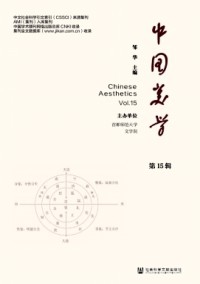元美學研究的思考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元美學研究的思考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善與正當的關系不僅存在于道德(狹義之“善”)領域,而且也存在于實利(“利”)、信仰(“信”)、認知(西方哲學強調的“真”)、炫美(“美”)等領域。這些領域雖然彼此有別,但又有一個共通點:都涉及各種事物對人具有的意義效應———也就是所謂的“價值”,因而可以稱之為生活世界的五大基本價值領域[2]5-6。善與正當關系在這五大領域的普泛性存在的一個直接體現就是:在所有這些領域中,人們都要運用“好”和“對”這兩個再普通不過的語詞,都要處理它們之間的復雜互動,都要憑借它們作為價值基準對各種東西的意義效應展開評判。所謂元價值學的使命,就是從這種最廣義、最有一般性的角度考察善與正當的關系。所以,只有在元價值學關于好對關系的研究基礎上,元倫理學的研究才能取得有說服力的成果,并且真正有助于規范倫理學方面的研究。
與元倫理學相似,元美學也構成了元價值學的一個理論分支,旨在從“元”視角出發,專門研究人們在炫美領域中的價值評判及其蘊含的好對關系。它與各種規范性美學(如儒家、道家、禪宗、浪漫主義、唯意志論、精神分析美學等)的區別在于:元美學主要從描述性和分析性視角出發,解釋現實生活中人們是在什么樣的語義內涵上理解和運用美、丑、崇高、悲劇、反諷、荒誕這些價值術語的;規范性美學主要從各種特定的規范性視角出發,解釋現實生活中人們是怎樣憑借這些語義內涵,對各種不同的東西做出美、丑、崇高、悲劇、反諷、荒誕的具體價值評判的。元美學主要研究美自身是什么,規范性美學主要研究哪些東西被人們看成是美的。盡管都涉及美丑之類的價值術語,元美學主要關注“事實性”一面,努力澄清它們在表述人們的價值評判方面有什么含義;規范性美學主要關注“評判性”一面,旨在運用它們具體評價各種東西對人們有什么意義。舉例來說,中文的“美”或英語的“beauty”,在用來表述“美”的價值評判時是什么意思,彼此有沒有相通的地方,便屬于元美學的范圍;相比之下,討論黃山美不美,杜尚的《泉》是不是件藝術品,乃至由于意見分歧而爭論,則屬于規范性美學的范圍。孔孟、老莊、康德、黑格爾這些大師的美學觀念,主要還是試圖從這樣那樣的規范性視角出發,告訴人們在現實中什么樣的東西美,什么樣的東西丑。可是,他們在闡述這些觀念的時候要對美丑這些概念的語義內涵做出解釋和界定,實際上已經為我們提供了元美學層面的大量素材,只不過這些素材總是與相關的規范性觀念交融在一起,還沒有清晰地區分開來。其實,就連聲稱要考察“美自身”的柏拉圖,最終也依然立足于理性主義的規范性立場,得出了“美是理式”、“摹仿不是真藝術”等規范性結論。這種將“元”與“規范性”兩個層面混淆起來的做法,兩千年來一直妨礙著美學理論研究的進展,甚至導致了某些嚴重的扭曲。倡導元美學研究的目的,正是想改變這種混亂的局面,通過把上述兩個不同的層面分離開來,一方面,引導規范性立場不同的人們在元美學層面上達成某些必要的理論共識,另一方面,在規范性層面上展開富有成果的理論交流,建構并且證成各自不同的具體美學理論。
元美學的頭號任務就是從描述性和分析性的視角出發,澄清“美”字的核心語義,因為美學理論的其他概念,諸如丑、崇高、悲劇、反諷、荒誕等等,都是在“美”概念的基礎之上形成的。就像“利”、“真”、“信”、“道德之善”能夠分別看成是實利、認知、信仰、道德領域的“好”,而“害”、“假”、“疑”、“道德之惡”能夠分別看成是這些領域的“壞”一樣,“美”也可以說就是炫美領域的“好”或“善”(所謂“美好”),“丑”則可以說是炫美領域的“壞”或“惡”(所謂“丑惡”)。以往在解釋《說文解字》中“美與善同意”命題時,更偏重于強調美與道德之善相互一致的一面,不過,從元價值學的維度看,它實際上也潛在指出了美與廣義之善(好)在核心語義上的彼此相通。所以,倘若我們接受《孟子•盡心下》有關“可欲之謂善”的元價值定義(2),那么,美就有理由說成是炫美領域內值得意欲的,丑則有理由說成是炫美領域內令人厭惡的。指出“美”字與“好”、“利”、“真”、“信”、“狹義之善”在“可欲性”上的相通之處,只是揭示了其核心語義的一個方面;更重要同時也是更困難的問題在于,揭示“美”字有別于后面這些字詞的特異內涵,說明當稱贊某個東西“美”的時候,與稱贊這個東西“好”、“有利”、“真”、“可信”、“道德上善”的時候,意思上有什么不同。事情很清楚:如果它們之間沒有任何差別,也就沒有必要在后面這些字詞之外,再多此一舉地發明和運用“美”字了。古今中外各種美學理論圍繞美和藝術與功利、科學、道德、宗教之間關系展開的大量討論,雖然不可避免地帶有這樣那樣的規范性烙印,但也在不同程度上包含著元美學的意蘊,試圖從不同的角度解釋這些概念在核心語義方面的微妙區別。因此,倘若我們能夠將其中那些往往引起歧異或爭論的規范性內容分離出去,而把目光聚焦在“美”字作為價值術語的事實性語義之上,那么,得出下面的元美學結論或許就不是特別困難了:美實際上是一種通過感性形象顯現人性內容的好東西,由于能夠使人產生心身方面的感性愉悅而值得意欲。正是這一點,不僅把美與廣義之善(對人有益、為人意欲、使人快樂的好東西)區別開來,而且也把美與利(能夠維持肉體生命、滿足本能需要的好東西)、信(能夠讓人崇拜信賴、獲取心靈慰籍的好東西)、真(能夠滿足人們求知欲的好東西)、道德之善(人們在人際關系中認為值得意欲的好東西)區別開來,從而體現出它作為生活世界中一個價值領域的相對獨立性。
再從這個角度反觀中外美學史上的種種規范性學說,我們會發現,它們之間圍繞“美的本質”問題呈現出來的根本性歧異,往往首先在于對人性內容的不同規范性指認上,其次在于對顯現人性內容的感性形象的不同規范性限定上,像儒家主張以溫柔敦厚的形象顯現忠孝仁義的人性內容,道家主張以素樸恬淡的形象顯現自然無為的人性內容,古典主義主張以典雅和諧的形象顯現理性的人性內容,浪漫主義主張以奔放動蕩的形象顯現情感的人性內容,馬克思主義主張以創造性自由的形象顯現人們在實踐中獲得的創造性自由的人性內容,等等。因此,基于上面得出的那種元美學共識來反思這些規范性美學之間的爭論,我們或許就能澄清它們的分歧焦點到底在哪里,哪些爭論是可以在美學領域得到解決的,哪些問題無法在美學領域得到解決而必須延展到其他領域(諸如道德領域、信仰領域,乃至更廣泛的人性領域)才有可能得到解決,從而避免一些沒有意義的爭執,推動美學研究取得有實效、有意義的進展。當然,還有一些規范性美學理論,認為美是客觀事物或自然界本身的一種屬性,因而不會接受上面論及的把美視為一種對人而言的價值意義的元美學共識。不過,即便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也可以在元美學的事實性層面上,通過分析“美”字的核心語義及其日常語用,尤其是通過分析持有這些觀點的美學家們自己對于“美”字的理論語用,來澄清彼此之間的分歧焦點,從而找到問題的實質所在。由此出發,還能進一步反思當前在中文語境里廣泛使用的“審美”一詞。它來自對古希臘文“aisthesis”、英文“aesthetic”的譯讀,原初語義是“感性認識”,或曰“通過感官認知外部世界”,因而具有濃郁的認識論意蘊。西方主流美學一方面憑借這個概念揭示了人與美之間的價值關系所包含的感性和認知性內容,另一方面又導致了許多扭曲,尤其是把美與真這兩種不同的價值混為一談,在主客二分的架構中將人看成是被動把握對象之美的認知主體,結果忽視了美是獨立于認知之外的自立價值領域、人首先是美的能動創造主體這些元美學的事實。在中文語境里也很容易遮蔽中國傳統美學在天人合一的架構中早已形成的把美視為人的一種存在境界、把人視為美的生成者和擁有者的深邃洞見。就此而言,這個西化了的“審美”概念明顯存在著嚴重缺陷。有鑒于此,從元美學視角看,在中文語境里運用“炫美”一詞替換西化了的“審美”一詞,以標示美對于人的獨樹一幟的價值意義,很有必要。
理由主要在于,與認識論意蘊過分強烈的西化“審美”概念相比,“炫美”概念能夠更充分展現人與美之間價值關系的本體論內涵:人是炫耀美的能動主體,不是認知美的被動主體;美是人通過感性形象顯現人性內容的存在境界,不是存在于人之外、與人沒什么關聯的客體對象。其實,在生活世界里我們很容易發現,無論對于藝術家來說,還是對于普通人來說,所謂“審美”都不只是把美當作一種外在的對象來欣賞來感受的活動,而毋寧說首先是把美當作自身存在的一種感性顯現來“炫耀”的活動,或者說是把人性內容通過感性形象“炫耀”出來的活動。所以,“炫美”概念要比西化的“審美”概念更能展示美在人生本體論中的定位。不用細說,漢語中的“炫”字也有“虛榮浮華”等貶義內涵。然而,第一,從發生學的角度看,美其實正是人們的虛榮心和炫耀欲的直接產物,無論是藝術家的經典創作,還是普通人的日常裝扮,都是如此,于今為甚。第二,從思想史的角度看,無論是中國美學,還是西方美學,早就有把“美”與“光”關聯起來的觀念,如《周易•賁卦》暗示的“山下有火”,《孟子•盡心下》說的“充實之為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托馬斯•阿奎那說的“美在鮮明”,席勒和黑格爾等人說的“Schein”(放光輝的幻象),海德格爾說的“Lichtung”(澄明),等等。[2]14-15第三,從現象學的角度看,我們在生活世界里面對的美和藝術也都是種種大放光彩的“炫”,其本質不是西化“審美”概念所強調的“再現”或“摹仿”,而是所謂的“表現”或“顯現”。最后,從辯證法的角度看,就連“炫”字含有的“虛榮浮華”的貶義內涵,也有助于我們批判性地考察美在生活世界里的復雜意義,尤其是它作為一種“好”在諸善沖突中可能產生的負面效應。
從某種意義上說,元美學研究對于當代美學發展可能具有的最重要價值,或許還不在于澄清“美”作為一種特殊之“好”的核心語義上,而是在于引起人們對炫美領域中“對”或“正當”問題的充分關注。尤其是考慮到以往中西美學傳統都在很大程度上長期遺忘了這個問題,情況就更是如此。如前所述,20世紀西方倫理學界討論的一大熱點便是善與正當的關系,但奇怪的是,與“善”甚至“right”的復數“rights”(權利)都得到了清晰界定形成了鮮明對照,“正當”這個詞在中外學界幾乎沒有得到任何界定,以致其核心語義總是顯得云山霧罩。其實,要找到這種語義并不困難,因為在日常語用中,人們總是用“是”、“對”、“right”表示他們接受或允許某個東西,用“非(不)”、“錯”、“wrong”表示他們拒斥或反對某個東西。就此而言,如果說“善”的核心語義是“可意欲性”,那么“正當”的核心語義則可以說是“可接受性”;就連“權利”的哲理意蘊,也只有憑借這種核心語義才能得到有說服力的解釋。正是由于擁有了這樣兩種不同的核心語義,善與正當的關系并不僅僅存在于道德領域,而是普泛性地存在于生活世界的五大價值領域,因為在所有這些領域的日常生活中,人們都要運用“好”和“對”這兩個標示人類生活價值基準的字,來處理可意欲性與可接受性之間的復雜互動。在人類生活中,善與正當關系的復雜性集中體現在:一方面,從語義分析的角度看,值得意欲之好總是可以接受之對;另一方面,從現實生活的角度看,值得意欲之好在許多情況下又是不可接受之錯。例如,孔子在《論語•里仁》中曾指出:“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墨子•非儒》也以類似的口吻強調:“不義不處。”說白了,西方后果論與道義論的長期爭執就是圍繞這一點展開的。(3)、[3]76-98在炫美領域內我們也能發現類似的現象:美女身穿比基尼肯定很漂亮(亦即在炫美意義上的“好”),但以這個樣子出席學術會議,許多人也許就會認為無法接受了(亦即認為“不對”)。此外,像經歷過納粹集中營的猶太人拒絕欣賞瓦格納的交響樂,的受害者認為樣板戲的旋律雖然很好聽但不可接受,同樣體現出炫美領域內“善”與“正當”的復雜互動關系。
然而,或許由于沒能清晰界定“正當”語義的緣故,20世紀的一批西方學者盡管花費了大量精力,撰寫了許多論著,還是沒能澄清好對之間的復雜互動關系,反倒讓善與正當的關系變成了著名的哲學老大難。其實,只要立足日常生活,我們很容易發現:造成這種復雜互動的現實根源就在于,在人們想要的各種好東西之間,往往存在著孟子所謂“不可得兼”的張力矛盾,或者叫“諸善沖突”,由此導致了某些好東西雖然值得意欲卻又無法接受的現象。[4]78-100具體到炫美領域,“諸善沖突”既有可能發生在炫美之善與實利、認知、道德、信仰之善的互動關系中,也有可能發生在若干不同的炫美之善的互動關系中。前者的例證有:一件藝術品從美的角度看很好,但要么不能帶來功利效益,要么違背了科學真理,要么有傷風化,要么被認為褻瀆了神靈,從而導致這些不同價值標準之間的張力沖突。后者的例證有:在一幅書法作品中,某個字的技巧成熟,功力深厚,卻與其他字僵硬對立,甚至破壞了整個作品的結構,從而導致幾種不同炫美要素之間的矛盾對立。不過,無論是面對哪種類型的諸善沖突,都將迫使人們處理好與對的互動關系:你會不會接受這件很美的藝術品、這個有功力的字呢?就此而言,正像道德和政治領域中的善與正當關系一樣,炫美和藝術領域中的善與正當關系也是一個值得我們深入探討的重要話題。
事實上,20世紀已經有一些西方學者開始討論“aestheticrights”的問題了[5]163-170,不過或多或少帶有與道德和政治權利相類比的色彩,卻較少從元美學角度考察炫美領域內更具一般性的好對關系。在這方面也許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傳統美學的某些洞見。例如,中文語境里的“審美”一詞,雖然是對英文“aesthetic”的譯讀,但其中的“審”字本身卻源于《荀子•樂論》說的“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以及《樂記》說的“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等。它一方面具有“aesthetic”包含的觀賞、審視語義,另一方面又有“aesthetic”所沒有的審理、審度內涵。《說文解字》曰:“靜,審也。從青爭聲。”段玉裁注:“人心審度得宜,一言一事必求理義之必然。”已經把“審”與“正當”(度、宜、理義、必然)聯系起來了。所以,如果我們回歸漢語的本意理解“審美”一詞,就能賦予它某些與“aes-thetic”很為不同的哲理意蘊,并且由此啟發我們深入思考一些在當前甚至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的理論問題:我們應該根據什么樣的“正當”標準,評判(“審”)各種“好”的炫美現象?應該如何建立或對待藝術審查制度,諸如是不是應當允許播出像“蝸居”這樣的電視劇,帶有情色或暴力內容的電影是不是應當分級,如何進行分級?炫美標準與政治標準(包括西方人說的“政治正確”在內)之間到底有著什么樣的互動關系?對于所謂的“低俗”作品,我們是應當寬容呢,還是必須封殺?[2]171-198只有把炫美領域內這些關涉到一般性正當之審的問題搞清楚了,我們才有可能從“right”走向“rights”,進一步回答在炫美尤其是藝術領域內,人們擁有什么樣的權利、應當如何維護這些權利的難題,才有可能在理論上和實踐中處理好炫美與實利、信仰、道德、真知等領域之間的互動關系,才有可能最終找到美和藝術在整個生活世界中的本體論定位。
在目前多樣化的背景下依據中國美學傳統的豐富資源開展元美學的理論研究,對于當代中國美學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不但有助于我們澄清某些一直糾纏不清的基本概念的核心語義,避免或終止某些意義不大的紛爭,而且有助于我們深入思索炫美領域內一些長期受到忽視的重要問題(包括那些與正當和權利內在相關的美學問題),從而把當代中國美學的理論研究推上新臺階,尤其是幫助它擺脫長期以來對西方美學的依附從屬乃至摹仿照搬,使當代中國美學能夠憑借自己的創新性研究,真正與當代世界美學尤其是西方美學展開實質性的對話交流。
作者:劉清平單位: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