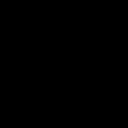小議后現代藝術文字的應用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小議后現代藝術文字的應用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在英文中,mutt意為笨蛋、雜種狗,紐約有一家賣小便器的公司亦名為“MuttWorks”,甚至還有一個卡通片名為“MuttandJeff”。杜尚對標題的設置與文字的簽題是很花工夫的,這也是他的標志。“泉”這個標題或許是對小便或者沖洗的暗示,不過也許也有美術史上下文的聯系,對象或許就是安格爾(JeanAugusteDominiqueIngres)的同名作品,如果說安格爾創造了一個女性化的陰性的《泉》,杜尚則創造了一個陽性意義的《泉》。如果說前者以一個看上去純潔但又有性誘惑力的裸女形象象征了古典主義純粹的藝術與生活,后者則以一個骯臟而隨處可見的男用小便池代表了大工業時代。而給《蒙娜麗莎》的印刷品添加胡子也許也有這類給陰性概念賦予陽性特征的意味。
不過杜尚他自己并不認為上面的討論是有必要的:“請注意,我沒有要拿他們做出藝術品來。‘現成品’這個詞是1915年我到了美國才出現的,這是個有趣的詞,但當我把一個自行車輪把兒朝下裝在凳子上的時候(1913)還沒有‘現成品’或其他想法,那只是個消遣。我沒有什么特別的原因要做它,也沒有任何意圖要展出它,或者拿它來說明什么……”①44杜尚的作品往往充斥著大量的性暗示,而他那些參與立體主義運動時期的畫作反而顯得過于純粹以至于純潔。不過,杜尚和他之前的那些畫家不一樣的地方在于,他并不通過畫面性的內容傳達性含義(按他自己的說法,就是不愿再通過視網膜的傳遞方式來解決問題,雖然在他早期的野獸派風格繪畫中有許多通過視覺呈現性暗示),而是通過在不具備展示性意味的物品上題寫具有隱秘含義的詞句,并通過與“現成品”的并置產生的互文關系來提示其含義,比如《泉》,還有他在1921年受凱瑟琳•德萊(KatherineDreier)所托創作并贈予她妹妹的《為什么不打噴嚏,羅斯•雪勒薇?》(WhynotSneezeRoseSélavy?)。同《泉》上題的“Mutt”一樣,羅斯•雪勒薇(RoseSélavy)在這里同樣是具有其他指涉的一個詞組及名字,Rose還可以寫作Rrose,讀作Eros,與希臘神話里司掌愛欲與性的神同音,而Sélavy則與法語里的習語C’estlavie讀音相似,所以這個簽名的隱藏含義即為“愛欲即生活”。而這件作品的標題“為什么不打噴嚏”則出自葛楚德•斯坦因(GertrudeStein)的現代詩歌《舉腹》(LiftingBelly)——一首具有瑣碎感覺記錄特質的非線性敘事詩歌。當然,這樣挖掘這件作品的意義對于我們的理解甚至還不夠,因為這件作品更為內在的密碼也許是作者杜尚與德萊姐妹之間所共有的私密故事或共同經驗,幾乎不能為后人所知。在整個西方美術史上,杜尚的創作方式在他之前幾乎沒有人嘗試過,雖然在他之后這種方式似乎被發揚光大了,但與再現性繪畫相比,他的方式仍然是很年輕以至于幼稚的(當然也避免了陳舊)。不過,杜尚在他的創作中對語言文字的應用以及與詩歌的聯系這一特征,被“二戰”后許多藝術家繼承下來,這些藝術家如博伊斯與基弗爾,則將其視線對準公共事務與血腥歷史,在繼承杜尚財產的基礎上,開辟出了自己的藝術天地。
約瑟夫•博伊斯的創作
與杜尚相比,博伊斯似乎更具有爭議性,而且關于他在藝術史中的貢獻至今也沒有定論。對于某些人來說,對待博伊斯這樣的藝術家,他們也許寧可繞開也不愿去討論,或者把他晾在一邊,等待所謂時間的考驗過去以后,自己方去撿起真金。不過,雖然面對的是缺乏共識的討論環境,但博伊斯仍然值得我們花費精力去研究,哪怕僅僅是出于擴展認知范圍的目的。對于博伊斯來說,杜尚與達達既是一種啟示也是一種約束,他自己應該也很清楚。所以他似乎從一開始就選擇了一種與杜尚截然不同的處理自己身份的方式,即將自身以往的生活經歷編織在自己的藝術創作里面,最有名的要算他在“二戰”時期當飛行員被擊中墜毀的經歷。據他自己的陳述,當他墜毀在俄國以后,是韃靼人用油脂和毛氈包裹他,運用巫術救回他一條命,他受到啟示,戰后遂決心以藝術作為自己的使命。不同于杜尚在訪談錄中將自己與自己的創作意圖塑造成平常人與平常想法,博伊斯幾乎在藝術生涯的開端就追求一種傳奇性,與杜尚的刻意隱藏相比,他的這種方式顯得要奇幻得多,但卻與空手道黑帶四段藝術家伊夫•克萊因(YvesKlein)相似(克萊因更多的是以其瘋狂的舉動聞名于世)。雖然博伊斯與激浪派以及伊夫•克萊因的淵源是顯而易見的,不過博伊斯更加聰明,在克里米亞凍土平原上行蹤不定的蒙古部落顯然比從二樓往下跳的行為更有吸引力。正如羅伯特•休斯(RobertHughes)所說的一樣:“在戰爭期間的經歷之于他的追隨者,幾乎相當于凡•高的耳朵。”②況且博伊斯講述這個故事,也不全是為了炒作自己:“墜機事件之所以獨特……因為只有他(博伊斯)成了解釋工具,并且使藝術家作品中那些突出而重要的方面,即油脂和毛氈獲得了意義。這些物品后來成了雕塑材料……這個故事的解釋力不僅依賴于自傳所建立的權威,也因為它用圖像志為觀眾提供了一把鑰匙。”③如果我們帶著這樣的所謂理論準備,再重新來看博伊斯的作品,就會發現并不費解了。比如《包裹》(圖2),從后門敞開的急救用面包車里面涌出許許多多的雪橇,每個雪橇上捆綁著毛氈、手電筒和一塊黃油,建筑在藝術家自身傳說故事基礎上的現成品有著治療的含義,而用于急救的面包車也許就是藝術家自己的化身——一個在大工業時代產生的現代化象征,由于某種遭遇,變成了傳播韃靼治愈術的巫師。不過從這幅作品中我們也可以看出急迫性:仍有如此多的人需要治療與救助。雖然“二戰”結束了,但德國的廢墟卻變成了冷戰的前線,戰爭的憂郁并未遠離。與杜尚相比,博伊斯的公共性相當突出,這不僅僅是因為二人面對的是不同的時代——一個是“二戰”前的優渥,一個是“二戰”后的倉皇,而且兩人對于文字的運用有所不同,杜尚的題字更多是一語雙關式的色情笑話,或者在小范圍內傳播的詩歌,而博伊斯則一開始就將自己置于大眾語境下的戰爭神話之中。也許其中更深的原因是兩者性格不同,或者博伊斯意識到不能像伊夫•克萊因或者激浪派那樣模仿杜尚或者模仿達達,從而刻意為之。甚至還有博伊斯本身的反戰主義立場在還起作用。
無論是其性格使然還是出于功利的目的,博伊斯堅定的公共立場使他有別于法國與美國的杜尚繼承者。雖然他為自己制造了一個怪異荒誕的故事,不過他或許是在“二戰”后涌現的藝術家里面最平民化、最缺乏精英意識的一位,畢竟韃靼神話并不像《杜尚訪談錄》那樣把自己用心地包裝在精致的語言里,以至于稍有常識的人都能看出韃靼故事的幼稚與漏洞百出。但博伊斯身上的這種小聰明卻并沒有掩蓋他的善良與公共意識,而常年在公共環境中摸爬滾打也使他做出了超越杜尚的作品,即“7000棵橡樹”。這一作品源自博伊斯在1982年提出的具有烏托邦特點的政治口號“都市森林化取代都市行政化”,作為德國綠黨思想先驅的博伊斯提出這樣的口號并不奇怪,但是,博伊斯完成這一作品的方式卻有異于杜尚,公眾的參與和明顯的生態與和平訴求是這一作品的特點,但是杜尚的影子仍然在作品實施前的政治口號上顯現了出來:“Stadtverwaldung”與“Stadtverwaltung”,一個字母的差別而已。如同杜尚將色情警句附屬在裝在籠子里的大理石方糖上,博伊斯將自己的想法和意圖通過口號附著在“7000棵橡樹”上,不僅如此,每棵樹旁邊矗立的玄武巖條石同樣暗示著博伊斯的雕塑家身份。每當公眾看到這些橡樹旁的條石的時候,就像看到小便池上的“R•MUTT”簽名一樣,條石也就是博伊斯的簽名。當他逝世時,計劃并未完成,只種下了5500棵橡樹,后來的橡樹則由其他人認領捐助,并被種下,樹旁也有同樣的條石。也許對博伊斯來說,這是最好的結果:在自身生命結束以后,仍有人完成其事業,繼續他的創作與簽題,而且這“簽名”不僅僅是公眾對藝術家的紀念,同時證明自己綠化與和平的愿望被公眾認同與繼承。
結語
在分析了20世紀最具代表性的兩位藝術家后,我們似乎傾向于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由杜尚所發明的一種依賴文字或者聯系其他信息的藝術創作手段,似乎逐漸成為當代西方藝術家的常用方法,這種方法不僅要求藝術家關注除手工技藝以外其他領域的知識,甚至要求藝術家對公共事務有獨到的見解與介入,最后使自己的藝術創作成為公共事務的一部分。
作者:孫乙量單位:四川大學藝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