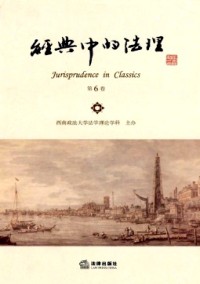經(jīng)典相聲段子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經(jīng)典相聲段子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fā)現(xiàn)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經(jīng)典相聲段子范文第1篇
馬三立 ,中國已故相聲泰斗,相聲八德之一馬德祿之子。回族,甘肅省永昌縣人。曾任中國曲藝家協(xié)會顧問、天津市曲藝家協(xié)會名譽(yù)主席等職。是五、六、七、九屆天津市政協(xié)委員。亦是一位德藝雙馨的人民藝術(shù)家,擅使“貫口”和文哏段子。馬三立在長期的藝術(shù)實(shí)踐中潛心探索,創(chuàng)立了獨(dú)具特色的“馬氏相聲”,是當(dāng)時相聲界年齡最長、輩分最高、資歷最老、造詣最深的“相聲泰斗”,深受社會各界及廣大觀眾的熱愛與尊敬。馬氏相聲雅俗共賞,在天津更是形成了“無派不宗馬”的說法。
(來源:文章屋網(wǎng) )
經(jīng)典相聲段子范文第2篇
刀子嘴豆腐心
2012年5月,王自健開始主持東方衛(wèi)視《今晚80后脫口秀》節(jié)目,從此一炮而紅,進(jìn)入了眾人的視野。他時而幽默,身著筆挺的西裝,用一臉無辜的表情扭曲著自己的身體;他時而尖銳,說在快速上漲的油價(jià)面前,加油管子好像變成了可怕的肺管自己身體;談到藥家鑫案,他說“一個叫‘漲工資’的,藥家鑫(諧音:要加薪),很殘暴”。人們熟悉他的樣子,是在閃耀的聚光燈下和精致的西裝上,其實(shí)王自健最被認(rèn)可的身份是草根相聲名人,低潮時,能容納百人的場子里只有7個人來聽他說相聲。人們漸漸發(fā)現(xiàn),在犀利如尖刀的王自健身上,有種不一樣的氣質(zhì),他對中國相聲發(fā)展前景的關(guān)注,打上了以“80后”為特征的時代烙印。
王自健是為數(shù)不多出名后仍堅(jiān)持小劇場相聲的相聲藝術(shù)家。他每周末固定在北京演出,基本都會回顧本周熱點(diǎn)話題,從利比亞局勢到日本核危機(jī),從油價(jià)上漲到80后生活困境,人們把他的這種相聲叫做“公民相聲”,也稱作“敢說真話”的相聲。王自健說自己的相聲是“槍版”的。槍版原是“搶先版”的意思,一般是在電影院里用機(jī)器偷拍回來的。王自健解釋說因?yàn)樽约旱南嗦暠硌葸^程中有笑聲。但過后人們會發(fā)現(xiàn),總有那么幾個當(dāng)下最熱的事在他的相聲里“中槍”。
王自健有很多經(jīng)典而尖銳的段子。反映百姓生活不易,他說,“其實(shí)老百姓沒什么要求,就是想過上和國企員工一樣的生活。如果我是在山溝里,忍一輩子我也不冤,您說我在北京跟生活在村里似的,那我冤不冤啊?”
王自健形容自己的職業(yè)狀態(tài)是“掙著賣白菜的錢,操著賣白粉的心”,其實(shí)也就是藏在刀子嘴后面的“豆腐心”。他習(xí)慣于把自己的團(tuán)隊(duì)推到風(fēng)口浪尖上,某種程度上代表了新一代藝人對未來的思考。
頑童與叛逆
王自健1984年出生,北京人,腦子挺靈光,卻從未正經(jīng)讀過書,他做事情追求要絕對有意義。
他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工薪階層。父親從事建筑工作,母親在火車站當(dāng)售票員。小時候,因不肯做沒意義的作業(yè),老師帶領(lǐng)同學(xué)們排擠他,沒有人跟他玩。為了逗同學(xué)開心,王自健從電視機(jī)中學(xué)習(xí)模仿馬三立說相聲,還因此上過中央電視臺。
9歲那年,他進(jìn)入中央電視臺蒲公英藝術(shù)團(tuán)學(xué)習(xí)相聲,還在央視的蒲公英劇場中多次表演節(jié)目。不過,學(xué)習(xí)只堅(jiān)持了一年,再次與相聲結(jié)緣已是14年后的事了。這是因?yàn)椋踝越∶χ芭涯妗比チ恕?/p>
他就像是一頭誤入田埂的斗牛,磕磕絆絆卻又極度豐富的度過了學(xué)生時代。中考那年,體育測試考1000米跑,王自健被另一個學(xué)校的考生插到前面,導(dǎo)致其“呼吸節(jié)奏被打亂”。他飛起一腳把別人踹出跑道,王自健因此在體育成績上一分也沒拿到,他只能上了一個非重點(diǎn)的高中。
考大學(xué)的時候,王自健又倔強(qiáng)的認(rèn)為自己用不著荒廢高三這一年的青春來復(fù)習(xí),讀到高二他就退學(xué)了,以社會青年的身份在街道報(bào)名參加高考,最終考上了一所大學(xué)。上了一年大學(xué),他又退學(xué)了,原因是當(dāng)時他收入不菲的兼職撰稿工作很有意思,也太忙,重要的是,他認(rèn)為大學(xué)教不了什么。
王自健說,這么多年也沒覺得后悔。因?yàn)樽约罕绕胀ū究粕吹臅辽俣?00倍,社會經(jīng)驗(yàn)、閱歷也比他們豐富,這源于在玩世不恭的背后,王自健也有對自己“下狠手”的一面。
王自健涉獵廣泛,就連與相聲毫不沾邊的外國文學(xué)也不放過,因?yàn)樗嘈拧斑@里面有好東西。”他逼迫自己看了很多書,“比如說梁文道推薦的《2666》,翻完了八百多頁仍是根本看不明白它要說什么。”他對自己說,“總有一天我會明白的,看這本書的痛苦程度直逼看《百年孤獨(dú)》,那本書我都看完了,這算什么?”
成名之后,經(jīng)常有家長帶著孩子去找他學(xué)相聲。王自健說:“全被我轟回去了,不上學(xué)什么都沒有。”
他干過很多工作,從電視競猜游戲節(jié)目、電視編導(dǎo)到廣告公司做提案,曾經(jīng)是標(biāo)準(zhǔn)的白領(lǐng)。直到偶然得到一個在大學(xué)校園里義演的機(jī)會,滿場的火爆讓他重拾相聲,“我當(dāng)時也挺奇怪:我也沒學(xué)過相聲啊,怎么就火了呢?”
包袱抖在心坎上
在王自健的相聲里,他把自己對社會、政治的最新熱點(diǎn)新聞進(jìn)行解讀,形成周周都有新段子,所有段子都與時事相關(guān)的運(yùn)作套路。王自健說,“我只表達(dá)自己的觀點(diǎn),但不輸出自己的價(jià)值。我是個善良的人,有的事我覺得我應(yīng)該去說,那么就去說說。”
他的師父、著名相聲演員侯耀華曾對他轉(zhuǎn)戰(zhàn)上海充滿疑慮。他說:“我之前不看好他,也不支持”,原因就是相聲中的方言文化很重要,王自健要想在上海站住腳很費(fèi)力。
王自健不以為然。他直言,以前的相聲演員和現(xiàn)在完全不同,生活節(jié)奏以及看到的事物內(nèi)容都不相同。他經(jīng)常問自己,自己在相聲中調(diào)侃的內(nèi)容既然是大家的內(nèi)心,為什么不說?如果相聲不關(guān)注這些話題,反而是虛偽的。
他的相聲已經(jīng)成為表達(dá)公眾意見、傳播常識的平臺,一個段子傳出去以后常能引發(fā)網(wǎng)民的一番討論,也有人會想方設(shè)法的聯(lián)系王自健,讓他把自己當(dāng)下看到的不平去說說。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接受了這種獨(dú)特的相聲,因?yàn)樗南嗦暲镉挟?dāng)代年輕人的共鳴,有人評價(jià)他“把包袱抖進(jìn)了心坎里”。
經(jīng)典相聲段子范文第3篇
一提起“曲山藝海”,人們馬上就知道這是在說濟(jì)南,而一提起濟(jì)南,人們又馬上能說出山東快書、山東琴書、山東評書等為大眾喜聞樂見的曲藝形式。或許正是濟(jì)南人骨子里那與生俱來的幽默情結(jié),傳統(tǒng)的曲藝早已經(jīng)融入了濟(jì)南百姓的生活。自古以來,泉城濟(jì)南就有著“曲山藝海”的美譽(yù),它曾與北京、天津并稱為曲藝的“三大碼頭”,多少名家從這里成名,多少名段從這里誕生,而又有多少的曲藝新秀來這里“朝圣”。那時的濟(jì)南觀眾非常精通曲藝,看得多了自然欣賞水平就高,一個曲藝新人到濟(jì)南一張嘴,濟(jì)南觀眾就知道他幾斤幾兩,一般演員想得到濟(jì)南觀眾的認(rèn)可和好評,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才有“北京學(xué)藝,天津練活兒,濟(jì)南踢門檻兒”等流傳了幾十年的老話。說白了,你只要得到了濟(jì)南觀眾的認(rèn)可,你在曲藝界就能火了。
“南來的角兒,北來的腕兒,都要到晨光露露面兒”。從1943年相聲大師孫少林創(chuàng)建晨光茶社,到1966年歇業(yè),晨光茶社極一時之盛,留下了許多令人津津樂道的故事。
馬三立給孫少林取“大號”
晨光茶社1943年9月2日由孫少林創(chuàng)建。
孫少林1923年出生于天津一個貧寒家庭。父親主要靠“踩百家門”生活,母親出身漁民家庭,嫁夫后靠做一些縫補(bǔ)活貼補(bǔ)家用。在這樣一個貧寒家庭,孫少林沒有機(jī)會入學(xué)讀書,平時就與一些孩子混跡于天津幾家大戲園子,看演出聽相聲。他天資聰穎,許多段子一聽就會,一學(xué)就像,很討一些老輩相聲演員的喜歡。
9歲時,孫少林正式拜師學(xué)說相聲,13歲時開始嶄露頭角,此后幾年,他一直在天津演出,磨練技藝。
1941年,濟(jì)南青蓮閣劇場老板馬玉山專門到天津請人來濟(jì)南說相聲。青蓮閣劇場位于濟(jì)南二大馬路,主要演出京劇、大鼓、山東快書等綜藝節(jié)目,有時也雜演濟(jì)南的地方相聲,但罵人的“臟口”多,難登大雅之堂。慕京津兩地相聲正宗之名,馬玉山才想到天津求賢。
經(jīng)過圈內(nèi)人推薦,李壽增、孫少林、趙蘭亭師徒三人成了南下山東的人選。
聽說這師徒三人要到濟(jì)南去闖蕩,馬三立等天津藝人無不寄予厚望,希望他們能一炮打響,給相聲開拓出一處新的立足之地。
當(dāng)時,孫少林還沒名字,平日里大家都叫他乳名“大萊子”。馬三立對孫少林說:“這次去濟(jì)南闖碼頭,不能再叫你大萊子了。但愿你們能夠三拳打出個少林寺,一炮震響濟(jì)南府。借這個意思,我給你起個名,就叫孫少林吧。”
從此,孫少林有了“大號”。
妹妹結(jié)婚聘禮用來租場地
來濟(jì)南演出一段時間之后,孫少林發(fā)現(xiàn)濟(jì)南的觀眾熱情,而且有眼光,相聲氛圍也越來越濃厚,就有了在濟(jì)南建立相聲大會的想法。這個想法與師父李壽增不謀而合。師徒二人相中了大觀園商場。1943年,大觀園商場已經(jīng)成為濟(jì)南初具規(guī)模的經(jīng)濟(jì)商貿(mào)、文化娛樂場所,人流密集。大觀園東門內(nèi)有一處曾經(jīng)演皮影戲的場子,正好閑置,非常適合舉辦相聲大會。只是,要租這個地方,租金要100余袋洋面的錢。這不是個小數(shù)目,當(dāng)時一袋洋面約折合一塊銀元。
孫少林其時并未有多少積蓄,一時犯了難。這時,有一位在鹽務(wù)局工作的人向?qū)O少林的妹妹求婚,并愿意拿出一部分錢來做聘禮。當(dāng)時,孫少林妹妹年齡尚小,家人本不太同意她過早出嫁。但為了支持孫少林建立相聲大會,不得已將女兒早早嫁了出去。用妹妹結(jié)婚聘禮的錢和全家微薄的積蓄,基本解決了租金問題。但接下來房屋維修、購置舞臺設(shè)施、觀眾座椅等,還需要錢。全家人東賒西借,甚至不惜借了印子錢(高利貸),晨光茶社終于成立了。
觀眾太多“提閘放水”
晨光茶社正式開業(yè)是在1943年9月2日。其時,20余位京津相聲名家前來捧場,盛況空前。
第一個節(jié)目,就是有“小神童”、“快嘴李”美稱的李伯祥和其父李潔塵共同表演的《六口人》,喻六六大順、開業(yè)大吉之意。李伯祥當(dāng)時還不到六歲,因?yàn)閭€子矮,只好踩條凳子。就是這條普通的榆木方凳,一直保存至今,成了當(dāng)年晨光茶社留到現(xiàn)在的唯一一件實(shí)物。
此后幾年間,張壽臣、馬三立、高德明以及周德山(周蛤蟆)、吉坪三、劉寶瑞、郭全寶等國內(nèi)幾乎所有大腕級的名家,紛紛來晨光演出。晨光的名頭越來越響,濟(jì)南也與北京、天津并稱為“曲藝三大碼頭”。
能在晨光登臺的,都是腕級的演員。他們的表演,不用說不斷增加的新段子,就是那些傳統(tǒng)段子,也是百聽不厭。所以一批相聲迷從進(jìn)場,屁股就粘在了那里。這樣,門外排隊(duì)的老是進(jìn)不來。
水庫滿溢,需提閘放水。為了照顧門外排隊(duì)等候的觀眾,晨光茶社也采取了“提閘放水”的辦法,讓喜歡相聲的都有看演出的機(jī)會。
這時,茶社往往會安排一名演員上場,說段平淡無奇、從頭到尾一個包袱都沒有的段子。如此一來,就有觀眾受不了了,起身拂袖而去。有的借機(jī)去吃飯,或者上趟廁所。茶社里的座位就會空出幾個,外面排隊(duì)的人就可以進(jìn)來聽了。
演員靠打分排隊(duì)吃飯
在晨光茶社演出,演員無論名氣大小,都要打分站隊(duì),根據(jù)排隊(duì)的情況,來決定每天演出所得的分成。
具體做法是,演員每周集合,自己先給自己定一個分,然后站在那里。如果有人覺著自己水平比這位高,就可以喊一個更高的分,然后站到前面。依此類推。不過,誰也不敢憑空往高里喊,不敢多要分。因?yàn)楹案吡耍瑒e人也沒異議,排到了前面,到時候接不住場,壓不了軸,流失了觀眾,那責(zé)任可就大了。
打分排隊(duì)一般一個星期進(jìn)行一次,有時半個月。為了能多取得分成,演員們自覺地挖掘自身潛力,排演新段子,練絕活,大大促進(jìn)了業(yè)務(wù)水平的提高,演出效益節(jié)節(jié)攀升,演員們的收益也是節(jié)節(jié)高,不少演員都置地買房,過上了好日子。
這“踢門檻兒”,有兩重含義。一個是踢觀眾的門檻。濟(jì)南觀眾見多識廣,不是輕易就能糊弄的。到晨光茶社演出,會的段子少了不行,而且不能僅會那些大路活,還應(yīng)該有新鮮活、絕活,觀眾看了覺著過癮,服氣,才會歡迎。二是踢晨光茶社演員的門檻。能在晨光演出立足的,都身負(fù)絕技。一般水平,到了晨光,只是看看、聽聽、學(xué)學(xué),連上場的機(jī)會都沒有。沒有真本領(lǐng),即使名家引薦,勉強(qiáng)登臺,最終也難以立足。
有這樣一個故事:馬三立的一個徒弟,被推薦到晨光來演出。根據(jù)慣例,第一天演出,他的名字在水牌上寫得最大,節(jié)目也放在最后壓軸。結(jié)果登臺后,效果并不理想。第二天,名字就被前移一位。最后,這位演員的名字逐次前移,排到第一個出場。因?yàn)橐沁€把他排在后面,壓不住場,留不住觀眾,就掙不到錢,連累了大家。
演出負(fù)責(zé)人就對這位演員講:“如果想繼續(xù)在晨光演下去,每天只能拿兩毛錢的薪水。”最終這個人還是走了。
作為晨光茶社的創(chuàng)始人,孫少林自己身體力行。從表演方面來說,孫少林說、學(xué)、逗、唱功夫全面,傳統(tǒng)的段子都能演好。而他又特別善于兼收并蓄,并迅速加以吸收利用。他或?qū)⑿聝?nèi)容融合到舊段子中出新意,或干脆創(chuàng)作出新段子。
比如,孫少林、劉寶瑞合作的《鍘美案》,是一個經(jīng)典段子。其中孫少林逼真模仿裘盛戎的唱腔,是一大亮點(diǎn)。連專程到茶社觀看孫少林演出的裘盛戎,也禁不住點(diǎn)頭稱賞。雖然如此,時間一長,觀眾也難免會有感到厭倦的時候。如何讓這個段子常有新意,孫少林一直煞費(fèi)心思。
后來,評劇名凈魏榮元等拍攝了評劇電影《秦香蓮》。孫少林敏銳地從中發(fā)現(xiàn)了機(jī)會。為了學(xué)習(xí)其中的評劇唱腔,電影甫一到濟(jì)南上映,孫少林馬上就到茶社隔壁的大觀影院去看,一場接一場連著看。到了晚上,就把這唱腔惟妙惟肖搬到了舞臺上。全場觀眾都驚訝不已。
經(jīng)典相聲段子范文第4篇
本期上海榜單被“達(dá)人”標(biāo)簽全面占領(lǐng),堪稱“達(dá)人”專屬榜。從總決賽到頒獎禮再到相關(guān)衍生節(jié)目,《中國達(dá)人秀》橫掃上海十月綜藝熒屏。收視率方面,《中國達(dá)人秀》一如既往傲視群雄,總決賽收視率達(dá)到34.93%,收視份額接近80%,連排名收視榜第五的《達(dá)人立波秀》都有20.21%的收視率,這樣的輝煌令其他所有綜藝節(jié)目望塵莫及。
可以說,首次引進(jìn)國內(nèi)的達(dá)人秀節(jié)目成功實(shí)現(xiàn)了與中國市場的對接,在同期其他各類選秀節(jié)目均“疲軟”的情況下,達(dá)人秀算是一針強(qiáng)心劑,給選秀節(jié)目的未來注入了希望之光。當(dāng)然,圍繞著《中國達(dá)人秀》的話題和批評也一直沒有間斷,包括有質(zhì)疑認(rèn)為該節(jié)目給予弱勢群體的同情分太多,有礙公平競爭,而評委的表現(xiàn)也有不盡人意之處等等,但這些爭議未妨礙達(dá)人秀的成功。相信在收獲首屆的豐厚成果后,未來的《中國達(dá)人秀》甚或中國選秀市場,都有新的思考和動力。
北京榜單體現(xiàn)的主要是“快樂”元素。分列榜單一、二、五位的《藍(lán)色經(jīng)典天之藍(lán)杯第五屆CCTV相聲大賽》《歡樂世博笑林盛典京津滬》和《國慶7天樂主持也快樂》都是充滿笑聲的節(jié)目。其中《藍(lán)色經(jīng)典天之藍(lán)杯第五屆CCTV相聲大賽》在國慶七天長假中,給北京觀眾奉獻(xiàn)了一道歡樂大餐,參賽作品中有不少段子融入了時下備受認(rèn)可的其他曲藝表演形式,在相聲藝術(shù)方面做出了創(chuàng)新。另外,《歡樂世博笑林盛典京津滬》也是曲藝類節(jié)目,可見北京的觀眾對于語言類節(jié)目有著特別愛好。
廣州榜單呈現(xiàn)出多樣化面貌,排名首位的《叮王爭霸》是類似《中國達(dá)人秀》的選秀比賽,第二名《花城新星大賽》是選美晚會,排名第四的則是煙花表演。值得一提的是,相對于港產(chǎn)綜藝節(jié)目的強(qiáng)勢,《叮王爭霸》幾次保持住了冠軍位置,由此可見綜藝節(jié)目的“接近性”作用有多強(qiáng)大。廣州綜藝節(jié)目應(yīng)多考慮融入本地文化特色,挖掘本地群眾的參與熱情,以增強(qiáng)對抗港產(chǎn)節(jié)目的實(shí)力。
經(jīng)典相聲段子范文第5篇
談到相聲在臺灣的發(fā)展情況,姜昆說,據(jù)他看到的資料介紹,1949年后,相聲藝術(shù)才正式在臺灣生根開花。臺灣相聲藝術(shù)傳承始自陳逸安、吳兆南、魏龍豪先生,他們都來自祖國大陸,憑籍著對相聲的喜愛與執(zhí)著,以年輕時在啟明茶社中聽得的相聲為藍(lán)本,從臺灣社會現(xiàn)實(shí)出發(fā),對諸多傳統(tǒng)名段重新加以演繹,起初主要在勞軍演出中表演,隨后在晚會上正式登臺表演。
據(jù)魏龍豪先生在臺北新舞臺《吳兆南、魏龍豪,上臺一鞠躬》演出自序中所述,這一時期,傳統(tǒng)相聲及其他曲藝品種在臺灣頗受歡迎,吳兆南、魏龍豪、周志泉、王靜波等相聲名家,聯(lián)合章翠鳳女士的京韻大鼓,高欣伯先生的戲法、孫玉鑫先生的評書,組成“鼓、溜、彩”的雜耍形式在螢橋河畔的納涼晚會上演出,后又在馬繼良先生創(chuàng)建的樂園書場,以及西門町的蓬園書場、紅樓書場等地演出,另有陳逸安與小齡童(楊寶華)搭檔登場,侯瑞亭、王祥林、趙如明三位組合,偶爾下海客串,也備受觀眾追捧。
上世紀(jì)六十年代,魏龍豪、吳兆南及陳逸安先生借助新興的廣播媒體推廣相聲藝術(shù),開始在電臺播出相聲節(jié)目,播出之后深受聽眾歡迎,魏、吳兩人的相聲成了當(dāng)時最受歡迎的廣播節(jié)目,街頭巷尾,到處可聽到“魏龍豪、吳兆南,上臺一鞠躬,現(xiàn)在輪到我們哥兒倆,侍候您一段相聲”的聲音,甚至還流傳有“武俠看金庸,相聲聽魏吳”的說法。那個時候臺灣社會中電視還未普及,廣播相聲是大眾最熟悉的文化娛樂活動,所以由廣播媒體普及,在臺灣,不論士農(nóng)工商、男女老幼,提起魏龍豪與吳兆南,幾乎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吳兆南先生曾告訴姜昆:“那個年代能聽一段正兒八經(jīng)的相聲,你不知道有多難。我冒著偷聽敵臺的危險(xiǎn),從短波里搜大陸廣播電臺,找侯寶林先生的段子,聽一段吱吱啦啦帶雜音的相聲,如獲至寶,錄下來大家傳著聽、學(xué),那是我們最開始的‘錄(音機(jī))老師 ’”。
1968年,魏龍豪、吳兆南先生在臺灣出版第一張相聲唱片,后又錄制相聲集磁帶《相聲集錦》、《相聲選粹》、《相聲捕軼》等,匯集了250多段相聲精華,包括《歪批三國》、《唐漢爭》等,使得這些經(jīng)典段子在臺灣社會迅速傳播開來,成為臺灣相聲愛好者的啟蒙資料。魏、吳兩位先生的努力,使臺灣民眾領(lǐng)略了傳統(tǒng)相聲藝術(shù)的魅力,為傳統(tǒng)相聲在臺灣的傳播奠定了基礎(chǔ)。但由于政治因素影響,加之相聲表演所得收入微薄,許多相聲從業(yè)者紛紛改行,上世紀(jì)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臺灣相聲藝術(shù)日漸式微,僅靠魏龍豪、吳兆南及陳逸安先生的相聲錄音,勉強(qiáng)維系著相聲藝術(shù)在臺灣的傳承。
說起相聲藝術(shù)在臺灣的傳承和發(fā)展過程,姜昆講道,1984年,在臺灣發(fā)生了一件讓“相聲”兩字走進(jìn)千家萬戶的事情。從美國學(xué)習(xí)戲劇歸來的賴聲川先生,為紀(jì)念在臺灣經(jīng)濟(jì)迅速發(fā)展的大潮中逝去的傳統(tǒng)藝術(shù),以正被人們逐漸淡忘的相聲藝術(shù)形式為素材,創(chuàng)作了《那一夜,我們說相聲》。這部作品在臺北演出獲得了極大的成功,以至于“觀眾幾乎是三句一笑、五句一爆,該笑的觀眾都如期笑了,不該笑的觀眾也出乎意料笑了”,演出實(shí)況錄音帶和CD的銷量超過100萬張,成為當(dāng)年的白金唱片。當(dāng)時在祖國大陸,有關(guān)臺灣的消息隔絕,相聲界不知道《那一夜,我們說相聲》是在演什么,直到1985年,姜昆和唐杰忠先生隨吳祖光先生到新加坡充當(dāng)新加坡相聲大賽的評委,有機(jī)會見到了臺灣漢霖說唱團(tuán)團(tuán)長王振全先生與有“新加坡相聲之父”之稱的郭寶昆先生,又聽到了實(shí)況錄音的帶子,才知道那是一出戲,是賴聲川先生用西方解構(gòu)戲劇的方式演繹的一出反映相聲藝人今昔對比,從而引起當(dāng)下對傳統(tǒng)藝術(shù)思考的戲。在姜昆接下來與賴聲川的交往中,他了解到,這部作品的本意是哀悼相聲藝術(shù)乃至傳統(tǒng)文化,在現(xiàn)代化洪流中漸次消亡的現(xiàn)實(shí),卻意外喚醒了民眾心中對相聲的記憶,改變了相聲在臺灣發(fā)展所面臨的困境,為相聲藝術(shù)在新時期的發(fā)展注入了活力,也喚起了臺灣相聲從業(yè)者對自己鐘情的藝術(shù)的那份自尊。此后,眾多臺灣相聲從業(yè)者根據(jù)自己對相聲的理解,重新開始探究相聲發(fā)展的可能性,在已經(jīng)經(jīng)營多年的老的團(tuán)體如魏龍豪創(chuàng)立的“龍說唱藝術(shù)實(shí)驗(yàn)群”、王振全創(chuàng)辦的漢霖說唱藝術(shù)團(tuán)等基礎(chǔ)上,涌現(xiàn)出眾多各具特色的相聲表演團(tuán)體,如金超群創(chuàng)辦的“游于藝”茶藝館、臺北曲藝團(tuán)、相聲瓦舍等。侯冠群、劉增鍇、剛、樊光耀、馮翊剛、宋少卿、葉怡均等臺灣新生代相聲演員,在保持相聲表演傳統(tǒng)、重新詮釋相聲名段上做出了積極努力,同時也在變革創(chuàng)新,在相聲表演中融入大量戲劇元素方面做出了大膽嘗試,使新時期的臺灣相聲發(fā)展呈現(xiàn)出多元化的特征。
相關(guān)推薦更多
經(jīng)典遺傳學(xué) 經(jīng)典哲學(xué)論文 經(jīng)典教育論文 經(jīng)典匯報(bào)材料 經(jīng)典誦讀總結(jié) 紀(jì)律教育問題 新時代教育價(jià)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