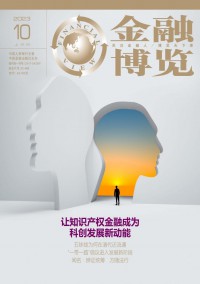金融自由化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金融自由化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摘要]一國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成功一般應具備四個條件,即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金融脆弱性的及時消除、審慎而有效的金融監管以及必要的制度環境建設。這些條件經過各國的實踐檢驗,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普遍性。但進行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前提條件并不絕對,更重要的是應該從本國國情出發,具體情況具體對待,不宜盲目模仿他國。
[關鍵詞]金融自由化;客觀經濟環境;金融脆弱性
金融自由化是國際經濟一體化的必然結果,是各國參與國際經濟合作、發展本國經濟的客觀要求。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拉美、亞洲的許多發展中國家都進行了大規模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從內容上來看,主要包括對內的金融自由化和對外的金融自由化兩個方面。對內的金融自由化主要包括放開利率管制、取消信貸配給、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取消中央銀行的利率補貼、放松對銀行、證券、保險的分業管理等;對外的金融自由化則包括開放資本賬戶、實行浮動匯率管理、對外放松金融業準入限制等。簡而言之,就是利率自由化、資本流動自由化、匯率自由化、銀行業務自由化以及金融市場自由化。
金融自由化改革為實行改革的發展中國家帶來了很多正面效應。例如實行利率自由化,市場機制的力量可確保帶來正的實際利率,以吸引游離于正規金融部門體系外的儲蓄,增加金融體系的資金來源;可以刺激借款人投資于更具生產效率的活動,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資本流動自由化增強了金融部門的活力,使儲蓄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優化配置,使本國居民可以在全球范圍內進行資產組合。在合適的宏觀經濟政策下,資本賬戶的自由化可以有效地控制資本外逃,并能對本國宏觀經濟起到內在的機制約束作用。更重要的是,金融自由化可以提高儲蓄率和資金分配效益,通過各種途徑推動經濟的發展。但金融自由化也是一把雙刃劍,把握得不好,可能阻礙經濟發展甚至引發經濟危機,造成災難性后果。拉美國家和東南亞國家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實踐證明:只有滿足了一定的前提條件,金融自由化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否則不僅難以達到預期目標,甚至可能會支付高昂的改革成本。由于各國的總體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結構以及金融市場發育程度不同,金融自由化的前提條件也不盡相同,但有些條件還是具有普遍性的,這些條件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
宏觀經濟穩定既是經濟政策的目標之一,又是金融自由化的前提條件。宏觀經濟穩定有利于投資,有利于實體經濟部門的經濟增長,有利于減輕金融自由化形成的沖擊,并且在金融自由化之后,能夠維持和鞏固金融自由化的成果。宏觀經濟穩定,在低通貨膨脹和預算赤字較小并能維持的條件下,金融自由化可導致適度的正的實際利率水平。信貸風險縮小,金融部門可能出現的各類問題,通過審慎的監管,可以較為容易地得到解決。如果改革是在動蕩不定的宏觀經濟背景下進行的,這種動蕩不定將會增加改革的難度,還會對金融自由化的沖擊擴大,難以保持和鞏固其改革成果。
宏觀經濟穩定是一個總體的概念,它包括國有部門的改革、通貨膨脹的控制、財政赤字的削減、國際收支平衡、靈活的匯率安排等十分豐富的內容,而其中又以通貨膨脹的控制和政府財政赤字的削減最為重要。通貨膨脹會引起相對價格的不穩定,使長期投資融資活動的風險增加并且難以進行,金融合同的未來購買力難以確定。即使利率不受規定限制,未來通貨膨脹率的不確定也使貸款人和借款人難以就一種合適的名義利率達成協議,增大了交易風險。在這種情況下,要維持正的實際利率是很困難的,而不能維持正的實際利率,又與金融自由化的核心精神背道而馳。在一些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變化不定的國家中,實行利率完全自由化,只會導致更高的實際利率以及貸款與存款利率之間的更大差幅。而且,在不穩定的經濟條件下,要防止實際利率的升值,只能是以影響實際部門的生產作為代價。
另外,如果一國在改革前政府財政赤字沒有消除或大幅度削減,金融自由化改革后將步履艱難。一般說來,在一定的廣義貨幣水平下,政府從銀行系統借款會減少國內私營部門可得的信貸額,在私營部門的活動比政府投資更具生產力的情況下,這種對私營部門借款的擠出,可能會對經濟運行有著嚴重的負面影響。因此,財政赤字的削減或控制是金融自由化的一個重要前提。另外,嚴明的財政紀律也是政府信譽的標志之一,有利于控制非經濟性通貨膨脹。從各國金融自由化的實踐來看,也是如此。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非洲許多國家在財政赤字沒有消減之前就開始金融自由化,結果受到嚴重影響,而亞洲大多數國家在金融自由化改革之前就削減了財政赤字,用貨幣和信貸衡量的結果,都表明這些國家出現了重大的金融深化,這很好地說明了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對一國金融自由化改革的重要性。
從實證研究方面來看,VillanuevaandMirakhor對南錐體國家20世紀80年代金融自由化失敗的實證分析表明:金融自由化失敗的主要原因是金融自由化改革之前的宏觀經濟不穩定,改革的進程和速度過快,在改革過程中又缺乏有效的金融監管。Caprio分析了6個發展中國家的金融自由化的經驗,認為宏觀經濟環境的穩定是取得改革成功的最重要的要素。
二、金融脆弱性的及時消除
金融脆弱性的一個突出表現就是銀行體系內高額不良貸款的累積。一國在進行金融自由化改革之前,如果銀行業積累了大量的不良資產,一旦進行自由化改革,這些不良資產很快就會暴露,危及金融系統的穩定。對于已經形成的不良資產,需要在自由化之前予以消除,這構成了一國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前提條件之一。但就一些發展中國家而言,在金融自由化改革之前往往難以徹底消除本國銀行體系內的不良資產,而是寄希望于在金融自由化的過程中予以逐步消化,這種現象往往被稱之為“邊做邊學”。
大量不良資產的存在,使銀行無法按照市場的原則來經營。而且銀行背負著沉重的不良資產包袱,需要中央銀行不斷予以信貸支持。這樣,商業銀行的信貸規模受到政府的約束。根據青木昌彥等人的研究,不良資產包袱還會將適應市場經濟的“保持距離型融資制度”扭曲為“關系型融資制度”。所謂關系型融資,按照青木昌彥的定義,是指出資者在一系列事先未明的情況下向企業提供融資,即商業化了的銀行仍然愿意在對融資風險缺乏把握或明知風險較大的情況下向企業融資。銀行已經發生的貸款成為企業不斷獲得新融資的“資產人質”,銀行為保證過去融資歸還的可能性不得不向企業提供不斷的關系型高風險融資。所以,關系型融資一旦形成,在很多情況下會形成自增強的機制。如果由于企業破產機制不健全,譬如形成內部人控制結構,融資道德風險就會演變為嚴重的企業對銀行的融資道德公害,在微觀和宏觀上形成資金尋租和貨幣漏損現象,進而削弱貨幣政策的效率。即使企業破產機制是正常的,關系型融資的道德風險也會導致企業破產逃債行為的泛濫。
東南亞國家在推進金融自由化時,大量的滯存不良債權未能及時處理。韓國、泰國銀行不良債權比例分別高達14%和18%,卻沒有增加貸款的損失準備金。菲律賓在1994~1996年間銀行貸款增加了38%,而貸款損失準備金在貸款總額中的比重卻從3.3%減到1.5%。如此孱弱的金融體系,必然難以承受來自國內或國外的沖擊,也容易被國際投機者所利用。相反,1997年中國臺灣銀行體系的不良貸款比率僅為4%,臺灣銀行憑借充足的盈余抵擋住了金融危機,遏制了實體經濟的衰退。
三、審慎而有效的金融監管
在金融自由化過程中,一國需要建立審慎而有效的金融監管體制,這適用于所有進行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國家。金融自由化并不意味著“金融機構的自由經營”,相反,金融機構所受的約束,在自由的環境中比在政府控制的金融約束機制下還要大。在自由的環境下,更加激烈的競爭以及金融創新使金融風險陡增,造成的破壞力更強,更不易被察覺。實施審慎而有效的金融監管,在于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健。不穩健的金融體系會對經濟產生極其嚴重的負面影響,銀行的穩健對金融體系的穩定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在金融監管不完備的條件下,銀行經理可能會由于利率管制的解除和銀行特許權價值的降低發放過量的風險貸款。很多國家在銀行部門引入競爭機制和賦予銀行自主權的同時,卻沒有采取措施控制這些相反的激勵,這一點成為金融自由化后發生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可見,主張金融自由化并不是完全否定金融監管,規范化與自由化并駕齊驅的金融改革,方是穩健的改革。
同時,金融監管應該建立在尊重銀行自主權的基礎之上,是一種審慎的監管。審慎的監管與金融管制之間的根本區別在于,前者對銀行的要求是一種規范性的品質管理,以防范金融風險和促進競爭為目的,銀行具有充分的業務自決權;后者則是銀行的大部分具體決定直接由政府機構做出。為達到防范風險和促進競爭的目的,審慎監管的中心工作在于鼓勵或強迫金融機構及時、準確、全面、公開地向公眾披露信息,增加透明度。在信息可得的基礎上,通過廣大市場參與者以自由選擇行為來發揮對金融機構的監督和制約作用。也即通過經濟力量本身對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活動實施制約,這是金融自由化下金融監管的精髓。
在實證研究方面,Williamson構造了一個謹慎監管水平指數,用來評估1973~1995年間33個發生過金融危機國家的金融監管水平。他運用1981~1995年三個5年期的全部數據進行卡方測試(Chi-Square),用來檢驗一個5年期內銀行危機的發生是否獨立于前5年審慎監管的平均水平。結果顯示,前兩個5年階段并不顯著,第3階段開始顯著。表明銀行危機與金融監管水平高度相關。其最終研究成果表明,沒有爆發系統性金融危機的國家的金融監管水平顯著高于爆發輕度危機國家的監管水平,而后者又比爆發嚴重危機的國家的金融監管水平高。
四、必要的制度環境建設
在實施金融自由化改革時,需要充實和完善一些基本的制度,以便為監管者發現和糾正錯誤實施有效監管創造條件。這些制度主要有會計制度、信用評級制度、資產評估制度、審計制度等。從操作性方面考慮,這些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應當在改革的早期開始,因為這能提高監管的效率。例如在衡量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標準時,要求正確評估銀行貸款組合、自有資產和其他表外業務。如果資產評估的標準不明確或不統一,評估的結果就會出現問題。巴塞爾委員會在《銀行業有效監管核心原則》中將制度環境稱為市場基礎設施,包容十分廣泛,如高度發展的公共基礎設施,包括公司法、破產法、合同法、消費者保護法、私人財產保護法;綜合的符合國際慣例的會計體系和規則;獨立的審計體系;嚴格而有效的支付和清算體系;有效的市場紀律,公開、可信、準確、及時的信息披露制度;以及系統化的社會安全網等。
為了說明一國制度質量對于金融自由化的影響,Deming-KuntandDetragiache用人均GDP與5個制度質量指數為代表,來檢驗在那些體制環境較差的國家中銀行危機與自由化的關系是否增強。將各種選擇性變量以金融自由化虛擬變量與代表制度環境質量變量之間的相互作用的形式,代入基線回歸方程中計算,計算結果表明,提高制度環境的質量,特別是減少腐敗的程度,加大執法力度,能夠減小金融自由化過程中伴發金融危機的概率。因此,在自由化進程中,首先應該重視制度建設。在制度不健全的國家,即使在自由化進程中或之前能保持宏觀經濟穩定,也會發生難以失控的金融不穩定。因此,構建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對于一國進行金融自由化至關重要。
綜上所述,本文歸納了一國進行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四個前提條件,這四個條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也為很多國家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實踐所證明。但是,金融自由化的前提條件并不絕對,有些條件本身可以融入金融自由化改革的進程中。另外,一國金融自由化改革成功的經驗往往很難直接移植到另一國,因此金融自由化還應該主要考慮本國的實際情況,從本國的具體國情出發,遵循一定的改革程序,循序漸進地走向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