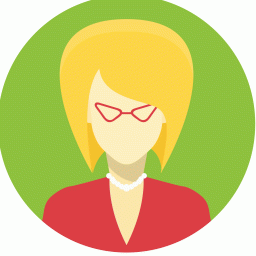商業銀行金融創新法律規避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商業銀行金融創新法律規避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內容提要】本文嘗試從法律規避角度為商業銀行的金融創新提供嶄新思路,文章首先借助經濟學和法學的研究工具對法律規避型創新進行理論探討;然后剖析了美國70年代以來在利率、分支機構、分業經營三個領域的法律規避型創新實踐;最后對我國目前普遍關注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和金融集團問題從規避創新視角予以深度闡釋。
【關鍵詞】商業銀行法律規避金融創新
俗諺云:“強龍不壓地頭蛇”,然而面對進入WTO的競爭與挑戰,中國金融業尤其各商業銀行并不由于自身豐富本土資源、服務網絡優勢而輕松幾許。“狼來了”,怎么辦?政府旨在提升商業銀行競爭力的若干政策相繼出臺,諸如發行特種國債充實資本金,剝離不良信貸資產,股份制改組以及上市等等,但是如何縮短與外資銀行之間創新差距的措施不多,因為行政手段在該問題上是束手無策的。本文與大量關于金融產品、金融市場、金融組織結構等技術層面研究不同,嘗試為商業銀行的金融創新規劃一個新思路——法律規避型創新。
一、法律規避型金融創新的經濟學與法學理論基礎
“創新”(Innovation)這一概念,最早是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Joseph·Alois·Schumpeter,1883——1950)于1912年出版《經濟發展理論》(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一書中首先提出。熊彼特觀點,所謂創新,就是建立一種新生產函數,即企業家將一種從來沒有過的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到社會生產體系的活動,“新組合”包涵以下內容:⑴引進新產品;⑵引用新技術;⑶開辟新市場;⑷控制原材料供應新來源;⑸實現企業的新組合。①熊彼特認為創新是理解資本主義體系以及發展的核心概念,創新是經濟發展的過程,也是經濟發展的原因,更是經濟發展的本質。上述創新理論,在上世紀50年代引起廣泛的重視,并首先應用于工業領域,技術創新成為一個流行詞語。發韌于70年代西方經濟發達國家的金融創新浪潮,促使傳統金融業發生深刻變革,金融創新(FinancialInnovation)的概念應運而生,面對眼花繚亂的新的金融工具、金融方式、金融技術、金融機構、金融市場及金融衍生產品,西方學者從不同角度探求金融創新原始動力,形成諸學派的創新誘因理論,而西爾柏(W·L·Silber)的約束誘導金融創新理論、希克斯(J·R·Hicks)和涅漢斯(J·Niehans)的交易成本創新理論、戴維斯(S·Davies)和塞拉(R·Silla)的制度學派創新理論以及凱恩(E·J·Kane)的規避型創新理論影響較大。②
字串7
上述創新理論都不同程度觸及金融監管與金融創新的互動性,凱恩理論認為當外在市場力量和市場機制與機構內在要求相結合,尋求回避各種金融控制和規章制度時就會產生金融創新。政府管制是有形的手,規避則是無形的手,許多形式的政府管制與控制實質上等于隱形稅收,阻礙金融業從事已有的盈利性活動和利用管制外的利潤機會,因此金融機構通過創新來逃避政府管制。金融機構對各種規章的適應能力較強,因為需求增長會促進貨幣供給,擴大貨幣供給的過程可以采取許多“替代品”的形式完成,但是當金融創新危及到金融穩定和貨幣政策不能按預定目標實施時,政府又會加強管制。同時,不同于傳統工具的替代品又會為規避而不斷生成,這樣管制又將導致新一輪創新。管制與規避引起創新不斷地交替過程,凱恩稱之為“管制辯證法”(RegulationDialectic)。
法律學者對“法律規避”問題,基于不同的法系理念而持有不一致的態度,普通法系賦予規避者較大的自由空間,“非法律明文禁止的都是允許的”,因此英、美等國是金融創新的主要策源地;相反,大陸法系僅在國際私法以及稅法的避稅問題上進行探討,而且相當學者認為法律規避是一種法律欺詐,所謂“欺詐使一切歸于無效”,對之持否定觀點。在我國“依法治國,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漸成共識下,法律規避問題似乎不合適宜,僅有朱蘇力學者從民間法與國家法沖突③,以及法律規避在社會轉型階段的制度創新作用的角度④給予肯定性的論證,筆者認為金融領域的法律規避型創新具有以下合理性:字串5
(一)法律規避型創新是對法律弊端的調適。任何法律不應以“良法”或“惡法”作以簡單評價,因為法律利弊可視為一枚銅板的兩面,所謂“有光的地方,就有陰影”。法律存在且不限于以下缺陷:⑴守成傾向,即法律是一種不可朝令夕改的規則體系;⑵法律規范框架中固有的剛性因素,法律具有地一致性與普遍性使解決個別案件面臨困難;⑶規范的控制和約束的擴張性。⑤寬容對待法律規避創新是矯正法律自身負面影響有效途徑之一:
例如,法律規避型創新是在發展變化客觀環境中對穩定的法律制度的新解釋或修正,使之在動與靜、保守與變革、僵化與無常的彼此力量之間謀求和諧統一;法律規避型創新給予資質相異的個體在法律的原則性下進行不同回應,獲取適己所需自由空間;法律規避型創新是對法律控制的反作用,法律的約束限制愈大,個體進行法律規避創新的動機也愈強,總之法律不能盡善盡美的客觀存在,是規避型創新存在的合理依據之一。
(二)法律規避型創新促使金融監管優化。凱恩理論認為金融監管當局和金融機構好似蹺蹺板做游戲的兩方,它們不斷彼此適應和作用。管制的理由不外公共產品、外部性、信息偏在等市場失靈,然而管制固化形成特定利益集團,也不可避免引致管制失靈,既限制競爭、減損效率和剝削消費者選擇機會等,而規避監管則可以打破舊利益分配格局,從而拋棄原管制不合理部分,繼承其合理成分,增添新內容產生新管制,再管制實質上是對原管制的否定之否定。該認識也適用于金融領域,我國金融監管內容強調合規性,即金融業務經營是否符合政策和法律法規,但在金融市場逐漸開放,金融業務日趨復雜,競爭日趨激烈的形勢下,勢必向風險性監管轉變,即觀察金融機構的經營管理及其業務活動是否在合理風險范圍之內,確認經營風險所在,并督促金融機構控制風險。風險性監管為金融機構實施規避型創新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也將與之相適應的不斷完善。
字串6
(三)法律規避型創新提升銀行業的經營競爭力。在我國舊體制下銀行業務可以用存、貸、轉予以簡單概括,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深入,證券、保險、信托等逐步構成對銀行業的全面挑戰,這也與世界金融業發展趨勢是相符的,商業銀行只有不斷發展新業務,開辟新增長點,才能立于不敗,其過程中也必然伴隨突破舊框架束縛的法律規避性創新,我國《商業銀行法》第四條規定商業銀行自主經營、自擔風險、自負盈虧和自我約束,商業銀行應以市場為中心,在經濟利益內在驅動下,在競爭中求得生存發展,以法律規避型創新的方式不斷在更高層次實現盈利性、安全性、流動性的平衡。在此應強調,帳外經營,變相拆借資金等違規活動絕不是法律規避型創新,不突破法律秩序性要求是其底線,實現商業銀行在法律框架下利潤最大化追求是其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