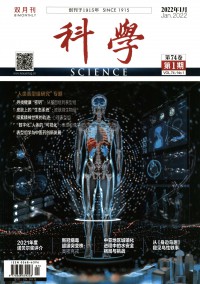科學與人性的沖突以及可能的未來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科學與人性的沖突以及可能的未來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提要:愛德華?威爾遜的《知識大融通》是一部當代科學名著。他用知識融通的眼光(其實基本上是以自然科學的眼光)來認識社會科學和藝術,能給出不少啟示。但是,科學固然可能統一知識,但不能統一人性。本文以實例說明今日科學與人性的沖突愈演愈烈,并且展望了科學與人性沖突的一些發展可能。
關鍵詞:科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藝術;人性;愛德華?威爾遜
多年以來,人們設想知識的寶庫藏于人跡罕見的深山野嶺。假如有人以勤為徑,以苦為車,來到寶庫洞口,又掌握了大門的秘鑰,此時只須大喝一聲:“阿里巴巴———”大門隨即洞開,知識便會坦然現身,任你擺布。但事實上,如今的你,如果真的進入了知識寶庫的大門,你更大的可能是看到一條和幾條走廊,走廊上密密麻麻地排列著一個個房間,且房門緊閉,但房門上有明確的學科標識,原則上每位訪客只配一張房卡。假如有人異想天開,或自命天縱英才,想在幾個房間串串門,一時間便會出現無數保安,或好言相勸,或冷嘲熱諷,目的無非是同一個,讓你不要游手好閑、輕舉妄動、自討苦吃。他們還會告訴你,你沉醉的幻想早已過時,原來亞里士多德、達?芬奇、朱熹等也許還有一絲絲可能,輪到你,那真是絕無機會。“那么,愛因斯坦呢?”假如你這樣發問,他們倒也回答順暢:“愛因斯坦的統一場論不是沒有構建成功么?”此時來談知識是統一的,真無異癡人說夢了。當然,統一知識的夢,今天我們都明確了一點,就是只有自然科學家還能做。至于別的人,哪怕想一想,都屬極端的僭妄。二十世紀不少君王有過這種企圖和操作,但最后均放棄了這種為力甚巨其效甚微或者干脆是無效的做法。科學家是在光明的前端摸索黑暗的人,他們沒有上帝指引,只有幾條簡單的科學原則可以遵循:一是要用精確的可度量的工具進行觀測和實驗,所以劉易斯?芒福德在《技術和文明》中首先強調只有時間和空間可以被度量后技術才能發展①;第二是經過觀測和實驗的結果在相同的條件下可以重復;第三是總結出更精簡、更具涵蓋性的理論和原理;第四是借此理論和原理制造出新的產品、工具等等。在當代這個世界,自然科學家已是靠譜的上帝。假如你完全不信上帝,也不相信自然科學家,當然這也沒關系,但如果這時還相信其他人,看來你只好被送進精神病院了。所以,當愛德華?威爾遜(EdwardO.Wilson)在1998年推出《知識大融通》(中譯本由中信出版集團于2016年出版,臺灣梁錦鋆譯。此前大陸尚有一個中譯本,被方舟子嚴厲批評過,此不談),盡管沒有涉及物理學和天文學遭人詬病,但大家也承認他有發言的資格。愛德華?威爾遜,1929年生,當今國際生物學界翹楚,社會生物學學科的開創者。我自己讀完此書后,覺得以前的很多模糊念頭得到了進一步的澄清,同時也產生了一些想法。作為一個文科從業人員,我的關注和胡想自有立場、重點以及必然的可被攻擊的破綻。
一、自然科學家眼中的社會科學
威爾遜先把醫學拿來與社會科學作對比,指出最大的兩點區別:一是社會科學會劃分為許多獨立的團體,盡管“強調專業上的用詞必須準確,但是不同的專業很少采用相同的術語。很多社會科學家甚至對這當中產生的混亂氣氛感到欣喜,錯以為是一種創作的熱情。”②是的,當一本綜合性的社科人文雜志很多篇論文談到某個字面一樣的名詞時,這個名詞很可能代表了不同的意思和概念。當然我們也可以指責威爾遜拿醫學一門科學與社會科學群體作比較不公平,但我們也應該知道,物理學、生物學、化學等說到的分子、原子,畢竟還是同一個東西。二是社會科學今天“仍然脫離不了開山鼻祖的掌握———若就科學領域的原理來看,這是一個壞征兆,因為人們遺忘創始者的速度通常是衡量科學進展速度的標準。”③如此說來,當社科論文的作者津津有味地從柏拉圖和孔子等等開始講述問題的由來時,不是顯露了他們的淵博而只是顯示了該學科的笨拙和缺乏進展。“社會科學當中,經濟學在形式和自信上最類似自然科學。”④但是大約在十幾年前,也就是“經濟學帝國主義”在我們這里最甚囂塵上之際,我對這門學科逐漸產生了一些外行的疑慮。這些疑慮集中于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在經濟學家看來,任何人針對任何問題都可以做出理性的選擇。而來自自己并不多樣的生活經驗和也不算淵博的閱讀體驗都在執拗地提醒我不要相信這個假設。古今中外的文學更是堅定地提醒我:如果任何人都能理性選擇,人世間的沖突至少可以減少三分之一,文學就更沒有理由存在了。
可文學頑強地存在!我的意思是:人不是電腦。盡管屁股從根本上指揮著腦袋,你立場的不同決定著觀點的不同,即使這些觀點相互沖突,但是這樣的不同仍然屬于“理性人”范圍。我說的意思是人腦會犯錯,而且犯錯的概率并不太小,情緒的沖動所帶來的決策失誤無論如何不是理性選擇。威爾遜更加明確地告訴我們:“人類大腦并不是運算快速的計算器,但大多數決定必須在復雜的情節和不完全的信息下快速完成。因此理性選擇理論涉及了一個重要問題:多少信息才算足夠?提供分界點的簡單策略,叫做‘足夠滿意’,足夠滿意是指,由短期中可以想到并可獲得的機遇中,挑選出最令人滿意的選擇,而不是事先想出最佳的選擇,然后再于其中尋找,直到找到為止。一個到了婚齡的男性,比較可能在已認識的未婚女性當中,因為‘足夠滿意’而向其中最有吸引力的女性求婚,而不會為了一位想象中的理想伴侶而長期尋覓。”⑤確實,我們在生活中做的決策基本是在有限的信息和時間范圍中做的,決不同于我們對論文寫作的要求必須通覽一直以來的學術成果。此與理性的標準相去甚遠。經濟學以及其他社會科學存在的另一重大問題是變量。在自然科學領域,實驗必須嚴格控制其它變量不變,然后,變動需要變化的變量,觀測該變化引起的后果,期間要保證沒有其它無關的因素介入。但是經濟學以及其他社會科學又如何能夠保證其觀測的變化不是來自其它未曾措意的因素?從根本上來說,這幾乎沒有可能。威爾遜說:經濟模型“不成功的另一個原因是封閉性,也就是說沒有考慮人類行為的復雜程度和環境附加的限制。”⑥在此情形下,我們為什么還要有經濟學?威爾遜一言中的:“經濟學家所享有的尊榮,多半并不來自他們的成功記錄,而是因為商業界和政府別無其他選擇。”⑦是的,我們仍要堅持科學的大方向,盡管社會科學比起真正的科學來距離十分遙遠,畢竟它走上了正確的道路。如果以社會科學的不成熟為理由拒絕它,正像一個極老的比喻即從浴盆里倒出未成熟的孩子。正因為如此,經濟學家還得坐在讓人尊敬的講臺上,雜志還得接連發表一篇篇經濟學的論文。我們所能的,只是希望他們的態度謙遜一些,小心一些。社會科學步向真正科學的道路還十分漫長,比人類步向火星的道路只長不短!
二、科學怎樣看待藝術什么是藝術?
從科學家的角度看,藝術“是以情緒和感覺表達人類處境,召喚出所有的感官知覺,并激發出秩序和混亂。”⑧附帶介紹一下他對人文學科的看法:“人文學科的學者也從事發現工作,但是他們當中最有原創性、最有價值的研究,一般都是針對既存知識的詮釋和解說。”⑨確實,人文學科重在詮釋和解說,而藝術主要使用的工具則是感覺和情緒。如果說如今的社會科學在自然科學家的眼里并無多少科學性,那么藝術是不是更顯荒唐、更為隨意而根本無需提起?當然,在傲慢的大英帝國,則是人文與藝術看不上科學,遂有C?P?斯諾試圖反駁古來的習見。但“兩種文化”的劃分,亦足見出科學與藝術的涇渭分明和勢不兩立。只是到了今天,自然科學家對藝術反多了一份理解。自然科學家對待自然,手上永遠拿著一把銳利的解剖刀,看見無論什么東西,必定上去先切一刀,看看里邊究竟有什么。分子、原子、電子、量子、細胞、DNA……等等,都是他們的解剖結果。從基本元素開始觀察,猜測答案,尋找模型,設計實驗,才能提出有益的理論。而這把刀,正規的名詞是化約主義。要承認,自然科學至今的輝煌成就,絕大多數是化約主義的功勞。如有人決心采取完全相反的另種方法,即綜合主義,任何事情先從整體開始觀察,這種嘗試在思想史上并不罕見,有時也頗見功效,但在自然科學領域則很難取得成功,關鍵在于牽涉到太多的變量而且無法控制。
所以,綜合主義的思路不可謂完全不合理,但應用在自然科學研究上鮮有可觀的戰績。但是今天的自然科學家開始發現藝術在科學上的價值。威爾遜以蒙德里安(1872—1944)在1905至1908年所畫《德伊芬德雷赫特的威爾特夫瑞登農場》系列為例。“在一棟幽暗的房屋面前,描繪了一排高而纖細的樹木。樹桿之間的距離直覺上似乎是正確的,樹冠上重復出現的鑲邊圖案,很接近于現代腦電圖監測表明的最能刺激大腦的圖形。畫中的空間和水面的安排,也和最近心理學研究揭示天生最具吸引力的安排相符合。蒙德里安對這些神經生物方面的關聯性一無所知(就算被告知,也可能不在乎),卻以樹列為主題,在10年中重復畫了許多畫,他感覺自己是朝著新的表達方式前進。”“蒙德里安最后獲得了純粹抽象的設計,他為此慶賀道:‘不再與人類相關,不再具有任何特殊性。’”⑩從自然科學家的眼中看見的偉大藝術作品,奇怪地卻又是顯然地集中于某些畫面和主題,借隱喻的方式傳達出自然的規律與人類的處境,對自然科學竟不失為一種有力的啟發。當然,他們也清楚地知道:藝術的中心是人性,而科學的中心是規律,兩者確乎不能等量齊觀。但是藝術又如何在直覺中直面人性,仍需科學尤其是大腦科學、心理學和進化生物學的進展來解決。在藝術中,“如果你必須發問,你就永遠不會知道(這是阿姆斯特朗談爵士樂時說的)。”輥輯訛而科學,則任何事必須發問,必須探索。直覺可以拿來指導實驗,但在被實驗證明前,它們仍然什么都不是。但無論如何,原先科學與藝術間高高聳立的藩籬,在自然科學家的眼里,已經開始消解。
三、科學與人性的沖突
說到這里,且莫以為科學真的可以一統天下。我同意科學能統一知識,但是,目前科學竟與人性發生劇烈沖突,作為人,你站在哪一邊?提出這個問題,起先倒不是由于本書,而完全由身邊的經驗引起:時至今日,“剩女”已經泛濫成災,本人雖忝為“剩男”家長,毋需為此操心,但此事已成社會問題則毋庸置疑。《錢江晚報》最近報導“10天8場相親,下沙女大學生逃回校園”,輥輰訛父母們焦慮爆棚。而另一邊,無數心靈雞湯在呼喚女性嫁人不能湊合,必須堅持標準。雙方各有各的“三觀”,也不能隨意判別誰對誰錯,但是我們可以從較客觀的角度即科學的角度來重新認識一下女性。女性到了18歲左右,有兩個共同的特點。一是美貌,幾乎可以說是達到一生美貌的高峰。古諺說:“十八無丑女”,就是最精當的概括。至于后來的以氣質勝、以打扮勝等等,都已是文化的產物,也都是遁詞,其實這些都不敵天生麗質,因為天生麗質也可以加上氣質和打扮。二是到此時,少女容易墜入愛情之海。有研究表明,“愛情與青春期同時到來”。輥輱訛歌德說:哪個少女不懷春?《詩經?野有死麕》云:“有女懷春,吉士誘之”。這完全是由于人在進化過程中設定的遺傳密碼,它讓女性在青春期綻放出最美貌的花朵,吸引異性前來求愛;同時又設定女性在此時雌性激素分泌加劇,荷爾蒙含量升高,極易墜入愛情之夢,愿意投入異性的懷抱,完成傳宗接代的自然使命。這個進化策略在幾萬年來早已成型,且屢試不爽。但是它與科學高度發展引起巨大改變的教育制度,發生了根本性的沖突。如今中國的孩兒七歲上學,義務教育九年,高中三年,在16至19歲間。
此時她們還穿著單調的校服,大多還戴個眼鏡,上課紀律嚴明,課外作業壓力沉重,天生的美貌就這樣淹沒在校服和題海之中,很少表達愛戀的空間。而等到大學或碩士、或博士畢業,美貌已逝,漸趨理性,難以墜入少年時的幻夢,看待異性漸為冷靜,更多雜以精確的度量與測算,所以婚姻難成,剩女增多。這是一個必然產生的現象。光靠調整個人的觀點、看法,起不到根本性的作用。但如果人類的教育制度不是這么設計,這個問題就根本不會存在。在中國,這樣的教育制度其實才短短幾十年。(我的姐姐出生于1951年,讀完了小學后就沒有條件繼續上學)但是這短短的幾十年就完全顛覆了幾萬年來的生活習慣,讓古已有之的人類的進化策略完全失效,引發了全新的社會問題。像這樣的問題,確實是由于科學的發展引起,由科學的發展引起制度的改變,由制度的改變引發與人性的沖突。我們都知道,與農業社會相伴的饑荒,是無法解決的災難。原先是一家人的辛勤勞作夠上溫飽已經是謝天謝地,只有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他們才略有積蓄,生兒育女,建造新居。他們沒有多少剩余勞動力,當然也用不著去學習非實用性的知識。隨著工業革命和綠色革命的推行,糧食產量大幅增加,災荒已經成為往事,而另一方面,舊日方式的勞作的不合算迫使農民從農舍中走出,投身到陌生的城市化世界,促進更多的“勞心者”工作崗位的設立;“勞心者”崗位的增多,也逼迫教育界設計更為費時復雜的教育制度,容納從古老社會中解放出來的巨大人群,以至于設計安排哪怕是冗余的教育空間。復雜化了的教育則需要時間填補,成年化的教育就這樣取代了熾烈的愛情之夢。其實類似的問題在今天不勝枚舉,比如老年病。在老齡化的現代社會,對抗老年病已經成為社會的沉重負擔。有學人設想要在人體中找到長壽基因來一舉解決老年病問題。
但可以肯定的說,人類五萬年來在青霉素發明以前,也就是說在任何遍布的小小細菌可以經常置人于死地之前,長壽不是人的生活通則。饑餓,戰爭,瘟疫、傳染病……皆可隨時奪去人類的生命,那時候人的平均壽命可能只有三四十歲,人類可能完全就不需要什么“長壽基因”,同時他倒是真需要繁衍的遺傳密碼,促使少女迅速成婚,生兒育女,傳宗接代。我回憶少年時的鄉村生活,記得根本沒有老人去新設立的醫院看病,哪怕是每個月幾元的醫藥費也非他們所能承受,通常的叮囑是想吃點什么就去吃點什么,余下的就是等死。當下人類科學發達,對抗疾病的手段多樣,“人生七十古來稀”的通則被完全摒棄,根據2015年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世界衛生統計報告》,全球人口平均壽命的男性71歲,女性73歲。如此,進入老年后,人的自毀的遺傳密碼也開始發動,老年病因此而來。對抗老年病,因此成為一項事倍功半的悲壯事業。歸根結底,也是科學發達后引發的新的矛盾沖突。如果說上面的例子都屬生物學范圍,在社會學意義上,科學與人性的沖突也是彰明較著。在我們現在最為熟悉的微信朋友圈,就可以看到明顯的情形。朋友圈本來是一群朋友的集合,原先或有在一起學習的經歷,或有工作聯系,總的來說志趣較為相投。他們說的話,本來應該是“不可使不知吾者知,知吾者亦不可使不知”,但是現在為了一個觀點和看法而反目相向、化友為敵的,也是屢見不鮮。為什么?歸根結底是無法讓一個現代化手段維系的群體對同一件事的看法相同。同一件事,是事實,更準確的說是事情的真相,對此事的看法,是觀點,是看法。我們原先的想法,只是要將事實原原本本的道出,將前因后果講清楚,所謂擺事實講道理,其方式是心平靜氣、從容不迫,其結論也將自然導出,確定無疑。換句話說,我們以為這是一道科學題目,只要等式的前半部按照實在的事實,用以科學的邏輯與方法,等式的后半不言而喻,也必定是唯一的答案。殊不知今天朋友圈激烈的交戰已粉碎了這個科學的幻夢。
其實前半部是科學,但是后半部是人性,這兩者決計不能以等號相連。科學跟人性在社會領域就是這樣無情地展開沖突。在這里要特別指出的,是關于每一件引起關注的公眾事件,大多有行蹤詭秘的人士出來講述事情的真相,拋出一連串復雜、細膩的細節,借以引導公眾輿論和情感走向他意欲導引的方向。這些文章,可以稱為偽文,它們或第一眼就能識別清楚,或經過細致的考證和辯駁才能知曉。但是,我仍愿將偽文的作者看成科學主義者,因為他們還是認為事實決定看法,所以作偽必須在事實上下功夫。殊不知在社會領域的多數場合下,科學其實遠遠不敵人性,事實根本難以奈何觀點。即使事實是同一個,觀點仍可有百千種。
到此可以為何謂人性作一個粗略的界定了。古往今來,多少哲人、政治家、企業家以及平民百姓對此深有體察,但是找一個共同認可的定義難上加難。(其實這就是科學與人性的沖突了)我個人比較傾向于生物學家們的看法,即把人性視為人在幾萬年至幾百萬年以來的進化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一些特質、傾向等等。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自我保存以及繁衍后代無疑是人的第一本能。試想在人類演化的漫長過程中,人類面對著環境的逼迫,面臨著許多動物的競爭,自我保護以及為了生存利用環境、戰勝他類甚至同類、生殖和養育后代,應該是人類的第一本性。至于這些本性有多少通過遺傳密碼植根于人類的身體深處,有多少需從后天習得,又是一個犯難的問題。比如現在科學家們已經認為人類自幼年起可以開啟語言學習的程序,任何一個正常的嬰兒,不管生活在何種地帶、何種民族,在正常的環境下,一定能很快的學會自己民族的語言。也就是說,語言本能已經成為人性中的本能。與之相比,科學呢?我同意科學是一種偶然的說法。科學不是人性的本能,它應該是人類大腦一種很次要的功能。科學是培根、笛卡爾、伽利略、牛頓以來的一種新玩意兒,論歷史只不過幾百年,與漫長的人類演化史相比不過是短暫的一瞬,不可能與人類與生俱來。它對人對物的要求也很苛刻,比如測量儀器的發明、加工物質的純凈、研究中的各種變量的控制、反復的實驗,它需要寬余的時間、嚴格而不帶意氣的辯駁、證明與證偽,需要冷靜的理性。
而人類的求生本能,大多是靠直覺的瞬間反應,靠的是情緒的調動、即時的反應和瞬間的注意力集中。我們豎起手指到嘴邊發出“噓———”讓人家安靜,這是不是來源于遠古蛇類動物的爬行聲音引起的人類的恐懼?我們看見突然的一個黑影閃過會突然閃避,這是不是遠古人類對猛獸突襲的本能反應,從而馬上浮現情況緊急的情緒反應而非悠閑討論逃跑路線?這些求生的本能幫助人類在幾百萬年的進化中得以幸存并勝出,且已深深植根于人性深處。但現代社會基本用不著這種本能,科學更是根本用不著這樣的玩意兒。從效能的角度看,人類在科學研究的過程中其實是受了本能的拖累。如果一切都順著邏輯走,科學發現的腳步或許根本不會這樣遲緩。科學不是人的直覺、本能所能達到的。巴什拉說:“面對現實,人們自以為明了的東西與人們理應了解的東西發生沖撞。”這里自以為明了的,就是人類本能能知道的;理應了解的,說的就是科學。這兩個東西不是一回事,而常常是矛盾的。所以巴什拉說:“從它需要完滿和從它的原則出發,科學絕對與見解對立。”問題是,其正當性完全無需置疑的迅猛發展的科學技術,確造成了當前的社會之最深刻、最尖銳、而且看來短期內根本無法解決的矛盾。針對此點,歷史學大師斯塔夫里阿諾斯早有洞見。他說:“至今世界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是連續不斷的技術革命的歷史。”“多少世紀以來的根本問題是,技術革命一直受人歡迎,因為它促使了生產率和生活水平的進一步提高。但是,世界上所有的技術革命,都導致社會分裂,這種分裂要求在制度、思維方式以及人際關系等方面實行變革。然而,這種社會變革總是遭到人們的拼命抵制,其激烈程度一如人們之熱烈歡迎技術變革。正是由于技術變革和社會變革之間所產生時間滯差,才造成了幾千年以來世界歷史上眾多的苦難和暴行。”他還說:為何社會變革較之技術變革困難?因為“現存的體制和習慣總是受到歷史傳統、啟蒙教育以及社會秩序的維護。因為,對社會現狀提出挑戰總要遇到排斥、恐嚇甚至迫害,很少有人能夠或者愿意忍受這些。
另外還存在既得利益集團的作用,這種集團顧名思義必然會因社會變革而喪失既得利益,因而通常總是反對變革。他們的反對通常總能成功,這不僅是因為他們具有雄厚的財力和良好的組織,而且因為他們利用人們對于社會革新的普遍厭惡態度。”對社會斷裂由科技變革造成,這個深邃的看法我舉雙手贊成。對于社會變革為何較之技術變革困難,我尚有一些想法可以補充。斯塔夫里阿諾斯對“既得利益集團”有所涉及,但是只講了他們的作用,未指證他們的構成。而人們通常以為代表新科技力量的,理所應當地應該是主張社會變革的主導力量。在這里我要著重指出,代表新科技力量的人們常常會變成阻礙社會變革的既得利益集團。其間的邏輯關系十分清楚:從起始看,新科技的代表者以科技改變了現狀,包括一部分陳舊的社會關系。但必須看到,這些新科技力量的攜有者,如果他們取得了成功,則必定是在舊的社會關系中取得了成功。他們做到的變革僅僅是在科技領域及極小部分的社會領域。而且在取得成功后,他們極愿意繼續前進,升級技術,依憑目前的社會現狀取得更大的成功,至于社會由此引起的劇烈變革,如舊有工作崗位的喪失、薪酬的改變、工作的概念以及相關理念的變化,都不在新科技人物的考慮范圍。他們以新科技觸發了一連串的社會問題,但這些問題的解決又被他們全盤推給了社會,所以造成了社會的巨大矛盾。從歷史上看,社會變革的任務確非科技界所能勝任,而且由此引起的巨大震蕩常常由全社會來痛苦地承受。我們只能祈愿在這場巨大的變革中少一些鮮血與苦難,多一些理解與和平。目前大眾已經對此巨變開始在全球有所反應,英國脫歐和美國特朗普上位均屬這一潮流。問題只在于:大眾的應對永遠只能從歷史中尋找借鑒,而面向過去永遠不能解決問題,最關鍵的還是如何開拓未來。
“面對重大轉折的新時代,人類的思想領袖尚未出現,而人類社會的變遷已形成對思想理論的巨大需求。”世界固然已有千百思想家如群星璀燦,但應對當下的問題及開創未來,則唯有靠我們自己。再回頭來看,未來究竟會怎樣?按著目前的發展趨勢,可以設想幾種可能。此處我擬從科學或人性各占上風兩種角度探討一下。如果科學在與人性的沖突中取得完勝,那么,科學將主宰科學界與社會,科技會更加迅猛地發展,人類將制造出有智能的機器,而且,按照歐文?約翰?古德的說法:“一旦機器設計成為一項智能活動,超智能機器就能設計出更好的機器,……人類的智能將被遠遠拋在后面。第一臺超能機器將是人類最后一個發明。”世界從此不再需要人類并不高明的智慧和無數非理性的想法,一切按照完美的邏輯進行,由永遠得勝的算法指引。對人類而言,比較樂觀的可能是人可以坐觀其成,享受科技無限進步的成果,聽從智能機器作出的各種安排。這樣的社會近似于人類在各個歷史階段夢想的仙境、天堂、極樂世界,生產由非人類的機器提供,這樣也就自然消滅了奴隸制、農奴制和資本主義等各種不平等的制度,人們的各種活動構成為非必要的活動,為幸福而設計而非為饑寒所驅動,進入一個自由幸福的境界。但另一種可能不得不想到,就是機器覺得人類已無任何用處,在效能法則的驅動下,人類被當作贅余而被移除,地球的進化由機器取代,科技的發展更為迅疾,在種類的競爭中無情地勝出,并像人類在進化過程中滅絕多種物種一般將人類滅絕。如果人性在與科學的沖突中仍占主導地位(完勝是絕對不可能的),比較理想的一種出路就是人性逐漸吸納科學因素,并將它作為人性的主導方面,自然而然地接受科學技術及科學原則,并將科學的一些部分植入自己的遺傳密碼。同時寄希望于機器永遠不會產生自我意識,積極順從科技發展,及時調整各種社會關系,將人類的存亡置于第一原則,長久保持人對科學的掌握。不太理想(權且對人類來言)的另一種可能,則是從自我保存的本能出發,將自我保存的本能限定于自身、自身所屬的小集團抑或階級、民族等等,任憑本能來支配未來社會結構的變化,如此,自然而然會引起的戰爭將以各種超級武器的絕大威力將地球摧毀殆盡。
說到這里,不能不對人類還抱一分希望:依照百年來的發展軌跡,第三次世界大戰應該早已打完,因為僅僅從20世紀的10年代到40年代,就打完了兩次世界大戰。真的是因為核武器的發明,促使最高統治者為了保持自身的生命等目的而克制了好幾次將人類全部毀滅的念頭。但是我們也不能由此而對人類的愚蠢視而不見。視自我的生存發展為最高目的的習慣仍然難以徹底改變,隨著科技的發展以及擴散,任一個不負責任的統治者(可能會發展到任一個不負責任的個人)都有可能發動一場意料之外的大變亂,比如說將原子彈拿來當鞭炮使用。自我保護雖是人類的本能,但在現代化到如此程度的當下,如自我利益無限膨脹,必將導致根本性的災難甚至滅絕。今天的我們,住在遍布地雷的這樣一個球狀物上,不能不膽戰心驚、如履薄冰。
注釋:
①參見劉易斯?芒福德《技術與文明》,陳允明等譯,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9年版,第13~22頁。
②愛德華?威爾遜:《知識大融通》,梁錦鋆譯,牟中原、傅佩榮校,中信出版集團,2016年,第257頁。
③《知識大融通》,第257頁。
④⑤⑥⑦⑧⑨⑩《知識大融通》,第273、288、276、277、299、83、310、311頁。
12、《錢江晚報》,2017年2月6日。
13、參見金伯莉?J?達夫《社會心理學》,宋文、李穎姍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42頁。
14、見www.ishuo.cn/show/103813.html。
15、參見白居易《和夢游春詩一百韻序》,見朱金城《白居易集校箋》(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63頁。
16、加斯東?巴什拉《科學精神的形成》,錢培鑫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頁。
17、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吳象嬰、梁赤民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904~905頁。
18、《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905頁。
19、《巨變來臨》,《文化縱橫》2017年2月號編輯手記。
20、轉引自RayKurzweil《奇點來臨》,李慶誠、董振華、田源譯,機械工業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頁。
作者:盧敦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