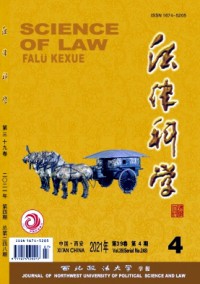法律原則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法律原則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法律原則范文第1篇
作者馬馳,天津商業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天津300134)
自羅納德?德沃金以法律原則為肇端向哈特式的法律實證主義發動攻擊以來,由這一論題引發的討論幾乎構成了半個世紀以來法律理論或法理學研究領域最為重要的內容之一。圍繞著法律原則,已有的研究實際上可以劃分為兩類,相互聯系卻又具備各自的獨立性。第一類研究主要涉及法律的概念,即區別法律規則的法律原則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則對回答“法律是什么”這一法律概念問題產生何種影響,尤其是,現有的法律實證主義能不能在堅持自己基本立場的情況下,回應與法律原則密切關聯的各種責難。第二類研究是有關法律原則的方法論,這類研究基本上已經肯認了法律原則的存在,重點在于,區別了法律原則和法律規則之后,無論它們的區別是何種意義上的,原則究竟在個案判決中充當了何種作用,對于法官來說,它的適用有哪些特殊的要求和特征。不難發現,無論上述哪類研究,在邏輯上必然要以“法律原則是什么”這一本體論問題的妥當回答為前提。法律原則的本體論問題是本文討論的基本范圍。我將以法律原則已經存在為前提,檢討其存在的條件是什么,即其效力標準(criterion of validity)是什么。我力圖證明,原則與規則無論在適用方法論上存在多大的差異,也不能簡單地說,相對于法律規則系譜的或形式的效力規則,法律原則的效力準則就是基于內容的;此種二元劃分簡化甚至遮蔽了法律原則效力標準的復雜性,造成了規則與原則之間某些不必要的對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法律規則與法律原則在本體論上的差異不應該被夸大。
一、效力標準的含義
在法律理論的研究中,如同很多名詞術語一樣,效力一詞含義并不總是十分清楚。在我看來,人們至少在如下幾個方面使用法律效力這一術語,并以此產生了多種相互區別卻又相互聯系的效力標準的含義:
其一,效力是法律的約束力(binding force)。漢斯?凱爾森曾提到,效力是法律規范針對其所調整的對象所具有的約束力,一個有約束力的法律也就是一個有效力的規范。①我國現行的某些法理學教科書也采取了此種用法②,“法的效力是對其所指向的人們的強制力或約束力,是法不可缺少的要素。”在此意義上,效力標準實際上是法律之所以有約束力的標準或原因。法律效力的此種定義實際上與法律的規范性或權威性如出一轍;尤其是,由于法律的約束力必定是針對人們行動的約束力,這種約束力在實踐中表現為人們的行動理由,故當引入行動理由這一重要概念之后,對法律約束力問題的研究已經被有關法律權威性討論所取代。③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沒有必要再使用效力一詞來與法律的權威性相以混淆。
其二,在語義學的意義上理解效力④,將效力視為法律規范為真的標志,進而將效力標準視為法律規范的真值(truth value)條件。法律規范要以命題的方式加以表達,作為命題,它或許可真可假,這樣一來,一個真的法律命題就是有效的法律,相反則是無效的。命題的真假通常受制于某種條件,這種條件便是其真值條件。例如,“火星上存在生命”這一命題的真值條件是,僅當火星上存在生命,該命題為真。然而,對于一個法律命題來說,稱其為真是什么意思呢?這里的問題在于,我們或許可以借助所謂真理符合論來判斷一個事實命題的真假,但法律命題作為規范命題或價值命題的真值條件卻似乎難有定論,甚至無所謂真假。例如,邏輯實證主義者就主張,價值命題無法證實,沒有真假可言,當然也就沒有真值條件。⑤實際上,命題的真值概念是用來處理命題演算的工具⑥,將之引入法律理論有關效力標準的討論,對問題的化解并無直接的助益,反而徒增了不必要的爭議。
其三,效力是法律規范存在的標志,因此效力標準就是法律規范的存在條件或前提。在這個意義上,法律的效力是法律的存在方式,因為沒有效力,法律就不存在了,無效的法律等于沒有法律⑦;當我們確定某個法律是有效力的時候,我們的意思首先是的確存在這樣一種法律。如果法律效力是法律存在的標志,那么效力標準的含義則在于,由于我們不總是任意地判斷某一規范是不是法律規范,而是會使用一個或多個標準來對相關規范進行鑒別,這里的標準決定了相關規范是否是法律,這便是法律的效力標準。H.L.A哈特創造性地使用了承認規則(the rule of recognition)這一術語來指稱法律的效力標準,在一個社會中,總會存在這樣的標準,來決定什么樣的規范能夠算在這個社會的法律,即便這一標準的內容在不同社會中會有所差異,不同學者對這一標準性質的認定也有所差異。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承認規則實際上是法律規范的存在條件或前提。這便是本文所采納的效力與效力標準的概念。當然,這里提到了承認規則,并不暗示效力標準規則一定是單一的一般性規則。實際上,本文的目標恰是要表明,法律原則的效力標準具有復雜性。浙江社會科學2012年第3期馬馳:法律原則的效力標準――基于系譜抑或內容?
效力標準的這一含義需要與認知標準加以區分。在將承認規則視為效力標準的情況下,承認規則可能被當作法律的認知(epistemic)⑧標準或手段,是獲得法律規范這一思維過程的工具。至少在《法律的概念》正文中⑨,哈特將承認規則視為一個單一的一般性規則,例如英國的承認規則是,女王議會制定的就是英國的法律。毫無疑問的是,如果一個對英國法律一無所知的人或英國法律的初學者想要知道英國的法律究竟是什么,那么“女王議會制定的就是英國的法律”的確是他們認識英國法律的快捷方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承認規則當然具有認識功能。然而即便如此,也必須區分作為效力標準的承認規則與作為認知標準的承認規則。實際上,法律的效力標準是判斷法律本身的合法性(legality)準則,是法律存在的前提與條件,它所具有的認知功能是偶然的。對此,朱爾斯?科爾曼曾舉過一個極為有趣的例證⑩:想象這樣一個簡單的法律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法律的效力規則是,“凡德沃金說的即是法律。”這無疑是該社會的承認規則,但對于識別或認知法律來說,最可靠的規則卻是,“聽拉茲的”,他知道這個社會的法律是什么。在這種情況下,效力標準與認知標準是可分離的。不僅如此,當法官進行個案裁判時,判斷何為法律,與法律如何適用至個案事實,也可能是兩個并不相同的活動。在我看來,區分認知標準和效力標準意義重大,很多有關法律原則效力標準的爭議其實是對法律原則認知標準的爭議,申言之,是將法律原則如何有效這一問題,與如何認知法律原則這一問題加以混淆。也即是將法律原則在適用方法上的爭議,看作法律原則效力標準的本體論爭議。對此,下文還會有進一步的討論。
二、德沃金論法律原則及其效力標準
德沃金對法律原則的界定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內主導著人們對法律原則的認識。在里格斯訴帕爾默案中,德沃金認定法官最終使用了“任何人不得從自己的錯誤行為中獲益”這一原則而不是法律規則,得出了正確的判決結果。在德沃金看來,法律并不僅僅由規則構成,它還包括原則。而原則與規則之間,存在“邏輯上的差異”,這種差異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規則是以全有或全無的方式來適用的,如果規則規定了既定的事實,那么當案件出現此種事實時,它就必須被適用;而在沒有這種事實出現的情況下,規則對判決不起任何作用。其次,原則具有分量(weight)和重要性的維度,而規則不具有這一維度。在特定案件中,可能適用的法律原則或許存在多個,對于哪個原則應該被使用也常常是有爭議的,法官需要對各個原則就個案而言進行其分量的平衡或衡量,才可能得出其正確的判決。原則和規則是否具有分量和重要性維度的這一區別還引發了它們之間的第三種差異,即在一個法律體系中,當兩項法律規則相互沖突時,除非存在調整這種沖突的規則,否則其中一條必定無效――法律的規則體系不能容忍規則之間的沖突。但若沖突發生在兩項原則之間,則不會導致原則的無效,無非是,法官此時只需斷定相互沖突的原則中的哪一項要更為重要一些。
德沃金之所以要在法律體系中區分出不同于法律規則的法律原則,是為了攻擊以哈特理論為代表的法律實證主義。其要義在于,哈特的法律實證主義使得法律難以容留法律原則的存在,而法律原則的存在又是難以否認的,因此哈特的理論必須被拋棄。德沃金認為,按照哈特的看法,法律規則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它們由某個權威機構頒布,例如由立法機構制定,或是由法官創制的;就此而論,作為法律規則的效力標準,承認規則是一個系譜(pedigree)的檢驗標準,它只能按照規則的形式或來源來確定或識別法律。如果承認規則是一個系譜規則,那么法律原則就無法通過這種規則進入到法律中。原因是,法律原則并不來源于立法機構或法院的特定決議,而在于法律專業領域與公眾當中長時間所形成的妥當感(sense of appropriateness),只有在此種妥當感的支持之下,法律原則才可能作為法律而持續下去。在此種論證之下,德沃金試圖將法律原則的效力與道德論證或原則的內容聯系起來――法律原則之所以能夠作為法律而存在,不是因為它的譜系或來源,而是因為它的內容是公平正義的,符合某種道德層面的要求或標準。
借助此種論證,德沃金顯然向我們提供了法律原則的效力標準。這一標準首先不同于法律規則的效力標準,法律規則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它的系譜或來源,即它是由權威機構頒布的。但法律原則的效力標準卻不在于此,法官在認定諸如“任何人不得從自己的錯誤行為中獲益”這一原則是法律時,并不會去考慮這一原則系譜或來源,他并不關心究竟是誰或制定了這一原則,他的問題在于,這一原則在特定的案件中是否公平正義,是否能夠被某個道德準則所容納,是否被法律專業人士和公眾的妥當感所支持,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法官就可以認定該原則屬于法律。因此,可以在這個意義上主張說,法律原則的效力標準是基于內容的,或者說是基于道德論證的。
仔細考察德沃金法律原則的概念,不難認定,德沃金工作的重心在于司法裁判活動,他主要借助法律原則在適用的意義上與法律規則存在較大的差異,來推斷法律原則與法律規則在本體論的意義上存在“邏輯上的差異。”然而,如果僅僅依據德沃金的上述論證就得出結論說,判斷一個原則是否屬于法律原則,確定其內容是否符合特定的道德標準是唯一的方法,以至于主張法律原則唯一的效力標準就是基于內容的非系譜標準,并以此區別于法律規則系譜的效力標準,則是將法律原則的效力標準簡單化和一般化了。實際上,法律原則效力標準需要我們再做進一步的討論。
三、基于系譜的法律原則
或許是因為竭力將法律實證主義的法律效力標準歸結為系譜規則,以便展開攻擊,德沃金似乎沒有注意到,法律原則的效力標準有時也可以是系譜的。即是說,我們可以因為某個原則的系譜或來源,斷定其可以作為法律原則而存在。而這種基于系譜的法律原則當然依舊可以滿足德沃金的原則概念。對此,至少存在兩種情況。
其一,立法機構或其他權威機構的法律文件中確立了某個原則,該原則因為這種確立而具有法律效力。或者因為出現在有約束力的判例中,因而具有法律效力。我國1950年的《婚姻法》第七條規定:“夫妻為共同生活的伴侶,在家庭中地位平等。”夫妻平等原則當屬于德沃金意義上的原則而非規則,然而,中國傳統社會男尊女卑的倫理觀已經盛行了千年之久,除非能夠證明,這種觀念在1950年前后突然被社會成員集體放棄,代之以男女平等的觀念,否則就難以主張說,該原則是因為法律專業領域和民眾中長時間形成的“妥當感”,或是經由道德論證,才成為法律原則的。不僅如此,在成文法系國家,由于人們通常將立法是否有規定視為法律效力的條件或標準,便出現了這種情況:同一法律原則可能既出現在權威立法中,又獲得了某種道德論證的支持,此時,主張該法律原則是僅僅基于內容而不是因為權威立法的規定這一觀點可能難以得到捍衛。我國《民法通則》第七條規定了公序良俗原則,幾乎所有對這一原則的引證或研究都會提到《民法通則》這一權威法律文件原文;至少在我國的法律語境中,很難想象,在缺乏該權威法律文件支持情況下,人們能夠主張公序良俗是我國民法的基本原則,可見其效力標準在于該原則的譜系或來源。
其二,法律原則的效力因社會民眾或法律專業人士的共識而獲得,但這種共識與道德倫理無關。德沃金主張法律原則的效力必須因為社會民眾和法律專業人士的長期形成的妥當感才能被確認并存續,他認為此種共識一定與道德論證存在必然的關系,亦即共識形成的原因在于法律原則內容的道德性,并由此得出結論說法律原則的效力標準是基于內容的。這里的問題在于,人們當然可以基于道德的理由形成共識,并因此產生妥當感。但同樣有可能的是,這種共識有時與道德判斷沒有關聯。其實,正是考慮到這種與道德無關的共識,哈特提出了基于慣習(convention)的承認規則理論,認定法律的效力可以與法律內容的道德性無關,而只需依靠法官群體的共識。那么,如果法官或社會民眾對某一原則存有此種共識,該共識是否可以作為該原則成為法律原則而存在的充分條件呢?這在邏輯上是完全可能的。例如,在訴訟程序中,法官的活動必定要受到法律約束,英美法中的法官在法庭上常常沉默不語,只是居中主持雙方律師的法庭辯論或交叉詢問;而在大陸法系中,法官要活躍得多,會通過言語等各種方式引導當事人和律師,控制法庭。如果法官在法庭上的活動不符合各自的原則,則被認為是怪異或不妥當的,然而,這種制約法官活動的法律原則的效力標準在于特定社會中法律群體的共識或慣習,對此并無明顯的道德依據,也無需經過道德論證;否則,就難以解釋為何人們通常不在這一問題上主張英美法系的法官要比大陸法系的法官更為高明或拙劣。
四、基于道德論證的法律原則
前文已經說明,某些法律原則的效力標準與規則類似,都是基于系譜或來源的;這并不會否認的確有些法律原則難以按照系譜或來源來決定其效力。對于這類法律原則,德沃金和柔性實證主義的共識是,它們是因為其道德性才構成法律原則的。但這種道德性究竟意味著什么呢?對此,我們仍然做更為細致的區分。
首先需要馬上澄清的是,道德性至多是此類法律原則效力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這是因為,如果所有道德上正確的原則都是法律,那么所有的道德原則同時也是法律原則,這種將道德與法律完全劃等號的看法自然是謬見。對此,德沃金認識到,如同法律規則一樣,法律原則必定要獲得某種制度上的支持,法律原則所獲得的制度支持越多,它的分量就越重。然而德沃金馬上指出,這種制度支持不應也無法等同于哈特所說的承認規則,原因依然在于,原則的確定需要原則在一系列變化和發展中的相互交錯的標準,這些標準難以被歸納為一條簡單而絕對的單一指示或承認規則。無論德沃金對承認規則的上述限制是否成立,都不會影響到這一結論:在單純的道德正確性之外,法律原則的效力標準包含了法律制度本身提供的標準。在許多疑難案件中,由于事實與規范不對稱,案件所涉的法律原則看起來好像只是因為其道德性并借由法官的法律推理而出現的,其中并不涉及制度支持。以帕爾默案為例,從表面上看,適用“任何人不得從自己的錯誤行為中獲益”這一原則而剝奪帕爾默的繼承權好像更加符合某種道德觀,于是該原則便是一條法律原則。但這至多表明,由于該案在事實上的特殊性,該原則因此具有道德性,卻不能說明該原則僅僅因為此種道德性就能夠成為法律規則。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法官所做的判決就完全是個道德裁定,他根本無需用法律原則這一說法掩蓋自己的道德推理。在這個意義上,法官在帕爾默中的法律推理并不是一個簡單的道德抉擇,而是對已經存在法律原則進行適用和取舍的過程。
當然,在德沃金對法律原則的認識框架中,畢竟要容納道德上的正確性作為原則的效力條件;換句話說,至少存在一些原則,對于這些原則來說,其道德性是其作為法律原則的必要條件。這樣一來,道德論證實際上起到了支持法律原則效力的作用,是其效力標準的一部分。問題在于,此種道德論證是在何種意義上進行的呢?這里爭議在于,法律原則究竟是在個案事實出現之前就已經存在了,還是說它僅僅是在個案中因為特定的案件事實而獲得了道德論證的支持。按照德沃金的看法,這種道德論證似乎是發生在個案裁判的法律推理過程中。這是說,就特定的個案事實而論,適用某項原則要比適用規則或另一項原則更具道德性,這種道德性因此成為該原則作為法律原則的效力條件。德沃金所反復引證的帕爾默案極易給人留下這種影響。由于原則具有分量或重要性的維度,在帕爾默案中,相對于其他可能適用的原則(例如意志自由原則),“任何人不得從自己的錯誤行為中獲益”這一原則更具分量,借助這種論證,便可以判斷該原則所具有的效力。然而,如果能聯系法律體系的觀念,德沃金的看法似乎有些太狹隘了。按照凱爾森的經典理論,法律規范的存在前提是另一個更高層級的法律規范。在這一解釋框架中,某項法律原則的效力受制于更高層次的另一法律規范。無非是,由于這里討論的法律原則必須通過特定的道德論證,于是作為效力標準的高層次法律規范內容將出現類似的表達方式:“凡符合公平正義的規范是法律”。無論如何,一旦我們承認法律原則與體現這一原則的個案判決或個別規范之間存在區別,那么就其效力而論,法律原則只要經過了高層規范所規定的道德論證,就已經存在了,無需等到該原則適用至個案之中。在這個意義上,之所以能夠認定法律原則的效力,不在于其在某個案件中符合某種道德論證,或是能夠產生公正的判決結果,而在于,一個在先的效力標準支持了這些原則。這里的關鍵仍然在于,必須區分法律原則的效力標準和適用標準或認知標準。在類似帕爾默案這樣的疑難案件中,法官的難題是如何適用法律,適用哪一法律的認識論難題,不是判斷何為有效法律的本體論難題;在這種適用或認知過程發生之前,相關的法律原則便成立了,而這些法律原則的效力標準與其是否應該被適用這一問題之間并無必然的聯系。否則,我們就難以主張一個法律體系中存在某項法律原則這樣一個一般性的判斷。
如果能夠斷定,法律原則的效力標準獨立于適用法律原則的個案裁判,以至于法律原則效力在邏輯上先于對該原則的適用,那么法律原則的效力標準將更為清晰地呈現出來。當法官判斷一項規則是否能夠作為法律規則而存在時,其標準在于看它是否符合另一個特定的規則,例如系譜的承認規則;當法官判斷一項原則是否能夠作為法律原則而存在時,其標準在于看它是否具有道德性,由于這種道德性能夠脫離一個具體的個案而存在,那么問題就變成了,如何論證一項一般性的原則具有道德性,這其實也就是要證成一項原則作為道德的效力。例如,對于“任何人不得從自己的錯誤行為中獲益”這一原則來說,效力標準實際上要求法官作出論證,證明在道德上是成立,可以作為一項道德原則而存在,進而成為法律原則。問題在于,這種道德論證在多大程度上是所謂基于原則內容的,或是實質的,并以此區別于規則的效力標準?這里其實涉及到了一個倫理學或道德推理意義的上的問題,即一個倫理命題的效力標準或條件是什么。對于這一問題,我們不必也難以展開詳考,但須重視此種情況:倫理命題有時也可以是基于系譜或來源的。就此,至少存在兩種情況。
其一,人們之所以認定某個倫理命題是正確的,理由只在于它是全人類或特定社會普遍看法或實踐。在另一個問題的討論中,哈特曾通過區別實在道德(positive morality)和批判道德(critical morality)表達了類似的意思,而德沃金區分一致性道德(concurrent morality)與慣習性道德(conventional morality)的效果也是一樣的。在這種情況下,道德本身實際上也是作為慣習而存在的。當法官判斷一項原則是否屬于法律原則時,表面看來,其效力標準在于它是否具有道德性;但此種道德性的標準又在于它是否獲得了普遍的認可,或是形成了普遍的實踐。
其二,倫理命題的效力標準有時可以因為該道德標準是由某個權威所的。此種情況在宗教氣氛比較濃重的社會中比較常見。在這些社會中,無論對于道德規范、法律規范還是宗教教義,其效力有無的標準都在于它是否來自于宗教權威,例如諸神的意志及其表達,宗教組織所的戒律等。當然,這種情況如果夸張到此種程度,即社會所有行為規范的效力標準都是同一個標準,那么也就很難主張這個社會還存在什么道德、法律或宗教之分了,本文所謂基于道德論證的法律原則效力標準問題也就不存在了。
在上述兩種情況下,要判斷一個道德命題是否有效,須考慮其是否是普遍共識或實踐,或是考慮該命題是否是由某個權威所的。僅就倫理命題而論,其效力標準也是基于系譜或來源,而無需對倫理命題的內容加以實質的論證。于是,雖然作為此種法律原則的效力標準本身要求原則必須經過某種道德論證,但這里的道德論證過程所考慮的仍然是道德命題的系譜或來源,而非其內容。換句話說,法律原則的效力標準經由一個基于內容的標準,最終指向一個基于系譜或來源的標準。此時,這種基于道德論證的法律原則與基于來源的法律原則,乃至法律規則三者的效力標準,即便在性質上有所差異,但在形式或結構的意義上卻極為相似,最終都將訴諸于原則的系譜或來源;無非是,確定此種法律原則效力的方式需要經過一個容納道德論證的效力標準的允許。
當然,這里并不是要堅持,所有倫理命題的效力標準都是系譜或來源。在上述列明的情形之外,人們當然可以主張說,一項倫理命題成立與否,要對其內容進行實質的道德論證或道德推理。例如,我們可以論證說,“任何人不得從自己的錯誤行為中獲益”這一原則是因為它符合功利主義這一基本道德原理而成為有效道德原則的。在這個范圍內,德沃金本人對于法律原則效力標準是基于內容或道德論證的,因而區別于法律規則的說法依然是可以成立的。
五、結語
法律原則的效力標準是多樣且復雜的,既不能簡單說它與法律規則效力標準一樣是系譜的,又不能主張它完全是基于內容或道德論證的,與原則本身的系譜和來源毫無關聯。實際上,某些法律原則的效力標準也是基于系譜的,而對于另外一些基于道德論證的法律規則來說,除了相應的制度支持之外,道德論證本身有時會指向系譜規則,并以此確定原則的道德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將規則與原則的效力標準簡單地歸納為系譜與內容的對立,其實質是加大法律原則與法律規則在本體論意義不必要的差異,將是難以成立的。
注釋:
①〔奧〕凱爾森:《法與國家的一般原理》,沈宗靈譯,中國大百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頁。
②張文顯主編:《法理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三版,第105頁。
③④⑦參見〔英〕約瑟夫?拉茲:《法律的權威》,朱峰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130、128頁。
⑤〔德〕石里克:《倫理學問題》,張國珍等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99頁及以下。
⑥陳嘉映:《語言哲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⑧⑩Jules Coleman, Authority and Reason,in The Autonomy of Law, edited by R. P. George, 1996,Clarendon Press, P291,293,287.
⑨H.L.A. 哈特:《法律的概念》(第二版),許家磬、李冠宜譯,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237頁。
Ronald Dworkin, “Models of Rules I”, 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 p. 39,22,22,53.
〔奧〕漢斯?凱爾森:《純粹法理論》,張書友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82頁。
法律原則范文第2篇
關鍵詞 法律原則 自由裁量 司法適用
作者簡介:劉佳瑤,南京大學法學院。
一、瀘州遺產案案情回顧
從“瀘州遺贈案”的判決以來,人們對于這個案件有著很大的爭議,同時也引起對對于法律原則適用的反思。首先我們對于案件進行一個回顧。
案件的內容可以概括如下:A在去世之前立了遺囑,將其財產遺贈給和其同居并且曾在其生病時照顧的B,并且已經過公證。A去世后,B要求A的妻子Q交付遺贈財產,遭到Q的拒絕,為此起訴到法院。一審法院裁定:遺贈雖然是A本人的真實意思表示且形式而言是合法的,但A的遺贈行為“違反公共秩序和社會道德,違反婚姻雙方關于夫妻應當互相忠誠、互相尊重,禁止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規定,是一種違法行為,應屬于無效民事行為”。駁回了B的訴訟請求,B不服且提起上訴。二審法院援引《民法通則》第七條“民事活動應當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即民法上的所謂的“公序良俗”的原則,同時認定本案的遺贈行為無效,因此維持原判。
本案在初審和終審時,裁判都適用了民法中“公序良俗”的相關規定。即便是從“公序良俗”的角度認定遺贈無效,但是根據《繼承法》的規定,H對于Z的遺贈是有效的遺贈,是符合相關法律規定的。這就帶來一個問題,法律原則的作用到底是什么?法律原則和具體的法律規則之間的關系?在具體適用時是不是有先后順序。
二、法律原則適用的限制
這里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法律原則是否能夠直接適用于相關案件中?筆者認為,應該嚴格按照適用規則的相關順序,只有在不能能夠從具體確定的法律規則里面找到適用的依據的時候,才能考慮適用法律原則。法律原則是一種高度抽象的原則,不同于法律規則。拉倫茨說過:“雖然法律原則通常具有主導性法律思想特征,其不能直接適用以裁判個案,毋寧只能借其于法律或者司法裁判的具體化才能獲得裁判基準……” 拉倫茨所說的“具體化”其實也即是指法律適用的時候應該找到一個合適的中介,也就是找到事務的本質。
可以說,社會生活其實就是法律原則的適用中介。法官在適用法律原則的時候不能離開生活本身。如果法官在訴訟當中找不到法律原則所能夠依賴的現實生活,那么,這位法官就無法引用法律原則作為判決的依據。正如著名法官卡多佐所言“規則的含義體現在它們的淵源中,這就是說,體現在社會生活的迫切需要之中。這里有發現法律含義最強可能性,同樣,當需要填補法律空白之際,我們應當向它尋求解決辦法的對象并不是邏輯演繹,而更多的是社會需求”
具體而言有以下幾點:
1.法律原則的適用不得直接適用。會有人有這樣的疑問,如果不能直接適用,是不是就意味著,不能適用。這顯然是兩個概念。法律原則畢竟不同與法律規則,其本身的特點,就是籠統,不明確。因此在使用時自然和法律規則有所不同,應該有一個前提條件。那就是在,法律規則可以適用或者可以類推適用的時候,法律原則不得直接適。也就是所說的“禁止向一般條款逃逸”。根據德沃金所理解的法律概念,最先適用的自然是法律規則,然后在沒有法律規則可以適用的情況下,才能適用法律原則。
法官在具體裁判案件的時候,由于現行法律的具體規定是比法律原則更具體明確,因此,為了得出一個可行的解決方案,法官必須避免運用抽象原理。盡量的使用規則,而避免比較偏向于價值觀判斷的規則。并且,適用規則并避免適用原則,也是對于法的安定和權威的保護、防止裁判者的恣意。
2.法律漏洞的判定。法律原則的適用,一方面是上文所說,將原則的作用限定在對于填補漏洞或者法律續造領域。那么這里就涉及一個問題,什么事“法律漏洞”,如何判定“法律漏洞”。所謂法律漏洞,“其實就是制定法或者法律規則體系并未給予待解決案件以確定的解決方案,因之引發的法律缺陷。” 根據規則與原則的區分,這就等于是說當規則應該有相關規定而未進行相應規定就是,原則能夠得到充當裁判性依據的資格。
法律漏洞如果要下一個非常明確的定義,其實還是比較難的。畢竟法律漏洞還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存在。基本一個比較寬泛的說法是:原則是規則的例外。如果規則沒有規定,那么法官將會按照原則進行裁判,這個判決仍然能夠保持與規則保持一致。還有另外一種情形,同時存在規則和有正當性基礎的原則,但是在某種情況下,規則限制了原則適用,那么此時,法官就有可能隨意性的去推翻和掙脫規則的約束。最后,存在于規則以及原則外,還有與原則相矛盾的一類原則,當規則對原則的種種情形沒有相應的規定。此時,就發生規則與原則的矛盾。
如果是第二種情形。所謂的疑難案件適用原則時,疑難案件的對立概念自然就是簡單案件。德沃金認為的疑難案件就是沒有明確規則用以解決的案件。如果按照這種定義,那么也就是說只有原則才能確定疑難案件的結果。要求裁判者只有在疑難案件的時候才能求助于法律。這樣的規定的確是更有利于對于法律原則使用的限制。這樣的限制是對于原則應用領域的限制,但是還是很難避免個案中對原則應用的約束問題。 三、法律原則適用的探索
上文中,筆者試闡述了幾個法律適用的困境,法律原則是否屬于法律規范,法律原則是否可訴,以及對于法律原則的分類。但是對于法官而言,在適用相關法律原則的時候,怎么樣才能恰當的適用法律原則。
在上文的論述中,誠如德沃金文章中的觀點,法律原則的適用是需要在法律規則之后的。只有在規則模棱兩可,難以具體適用的時候才能夠適用法律原則。比如說,在刑法上有“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的原則,它的意義也就在此,是為了劃定刑法的界限和范圍,體現了國家權力的節制與人們行為的安全,很顯然,這個原則是沒有具體的法律規則與之相配套的。
這里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法律原則是否能夠直接適用于相關案件中?筆者認為,應該嚴格按照適用規則的相關順序,只有在不能能夠從具體確定的法律規則里面找到適用的依據的時候,才能考慮適用法律原則。畢竟,法律原則是高度抽象的,與法律規則不同。拉倫茨說過:“雖然法律原則通常具有主導性法律思想特征,其不能直接適用以裁判個案,毋寧只能借其于法律或者司法裁判的具體化才能獲得裁判基準...” 拉倫茨所說的“具體化”其實也即是指法律適用的時候應該找到一個合適的中介,也就是找到事務的本質。
法律原則范文第3篇
關鍵詞:法律原則;適用條件;衡量方法;限制
中圖分類號:G712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2-7661(2016)11-003-02
盡管國外早有拋棄法律規則而適用法規原則裁判個案的先例,但這類情形在我國非常少見,一般僅停留在學者的研究視野中,真正將這一問題引發關注和探討的是2001年發生在四川的“瀘州遺贈案”。案情大致如下:“黃永彬和蔣倫芳夫婦為四川省滬洲天倫集團公司404 分廠職工,二人于1963 年結婚。1994 年,黃永彬與比其小22 歲的張學英相識并產生感情。1996 年底,兩人公開以夫妻名義租房同居。2001 年2 月,黃永彬被查出患有肝癌(晚期)。在黃永彬治療期間,張學英不顧他人嘲笑以及蔣倫芳的諷刺和挖苦,以黃永彬‘妻子’的身份陪護在黃永彬的身旁。2001 年4 月17 日,黃永彬通過朋友找到律師,表示死后將把自己的財產遺贈給張學英。在律師的配合下,黃永彬于4 月20 日在滬洲市納溪區公證處對下述遺囑進行了公證:‘我決定將依法所得的住房補貼金、公積金、撫恤金和賣滬洲市江陽區一套住房售價的一半(即4萬元) 以及手機一部遺留給我的朋友張學英一人所有。我去世后骨灰盒由張學英負責安葬’。4日后,黃永彬去世。4 月25 日,黃永彬的朋友公開宣讀了上述遺囑。在黃永彬妻子蔣倫芳拒絕執行遺囑后,張學英將蔣倫芳告上法庭,要求法院依法判決蔣倫芳執行遺囑。”
一審法院四川省滬洲市納溪區法院認定,黃永彬的遺贈行為損害了社會公德,破壞了公共秩序,屬于無效民事行為,依據《民法通則》第7條“有關民事活動不得違公德”的規定,判決宣告遺囑無效。二審法院也以違背公序良俗原則直接認定黃永彬的遺贈行為無效,駁回了上訴人的訴訟請求。
該案宣判后引起法學界的強烈震憾,爭議之聲至今未絕。上海閔行區人民法院于2002年底審理的“夫妻不忠賠償案”,又再次引發了對能否適用法律原則裁判個案的爭論。法律原則作為法律規則的基礎和本源,在法律體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其可用作司法裁判的依據已為學界公認。然而在何種條件下可以適用原則來進行個案裁判,如何適用以及應該受到哪些限制等諸如此類的問題,直至今日也未有完全統一的意見,因而需要進一步加以探討。
一、法律原則的適用條件
法律要素的主要內容是法律規則。而規則之所以有意義,在于它們都要與某個更為一般性的規則相一致,并因此被視為這一規則的特定的或具體的表現形式。如果那個更為一般性的概念被人們認為是一個合理的、有意義的概念,或者對于指導具體事務來說是正當的、可欲的標準,那么人們就會把這一標準視為一項“原則”。
法律原則該在何種條件下適用呢?“窮盡法律規則方得適用法律原則。”現有法律體系中,法律規則作為法律推理的前提,理所當然應該得到優先適用。但現實生活是五彩斑斕的,生活中的問題也是層出不窮的,人類無法在立法之初就預計到今后社會生活中出現的所有難題,因而就出現了法律上的漏洞:“漏洞是實證法(制定法或習慣法)的缺陷,在被期待有具體的事實行為規定時,明顯地缺少法律的調整內容,并要求和允許通過一個具有法律補充性質的法官的決定來排除。”我國臺灣民法第1條規定:“民事,法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法理。”所謂法理,按照臺灣學者的一般理解,“應系指自然法律精神演繹而出的一般法律原則,為謀社會生活事物不可不然之理,與所謂條理、自然法、通常法律的原理,殆為同一事物的名稱。”據此可見,個案中適用法律的順序是規則優先,只有當法律規則缺位時,一般法律原則才可以用來彌補法律上的漏洞。
另外,由于法律規則是由法律語言書寫的,既作為語言,就必然具有語言所不可避免的缺點,從而導致法律規則適用過程中出現含糊不清的狀況。并且,就我國目前的立法狀況來說,即使是同一位階、同一法律文本之內的兩個或兩個以上不同的規則,它們的效力都可能出現沖突的情況。實際上,語言表達從不曾持久地保持“清晰”,因為它們可能隨著被表達、以后被接受的環境的改變而改變。另外,任何法律規定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由此,看起來清晰的文義可能與同一法律的其它規定產生矛盾,也可能與以后頒布的或者更高位階的法律的要求內容產生沖突。況且,立法者也會犯錯誤,他們也可能做出明顯矛盾的規定或者錯誤的表達,即使“文義清晰明確”。這時,究竟該如何適用法律規則呢?正確的選擇是,“當我們對于一項規則在具體情境中的恰當含義猶豫不決時,原則可以幫助我們做出恰當的理解;而且,在很多具體場合中原則也幫助我們解釋為什么該規則應當予以堅持”。
在兩種情形下法律原則可以“出場”,直接作為裁判依據而予以適用:一則是沒有規則可循,作為司法機關的法院此時在漏洞領域發揮著造法功能,“禁止拒絕裁判”是法院在該領域進行立法的依據。當然在刑法中,這個原則將受到嚴格限制。刑法領域之下,“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如果法律沒有明確規定,法院就不得通過類推填補漏洞,否則會擴大被告人受罰的可能性;一則是規則模糊不清或者適用規則將導致明顯的不公時,個案裁判就應摒棄規則,而訴諸于規則背后的原則。即當出現“實在法模棱兩可或未作規定”的情形方得適用法律原則。
二、法律原則的適用過程
在司法審判中,如果有針對個案的規則,并且沒有與規則相沖突的原則,那么就將適用規則裁判個案。這也即理論上的“禁止向一般條款逃逸”,即當適用法律規則或法律原則會獲得同一結論時,具體法律規則應當成為司法適用的首要依據,只有在窮盡法律解釋及類推適用等法律方法仍然不能解決問題時,才能訴諸原則的適用。
而法律原則的適用過程是一個將法律原則“具體化”的過程。首先,在規則缺位或模糊的情況下,法官需要找尋可以作為裁判依據的法律原則;其次,聯系個案事實,解釋和論證法律原則具有針對審理案件的合理性和正當性;最后,法官對可適用的法律原則進一步解釋,形成應用于個案的“裁判依據”。這個過程實際是一個在事實、規范之間進行判斷衡量法律原則適用的方式和范圍的過程。原則與規則、原則和原則之間存在矛盾或“競爭”關系時應該如何比較選擇是這一過程中的重要環節,對適用法律原則審理案件的合理性和正當性的論證也至關重要,以至成為法院判決具有權威性的關鍵。當然,最后形成的個案裁判依據的合理性說理和證成也必不可少。
但法律原則適用具有極大地危害性,其適用必須受到嚴格的限制。首先,必須在出現“沒有規定或模糊不清”的情況下才可以適用法律原則,也即沒有窮盡法律規則時不得適用法律原則。其次,在適用法律原則,必須嚴格遵守法律原則“具體化”的步驟和方法,依照衡量標準選擇適用法律原則,并進行充分合理的論證和解釋,最終形成具有正當性并具可接受性的個案“裁判依據”。也就是其適用范圍及方式、過程都應受到限制,最大程度縮減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間,保障法的穩定和確定性。
一方面,實踐中確實存在“實在法模棱兩可或未作規定”的情形,法官沒有拒絕裁判的權力,因此必須援引法律原則彌補漏洞,進行個案裁判。另一方面,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法律原則的適用具有極大的危險性,可能帶來的恣意裁判和借法律之名干預社會生活將會對法律造成的巨大危害。法律需要被信仰、被尊重,因此必須維護法律的穩定性和強制性,這就必須嚴格限制原則在個案中的適用,嚴格遵循法律原則裁判個案所應遵循的方法,從而真正實現法的正義。
參考文獻
[1] 尼爾麥考米克:《法律推理與法律理論》,姜峰譯,2005年版,法律出版社.
[2] 舒國瀅:《法律原則適用中的難題何在》,載《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6期.
法律原則范文第4篇
“四川瀘州遺贈案”是我國司法實踐中頗受爭議的案件,曾經在司法界引起了廣泛的討論;美國的“里格斯訴帕爾瑪案”是普通法系國家關于法律原則司法適用最為典型的案件。本文將在以上兩個案例的基礎上,具體闡述法律原則的司法適用。
為了維護法的安定性和權威性,通過對法律原則適用的適當限制,法律原則也可以作為法官裁判案件的依據。在個案中根據法律規則的具體情形來適用法律原則。具體分為三種情形,第一、當存在既定的法律規則時,依靠法律原則防止適用法律規則違背立法目的;第二、在不存在既定法律規則的情況下,適用法律原則填補法律漏洞;第三、當法律原則與法律規則或法律原則之間出現抵觸時,法官對個案法益的權衡成為必要。
在“四川瀘州遺贈案”中,第一審人民法認為:黃永彬將所有財產贈給“第三者”的這種行為違反了《民法通則》第7條“民事活動應當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規定,駁回了原告的訴訟請求。第二審法院以遺贈人黃永彬的遺贈行為違反的公序良俗原則,應屬無效,駁回上訴,維持原判。但是我國《繼承法》第16條明確規定“公民可以立遺囑將個人財產贈給國家、集體或者法定繼承人以外的人。”而且,該遺囑是黃永彬本人內心真實意思的表示,并且通過公證具有更高的法律效力。其次,根據特別法優于普通法,我國《繼承法》屬于特別法,《民法通則》屬于普通法,就本案應當優先適用《繼承法》。在對個案進裁判時,如果存在具體法律規則,一般情況下,適用法律原則裁判案件的結果與直接適用法律規則不一致,法官不能放棄具體法律規則適用法律原則。我國《民法通則》第七條、《合同法》第七條明確規定了社會公德和社會公共利益,在學界通常被認為是關于公序良俗的規定。公序良俗原則體現了“法無明文禁止即可為”和“權利不可濫用”的辨證統一。法官判斷一個法律行為是否違反公序良俗原則,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來考察:一是該法律行為的客體是否違法;二是法律行為的內容是否違法;三是法律行為所附條件是否違法;四是動機或目的是否違法。本案中,黃某在有配偶的前提下,與張某公開同居的行為是違反道德的,但并不是所有與婚外同居有關的行為都是違反公序良俗的。如本案中,張某在黃某彌留之際對黃某悉心照顧,黃某出于感激之情的贈予就不是違反公序良俗的。如果說公序良俗原則維護了“法律本身內在的倫理原則和價值標準”那么在對與婚外同居有關聯的遺與行為進行效力判斷時,也必須注意這些行業是否違反“法律本身的倫理原則和價值標準”。在現代社會中,很難對公序良俗原則進行一個統一的定義,不同的法官對公序良俗原則的內涵與外延把握不同。以公序良俗來判斷法律行為無效的,是依據具體的法律規范,而是在于法律本身的價值體系(公共秩序)和法律外部的倫理秩序(善良風俗),不是為了倫理秩序的完善而使道德義務轉化為法律義務;而是為了不使法律行為因為法律規定的機械和僵化而違反法律本身體系和外部倫理體系。本案中,法官直接基于黃永彬與張學英的婚外同居關系,判決贈與行無效,只是考慮了判決結果所產生的社會影響,并未注重法律行為本身是否違反公序良俗。納溪區人民法院副院長曾說“如果支持了原告張學英地訴訟主張,會滋長了‘第三者’、‘包二奶’等不良社會現象,找破了法律在廣大老百姓心中的形象”。顯然,法院在審理時過分注重了社會輿論沒有正確運用公序良俗原則,違背了法律本身的價值理念,損害了具體法律規則的尊嚴。
美國的“里格斯訴帕爾瑪案”,雖然紐約州遺囑法沒有對繼承人謀殺遺囑人情況作出規定,但是最高法院根據“任何人不應從自己過錯中獲得利益”,判處帕爾瑪敗訴。從法學倫理角度講,作為法律規范要素之一的法律原則可以作為法官裁判的依據,但問題是在司法裁判實踐中,一旦法律原則作為有效規范被援引,那么它的正當性經常被面臨質疑,甚至以法律原則作為裁判依據往往被認為是法律或者司法存在所謂“泛道德化”的傾向。因此,我們既要意識到在具體法律規范出現漏洞時,援引法律原則作為判案依據,又要注意到法律原則進入裁判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在司法裁判的過程中,案件雖然是由法官在認定事實的基礎上依據法律進裁判的,但法官在本質上仍是一活生生的人,他既不是一臺司法的自動售貨機,也不只是法律的留聲機。法治的核心是規則之治,在哈特看來,法律是一種社會規則,并認為社會規則的主要特征是多數社會成員從內在的、批判反思的觀點接受某些社會上多年奉行的慣例,為指導人們應當如何行為的普遍準則。因此,如果缺乏這種內在的規范態度,任何外在的行為習慣均皆不足以構成具有普遍的、規范的、具有約束力的社會規則。但是,法律規則存在局限性。法律規則存在普遍意義在于保障每一個公民都能受到法律保護,以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在法律規則追求普遍正義的同時,很可能會忽視個案正義的實現,法律的目的也就很難實現。社會生活復雜多變,法律規則不可涵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必然存在盲區和漏洞。規則漏洞是法律原則適用的前提條件,在司法實踐中,雖然法官可以通運用法律原則對現有法律規則存在的漏洞進行修補、調整,但是往往會造成法官濫用裁量權。因此,法官需要在促進社會正義與維護成文法的權威性、安定性之間作出價值比較和選擇,通過折衷的方式作出判斷。當適用法律規則可能造成個案的不公正時,就需要法官造法,行使自由裁量權選擇適用法律原則進行裁決。但是,法律原則不得向一般條款擴張,禁止直接適用法律原則,適用法律原則時必須加以嚴格的限制,防止法律原則成為法官濫用自由裁量權的借口。在里格斯訴帕爾瑪案中,律師認為,帕爾瑪祖父的遺囑沒有違反紐約遺囑法所明確的規定的條款,遺囑是有效的,帕爾瑪并未喪失繼承權。如果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訴訟請求,那么法院就更改了遺囑,用自己的道德信仰來代替法律。在運用法律原則之前要進行充分的論證,對法律原則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進行論證,這個論證實際上可以對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進行制約和監督。
法律原則范文第5篇
在一定意義上講,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法律經濟原則從經濟學成本投入與資源分配等角度出發,對法律與制度的安排作經濟的分析,以期使這種安排達到最佳效益。婚前體檢是降低新生兒出生缺陷率的第一道防線,是我國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從源頭上預防各類遺傳性、傳染性疾病的重要舉措。筆者認為,修訂后的5婚姻登記條例6變強制婚檢為自愿婚檢,帶來了一些負面效應。目前取消強制婚檢問題已經引起了國家有關部門的重視,黑龍江省率先恢復實施強制婚檢值得贊許。筆者認為,就我國目前的國情而言,依據法律經濟原則盡快完善我國的婚前體檢法律制度非常必要。
1關于實行自愿婚檢還是強制婚檢的問題
我國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國,其中農村人口占大多數,24年我國的人口總量已經超過13億,在巨大的人口增長慣性作用下,中國的育齡婦女數量龐大,在未來的幾年中仍然繼續增長,將形成第四次人口出生,與此同時,我國不少地區仍有大量的傳染性、遺傳性疾病流行,一些新的傳染病如艾滋病等也存在蔓延趨勢,基層衛生保健工作仍不到位,公民對婚前保健和孕產期保健的重要性認識不夠,傳宗接代思想嚴重,根據取消強制婚檢幾年來的實踐,婚姻當事人自愿婚檢意識極差,自愿婚檢者寥寥無幾,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了零婚檢現象。有統計顯示,23年5婚姻登記條例6出臺之前,我國的婚前體檢率基本達到8%,然而,取消強制婚檢后,全國各地普遍反映婚前體檢率呈下降趨勢,相對應的是新生兒出生缺陷發生率上升。據新華網報道,24年,北京市婚檢率僅為5%,出生缺陷發生率由之前的1j上下上升到24年的14j,這一現象在全國范圍普遍存在[2]。由此,不難看出,目前在我國實行自愿婚檢條件尚不成熟,為了確保優生優育,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繼續保留強制婚檢仍有必要。
2盡快明確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
既然目前在我國實行自愿婚檢的條件還不成熟,那么就應當盡快明確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類型,以便于婚姻登記機關操作。5中華人民共和國母嬰保健法實施辦法6規定:婚前醫學檢查應當查明是否發現下列疾病:¹在傳染期內的指定傳染病;º在發病期內的有關精神病;»不宜生育的嚴重遺傳性疾病;¼醫學上認為不宜結婚的其他疾病[3]。5中華人民共和國母嬰保健法6第1條規定經婚前醫學檢查,對診斷患醫學上認為不宜生育的嚴重遺傳性疾病的,醫師應當向男女雙方說明情況,提出醫學意見;經男女雙方同意,采取長效避孕措施或者施行結扎手術后不生育的,可以結婚。但5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6規定禁止結婚的除外[4]。對有生理缺陷者在婚前體檢時也應檢查,保障當事人的知情權,至于是否要結婚,由當事人知情后自主決定。為此,應該站在促進中華民族健康繁衍的高度,依據法律經濟的原則,盡快明確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的標準[5]。由國務院民政部門和衛生行政部門聯合組織有關專家進行論證,明確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暫緩結婚疾病、可以結婚但不宜生育的疾病、限制生育的疾病等的種類,要求婚檢醫院出具婚前醫學檢查證明,明確提出建議不宜結婚、不宜生育、暫緩結婚、采取醫學措施等結論,供婚姻登記機關在是否給予登記時參考。
3關于婚檢醫院及婚檢費用承擔問題
由于我國目前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特別是貧困落后地區的公民收入欠低,一部分人生活仍然十分困難,讓他們承擔婚檢費用很困難。我國新修訂后的憲法明文規定國家建立健全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6],因此,應盡快完善我國的婚前體檢社會保障制度。建議將婚前體檢固定在縣級以上婦幼保健醫院,設立專門科室,統一檢查,完善、規范婚前體檢制度,明確責任與義務,建立責任追究制度;培訓專門體檢人員、提高體檢人員隊伍素質;逐步完善婚前體檢社會保障制度,劃撥專項經費,具體由中央和地方財政共同承擔婚前體檢費用;保留完整檔案,對患病結婚者進行追蹤指導,為優生優育指導提供參考。要降低新生兒出生缺陷率,單靠婚前體檢遠遠不夠,孕產期的保健與婚前體檢相比更為重要,因此,要處理好婚前檢查和產前檢查的關系,各級婦幼保健醫院同時承擔著優生優育的職責,由婦幼保健醫院統一檢查的另一個優點就是有利于保持婚育工作的連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