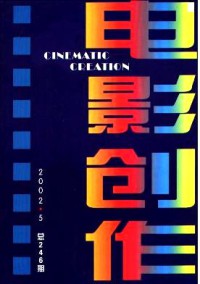對電影進行現象學的研究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對電影進行現象學的研究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燈光是電影敘述情節的工具,直接影響著成像的深度、色調、氣氛。通過補強、減弱、降低、提高等手法,燈光可以創造意境,烘托氣氛。香港導演王家衛在其作品中,對燈光、色調、明暗的運用,極大地體現了影片整體基調、氛圍和主題。王氏風格的電影,通常畫面暗淡,主人公低沉、壓抑、傷感。
在《花樣年華》中,昏暗的樓梯、走廊、房間、街道,重復出現,使影片流露出無限的懷舊、傷感。兩位主人住在租的房間,內心由于感情缺憾始終流離失所觀影者很容易被這種暗色調的光影打動,進入深沉壓抑的憂郁情緒。在蘇麗珍去看望周慕云的走廊上,原本簡單的場景轉換,因為燈光處理,凸顯了蘇麗珍的優雅身軀,一組長鏡頭中彌漫著無限的誘惑和美感。從這個角度甚至可以說,正是燈光,寫就了電影的內在,構建了影像的蒙太奇。電影人的藝術創造,不僅是創造視覺美,更是要通過影像這種自動思維裝置來傳達思想和信念,這才是光影的魅力所在。現象學將這種功能解釋為:將意向對象的圖像客體,變成“我”的意識,如“對的圖像”,“對的記號”。電影人在對抒情和感覺再造的過程中,以影像的方式賦予其有形的意義,喚醒觀影者的感覺和知覺,使這次審美歷險達到悅己的功效。
巴贊之于電影現象學作為法國戰后現代電影理論的集大成者,安德烈•巴贊發表的《攝影影像的本體論》和《電影手冊》,夯實了電影現實主義的理論基礎,由他引領的新浪潮為電影美學帶來了新氣息。現象學的概念被普遍運用到巴贊的理論和實踐中,例如在評論《奧內齊姆》時,他說道:“大多數這類滑稽喜劇片主要還是關于人物的一個基本計劃的直線連續表現。它們屬于一種固執的現象學。”他甚至認為意大利新現實主義是一種現象學的現實主義。身為巴贊同時代人的梅洛龐蒂也很關心電影,親自寫過關于電影的論文。
影片是個可以信息疊加的“場”。它貌似是“實體”,其實是虛擬,是技術性圖像。最終,“圖像制作者的想象變成了(圖像接受者的)幻覺”。[3]對于意識怎樣認識世界、認識現象這個哲學的一般問題,致力于回到事物本身的現象學有自己的獨特建構。胡塞爾給予的第一個規定就是其方法在于描述,梅洛龐蒂也認為:“現象學只有通過現象學的方法才能理解。”[4]現象學主張的回到事物本身,而巴贊認為電影首先應當記錄和描述現實,兩者在原理上異曲同工。現象學的還原法要求描述不能暗含任何前提,且須建立在意識對事物的直觀的感知上。巴贊對于一部影片的要求也是如此,“重要的不是證明,而是表現”。他引領的新浪潮中,電影的編導們紛紛從當時的社會實際和現實生活中尋找情節和素材,從而賦予意大利新現實主義的強大的紀實價值。這得益于巴贊的電影理論新發現,即攝影機完全可以做到不附帶前提地表現現實世界,影像不需要人們的干預和創造而自動構成。
他聲稱“所有藝術都是以人的參與為基礎的,唯獨在攝影中,我們享受到人的不介入照片作為‘自然’現象表現給我們,好象一朵花或一個雪的晶體,它們的美離不開植物和大地的本源。”當然,巴贊電影理論與現象學的聯系,很大程度上是在方法論或認識論方面,絕不表現為目的上的一致。現象學描述的是純粹的意向對象和意識活動。而電影人有意識的創作目的在于有效、深入地表現現實,以完整自然地方式呈現真實和虛幻。
作者:鄭麗娟單位:華南理工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