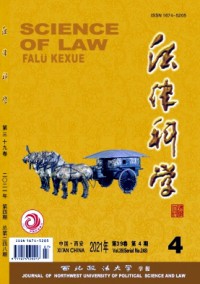法律適用論文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法律適用論文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法律適用論文范文第1篇
隨著全球經濟交往的加快與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商品在多個國家之間進行生產、加工、交換、流通、消費、使用,這使得跨越國境的產品責任案件日益增多。就中國而言,中國產品在國外發生產品責任問題以及外國產品在中國發生產品責任案件已屢見不鮮;在司法實踐中,原有的產品責任立法往往不能很好地保護消費者、使用者的正當權益。為此,我國與2000年9月1日正式實施了新的產品質量法,對產品質量責任實體法律制度作了較大修改,使之更加符合當今世界各國普遍做法,例如擴大了產品范圍、產品責任主體范圍;明確地規定了產品責任的賠償范圍,使之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規定了受害人親屬可以向產品的生產者或銷售者要求給付死亡賠償金,加大了對產品責任人的處罰力度。然而,我國當前還沒有調整涉外產品責任法律適用的專門制度。對于一國涉外民事法律關系而言,需要實體法與沖突法來共同調整,修改后的產品質量法在一些操作層面已“與國際接軌”,如再專章規定涉外實體規范已不必要;但在沖突法領域,我國只是籠統地采用了侵權行為法律適用規則,過于原則、簡單、缺乏可操作性,且不說立法的缺陷需要仔細考察而知,就說由此而導致司法上的困惑與矛盾至少會有:(1)如該侵權行為發生在外國,依行為地法和中國法均構成侵權時,應適用哪一國家的法律來確定當事人的賠償責任?(2)如受害一方為中國人(即原告),是否可以根據行為地法(外國法)得到較高賠償?(3)如雙方均是外國人適用中國法是否有充分理由?[1]既然問題已經提出,筆者就有可能也有義務結合這些問題分析我國現行涉外產品責任法律適用制度的缺陷,對相關立法的健全提供一些思考和建議。
一、現行涉外產品責任法律適用制度的缺陷
產品責任歷來被認為是各國的強行法,是事關當地公共秩序的“直接適用的法律”和“專用實體法”,如有專家認為“產品責任法的各項規定和原則大多屬強制性規定,雙方當事人在訂立合同中不得任意加以排除或更改。”[2]如果我們把視野僅僅局限在本國范圍以內或把前提條件設為不存在或不允許法律沖突及法律選擇時,這一論斷無疑是正確的。然而,國際產品責任作為跨越國境的客觀存在從20世紀60年代末成為當代國際私法中所關注的問題,不再純粹是一個國內法問題。
從我國的角度看,國際產品責任即我國的涉外產品責任,它的主要形式有以下三類:(1)中國產品在國外發生產品責任問題;(2)外國產品在我國發生產品責任問題;(3)外國人在中國境內遭受產品責任侵權問題。而中國人在外國境內遭受產品責任侵權問題一般不由我國法院受理[3],故不在我國涉外產品責任案件范圍之內。涉外產品責任同一般侵權責任相比具有其特殊性及復雜性,其特殊性表現在它的涉外因素:或涉及外國產品或涉及外國消費者、使用者,這就決定了不同國家對產品責任的認定、損害賠償的范圍金額、責任主體的范圍等均差別較大,最終影響對受害人權益的保護程度,所以,往往只允許適用法院地法會對當事人造成不公正的待遇,貌似“平等”的、“無一例外”的適用法院地法恰恰與實現“個別正義”背道而馳;其復雜性表現在它是產品責任:經濟全球化加速了產品的流通,一件產品可能由若干國家共同加工制造、一件產品可能在多個國家流轉、產品的消費者使用者可能跨境移動、一個產品責任可能有多個責任主體,因此與判定產品責任所依據的連接因素必然是復雜多元的。涉外產品責任所具有的特殊性、復雜性也就成為我們考察評判我國現行涉外產品責任法律適用制度是否合理完善的出發點和依據。
我國尚無調整涉外產品責任法律適用的專門制度。在司法實踐中,對于涉外產品責任的法律適用依據是《民法通則》第146條,該條規定:“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適用侵權行為地法律。當事人雙方國籍相同或者在同一國家有住所的,也可以適用當事人本國法或者住所地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不認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發生的行為是侵權行為的,不作為侵權行為處理。”可見,我國涉外產品責任法律適用籠統地采用侵權行為法律適用規則,完全忽視和掩蓋了其同一般民事侵權責任相比應具有的特殊性與復雜性。盡管“場所支配行為”這一沖突法的古老法諺仍被一些國家(如英國、加拿大、比利時、希臘、德國、意大利等國)遵循為國際產品責任法律適用的基本原則,但是各國經貿往來的現實與司法實踐表明:單純按照侵權行為法律適用規則解決涉外產品責任問題存在以下缺陷和弊端。
首先,“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適用侵權行為地法律。”而什么是“侵權行為地”呢?這一詞語本身就包含了不確定因素,這是因為各個國家對于侵權行為地的認定并不相同。如比利時法認為發生地與傷害地不一致時,應將行為發生地視為侵權行為地。而英國法為了確定侵權行為地,法院必須弄清導致行為發生的實質性原因發生在哪里,而這一問題的答案卻因不同類型的侵權行為而有所不同。[4]德國法則規定,如果被告做出行為的地方與原告遭受損害的地方不在同一國家,法官有義務將對原告有利的地方作為侵權行為地,并且只能適用該地的法律。[5]而美國1972年第二次《沖突法重述》采用較具彈性的規則,按照最密切聯系的需要由法官自由裁量把損害發生地、引起損害的行為發生地或其他當事人關系集中地作為考慮的聯系因素。[6]根據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87條規定,“侵權行為地的法律包括侵權行為實施地法律和侵權結果發生地法律。如果兩者不一致時,人民法院可以選擇適用。”該規定針對事實不一致情況下,法院有權做出選擇作了靈活規定,但并未規定應依什么標準來做出選擇判斷。至此,“侵權行為地”在法律上仍是一個模糊不易確定的概念。
其次,就涉外產品責任而言,什么是“侵權行為地”在司法實踐中也是一個不易認定的事實問題。一方面在一些復雜的國際產品責任案件中,缺陷產品造成的損害既可能與產品設計有關,也可能跟產品生產、銷售有關,還可能與產品零部件的提供有關。若一件產品在甲國生產、在乙國設計、在丙國銷售、在丁國消費,而其零部件又由不同的國家提供,那么,究竟何為侵權行為地,是極難判斷的;另一方面,現代社會中交通條件極大提高,交通設施意外事故時有發生,行為地常常帶有偶然性,而此偶然行為地一般為被告(產品責任人)不可預見到地點,如原告(受害人)在某國遭受損害,而被告卻并未將其產品投放該國市場,此種情形若適用傷害地法,顯然對被告而言有欠公正。此外,還有一種特殊情形,就是持續性傷害(cumulativeinjury),舉例說明:消費者服用了有缺陷的藥丸在不同國家進行旅游,此時是很難確定哪里是損害發生地的。
再次,適用侵權行為地法律有時不能很好地保護產品責任受害人的利益。涉外產品責任的特殊復雜性決定了侵權行為不僅與行為地有關,它還與行為的性質、案件的重心、當事人利益集中地、當事人國籍、住所(居所)以及營業地等連接因素有著更密切都聯系,如果僅以侵權行為地法為準據,難免會造成對當事人利益保護不當的情形出現。[7]
本文開篇提出的三個問題即是明證:其一,我國產品在外國對受害方(外國人)造成損害,若原告訴至我國法院,法院是否應該考慮適用其本國法(同時是侵權結果發生地法)還是以產品在中國制造為由適用侵權行為實施地法律——我國法律,后者顯然對外國受害人保護的范圍、程度比起其本國法是遠遠不夠的。我們知道,外國法對產品責任的認定一般采取嚴格責任使得責任人承擔責任的范圍較廣,且外國法所確認得損害賠償一般既包括精神賠償和懲罰性賠償,甚至部分間接損失。其二,外國產品在我國對我國消費者造成損害,若我國法院以侵權結果發生地在中國為由適用我國法律而不顧原告(我國消費者)根據被請求承擔責任人(外國產品制造商)主營業地國國內法(同時是侵權行為實施地法)獲得較高賠償的請求,其結果同樣顯失公正。其三,如果原、被告雙方均是外國人在我國法院提起產品責任侵權之訴,這里又分為兩種情形。一種是雙方具有同一國籍或者在同一國家有住所,我國《民法通則》規定“可以適用當事人的共同本國法或住所地法”。此條款從某種角度看,是最密切聯系原則在我國侵權行為法律適用中的具體立法體現。不僅比適用侵權行為地法更顯公正合理,并且有利于判決定承認和執行。還有一種是雙方具有不同國籍也不在同一國家有住所的情形,在司法實踐中,法院往往適用侵權結果發生地——中國法律,造成對外國受害人保護力度不夠,甚至按照中國實體法的要求外國被告不承擔或減免產品責任。而同樣是適用原告或被告國籍或住所地法,受害人的利益可能得到充分保護。
我們知道,產品責任侵權雖然關系到侵權行為地的司法與公共利益,但產品責任侵權歸根結蒂是侵權行為的特殊形式,擺脫不了同一般侵權行為的共性,即受害人提起侵權之訴旨在獲得他所滿意的損害賠償,其本質是一種私權之訴。法院實現公正的途徑恰恰是在合理依據的范圍之內,保證受害人獲得令其滿意的、充分的賠償。加之涉外產品責任的特殊性,當涉及到外國當事人的情況下,給予外國當事人按其本國賠償范圍及標準的判決并不意味對侵權結果發生地公共秩序的破壞;相反僅僅以侵權結果發生地這一偶然因素為由拒絕以其他更密切的聯系因素所指引的準據法為判定實體權利義務的根據,其理由是不充分的,也是不合理的,最終會影響案件的公正解決,進而影響到外國當事人對我國法院的信賴與尊重。我們并不能推斷出依照當事人本國(尤其是受害人本國)的法律使受害人獲得較高額度的賠償會擾亂損害發生地(多數情況下是法院地)的公共利益與安全:一方面損害賠償之訴根本上不同于公訴機關對犯罪行為的追究,對侵權人責以高額賠償不會導致侵權行為地當事人間的平衡再度被打破,它既能滿足受害人的賠償訴求,又能懲戒侵權行為人,使其在經濟上更是在心理上對類似行為望而卻步;另一方面,平等公正地實現審判正義,要求法院在應當適用外國法時毫不猶豫地適用外國法,盡可能地充分保護受害人利益,同時兼顧產品責任人的合理抗辯,最終有利于而不是與侵權行為地的公共利益背道而馳。
最后,涉外產品責任采用侵權行為法律適用規則的現實后果往往是不自覺地擴大了法院地法的適用途徑和機率,阻礙了國際私法機制發揮正常的作用。從我國法律規范本身來看,我國對“侵權行為地法”的司法解釋是“包括侵權行為實施地法律和侵權結果發生地法律。如果兩者不一致時,人民法院可以選擇適用。”若遇到外國產品在中國發生侵權損害,司法實踐中人民法院大多考慮何者同時又是法院地法做出選擇。例如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審理的一起中國技術進出口公司訴瑞士工業資源公司侵權賠償糾紛上訴案中,既選擇了侵權結果發生地,同時又是法院地法即我國法律,作為該案的法律適用依據。[8]若我國產品在外國發生侵權損害,法院會以產品制造地同時又是法院地為由,以侵權行為實施地法我國法律作為準據法。其法律選擇的任意性可窺見一斑,但都為達到適用法院地本國法解決糾紛的效果。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其理論上的依據不外乎:適用法院地法是司法的需要,是法院地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需要;產品責任法具有強行性和公法的性質,而外國的公法一直被認為不具有域外效力。這樣即使在應當適用外國法的場合也以公共秩序保留或公法不具有適用性為由排除其適用,轉而適用法院地法。關于損害賠償之訴是私權,筆者在前已有論述。我國《民法通則》第146條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不認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發生的行為是侵權行為,不作為侵權行為處理”的規定,實際上是過分強調了我國的司法,對在我國境外發生的但我國產品責任法不認為是侵權的行為關閉了法律選擇的大門,其立法本意在保護我國產品制造者不受外國產品責任法的追究,但這把雙刃劍在傷害了外國消費者利益的同時也傷害了自身。試想,若我國消費者在境外遭受產品侵害將得不到我國法律保護,即使他在外國法院得到了判決支持,若需要我國法院承認和執行,當如何處理?是認定為侵權還是否定之是一個兩難問題。“其實,并不用做什么理論上的深究,最明白不過的事實就是內國的法官無疑最熟悉自己國家的法律。他們適用自己的法律輕車熟路,簡便易行,而且大多可以做到不出解釋上的錯誤。更何況許多國家的法官,經訓練培養后,就會認為適用自己的法律是實現審判公正的保障。”[9]據此,在涉外產品責任案件中,面對復雜的連接因素,只要可以找到適用本國法的借口或只要雙方當事人都不堅持適用外國法,又有幾個法官不愿避重就輕呢?畢竟從識別到連接點的確認到反致到外國法的查明到公共秩序保留直至最后做出一個涉外判決不僅是一項繁重的工作,而且對法官的專業素質要求極高,恐怕這不是我國法官隊伍與法律資源現狀所能勝任的。盡管如此,當代國際私法——進入全球化時代的國際私法要求我們既不能簡單認為遇事只有適用外國法才能發揮國際私法的機制作用,也不能簡單認為凡適用法院地法就能保證判決的公正,而必須平等地對待內外國法律,從案件本身而不是從習慣、方便、與思維定勢出發查找應適用的法律依據,衡量我國未來涉外產品責任法律適用制度是否先進是否健全,很大程度就看它有沒有充分、合理、科學地貫徹“平等對待內外國法律”這一原則。
此外,現行法律條文本身失之片面,不夠嚴密。《民法通則》第146條之“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適用侵權行為地法律”只規定了“損害賠償”適用侵權行為地法,沒有明確侵權行為的認定、責任主體的確定、責任之減免等侵權行為其他方面的法律適用問題。但考察立法者的意圖,從有關上下文及邏輯結構看,立法并未旨在分割侵權行為法律適用的各個方面,而是統一由侵權行為地法律調整。據此,在今后的條文表述上,修改為“侵權行為之債,適用侵權行為地法律”似更全面。
二、從各國產品責任訴訟的法律適用看有關國際通行規則
(一)美國
美國在本世紀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爆發了一場沖突法的革命,該革命對侵權行為領域法律適用問題形成很大沖擊,對產品責任沖突法的適用也有同樣的影響。60年代前,美國對涉外因素的侵權行為案件大多適用侵權行為地法,所謂“侵權行為地”,依第一次《沖突法重述》(1934年)解釋為:“構成行為人負侵權行為責任的最后事實發生地。”[10]因此,在產品責任訴訟中,侵權行為地即指損害發生地而不是指缺陷產品制造地。其理論基礎是既得權說(vestedright),即原告不管在何處,都攜帶該法所授予的權利,訴訟法院只不過是被請求支持或協助取得這一權利。[11]上述法律適用規則雖有不可否認的易于操作、簡便高效的優點,但由于損害發生地常屬偶然,與當事人之間并無實質上重大牽連,因此,以侵權行為地法為準據法時,不僅不能促進該州立法目的,而且損及有更重要牽連地的正當政策。因此,美國開始在不違背第一次沖突法重述的原則下,努力避免不合理結果的發生,而試圖以種種借口以法院地法代替行為地法的適用。如法院主張外國法是有關程序方面的,此外法院還可以基于公共政策的理由來拒絕適用行為地法。例如在“Kilbergv.NortheastAirlines,Inc.”一案[12]中,紐約州上訴法院即認為基于該航空公司主營業所的事實,“法院自亦可主張允許飛機制造商逃避本州無過失責任,僅是因為該有缺陷的飛機并未于紐約州墜毀而是在一采過失責任州的領域上空失事,則顯不公平。”從60年代后,絕大多數州都相繼放棄了這個原則,轉而采用最密切聯系原則,該原則來源于美國法學會1972年編訂的《第二次沖突法重述》,該重述第145節規定:1、當事人對侵權行為中的權利義務,應由同該事件及當事人有最密切聯系州的法律決定。2、在確定問題應適用何種法律時,應考慮到聯系是:1)損害發生地;2)引起損害的行為的發生地;3)當事人的住所、居所、國籍、公司的地點和各當事人的營業地點;4)各當事人之間關系集中的地點。該重述指出應考慮爭執的問題、侵權行為的性質以及利害關系國侵權行為法的目的等。其中利害關系國法律內容之分析及立法目的之探究,最有助于確定哪一國成為最具利害關系國。上述方法即柯里“政府利益分析說”[13]的實際應用:即在分析各關系國法律后,常能發現關系國法律并無沖突,也就是說,只有一國因為適用其法律使其政策得以促進,而其他國也沒因此喪失其利益,那么此時即可適用該國法為案件的準據法。[14]如果在分析各關系國法律后,發現會有兩個以上國家的法律因適用其法律,其立法政策會得以促進,則是屬于真實利益沖突的案件,此時應在利害關系分析辦法(或稱功能分析辦法)下,選擇其中一國法律適用,該國法律較之另一國則有利于案件的審理,也更合理公正。
一般來講,在有關產品責任的訴訟中,美國法院傾向于以損害發生地作為最密切聯系因素。然而損害發生地有時很難確定或依損害發生地并不利于保護消費者利益。此時,也可將產品制造地、產品購買地、產品使用地和原告住所地等有聯系的因素作為選擇準據法的因素。在此種情形下,法院往往需要綜合各種有聯系的因素作全面考慮。例如,1971年“麥坎訴阿特拉斯供應公司案”(Maccannv.AtlasSupplyCo.)[15],原告在賓夕法尼亞州購買汽車輪胎,當他在俄亥俄州旅行時,因該輪胎缺陷使原告發生車禍受傷。訴訟地賓夕法尼亞州法院認為傷害發生地不足以說明有最密切聯系。因此法院適用了原告住所地、購買地和法院地法即賓州法律。
從許多判例來看,美國法院對最密切聯系原則的適用是靈活的,多數場合從保護消費者和使用者的利益出發考慮。如在“特考特訴福特汽車公司”案[16]中,原告是羅德島居民,在羅德島為其子因駕駛在麻省購得的汽車在當地與人相撞喪生對被告福特公司,聯邦高等法院在上訴中適用了羅德島法律而非麻省法律時,重點置于“州利益”上。因為羅州與麻省法律有兩點不同:一是羅州法律沒有規定關于非正常死亡可追償的最高限額,能確保對其居民相當充分的賠償;二是麻省未采取嚴格責任制,而羅州則采用了嚴格責任的規定,所以羅州對該案利益是主要的,且對保護其受缺陷產品損害的居民更為有利。但有時,法院也從保護制造商的利益考慮。如1975年加利福尼亞聯邦地區法院審理的1974年3月3日巴黎空難事件案即屬此。[17]當日一架土耳其航空公司的DC-10客機在巴黎附近失事,造成346人死亡。近1000名繼承人和被撫養人在加州對飛機制造商麥克唐納.道格拉斯和飛機機門制造商通用動力公司提訟。由于法國和日本法律規定賠償費較高,多數原告人主張適用飛機失事地法國法律,有些日本籍原告則要求按照日本法律賠償。這些要求均遭到加利福尼亞州聯邦地區法院的拒絕。法院在判決中指出:“加利福利尼州法院將保護居住在其境內的制造者,不允許由于失事地點或人住所的偶然因素而增加對原告人的賠償費”,“應保證使世界上任何人受傷后,能按照飛機設計和制造國的法律得到賠償。”
(二)英國、加拿大
在具有涉外因素的侵權行為訴訟中(包括涉外產品責任訴訟),英國、加拿大的法院過去也適用損害地法,但這種法律不得違反法院地的公共秩序。現在這兩個國家的法院也認為在涉外侵權案件中一律適用損害發生地法并不合適。1971年英國上院的多數法官在審理一起上訴案件時,也贊同適用美國《第二次沖突法重述》中提出的最密切聯系原則。在加拿大,1970年安大略省法院在審理一起有缺陷的美國福特汽車公司制造的汽車案時,也沒有適用損害地法,而適用了汽車出售地法。[18]
(三)歐洲大陸
聯邦德國、法國和荷蘭等國法院在審理國際產品責任案件時,一般都適用法院地的本國法。
德國有關法律選擇的案例很少,然而在一些實體法案件中也存在潛在的法律沖突因素。1974年德國一初級法院審理一涉外案件,該案原告從西柏林購買了一輛法國制造的標志汽車,當他駕車在瑞士旅行時,由于汽車結構上有缺陷而致傷害。該案的問題是被告,即西柏林的法國汽車結構上有缺陷制造商的子公司,是否應按照德國制作商的有關制造結構缺陷的責任標準承擔責任。法院對此持否定觀點,認為任何產品責任訴訟都應直接針對法國的母公司。法院在作上述決定時,并沒有進行法律選擇,而實際上所采用的仍是德國的法律。
法國在適用法律方面也沒有代表性的判例。1975年,一名法國試飛員駕駛的直升飛機與一架法國滑翔機相撞,致使飛行員死亡,其妻被告美國加利福尼亞的飛機制造商,指控其飛機控制系統存在缺陷并要求對其經濟及精神損失予以賠償。法院審理該案時,首先以法國法律為根據,認為原告應證實失誤的存在。在認定不法責任方面,法院認為必須適用缺陷發生地法律,即加利福尼亞法律,然而由于沒有證明飛機存在設計上的缺陷,所以也未適用加利福尼亞的法律。[19]
荷蘭一地方法院在1976年審理過一起涉外產品責任案件時,就適用了荷蘭法律。盡管負有過失責任的制造者主要營業地在原聯邦德國,但荷蘭法院認為侵權行為發生地及受害人住所地均在荷蘭,故應該適用法院地法即荷蘭法。[20]雖然荷蘭在1979年9月1日,批準了1973年訂立于海牙的《產品責任法律適用公約》,但該公約只是對荷蘭的有關理論產生了深遠影響,對于荷蘭國際私法的實踐卻影響甚微。
由上述事實可知,之所以德、法、荷三國往往適用法院地法,究其原因是與借口侵權行為適用侵權行為地法擴大法院地法(大多數場合侵權行為地就是法院地)的適用分不開的。對傳統的撼動和突破自然也必須從產品責任法律適用所依據的原理——一般侵權行為法律適用規則入手。今天,雖然侵權行為地法仍在歐洲各國司法實踐中居主導地位,但“什么構成侵權行為地法的補充和例外”則是與傳統原則迥異其趣的。歐陸各國摒棄了傳統原則中把侵權行為地法作為單一、僵硬的做法,轉而適用以侵權行為地為主,同時根據“政策導向”、“被害人導向”等政策因素考慮采用法院地法、當事人共同本國法、當事人意思自治、最密切聯系地法等法律選擇規范。其中,最能得到一致承認的例外是當事人共同本國法或稱當事人共同屬人法。如1979年《匈牙利國際私法》第32條規定:“侵權行為適用侵權行為地法,如果侵權行為人與受害人的住所位于同一國家的,適用該共同住所地發法。”現在除了法國、捷克在立法和實踐中不愿采此一例外外,其他國家均予以承認。適用當事人共同本國法的一個主要問題是,有時單純依靠住所或國籍不一定能反映事實上的聯系,為了彌補這一缺陷,瑞士1988年公布的《瑞士聯邦國際私法》第133條規定:“如果加害人與受害人在同一國家有共同慣常住所時,侵權責任受該國法支配,”“如果加害人與受害人在同一國家沒有共同慣常住所時,這種訴訟應受侵權行為地法支持。但是,如果損害結果發生于另一國,并且加害人可以預見到損害將在該國發生時,應適用該國法。”這樣,比單純依靠國籍和居所更為合理。其他一些例外情況也已得到歐洲多數國家的承認,并以成文法的形式加以肯定。例如,1979年生效的《奧地利聯邦國際私法法規》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最密切聯系原則作為立法的理論依據。該法規第48條第一款規定:“非契約損害求償權,依造成此種損害的行為發生地國家的法律。但如所涉的人均與另外同一國家的法律有更強聯系時,適用該另一國家的法律。”1982年公布的《土耳其國際私法和國際訴訟程序法》對侵權行為法律適用的規定,和上述奧地利法有相似之處。該法第25條規定:“非合同性的侵權行為之債,適用侵權行為實施地法律,當侵權行為的實施與損害結果位于不同國家時,適用損害結果發生地法律。因侵權行為而產生的法律關系與他國有更密切聯系時,則適用該國的法律。”1988年公布的《瑞士聯邦國際私法》,把侵權行為區分為一般的和特殊的,而分別規定其法律適用。在特殊侵權行為中又細分為公路交通事故、產品責任、不當競爭、妨礙競爭以及因不動產產生的有害影響和基于傳播媒介對個人人格的損害等6種,并分別規定了其法律適用。同時,該法規還把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首先引入侵權行為法律適用領域。其第132條規定:“當事人可以在侵權行為出現后的任何時候,協議選擇適用法院地法”。盡管該規定只賦予當事人有限的意思自治,當事人協議選擇適用的法律也只能是法院地法,但畢竟突破了意思自治原則僅僅是合同準據法的原則的傳統觀念,第一次在侵權行為法律適用領域采用了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具有積極進步的意義。
通過對以上各國產品責任訴訟法律適用的分析和比較,我們可以對當今世界相關國際通行規則的變化發展趨勢作如下歸納:
總體上看,在涉外產品責任的法律適用上,不少國家拋棄了機械的、單一的法律選擇方法,而主張采用靈活多樣的規則和方法來確定準據法。在法律選擇的過程中,往往透過法律沖突的表面假象去分析法律所體現和保護的政策和利益,同時強調法律適用的結果,從立法上更加追求對當事人的公正待遇和平等對待。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將最密切聯系原則引入侵權責任領域,使涉外產品責任法律適用日趨靈活。傳統沖突法的盲目性及其所提倡的那種機械、呆板的單一連接因素分析方法從根本上忽視了某一類案件(如產品責任案件)事實構成上的復雜性、特殊性,以及根本上忽視(甚至有時故意漠視)對與案件具有聯系的法域的法律內容進行分析。因此,為保證對案件當事人的公正性,體現法律上的正義,不僅要對每一個具體案件的事實構成進行分析,而且法律選擇上必須提倡多個開放的連接點,以排除單個封閉的連接點所不可避免的偶然性。法官可以在政策分析、利益比較、結果選擇的基礎上決定何國法律與發生“損害事件”有最重要關系及與發生“損害事件”當事人有最重要關系,就適用該國法律,這就是最密切聯系原則在侵權責任領域內適用的涵義。在最密切聯系原則引入侵權責任領域的基礎上,英國莫里斯于1951年就在《哈佛法律評論》上發表的《論侵權行為自體法》一文中提出“侵權行為自體法”的概念,對侵權行為地法、法院地法以及當事人屬人法加以綜合考慮,以使其能夠顧及各種例外情況。這種方法是對傳統國際私法上侵權行為法律適用的改革,它顧及到侵權行為地法之外法律的可適用性,但又不是機械地重疊適用。
其二,以保護受害人利益為導向,在涉外產品責任訴訟中適用有利于受害人的法律或直接在立法上肯定對受害人利益的保護。前者如美國法院在德克爾訴福克斯河拖拉機公司案(Deckerv.FoxRiverTractorCo.)的判決中“適用的較好的規則”,事實上也就是能使原告從被告那里獲得賠償的規則,可以說是“最有利于原告”原則的貫徹。[21]后者如1979年《匈牙利國際私法》第32條第2款規定:“如果損害發生地法對受害人更有利,以該法作為準據法。”我們知道,每一個時代侵權實體法都有自身的立法目標、政策導向和價值訴求,侵權行為沖突規范雖然不是直接規定當事人的權利義務,但必定受到以上實體因素的制約決定,故現代社會化生產條件下的消費者、使用者相對于生產者、銷售者的弱勢地位就要求產品責任法律適用上突出保護受害人的權益。正如Reese教授所說:“當一項基本政策或者所在涉及的多項政策均導向同一趨勢時,……法律選擇法則成效的主要標準是它能達成‘促進主要的政策和多數政策’到什么程度……幾乎全世界所有國家的‘產品責任法’趨勢都是有利于原告,而加諸給制造者更嚴厲的責任。”[22]
其三,“排除被告不可預見的法律的適用”原則已逐漸被各國在涉外產品責任法律適用制度上接受。如前述《瑞士聯邦國際私法》第133條規定了適用損害發生地法律須以加害人可以預見到損害將在該國發生為條件。又如海牙《產品責任法律適用公約》第7條規定了如果被請求承擔責任人證明其不能合理預見該產品或同類產品經商業渠道在損害地國或直接受害人慣常居所地國出售時,則該兩地法律均不得適用。這樣的規定一方面排除了產品損害發生地及受害人慣常居所地的偶然性使被告承擔不公正責任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體現了平等對待原、被告雙方當事人,顯示出法律選擇對雙方當事人利益兼籌并顧。
其四,將有限的意思自治引入侵權責任領域,尊重產品責任當事人的自主意愿來選擇適用的法律。如前述1988年公布的《瑞士聯邦國際私法》規定了當事人可以通過協議方式選擇適用法院地法。又如1995年《意大利國際私法》規定,侵權責任應由損害結果發生地國法律支配,但受害人可以要求適用導致損害的行為發生地國法律。海牙《產品責任法律適用公約》第6條亦規定,如果按第4、5條指定適用的法律均不適用,原告可以主張適用侵害地國家的法律。規定有限意思自治的好處之一即是當侵權行為準據法為外國法時,通過當事人的協議可以選擇適用法院地法,即中國法,從而可以起到巧妙地達到規避外國法適用的功效,進而維護法院地國的司法和公共秩序;另一個好處是保護了產品責任受害人的切身利益,使產品責任之訴更具“私權之訴”的性質。
三、我國涉外產品責任法律適用制度的健全
一方面鑒于我國涉外產品責任法律適用制度具有以上種種缺陷,另一方面考察了國際上產品責任法律適用的通行規則,筆者認為應及時健全和完善我國相關立法,否則越來越多的國際產品責任糾紛將會難以解決或無法解決,勢必影響我國的國際經貿往來,對我國出口企業及消費者權益保護都極為不利。
健全和完善相關立法的途徑有二:
其一,適時加入海牙《產品責任法律適用公約》。該公約為了統一各國在產品責任法律適用方面的分歧,采用了一種較為科學合理的法律適用制度,其特點如下:
(1)該公約規定了五種連接因素作為法律適用的連接點,即損害發生地、直接受害人慣常居所地、被請求承擔責任人的主營業地、直接受害人取得產品所在地以及當事人的選擇。
(2)該公約規定了一個法律要成為準據法至少需要兩個以上連接點作為條件。比如僅有損害發生地這一因素還不能適用損害發生地法,只有當損害發生地同時又是直接受害人慣常居所地或被請求承擔責任人主營業地時,方可適用損害發生地法。所以,在實際上,公約并非適用的是損害發生地法,而是損害發生地與其他連接因素地法的組合適用。
(3)該公約規定了四個獨一無二點法律適用順序:第一適用順序即該公約第5條規定,關于涉外產品責任的準據法首先應該適用直接遭受損害的人的慣常居所地國家的內國法,只要該國同時又是1)被請求承擔責任人的主營業地;或2)直接遭受損害的人取得產品的地方。第二適用順序即如果不存在公約第5條規定的情形,則按該公約第4條規定,適用的法律應是損害地國家的內國法,但也需要符合下列條件之一:1)該國同時又是直接遭受損害人的慣常居所地;或2)該國同時又是被請求承擔責任人的主營業地;或3)該國同時又是直接遭受損害的人取得產品的地方。第三適用順序即該公約第6條規定,如果第4、5條指定適用的法律均不適用,原告可以主張適用損害地國家的內國法。第四適用順序則規定,如果第4、5條指定適用的法律都不適用,并且原告沒有提出主張適用損害地國家的內國法時,則適用被請求承擔責任人的主營業地國家的內國法。
(4)該公約著重體現了對當事人意愿的尊重,這不僅表現在原告在第三順序中可以選擇損害發生地,還表現在它對被告作了恰當地保護,即如果被請求承擔責任人證明他不能合理地預見該產品或同類產品會經商業渠道在該國出售,則第4、5、6條規定的侵害地國家和直接遭受損害人的慣常居所地國家的內國法均不適用,而應適用被請求承擔責任人的主營業地國家的內國法。
公約還規定了四個必須遵循對共同條件:第一,適用第4、5、6條時不應不考慮產品銷售市場所在國家通行的有關行為規則和安全規則(第9條);第二,根據該公約規定,適用的法律只有在其適用會明顯地與公共秩序相抵觸時方可拒絕適用(第10條);第三,即使應適用的法律是非締約國的法律,本公約應予適用(第11條);第四,該公約規定應適用的法律是指該國的內國法,排除了反致的適用。
關于中國是否應該加入海牙《產品責任法律適用公約》的問題,國內學人主要有兩種對立觀點:一種是中國不宜加入該公約或加入該公約不具可行性。理由是,該公約是法國、德國等傳統國際私法與英美國家新沖突法相互妥協相互制約下的產物,更多地從經濟科技發展水平相差不遠的發達工業國家的利益出發,幾乎沒有考慮發展中國家的特殊立場;此外我國國內產品責任實體法與公約中規定的實體內容如產品的范圍、產品責任承擔者的范圍仍有一定差異,尤其認為在我國對產品責任賠償標準規定較低的現狀下,加入公約將對我國出口生產企業造成損失和負擔,因為我國出口產品的質量現在還落后于發達國家,往往不能滿足發達國家的“無缺陷”標準,企業因產品質量問題涉訴也就不足為奇。問題在于按照公約的硬性法律適用的順序,我國產品在外國造成損害只能適用該外國法即“直接遭受損害的人的慣常居所地國家的國內法”,往往就是發達國家的法律,而這些國家的法律對產品責任者苛以嚴厲處罰。由于我國產品責任賠償的標準低,按照公約規定,原告有權基于侵害地國家的國內法提出請求,否則適用的法律為被請求承擔責任人的主營業地國家的法律,但是我們不能寄希望于外國原告放棄適用其遭受侵害地國的外國法律,轉而適用賠償標準既低又采取不完全嚴格責任的產品歸責原則的我國法律。同一道理,當外國產品在我國給我國消費者造成損害時卻只能按公約的第一適用順序適用賠償標準較低的原告慣常居所地國我國法律,往往對我國消費者使用者的利益不能很好地保護。相反的觀點是加入該公約是我國目前的當務之急。中國應盡早地加入該公約。理由是,該公約雖由少數發達國家擬定,但貫穿其中的吸收了各國最先進的立法原則的法律選擇方法無疑是科學、合理的,恰恰反映了全球化市場經濟條件下產品生產、流轉、消費的客觀經濟規律;公約在制度設計上大體平衡,兼顧了原被告雙方當事人的利益,既保護受害人的利益(公約第6條),又保護被告不受不可預見到或不公正的法律的影響。至于適用公約對我國出口企業處罰過重或對我國消費者利益保護不當情形的出現并非由于公約本身有何欠缺,恰恰是因為我國產品責任實體法的缺陷所致。
筆者基本贊同第二種觀點,但主張加入《產品責任法律適用公約》不可操之過急,應當適時加入。的確,該公約適用于各發達國家之間所產生的結果是公平的,當事人選擇法律的機會是均等的,但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就會出現上述情況,尤其在發展中國家自身國內立法不完善的條件下和加入公約后的短期內,情形對發展中國家企業和消費者更為不利。況且公約除了時效規則和聲明公約不適用于未經加工的產品兩項保留外,不允許締約國做任何其他保留,意味著加入公約就是接受現有的既定的游戲規則,一日之間與國際“接軌”。以上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我們不能忽視它,但是更需要我們正視的是:質量才是產品真正的生命。而質量檢驗的標準來自于市場,沒有市場壓力和刺激(包括對產品質量的懲罰機制),是很難提高產品質量的,更不要說具有國際競爭力了。產品質量不過關,靠法律或政治上的保護,只能在短期內有效,最終影響我國對外經貿往來。更深層的負面影響是不利于我國健全市場經濟體制,推進市場經濟法治。尤其是在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不得不參與到全球化的市場競爭中去,因而不得不在制度上借鑒吸收國際通行規則,在參與中提高自己、壯大自己、完善自己。從短期看,加入公約的確會給我國出口企業造成壓力和負擔,甚至是巨大的,也會對我國消費者的利益保護不充分。但隨著我國產品責任實體法的完善和與國際公約慣例趨同以及企業產品質量意識的增強,必將促進我國對外經貿往來,公平地對待我國與外國產品責任當事人。何謂“適時加入”,這不僅是個時間問題,也是個觀念問題,恰恰是觀念的更新促成時機的成熟。在不過分強調狹隘的視角和短期利益的前提下,我國目前已初具加入公約的法律條件,即我國產品質量法的修訂是最重要大法律條件,新法在很大程度上縮小了與發達國家的差別。但加入公約的經濟條件尚不夠成熟,即產品質量法貫徹實施還需要一段時間、企業的產品質量意識還有待提高、市場秩序還應進一步清理完善。這就不單是立法所能解決的問題了,關鍵在于執法與司法環節。
其二,加快將我國涉外產品責任法律適用專項立法提上議事日程。這也是一個有效途徑,并且可與加入海牙《產品責任法律適用公約》并行不悖。
為此,我們應當注意避免一些國家在立法中的不良傾向與缺陷:第一,適用法院地法的趨向明顯增強。與其說適用法院地法是公共秩序、公共利益的需要,莫如說其背后隱藏著公平與效率這對矛盾的取舍問題。“法律是一種地方性知識”,[23]所以適用法院地法無疑是最有效率的。在最密切聯系、政府利益分析等學說中,擴大法院地法適用傾向較明顯,這就為法官適用法院地法制造了理論依據。同時,法律允許當事人根據有限意思自治原則通過協議選擇適用法院地法,更加強了法院地法適用的可能性。第二,法律適用標準主觀化傾向。由于法律適用規則多傾向于政府利益或政策考慮等寬泛的無明確含義及范圍的原則,法律選擇適用方法則留給法官在具體案件中依其經驗和對法律的理解來確定。因此,對于同樣的問題有可能因不同法官的理解不同而做出不同的判定。這樣在一定程度上勢必不利于對當事人利益的保護。第三,當事人任意挑選法院(ForumShopping),往往選擇有利于自己的法院管轄,這樣可能會出現任意選擇法律適用的現象,加之法院經常選擇法院地法作為審案的準據法,這就產生一種后果,使原告能選擇的不僅是更方便的法院而且是最為有利的法院。
從形式上看,可以將專項立法納入我國產品質量法中獨立為“涉外產品責任法律適用”一章,也可以在我國將來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私法》中做出專門規定。
最后,值得肯定的是,中國國際私法學會的有關專家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私法示范法》(2000年第6稿)對我國涉外產品責任的法律適用作了專門規定。示范法第121條規定:“產品責任的損害賠償,當侵權行為地同時又是直接受害人的住所和慣常居所地,或者被請求承擔責任人的主要辦事機構或營業所所在地,或者直接受害人取得產品的地方時,適用侵權行為地法。如果直接受害人的住所或慣常居所地同時又是被請求承擔責任人的主要辦事機構或營業所所在地,或者直接受害人取得產品的地方時,產品責任的損害賠償,也可以適用直接受害人的住所地法或慣常居所地法。”[24]其第112條規定:“侵權行為地法包括侵權行為實施地法與侵權結果發生地法。侵權行為實施地法與侵權結果發生地法規定不同的,適用對受害人更為有利的法律。”[25]由此可見,示范法規定在采用組合連接因素、注重最密切聯系原則、加強對消費者的保護等方面與海牙《產品責任法律適用公約》的精神基本一致,但仍存在顯著差別:一、示范法承襲了我國《民法通則》“侵權行為地法”概念,雖然不似公約“損害發生地國內法”具有確定性和可預見性,卻能發揮靈活性的作用,擴大準據法的選擇范圍;二、公約采用的是按順序的連接點組合適用,而示范法在侵權行為地法與直接受害人的住所地法或慣常居所地法之間是選擇適用的關系。此種規定對于外國產品在我國境內對我國消費者造成損害的賠償認定是極為有利的,避免了公約對此情形只能強制實施損害賠償較低的我國法律的弊端。筆者對示范法有三個看法及建議與大家商榷:一是關于侵權行為地的認定上建議由受害人選擇何者是對其有利的法律,而非法院徑自決定哪一種法律是“對受害人更為有利的法律”;二是建議將“排除被告不可預見的法律的適用”這一公約規則吸收進示范法,以反映法律適用對當事人雙方利益保護的平衡;三是關于示范法第117條規定的“有限雙重準則”的問題,該條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發生的侵權行為,以外國的法律為準據法時,在侵權行為的認定及在損害賠償限額方面,該外國法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規定相抵觸的,不得適用。”[26]筆者的看法是雖然該原則對于類比于刑事違法的一般民事侵權來說,具有重大意義,但由于涉外產品責任的特殊復雜性,在操作中不宜作為特殊的產品責任法律適用的一般原則,而只能在考察個案與法院地國聯系之密切程度的基礎上決定是否對其加以法院地法或當地公共政策的限制,作為例外而生其效力。
【注釋】
﹡郁雷,南京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
[1]、林燕平:《對完善中國涉外產品責任法律的思考與建議》,《法學》1999年第7期。
[2]主編:《國際經濟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66頁。
[3]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編第2章29條規定:“因侵權行為提起的訴訟,由侵權行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據此,我國涉外產品責任管轄權基礎有兩種:一是某產品責任案件只要涉及在中國有住所、居所、代表機構、營業所或在中國登記成立的外國被告,我國法院即有管轄權;二是侵權行為實施地或侵權損害發生地有一項發生在中國境內就受中國法院管轄。所以,中國人在外國境內遭受產品責任侵權至我國法院,我國法院一般不予受理。
[4]SeeCheshireandNorth,PrivateInternationalLaw,12thed.(1992),pp.552-557.
[5]BGH[1981]NJW1606f.
[6]參見美國法學會:《第二次沖突法重述》,第145節。
[7]參見(臺)馬漢寶編:《國際私法論文選集》(下),五南圖書出版公司,第117頁。
[8]參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1989年第1號。
[9]李雙元、鄧杰、熊之才:《國際社會本位的理念與法院地法適用的合理限制》,《武漢大學學報》(社科版)2001年第5期。
[10]AmericanLawInstitute’sRestatementofConflictofLaws,§332(1934).
[11]韓德培主編:《國際私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05頁。
[12]Kilbergv.NortheastAirlines,Inc.,9N.Y.2d34,(1961).
[13]Currie,SelectedEssaysontheConflictsofLaws,1963,p.229.
[14]此種情形稱為“虛假的沖突”。Traynor,IsThisConflictReallyNecessary?37,TexasL.Rew.657(1959).
[15]Maccannv.AtlasSupplyCo.,325F.Supp.701(W.D.Pa.1971).
[16]Turcottev.FordMotorCo.,494F.2d,173(1974).
[17]美國《聯邦地區法院判例補編》,第399卷,1975年版,第732頁。
[18]Tebbens,InternationalProductsLiability,1980,theHague,p.290.
[19]Tebbens,InternationalProductsLiability,1980,theHague,p.109.
[20]DCZwolle,February18,1976,23NILR364(1976).轉引自袁泉著:《荷蘭國際私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07頁。
[21]韓德培主編:《國際私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07頁。
[22]Reese,ProductLiabilityandChoiceofLaw:TheUnitedStatesProposaltotheHagueConference,25Vand.L.Rew,1972at10,38.
[23]“地方性知識”這個概念來自于美國人類學家吉爾茨,他主要用它來描述法律知識所具有的本土文化特性。參見克林福德•吉爾茨:“地方性知識事實與法律的比較透視”,鄧正來譯,載梁治平(編):《法律的文化解釋》,北京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73-171頁。
[24]中國國際私法學會:中國國際私法示范法(第6稿)第121條。
法律適用論文范文第2篇
一、洗錢罪的上游犯罪的若干問題
(一)洗錢罪的上游犯罪的界定全國公務員共同的天地-盡在()
在談論洗錢罪常常涉及到上游犯罪和下游犯罪兩個概念。由于洗錢行為一般是將販毒、走私、黑社會、貪污賄賂、詐騙等犯罪所得和收益通過復雜的交易手法轉變為表面合法化的財產。因此,我們將能夠獲得資金收益并直接誘發洗錢動機的犯罪稱作上游犯罪,而將洗錢罪稱作下游犯罪。如果要準確的把握洗錢罪,應該首先界定洗錢罪的上游犯罪。“上游犯罪”范圍的界定,大致有四種做法:一是將“上游犯罪”的范圍限制在某些特定的犯罪。如意大利1978年刑法典將洗錢罪的范圍限制于搶劫、敲詐或詐騙以及綁架犯罪;二是將“上游犯罪”的范圍限制為犯罪。比如法國在1994年生效的刑法典,也正是為了遏止犯罪這個初衷而設立洗錢罪。但是由于這種做法使洗錢罪范圍過窄,基本上已被大多數國家所拋棄;三是將“上游犯罪”的范圍擴大到了所有的犯罪;四是將“上游犯罪”的范圍泛化到所有的違法行為,只要行為人實施了將非法獲取的貨幣資金或其他財產合法化的行為,就構成洗錢罪。1從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將洗錢罪的修改來看,我國應該屬于上述四種分類中的第一類。不過有關立法部門已經把立法重心有所擴大,把法律制裁的著力點轉移到打擊洗錢犯罪的實際需要和有利于加強打擊洗錢犯罪的國際合作需要這個出發點上來了。但是目前國際反洗錢立法的趨勢已經是對一切犯罪所得的清洗行為定罪,即不限定上游犯罪范圍。而我國現行刑法將洗錢罪的上游犯罪限定為犯罪等七類犯罪,范圍明顯過窄,這一限制既不利于反洗錢犯罪的國際協助和合作,也不利于有效預防和打擊洗錢犯罪及其上游犯罪,實踐中對某些案例處理已經缺乏刑法依據,已不能適應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
(二)在現實法律操作中,狹窄的上游犯罪可能會造成罪刑不相適應。
在黑社會性質的犯罪中,可以包括盜竊、搶劫、搶奪等的犯罪,而這些犯罪往往伴隨著收益,所以,上述的這些犯罪是可以成為洗錢罪的上游犯罪的。但是在一般情況下,盜竊、搶劫、搶奪等犯罪又是不歸屬于洗錢罪的上游犯罪的。我們可以看出這些犯罪單獨發生不能作為洗錢罪的上游犯罪來對待,以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身份出現卻能夠成為洗錢罪的上游犯罪。這樣情形勢必會導致同罪異罰的現象發生,有違罪刑均衡原則。再如海南黃漢民案中犯罪嫌疑人黃漢民非法侵占了他人家族企業一億多元資產,并采取欺詐開戶、虛假過戶、虛假交易、暗箱操作等手段據為己有。全國公務員共同的天地-盡在()黃漢民通過各種手段,隱瞞、掩飾犯罪所得及其非法收益,使其合法化,完全符合洗錢罪的通常定義。然而,限于我國刑法對洗錢犯罪的上游犯罪限定,因此,但檢察院卻不能以洗錢罪而以誣告陷害罪和職務侵占罪提訟。該案僅僅以上游犯罪對嫌疑人偵查、,極易導致處罰過輕的結果,也明顯違反了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悖離了《刑法》有效保護人民、懲罰犯罪的基本立法原意。這反映出我國有關立法已經嚴重不適應打擊日趨猖獗的洗錢犯罪的刑事司法實踐,反洗錢立法亟須完善,因為“正義乃是對法律的正確適用”。
(三)擴大上游之于洗錢罪的預防。
上游犯罪作為洗錢犯罪的“對象性犯罪”,與洗錢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但是從預防犯罪的角度看,如果只有針對性的限定上游犯罪,那是否意味只要不是刑法所限定的洗錢罪的上游犯罪的非法收益,便可以大膽的進行清洗呢?這于情于理都說不通。所有的犯罪分子從事經濟犯罪的考慮之一便是他能夠預見到可以使用多少非法所得,假設犯罪行為人認識到非法所得的使用或者清洗困難,銀行或司法機關會格外注意,那么他犯罪的原動力就會少得多。由此可見,擴大洗錢上游犯罪的范圍,是打擊這些上游犯罪的重要手段。鑒于洗錢行為所具有的獨立性特征和嚴重社會危害性,筆者認為上游犯罪的范圍擴大到所有能夠產生違法所得的犯罪。
二、司法中對于“明知”的的內容、程度的把握
根據刑法的規定,行為人要具有特定的“明知”,即“行為人明知是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恐怖活動犯罪、走私犯罪、貪污賄賂犯罪、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詐騙犯罪的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所以,對“明知”的把握至關重要。但是對于“明知”如何把握,以及“明知”的程度和判斷標準如何界定該規定沒有作出相應的解釋,這給執法人員在實際辦案中增加了難度
(一)明知的內容
“明知”的內容學界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只要行為人具有認識其經手的資產是犯罪所得這種可能性,或者有足夠的理由認為可能是犯罪所得就足以成立“明知”。顯然,這種觀點認為洗錢罪主觀上的“明知”并不將其內容限定為特定種類犯罪,只要行為人“明知”的是犯罪所得就足夠了。另一種觀點認為,“明知”的內容僅限于為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恐怖活動犯罪、走私犯罪、貪污賄賂犯罪、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詐騙犯罪的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如果行為人誤認為是合法的財產或收入而提供賬戶協助將資金匯往境外等行為的全國公務員共同的天地-盡在(),則不構成犯罪。也就是說“明知”的內容不僅是犯罪所得,而應是上述七種犯罪所得。雖然筆者認為應當把洗錢罪的上游犯罪擴大到所有能夠產生違法所得的犯罪,但是就目前的司法實踐中對于“明知”的運用來看還是前一種觀點較為合理。因為在《反洗錢法》第3條也將“明知”的內容限為特定的7種犯罪的違法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由此可見,對犯罪嫌疑人的主觀心態“明知”的查明是整個反洗錢刑事訴訟的臨界點。
(二)明知的程度
在刑法學界對于“明知”的程度亦有幾種不同的觀點。但是從法律在實際中的適用的角度來看,明知應當包括“知道或者應該知道”。理由有如下幾層:
1.司法解釋給我們提供了理解“明知”的依據。司法解釋認為,“明知”包括“知道”和“應當知道”。在《關于辦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解釋》中,對于銷贓罪的“明知”是有具體規定的,即不能光靠被告人的口供判斷,應當結合案件的客觀事實加以分析,只要證明被告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是犯罪所得的贓物而窩藏或代為銷售的,就可以認定是銷贓罪。所以可以看出,司法機關完全可以根據案件的客觀事實而進行判斷行為人的行為是否屬于“明知”的。
2.是法律實踐的客觀需要。在上游犯罪中,行為人對于自己的非法收益應該是明知的,所以他們清洗犯罪所得的行為是一種事后不可罰的行為。在刑法中,犯罪成本是行為人實施犯罪的重要標桿,如果他人知道需要漂洗的是非法收益,那么犯罪成本就會大幅度的增加,因此在現實生活中,上游犯罪行為人不但不會交代非法收益的具體來源,在行為人將非法收益交由他人清洗漂白時,其必定會竭力掩飾其所得為違法犯罪所得。所以,從目前法律的社會需求來看,洗錢罪中的“明知”,包含兩層含義,即“知道”和“應該知道”。
3.是國際立法的大勢所趨。事實上,在國際立法中,肯定以推定的方法來證明“明知”存在的規定是非常普遍的。例如,聯合國《與犯罪收益有關的洗錢、沒收和國際合作示范法》(1999)對洗錢行為進行定義時指出:“作為洗錢犯罪要素的知曉、故意或企圖可通過客觀事實環境推知。”可以看出,在打擊洗錢犯罪日益重要的今天,推定犯罪嫌疑人“明知或者應當明知”這一看法應該是順應歷史洪流而對刑法做出的正確解釋。
值得注意的是,對于一些特殊主體來說,其“明知”的含義應當重新的加以定義,對于該特殊主體的要求應該更加嚴格。現在我國刑法中規定的洗錢罪的主體為一般主體,包括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工作人員和非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對這兩類人來說,由于熟悉金融業務,其自身對于洗錢罪認識應以行為人從事職業活動所要求的一般業務能力作為判定“應當知道”為票據。
三、與相似犯罪的區別
在司法實務的實踐中,行為人在實施洗錢行為同時又可能實施窩藏、轉移、收購、銷售贓物的行為,涉及洗錢罪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或者介于二者之間。在司法實務中,此罪是存在同和性的,是普通罪名和特殊罪名的關系,從現實司法實際中,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方面進行甄別:先看這種違法處理犯罪所得的這種行為與取得這種違法所得贓物的行為在犯罪前是否有犯意聯絡,如果有,那么這種情況就直接是取得贓物犯罪行為的共犯,所以也不必再去區分這種贓物處理是洗錢罪還是贓物罪。如果事先未進行通謀,則有必要進一步分析。此時,不妨去看這種處理贓物行為的犯罪對象,如果這種犯罪對象是在刑法規定的洗錢罪上游犯罪的那7種違法所得,那么毋庸置疑可以認定此罪為贓物罪。如果是洗錢犯罪的上游犯罪的違法所得,那就從這種處理贓物的行為方式上去看犯罪嫌疑人有沒有采用的掩飾、隱瞞等手段使其違法所得具有合法性的行為,如果有,則為洗錢罪。反之,則為一般的贓物犯罪。不過現實中某些犯罪行為是想像競合的,對這種情況,應當適用特別法優于以一般法原則。
法律適用論文范文第3篇
實踐中,不符合法定程序收集的、可能影響司法公正的其他證據如電子數據是否屬于立法上需排除的非法證據?有一種觀點認為,電子數據常常是以書證、物證形式存在,應適用刑訴法第54條,但筆者認為,電子數據不是書證,也不是物證。理由是:
1.刑訴法第48條已將“電子數據”規定為一種證據類型,明確寫入法律,確立了電子數據的獨立地位,可見,電子數據不是物證、書證,盡管在某些時候形式上體現為物證、書證。
2.2010年“兩高三部”聯合《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時,采用羅列的方式分別明確了對書證、物證、電子證據的審查內容,即要審查電子證據存儲磁盤、存儲光盤等可移動存儲介質是否與打印件一并提交;是否載明電子證據形成的時間、地點、對象、制作人、制作過程及設備情況等五項內容,這種羅列也說明,電子數據不同于物證、書證。
3.《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的解釋》中第94條專門規定了電子數據的審查、適用規則,明確規定“電子數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一)經審查無法確定真偽的;(二)制作、取得的時間、地點、方式等有疑問,不能提供必要證明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這一規定,對電子數據也是區別于書證、物證看待的。
實踐中,電子數據在收集上存在諸多違法和不規范的情形,因電子數據本身的無形性、易損性、依賴性、智能型等特點,因違法取得和不規范取得往往會導致案件無法偵辦,影響公正。對于這些“非法證據”應怎樣依法確定和排除亟待作出明確解釋。
法律適用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 旅游文化 旅游產業 發展 作用
2010年,文化部聯合國家旅游局《關于促進文化與旅游結合發展的指導意見》,指出:文化是旅游的靈魂,旅游是文化的重要載體。加強文化和旅游的深度結合,有助于推進文化體制改革,加快文化產業發展,促進旅游產業轉型升級,滿足人民群眾的消費需求;有助于推動中華文化遺產的傳承保護,擴大中華文化的影響,提升國家軟實力,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隨著我國旅游業的興起和迅猛發展,文化在旅游業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重要,它正在成為整個旅游業的靈魂和支柱,決定著旅游業的發展方向和興旺。與此相適應,旅游文化的研究也正在向縱深發展,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其內容亟待建設和完善。因此,深入探討旅游文化的特征及其在旅游業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意義。
一、發展鷹潭市旅游文化有利于鷹潭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促進全市經濟社會平穩發展。
利用中國五千年的悠久歷史文化,把旅游經濟搞活,已經成為一條公認的、行之有效的經驗。2008年下半年以來,國際金融危機引發的全球經濟下滑深刻影響到世界各個角落,許多產業發展陷入困境。在世界旅游產業一片蕭條的背景下,我國旅游產業卻保持著強勢增長,國內旅游需求旺盛。2008年,全國接待國內游客17012億人次,比上年增長6.3%;國內旅游收入8749億元,比上年增長12.6%。旅游業之所以獲得了這樣大的發展,主要是因為我們在發展旅游業的同時,充分利用了中華民族的悠久歷史文明。文化搭臺,經濟唱戲,已經成為中國近年來發展旅游業的最大特色和主要經驗之一。大量事實證明,挖掘、利用、弘揚傳統文化,能夠推動旅游業發展。我國許多地區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取得了巨大成功。例如,山東濰坊的“國際風箏會”,山東曲阜的“孔子文化節”,東北通化的“葡萄酒節”,四川的“國際龍舟”活動,菏澤和洛陽的東西牡丹盛會,等等,這些都把中國的古老文化與現代旅游相結合,收到了很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可見,旅游文化對旅游經濟的作用是巨大的。
近年來,鷹潭市委、市政府把旅游業列為全市“三項重點工程”之一,提出構建“以龍虎山景區為龍頭,市區為腹地,貴溪、余江為兩翼,道教文化為特色,吃、住、行、游、娛、購相配套,景區、市區聯動,旅游、文化互動”的全市大旅游格局。遵循這一發展思路,鷹潭在旅游開發中,十分注重鷹潭文化與旅游業融合,既可以發揮文化產業的特長,又可以發揮旅游產業的優勢。由于旅游業綜合性強、關聯度大、產業鏈長,能夠影響、帶動和促進與之相關聯的多個行業發展。
二、發展鷹潭市旅游文化有利于發揮鷹潭市的比較優勢,構建鷹潭城市未來核心競爭力。
隨著社會文明的進步,人們對精神生活的需求愈發強烈,旅游者將愈來愈不滿足于山水景物的淺層觀賞,而追求從文化的高品位上,從我國的自然、人文景觀與華夏民族文化的契合點上去獲得一種審美愉悅,去探求認識生活、美化心靈的真正價值,這其中當然包括從旅游文化作品中尋求并且感悟我們民族的文化底蘊和厚重美感。就國際旅游業的整體而論,由游山玩水的單一目的到增進友誼、推動文化交流的多元化選擇,由風景觀光熱潮到民俗文化旅游熱潮的變化發展過程是十分明顯的。今天的旅游業,無論是其外形,還是其內涵,只有體現出各種不同的文化特點時,才更能吸引旅游者。而一般說來,文化的差異越大,所引動的旅游行為的內驅力就越大。最富于民族文化特點的旅游項目,往往是最受歡迎的。我們應該正視和把握這一規律和趨向,才不會在國際旅游業的激烈競爭中茫然無措。
近幾年來,鷹潭市重點圍繞道教文化、崖墓文化、水滸文化、角山文化、古越文化等文化資源進行發掘,使嗣漢天師府、大上清宮、仿古升棺表演等人文景點的建設不斷完善,成為鷹潭的經典旅游品牌。歷來被尊稱為“道教祖庭”、“百神授職之所”的大上清宮,始建于東漢,為祖天師張道陵修道之所,宮內伏魔殿內的鎮妖井,就是施耐庵筆下梁山108將的出處。莊嚴肅穆的宮觀、參天蔽日的千年古樟讓人如同徜徉在歷史長河,真切感受魯迅先生“中國根柢全在道教”這句話的精髓真諦。龍虎山1900多年的道教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鷹潭旅游文化資源的精品。
2005年,首屆海峽兩岸道教文化論壇在龍虎山舉行,來自海峽兩岸及海內外經濟界、道教界、學術界知名人士200余人參加盛會。同時,美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家及我國香港、臺灣地區派出了道教代表團參加了嗣漢天師府建府900周年慶典,進一步奠定了嗣漢天師府道教祖庭的地位,也在海內外打響了龍虎山、天師府這一文化旅游品牌。
三、旅游文化素養的提高可以促進旅游管理水平的提高。
旅游行業內部包括許多部門和企業,如飯店、旅行社、各旅游景區景點等。高水準的經營管理工作是旅游行業的靈魂和創匯達標的保證。一個賓館,出售給客人的不僅是客房,更重要的是熱情周到的服務和文化氛圍。這就要求賓館的管理首先要講究科學,形成特色,然后才能吸引客源。在賓館管理中,尤其要注意飲食文化與服務文化的建設。在旅行社管理中,導游人員的文化素養直接關系到游客能否達到旅游的目的。一次,幾名日本游客在杭州旅游,午餐時對安排的“東坡肉”這道菜不感興趣,導游小姐針對他們的思想顧慮,饒有興致地講述了北宋著名文學家坡發明這道菜的故事,說明這道菜的特點是肥而不膩,富有營養,勸大家嘗一嘗。客人聽后,躍躍欲試,吃過之后贊不絕口,并表示下次來中國,還要吃“東坡肉”,可見文化的作用是多么大。在景區景點的管理中,文化素養的重要性更不必細說。反之,如果缺乏必要的文化水準和管理水平,旅游業就會陷入困境。許多大酒店設備先進,服務也不錯,但游客卻抱怨說:“我好像不是在中國。”在賓館管理中,如果不注重文化品位、管理水平和服務質量,以為只憑設備先進,就可以“皇帝女兒不愁嫁”,很難獲得好的經濟效益。開發和營建旅游景點,更要講求文化特色。繼深圳“錦繡中華”和“世界之窗”取得成功后,各地紛紛仿造的微縮景觀開業不久就“門前冷落鞍馬稀”,正是不講求文化特色,不注重文化創新釀成的苦果。在旅游文化方面的競爭,將是未來旅游業發展的一大趨勢,因為隨著經濟、科技的發展,人們對旅游景點的需求,趨向于文化性強、科技水平高、更富有參與性。為適應這一要求,對旅游文化的研究和投入要加大力度,旅游管理必須盡快與國際接軌,旅游業從業人員的文化素質也要相應提高。在這一變革中,旅游文化將推動旅游管理現代化的實現。
四、發展旅游文化是弘揚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手段,是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要內容。
讓世界了解中國,讓各國人民熱愛中國,對我國人民尤其是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是我國旅游業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我們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旅游事業,其核心就是要在旅游中加大文化建設的力度,把開發重點放在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其中精神文明建設顯然位于不可忽視的地位。旅游,作為一種民間的、非官方的外交活動,在發展國際關系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人們在旅游過程中感受異邦文化,增進彼此間的了解,縮小彼此間的差異,消除彼此間的隔閡。可以說,旅游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為人類創造一個和平的生存空間。
龍虎山距今2600多年的春秋戰國崖墓群,在人類崖墓文化中堪稱中國之最、世界一絕,并以其分布廣、數量多、位置險、造型奇、文物豐被譽為“天然考古博物館”,是研究古越族史及中國紡織史、樂器史、音樂史等學科的珍貴寶庫。然而關于這些百米懸崖絕壁洞穴中的棺木卻有許多千古之謎。鷹潭市先后在北京、杭州、福州、武漢等城市召開新聞會,懸賞40萬元,征破解之道。無疑這種形式別樣,富含文化內涵的推介活動取得了預想不到的效果,獲得了事半功倍的宣傳效應,在當地媒體和市民中激起不小波瀾。2005年5月,鷹潭市舉辦的龍虎山崖墓文化科考活動更是大手筆,來自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哈佛大學、韓國國立文化研究所等國內外知名學術機構的20余名專家學者,對崖墓懸棺葬地的選擇、棺木的吊運、墓主人的身份及族屬、墓葬形制、葬品文化特征及歷史價值等作出評估。這既是一次規模空前、具有很高學術價值的科考、科普活動,又通過中央電視臺、人民日報、人民網,以及周邊地市新聞媒體濃墨重彩的報道,提升了人氣,擴大了影響,聚集了財氣,促進了發展,從而讓世界更加了解了鷹潭,讓鷹潭走向了世界。
總之,旅游文化在現代旅游業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顯而易見的,鷹潭旅游業要取得大的發展,就必須注重旅游文化的開發和建設,只有這樣,才能在激烈的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參考文獻:
[1]渠銘.旅游文化在旅游業中的地位和作用[J].山西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8.1.
法律適用論文范文第5篇
內容提要:中國在民法和商法關系方面采納了民商合一模式。商法責任是民事責任的特殊形態,但是也有其自身特征:包括歸責原則的二元結構;責任的相對性、替代性;商業判斷規則的適用;損害賠償替代原則在責任形態中具有根本地位等。未來的制度體系建設包括以企業為中心的商事責任制度的構建、嚴格責任和過錯責任原則的相互為用和損害替代規則的體系構建。
法律責任具有一種恢復和保障權利的職能,以民商法為核心的私法領域尤為如此。根據中國學界通常認識,民事責任是民事主體違反民事義務所應承擔的不利法律后果。
民事責任因所違反的義務不同,大致可分為違約責任與侵權責任兩大類型。[1]而就其性質而言,有債務說和獨立責任說兩種觀點。[2]自羅馬法以來,傳統私法學及多數國家或地區的民法典均贊同債務說。并在立法上將侵權責任及違約責任均作為債的類型或內容,后者認為民事責任獨立于債務,中國《民法通則》采取的是責任獨立說。該法在債權之外,設民事責任為獨立一章。
然而,上述關于民事法律責任的討論都是在民商合一模式下加以探討的,因此都具有極大的局限性。筆者認為,在當下的市場經濟建設進程中,民法和商法合一的關系定位應該以科學的態度重新進行審視。但是,無論是堅持民商合一還是民商分立,商法的獨特性已經越來越被學界所認同。因此,作為現代商法體系中重要組成部分的商事責任制度,自然也應當適應這一趨勢,以建立相對獨立、完善而具有體系的制度。本文以此論點為基礎而展開討論,研究中國商事責任法律制度的特征,構建相應的制度體系。
一、商事責任制度建構對民商合一模式下民事責任制度的挑戰
(一)民事責任概念、性質及其源流考辨
法律責任是一般社會責任的特殊表現之一。與法的本質特點相適應,這種現象直接表現法的國家權力性質。依據學界的現有研究成果來看,古代羅馬并無獨立的責任觀念,責任歸屬于債,與債務沒有嚴格的區分;區分債務與責任,主要是日爾曼法學的貢獻。[3]
在羅馬法上,債系指“法鎖”。“法鎖”之義,在早期的羅馬法里,不僅意味著債務人應履行給付的義務,債權人有權接受此給付而獲得一定的利益;而且意味著當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債權人可以羈押債務人,加以奴役、買賣甚至奪其生命。因此,盡管羅馬法上沒有嚴格區分債務和責任,但“法鎖”已經體隱隱現出債務和責任的最早區別。值得注意的是,根據資料考證,羅馬法上的債的真正起源是“私犯”。“羅馬債的歷史起源產生于對私犯(exdelicto)的罰金責任”,私犯“是產生債的真正和唯一的淵源”。[4]由此可見,羅馬法上,作為義務違反的法律后果,無論是違反一般性法律義務的法律后果,還是違反合同義務的法律后果,責任這一法律現象也是存在的。只是羅馬法沒有將這種后果與債務嚴格區分開來,而是將其溶入債的范疇,作為債的內容而規定在債的概念中:羅馬法上的債乃指“法鎖”,是指當事人間的羈束(Gebundenheit)狀態,實與責任(Haftung)意義相當。[5]
責任與債在日耳曼法時期被嚴格加以區分。在日爾曼法中,債務是指“法的當為(rechtlichesSollen)”,其不含有“法的必為(rechthchesMüssen)”的意義。在債的關系里,“當為”不僅是對債務人而言,也可以是對債權人而言。所以,債務者,謂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之“當為”狀態。因而,在日爾曼人那里,債務和債權,債務人和債權人,都可以用相同的詞來表達。然而,責任的意義則是“法的必為(rechthchesMtissen)”,指債務不履行時,債權人可以對債務人的人身或財產實行“強制取得(Zugriff)”,以代替債務人的給付。[6]因此責任具有強制性:責任(Haftung)者,為服從攻擊權之意。故在日耳曼中世法往往謂責任為保證或擔保。[7]
從上述對古代羅馬時期和日耳曼時期的責任制度的演進進程來看,我們可以看出古代法中的民事責任的基本屬性,即相對性、強制性和擔保性,盡管其中仍然存在紛爭。歷史總是繼承和發展的統一,古代法時期的民事責任和體系在近現代以來都得到了繼受,其中也必然有所完善。
德國普通法時期繼受了羅馬法關于民事責任制度的遺產,也未嚴格區分債務與責任,一般認為責任為債權及于債務人財產上之效果。但是到了《德國民法典》制定之時,資本主義立法思想已經從單純的個人本位趨向于社會本位,日耳曼法的團體本位也就更多的重新進入到立法者的視野中。Gierke將日耳曼法上的責任分為人上責任、物上責任和財產責任三種。
《德國民法典》的這種繼受和發展不僅承載著對后世民法典關于債務和責任區分的榜樣作用,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從人的責任到財產責任的轉變,不僅表達了社會的進步,同時也表明了對人的自由價值的承認,并將人的價值確定為法律的基本價值內涵,這是法律發展史上的最輝煌的飛躍之一。同時,古代法時期的責任具有債的擔保的意義,從而責任也就構成了現代民法擔保制度的淵源;但是就責任的本質屬性來說,因為其具有強制性特征,和私法的價值屬性有所不同,因此,現代民商法上的責任制度開始逐步剝離了責任的強制性特征,而向財產替代責任形態轉變。
(二)商事責任對傳統民事責任制度的挑戰
盡管目前我國理論界關于民法和商法關系的問題仍然見仁見智,但不可否認,無論民商分立論者還是民商合一論者,對商法自身的特征都予以肯定,認為無論是分立還是合一,均不應影響商法規范的存在和發展。但是,事實上,現代商法的實踐已經凸顯出傳統民事責任制度在商法領域的局限性,而一些商事責任現實實踐也對現行的理論和制度提出了挑戰。
第一,社會本位主義和社會責任制度的發展對建立在個人主義之上的“私權利益至上”和以過錯為基礎的個人責任原則的挑戰。私法是權利法,即從法理上講,民法規范的邏輯起點是個人主義,這種個人主義以個人理性和個人權利為基本核心。與此相反,商法規范的邏輯起點則是整體主義。一般來說,商事主體多系由多數人和資本組成的營利性人合團體,以其作為主體而產生的具有交易性質的商事關系往往聯結著眾多的內部和外部當事人,商法作為調整這種團體性組織的社會關系的法律無疑具有團體法的性質和特點。因此,與調整個人之間的法律關系的民法不同,商法受團體法原理的支配。所以,對于以商主體為當事人的商事關系發生紛爭時,其救濟機制的制度供給也必須考慮團體法上的問題。
個人主義只是一種人為的假設,是時代的產物,同時也是政治的需要。但是,我們必須注意的是:個人主義作為一種人為的、并被廣泛接受的一般性假設,卻不是天然的不證自明的公理。同時,理性經濟人也假定認為“人是其自利的理性最大化者”,這也僅僅只能局限于單個微觀經濟主體,主要是存在于個體經濟行為之中的,并不適用團體經濟行為以及團體經濟中的個體行為,如果賦予由某些單個人組成的團體以獨立的人格,那么就需要也會實際上產生一個團體理性,而我們知道這個團體理性始于、源于這個團體中的個體理性,但團體理性和個體理性是存在很大差異,不可能完全一致的。功利主義雖然在理論上提出了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一致性問題,有其合理因素,但是公共利益是由個人利益中帶有共同性的部分抽象、提升出來的整體利益,抽象提升后形成的公共利益具有相對獨立性,是不能等同于個人利益的,這就產生了個人理性與團體理性的深刻矛盾。
而且,以法的社會化為特征的法律變革在當下環境可謂方興未艾,其典型特征表現為社會責任運動的興起,這一運動的參與主體主要是企業。傳統上,人們一直將企業的贏利與企業的社會責任對立起來,似乎企業的贏利與企業的社會責任之間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但是這些認識在現代社會都遭受了挑戰。所有這些問題,在傳統的民事責任制度體系下的都無法得到有效的解決。
第二,商事責任過錯層級規則的發展。過錯的層級規則早在古羅馬法即已有之,并為兩大法系所繼承。但是,過錯程度分類在英美普通法中具有重大意義,因為普通法中侵權行為以類型化為其典型特征,每一不同程度的過錯本身即可能有其相應的賠償責任。盡管如此,也仍然有觀點對之持否定態度。[8]而在大陸法上,因為侵權行為法立法目的在于對受害人的補償,加之立法一般化特征,對之區分意義相對較小。[9]
實質上,過錯層級的細化是對商事主體的注意義務的要求,并可能因為注意義務的違反而需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注意義務乃指行為人在特定情形下所必須遵循的行為準則以及依該準則而采取的合理防范措施。從英美國家過錯層級規則劃分的實際效果來看,它確實迎合了商業社會對商事主體追究責任的特殊需要:商法是為那些精于識別自己的利益并且毫無顧忌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極端自私和聰明的人而設計的,商人被推定為在商務方面是有能力、有經驗的。因此,對于商人,那些對權利保護性質的規則的關注已顯得無足輕重。關于能力、意思表示瑕疵、對“意思表示自由”的保護,等等,也都退到了次要位置。例如,商人不能因締約時的疏忽或其他原因而提出免責的規則、[10]流質契約條款的許可、[11]對要約的承諾與否的通知義務、[12]連帶保證的推定、[13]法定的保管責任[14]等。商法之所以強加于商人予較高的謹慎注意義務,其目的在于敦促商主體更加認真負責地履行自己的行為,加強對商業風險的評估與防范,從而營造一個有效率的市場。
第三,國際社會民法和商法的深度區分要求適用不同的法律責任規則,而這些在民商合一模式下幾乎無能為力。國外的民商法律立法實踐表明,隨著所考慮的行為屬于民事性質還是商事性質之不同,或者視行為人是商人還是普通個人之不同,對許多完全相同的“事實狀態”,卻存在兩種不同的處理規則。例如,關于告知義務的界定,在商事買賣(雙方均為商主體),告知的義務必須不被不合理地擴大。從通常商業的角度來看,買方和賣方存在沖突,不能相互期待提供與價格有關的市場信息,尤其是不能提供價格是否可能上漲或下跌的信息。對這些問題人們只能向無利害關系的第三人咨詢,否則,就會犧牲他的信息優勢,從而減弱了法律的這種刺激作用。[15]與之相反,在單方商行為(一方為商人,另一方為消費者)中,商主體除了負有“不得欺騙顧客”這一傳統的“否定性義務”之外,又增加了一項“向顧客提供信息”的積極義務。如果因為經營主體沒有向消費者說明情況而使消費者受到了損害,消費者可以獲準撤銷合同,或者獲得損害賠償。因為中國深受“民商合一”立法模式的影響,并已經影響到立法,所以現行民商立法在商事交易與民事交易之間未作出任何自覺的區分,導致本應適用不同規則的不同交易方式,卻人為地設定了相同的規則,如《合同法》中的嚴格責任及違約金的變更、《擔保法》中的流押條款之禁止及嚴格的留置權設定條件等。
二、現代商事責任制度的特征
(一)從過錯責任向嚴格責任原則轉變
在商事責任的歸責原則中,對過錯的考察已經無足輕重,而嚴格責任原則卻成為現代商業社會的責任體系構建的重要議題。就過錯責任而言,有所謂客觀過錯和主觀過錯之別。主觀過錯和客觀過錯理論在形式上的分歧焦點為:在對行為進行價值評價的時候,需要考察的是行為人主觀的心理狀態還是客觀的行為狀態。主觀過錯責任具有“懲罰”的價值取向。然而,法律只能滿足于調節和規范人們的行為而絕非控制人的思想世界,況且它也無法直接去探究人的精神領域,因為依賴某種心理分析法對人內在意志的探究以及對思想倫理道德應受非難性的考察根本不可能實現。因此,在法律責任的評價機制中,只能通過行為的“中介”評價,最終達到對意志的評價。即使在主觀過錯盛極一時的年代,判斷行為人在行為時的主觀態度全然是比照一個比“理性人”或“善良家父”更具體的、與行為人具有相同條件的“人像”。在評價過程中,行為人的個人情況包括年齡、性別、缺陷、技能和資格,以及其當時所處的環境、時間、行為的類型等因素都應當加以考察,并依據具體行為人的因素審查行為人是否對損害具有預見的可能性進而判斷過錯的有無。這種過于偏重人的意志自由、違背人類有限理性之現實而建立起來的過錯責任法律制度,從其產生開始就要以犧牲廣大受害人的利益作為代價,根本無法實現侵權法補償損害、預防事故的社會功能。
尤其是到19世紀末期之后,人類社會進人到一個高風險的時代,各種新型的科學技術投入到生產和生活中,尤其現代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給整個人類生活帶來了巨大的影響。過錯責任雖然在調整人與人的行為沖突上具有重大的作用,但是在這些商事責任領域,如果繼續使用過錯責任將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在上述情況下,如果受害人必須證明加害人具有過錯,則在實踐中,作為弱者的受害人幾乎不可能獲得賠償。因此,危險責任或者嚴格責任逐步發展成為與過錯責任具有同樣重要地位甚至更為重要的歸責原則。
所以,工業革命不僅僅是一場經濟和社會革命,同樣是一場法律革命,對商事責任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工業社會使得人類社會變成了“風險社會”或者“事故社會”,隨著企業的各種危險活動成為社會共同生活中最主要的潛在加害來源,導致傳統一元的“過錯責任”呈現出了巨大的局限性。從過錯責任原則過渡到以“過錯責任和嚴格責任”為中心的二元歸責體系,是未來商事責任法律制度體系構建面臨的艱巨任務。
(二)從強制性責任向替代性、相對任意性責任的轉變
如上所述,在法律責任的演變過程中,呈現出從強制性責任向替代性、相對性責任的轉變,這一趨勢在商事責任中表現的更為明顯。
實質上,無論是在民事責任領域還是在商事責任領域,責任的強制性并沒有完全消失,其中的財產強制移轉至強制執行法,較少部分留在私法,構成私法中的自力救濟制度。德國卡爾?拉倫茨在分析債務與責任時還明確指出,責任的強制性最終依賴強制執行(zwangvollstrekung)。[16]而在現代法里,不管是侵權行為引起的損害賠償責任,還是違約行為引起的繼續履行、支付違約金或賠償損失責任,債權人如不能通過和解獲得救濟,那么就只有向法院提訟,請求法院以國家強制力強制債務人承擔責任,債權人并不能直接對債務人采取強制措施。法院強制債務人承擔民事責任,屬于強制執行法的對象,須嚴格依據強制執行法的規定。這幾乎是對古代責任強制性特征的脫胎換骨的變革:人身責任逐漸消亡,取而代之的是單純的財產責任;責任的強制性逐漸從私法中退出,而進入公法領域;古代法上責任的諸多類型,逐漸發展出獨立的債的擔保制度,責任所固有的擔保意義淡化。古老的責任制度被繼承下來的只有其相對性和替代性以及取代人身責任的財產性,即現代法上民事責任意味著違反義務人依法應承擔的第二次義務,只能是財產責任。相對性、替代性和財產性,使得現代民法的責任與債務沒有本質差異。
而在商事責任中,基于商法的效率理念和商人的盈利需求這一前提,在實踐中商事責任的替代性、財產性和相對性更是備受張揚。正如學者所指出,商人的精明不僅反映在其精于預測物價行情的波動,利用貨物供需之間的價差獲取利潤,而且,還反映在其對待沖突的態度上,商人通常愿意以談判的方式解決問題,他們幾乎認為,一切都是可以談判的,談判是最好的糾紛解決方式。相較于普通民事主體而言,商人對仲裁的熱衷即為例證。因此,如果將圓桌搬入法庭,采取商事談判慣用的圓桌形式,改造目前對抗式的法庭設計,恐怕更有利于商事糾紛的解決。對此,甚至使人無比留戀馬錫五式的“田間審判”。[17]所以,筆者認為,商事責任的這種相對性、替代性和財產性的特征,在未來商事責任法律體系的構建中必將大放異彩。因為我們面對一個多元風險的商業社會,理性往往受到“多元性無知”的阻礙——誰也無法保證自己的判斷絕對正確,具有柔性化的財產替代性和相對任意性商事責任范式在商業社會的擴張無疑會縮小我們犯錯的成本,最終促成一個寬容的法治社會。
(三)商業判斷在商事責任中的運用
商業社會交易目的是為實現商業利益及利潤,但是這必須在法律規范的框架下進行。否則,商業主體就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商事責任的確定規則中,商業判斷規則是判斷主體是否承擔商事責任的重要的判斷標準,這與傳統民事責任的具體規則具有重大區別。商業判斷規則本質上要求法律對商業主體交易行為進行形式上的審查,保持形式公平,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這就要求在商事責任的判斷中,一般將維護合同的有效性,鼓勵并促成交易的達成作為商人的交易模式,同時也作為司法掌控的價值取向。
然而,大陸法國家法官在處理合同糾紛時,通常遵循如下分析邏輯:首先確定合同的性質和類型,隨后探討合同效力,再分析是否存在違約,最后審查有無不承擔責任的事由。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為按照成文合同法體系,合同性質或者種類不同,合同的成立或者生效條件未盡一致。如為實踐合同,當事人未交付標的物,為合同不成立。若為諾成合同,當事人未交付標的物,則為債務的不履行。若有導致合同無效或者不成立的事實,即無須分析應否承擔違約責任。因此,分析合同或者法律關系的性質和類型,遂成為大陸法系法官分析合同案件的邏輯起點。就此而言,我國法院也大體遵從了這一邏輯。如果在審理商事合同案件時采用上述分析方法,法官會遇到障礙甚至窘境:在商業活動中,為了規避類型化合同風險,商人有意識地模糊各種合同性質,或者基于營業目的而淡化合同性質的法律意義。前者如商場促銷商品時的附贈銷售行為,這種做法看似無償,實則有利可圖。后者如某財務軟件公司以簽訂“買賣合同”的形式向用戶“銷售”軟件。就性質而言,軟件銷售實為“軟件著作權之實施許可”,而在國內軟件行業,類似使用許可向來被稱為軟件銷售。與法律專家不同,商人從來不會刻意關注合同的性質或者類型,而更關心交易是否有利可圖。所以,基于商事關系的特性,法官審理商事合同糾紛時,就有可能形成特有的分析路徑,即有時要“忽視”合同的法律性質,轉而斟酌并尊重“利之所屬、損之所歸”的商業判斷原則。[18]
(四)損害賠償替代原則的確立
必須明確的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商業主體從來只會關注商業利潤,關心交易本身是否有利可圖,而很少去刻意求證合同的性質及其效力。同時,盡管在合同的簽訂、履行過程中需要注意合同的公平,但是也不會讓過多的基于道德的價值判斷超越經濟價值判斷而占了上風。所以,基于商事交易關系主體的這一特性,在制定交易合同的效力規則和責任承擔規則方面,我們要更多地考慮基于效率要求的經濟賠償規則的替代性機能。而這些在國內卻還沒有引起應有的注意。相反,多數學者仍然恪守傳統民事法律責任的的公平理念和規則,沒有考慮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效率價值的優先地位和平衡設計,沒有考慮商業領域的市場主體對物的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的差異對待,局限性十分明顯:(1)在合同效力的認定方面,著重考慮合同的公平價值,追求所謂實質的公平,對非法交易的效力多認定為無效。結果導致現實實踐中的大量的無效合同的出現。(2)在損害責任的承擔方式上,從而不論地認為《民法通則》第134條所規定的十種民事責任方式的開創性,[19]并將這些責任方式當然地適用于現代商事責任領域。(3)在商事責任的價值取向方面,過于注重考慮道德因素,而忽視了商業責任的經濟屬性。
三、中國商事責任制度體系構建
(一)以企業為中心的商事責任主體制度
傳統私法責任制度在構建其體系時,從歸責原則到具體行為類型,都是從單個的“自然人”為基礎,去調整當事人之間權益糾紛。現代商業社會的“自然人”對商事責任體系的構建仍然具有根本意義,但是其“人像”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原型已經發生從啟蒙運動中的“理性人”到風險社會中的“角色人”或者“謹慎人”的轉換。[20]不僅如此,商事責任主體還發生了從自然人到企業的重大變革: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各種風險引致者發生了從自然人到企業的主體轉移,在社會分工中,眾多自然人成為特定企業的各種雇員;企業的組織經營活動成為社會共同生活中危險的主要來源。各種類型的企業在追逐自己的利潤時,一方面給全社會提供了人類共同生活所需要的現代工業產品和服務,但與此同時,工業革命給人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風險。
所以,以雇主責任、企業組織責任和危險責任為中心的企業責任成為現代商事法律責任制度的核心要素,而制度的設計也要以此為中心而展開。
(二)以嚴格責任為中心商事責任歸責原則
現代企業作為一個等級森嚴、分工細密的現代商業組織,若使其成為真正的現代商事責任主體,還需要考量傳統民事責任的過錯歸責基礎的該當性,轉而開始注意嚴格責任原則在現代商事責任領域的重要地位。這已經引起很多學著的注意。
事實上,嚴格責任自古羅馬時期就已經存在,比過錯責任原則歷史更為久遠,而且在權利救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無論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嚴格責任并非工業社會的產物——盡管嚴格責任的抽象在近代以前的法律中遠未形成——在人類初期的法律中,嚴格責任占有非常重要甚至是絕對的地位。從嚴格責任的歷史發展來看,只要人類所面臨的風險存在不對稱性或是嚴重到足以構成對生命的威脅,當安全需要超過了其它的人性需求,嚴格責任體系就有其發展的舞臺。
從比較法視角來考察,以雇主責任、企業組織責任和危險責任為中心的企業責任,在歸責原則方面都采納了嚴格責任原則。可以肯定的是,商事責任的歸責原則已經不能建立在以自然人為基礎的過錯責任原則之上,19世紀之后飛速發展的現代企業的復雜組織形態,顯然超出了當時立法者所可以預想的程度。一個建立在單個自然人基礎上的過錯責任不能勝任現代高風險的工業社會責任承擔。19世紀之后西方工業社會的出現,使得侵權法學者敏銳地感受到侵權法新的歷史使命的到來,他們針對過錯責任的社會基礎提出質疑,因為風險社會以及非個人化的大企業的現象導致過錯責任的衰落,而一度式微的嚴格責任原則再次擔負起社會重任。
(三)建立損害賠償替代規則
傳統的承擔民事責任的方式有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返還財產、恢復原狀、修理更換重做、賠償損失、支付違約金等十種方式。其中前五種屬于物上請求權權能,是物權的特有民法保護方法。在商事活動領域中,雖然上述責任承擔方式仍具有一定的意義,但卻忽視了商事活動有別于一般民事活動的特有屬性,無法對商事活動受害方提供有力的救濟。首先,商事活動講求效率優先。遲到的正義是非正義,交易時間是商事主體從事商事活動時的重要考量因素。反觀傳統的民事責任承擔方式,其都是從傳統民法的公平原則角度構建,如返還財產、恢復原狀、修理更換重做等方式,這些或是要求當事方將行為恢復到發生前的初始狀態,或是需要當事方重新協商以實現對受到破壞的商事關系的補救。在商事領域選擇這些救濟方式往往耗時耗力,而對那些可能已經對彼此失去信任,無心繼續交易的當事方來說也無必要,甚至造成其負累。其次,在商業領域,對物的交換價值及其相應利益的保護的注重遠遠超過對使用價值利益的保護。商事主體總是更注重實際利益的獲得,傳統民法責任承擔方式更傾向于對物使用價值利益的保護,使得受損一方商事主體的利益難以滿足。而從整體上來看,將損害賠償作為主要的商事責任承擔方式,優先于傳統民事責任承擔方式,符合商事活動的特征,也能最大限度地彌補受損當事方的利益。另外,必須注意的是,對損害賠償制度的具體設計,必須要關注對預期商業利益的保護,這就要求在確定預期商業利益的損害賠償的構成要件設計上,不能太苛刻。
注釋:
[1][德]迪特爾•梅迪庫斯:《債法總論》,杜景林、盧諶譯,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頁。
[2]黃茂榮:《債法總論》(第1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64頁。
[3]林誠二:《民法理論與問題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06-207頁。
[4][意]彼德羅•彭梵得:《羅馬法教科書》,黃風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84頁,第401頁。
[5]AlorisvonBrinz.lehrbuchderpandekten(band2),verlagvonandremsdciwert,1879,1.
[6]ottovonGierke.DeutsechesPrivatrecht(Band3:Schuldrechit),Verlagvonduncker&humblot,1917.9-13.
[7]李宜琛:《日耳曼法概說》,夏新華等勘校,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105頁。
[8]JeanLimpens,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ComparativeLaw,Vol.4,Torts,Chapter2,LiabilityforOne’sOwnAct,J.C.B.Mohr(PaulSiebeck,Tuebingen),1975,at132.
[9]劉道遠:《證券侵權法律制度研究》,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版,第159-160頁。
[10]《德國商法典》第348條。
[11]《韓國商法典》第59條,《日本商法典》第515條。
[12]《德國商法典》第362條;《韓國商法典》第53條;《日本商法典》第509條。
[13]《韓國商法典》第57條;《日本商法典》第511條。
[14]《韓國商法典》第60條、第62條、第70條;《日本商法典》第510條、第527條。
[15][德]海因•克茨:《歐洲合同法》,周忠海、李居遷、宮立云譯,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89頁。
[16]Karllarenz.LehrbuchdesSchuldrechts(Bandl:AllgemeinerTeil),C.H.BeckVerlag,1982.21。
[17]蔣大興:《審判何須對抗》,載《中國法學》2007年第4期,第129頁。
[18]葉林:《商法理念與商事審判》,載《法律適用》2007年第9期,第17-20頁。